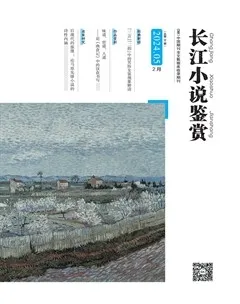论陈彦小说《喜剧》的喜剧之美
李楠楠 亓雪莹
[摘 要] 陈彦深受戏剧的影响,其作品故事往往围绕着戏曲舞台而展开。陈彦“舞台三部曲”的收官之作《喜剧》,延续着以戏剧为主的生命故事,描绘出贺加贝跌宕起伏的情感历程以及悲喜交加的一生,并借助其人生经历,将故事聚焦并延展于戏曲表演的方方面面,呈现出不同形态的喜剧效果,给予读者丰富的喜剧美感。在陈彦笔下,喜剧演员有着丑陋的外表,滑稽的行为和可笑的话语;而贯穿人物的故事情节则扣人心弦、跌宕起伏;讲述故事的语言既通俗易懂,又诙谐幽默。《喜剧》通过塑造喜剧人物、设置喜剧冲突和运用喜剧语言达到了融会贯通的美学效果,并将讽刺手法贯穿其中,实现了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的高度统一。
[关键词] 陈彦 《喜剧》 讽刺 喜剧美
[中图分类号] I2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2881(2024)05-0044-04
美隐藏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只是大多数人缺少了一双发现美的眼睛。作家、艺术家往往比常人更加敏锐,善于发现生活中的美,并将它融于作品当中。陈彦浸润在戏剧界长达三十几年,其感受到的喜剧元素与独特的美学思想在小说《喜剧》中有所展现。陈彦的长篇小说《喜剧》以传统文化的冲击为背景,描述了喜剧人物贺加贝在时代的经济浪潮中起起伏伏的人生过程,从中流露出了作者的思考,极具喜剧色彩,富含美学意蕴。
《喜剧》是陈彦“舞台三部曲”的收官之作,学界目前对于《喜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陈彦的现实主义手法和戏剧化创作方面;二是对《喜剧》中的泛娱乐化和喜剧艺术价值跌落的批判;三是侧重于阐述《喜剧》表现出来的悲剧精神和悲与喜在作品不同层面的交织。本文结合艺术审美和思想价值两方面,从人物、情节、语言和艺术手法四个角度来探讨小说《喜剧》里蕴含的喜剧美,挖掘其美学思想。
一、以丑为美的喜剧人物
塑造人物形象、展现人物性格,是小说表现主题、形成风格的主要方式和途径。陈彦《喜剧》的喜剧美表现在喜剧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喜剧人物性格的刻画上。作者以喜剧表演作为整个故事情节演变的背景,同时又围绕喜剧表演塑造出许多生动且富有真实感的人物,通过对小說人物外貌的描写以及人物之间各个方面鲜明的对比,呈现人物的喜剧美。
朱光潜在《诗论》中指出,笑的对象是丑拙、鄙陋和乖讹,延伸为喜剧的对象则主要表现为容貌的丑拙、品格的欠缺和人事的乖讹[1]。喜剧以“丑”为基础,人物形象的滑稽可笑往往可以直观地展现喜剧特点。小说中火烧天的长相极其具有喜剧色彩。“火烧天头上寸草不生,长得奇怪诡谲”“额颅前倾如瓠瓢”“后脑勺凸出似倭瓜”“嘴大、耳大、鼻子大,眼睛却小如绿豆”[2],这样“容貌的丑陋”本身就给观众喜感,再加上其作为喜剧演员的专业性表演,喜剧性得以显现。与此同时,他的两个儿子贺加贝和贺火炬和他长得几乎一模一样,周围人不免调侃道:“父子三人长得跟克隆人似的,把人间之丑算是一网打尽了。”[2]作品中的喜剧色彩通过简单的外貌描写就得以窥见一二。除了作为丑角的父子三人,作者还塑造了许多具有喜剧性的人物形象,可以简单归纳为“品格的缺陷”。武大富是一名度假村老板,他对于喜剧的专业性知识比不上贺加贝等人,作为商人,他最看重的是利益,而不是剧本质量的好坏,因此他轻视真正优秀的剧本,而将毫无内涵的媚俗之作视为赚钱的利器,结果导致剧本的创作走向低俗。除此之外,还有镇上柏树、王廉举和史托芬等,他们不是专业的喜剧演员,但都与这个行业相关,他们逐渐影响、控制、改变着喜剧的走向,他们自私虚伪、唯利是图,小说对他们行为的叙述是对丑恶现象的无情嘲讽,饱含讽刺意味,让读者发笑的同时看到人性的罪恶[3],在思想上得到净化和升华,从而达到了“以丑为美”的美学效果。
喜剧美通过喜剧性格来展现,可以得到更强烈的审美情趣。喜剧性格是营造喜剧氛围的基本点,也是喜剧艺术家的追求所在。这类人物性格表面上固执、可笑,甚至丑陋,但实际上却是美的化身[4]。潘五福是潘银莲的哥哥,虽然他与潘银莲是亲兄妹,但是在妹妹花容月貌的对比下,潘五福矮小的身材就显得丑陋。他刚开始在河口镇经营着芝麻饼的小摊,后来找到了一门钉鞋的手艺,以给人修鞋、钉鞋赚取微薄的收入度日。然而这样一位勤劳善良的人,却总是得不到命运的眷顾。潘五福出身贫寒,父亲在挖煤时发生意外去世,母亲因此备受打击而精神失常,经常辱骂儿媳好麦穗。但是他并没有埋怨过谁,一直踏踏实实地赚钱养家,供儿子上大学。由于妻子好麦穗生活不检点,河口镇的街坊邻居都暗自嘲笑他,并说潘上风不是他的亲生孩子,但他并不理会这些闲言碎语,依旧维护这个家庭,甚至在妻子跟人跑了染病死亡后,也坚持把妻子的骨灰带回家。潘五福是一个坚忍的伟丈夫形象,是“美”的化身。
小说《喜剧》中,贺火炬是贺加贝的弟弟,两人都继承了父亲火烧天丑陋的容貌,成为丑角。弟弟贺火炬在贺加贝事业红火时想要一辆摩托车,但贺加贝因为要扩大喜剧场地而忽略了弟弟的要求,于是兄弟之间生出了嫌隙,后来贺火炬在追逐爱情的过程中又上当受骗。经历了爱情和亲情双重打击的他,可谓是一个真真切切的“小丑”。贺火炬及时醒悟,在贺加贝表演偏向低俗时就毅然决然地抽身离开,走向追求真正喜剧的道路。尽管后来贺火炬在艺术学院里接触到的喜剧艺术与自己所理解的并不相同,甚至感觉有点失望,但随后遇到的顾教授却让他认识到真正的喜剧艺术是怎样的,并走上了正统艺术的道路。作者将贺加贝与贺火炬作鲜明的对比,从而突出了贺火炬的迷途知返与清醒。由此可见,喜剧性格不仅通过荒诞的举动让人发笑,也要让人意识到问题的所在,发人深思。
二、误会加巧合的喜剧情节
喜剧效果的产生依赖于喜剧情景的设置,所谓喜剧情景,就是将人物置身于能使人发笑的特定的场景中。在小说中,往往表现为情节的巧妙安排。陈彦《喜剧》的喜剧美表现在追求小说情节的跌宕起伏上。作者将贺加贝的喜剧表演和创办剧院的过程用不同的人物分成了几个阶段,在这几个阶段情节之间的起承转合中,作者运用巧合、误会、突转等艺术手法推动情节的延续[5],使故事在出乎意料的同时又充满喜剧性。将喜剧人物形象放置在喜剧化的情节中,往往能让读者得到满足,也使喜剧人物性格更加饱满。
在整部作品的一开始,作者就采用了误会加巧合的方式来展开整个故事,同时表现贺加贝这一人物的滑稽可笑。贺加贝在剧团作为其貌不扬的丑角,偏偏对美丽动人的万大莲死心塌地,两人巨大的差距,不仅没有阻挡贺加贝对万大莲的爱慕之心,反而愈演愈烈,闹出了一系列啼笑皆非的场景。贺加贝因看见廖俊卿溜进万大莲的房间,所以就蹲守在万大莲的窗外,想要知道屋内发生了什么事。胡思乱想的他没有看到万大莲的身影,就误认为他们二人此时此刻都在房间内,内心愈发着急上火,并在屋外蹲守了一夜。直到第二天万大莲从背后发现了他,才恍然大悟昨夜只有廖俊卿一人在万大莲的房间里。最后贺加贝因为在草地蹲守了一夜还生了一场病,引来人们的嘲笑,闹得人尽皆知。作者笔下所有喜剧表演都是从这一场滑稽可笑的“加贝蹲坑守夜”的故事开始,喜剧人物置身于这样一个尴尬的场景中,并与相关人物形成了荒唐可笑的关系,具有强烈的喜剧效果。
贺加贝的喜剧事业是在父亲火烧天、弟弟贺火炬、武大富、镇上柏树、王廉举、史托芬等人的围绕下展开的,其中也经历了各种巧合和突转。在父亲火烧天的带领下,他们父子三人的事业如日中天,但就在此时火烧天被查出来患有癌症,很快便去世了。父亲火烧天去世后,在镇上柏树的“帮助”下,贺加贝的喜剧事业又变得红火起来,但他也是在此刻选择离开。后来王廉举的加入与贺加贝的决裂、史托芬的创作与武大富的陷害,这种种情节无不是在突转中延续着的,仿佛每一次贺加贝的事业遭受打击时就会有新的人物加入来改变当前局势,但这些人物的加入在看似让演出变得红火的背后也逐渐背离“丑角之道”,最终导致贺加贝的喜剧事业走向衰亡。事业如此跌宕起伏,他的爱情也坎坷不平。贺加贝从一开始就着了魔似地迷恋万大莲,不管周围人如何阻挠,他都对万大莲死心塌地,甚至他对事业的追求,也是为了得到万大莲。作者运用了巧合的手法,潘银莲这个善良的女孩与万大莲的外貌极其相似,但人物性格与行为举止却完全不同。在这种情形下,贺加贝自然而然地迷恋上了潘银莲的外貌,并对她疯狂求娶,成功走在了一起。但后来得知万大莲与廖俊卿离婚之后,他内心的火焰又重新熊熊燃烧,也逐渐对潘银莲感到不耐烦。可纵观其感情的起伏脉络,他总是与万大莲错过,求而不得,即将成功在一起时,又发生各种意外,导致其幻想破灭,最后万大莲与廖俊卿复婚,贺加贝却落得家庭破碎,实在是唏嘘一场。这一幕幕跌宕起伏的情节,将喜剧冲突全面地展开,达到了揭示喜剧美的效果。
三、诙谐幽默的喜剧语言
喜剧语言在喜剧美的创造中起着表现性格、制造欢乐、发人深省的重要作用。它可以表现为警句、俏皮话或是嘲讽性的话语,即使是陈述性的语言也会在特定的场景中表现出与常理相悖的幽默来。陈彦《喜剧》的喜剧美与小说中诙谐幽默的语言密切相关。作者在语言方面彰显了优秀的文学功底,小说语言既幽默诙谐又不失文学性,充满喜剧性。作为一部以喜剧为背景环境、以喜剧中的丑角为主人公的小说,这本身就向人们“暗示”了其内容免不了插科打诨的话语,这也正符合小说人物的设定,与此同时作者也在人物交流中穿插着大量的对话与独白,造成一种幽默的喜剧效果。
文学艺术需要幽默、诙谐和喜剧,这种富有感染力的语言,可以引发深入的思考。《窦娥冤》虽为悲剧,里面也出现了一群丑角,这正是作者以喜剧风格将悲剧引人入胜的一种手法。作者将小说中的柯基犬命名为“张驴儿”,张驴儿原本是《窦娥冤》中的反面人物,之所以给狗用这个名字,是因为作者希望统一起一种喜剧叙事风格的书写方式。作者在小说中给了这条狗思想,借助狗的内心独白来表达作者自己想说的话,这不仅是一种喜剧方式,也是对贺加贝等人所作所为的一种及时反馈。“你们都看见了,这就是人类,把啥脏水都朝我们狗身上泼”[2],作者借助狗的视角、狗的语言让读者看到贺加贝与王廉举之间发生的冲突,也让读者可以以有趣的视角看到真正的张驴儿,给小说增添趣味。小说中以狗的视角去叙述内容的篇幅并不小,每当贺加贝的喜剧表演更加低俗化,或者它的主人潘银莲受到不公平对待时,狗的内心独白就会展现。张驴儿说的话往往具有启发性和嘲讽意味,会在读者发笑的时候给人当头一棒,使小说的幽默具有了一种特殊性。
在火烧天患癌症之后,他的疾病并没有打击他的心态,反而让他更加迫切积极地去表演喜剧,从他的言语里可以看到其中表现出来的幽默诙谐。比如“地球本是一堆土,你来我往都得走。倘若个个耍死狗,人满为患往哪蹴”[2]。作品围绕着喜剧而展开的大量对话也体现着语言的喜剧化倾向,小说后面的喜剧表演并不是真正优秀传统的剧目,但王廉舉口中插科打诨的话,往往也能令人发笑。比如王廉举之前在泡馍馆里时不时说出来的顺口溜和后来因为低俗喜剧表演走红后的一系列行为举止,就显示出了“丑角”的喜剧色彩。另外,纵观贺加贝的一生,作者也是以幽默诙谐并辅之以略显夸张的语言来讲述的,从蹲坑事件,到他事业的红火与衰落,再到对万大莲的执着追求,这些场景在作者的笔下充满喜感,饱含意趣。
四、寓教于乐的讽刺艺术
在鲁迅看来,讽刺美就是喜剧美。喜剧是有边界的,并不是所有使人发笑的艺术创作都可以简单称之为喜剧。喜剧的独特内涵是能在人发笑的同时也给人警醒,这是讽刺艺术能够达到的喜剧效果,也是喜剧美的展现。陈彦的《喜剧》聚焦于传统戏曲中的“丑角”行当,“小丑”通常只是舞台上的配角,然而正是这些不起眼的小角色承载着故事的起承转合和人物情绪的变化发展,从而成为舞台上活跃的角色[6]。纵观古今的戏剧舞台,喜剧演员们用诙谐幽默的方式来娱乐大众,喜剧表现给人们的不仅仅是有趣的动作和语言,还有其想传达的意图。
喜剧美体现在小说中传达出来的讽刺和批判上。火烧天去世前要求在他死后不要给他化妆,也不要给他做遗体告别,但最后一切都没有按照火烧天的想法来。团长的告别词是火烧天用来讽刺人的话,却在死后用在了自己身上,颇具讽刺意味。火烧天在病重时也不忘叮嘱贺加贝作为一名喜剧演员应当具备三点:“得有点硬功夫,得有底线,凡是戏里面做的坏事,生活中绝对要学会规避。”[2]可贺加贝在后来的人生中,不仅为了利益,将低俗喜剧搬上舞台,同时也为了私欲,不惜抛妻弃子。在消费主义时代的洪流下,他早已将父亲的嘱托忘得干干净净了。
作者笔下的南大寿虽不是上台表演的丑角,但也十分精通喜剧文化。在度假村的时候,南大寿被贺加贝请出山帮助其创作剧本,但在创作过程中被武大富嘲笑剧本无趣,不能满足听戏人的需求,所以要改剧本,加入一些低俗的内容。作为老一辈的传统文艺人,南大寿坚持着自己的价值立场、不写下三滥的内容,认为舞台是需要净化的,喜剧不是儿戏,它必须纯粹。最终南大寿拒绝了武大富的提议,并愤然回家。武大富作为生意人,在面对南大寿创作出的剧本时,只考虑能不能满足其低俗的笑点和能否吸引更多的观众,为自己的度假村创造收益,而丝毫不考虑喜剧本身的内容。作者叙述这样的情节正是对武大富这类贪婪、低俗的人的讽刺和批判。
潘银莲是作者着墨较多的一个人物,她的身上有着善良美好的品质。潘银莲因为容貌极像万大莲,而被贺加贝疯狂追求,这也正是她悲剧的开始。每一次贺加贝对万大莲感情的死灰复燃,就是潘银莲的万劫不复。当贺加贝的喜剧事业突飞猛进时,迎娶万大莲的欲念也再次泛起。于是,他联合史托芬欺骗潘银莲,想要抛弃她。与此同时,潘银莲也爆发了,她面对史托芬的欺骗,指责他们的行为有多么不堪,她抨击了程序化的喜剧表演。实际上,这也是作者借潘银莲的爆发批评如今喜剧表演的胡乱不堪。史托芬带着他的学生对喜剧表演进行数据分析,并呼喊口号“笑料和包袱就是一切”“笑料和包袱就是我赖以生存的衣食父母”[2],这无疑颠覆了喜剧表演的本心,是对如今看重利益、金钱的艺术创作的讽刺和批判。立足于现实人生,以美去撕破丑,使丑的无价值的东西显露本质,受到毁灭性的嘲笑与批判,是喜剧创作、喜剧审美的出发点和落脚点[7]。作者也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批判低俗恶劣的喜剧表演,展现了喜剧美。
陈彦曾说过:“我的写作是两个维度的集合、交汇。一个是对生活的熟悉,另一个是对世界戏剧和中国戏剧的熟悉。”陈彦擅长在戏剧世界里塑造人物,并挖掘现实世界的人生百态。他认为戏曲舞台上的丑角看似滑稽可笑,实际背后意味深长。小说《喜剧》中,贺加贝在消费主义时代的洪流下,逐渐背离传统价值观念,而贺火炬在经历挫折后则幡然醒悟,扛起丑角正道艺术的大旗。其间各个人物悲与喜的转换以及时代与个人命运的联系,既有着丰富的思想内容,也有着独特的艺术化处理。总之,陈彦的《喜剧》无论是在人物塑造、情节描写,还是语言编排方面,都能看出明显的喜剧特征,让读者产生喜感,寓庄于谐,从而展现了喜剧美。同时作者通过贺加贝等人的人生经历把喜剧不同的审美品性展现到读者面前,从批判和讽刺的角度突显了喜剧美,既让作品充满了文学性,又做到了形式上的喜闻乐见,营造出了意蕴丰富的喜剧效果,使作品整体呈現出浓烈的美学色彩。
参考文献
[1] 朱光潜.诗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2] 陈彦.喜剧[M].北京:作家出版社,2021.
[3] 武文宇.论陈彦《喜剧》的喜剧美学及悲剧意识[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5).
[4] 周安华.论喜剧与喜剧美的形态[J].江苏社会科学,1996(6).
[5] 吴义勤.日常性·戏剧性·中国故事——读陈彦长篇新作《喜剧》[J].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1).
[6] 卫佳.重提一种喜剧精神——评陈彦小说《喜剧》[J].新纪实,2021(16).
[7] 黄志刚,刘家思.论鲁迅喜剧观的三个问题[J].四川戏剧,2006(5).
(特约编辑 刘梦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