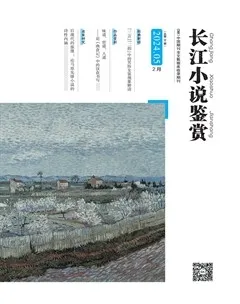《故事新编》的后现代主义叙事技巧与故事结构
苟艳丽
[摘 要] 《故事新编》将一个个古老的英雄人物拖入了日常琐事之中。鲁迅的诙谐、戏谑、戏仿给现代人留下了“大话”与“无厘头”的印象,本文认为,《故事新编》有类后现代主义特点。《故事新编》是以“源文本”为基础,通过对各种元素的再整合与再创造形成的一种特殊的叙述方式。《故事新编》在对事件的处理上采取了“并”“改编”“添枝加叶”的方式,把原本的事件转化为“情节”,并将其置于作家的价值链中,从而取得了对历史的诠释,使《故事新编》变成了“人的历史”的现代性写作。鉴于此,本文将以《故事新编》为研究对象,从著作中油滑与反讽戏仿、故事结构及变奏、消极懈怠几个方面分析《故事新编》的后现代主义叙事技巧与故事结构,为理解该著作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关键词] 《故事新编》 后现代主义 叙事技巧 故事结构
[中图分类号] I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2881(2024)05-0017-04
鲁迅被誉为中国现代小说之父,他对古代小说进行了全方位的革新,同时对现代小说也进行了多方面的优秀创新。鲁迅在其唯一的历史主题小说《故事新编》中用民俗叙事的手法对历史小说做了新发掘。鲁迅写作《故事新编》历时13年。《故事新编》是鲁迅在对散文进行历史反思的基础上以小说的方式对历史进行的再写,获得了一种特殊的美学效应,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部“不可模仿,不可复制”的当代杰作[1]。鲁迅在创作《故事新编》时并不是简单地对原有的文言文进行直译,而是通过对源文本的深入剖析将其中的各个故事元素进行重新组合、重新编排,创新地重写,使故事的含义得到再一次的充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鲁迅创作《故事新编》的进程就是一种特殊的叙述方式。《故事新编》表现了文学创作的一种后现代主义趋势。比如,部分学者认为《故事新编》是后现代作品的一种镜像模式;还有部分学者试图从后现代主义的角度阐述《故事新编》的叙事方式,直接从后现代的视角来探究《故事新编》的创作内涵,并指出《故事新编》通过戏仿、反讽和对话等手段实现了对本体的解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故事新编》和后现代具有共同的价值向度。尽管《故事新编》和后现代小说在叙述手法上存在着诸多的相似性,但是,这并不能成为评判一部小说是否是后现代主义小说的重要依据。因为,尽管作品在艺术特征上有着相同的特点,在叙述手法上也是相同的,但它们的思想本质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对《故事新编》的后现代主义叙事技巧与故事结构进行分析,一方面可以探讨鲁迅小说创作背后的思想内涵以及意义指向,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分析其叙事结构等感悟鲁迅的创作笔法,深刻揭示出鲁迅文学创作的本质。
一、《故事新编》的类后现代主义特点
后现代主义文学是在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中孕育而生的。后现代主义理论是在现代哲学成为一个问题并被广泛讨论后才出现的。它采取一种极端反叛的形式,以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消解一切的决绝姿态,展示社会的荒诞。后现代哲学并非一味地追逐虚无,它所表现出来的破坏、解构、无深度、叛逆、平面化、复制……这些都是生产性的。它旨在实现一种在一元中心消除以后更加宽松、公正的理论环境。
鲁迅先生站在启蒙的高度,本着“立人”的思想,对横亘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进行了一次革新,以西方文化为坐标和参照系进行。如文本《采薇》中,当武王的军队开进商的国都时,鲁迅是这样描述的:“咱们大王就带着诸侯,进了商国。百姓都在郊外迎接,大王叫大人们相互称呼他们道‘纳福呀!他们就磕头、一直进去,但门上都贴着两个字‘顺民。”
不管是周王还是纣王,这些被鲁迅用聚光灯照着的顺民关心的只是自己能否坐稳奴才的位子。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把自己对奴性的愤怒以极其夸张、讽刺的手法写了出来,这种对封建传统权威的反叛与挑战,是符合后现代主义解构、重建的特点的。
二、《故事新编》本末倒置的标签
《故事新编》中的解构、并列、互文、戏仿、荒诞色彩等都是后现代小说的特色。《故事新编》与后现代小说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又有不同之处,这对读者理解和剖析作品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鲁迅在作品创作的过程中非常重视影射和象征的手法,且在很多作品中都有具体的体现。《故事新编》的大部分篇章都充分运用了幽默的写作手法,这与后现代主义小说的荒诞手法有着高度的相似性,它们都是对神话的戏仿。鲁迅将《故事新编》中的英雄圣贤一一搬上了舞台,剥去了圣洁、高尚的光辉,变成了一堆又一堆的琐事,并对其毫不留情地解剖、分析[2]。
有的学者将这种戏仿视为当今中国后现代“大话”类型电影的鼻祖,拿鲁迅《故事新编》和周星驰的几部电影做对比。但我们应当看到,戏拟并非后现代文本所独有。如果说《故事新编》是一部后现代小说,那么阿里斯托芬的《蛙鼠之战》就是一部类似于古代神话战争的希腊小说。《故事新编》中存在着戏拟与文本交互的现象是无可置疑的。巴赫金曾说过:“世上最有力的武器莫过于微笑,以抵御这世间的嘲笑!”“以游戏的态度来看待文本,这就是后现代主义文本所具有的特质。”所以,有學者认为《故事新编》是一部后现代主义作品[3]。以游戏的态度来看待作品并非后现代主义所特有的特性和评判标准。虽然从形式上来看两者都是以游戏的形式对文本的内容进行展示,但从思想内涵的层面来看,其想要达到的文本特征以及目的还存在较大的差异。王亚娟在自己的作品《游戏不等于后现代主义》一文中针对游戏文本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后现代文学作品的写作手法、创作方式以及叙事技巧等都是在长时间的文本探索中总结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后现代主义小说是对传统小说的一种传承和发扬。无论后现代主义如何吹捧这种创作形式,其本质都是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沉淀。对于后现代主义的评价,人们不能用戏谑、无厘头、恶搞、荒诞等方式去判断,这似乎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做法。
三、《故事新编》的油滑与反讽戏仿
鲁迅在《补天》中的看法是:“油滑是创作的大敌,我对于自己很不满意。”但是鲁迅对这一点却表现出不无得意,他说:“虽然他并没有把古代的东西弄得太死,但是,也许有一段时间他还可以继续写下去。”鲁迅虽然意识到油滑的写作有损其艺术美感,但他还是继续以油滑的方式进行文学创作,在“油腻”而“不严肃”的情况下加强了其“战争”的意味。鲁迅这类“游戏狂欢”式的写作体具有很强的讽刺色彩。“反讽”是一种装聋作哑,善于用看似愚蠢的话语来战胜自以为是的敌人,其最根本的特点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和深层的意思不相符。《奔月》中,嫦娥偷了仙人的丹药上天之后,后羿想要用射日的勇气去射月,但他的英雄气概并没有多大的力量,于是,当他从为天下苍生伸张正义到对妻子的背离,从射九日、射封猪到射月亮,结果月亮一动不动,他的动作越是自然,讽刺的意味则越是浓烈。《补天》中,造物成了女娲枯燥无味的游戏,她随手一挥就制造出了一个又一个的活人,那些“小东西”非但不感激,还想方设法地想要毁掉这个世界。他们讲的是“尚书式”的古老语言,浑身上下都是破布,语言优雅、道貌岸然,与女娲的淳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与赤身裸体讲白话的女娲相比,人类的异化和创造的悲伤显得更加讽刺。鲁迅使用历史讽刺的手法,并尽可能地用戏仿和改写经典文本等幽默方式,让历史文本中的经典含义得以被重新审视和解读,从而揭示出历史和社会现象背后的深层次问题。
四、《故事新编》的故事结构及变奏
鲁迅在谈到《故事新编》创作的时候,说他读到一半时看见一位绅士“含泪哀求”,“这是一种可悲的邪恶,我觉得很可笑,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不能阻止一个穿着古代衣服的小个子男人站在女神的双腿之间。这是从严肃到油滑的开始。”他说:“油滑是创作的大敌,我对于自己很不满意。”他不喜欢那些圆滑的东西,“不仅没有必要,而且破坏了整个结构的宏伟”[4]。从这一点来看,《故事新编》从写作之初就有了宏大的题材架构,但在写作的过程中,作家的笔锋却出现了偏差,陷入了一种被称为“油滑”的状态,这种状态毁坏了宏伟的架构。这样的情况下,在整个《故事新编》中是否也是如此?
1.宏大正面的故事结构构建
首先,这种故事结构构建表现为对原故事主题的取舍和主题的提炼。《故事新编》在创作的过程中,其主线主要是以历史事件为发展脉络,其中所承载的中华文明从发展到昌盛都有相应的呈现,其本质上带有一种史诗性,但在故事的表达上又偏向于后现代主义的叙事技巧。《故事新编》建构的重点在于展现出这一类精神脉络在确立与嬗变过程中的兴衰。同时,其主题也集中于创造、死亡、拯救、信仰等生存主体所要面对的生命问题,表现出一种对生活的态度。换言之,鲁迅从一开始就从人的历史的角度(不去计较每一个具体的史实的考订)考察古今人情。因此,基于此而产生的每一种联想都带有一种文化人类学与个人人生哲学的意义,是一种从根本上提高作品风格的方式。
其次,这种建构是一种过程。鲁迅在描写人物、事件时将他们置于时间的洪流之中,使得人物的成长、事件的发展在时间的推移下逐步积聚着读者的心理势能。这是一种上升的力量,它如同旭日一般在早晨冉冉升起,在中午的强光中闪耀。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铸剑》中的“眉间尺”,从一开始的犹豫不决到后来的鲁莽,再到后来的坚毅和果决。这在原作中是很难找到的,而鲁迅则是一步步地把他的成熟展现出来,完成了这一角色的建构。《铸剑》这本书也是一部成长历程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同时也是成长过程的象征。
另外,这种“建构”伴随着强烈的抒情性。《女娲》主要展现的是女娲挥舞藤蔓造人的一幕,行云流水且充满了动感,造物主的动作一气呵成,姿势优雅,让人看不出她是在玩还是在工作,又或者是在跳舞。而在描绘画面的时候,作者所用的文字色彩浓淡交织、鲜明纯净,音节间也兼顾了韵律,充满了感情,用这样一种诗意的语言将女娲那充沛的生机展现了出来,大自然的力量与美让人着迷[5]。
2.消极懈怠的故事结构构建
小说中用各种构造手段建立起来的伟大突然就像是从山顶掉到了山崖上,给人一种既惊讶又迷茫的感觉。王瑶说过,“圆滑”是一种类似于话剧中小丑的幽默,也就是说它是一种喜剧,“古今交融”确实是一种“油滑”,但却是一种幽默、一种讽刺、一种“插科打诨”,就是小丑用一种不对等的语言来回应主人公,把严肃的题材变成了幽默,让人产生了一种升华。鲁迅在《故事新编》中总体上是以一种“滑溜”的手法,把他在作品中构筑起来的心灵坐标一一抹去,从而造成了前后两面的互相颠覆[6]。
从《故事新编》中读者可以看出,女娲的健康本性受到了伪君子的攻击,合理的道德必须以良好的人道为前提。然而,在经历了文化异化之后,人开始削足适履,人的神圣性随之丧失。射杀封豕长蛇的后羿虽然还保留着圣人和武士的传统,但他每天都要为了食物而东奔西走,还被他服务过的人误解,被他的弟子背叛,被他的爱妻抛弃,他的英雄传说被打破了。大禹虽然克服了重重困难,不顾各种夸张的说法,最终还是逃不过被同化的宿命,进入了浮华的尘世,行动派的形象开始被吞噬。伯夷与叔齐一生所坚守的“忠孝”,到头来沦为别人的谈资,并背负着不忠不孝的骂名,忠孝者的形象也隨之消失。杀死国王的人与国王一起接受祭祀,享受臣民的崇拜,消除了复仇的含义。而自认为以柔克刚、以弱胜强的老子在沙漠里留下了五千字的话也难免被嘲笑。庄子能召唤神灵,能理解生命,却不得不报警才能摆脱清醒的男人,这已经不是可笑,而是一种嘲讽[7]。
五、结语
综上所述,《故事新编》中所谓过程就是通过故事的情节化来实现作者对历史的解读。小说中蕴含的丰富内涵以及人物性格的多变性恰恰说明这是一部描述人的历史的著作,它以其虚构的作用使得老文本中出现了各种角色的对峙,各种形式的语言交错,但实质上却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与世俗的对立。但是,只有在摆脱了单一解释的束缚之后,才会出现各种不同的诠释与叙事方式。读者可以从鲁迅独特的人生经历和对文化的深刻批评中,体会到他的写作方式对后现代主义叙事技巧的发展,他的《故事新编》对现代小说的改编风格产生的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郜元宝.《故事新编》改名记——以《非攻》《理水》手稿为中心[J].现代中文学刊,2022(1).
[2] 房伟.历史、自然与现实生活中的探索与创新——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综述[J].南方文坛,2023(1).
[3] 陈蘅瑾.“油滑”中的现实穿透与悲剧性体认——鲁迅小说《故事新编》解读[J].浙江社会科学,2021(8).
[4] 荆亚平.母题学与“文学鲁迅”的创构及其经典化——评谭桂林《记忆的诗学——鲁迅文学中的母题书写》[J].鲁迅研究月刊,2021(12).
[5] 徐公持.关于鲁迅文学起源理论的再认识——从“杭育杭育派”说起[J].文学遗产,2021(3).
[6] 周海波.鲁迅研究的新维度——评《现代教育与鲁迅的文学世界》[J].山东社会科学,2021(6).
[7] 汪佳妮,孙海军.经典阐释与鲁迅研究再出发——“《阿Q正传》和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阐释”学术研讨会综述[J].鲁迅研究月刊,2022(10).
(特约编辑 刘梦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