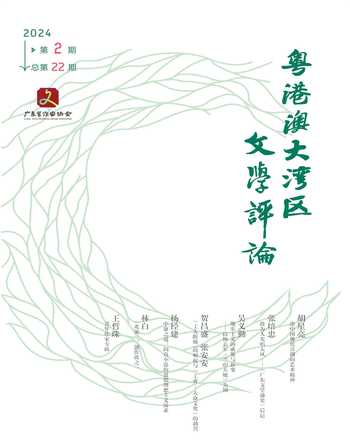史诗追求、“登山”叙事与神话意指
刘志权
摘要:《玉色》是一部题材独特的主旋律小说。小说扎根广东揭阳农村,揭示乔阳商人夏文达是为何又如何完成从商人向基层村干部、从非党员向党员转型,并推动乔阳发展的。小说的开头略类《红旗谱》,用集中的冲突凸显乔阳与个人的转折时刻,显示了作者史诗式书写乔阳的雄心。小说以问题意识引领,在结构与语言层面,都采用了“登山式”的叙事策略,形成了包括历史与现实的主暗线映照、非党员与党员的形象对位、传统与当代的理念碰撞的三重对位结构。在艺术层面,小说提供了一个由父亲、工作日志与书生构成的改革神话框架,以及围绕“玉”的私设象征构建的三级所指系统,有效丰富深化了小说的主题内涵。《玉色》不缺乏力量,但需要刚柔并济。在既宏大又细腻的社会生活长卷中,尊重人物命运的必然性,真实而真诚地揭示人性的复杂与幽微,永远是现实主义文学成功的不二法门。
关键词:主旋律小说;能人治村;“登山式”叙事;象征系统
一
《玉色》是一部写翡翠之乡乔阳村改革发展之路的现实主义小说,同时也是写乡村基层干部成长的主旋律小说。小说容易让我们联想到20世纪80年代以柯云路《新星》为代表的改革小说(有点巧合的是,小说中支持改革的街道领导名叫萧向南,不知是否在向“李向南”这一人物致敬),20世纪90年代的“现实主义冲击波”作品,以及近年来滕贞甫的《战国红》、王华的《大娄山》、海燕《小康之路》、赵德发的《经山海》等以基层干部在脱贫攻坚中成长为主线的系列作品。
《玉色》与上述小说有着重要的不同,首先在其坚实而具体的现实指向。作者王哲珠是广东揭阳人,揭阳本身是中国玉都,当地同样有介公庙,还有和乔阳一样被称为“金玉之乡”的阳美村,也同样有浓厚的宗族文化及经商传统。而包括公盘、石料、切石、调玉等在内的关于玉的商业文化也非常有特色,因此,小说体现了鲜明的、无可替代的地域性。这些都注定了当地的基层干部也需要有符合当地“地情”的工作方式。比如,小说是基于“能人治村”这一乡村治理的“南方模式”。能人治村并不是新近才有的现象。早在世纪之初,研究者就指出,“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能人治村并不是个别现象,特别是在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这一现象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1因此,夏文达这样的形象在乔阳出现并不偶然。总之,《玉色》是一部扎根于广东揭阳农村现实的扎实之作。如果把“乔阳”替换为现实地名,这部小说差不多可视为典型的非虚构写作或者一部乡村振兴的长篇通讯。事实上,就文体而言,非虚构写作更显时尚,而长篇通讯功效性更强,作者为什么选择小说体裁呢?也许有两种可能,一是基于作家对小说文体的热爱,二是因为小说更能安放作者史诗式书写地方发展史与人物成长史的野心。
《玉色》更大的不同体现在其主题的独特性。对大多数同类小说而言,主人公一般是党员,这决定了其思想认识已经具备相当的基础,而其基层(挂职)干部身份的获得,大多情况下来自组织任命。但《玉色》意在展示的是,在做生意为主流、很少有人在意行政组织的乔阳,一位辈分高、生意场有威信的成功商人,一位已届中年、世界观理应已经确定的无党派人士、一位从来没有群众工作经验的政治“素人”或乡村“能人”,为何选择了做吃力不讨好的村干部,并如何不断成熟并成长为党员的——小说的最后,主人公夏文達已经成为一名中共预备党员。从这个意义上说,夏文达是当代文学史上具有独特意义价值的“新人”。
这一人物形象容易让我们联想到红色经典小说《红旗谱》。朱老忠作为小说第一部的主要人物正式出场时,已经并不年轻,他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是一个传统的、带着草莽气的农民英雄,小说正是通过一系列事件,展示了他是如何成长为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但二者的联系不限于此,《玉色》的开头与《红旗谱》也有诸多神似之处。《红旗谱》以“平地一声雷”开篇,展示了一场三十年前的悲剧冲突和命运转折:地主冯兰池为霸占锁井镇官地,设计砸毁了千里堤上的古钟;朱老忠父亲护钟而死,就此家破人亡,年幼的朱老忠被迫出逃关外。砸钟的钟声响彻全书,以富有象征意味的鲜明形象,展示了阶级斗争和农民作为革命斗争主力的坚实根源与内在逻辑,从而使之成为当代长篇小说的经典开篇之一。《玉色》中,读者同样猝不及防,开篇就被抛入一场关于乔阳的现实冲突之中。正如作者以不加掩盖的预述指出的,这一冲突不仅是后来乔阳转折的标志,同时也是夏文达以及欧阳立等主要人物人生转折的标志。它唤起了夏文达关于三十几年前“那个夜晚”的清晰记忆,大人们“神情和语气中夹杂着紧张、兴奋、疑惑与期待”2。作者指出,那时的夏文达“不到十岁”——正是与《红旗谱》中小虎子类似的年龄,但与小虎子的仇恨记忆截然相反的是,记忆赋予夏文达的,恰恰是改革开放所给人们的希望,也正是当下乡村再次振兴的历史源动力。带着希望与憧憬的历史与乔阳村正面临的黯淡现实一起,被作者压缩与并置到这场乔阳大道路口牌门下的冲突之中。这种劈空而来的开头,如同唱歌时以高音调门起唱,对作家而言其实是一种挑战,但同时也佐证或者说凸显了作家史诗写作的雄心。
为了强调冲突所引发的转折的历史性意义,小说特意调用了中国古代小说的技巧。其一是穿插藏闪之法。例如,小说以几近刻意的方式,多次提及“那个决定”“那件事”“你的路”,甚至明确指出,“那个决定愈来愈清晰。夏文达人生最大的转折,此刻开始。”3但究竟是什么事、什么决定或者说什么转折,始终犹抱琵琶半遮面。再如,作为冲突中舆论对象的乔阳牌门上的八个字始终没有透露,作者半遮半掩地呈现了非议者对“天下”与“成器”这四个字的质难,但一直要到这部分的最后,我们才知道完整的八个字是“天下美石,乔阳成器”。加以细究,可以发现,延宕叙事的功能,是为了突出强调夏文达“决定”以及“转折”的历史意义——对历史意义的强调,正是史诗特征之一。第二种技巧是“游丝惹花”式的描写,和情节上草蛇灰线的铺垫。乔阳毕竟只是一个“村”级单元,一个村中心路口的冲突,就已经足以让作家不动声色地将乔阳几乎所有的重要人物,如夏文达、欧阳立,林墨白、夏天莹、陈修平、陈商言、萧向南等等,都聚拢到一起亮相。几乎所有人物之间的关系亲疏或立场冲突,都通过上述技巧得到了暗示性的描写。由此,借助冲突,“引言”留下了关于乔阳发展之初整个村落的全息影像,就像一扇带着中国传统艺术风格的旋转门,隔开同时也是联结了乔阳的过去和现在。牌门“天下美玉,乔阳成器”八个字的霸气与争议,正如《红旗谱》开篇“平地一声雷”式的砸钟声一样,被赋予了统摄全书主题的意义与功能。
二
主旋律小说,就其本质而言,是特定题材的现实主义小说,其优劣成败首先遵循现实主义小说的普遍美学,包括小说是否真实可信地写出了人物成长的必然性与内在逻辑,以及是否创建了丰满、立体、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在此基础上,还应该考察小说是否以文学的形式深入挖掘、提炼、尝试解决时代的重要问题,是否呈现、响应、服务了时代发展的重要主题。厚重的历史感、鲜明的问题意识与标志性的人物形象,是绝大多数史诗性小说的共同特征。正像茅盾明确表示,通过《子夜》“我所要回答的,只是一个问题,即回答了托派中国并没有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是更加殖民地化了。”1
问题意识是《玉色》的鲜明特征。在问题意识引领下,《玉色》采用了一种我称之为“登山”式的叙事策略:小说放弃了传统小说的“起承转合”,每每先劈头提出问题,或者毫无铺垫直奔焦点,如同登山者先一节一节向上方凿出的锚点,然后再拉动语言或情节的登山绳向上攀升。试看,“在生意兴旺,身家丰厚,后辈又接得起的时候,夏文达要当村委会主任?他想什么?”(第一章);“夏文达想知道,欧阳立整日看玉石生意,有人成千成万地赚钱,真没一点动心?”(第三章)“‘什么人,说乔阳人不懂翡翠?郭诺一的话,让夏文达耿耿于怀。”(第五章)“‘你真以为能改天换地?夏文腾不止一次问夏文达,每次都没听到答案。”(第八章)从语言学上看,锚点体现为小说在许多章或节的首句频频使用的没有前置提示的“那”,如“那个狂风暴雨的夜,成为夏文达父亲岁月中浓重的暗色”2“那个人出现时,夏文达在正合号的展位坐镇”3“夏文达那块料要切了”4“那天回村委会,夏文达告诉欧阳立,这次公盘陈修平会出力”5。这种叙事方式,增强了叙述的张力与语言的力度。这种叙事特点也扩展成为小说结构。《玉色》每一章几乎都如同一座由全新的冲突矗立的峭壁,人物被要求向既定目标攀登,在此过程中,人物得到不同方面的“试炼”。
通过“登山式”叙事,《玉色》建构了全书情节和主题上的对位体系。首先是历史与现实的主暗线映照。夏文达从生意人向基层工作者的人生转型表面看较为突兀,内驱力其实是父辈几十年前一起探索农村发展的革命(改革)友谊与革命理想的历史传承。夏文达的父亲与欧阳立的父亲(“书生”)相识于改革之初,作为外来党员干部,书生为地区的改革与发展殚精竭虑、全心全意,乃至献出生命,他深刻地影响了夏家两代的人生道路。比如“乔阳开公盘”的梦想由书生启发了夏文达的父亲,最终在夏文达这里实现。欧阳立发展夏文达入党的念头同样受书生启发:“父亲工作笔记里的一些话浮现出来:总有一天我得离开这个村子,不管什么地方,得有要紧的人带,不能单单认定某个人,带村子重要,带人更重要。”1正如小说多次指出的那样,在欧阳立身上有着书生的影子。因此,乔阳当下的改变,都像埋在岁月深处的种子在特定时刻“结成日子里的果子”,而作为父亲的“书生”则是直接或间接影响乔阳历史与现实的灯塔。还需要指出,如作者有意强调的,党的事业继承不意味着亦步亦趋的重复,要葆有其精神内核,与时俱进,自己想,走自己路,自己寻找答案。正如见证过两代人历史的夏文达二叔所言,“我是那时的人,只能看那时的东西,现在的人才有办法看现在的东西,总得试一试。”2
其次是夏文达与欧阳立的核心形象对位。对作家而言,正面写农村基层工作,以及一个无党派人士认识不断向党的靠拢和进步,无疑是一种考验。看得出作者对此下了不少功夫。“带村子”和“带人”是小说的两个重要主题。夏文达尽管从书生那里继承了奉献的精神,但如果缺少了欧阳立这个“领路人”,很难独立成功;反之,欧阳立也从乔阳和夏文达那里,丰富了工作方法以及对基层的认识。二者构成了《玉色》中对位的主旋律和副旋律。作为“能人”,夏文达继承了“三分本事,三分胆识,三分运气”的潮汕传统,敢干敢试,雷厉风行,他为乔阳增收扩容、引入公盘、重兴玉坊街、建设精品交易馆,乃至最后拆迁征地办玉色华城项目,善于借用各方力量、采取多种策略达成目标,好多做法让欧阳立承认“我们这些‘书呆子想不出,甚至不敢想,有些感觉怪,甚至夸张,可确实有效。”3作为党员,欧阳立尽管年轻,但在抓环境和精神建设、拆除违建、改进合伙规则、反思玉文化内核、推动乔阳玉文化建设方面,体现出理论水平、规矩意识、无私精神、服务情怀等各方面的“先进性”。正是由于这种人格感召力,欧阳立动员夏文达入党的事才水到渠成。两人可谓取长补短,相向而行,互相成就。如小说第七章借萧向南之口说,欧阳立说话都带夏主任的霸气了,并通过陈修平感觉到,夏文达这语气神情,跟欧阳立太像了。夏文达最终得到了村民的认可,成就了准党员干部的“玉色”,这是欧阳立对夏文达、乔阳对夏文达以及夏文达对自己三重磨砺的结果。
再次是传统与当代的价值理念碰撞。小说写了三代党员与乔阳三代人。前者分别以书生、欧阳立与陈商言为代表,欧阳立处于中心位置。乔阳三代人中,第一代以夏文达父辈为代表。在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浪潮中,他们摸着石头过河,远赴云南、缅甸,开创合伙买石先河,奠定了乔阳“翡翠之乡”的发展道路;第二代是夏文达、陈修文、林墨白一代。他们重信义、讲规矩、敢拼搏,成就了“天下美玉、乔阳成器”的美名,但文化程度不高,思路和視野受限,这是他们与第三代的主要隔阂所在;第三代是守成一代。一部分人(如林山、林水、陈商成等)继承了父辈的传统,可能迷失在相对优渥的物质生活之中,精神相对空虚,但对翡翠有着骨子里的痴爱,如欧阳立所言,“这是乔阳的底气,是乔阳之所以成为乔阳最大的原因所在。”1另一部分人为赚钱不择手段,构成了对传统游戏规则的挑战;还有一批年轻人正将新的价值观、新的视野、新的理念带回或即将带回乔阳,如陈商言作为年轻党员对奉献精神的追求,夏天莹对玉雕文化的继承与创新,夏天正关于现代管理的思考等,他们代表了乔阳的未来与希望。小说围绕乔阳合伙买石风波、陈商成偷戒王事件,以及关于玉雕理念的传统与现代之争等,系统性地思考了社会风气、管理理念、文化创新等方面的问题。
小说的末章,以“开始与结束”为题,将三种对位再次融合到一起:历史、现在与未来,是一个生生不息的过程,它需要每一代共产党员的智慧与付出,而随着夏文达一届任期的行将结束,乔阳的未来,将转移到陈商言、夏玉影等新一代年轻人肩上。
三
在美学层面,象征构成了《玉色》的重要艺术特色。比如,在传统的红色经典作品中,太阳、红旗、青松等公设意象几乎是标配。这种象征的规定性与清晰性具有神话的特征,罗兰·巴特曾用“神话”意指左翼叙事的不可避免,他说,“当革命将自己改革为“左翼”时,左翼神话就会并发”2。“神话”的存在不必然与文学性发生冲突,其优劣取决于象征架构的新意、弹性与可阐释性等等。
《玉色》提供了一个由父亲、工作日志与书生构成的革命(改革)神话框架。首先是父亲。在革命文学中,“父亲”往往具有革命源泉或精神导师的意义,也是党与党员之间关系的情感象征。如一句歌词所唱:“我把党来比母亲。”书生不只是欧阳立的生理父亲,也是给予其精神鼓励与工作指导的精神父亲。他还深刻地影响了夏家两代人,并因此对乔阳的当下和未来产生影响,因此也可以说是乔阳的“父亲”。其次是工作日志。工作日志是父亲形象、精神、经验和思考的物质载体,相对于传统父子之间的言传身教,纸质笔记更能确保革命传统的准确、连续和普及,并有助于使个体父亲变成广义上的精神父亲,这一意象在主旋律文学中颇具代表性。如王华的《大娄山》写两任乡村第一书记脱贫致富接力,就写到龙莉莉继承了前任娄娄的工作手册,“她是有自己专门的日记本的,但她决定接着娄娄的日记往下写。她来这里就是接任娄娄的……”3。再次是“书生”意象。书生作为私设意象,代表了作者对党员核心素质的认识。欧阳立父子都不约而同被认为书生(或者说书生气),并不偶然。用肖月柔的话说,“欧阳立是真正的书生,看着软绵绵,芯子硬得很。”4这一概括来自民间的现实体悟,形象而精当。小说对欧阳立父子两代党员的展开,其实就是给“书生”注入内容,诸如有原则、有文化、有理论、有梦想等,这一形象的凝练无疑是有新意的。
在大的神话框架下,《玉色》更富特色的是“玉”象征系统。历史地看,关于党员的多见意象是“钢”,如我们惯常说钢铁战士、钢铁意志;前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艾芜《百炼成钢》等作品也都以此为核心意象。玉与钢有诸多相似性,如“钢”往往喻指意志的坚强,而“玉”喻指品格的高洁。此外,二者的共性还在于都需要淬炼,如俗语说“千琢璞为玉,百炼铁成钢”。除了开篇的“天下美玉,乔阳成器”八字外,在此可以对小说涉及“玉”的主要象征作简单罗列:
“重要的是怎么用。”萧向南很认真,“用乔阳人的话讲,好翡翠得有好师傅调,好翡翠石料得有制玉高手。”(——指夏文达,第20页,括号为作者所加,下同。)
“懂玉质,发现玉,这是乔阳人擅长的。”欧阳立说,“玉是乔阳的光,乔阳不但得有玉生意,还得有玉的光芒。”(第126页)
欧阳立很严肃,这两年,夏文达一直在自我发现,像懂玉人发现玉的光彩,乔阳也需要自我发现。
“如果你是翡翠,村委会、乔阳、这几年所有的,都是你的墨白或天莹。”127(——夏文达,第127页)
活了半辈子,他开始调自己的种水和颜色。……(——夏文达,第128页)
与书生的相遇,在夏文达的父亲眼里,就像遇到好翡翠,是机缘也是心意。(第200页)
欧阳立说,“玉色是类似于灵魂的东西。”(第357页)
玉色,必是懂玉者与玉石的相互成就。(第360页)
上述列举围绕着玉这一核心本体,构成一连串不断扩展的意象,不妨略作分析:在第一层级,玉/翡翠作为美好的具体之物,先后被用来褒指书生、夏文达,以及作为地方的乔阳等,即他(它)像玉一样美好;第二层级则是玉的延伸之物,如玉的光芒、玉的光彩、玉色、玉的种水和颜色等,它们同样被用为意指乔阳或人内在的抽象品格,如精神面貌、思想境界、认识水平等等;作为第三层级的意指,一块“美玉”的形成,离不开后天的环境。正如好玉的最终形成需要经过选石、切玉、调玉、制玉等专业工序,每道工序都离不开人,党的人才尤其是基层干部的培养,也离不开发现、引导、磨砺以及使用,因此,这对领路人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同时,乔阳作为一个有良好的经济基础与经商传统的乡村,也如同一块美玉,是可以施展雄心和抱负的舞台,它既呼吁好的领导,也能成就好的领导。这正是本书重点指出的“相互成就”的关系。这样,通过多重意指,人才之“器”,与小说开头“天下美玉,乔阳成器”的隐喻形成了完美的呼应。
除了上述象征体系外,还有一个与玉有关的特别的意象是龙凤牌。龙凤牌在引言部分就已经出现,隐现在《玉色》三十多年的故事线中,并以龙凤纹、龙凤璧等衍生意象贯穿始终,是“玉色”不可或缺的一块拼图。龙凤牌本是欧阳立家的祖传之物,书生为了拓展他挂职地方的农产品销路,卖了龙凤牌筹钱买小货车,龙凤牌因此转入夏文达父亲手中,由于书生的意外牺牲,龙凤牌一直留在了夏家。寻找父亲的龙凤牌,其实也是欧阳立的一个心结,龙凤牌因此与工作日记一样,被赋予了革命精神传承的意义。与此同时,对夏文达、林墨白等多数人,龙凤图案还承载着更为独特的情感与更为丰富的文化内涵,即对幸福生活的祈愿。如林墨白所阐述的:“龙凤呈祥,人世极致的美好。”“这些看似大俗大土,包裹着中国人心灵最深处对日子的眷念,这种俗是痴迷生活最生动的体现,是对人世最深的慈悲,包含着日子最柔软的暖意。”1这一象征意象,将“玉”从形而上的高蹈层面,拉到了热闹生动的世俗日常生活层面,与此同时,也更为生动地揭示了党员的人生追求。“我们想着自个的日子,那个人想着别人的日子。”——这正是那个卖掉龙凤牌为人民谋福利的書生的写照,也是一切优秀的党员基层工作者的写照。这一意象的存在,在充实“玉”象征系统的同时,也深化了本书的主题。
四
在关于龙凤璧的对话中,林墨白曾谈到自己的理解:“龙是刚,凤是柔;龙是放,凤是收;龙是张扬,凤是含蓄。这类似于阴阳,既是事物的两面,也是同一事物的相生相融,是我们的文化中重要的内核。”2这一看法也可以作为艺术论。《玉色》诚然不缺乏力量,无论是史诗化的追求,抑或登山式的叙事,或者含义鲜明的多重意指,都彰显着力量。力量几乎可视为主旋律小说对自身的文体要求,因为主题任务的抽象化与宏大性本身是刚的。但正因如此,作品尤其需要有“柔”,这种柔,不只是在叙述节奏的张弛有度,更重要的是在生命的温度,以及生活的烟火气。正如林墨白对自己的作品龙凤璧内心还存在着遗憾一样,《玉色》多少也存在着遗憾。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其一在于人物刻画方面。夏文达和欧阳立是刻画较为丰满的两个主要人物,但本可以更蕴藉些,用更丰富的细节充实形象,将评判的权力交给读者。另外,他俩始终影子一般结伴出现,但作为主任和书记,他们难道没有工作范围的区分,没有各自的日常生活吗?欧阳立与夏天莹之间从未正面展开过的爱情,不是可以揭示人物思想、性格的重要事件吗?党员干部也应该可以拥有爱情的。还需要关心那些次要人物。如纳博科夫所言,“大作家的世界确实是个魔幻般的民主世界,哪怕是很小的小人物,……在那个民主世界中都有生存、繁殖的权利。”3小说聚光于夏文达和欧阳立,而聚光灯外的人物几乎都处于情节的暗夜之中,他们的情感逻辑、他们的世界很少得到关注。例如,作为和夏文达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陈修平真的对书生一无所知、一无所感吗?作为夏文达的妻子,肖月柔不应该只是作为家中传统而贤惠的妻子形象,她其实有她的思想和事业。即便是代表了乔阳未来的第三代“新人”,无论是作为党员的陈商言,还是代表了乔阳玉文化传承的夏天莹,遑论笔墨更少的夏玉影、夏天正,都同样缺少了性格成长与精神世界,是福斯特所谓的扁平化人物(例如,夏天莹始终保持了一尘不染的仙女形象;那个在外读书的夏天正,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似乎从未回过乔阳),这也导致改革的未来缺乏交接,夏文达之后乔阳的未来如何,小说没有提供坚实的历史必然性。
其二在于场景和细节的营构方面。如前所述,《玉色》通过“龙凤呈祥”表达了民众对美好生活的祈愿,而热气腾腾的、富有地区特色的世俗生活,既能激发读者的情感共鸣,也可以对主题形成有力的支撑。对于现实主义小说,世界的真实细腻,既是其主题和思想说服力的来源,也是再现真实性的美学追求。借用海明威的冰山理论,想要露出海平面的八分之一神圣而庄严,需要海平面下那个庞大而缜密的世界来支撑与推动。小说每章都是如拔地而起的事件冲突的峭壁,诚然是紧凑而有力的构思,但也以损失了低处日常生活的层峦叠嶂为代价。情节的疏朗不等于简单。例如,作为民俗每年正月初六晚上举行的乔阳火把节,仅在小说开头惊鸿一瞥,在随后五年的时间里彻底消失了,从艺术的角度看颇为可惜。它本可以连同乔阳的春节风俗、乔阳独有的宗族文化等一起得到描写——民俗风情描写本是中国乡土小说的优秀传统。再如,小说不乏夏文达与欧阳立一起吃肠粉、潮汕牛肉面、腐乳粿条、牛杂汤等乔阳小吃的情节,这些才是世俗生活的真面目。但对于传统农村,每个饮食店其实都是熟人聚谈的天然广场,可以有喝茶下棋的闲逸,可以有插科打诨闲言碎语,甚至也可以安放乔阳人的生老病死,这一切都可以让乔阳更为立体丰满。但在向主题的大踏步前进中,二人所到之处都仿佛特意经过了清场,是一个没有日常生活的寂静世界。小说不妨稍为舒缓密实,或者可以适当借鉴中国世情小说的传统——当然,这也许意味着《玉色》将会成为一部完全不同风格的小说。
上述问题其实并非《玉色》独有,在同类作品中较为普遍,这也是近年来主旋律小说较多,却难以出现经典之作的重要原因。讲述中国故事、讲好中国故事,是当下中国作家不可回避的使命,但在既宏大又细腻的社会生活长卷中,尊重人物命运的必然性,真实而真诚地揭示人性的复杂与幽微,永远是现实主义成功的不二法门。对曾经创作过《长河》等作品的作家王哲珠来说,她所生活的广东有太多关于这个时代的故事,或者说,有很多上佳的玉石料;《玉色》似乎只是她风格转型的第一次试手。作家已经呈现出在生活积淀、思维视野、文体驾驭等方面的优势,如小说中的夏文达一样,正在“调自己的种水和颜色”。相信稍假时日,她会和这个时代和她的作品一起互相成就,绽放出瑰丽的“玉色”。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平民文学理论与中国现当代平民文学史建构研究”(21BZW137)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1 广新力、张日新:《“能人治村”与村民自治组織治理》,《南方农村》,2004年第6期。
2 王哲珠:《玉色》,花城出版社2023年版,第4页。3 王哲珠:《玉色》,花城出版社2023年版,第4页。
1 茅盾:《〈子夜〉是怎样写成的》,《新疆日报》副刊《绿洲》,1939年6月1日。
2 王哲珠:《玉色》,花城出版社2023年版,第9页。
3 王哲珠:《玉色》,花城出版社2023年版,第10页。4 王哲珠:《玉色》,花城出版社2023年版,第99页。
5 王哲珠:《玉色》,花城出版社2023年版,第284页。
1 王哲珠:《玉色》,花城出版社2023年版,第166页。
2 王哲珠:《玉色》,花城出版社2023年版,第353页。
3 王哲珠:《玉色》,花城出版社2023年版,第85页。
1 王哲珠:《玉色》,花城出版社2023年版,第223页。
2 [法]罗兰·巴特:《神话——大众文化诠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7页。
3 王华:《大娄山》,山东文艺出版社2022年,第65页。
4 王哲珠:《玉色》,花城出版社2023年版,第100页。
1 王哲珠:《玉色》,花城出版社2023年版,第266—267。
2 王哲珠:《玉色》,花城出版社2023年版,第266页。
3 [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文学讲稿》,申慧辉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