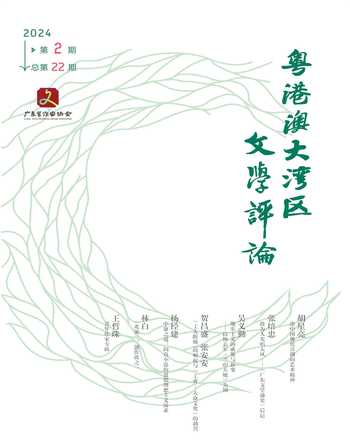论黄药眠四十年代小说的乡土书写
林分份
摘要:黄药眠四十年代的小说,书写了抗战时期粤东北客家侨乡社会的风貌及其变迁。其变,既在于南洋风情的愈发浓厚,以及金钱势力的崛起左右了人的地位、尊严和命运,影响了他们的观念、信仰和社会风气,也在于世家的没落、长老教化的式微等权力结构的更替。其不变,则在于客家侨乡社会的特质,包含妇女的隐忍和卑微命运,异姓族群的龃龉和敌意,以及民众直面生活磨难的勇气、决心和爱等“灵魂的光辉”。由于作家出身、阅历和生活环境所限,这些小说的主题、基调等与主流抗战文学或有参差,但在书写“真正的中国人物”、展现其反抗性及作家的倾向性方面,它们既是彼时黄药眠有关文艺“中国化和大众化”主张的具体实践,更是其吹响的战斗号角。
关键词:黄药眠;四十年代;乡土小说;抗战文学
作为小说家的黄药眠,其小说创作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为1927年至1929年,黄药眠在上海先后创作了中篇小说《痛心》《一个妇人的日记》和短篇小说《毒焰》《A教授的家庭》《工人之家》等,从题材内容看,这些作品大体属于当时的“革命文学”1。后期为1938年至1949年间,自1938年春他在武汉完成短篇小说《陈国瑞先生的一群》开始,此后在梅县、桂林、广州、香港等地,先后创作了以故乡见闻及个人阅历为基础的中篇小说《克复》《热情的书》《李宝三》《古老师和他的太太》《县长》《暗影》,以及短篇小说《一个老人》《章红嫂》《小城夜话》《尼庵》《淡紫色之夜》《再见》等,后于香港出版了两部小说集《暗影》和《再见》2。
有关黄药眠后期的小说创作,以往的文学史家主要聚焦于其1939年初发表的《陈国瑞先生的一群》,将它归入抗战时期以张天翼《速写三篇》为代表的讽刺小说序列,着重肯定它在“塑造反面人物形象”“揭发抗战痼疾”“侧重道德虚伪性的揭发”1等方面的特色,而对于其在1940年代创作并刊行的诸多中、短篇小说,则几乎未曾提及。本文拟将重点放在后者,围绕黄药眠的小说集《暗影》《再见》及其诸多未收入集的小说,结合相关史料和文献,从文学史、社会史的面向,考察其四十年代小说的主要特色和价值,以期对黄药眠文学创作的研究,以及四十年代的文学史研究有所补益。
一
就目前笔者所收集的作品来看,黄药眠四十年代的小说,大都书写抗战爆发后位于粤东北的梅县及周边客家人聚居的社会。其中,直接涉及抗战题材的作品,主要有中篇小说《克复》和《热情的书》。《克复》刊于1943年12月1日桂林《文学创作》第2卷第5期,写沦陷区S县郊区的萧村,以萧寿为代表的青年反抗日军扫荡并克复县城的斗争。《热情的书》初载1944年1月1日桂林《当代文艺》第1卷第1期,是一篇由八封信组成的书信体小说,写军队在蜈蚣岭击退日军之后,S城附近相邻部队的古慕韩、碧澄这对恋人之间的通信,暴露了国民党军队中的丑恶现象和青年人的精神苦闷。结合作品的发表时间以及作家的实际经历,这两部小说所涉抗战题材,大体以1940年5月至7月间黄药眠与钟敬文、杨晦及抗敌文协干事郭弼昌一起采访粤北大捷,从当时的广东省会所在地韶关(曲江)往清远、从化、翁源一路的所见所闻为基础2。
以抗战为背景的作品,则主要有《李宝三》《古老师和他的太太》《暗影》《县长》四部中篇小说,以及《一个老人》《章红嫂》《小城夜话》《尼庵》等多部短篇小说。这些篇章主要通过刻画归来番客、中学教师、大学生、国民党基层官员、世家长老、劳动妇女、强盗头子、斋妇等各色人物,展现了抗战时期梅县及周边地区乡土社会各阶层人物的生活实景。中篇小说《李宝三》初载1944年3月10日桂林《文艺杂志》第3卷第3期,写的是欧战爆发以后,附城3的归来番客李宝三从风光无限到潦倒至死的故事。《古老师和他的太太》初载1946年2月1日桂林《文艺生活》光复版第2期,写因受日军轰炸波及,跟随学校搬到邻县福兴乡的省立高中古培仁老师,他的太太得了肺痨且失业在家,而他每周教课多达三十个钟头却无力养家,呈现了抗战时期底层教师艰难、绝望的生存状态。《暗影》为小说集《暗影》中的同名作品,1946年8月由香港中国出版社出版,以进步学生廖国宣、陈一谔为视角,展现了1942年间X战场战争吃紧的当口,国统区A学院动荡、混乱、堕落的校园实景。《县长》为小说集《暗影》中的一篇,主要写沦陷区附近的P县,以县长冯士怀为代表的国民党基层官员倒卖粮食、大发国难财的腐败行径。
短篇小说方面,《一个老人》刊于1942年10月15日桂林《文艺生活》第3卷第1期,主要寫在日军攻打洛城之前,林家的长辈傅叔公由于贫穷,无法带着家人逃难的困境和心态。《章红嫂》刊于1943年10月15日桂林《新建设》第4卷第10期,写的是农村妇女李阿昭嫁给章红之后,辛苦劳作二十多年,独子章英在抗战期间被拉去当兵,使她绝望、发疯并最终跳江自杀的悲惨故事。《小城夜话》初载1944年6月15日桂林《文学创作》第3卷第2期,写的是“我”在故乡广东期间,听兄弟洪子良讲述他往昆城经商途中遭遇强盗的奇遇。《尼庵》刊于1946年8月1日桂林《文艺生活》光复版第7期,写“我”在三十多年后重游故乡的净土庵,看到了尼庵的萧条,也回想起童年与小斋妇月痕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
实际上,诚如黄药眠指出,这些小说“是写我们家乡的所听所闻,但当时立意也只求写出一些气氛和情调……”1作者的家乡为广东梅县,古称嘉应州,是客家人的聚居地。据文献所载,古时的梅县是畲瑶土人的居住地,“客族初来,人数尚少,常常受土人的骚扰;元末畲种渐亡,流寓闽赣的客族,渐次迁来,至明朝全境遂为客族所有”2。此外,从地理位置上看,梅县东界大埔,西接兴宁,南连丰顺,北邻蕉岭、平远,东北端则毗连福建上杭,是一个山多田少、人口过剩之地,“故相率往南洋群岛佣工经商,其旅外男丁,几逾人口总数之半”3。因此,南洋成为梅县客家人的第二故乡,而梅县则成为中国著名的侨乡。
黄药眠四十年代的诸多小说,往往借助人物下南洋的经历或背景,再现了归侨、侨眷的独特地位,以及侨乡人民的生活面貌。在《李宝三》中,C城的富翁熊致祥就是一位从南洋发财回来的番客4,“他的肥短的手指上戴着三只戒指,黄豆般大的一颗钻石闪耀着,金表上的金链有筷子那么粗大。他在城里大街上一走过,在他后面就有不少的人闪着羡慕的眼睛……”而过番归来的李宝三出手阔绰,使得一向看不起他的李树明也不无艳羡地表示:“我一个高中生,在小学校教书,也赚不到什么钱,有机会倒真的想到南洋去走走。”《县长》中的邱志敏能当上参议员,也得益于十一年前“他在南洋爪哇做小摊贩,从小就学会了一副欢迎顾客的笑脸”。此外,在《章红嫂》中,章屋的骥叔公“因为近来他的儿子在南洋发了一点财,只一点点……所以他说起话来,章家人大家都是钦此钦遵”。在侨乡人民看来,下南洋是发财致富的捷径,以至于沦为鸦片烟鬼的章红哥,都要怪罪于章红嫂:“唔,如果不是娶到你这个衰家猫,我早就过南洋去发了大财回来呀……”
然而,下南洋的人就一定能发大財回来吗?实际上,下南洋的人多出自穷困家庭,虽富于冒险精神,但教育程度大多不高,去到南洋后,往往一开始只能从事割胶、挑锡等小工,有本钱经营买卖的人极少,客家山歌中所唱“日头似火热难当,挑担锡泥上跳梆,一身晒到锅底黑,心中苦楚谁思量”5,正是多数客家人初到南洋时的写照。因此,只读到小学三年级的李宝三去南洋八年,在那边干过各种小工,也没能发财,最终向人借了两千多荷盾,跑回了家乡。而章红嫂的堂兄李达荣,到南洋十几年后也未能行大运,因此他不仅惦记着祖母留下的二亩地,还让儿子小苍回来经营小饭馆。此外,《一个老人》中傅叔公的第二个儿子去了南洋,但他不仅没能发财,还病死在那儿。可见,并非所有下南洋的人都能发大财,更遑论能为家人提供足够的侨汇。
尽管如此,客家人下南洋的潮流仍然无可阻挡。以抗战期间的1940年为例,仅就梅县第四区松口区而言,“区内有六堡,共有人口十余万,出洋谋生者占十分之五,内地经济除靠农业供给外,全由南洋侨汇接济”1。正因如此,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导致侨汇中断,给地处内陆、生计不足的梅县人民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其情景如《李宝三》所叙:
不久太平洋战争发生了,这使到这一向在战争中繁荣的小市受到闪电一般的打击,每年几千元的侨汇断绝了。有钱的富佬,一下子变成了穷人,十有八九靠南洋汇款生活的,家人现在都口里喊着“怎么办呀!怎么办呀!”新起的洋房子里,住着袋子里没有一个钱的人,他们开始把箱子里藏着的毛毡、皮衣、反领西装,拿到故衣摊上去出卖了。
实际上,当时除了故衣摊,也有称为拍卖行的,常常摆着新的旧的衣物,也有翡翠、钻石一类的珍贵物品出售,可谓包罗万有,以至于“一般达官贵人,富庶之家,亦多到那里寻购珍奇的衣料实物,并不以到旧衣摊为不高尚,反之到那里或可以寻到稀世之珍,或便宜货”2。
而对于太平洋战争给梅县华侨带来的影响,四十多年后,黄药眠仍然印象深刻:
有些华侨回家来探亲,本来打算住个三两个月就回去的,但是路断了,不能回去了,他们初回来还是有钱的番客,逢人便送“利事”,但半年以后,钱就花光了,连回去的路费也用完了,甚至当番客以后积蓄下来的钱也用光了,于是只好脱下西装,穿上半新不旧的便服。有些人做些小买卖,有些人甚至连小买卖的本钱也没有了,只好出来做零工,做小贩等等。3
在此情形下,华侨学生的生活和心态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暗影》中A学院来自马来半岛彭亨的侨生萧衍庆,原本花钱慷慨且好献殷勤,是众人眼中的“大脚色”,但侨汇断了后,他反而要靠借贷度日,“从前对他非常亲热的几个女同学,现在也公然有时故意装着没有看见他,这使他很痛苦”。而《李宝三》中,从前在饭馆里吃一百两百元点心毫不在乎的侨生们,“有些到了旧历新年放寒假的时候,竟拖下了一千几百块钱账,悄悄地挑着铺盖溜走了”,真可谓落魄到了极点。
二
据黄药眠多年后回忆,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后,他回到了故乡梅县养病,直到1943年夏天离开。在故乡所住的一年多期间,他同那些旧时的亲戚、同学、朋友往来,“其中有养老的闲人,有乡村的中小学教师,有半学半商的绅士,有归侨,有商人,有机关工作人员。在同他们的闲聊中,我知道了国民党基层机关的腐败的内幕,学校中派系的斗争,穷教师的苦难。”由此,黄药眠看到了家乡的主要变化:其一是“侨乡的色彩更浓了”,其二是“商人的势力更大了”1。结合其四十年代的小说篇章来看,所谓“侨乡的色彩更浓了”,指的是由华侨所带回来的南洋殖民地的风情,包括咖喱、咖啡、饼干、冷饮、各式西餐、手杖、高跟鞋、毛毡、皮衣、反领西装等更为流行,以及西式桥梁、洋房等各种建筑大量涌现。而所谓“商人的势力更大了”,则不仅指商人地位的提高,而且指金钱或经济势力的崛起对侨乡人民的价值观念、社会风气乃至权力结构的冲击。
《李宝三》一开头,欧战爆发后,从南洋回到附城的李宝三出手阔绰,给李屋老幼派发礼金和礼品,俨然是个发了大财的商人,一度成为李屋的骄傲。然而当他很快败光钱财,且在南洋的底细被揭穿以后,便受到了大家的冷遇,“甚至有些人,一看见他走过,就吐一撮口水,来表示他的厌恶”。而当李宝三将来路不明的鱼和菜廉价卖给街坊邻居的时候,大家还都抢着去买,“有时为了便宜,还叫一二声宝三叔”。不唯普通民众如此,在金钱面前,当地的绅士、文人乃至女学生们也往往谄态百出。番客中的大富佬熊致祥在C城的大街上一走过,“在他后面就有不少的人闪着羡慕的眼睛……连在学校里读书的少女们有时也不免回过头来对这个财神投视一瞥多情的眼睛”。而在欢迎宴中,绅士、文人们都费尽心思巴结熊致祥,有个诗人恳求为他的诗集捐一万块钱的印刷费,最后所得“虽然不过十分之一,但也够他感激涕零了”。
实际上,金钱的势力不仅极大地影响了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它还左右了人心和尊严。据有关梅县的文献记载,抗战爆发后,物价飞涨,基层公教人员所受的影响尤其大:
无家庭负担的人,尚可勉强维持生活,数口之家的人,便无法维持了。这种生活上的苦闷,是无法解除的。然公教人员,不能眼睁睁看着家人活活饿死的,一方为了看见人家发财这么容易,不免见猎心喜,稍有机路的,就改行经商,或投入税务界做税官,较有油水可揩,藉以增加收入的也不少……2
除了另谋出路者,擅长投机钻营、巧取豪夺的公教人员和基层官员也大有人在,此类反面人物在黄药眠的小说中不胜枚举:比如《暗影》中,在宿舍附近开小饭馆“做起生意来比上课还认真”的商学院教师姚瑛,向学生推销西药的热情胜过指导学生的数学系吕姓教师等;比如《古老师和他的太太》中,将学校存款当成个人资产来实现“三油主义”(囤积汽油、豆油、花生油)的省立高中的胡校长,和学生合伙做生意还侵吞学生钱款的省立商业学校的田校长,以及虚报学生人头领空饷、做奎宁生意的师范学校的程校长等;比如《县长》中靠包赌台发财的区长冯老三,以撤职为要挟向中学校长索贿的教育科长萧凡,以及联合商会倒卖救济粮的县长冯仕怀等等。
虽说如此,彼时黄药眠小说刻画的重点,却是底层教师面对金钱势力和生活困境的无奈。《李宝三》中,高中毕业后当了教师的李树明,一向看不起才读了三年小学的阿宝三,可是现在却不得不高看他,只因为“现在他手里有钱呀!”《古老师和他的太太》中,由于物价飞涨,古培仁老师到处兼课却难以养家糊口,儿子古阿顺也辍学在家,引来病中的古太太火山喷发一般的怒斥:“唔!你也做工!老婆儿子都养不活,试问你做什么工!我如果是你,我早就拉黄包车去了!”古老师教书十多年的“坚守岗位”,在古太太看来也无非是“误了自己,还要去误别人”。无独有偶,《小城夜话》中的中学教员洪子良,由于收入低微,经常被妻子埋怨,不得不辞职,前往昆城做生意。而洪子良的大学同学陈子犹毕业后也当了教师,但两年前他的恋人密司曹抛弃了他,嫁给了昆城最大商号的老板,致使他愤而辞去教职,回到家乡落草为寇。成为“大哥”头子的陈子犹,不忘拜托洪子良到昆城给密司曹带话:“……你告诉她,我现在也不见得比他的丈夫没有钱呢!”对于陈子犹而言,金钱的势力曾使他遭受巨大的打击,但落草之后迅速积累的巨额财富,又帮他找回了自信和尊严。而结局最为悲惨的,当属《暗影》中A学院的中文教师杨学诚,在大家看来,“这样酸溜溜的穷教员去爱上一个文学院的密司,香港小姐,自然只好失恋上吊了……”
此外,物价的飞涨和金钱势力的崛起,也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侨乡人民的婚配观念。抗战爆发之前,受到“五四”以来婚姻自主之说的洗礼,教育程度较高的梅县男女一度视嫁人做侍妾为可耻之事;但自抗战以来,因生活动荡,梅县五方杂处,且受都市风气的影响,有不少女子以“能作英雄妾,勿作庸人妻”为意向,看重物质的思想观念兴起,以至于“嫁一个富商,做二奶三奶,也是常事,不足为异常了”1。黄药眠四十年代的小说,再现了彼时侨乡人民看重物质的婚配观念。《热情的书》中,女大学生素澄同一个跑滇缅路的司机结婚,两人文化程度相差明显,但她的母亲之所以允许,原因正在于,母亲要她读书,“无非也是想买一些资格,将来好嫁好丈夫。自然哪,现在汽车司机有钱,资格又合标准,还有什么不好呢?”同此道理,《古老师和他的太太》中,古太太的堂妹在联立中学当教务员,却怀了已有妻室的谷校长的孩子,结果不仅她愿意给谷校长做妾,古老师夫妇也乐于去帮忙说服她的老父亲,只因谷校长许诺为她的两个叔叔解决工作,同时要送古老师夫妇一块衣料。而《李宝三》中,绅士徐秀文一直盘算着要把即将高中毕业的女儿送给番客熊致祥做妾,他甚至早已拟好了说辞,寻思着找个时间去跟熊致祥说:“熊先生,小女虽是中等程度,但能够有机会伺候你老先生,那她一定会觉得十分快乐而且会觉得骄傲的!”
抗战的爆发使得金钱的势力日益强大,也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尤为复杂,一向不被人注意的方面,现在都由于金钱的因素得以凸显。《古老师和他的太太》中,古母在来信中控诉了小商贩的发迹和变坏:“从前我家隔壁做豆腐的蔡阿福现在发了财,专门放利,利息最高,要三分起码,甚至要三分半。这些人没有读过书,做起事情来,真是毒辣,刻薄。”而《热情的书》中的几个乡下人,更是把救人生命当作发财的买卖:有个叫阿桂的外村人在深潭里溺水了,擅长游水的阿宝等三个本地村民,坚持要价三百块才肯下水救人,导致阿桂在水里淹得太久,虽然最后被捞了起来,却没能救活。此种看重物质、贪图金钱的社会风气,诚如作者在1946年初发表的组诗《街,商品》中所慨叹:“一切都变成了商品,商品。”“一切都被推送到市场上去陈列!”2
金钱的势力不仅影响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甚至决定了个人的命运。《章红嫂》中,乡长对穷苦的章红嫂声色俱厉,硬要抽她的独子章英去当兵,而对隔邻富有的陈大爷家两个正当年的儿子,则只字不提征兵之事,并且极尽恭维之态。结果,章红嫂被迫四处借钱,好不容易筹集了缓役金,却在交纳前被偷了,章英最终被拉上了战场。必须指出的是,章英的结局不仅表明了彼时金钱对于个人命运的决定作用,而且再现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征兵过程中的腐败。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由原来的募兵制度改为征兵制度,征兵业务由军政部统辖,其最基层则为乡保甲。但在实际征兵过程中,全国各地方的军政部门或乡保长经常趁此勒索,由此导致的兵役舞弊可谓层出不穷。仅据兵役部督察处统计,1942年10月15日至1944年11月短短两年间,兵役舞弊案就多达11380件;即使在抗战末期的1944年10月15日至1945年8月间,兵役舞弊案也有2719件1。同一时期的社会调查则表明,在当时的广大农村中,如果一个略有资财的农民不按指定日期准时把应征的儿子送来,他就会被逮捕入狱,但这农民如果送上贿赂,他的儿子就免去兵役2。而实际上,在当时的梅县,“亦有家庭富裕出资买人顶替的,虽为法所不许,亦在所难免”3。有鉴于此,让章红嫂失去儿子的主要原因,与其说是因抗战而起的征兵制度,不如说是在催收壮丁过程中贫富的差距、金钱的势力所导致的实际不公。
三
当然,章英的结局,也与李、章两个世家的没落有关。关于李家,小说写道:“章红嫂在李家兄弟叔伯是很少的。她的父亲是一个穷秀才,七岁时候她的父亲和母亲都死了,只由一个祖母抚育她长大。一个堂兄达荣很小的时候就到南洋去,七八年沒有消息。”李家的没落,加上刚嫁到章家半年内公婆双双去世,使得章红嫂头三年在章家受尽了敌视和咒骂。而当儿子章英被乡长宣布抽中兵役时,章红嫂跑到李家堂侄小苍那里去寻求帮助,得到的回应是:“‘照理,独子不应该抽兵役呀……小苍沉吟着说。但当章红嫂要他去见乡长,他又不敢去了,他说:‘总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作为李家人,除了借一百块钱给章红嫂准备交缓役金外,小苍没能给她更好的帮助。
而章家呢,当章红嫂四处借来的一百五十元钞票被偷之后,无论丈夫章红,还是章屋的其他人,全都难以指望:
现在这个章屋已经是没落中的世家,老辈是已经死光了,超叔公的儿子,早就把身家用得精光,后一辈的人,大多数是做生意,经营小贩或是在机关里做小吏,又有谁敢去同乡长说话呢?即使有些亲戚,能够做到,但谁又肯为这个章红嫂,一个挑担脚的妇人,去奔走,去向上级机关据理力争呢!
概而言之,征兵过程中的腐败,章红嫂的贫穷,李、章两家的没落以及族人的冷漠等等因素,最终使得章红嫂哭告无门,儿子章英被拉上了战场。
从历史上看,客家人本是住在中原地区的汉族,汉末东晋南宋的时候,因避乱南迁,初到江西和福建,后来又迁移到广东、广西和四川等地,所以又称为“客族”。因为所处地方自然条件艰苦,交通闭塞,要生存就得力耕,要发展全靠苦读,所以,客家人形成了“耕读传家”的传统。此外,由于深受中原儒家文化的影响,客家人往往以读书致仕为追求,正所谓“读圣贤书,学而优则仕,这是客家人的骄傲”1。因而,即使在抗战时期,“仕官之家”“世代书香”之类仍然为老一辈客家人所珍视。在《一个老人》中,林家的傅叔公出身于仕官之家,“他的祖父是前清的举人,做过知县,他的父亲也是举人,而他自己则仅仅比祖父、父亲差一点,是一个秀才。”在《古老师和他的太太》中,鉴于古老师一家“五代书香,代代相传都是读书人”,他的母亲不仅希望古老师能发扬光大先人事业,也期盼孙子“能继承祖父、父亲做一个读书人”。而在《克复》中,一个日本兵在村口被杀,当鬼子军官和汉奸威逼萧慕春交出儿子萧寿时,萧慕春坚称:“我们书香之家从来也不会……做这些事!”
然而,世家的崛起或没落,往往与家族子弟为官的数量、等级及其所掌权力、社会地位的具体变化密切相关。换句话说,对于读书致仕的热衷,某种意义上也是客家人权力崇拜的表征,即如作者后来写道:“我们的民众并不是欧美的群众,还有很深的封建传统,有天子皇帝传下来的英雄崇拜、权力至上”2。对此,黄药眠也屡屡在小说中予以揭示:《热情的书》中,碧澄所在军队驻扎地的村中学校,用的国文课本仍然是宋代吕祖谦为方便诸生参加科举考试所作的《东莱博议》;《章红嫂》中章红哥的观念则停留在科举取士的时代,他反对儿子读书的理由是:“怎么的?你想将来把你的儿子送上京去中状元吗?”《一个老人》中的傅叔婆,最近十多年把全部的希望都放在仅存的幺儿子林基瑞身上,“最先是希望他快快长大,以后送他入高中,又希望他快快毕业,毕业以后,能获得一官半职”。而现实中,即便在实行征兵制的抗战年代,梅县人民“多不愿当兵,而喜做官,富领袖欲。故各部队宪警来梅招考干部人员,莫不踊跃报名,考验结果,多被取录……”3因此,在黄药眠彼时的小说中,侨乡人民眼中的“出息”,首先是做官,其次是经商,而教书则常常被视为导致家庭经济困难的根源。比如《李宝三》中,姚淑婆说她早就相信李宝三总有一天会发达,其根据是“他走路也就像个官坯子!”李宝三为了吹嘘他在政府里有门路,则说“做生意也没有什么意思,我现在常常到党部里去!”《古老师和他的太太》中的古老师到处兼课仍然无力养家,他的表弟董志学“不大相信读书”,却当上了权力比县长还大的民政厅视察,相比之下,古太太觉得“真是前生作了恶才会嫁到这样的读书人!”而《小城夜话》中洪子良的妻子则嫌弃丈夫收入低微,整天对人说:“哎唷,教什么鬼书!早就应该做生意呀,你看宝叔!”不难看出,在彼时董志学、古太太、洪太太等人的眼中,当“读书”不再是“致仕”的捷径,且“教书”已成为贫穷的根源时,传统的“书香之家”也就到了弃之如敝屣的关口了。
不唯如此,诚如黄药眠晚年指出:“由于经济上的困难,也就造成了人们在思想上更势利。一些过去的封建道德传统都变成了空壳,没有内容。”4实际上,变成空壳的不止于封建道德传统,也包含了乡土社会原有的权力结构、教化观念等。按照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出的观点,中国乡土社会的权力结构,其实更为确当的是一种称之为“长老统治”的结构,这种结构遵循的原则是长幼之序,具体实施方式则是每一个年长的人都握有对年幼的人强制教化的权力——“出则悌”——年幼的人逢着年长的人都得恭敬、顺服于这种权力1。据此而言,族中辈分最高、年龄最长的人,往往拥有最高的教化权力。即使是在抗战时期,在中国的广大地区,尤其是华南地区,仍然保留着聚族而居的社会结构,而在这种社会结构当中,族中长老大多处于威望甚或权力的顶端,“凡本族一切内部或外部的问题,都靠他们去解决去对付”2。甚至在某些地方,族长的权力不在县长之下。1940年,黄药眠以客家人的另一个聚居地广东翁源县为例指出:
在翁源,族长的权力是很大的,乡长保甲长要听他指挥,县长要俯顺他们的“舆情”,新县长来上任,首先必得去拜候他,听他们的意见,如果一个新县长想推行一些他们所不赞成的新政,那好了,他们袋子里早就拟好有控告县长的状词了,他们或是故意做出一些难辨的案子,或是捏造出一些事实,或是强迫各乡长联名辞职。在南浦的两间当铺里早就存好了三五千块钱,作为同县长打官司的资本。3
而在家族内部,家长或者族长的地位让人敬畏,同时也令人向往。在《李宝三》中,李宝三从南洋回来之后,就单独包了五百块钱讨好李道先这位族里最年长的人,此后还经常隔三差五地给他孝敬猪蹄膀。而在《章红嫂》中,章红嫂刚嫁到章家不久,骥叔公因为近来儿子在南洋发了一点财,他开始以族长自居,甚至打算利用族长的威望将章红嫂赶出章家。
然而,随着抗战的爆发,经济的困顿和仕官之家的没落使得族长、世家长老的权威遭遇了危机。小说《一个老人》生动地展现了林家的长辈傅叔公的这一境遇:
他虽然靠着先人的余荫,能够有机会在乡下人和衙门中间行走行走,可是近十多年傅叔公的家道的确是不大好。第一个儿子于刚进大学的时候,患肺病死了;不久,第二个儿子又在南洋病死了,现在只還剩下第三个儿子,吃机关饭吃了六七年,现在也还不过是一个上尉军需。因为他的儿子没有很快升官,也就连带影响到他傅叔公的长辈地位的一天天的衰微。从前在外头做过县长的,做过洋学生的,发过财的绅士,逐渐加多,傅叔公已渐渐的被人升格升到老臭之列。他眼看着他自己同屋的侄孙辈,做县长的,做处长的,而自己的家道却一天天穷,因此他常埋怨到自己的儿子不会做官。
按照费孝通所说,在乡土中国“长老统治”的权力结构中,当文化不稳定,传统的办法并不足以应付当前的问题时,教化权力必然很快跟着缩小,缩进亲子关系、师生关系中4。换句话说,正是家道的中落,经济的窘迫,留洋学生的受青睐,以及商人势力的崛起等因素,导致了傅叔公长老地位的衰微,使得他的威信已然不足以对整个林氏家族发号施令,而仅能指挥得动自己的老婆和儿媳妇了。因而,在是否搬家以便于躲避日军这一件事上,尽管侄孙辈们不来征求他的意见,“各做各的”,“有钱的只管自己”,傅叔公对此也无可奈何。
另一方面,战争的爆发、生计的困顿冲击着乡土社会原有的观念和秩序,而当金钱和利益成为主宰力量,一切都变得可交易的时候,长老教化的威信也就渐趋式微乃至荡然无存了。《李宝三》中,李宝三每天大鱼大肉惹得周围的人眼红,以至于道先叔为此大不高兴:“唔,阿宝三,逞袋子里有两个钱,每天这样大鱼大肉地吃,就是万户也不是这样吃法!一个人也总要留一点福给子孙享享……”一般而言,李道先本该就此教育阿宝三,但实际上,他的不满很快就消失了,因为“李宝三到了初二那天,买了一只鸡四两酒,请道先先生过来大大地吃了一顿。而且告诉他,以后每个月初二,十六都要请他过来吃饭,于是他抹抹嘴唇,什么话也不说了。”对于李道先而言,相比颇费唇舌的教化而言,轻松到嘴的酒肉显然更为重要。也正因此,对于后来李宝三的沉迷赌博,乃至近于“奸淫邪道”(把来路不明的妇女领回家做老婆)等足以被实施“出族”1惩罚的行为,李道先则奉行“只要阿宝三在他面前不会忘记孝敬,他一切都可马虎”的宗旨。然而,李宝三把家败光之后,李道先为了得到他的两间空房子,“于经过一番假装的沉吟以后,他就决定放弃阿宝三每个月所孝敬的蹄胖,而把假的契纸都做好了。”而当李宝三被警察抓去关了三个月,像个叫花子爬回来的时候,也正是作为长辈的李道先,咬牙切齿地挥舞着手杖,带领族人把他赶出了李家的大门。
四
战争所带来的动荡和贫困,对侨乡妇女的冲击尤其巨大。这种冲击不仅作用于她们的日常生活,而且波及她们的精神世界。在梅縣,妇女是家庭生活的主力,诚如1941年出版的《梅县要览》所载:“妇女差不多已成为乡村的主要人物。因为梅县的男子多出外谋生的,妇女因为家里丈夫走了,养成了一种独立生活的艰苦[卓]绝的伟大性格。”2事实上,客家民谚中有关妇女的“四功”,即“家头教尾、田头地尾、锅头灶尾、针头线尾”,说的就是侨乡妇女不论养育子女、耕种、家务、女红等样样都是能手。然而,作为家庭主要劳力和乡村社会主要人物的侨乡妇女,其在家庭和族群中所得到的尊重,却远远比不上她们的实际付出。其中的主要原因,也是侨乡家庭的特色之一,即不少妇女只是作为男人所娶的“屯家婆”。所谓娶“屯家婆”,乃是“有些华侨在家乡有父母等亲人,在侨居国亦有妻室,但他挂念双亲,欲继承祖业,传宗接代,便在家乡娶‘屯家婆”,“有的人娶亲之后从不回乡,他们名为夫妻,实终生从未谋面,妇女含辛茹苦度过人生,精神上受到极大的摧残”3。
然而,不管是否作为“屯家婆”,大部分侨乡妇女在家庭和家族中的实际地位都十分卑微。在黄药眠书写侨乡社会的小说中,无论丈夫是否下南洋,已婚女人的称谓,无一不冠上了丈夫的姓氏或名字,以此显示妇女对于男人的附属性,如《章红嫂》中的章红嫂、阿英嫂、勤嫂子、章杞嫂、章柳嫂,如《克复》中的福来嫂、萧伍嫂、廖辛嫂、富民嫂,如《一个老人》中的傅叔婆、阿基嫂,如《李宝三》中的宝三嫂、任嫂子、风嫂子等等。此外,妇女经常被视为不祥的征兆。章红嫂嫁到章家半年之内,公公和婆婆先后去世,“所以章家的人都说章红嫂入门的时辰不利,命中带来了煞星,他们都骂她,说她是衰家猫。”骥叔公甚至觉得他老婆之死也一定和章红嫂嫁到章屋有关。实际上,此类充满迷信色彩的成见一直流行于梅县民间,最为典型的是乡下的大人经常告诫孩子不要从妇人的胯下和裙裤下钻过,否则会有两种损失:第一是小孩身体不会再长高了,第二是小孩子读书识不了字了1。再者,由于在家族中地位低下,妇女后事的处理也有诸多禁忌,《李宝三》中宝三嫂的遗体只在大厅里停了几个小时,李宝三就遭到了道先叔的威吓与训斥,以及“同屋住的人都翘着嘴唇骂”。
在黄药眠四十年代的小说中,侨乡妇女在家庭和族群中地位的卑微,与客家人要求女性“三从四德”“勤俭持家”的传统观念密切相关。《章红嫂》中,在李阿昭出嫁前,祖母反复叮嘱她:“你要孝顺亲家的父母,就同自己的父母一样,你要服从丈夫,不要好食懒做……要能吃苦,要能受气,对大人的说话你不要应嘴……”嫁给章红后,章红嫂谨守祖母教诲,不仅每日起早贪黑地劳作,而且对于一切责骂都忍气吞声。当章红哥成了鸦片烟鬼后,为了养育儿子,章红嫂出去当挑脚工,却又被骥叔公等人视为破坏了世家的规矩:“我们章家是老世家,谁不知道?女人家也出去挑担,这是羞祖羞宗的事情……”女人只能在自家的屋中、地里劳作,是侨乡人民的传统观念。正因如此,在《热情的书》中,对于女孩子在外抛头露面,乡村学校的教书先生认为是“‘牝鸡司晨,哪得不乱!”而《一个老人》中,傅叔公也感慨:“唔,这真是国家将亡的现象,连妇人家也要在衙门里走出走进!”甚至《李宝三》中,李宝三夫妇在傍晚携手到河沿边散步和唱山歌,也都惹来李氏族人的咒骂。
实际上,在一些客家人聚居的地区,人们对于妇女人身自由、言行举止的限制尤为严苛。据黄药眠指出,在广东省翁源县,“男人们虽然尽量可以在外面放浪,然而妇人们却绝对不能和外间的男子通话,有时就连丈夫的朋友都包括在一起”,一旦妇人们犯了戒,就会受到族人拳打脚踢乃至挖去双眼等惩罚,“因为这是家法,连她的丈夫都出不了主意”2。如此卑微的地位,使得客家妇女即便操劳一世,也无法改变她们痛苦的境遇和命运。章红嫂自从嫁到章家,“没好吃没好穿,做生做死还要受气,一走过人家的房门,大家都吐着一撮口水……”就连丈夫章红变得好吃懒做乃至沦为鸦片烟鬼,族人都要怪罪于她。而她的儿媳阿英嫂,虽然不再有人骂她是“衰家猫”,却也仍然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当章英被拉去当兵不久,阿英嫂就被陈家人抢去抵了章红哥欠下的四百元债。实际上,章红嫂、阿英嫂们的命运,正是彼时中国农村女性的缩影。1948年,在以“番茄”为笔名发表的《洗衣妇》一诗中,黄药眠通过洗衣妇的心声,不仅展现了农村中抓壮丁的场景、洗衣妇四季洗衣的劳累,而且控诉了富家子“整天‘油头粉脸,装疯逞野,存心勾引”3对洗衣妇的骚扰与欺凌。不难看出,抗战虽然胜利了,但侨乡妇女所承受的痛苦,丝毫未曾改变。
这种无从摆脱的痛苦和无法掌握的命运,使得侨乡妇女转而从精神上寻求慰藉,即如作者记忆中的母亲那般迷信,殷勤跪拜各种神明,“甚至离我们家门很近的土地公公、土地婆婆的木牌子,她每逢初一、十五也都要去烧香跪拜”1。尤其在物价飞涨的战争年代,生活愈加穷困,个人的吉凶祸福难料,更使得不少侨乡妇女到处求神问卜,聊以慰藉心中的苦闷和惶恐。为此,她们不惜将自己挣来或南洋汇来的钱拿去买香纸,送到庵庙里去,以至于一度造成“全县庙宇庵场,统计大小共有两百余所,僧侣斋妇约计一千余人,日常庵庙一切开支以及和尚斋妇尼姑之生活,皆仰给于全县之一般妇女”2这样的局面。当然,在黄药眠四十年代的小说中,热衷于求神问卜之人,除了普通家庭妇女,也包括族中长老、政府官员乃至读书人,比如《一个老人》中信奉土地伯公的傅叔公,《县长》中信奉定光菩萨的冯县长,《古老师和他的太太》中信奉药师菩萨的古老师夫妇等等。不惟如此,彼时的侨乡堪舆之学盛行,人们往往把个人的兴衰浮沉归因于风水、命水等因素,比如:《李宝三》中的温姓后生,一开始将李宝三发财回来视为李家“风水转运”的结果,而李宝三后来也将输光身家归于“命歪,和我李姓的风水不好”;《一个老人》中的傅叔公因家道中落,“也曾相信堪舆先生,认为风水不好,把祖父的墓改葬了一次”;《克复》中的萧寿带领游击队消灭了鬼子小队,村民们也归因于萧慕春“他家父亲的风水好,他的后代大有发达呢!”而《章红嫂》中章红嫂的悲剧,章柳嫂等人认为她“真是命水不好,什么做生做死也没有用呀……”
实际上,侨乡人民的求神问卜和迷信风水,就如同中国其他地方民众的信仰一般,大都染上了功利的色彩。当章红嫂在绝望之际扮起了仙姑,假装驱邪赶鬼之际,附近的乡民都将她当作“莺莺娘娘”附体,跪拜于她的脚下,目的是求得“法水”给家人治病。而章杞嫂之所以热心充当托客,以证明“莺莺娘娘”确实灵验,也无非是在每次“显灵”结束,她扶着章红嫂进屋时,有机会“捡取她袋子里的钱”。此外,《一个老人》中的春叔婆每天总有两三次站在土地伯公神龛面前,喃喃不休,乃是因为“她不仅烧香,祈祷,问事,决策,而且她简直把土地伯公当成她自己的朋友,她向它发泄愤怒,申诉痛苦,表示自己的希求”3。冯仕怀县长之所以信奉定光菩萨,则是因为他将老婆顺利生子、自己落水后侥幸获救以及嫁女儿之后他顺利当上县长,都归功于定光菩萨的显灵。而古培仁老师信奉药师菩萨的神方,则是为了保留希望,因为一旦承认太太得了肺病,“那岂不是又要吃药、打针、营养,花许多钱吗?那岂不是什么希望都完了吗?”或许由于掺杂了太多的功利因素,侨乡人民的信仰或迷信,已然失却了该有的庄重与敬畏。《尼庵》中净土庵里佛像市侩、陈腐的气味,以及斋妇势利、冷漠的表情,显示的不仅是农村经济的萧条,更是佛教尊严的没落。《一个老人》中的芳嫂子,在日军攻打过来的前一天,从土地伯公那里求得的答案是不要走,然而第二天一早她仍然打叠了行李离开,这使得春叔婆咒骂道:“唔,这是神明呢!怎么好骗神明呀!以后天理要罚!咄咄!唔!这些无神无鬼的!”而《热情的书》中,擅长游水的乡下人由于贪财,迟迟不肯出手救援,导致落水人最终溺亡,他们却说这是水鬼拖脚的缘故,把责任推给了水鬼作祟。
五
在黄药眠四十年代小说书写的侨乡社会中,与功利的迷信相伴随的,是通常所谓客家人“狭隘的团体意识”1。《章红嫂》中的阿英嫂被几个陈家的男子抢上轿,要去抵公公章红哥欠下的四百元债,此时章家族人的反应是:“‘怎么到我们章屋抢劫人来……四五个人一齐赶了出去。”而在《李宝三》中,当李树明向父亲李道先转述温姓人传来的消息,说李家有钱番客李宝三“在外头是在妓院里当茶房”时,李道先虽然感到震惊,但想到这可能是温家的恶意造谣,就告诫儿子说:“英雄不论出处……你们年轻人更应该学到隐恶扬善……”由此,李树明顿时醒悟,感到“那温某亦是太可恶了!”对于习惯聚族而居的客家人而言,在涉及族群利益时,族人的齐心协力和一致对外,既是基于血缘亲情的本能反应,也是出于维护族群这个“共同体”的理性抉择。
此种“狭隘的团体意识”,实乃客家人应对异姓族群之间的龃龉或敌意时的集体表征。诚如朱希祖指出:“广东之客家,不与其土著之民相龃龉,乃与其临近先来之客相龃龉,先来之客,忘其己之为客,而自居于主……”2换句话说,广东客家不同姓氏、族群之间的龃龉或敌意,其来有自。而呈现客家族群之间的龃龉或敌意,也是彼时黄药眠小说的着力点之一。在《古老师和他的太太》中,蔡阿婆听说地里的萝卜和番薯被古老师的儿子偷了,就认定这是古家人的强蛮行径,故而她一边威胁着要叫警察来抓贼,一边咒骂道:“老实说,我蔡家也不是好欺负的。现在让你们吃了我的萝卜,发瘟,屙痢,死三代!……”《章红嫂》中,异姓族群的敌意不仅有章家人对李阿昭(章红嫂)的孤立,更有陈家人对章家人的落井下石——催抽壮丁的乡长刚走出章红嫂的家,隔邻陈大爷的儿子就特意提醒他:“这章姓有不少的壮丁呢,不妨多抽几个呀!”而在《李宝三》中,温姓人的敌意则一直伴随着李宝三的浮沉。听李树明说李家出了个有钱的番客后,一个温姓后生鄙夷道:“‘啊,就是阿宝三,从前每天挑着篮子卖麦芽糖的!那人特别着重卖‘麦芽糖三个字。”李宝三在南洋的底细被番客熊致祥揭開之后,温姓绅士则满心欢喜,“因为他觉得他的邻居李姓出了一个有钱的番客,实在是对温姓人的一个最大的威胁”。而当李宝三因赌博败光财产以后,温姓人更加不屑地说道:“唔,什么番客,原来是流氓赌棍啊!”最后,当李宝三在桥头泰兴饭店打工时,路过的温姓人都会挤眉弄眼地嘲笑:“又说李家出了番客,但现在番客在替人当小工……”其幸灾乐祸的心理溢于言表。在谈到四十年代故乡梅县的社会特征时,黄药眠指出,“社会的基本内容即特质则没有变化,而风俗习惯、语言更没有变化”3,而其诸多小说所展现的异姓族群之间的龃龉或敌意,正是彼时侨乡社会不变的“特质”之一。
耐人寻味的是,多年后回顾这批小说时,黄药眠感慨道:“我很惭愧,由于生活环境的局限,地区的局限,我没有写出这个时代的积极性的人物。”4这是作者的自我反思,但并不意味着事实就是如此。实际上,在1948年2月出版的《抒情小品》后记中,黄药眠谈到,在1941年至1944年正值大后方民主运动低落的时期,自己在故乡“除了闭户读书外,很少活动,也很少和外间接触,因此写起文章来也充满着知识人的忧郁的调子。”1这种忧郁的调子,究其原因,一方面源于作家本人的出身、阅历和气质,诚如彼时黄药眠在《论忧郁》一文中指出:
怎能够不忧郁呢?自己所出身的家庭是一天天破落了,自己虽然受过了良好的教育,可是并不容易找到职业,商品经济一天天深入,而恰好这些出身于破落的书香之家的子弟又偏不善于应付这样的一种风尚,所以生活一天天贫穷,加以事业被摧残,所谋多不遂,思想被统治,言论不自由,怎能够不忧郁呢?眼看着国家民族的地位一天天低落,人民的生计一天天穷蹙,贪官污吏这样纵横,豪门财阀这样独霸天下,眼看自己的朋友在穷困中没落,亲戚在迫害中死亡,谁要是有一点感情,谁也会感到心头的重压,可是知识分子,虽然目击着这些,但又深深地感到自己的缺乏力量,这一种意识自然就可以加深了忧郁的病症。
因此,在黄药眠看来,忧郁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阶级的病态,尤其对于站在最前列的文艺战士而言,“他们的灵魂时常受到忧郁的苦恼,他们的文章自然也难免忧郁的调子”2。另一方面,这种忧郁的调子,也源于当时作家所处的恶劣环境:“但据朋友们从桂林来信说,那边的情形不好,时常有人失踪,文章常常被扣,连原稿都不能拿回来,所以叮嘱我写东西的时候千万要考虑到如何通过国民党检查官的眼睛”;“在这样四面八方压迫之下,构思的时候就不免总是极力设法避开正面去处理什么问题”3。有鉴于此,在《章红嫂》中涉及农村征兵腐败时隔靴搔痒般的描写,在《热情的书》中试图暴露国民党军队中丑恶现象时的欲言又止,乃至在《淡紫色之夜》中对于英国水兵的在华兽行“只从侧面轻轻地描写一下”4等等,与当时的主流抗战文学相比,对于那些重要且敏感的“问题”,黄药眠小说中过于曲折迂回、轻描淡写的笔法也就不难理解了。
然而,正如作者在1939年底发表的《中国化和大众化》一文中指出,如果作家能够留心最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写“中国土生的农民”,写“真正的中国人物”,把他们的生活态度、习惯、姿势和语言,加以选择和淘炼,如实地写了出来,“那么他这个作品一定是中国化的,同时也是大众化的”5。从实际来看,黄药眠四十年代的小说,以梅县及周边地区的归侨、中小学教师、农村妇女、绅士、商人、基层官员、养老的闲人等为刻画对象,写出了客家侨乡特有的气氛和情调,既是彼时其小说创作在题材选择、人物塑造方面的基本特色,也是其文艺上“中国化和大众化”理论主张的具体实践。
此外,就小说题材而论,黄药眠书写故乡见闻的《李宝三》《小城夜话》《章红嫂》等作品,可以归入鲁迅开创的“乡土文学”系列6。而关于“乡土文学”的评价问题,茅盾早在1936年就指出,决定“乡土文学”价值的,并非在于其“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而是在于作者必须将那片土地上的人“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运命的挣扎”展示给我们1。若以这个标准来看,在黄药眠这批书写乡土的小说中,其人物并不缺少“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运命的挣扎”:《章红嫂》中的章红嫂不甘于向生活屈服,不仅敢于反抗世家的规矩去当挑工,而且冲破丈夫的阻挠,竭尽所能供儿子读到初中毕业;《小城夜话》中的陈子犹在遭受金钱打击后不甘于向生活低头,毅然落草为寇,由此迅速积累了财富;《克复》中的萧寿、廖昌等青年,在面对日本鬼子和汉奸的淫威时,突破了异姓族群之间的壁垒,联合起来消灭了敌人……而在小说中选择并刻画这些与命运抗争的人物,恰好展现了彼时作者所主张的“文艺家的倾向性”:
文艺家的倾向性是在于文艺作家能根据自己的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去观察这个世界,并凭着这个世界观和人生观去接触形象,选择形象,排列形象,在他的作品世界里布满着这样的一种氛围,使人们读过以后,能够有很大的感动,而跟着著作者趋于同一的倾向。2
进一步而论,黄药眠四十年代的乡土小说,不仅堪称写出了那个时代“积极性的人物”,而且挖掘出了人物直面生活磨难的“勇气”“决心”和“爱”——比如李宝三在穷困潦倒时不避非议并大胆恋爱,比如《暗影》里的大学生刘淙、陈一谔、廖国轩决心退学并用自己的手来创造一个新的世界,比如“大哥”头子陈子犹在劫掠时仍然顾念同窗旧谊,比如同样穷苦的章柳嫂几十年间对章红嫂不计回报的关心与帮助等等——而这些,正是身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黄药眠所讴歌的中国人民“宝贵的灵魂的光辉”3。也正因如此,作者后来承认,虽然当时他的创作难免于忧郁的调子,但“忧郁并不是悲观和失望……”而且,他相信,此时正是“放下个人的牧笛,吹起群众给予我的号角”4的时候。就此而言,黄药眠四十年代创作的乡土小说,虽难免于忧郁的调子,却也是身处艰难时世的作者竭力吹响的战斗号角。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1 参见拙文《黄药眠创造社时期的小说创作》,《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2 《暗影》,署黄药眠著,香港中国出版社1946年8月出版,内收《古老师和他的太太》《县长》《陈国瑞先生的一群》《暗影》四篇小说;《再见》,署黄药眠著,香港群力书店1949年2月出版,内收《再见》《热情的书》《淡紫色之夜》《小城夜话》《李宝三》五篇小说。多年以后,黄药眠从这两个集子中挑出《陈国瑞先生的一群》《重逢》(即《再見》)《淡紫色之夜》《古老师和他的太太》《暗影》五篇,编为小说集《淡紫色之夜》,由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4月出版。
1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下册(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版)第90页;唐弢、严家炎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37页;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5页;朱栋霖等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00》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278页。
2 钟敬文:《〈战地报告文集〉序》,《钟敬文全集》第21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第174页;另见黄药眠《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500—512页。
3 这里的“附城”是客家话的说法,意为“城郊”,即靠近旧时梅县县城的地区。在此特向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2022级梅州籍博士研究生刘璐及其家人致谢。
1 黄药眠:《〈再见〉作者自序》,群力书店1949年版。
2 杨梅、钟恕编:《新梅县地理》,新时代书店1932年版,第6页。
3 广东省民政厅编印:《广东全省地方纪要(附图)》第二册,东明印务局1934年版,第47页。
4 广东韩江一带的俗话说往南洋是“过番”,南洋回来的华侨俗话叫做“番客”。
5 佚名:《过到番邦更加难》,广东省梅县地区民间文艺研究会、梅县地区群众艺术馆:《粤东客家山歌》(内部资料)1981年编印,第153页。
1 谢复生编:《梅县要览》,新中华书局1941年版,第38页。
2 黄文英:《抗战八年来的梅县社会回顾》,中国复兴文化社1948年版,第106—107页。
3 黄药眠:《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571—572页。
1 黄药眠:《〈淡紫色之夜〉后记》,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88页。
2 黄文英:《抗战八年来的梅县社会回顾》,中国复兴文化社1948年版,第108页。
1 黄文英:《抗战八年来的梅县社会回顾》,中国复兴文化社1948年版,第148—149页。
2 黄药眠:《街,商品》,载桂林《文艺生活》光复版第1期,1946年1月1日。
1 兵役部役政月刊社编印:《抗战八年来兵役行政工作总报告》,兵役部役政月刊社1945年,第105—107页。
2 周荣德:《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一个社区中士绅身份的研究》,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63页。
3 黄文英:《抗战八年来的梅县社会回顾》,中国复兴文化社1948年版,第10—11页。
1 曾祥委:《田野视角:客家的文化与民性》,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56页。
2 黄药眠:《黄药眠口述自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23页。
3 黄文英:《抗战八年来的梅县社会回顾》,中国复兴文化社1948年版,第10页。
4 黄药眠:《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572页。
1 费孝通:《乡土中国》,观察社1948年版,第70—75页。
2 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138页。
3 黄药眠:《翁源风俗小纪》,载桂林《中学生战时半月刊》第30期,1940年9月5日。
4 费孝通:《乡土中国》,观察社1948年版,第74页。
1 曾祥委:《田野视角:客家的文化与民性》,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6页。
2 谢复生编:《梅县要览》,新中华书局1941年版,第22—23页。
3 王华:《客家侨乡习俗的形成和发展》,邱权政主编:《客家民系研究》,中国工人出版社1992年版,第62页。
1 嘉应民俗学会编:《嘉应风谣全集》,嘉應民俗学会1931年版,第126页。
2 黄药眠:《翁源风俗小纪》,载桂林《中学生战时半月刊》第30期,1940年9月5日。
3 番茄:《洗衣妇》,载香港《新诗歌》丛刊第7辑,1948年2月。
1 黄药眠:《我的母亲》,李渔村、彭国梁编《中国当代文化名人亲情散文选》,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456页。
2 谢复生编:《梅县要览》,新中华书局1941年版,第21页。
3 这里的“土地伯公”即土地神,为潮州、梅县一带的称谓。参见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276页。
1 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希山书藏1933年版,第277页。
2 朱希祖:《〈客家研究导论〉序》,收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希山书藏1933年版。
3 黄药眠:《〈淡紫色之夜〉后记》,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89页。
4 黄药眠:《淡紫色之夜〉后记》,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89页。
1 黄药眠:《〈抒情小品〉后记》,文生出版社1947年版。
2 黄药眠:《论忧郁》,载上海《大公报》,1949年5月4日,第4版。
3 黄药眠:《〈再见〉作者自序》,群力书店1949年版。
4 黄药眠指出,《淡紫色之夜》“是写战前香港的,因为(英国)是战时的盟邦,所以不能不特别客气,只从侧面轻轻地描写一下。”参见黄药眠《〈再见〉作者自序》,群力书店1949年版。
5 黄药眠:《中国化和大众化》,载香港《大公报·文艺副刊》,1939年12月10日。
6 参见拙文《论黄药眠小说〈李宝三〉的文学史意义》,《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1 蒲(茅盾):《关于乡土文学》,载上海《文学》第6卷第2号,1936年2月1日。
2 黄药眠:《文艺与政治》,见黄药眠《论诗》,远方书店1944年版,第151页。
3 黄药眠:《从泥土里生长出来的》,载香港《小说》第1卷第5期,1948年11月1日。
4 黄药眠:《〈抒情小品〉后记》,文生出版社194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