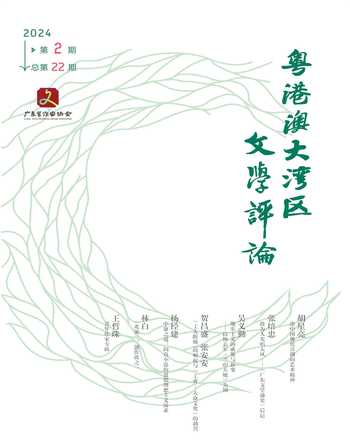李维陵的图文跨界与香港诗学
杜英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李维陵的现代主义小说与香港素描,探索其图文跨界与诗画合作。李维陵不仅造就了一个有生命的日常香港,还探讨了战后的理性时代的重建与道德承担的问题。他的现代主义文艺观,应置于其世界主义的视野与改造社会的要求中予以考察。
关键词:李维陵;香港;现代主义;图文跨界
图文跨界的创作在中西艺术史上早有渊源。无论是中国传统的“诗意画”和“题画诗”,还是西方古典的“读画诗”(ekphrasis),都是一种艺术媒介试图通过描述对象的本质和形式来与另一种媒介建立互涉的关联,进而更直接、更生动地向受众表现与传达这一对象。在此过程中,图文两个符号系统间的互动与罅隙,不仅构成了互文关系,也彰显了各自媒介的特征。在当代香港艺术史中,李维陵的创作即图文跨界的典型代表。
小说家卢因被问到:“香港小说家中最佩服谁?”他答曰:“李维陵!”并说他的小说“对人性有深入的探讨。”1李维陵(1920—2009),广东增城人,原名李国梁,画家兼作家。生于澳门,1935年起在香港居住,后于重庆就读大学,1948年回港。先后任教于香港联合书院、葛量洪教育学院,1982年移居加拿大。2李维陵作品结集有《荆棘集》(1968)和杂文《隔阂集》(1979)。
1950年代的李维陵作画处于狂热时期。一方面因相识杨际光,志同道合;另一方面因重回香港,印象难忘。李维陵1930年代在香港度过“少年时代”,重返香港后熟悉的建筑激发了创作欲望。3李维陵常常在香港街头作画,受到法国街景画家郁特里洛(Maurice Utrillo)、弗拉明克(Maurice de Vlaminck)与杜菲(Raoul Dufy)的影响。有美国驻香港副领事曾收集过李维陵的作品,并推荐给港督葛量洪,亦获赞许。《四海》编者称,“他以生动流畅的线条和清新脱俗的風格,锐敏地体现这城市丰富的面目特征,并深刻而诗意地,反映出生活在这里的人对这城市的感情和经验。”4叶灵凤称赞李维陵“所作素描很清秀。”5也有国际人士称,他的画“已经扩展了把东方艺术的线条和境界融注入世界艺术的途径。”1 1957年2月7—17日,英国文化委员会在香港举办李维陵画展,对其作品作首次国际性的介绍。2这一画展,一方面,展示香港已有本土的画家、画作;另一方面,也意味着香港的再现在绘画领域已成就了独特世界。
香港,成为战后一群南来青年相知相识,追求纯境的起点;亦是他们日后飘零四方,缅怀青春憧憬的家园。杨际光1950年代初到香港不久后,在一家报馆做翻译,因为遭遇不快而开始写诗。据李维陵回忆,他第一次看到杨际光以贝娜苔笔名发表的诗歌时,即被“那种强烈的感情、新鲜的风格和丰富的形象”所吸引。他甚至赞誉杨际光的诗歌如此纯粹完美,可以媲美古典杰作。兴奋激动下,他给素未谋面的杨际光写信。3从此,两个陌生的年轻人相识相交。1950年代,李维陵画了大量的香港景物素描。杨际光跟随他走过香港大街小巷,漫无边际地闲谈。4两人的合作成就了1951年8月至11月《香港时报》上发表的16辑“香港浮雕”——维陵图、麦阳诗。麦阳即诗人杨际光。杨际光的诗歌有《筲箕湾石级》《穷巷》《跑马地》《半山的白昼》《教堂》《木屋》《钻石山竹林前》《坟场》等。李维陵的配图是1950年代初香港的城市速写,有混沌的屋舍,也有巍峨的高楼;有圮废的木屋,亦有安闲的半山。从此时到1959年杨际光离开香港,李维陵的香港素描大多数由杨际光跟他一起完成。刘以鬯将两人的诗画幷列发表在《香港时报·浅水湾》上。杨际光回忆,这是李维陵作画最多的阶段,也是自己写诗最忙的时期,还是他们一生中物质最贫困却精神最快乐的时期。他们彼此影响,共同建构灵魂可得安乐宁静的纯境。5
在描画香港方面,李维陵的“香港速写”“香港素描”,记录了日常生活下的城市地景,也造就了一个有生命、有情感、有灵性的香港。而这一速写与文学的对照碰撞,绽放出多彩的城市之光。李维陵曾为今日世界社早期出版的丛书做封面设计与插图;《星岛周报》在1953年、1956年也刊登过“李维陵笔下的香港”“香港速写”图画。6画作中的香港,有麦当奴道、德辅道中、和平纪念碑、香港大学,有熙攘的街头小巷,也有明亮华丽的高楼大厦。《四海》专页刊载他的绘画,并向读者作推荐(第18、46、49、51期)。《四海》第18期辟专页介绍李维陵的绘画“香港速写”。编者从他的作品中选刊了“普庆坊”“金花殿”两幅图,并派记者前往实地摄影,将照片与图画并列刊出,“在‘图‘影对照之下,让读者有机会去体味,一幅艺术家笔下的有生命有灵性的作品,和机械的摄影纪录究竟有何不同。”7杨际光为《香港素描》撰写介绍指出,称香港没有文化早已成为滥调;但也有人把它描绘成美妙的乐园。“香港是一个典型的缩影;它是大冲突与大混乱的焦点,在某个角度上,可与今日的柏林、维也纳、或的里雅斯德相比拟。……就因为他们真诚做出的这点工作,文化的延续并没有如许多人想象那样的中断或静止。……在今日这香港,李维陵是这样的人之一。……他是在运用他所能运用的工具与能力,把他目光所接触的环境与这时代的具体风物,加以记录和表现,再注入他感觉中属于这环境与时代的精神。”8
李维陵小说的主人公多为艺术家与文人,念兹在兹的是沉滞时代的道德承担问题。《魔道》写“我”(画家)与朋友“他”从相识、相知到相别,见证了其灵魂在恶的深渊从沉沦至返途的过程。“他”是一位从内地来港的难民,流落街头乞讨,被一对贫困老夫妇收容。“他”知识渊博,但个性乖戾。“他”在大学期间加入在国外训练的抗战部队,在印缅边境连绵雨季的森林中苦战;后做过执行清算的干部。他象征着一个堕落的、被毁坏的灵魂;代表着被战争暴力与战后混乱所摧毁的良知。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见证者“我”。“我”,素来怀有理想主义的信仰,相信人类良知、智识终将征服野蛮。“我”以为“他”并非本性为恶,而是错误时代的结果:“在大规模的杀人已成为公正和道义的必然的时候,他已经不复有所谓良心和道德的感觉了。”1《魔道》探寻的是如何在经历过血腥的战争与理想的失落后再出发,如何从时代罪恶与历史教训中创造出一个理性时代。所谓的理性时代,就是以“乐观积极的合理世界观念”引导人们走出沉滞现实,建设美好未来。2对于人类美好远景的憧憬与努力,这种信念是凝聚李维陵、杨际光、马朗等人的根本。李维陵认为,杨际光是时代的先驱者,把诗歌提高到关怀人类的美妙高度。他的诗歌与品格令李维陵深信:“全世界的黑夜是终会逝去的”,文学的光辉终将再次普照大地。3
《魔道》中,“他”魔性驱除的方式设计得有点匪夷所思。一晚,“他”无意瞥见那个老妇人换衣,情欲躁动并强暴了她。老妇人的丈夫目睹了一切,偷偷哭泣。“他”憎恨丈夫的卑怯,挥拳相向,却被老妇人挡住。“那一瞬我好像清楚地内省到什么是真正的罪恶,不像我平素所想到说到的空泛概念,那是一种非常实在的具体感觉。我从没有像这一刻那样厌恶和痛恨我自己,我觉得我就是罪恶的化身。”4那晚的经验比“他”在战时杀人和战后执行清算更动魄惊心。从此,“他”消逝了。该篇小说的插图为作者的兄弟李维洛所绘。插图展示的是一个赤裸男子面对着一扇低矮的窗口,背对着读者。那垂着布帘隔出来的板间,摇摇欲坠、贫败破旧,象征着老夫妇的居所。窗口与人体周遭延展着暗沉的、令人不安的阴影。图画表现了“他”裸灵震颤、痛悟罪恶的那一瞬间。
“他”的人性复位是李维陵欲以理想振奋暮气沉沉时代的美好愿望使然。故事展现了道德如何战胜知识、暴力、教育而促发了个体去反省赤裸灵魂,发现爱及其意义。“他”的幡然悔悟并非源自他素有修养的智识世界,如莎士比亚作品、《罪与罚》,以及存在主义等西方文艺作品,而是来自道德典范的指引力量。那对老夫妇可视为道德的表征,他们不仅背负经济重担收容他,还在遭受暴力后仍然选择宽恕,待其归来。小说的结局,寓意了人性之善可以克服魔性。这也重申了李维陵战后重建理性时代的主张:理性道德而非英雄狂飙是建构战后“民主自由”的途径之一。小说反映了战后大时代如何重建心灵皈依之所在的普遍困惑。 李维陵的《荆棘》亦展示了他对人类社会未来远景的关怀。小说以第一人称“我”为叙述视角,展示朋友“他”与其子之间的矛盾。父亲身为大学教授,却无法供养儿子受高等教育;“他”的诗集与书稿讨论人类社会的未來走向,却无出版商愿意出版。儿子支撑起家中的大部分生活费,视父亲为“空想”的疯子。“他”经历了学校的解聘、世人的嘲笑及儿子的抛弃。“我”劝“他”的儿子,要尊敬上一代,因为他的工作有极重大的意义。而儿子却坚持,“以他父亲那样一个贫穷、卑微的、自顾不暇的老头子,竟然敢去放肆地讨论什么世界和人类等大事情,而且还要发表出来,这分明是一个胡闹”。1叙述者“我”并未嘲弄朋友儿子的无知与冷漠。“我”对于朋友儿子的劝说,也是对自己所坚持的价值之辩护,而非仅仅从现代家庭观念与传统孝顺伦常出发。
《荆棘》中,父子矛盾象征着世俗/物质/无信仰与精神/理想/人类关怀之间的冲突。父与子两个世代的冲突自古有之,往往意味着一种新的观念正在取代一种旧的观念。但李维陵参照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将朋友的父子矛盾归因于下一代的蒙昧无知。“我朋友的儿子不相信日常生活以外还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他所希望和要求的只是些可以看得见的个人物质状况的改善,他不关怀似乎是概念上的人类或抽象的世界,那对他是极遥远渺茫的事情。”2李维陵以代际冲突表现信念理想与悲剧现实的悖论。《荆棘》中,小说的隐含作者、叙述者“我”对小说人物“他”持同情理解之立场,三者有着精神同盟的关系。“我”与“他”满腔现实关怀,兴致相投:从匈牙利革命、人造卫星谈到当时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两位中国青年科学家。而“他”可视为“我”之镜像,彼此相知相惜。 《荆棘》最终给予“他”的悲剧人生设置了些许光晕。“他”的著作后来得到了同行的认同,一个外国学术团体要特别讨论其于思想领域开辟的新路径。小说的结尾写“他”死在书桌上,儿子去坟前悼念。这一结尾表现了作者对于人性仍持有希望,无论儿子是否觉悟或尊重父亲的价值观,但父子之情都已流露,这是人性人情终未泯灭的表现。作者为知识分子的理想信念留下一抹暖色:胶着于暗哑的现实生存状态,备受无知或世俗嘲笑,却仍然关怀人类、思考未来。父子冲突最终也许在价值观念层面无法和解,但可能在人性层面达到些许调和。这种调和恰恰是一切追求理想、信仰、信念的出发点。追求理想的努力最终以人性、人情为指向。
李维陵的《两夫妇》探讨了希望与真实之间的两难关系。小说以第一人称“我”为叙述视角,见证朋友“他”(音乐家)及其跛脚朋友的故事。“他”认为艺术的世界是公开的世界,表演即袒露出艺术家修养的优劣。应跛脚朋友之邀参加其妻子的钢琴演奏会,“他”感受到的并非旋律的优美,而是贫乏浮薄的修养。3“他”的困扰在于:一方面,坚守艺术的真实性,即评价艺术的标准在于艺术本身;另一方面,对于艺术表演者的真实评价会摧毁跛脚朋友的人生意义。朋友幼年因为跛脚而生自卑,在遇到现在的太太后,心理得以疗治。跛脚朋友将其人生的希望寄托在对她的音乐培养上,耗费了大部分积蓄。“他”所面临的两难选择是:说真话,朋友及其妻子将失去生存之希望;不说真话,那将是对艺术的亵渎。“他”最终选择了为了艺术的忠实而粉碎善良人的美梦。跛脚朋友用毕生希望的崩塌换来真相的发现:自己因缺陷而造了一个幻象欺骗自己、麻醉自己;太太利用自己的纵容变得妄诞。
李维陵的创作独具一格,辨识度极高。小说《魔道》《荆棘》《两夫妇》中的人物“我”与“他”,均与作者李维陵有着隐约的交集处。小说多以见证者或旁观者“我”为叙述视角,展开朋友“他”的故事,裹挟着“我”的感慨。比如,《魔道》的人物设置上,“我”的画家或艺术家身份,与李维陵的身份相同;而“他”对现代主义艺术的熟谙,亦与李维陵的艺术追求相似。“我”与“他”的关系,可解读为“我”的一体两面,是两种对立观念辩驳之合体;“我”与“他”的交往,可视为探寻个体如何在经历过血腥的战争与理想的失落后再出发。“我”相信人性本善,以道德理性支配行为;而“他”代表着对立面之镜像——被战争暴力、战后混乱、庸常人生等所摧毁的人性。“我”以道德理性否定狂飙主义、英雄主义、人性向恶论。李维陵的小说一向关注于拷问人性、追求理想的主题。他对人性向善的一面始终持有信仰,否则一切抽象的理想奋斗将失去根基。由于李维陵怀有战后重建社会之道德理想,其作品自然呈现训诫色彩。这在戏剧创作《菌》中尤为明显:戏剧文体往往缺乏小说文体刻画、皴染人物深层心理的摹写空间。李维陵创作于1970年代的《荆棘集》,收入大量短文,道德说教色彩浓厚。
李维陵认为,现代主义的文学艺术,“描写个人心理历程的没有故事情节和结构的小说,浓厚玄秘意味与纯粹感觉经验的诗,不协调音乐及夸张地表现直觉与幻象的绘画,虽然它们是那样标奇立异和极端化,但它们的确已扩大了现代人狭隘的观念和视野”。1现代艺术无视传统格律与形象的限制,提倡一切外界物象由自己独特的感受予以表现。现代艺术给现代庸俗物质生活带来了一丝清新,但李维陵亦看到了现代艺术的消沉一面。这早在李维陵翻译的《现代主义派运动的消沉》(Stephen Spender)中,即有专门讨论。李维陵认为,现代文学艺术的消沉主要在于它哲学的焦虑:“当它以无忌惮的冒险击溃了十九世纪后期猥琐庸俗的物质主义的暴虐而建立自我主义的天地,并不是说当时的人们已能较深刻地认识自己与了解自己,这不过是一种自由方式的反抗,一种无法忍受现实处境的叛变。”2而加深这种焦虑的是现代人性的问题。“自从文艺复兴期以来的自然人在现代物质主义的扩大压迫下,人类本性上有了很大的改变,他们不以作为一个自然人为满足,他们需要决定一个新的关系,就是说人究竟怎样安排他们自己和环绕他们的外界。”3
李维陵的现代主义文艺观应置于其世界主义的视野与改造社会的要求中予以考察。他认为,文艺的现代任务不仅包括表现作家与艺术家的自我感受及其和外界的关系,还要帮助现代人探求自己与他人存在之意义,探寻个体如何与外界取得新的协调之道。4而一个现代文学家或艺术家,不仅须具备独特的文艺技巧与特质,还要具备社会指导与改造者的职责。5李维陵的基本理念在于现实是可以完善和提高的;而艺术或道德等可以通过感化或启示人们成为实现此目标的中介。李维陵认为,现代主义文艺增加了读者对于现代社会的迷惘困惑,对人生的黯淡忧戚,而现代主义本身就是个人主义的,后来受到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很多现代主义作家转向集体主义。李维陵以为,衰落中的现代主义文艺的出路在于超越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冲突纠缠,在人类精神生活衰竭的状态中保持对未来美好的理想渴望。他对于现代文艺的衰落的解救方案,是将艺术定位为提供人类对于现实生活的理解和启示,激勉他们积极正视时代、改进现代生活。李维陵认为:“文学艺术不是为个人主义和阶级主义服务的,是为整个的人类与世界之向上与向前的迈进而歌舞而创造。”6他对于现代主义艺术在当下出路的观点与其战后理性时代重建的主张是相互呼应的。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1 许定铭:《许定铭文集》,https://huitingming.wordpress.com/
category/%E6%9D%8E%E7%B6%AD%E9%99%B5%E3%80%81%E6%9D%8E%E5%9C%8B%E6%A8%91/,2014年10月14日。
2肯肯、俊权、阿草、凌冰、小风访问,丹倩纪录:《访问李维陵》,《大拇指》,1979年第91期。
3 李维陵:《印象》,《大拇指》,1981年第142期。
4 《香港速写》,《四海》,1955年第46期。
5 叶灵凤:《叶灵凤日记·上1943-1967》,卢玮銮、张咏梅笺注,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20年版,第242页。
1 《李维陵画展》,《四海》,1957年第51期。
2 《李维陵画展》,《四海》,1957年第51期。
3 李維陵:《雨天集》,华英出版社1968年版,第9页。
4 杨际光:《李维陵描绘的香港面貌》,《香港文学》,1998年第162期。
5 杨际光:《李维陵的画》,《香港文学》,1996年第140期。
6 冬令:《怀念》,《70年代》,1972年第28期。
7 《香港速写》,《四海》,1955年第46期。
8 李维陵:《香港素描》,《四海》,1953年第18期。
1 李维陵:《魔道》,《文艺新潮》,1956年第5期。
2 李维陵:《魔道》,《文艺新潮》,1956年第5期。
3 李维陵:《雨天集》,华英出版社1968年版,第31—32页。
4 李维陵:《魔道》,《文艺新潮》,1956年第5期。
1 李维陵:《荆棘》,《文艺新潮》,1958年第2期。
2 李维陵:《荆棘》,《文艺新潮》,1958年第2期。
3 李维陵:《两夫妇》,《文艺新潮》,1956年第6期。
1 李维陵:《现代人·现代生活·现代文艺》,《文艺新潮》,1956年第7期。
2 李维陵:《现代人·现代生活·现代文艺》,《文艺新潮》,1956年第7期。
3 李维陵:《现代人·现代生活·现代文艺》,《文艺新潮》,1956年第7期。
4 李维陵:《现代人·现代生活·现代文艺》,《文艺新潮》,1956年第7期。
5 李维陵:《现代人·现代生活·现代文艺》,《文艺新潮》,1956年第7期。
6 李维陵:《文艺断想》,《文艺新潮》,1957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