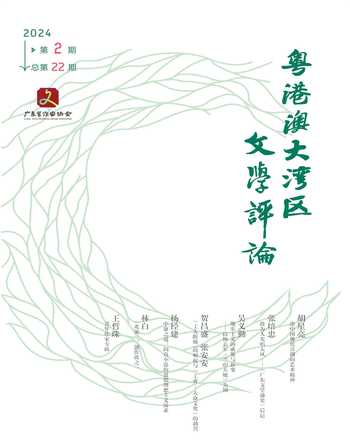魔幻、第三只眼与后殖民文学叙事的混杂性
王爱松
摘要:在后殖民时代,众多作家基于跨国经验和跨文化认同,同时受到第三世界和全球南方当下处境的深刻影响,获得了文学叙事的“第三只眼”,成就了后殖民文学叙事的混杂性。这使后殖民文学与殖民文学产生了差异,同时使各民族国家文学寻求纯洁性与本真性的冲动面临巨大挑战。
关键词:魔幻;混杂性;第三世界;后殖民文学
在本·奥克瑞《饥饿的路》第一部第二卷第一章,阿扎罗的母亲给饥肠辘辘的阿扎罗讲了两个有关胃的故事。一个是,奥图村的巫医为了去白人之国参加一个事关世界命运的会议,必须做一件令人称奇的事(飞往月球和许多行星),并在入境白人之国前回答一个问题,“你去月球之前吃的是什么?”巫医的回答是,“一只蟋蟀”,“一只烤熟的小蟋蟀”。第二个故事,是有关一个没有胃的人的故事,这个没有胃的人每年都要去圣地朝拜,出人意料的是,他在遇见一只没有身体的胃并与之成功合体后,却在抵达圣地之前因饥饿难支而不得不和哀求“给我喂食”的胃约法三章:“你要么现在就离开我,要么免开尊口”。阿扎罗母亲讲这两个故事的目的,是为了让孩子凭借精神的力量战胜实实在在的饥饿,而“鬼孩”阿扎罗却进入了典型的魔幻时刻:“不知故事讲到哪个关口时,我忽地穿过椅子后背,骑到蟋蟀后背上飞了起来。我就是那个没有胃的人,要去参加月球上的一场盛宴。”1
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萨尔曼·拉什迪的《午夜的孩子》等作品一样,《饥饿的路》经常被人视为世界文学范围里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杰作。面对这一类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读者感兴趣且需要做出解释的是骑到蟋蟀后背飞升一类故事情节和创作手法的来源问题。追溯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文化来源,以及魔幻与奇幻等之间的异同,往往成为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研究的重要议题。2从西欧的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及塞万提斯、卡夫卡的小说创作寻找魔幻现实主义的起源,成为一条相沿成习的重要研究思路。但是,建立在极端的起源崇拜基础上的追根溯源,极易放大外来的文化影响,落入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陷阱,将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视为西方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文学的空间迁移,同时将拉什迪、奈保尔、奥克瑞等的创作视为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在世界其他范围的扩散和拓展。在这种文化旅行的追踪中,第三世界/全球南方本土的文化资源的巨大作用被无声地淡化和湮灭了,殖民者创造、被殖民者模仿的文化等级结构和刻板现象得以留存和固化。这正是无论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作家,还是世界其他区域从事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作家,都力主本土的魔幻资源的一个深层原因——让本土的原创性和自身的创造力回到自己恰当的、应有的位置。马尔克斯曾说,在南美洲,一些看似不可思议的事有时不过是人们的日常生活1,而有时,“这块大陆的绝大多数事物,从餐勺到心脏移植,在存在于现实中之前人们就已想象到了。”2同样,《饥饿之路》中能够穿越幽明两界、沟通生死,既读得懂人的心灵、也能预知人的未来的阿扎罗,首先也是作者奥克瑞所挚爱的尼日利亚约鲁巴文化的产物。
魔幻元素的加入,使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有了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的特征。建立在反映论基础上的写实模式被打破,文学与现实之间的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得到修改和更新。乌苏拉·克鲁维克认为,拉什迪小说中的魔幻现实主义存在两种编码:现实主义的编码和超自然的编码;现实主义的编码让魔幻的成为现实主义的,超自然的编码让现实主义的成为魔幻的。3着眼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中魔幻与现实主义两种艺术元素的融合问题,其他作家的创作也大抵呈现出这种双向运动:魔幻的现实主义化与现实主义的魔幻化。以前述《饥饿的路》所述的故事为例,无论巫医的故事,还是朝圣者的故事,抑或是阿扎罗的故事,每个故事都既充满了魔幻色彩,同时又是以后殖民时代尼日利亚人民的现实生活打底的,总体堪称詹姆逊所说的那种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的民族寓言。长期以来,非洲的巫医是被殖民者视为落后的、愚昧的、迷信的、前现代的、非理性的文化象征,但在后殖民时代里,他也获得了从边缘到中心前往白人之国的通行证,但这通行证仍是要由白人之国来颁发的,前往的前提条件也得充分满足白人之国对他者的奇异化的、刻板化的文化想象(能奔月、吃蟋蟀);非洲大陆上底层人民的灵与肉、宗教生活与世俗生活的关系,始终是受到人的肉身存在与现实的物质生活条件限制的,朝圣者要想最终抵达圣地,首先要做一个没有胃的人,与自己的肉身做彻底的切割和剥离。至于阿扎罗骑蟋蟀去月球参加盛宴的魔幻故事,本质上不过是一个饥饿中的孩子身上人的基本生存欲望的曲折表达。可以说,在典型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现实的是魔幻的,魔幻的也是現实的,现实的与魔幻的彼此交织、水乳相融,共同构成了一个既不是完全现实的、也不是完全魔幻的第三空间。
这种第三空间的创造,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后殖民时代世界文学范围内众多作家获得了回溯过去、观察当下、展望未来的第三只眼。从事后殖民叙事的许多世界级作家,往往是移民作家、离散作家、流亡作家,或者是一个民族国家内部的少数族裔作家、女性作家,他们从自己的跨国经验或本土经验中养成了一定程度上跨国界、跨种族、跨性别等的超越性立场。德里克曾说,后殖民主义始于“第三世界知识分子抵达第一世界学术界之时”1,这道出了一个事实——是马尔克斯、奈保尔、索因卡一类的创作家和斯皮瓦克、霍米·巴巴一类的理论家从边缘到中心、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共同推动了后殖民主义的叙事和批评。与殖民文学相比,后殖民文学的民族主义文化立场有所淡化,世界主义立场有所加强,或者说,其文化立场既是民族主义的,更是世界主义的。本质上,这种立场也即胡克斯基于自己的少数族裔身份和女性身份所采取的在边缘的、居中的立场。“在边缘”不是不介入、不关心,而是“在全体之中却在主干之外”,是“一种看待现实的独特方式”,“我们从外往里看,也从里往外看。我们既关注中心,也关注边缘。我们了解中心也了解边缘。这种看的方式提醒我们存在一个整体的宇宙,存在一个由边缘和中心两者组成的主干。”2这种既从外往里看、也从里往外看的方式,不外乎是一种关注总体,既入乎其内、又超乎其外的看待现实、历史和文学、艺术的方式,一种布伦达·库珀所主张的“用第三只眼看”的方式,这种方式力图把握总体性,“不简化政治或艺术的复杂性。相信压迫体系继续决定历史,也相信生活是复杂的、悖谬的、神秘的和怪异的;确信如果生活是这样,艺术就更是这样。”3不虚美,不矫饰,不简化,不夸张,这使包括魔幻现实主义在内的后殖民文学与广义的现实主义文学不矛盾,在内在精神上息息相通。
这必然通向后殖民文学的混杂性。从文学史发展的链条来讲,后殖民文学总体上是伴随着二战结束、殖民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而兴起的文学,很长时间内,它主要被视为第三世界的文学现象,全球化运动兴起、冷战结束后,又被视为全球南方的文学现象(当然也不排除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和全球北方的某些具有相同趋向的作家作品被纳入到后殖民文学中来谈论),这使后殖民文学与殖民文学产生了种种内在延续与关联,又受到第三世界和全球南方国家当下处境的深刻影响。
殖民文学的诞生,基于殖民者对殖民地的发现、征服和剥夺,反映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压迫与被压迫、反压迫的关系是殖民文学的一个重要内容,从上至下地看和从下至上地看的两种不同的观察世界的方式,往往折射出殖民时代普遍存在的压迫和剥夺体系。普拉特曾引用一位采矿工程师于1827年记录下的安第斯山脉的景象:“凝望最近的山脉及其高耸的峰顶,唐·托马斯和我自己在巨大的山坡上建立起空中城堡。我们挖掘丰富的矿脉,竖起锅炉进行冶炼,在想象中看见一群工人像繁忙的昆虫沿着高处运动,幻想着蛮荒而广阔的地区,那里充满不远万里到来的英国人的活力。”4在这段文字中,无论是“昆虫”的比喻,还是“蛮荒”的措辞,都透露出了这个外来的英国人居高临下的掠夺性的眼光。这种掘地三千尺式的“风景”的发现,与卡莱尔的一段文字神形毕肖、内在相通:“肉桂、糖、咖啡、黑胡椒灰胡椒的高贵元素,都安睡着,等着白人魔法师对它们说,醒来吧!”1
到了后殖民时代,一方面是宗主国的殖民力量在减退,军事的征服、土地的夺取变得日益不可能,对前殖民地原材料的攫取更多地采取了经济契约的形式;另一方面是前殖民地和全球南方的主体意识和主权意识在觉醒,日益寻求摆脱殖民母国和世界强权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上的宰制和剥夺。这使全世界的去殖民化运动与全球化、现代化趋势产生了多重勾连(虽然近年又兴起了逆全球化趋势)。特别是,由于许多前殖民地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也在寻求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殖民时代宗主国与被殖民国家、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中心与边缘、统治与依附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变化。霍米·巴巴因此写下这样的文字:“美洲通向非洲;欧洲的民族和亚洲的民族在澳大利亚相会;民族的边缘替代了中心;边缘的人们回过头来重写大都市的历史和虚构故事。岛屿的故事是从飞机的视角来讲述的,这种视角成为一种将公众和私人悬置了起来的‘装饰。英国特性(Englishness)的堡垒在移民和工厂劳工的眼中轰然倒坍了。”2张颐武甚至用不无夸张的语气写道:“个人开始不需要任何中间群体就可以进入全球资本主义的逻辑之中。跨国资本在世界各个地方寻找人力资源,在无限扩张中改变着人们的生活。”3或许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有人甚至宣称,作为后殖民理论中一个重要概念的“第三世界”概念过时了,并直接将自己著作的一章标明为“再见,第三世界”4。
而之所以如此,是产生于冷战时代的“第三世界”理论确实面临了新的时代状况和理论挑战。德里克曾指出,资本主义的全球化重构了全球关系和空间分布,在目前世界上,“既有存在于第三世界中的第一世界(如上海),也有第一世界中的第三世界(如美国的新奥尔良)。”5乔万尼·阿瑞基则将自己专著的第一章题名为“马克思在底特律,斯密在北京”6,以指代理論资源的文化旅行的复杂路径和空间布局。在此背景下,后殖民文学叙事中,涌现出了折射全球化时代文化混杂性的众多例证。在奈保尔的《抵达之谜》中,“我”从杰克的花园、鹅群及老岳父那里感受到不一样的文化气息,觉得“似乎都是从文学、古代和周围的景物中衍生出来的”7,这既得力于一个从澳大利亚来到宗主国的家庭从边缘到中心的传奇所提供的文化震撼,也得力于奈保尔身为特里尼达移民所具有的怀乡情感。跨国和跨种族婚姻也会带来血缘和文化的混杂性,产生奈保尔《河湾》中“墨迪”那样的“混血儿”:墨迪虽与非洲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在当地人眼里又不是地地道道的非洲人,而是会引起种族间的不安的异乡人,“墨迪”并不是他的真名,而是法语的métis(混血儿)。最能反映后殖民文学叙事的文化混杂性的,是霍米·巴巴所说的那种殖民文化的模仿者。这种模仿者的出现,首先是基于殖民统治的需要,殖民统治需要创造一批欧洲化的土著人,也就是类似于托马斯·巴比顿·麦卡莱所期望的那类人:“在血缘和肤色上是印度的,但在品味上、观点上、道德上和思想上是英国的”1。这种精神上的混血儿对殖民主体的模仿,部分是复制和重复,部分是改写和扭曲。他们有时是巩固和稳定,有时又颠覆和瓦解殖民者的统治结构。在后殖民时代,虽然一方面是广泛的去殖民化趋势无处不在,但另一方面,殖民的文化残留和文化心理的再殖民例证也俯拾皆是。在《模仿者》中,奈保尔对那种生活在一种借来的文化中的模仿者即有所反映。
后殖民文学叙事混杂性的兴起,使各民族国家文学寻求自身纯洁性和本真性的冲动面临挑战、难以实现。阿契贝甚至发现,在尼日利亚这样的国家,哪怕用本土语言进行写作也是一种奢侈,乃至有害于社会的稳定并导致文化的分裂:“只要尼日利亚想要作为一个独立国家而存在,在可预见的未来,它除了用一门外来语言,即英语,将国内两百多个民族团结在一起,别无选择”2。当然,即使如此,当谈论“第三世界的第一世界”一类后殖民文化现象时,我们还是要注意到,虽然20世纪30年代早就有人将上海称为“另一个中国”,但到目前为止,中国也仍然自我定位为发展中国家。而在全球范围内,殖民时代的沉重遗产和后殖民时代的不平衡发展格局,使恩格鲁玛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仍有理由将后殖民时代命名为新殖民主义时代。在王安忆《我爱比尔》所塑造的阿三身上,在白先勇的《芝加哥之死》《谪仙记》所塑造的吴汉魂、李彤身上,乃至在玛琳娜·柳薇卡的《乌克兰拖拉机简史》《英国农民工小像》所塑造的乌克兰、波兰移民乃至中国留学生身上,读者仍能经常观察到世界发展不平衡格局中边缘与中心关系的根深蒂固和巨大惰性:变还只是偶然,不变才是常数。可以说,正是这种变与不变的真相,决定了《饥饿的路》中的阿扎罗,只有在魔幻状态中,才可能赴一场“盛宴”。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1 [尼日利亚]本·奥克瑞《饥饿的路》,王维东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84—85页。
2 参见:Lois Parkinson Zamora and Wendy B. Faris(eds.). Magical Realism: Theory, History, Communit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5. Amaryll Beatrice Chanady.Magical Realism and the Fantastic: Resolved Versus Unresolved Antinomy. New York & London: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85.
1 “陪同麦哲伦做第一次环球旅行的安东尼奥·皮加费塔看到过一些不可思议的植物、动物和人的足迹,但后来再也没有关于它们的消息。在阿根廷南方一个名叫科莫多罗·里瓦达维亚的荒凉地方,南极风把整整一个马戏团卷上了天空,第二天渔民们用网打上来的不是海鱼,而是狮子、长颈鹿和大象的尸体。”([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两百年的孤独》,朱景冬等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3页。)
2 [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两百年的孤独》,朱景冬等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3页。
3 Ursula Kluwick.Exploring Magic Realism in Salman Rushidies Fic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pp.34-76.
1 Arif Dirlik.The Postcolonial Aura: Third World Criticism in the Age of Global Capitalism. Colorado: Westview Press.1997. p.52.
2 ‘Preface to the First Edition, in Bell Hooks: Feminist Theory: From Margin to Cent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p. xvii.
3 Brenda Cooper.Magical Realism in West African Fiction: Seeing With a Third Ey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1998. p.3.
4 〔美〕玛丽·路易斯·普拉特:《帝国之眼:旅行书写与文化互化》,方杰、方宸译,译林出版社2017年版,第193頁。
1 Bruce Robbins. “Foreword to the edition”, in Jonah Raskin.The Mythology of Imperialism: a Revolutionary Critique of British Literature and Society in the Modern Age.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9.p.11.
2 “Introduction: Narrating the Nation”, in Homi Bhaha. Nation and Narration. London: Routledge.1990. p.6.
3 张颐武《全球化的文化挑战》,王宁编《全球化与文化:西方与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2页。
4 Arthur A. Natella, J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Post-Industrial Era: Rephrasing the Third Worl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p.21.
5 [美]阿里夫·德里克:《后革命时代的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90页。
6 Giovanni Arrighi. Adam Smith in Beijing: Lineage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2007. p.13.
7 [英]V.S.奈保尔:《抵达之谜》,邹海仑、蔡曙光、张杰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9页。
1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Spread of Nationalism (Revised Edi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91.p.91.
2 《非洲文学中的语言政治与语言政治家》,[尼日利亚]钦努阿·阿契贝:《非洲的污名》,张春美译,南海出版社2014年版,第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