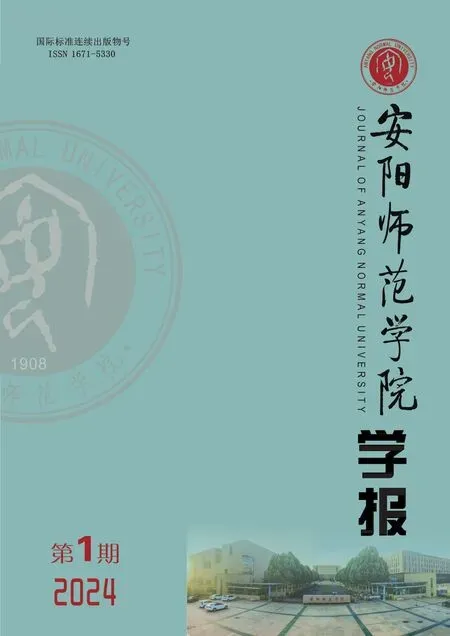试论《周易》中演绎逻辑的核心地位
王培暄
(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一、问题的缘起
中外学界几乎有一个普遍的观点,即认为西方人的思维重在演绎逻辑,以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为原型;而中国人的思维则是类比逻辑特别突出,以《周易》为典范。这种逻辑上的差异导致了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擅长于具体技术的发明,而不像西方人那样擅长于科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中国古代的一切技术只能归结为“经验技术”而非“科学技术”,这就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产生在西方的原因。
事实果真如此吗?作为“群经之首”的《周易》到底包不包含演绎逻辑,或者说,《周易》的核心究竟是类比逻辑还是演绎逻辑?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已经超越了易学和逻辑学自身的意义了。
二、以往的研究综述
近代以来,最先关注到《周易》中所包含的丰富逻辑思想的当数严复,最先提出《周易》中的逻辑方法是演绎方法的也是严复。严复在向国人介绍“为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1]的西方逻辑时,就注意到《周易》中所蕴含的逻辑思想,严复不仅认为《周易》与西方的逻辑学都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方法论,更认为《周易》的构建方法其实就是西方逻辑学中的演绎逻辑。他在《天演论·自序》中说:“及观西人名学(即逻辑学) ,则见其于格物致知之事,有内籀之术(即induction,归纳推理) 焉,有外籀之术(即deduction,演绎推理) 焉……外籀云者,据公理以断众事者也,设定数以逆未然者也。乃推卷起曰:有是哉! 是固吾《易》《春秋》之学也。迁所谓本隐之显者,外籀也。”[2]在这里严复指出,《周易》的逻辑方法是“观《象》《系辞》以定吉凶而已”,是一种“本隐之显”(由抽象到具体)的方法,这种方法就等同于西方逻辑学中的“外籀法”(deduction,演绎推理) 。另外,严复在1905年所译的《穆勒名学》中也明确阐述了他的这一观点,即“大易所言之时、德、位皆品也,而八卦、六爻所画、所重皆数也。其品之变依乎其数,故即数推品,而有以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此易道所以为外籀之学也”[1](P202)。在这里,严复同样认为《周易》的逻辑方法是“即数推品”(由形式到内容)的“外籀法”[3]。
然而自严复以后,认为《周易》的逻辑是演绎逻辑的观点几乎没有。虽然章士钊在其《逻辑指要》一书中曾言“逻辑起于欧洲,而理则吾国所固有”[4],但他的关注点则与梁启超一样,在于先秦名辩学尤其是墨家辩学与欧洲逻辑的比较。胡适在《先秦名学史》中曾辟专章论述《易经》,但由于他将“易”与孔子的逻辑思想混为一谈,因而没能明确地阐明《周易》逻辑的性质。胡适之后的中国逻辑史研究者,如汪尊基、虞愚等人也都是重视墨辩的逻辑学研究,在其著作中对《周易》经传几乎不置一词。
在今天,“易学的逻辑学研究”(Logical studies for I Ching)或“逻辑学的易学研究”(I Ching studies for Logic)已成为当代易学和逻辑学的热门课题,很多学者都对《周易》中的逻辑思想进行了有益的研究和探索,但绝大部分学者认为《周易》逻辑的核心是类比逻辑。例如周山指出:“《周易》的符号系统,应是受到了由单体象形字组合而成象意字的启示,是类比思维方法这一条藤上结出的又一硕果,从而使得文字与卦象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有着惊人的一致性,使得华夏民族注重类比的思维方法再一次获得了确认。”[5]朱志凯[6]、王颖[7]等人也基本持此观点。此外,也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周易》逻辑的核心是辩证逻辑,例如倪阳认为:“《周易》是一个辩证法的泛演化逻辑体系。各卦之间的流转关系,充满了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的变化流转关系,是一个流动、相续的概念体系。”[8]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周易》逻辑的核心是数理逻辑,例如杨宏声指出:“莱布尼茨曾对《周易》卦图的数理结构的二进制原理进行过探讨和解说,然而后来的学者往往将其解说与现代计算机的二进制问题联系在一起,其实它的逻辑意义要远远大于其具体的数学意义。”[9]
当然,也有学者关注到了《周易》中的演绎逻辑方法,但他们的观点并不彻底。例如吴克峰把《周易》的逻辑方法称为“推类”,其实就是演绎逻辑方法与类比逻辑方法的综合,他指出:“《易经》及其后的《易传》包含了较为丰富的逻辑理论,其主导的推理形式是‘推类’。《周易》中的逻辑思想包括:阴阳、八卦是按照归类方法建立的;《易》的逻辑系统是变化的和可推的,这种性质为《易》的逻辑推演提供了根据。”[10]又如,张晓芒认为《周易》中包含着一种“格式化的形式方法”,但同时又指出《周易》思维方法的底蕴还在于“取象比类”的推类方法[11]。王俊龙证明了“八卦是八个逻辑范式,而六十四卦是演绎逻辑体系”,但同时又认为“《周易》是基于空无律和互补律在整个实数系上建立起来的广义太极代数公理体系(即数理逻辑)”[12]。总之,以上学者只是论证了《周易》中“包含着演绎逻辑”,却未能论证出《周易》的“核心是演绎逻辑”。
三、《周易》中演绎逻辑的核心地位
《周易》作为一个博大精深、一体多元的思维框架,其中固然包含了本体论、价值观,但它的核心却是逻辑学。而在逻辑学中,固然包含了类比逻辑、辩证逻辑乃至数理逻辑,但它的核心却是演绎逻辑。
(一)从《周易》的起源考察其演绎逻辑的核心地位
《周易》的演绎逻辑特质,可以从《周易》的起源来进行考察和论证。传说中以三爻为一个符号组的八卦是由伏羲氏所创,以八本卦相重而成六十四别卦的符号系统《易经》则诞生在青铜器时代。《周易》的形成方法是“推”,是演绎,即以阴爻、阳爻为初始符号,推演排列出八本卦的符号组,再由八本卦相重,推演排列出六十四别卦的符号系统。在推演过程中必须遵循一整套语法语言,如爻、卦、经卦、复卦、本卦、别卦、变卦、九、六、位、承、乘、比、应、据、中等等,这些都与西方演绎逻辑方法相似。
关于《周易》的起源,《史记·自序》中说:“西伯囚羑里,愤而演周易。”说的是姬昌在被商纣王囚禁的七年里推演易卦,变先天之体为后天之用,将“对待之易”推衍为“流行之易”。姬昌出狱后,举兵伐纣,史称其为周文王,故而他创作的《易经》又被称为《周易》。在今人看来,《史记》中的说法基本上是准确的,《周易》的经文的确形成于殷周之际。《周易·系辞下》说的“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也得到新近考古学等方面证明[13]。
那么,有关《周易》一书的起源中至少包含两个重要的信息:第一,这本书是“演”出来的,而不是“归”出来的;写这本书用的是从抽象到具体的演绎法,而不是从具体到抽象的归纳法,是deduction,而不是induction。第二,这本书是周文王的“狱中”之作,一个被囚之人,不假外物写出一部巨著,靠的只能是演绎逻辑的方法。
(二)从《周易》的体系考察其演绎逻辑的核心地位
使用演绎逻辑的方法,首先必须设立几条“不证自明”的公理,然后再从抽象简单的公理推演出具体复杂的定理,并依据定理进行演算,在推演过程中必须遵循既定的规则。
首先,公理的设立来自心灵对宇宙感通的“本质的直观”,例如欧几里得几何学中的“两点之间直线最短”“平行线永远不相交”。公理必须具备普遍承认、无需证明的性质,罗素把公理称之为“原子命题”,即不可再被分析的简单性质或关系,是逻辑的最基本单位[14]。这种逻辑的最基本单位正因为其是不可分析的,所以只能是来自于心灵的本质直观,即胡塞尔意义上的“现象学还原”方法,是对宇宙本体的“先验认识”。胡塞尔说:“先验认识无非是指一种纯粹针对整体实质的、纯粹从本质中汲取其有效性的认识。”[15]而圣人正是在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的过程中,通过“天人合一”的感通,在对宇宙万物的“本质直观”中设立了“易”的初始符号“—”“--”,这就是最基本的公理或“原子命题”。
其次,初始符号“—”“--”的组合,推演出了八条总定理,即八本卦:(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如果用现代两进位制的符号“1”代表“—”,而“0”代表“--”的话,则八本卦可表述为:111(乾)、000(坤)、001(震)、110(巽)、010(坎)、101(离)、100(艮)、011(兑)。在此基础上再将八本卦重叠,推演成六十四别卦,就是六十四条二级定理。而这六十四条二级定理每个又包括六爻,则可形成三百八十四条三级定理。如果把每一爻的变化考虑进去,会形成共计4 096 种变化(64×64),即4 096 种“某卦之某卦”,这可以看作是四级定理。这样一来则几乎涵盖了宇宙万物森罗万象错综复杂的变化,正如维特根斯坦所指出的那样,逻辑是世界的一面镜子[16](P127)。在维特根斯坦看来,世界虽然是由千差万别、千变万化的事物组成,但这些事物都是按照符合它们内在属性的方式组成,而逻辑所反映的不是具体形态下的事物(thing),而是作为事物之内和之间必然联系的事实(fact)。
最后,“易”具有自己的推演规则: (1 ) 合式规则。初始符号(公理)通过合式规则形成总定理,“—”“--”的任意画组合是合式公式。(2)自重规则。任何一个总定理都可以通过自重形成二级定理。(3 ) 他重规则。任何一个总定理可以通过和其它总定理的重合形成二级定理。(4 )代换规则。三级定理中的任何“—”“--”都可以互相置换(变爻),从而推演出四级定理(变卦)。“易”依照上述规则,便可以进行逻辑推演。
(三)从《周易》的运用考察其演绎逻辑的核心地位
《周易》在古代是一部用来占卜的书,而中国古人的占卜行为就好比是在运用公理和定理来“做习题”。《周易》作为中国古代最早具备抽象水平和完整理论的典籍,“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其演绎逻辑的方法早运用于中国古代的天文、历法、医学、音律、兵法等学科,从而影响了整个中华文明。
例如,在中国古代的天文学中,人们很早就发现北斗斗柄与地面上的气候之间的密切关系,天文学认为这个可以见到的北斗是“阳斗”,于是依据“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公理又推演了一个“阴斗”天体的存在,其运动方向与“阳斗”相反[17]。由此也发现中国古代天文学家对演绎逻辑的运用,如果将北斗(阳斗)的运行规律看成是古人观测的结果,是经验技术的话,那么阴斗的设定,则可以看成是《周易》“—”“--”公理的推演结果,是科学技术。
又如,中医学里面也大量运用了《周易》中的演绎逻辑方法。“—”“--”公理一直以来就是中医学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法则,中医学的“八纲辩证”里,阴阳是八纲的总纲。《黄帝内经》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而“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然其要,一也”。这里的“数”“推”反映了中国古人从抽象公理到具体个案的演绎思维能力。
还有中国古代兵法家的“以易演兵”现象。《三十六计》作为兵家诡道,一开始是战争经验的总结,其中有些计名如“围魏救赵”等,历史上就确有真实战例。但是,中国古代的兵法家们却认为,这些兵家诡道的正确性,不在于它被多少战争经验证明了,而在于它被《周易》中的公理和定理证明了。所以,古代兵法家把《三十六计》中的每一计,都从《周易》原理中去论证,其解语也均选用《周易》中的语辞。如“借刀杀人”一计的解语为“敌已明,友未定,引友杀敌,不自出力,以《损》推演”,这里的“《损》”即《周易》中的《损》卦。
四、与几种不同观点的商榷
如前所述,《周易》作为一个博大精深、森罗万象的思维体系,既包含了本体论、价值观等哲学思想,又包含了类比逻辑、辩证逻辑、数理逻辑和演绎逻辑等逻辑框架。因此,对其核心到底是什么,一直以来都有不同的界定。
对于“《周易》的核心到底是不是哲学思想”这个问题比较容易回答。《周易》原本是用来占筮的书,其中的卦爻辞也是一种特殊的占筮语言,朱熹就说过,“《易》本卜筮之书”“《易》之作,本只是为卜筮”[18](卷66)。 当然,不排除这里面也包含有丰富的宇宙智慧和人生哲理,但严格来说还不足以作为一部正式的哲学著作。《周易》的哲学化始于《易传》,这种由“经”至“传”的过程,也就是由“占筮语言”转向“哲学语言”的过程。传说《易传》是孔子所做,但现代很多学者已经考证出它是战国时期诸子思潮与百家争鸣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因此把战国中期以后形成的哲学思想作为殷周交替之际成书的《周易》的核心,似乎不妥。更何况秦始皇焚书坑儒,《周易》却独能免于秦火,由此也可推断,虽经战国中后期民间诸子百家的释义发挥,但在官方那里,至少一直到秦初《周易》也不是被当作一种宣扬德义或人生价值理念的哲学著作,而是被当作一种不带任何价值取向的逻辑框架(卜筮之书)而得以保存的。如果《周易》的核心的确是一种逻辑框架,那它为什么是演绎逻辑而不是其它类型的逻辑呢?
其一,最具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周易》逻辑的核心是类比逻辑”,其理由在于《周易》采用的是“以物取象”“取象比类”的方法。实际上,持这种观点的人混淆了《周易》的表述方式与其真正的思维方式和推演方式,仅因为《周易》表述文字的形象性和隐喻性,而误认为《周易》的核心是类比逻辑。
要知道,中国古人很擅长运用日常语言而不是元语言符号来表达某种严密的思维体系,例如用“阴”“平”“赏”“仄”四个字来表述四声,又如用“勾三股四弦五”来表述整个的“勾股定理”,再如用“水”“火”“金”“木”“土”五行来表述阴阳交汇的五种状态,即纯阴、纯阳、阴多阳少(少阴)、阴少阳多(少阳)、阴阳均衡。否则,为什么不是“四行”或者“六行”而恰恰是“五行”呢?那是因为阴阳交汇只能形成这五种状态,如此等等。中国古人的智慧在于认识到了对于一种逻辑体系而言,元语言符号的使用尽管具有抽象性和规范性的优点,但同时也会流于空泛而难以理解,所以宁愿使用形象的日常语言来进行隐喻性的表述。恰如现当代日常语言分析哲学家斯特劳斯所认为的那样,形式逻辑(元语言符号)中的反省没有穷尽日常语言的一切逻辑问题,无论怎样完备的逻辑系统(元语言符号系统)都只是日常语言的部分而不是全部[16](P319)。维特根斯坦更是形象地比喻道:“我们是在没有摩擦力的光滑的冰面上,从而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条件是理想的,但是,正因为如此,我们也就不能行走了。我们想要行走,所以我们需要摩擦力。回到粗糙的地面上来吧!”[19]在这里,导致不能行走的“光滑的冰面”就是完美纯粹的元语言符号,而我们必须要回到的“粗糙的地面”恰恰是朴实无华的日常语言。因此,《周易》的“以物取象”“取象比类”,仅仅是它借助日常语言隐喻性地表达其逻辑体系的表述方式,而《周易》的本质“内核”却是其内在的元语言符号和规则下推演出来的逻辑体系,即《周易》的核心其实是演绎逻辑而非类比逻辑。
其二,另有一种较具代表性的观点是认为“《周易》逻辑的核心是辩证逻辑”,其主要理由在于《周易》中阴阳相感、相和、相生以及相互转化的逻辑体现了矛盾对立统一的辩证思想。其实,这种观点同样混淆了《周易》与后来《易传》之间的关系。《周易》中虽有“—”“--”这两个初始符号,但经文中通篇没有“阴阳”概念。真正赋予这两个符号以“阴阳”意义的,乃是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也就是后来《易传》的作者们,主要是道家。“阴阳”第一次成为哲学范畴始见于《老子》(第四十二章),但在《老子》中“阴阳”概念也只一见。到了庄子,“阴阳”概念才被大加发挥,在《庄子》中“阴阳”概念出现约三十次,并明确指出“《易》以道阴阳”(《天下》篇)。而“阴阳交感以生万物”“阴阳转化蕴含动静”等辩证思想也是在庄子这里才得以正式形成,并对后来的《易传》产生了深远影响,这就是陈鼓应所认为的“以道解易”和“引道入易”[20]。由此似可得出结论,《周易》逻辑体系中“—”“--”符号在推演过程中的代换规则(相互置换)包含着原始朴素的辩证思想,并孕育了后来的“阴阳学说”,但不能说辩证逻辑是《周易》逻辑的核心。
其三,还有一种较具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周易》逻辑的核心是数理逻辑”,其理由在于西方逻辑史学者肯定了17 世纪的莱布尼茨把代数方法运用于逻辑领域,是现代数理逻辑的奠基人,而莱布尼兹的数理逻辑、二进位制算术和计算器制造都是在《周易》启发下的结果(1)当年,一位叫鲍威特的法国传教士从康熙皇帝身边来,带给莱布尼茨中国的《周易》。莱布尼茨意外地发现《周易》与二进位制之间具有对等关系,他在《论中国伏羲二进位制级数》一文中说道:“我不可思议地发现,因阅读3000余年以前伏羲的古代文字发现了秘密。”后来,莱布尼茨根据二进位制原理,制造了现代意义上的计算器,他还特意把他发明的计算器复制了一套送给康熙皇帝,目的是希望中国人知道,用《易经》还可以制造计算器。。这种观点虽有一定的道理,但最近已有逻辑学者证明,对于内容繁多的逻辑问题来说,易卦并非是万能的解答工具,它只对二值逻辑具有天然的适用性,一旦超越了二值逻辑的范围, 卦象分析法则对于其中的任何一个逻辑问题的解决都显得无能为力。同时,即便是二值逻辑领域, 卦象分析法对复杂的逻辑问题也不是都能适用[21]。 由此可见,《周易》虽然对现代数理逻辑有启发意义,但其自身作为一个数理逻辑体系则不具有完备性,所以《周易》的核心仍然是演绎逻辑体系。
五、确定《周易》演绎逻辑核心地位的当代意义
综合以上研究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作为“群经之首”、发轫了整个中华文明的《周易》,其核心是演绎逻辑。这种演绎逻辑在公理中包含了辩证逻辑的智慧,在推演中使用了数理逻辑的符号(尽管不是阿拉伯数字和英文字母),在表述和运用中赋予了类比逻辑的灵性,从而使其可以“类物之情、尽事之理”,最终孕育了后世诸子百家的本体论和价值观的哲学思想。
确定《周易》演绎逻辑的核心地位对于国人树立文化自信具有十分重要的当代意义,它可以证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并不缺少演绎逻辑方法。今天和未来的中国要向世界展示并贡献中国智慧,但前提是我们必须充分尊重和深入研究我们前辈的智慧。自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所占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这个数据仅靠“经验技术”概念是无法解释的,因为任何技术辉煌的背后总有科学理念的支撑。事实是,中国在这一阶段贡献给世界的不只是经验技术,更多的是“科学技术”。那么,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诞生在中国呢?原因还是应当从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发展过程中去寻找,而不是简单归因于中国人天生就缺少演绎逻辑和科学精神。中国人并不缺少演绎逻辑和科学精神,这一点可以从中国辉煌的科技历史得以证明,也可以被中国科技的灿烂复兴所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