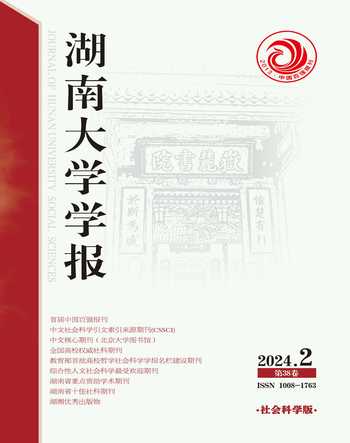清儒礼学研究中的“礼意”追求
林存阳,罗刚
[摘要] 在礼学的发展过程中,“礼意”受到治礼者的重视。“礼意”源自“礼义”,可看作是对“礼”的义理或意蕴的诠释。作为记载礼学内容的“礼文”经层累的构建而愈密,“礼意”经层累的构建而愈精。历代的礼学研究均注重寻求“礼意”,也关注到了“礼文”和“礼意”的关系。清儒在治礼过程中格外关注对“礼意”的寻求,主张“通礼文之穷”以寻求蕴藏在“礼文”背后的“礼意”,并呈现出清初“礼时为大”、清中期“即器明道”、晚清“会通汉宋”的阶段性特征。对“礼意”的寻求与阐发,既是一种治“礼”的方法,也是一种治“礼”的理念,更是一种治“礼”的目的,展现了清儒“通经明道”的立学旨趣及“以礼经世”的礼治思想。
[關键词] 清儒;礼学;礼意;礼义;通经明道;以礼经世
[中图分类号] B249[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1763(2024)02-0016-09
Pursuit of “Idea of Rites” in the Study of the Confucian Scholars in the Qing Dynasty
LIN Cunyang1, LUO Gang2
(1.Institute of Ancient Histor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100101, China;
2. School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102488, China)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of rites, “the idea of rites” has been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by those who study rites. “The idea of rites” originates from “the meaning of rite” and can be seen as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argumentation or implication of rites. Based on the content of rite studies, “the text of rite” becomes more dense, while “the idea of rite” becomes more refined. The study of rites has focused on seeking “the idea of rite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ext of rites” and “the idea of rites” in the past dynasties. In the process of studying rites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Confucian scholars were especially concerned about the search for “the meaning of rites”. They advocated “studying the text of rites carefully” to pursue “the idea of rites”, under lying “the text of rites”. And it presents the phased characteristics of “rites being the most important”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understanding the Tao through artifacts” in the mid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mixing Song Study and Han Study”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pursuit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idea of rites” is not only the method of studying rites, but also the idea and the purpose. It demonstrates the academic purport of “studying sutra and understanding Tao” and the thought of “ruling the world by rites”.
Key words: the Confucian scholars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theory of rites; the idea of rites; the meaning of rites; studying sutra and understanding Tao; rule the world by rites
在礼学的发展过程中,“礼意”受到治礼者的重视。明代何廷矩就专门撰《礼意大全》以阐发“礼意”,可惜此书已亡佚,未能得见。其他礼学著作也多通过判断具体礼仪是否合“礼意”,进而希望“得礼意”抑或“昭明礼意”,可见“礼意”在礼学研究中的重要性。作为礼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对“礼意”的寻求与阐发既是一种治“礼”的方法,也是一种治“礼”的理念,更是礼学家“通经明道”的重要手段。历来礼学家主张探求“礼意”的方法并不一致。汉代郑玄通过训诂考证“礼文”来寻求“礼意”。宋代二程主张“礼者,理也”[1]125,用理学的方法寻求“礼意”,强调“克己则私心去,自然能复礼;虽不学文,而礼意已得”[1]18。朱熹并不忽视对三礼文本的关注,认为“今则礼乐之书皆亡,学者却但言其义,至于器数,则不复晓,盖失其本矣”[2]2972,由此落实“礼”、探求“礼意”,并将“天理”作为一种先验的“礼意”加以推崇,扩大“礼意”的内涵。及至清初,批判理学的思潮使士人将目光转向经学,经学的复兴又以礼学为先导。虽然清儒陈灃指出:“国朝儒者之于《礼》学,为宋以后所不及,然考证礼文者多,发明礼意者少。”[3]106但实际上学人对“礼意”的寻求贯穿于清代学术发展的全过程。学界对“礼意”诠释,“礼意”与“礼数”“礼文”的关系等已有所研究
方竑《论语礼意述》(《礼乐半月刊》1947年第3期)指出“礼意”为本,“礼文”为末,“礼意”通过“礼文”得以呈现;梅珍生《论礼数与礼意的统一》(《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指出对“礼数”与“礼意”的探求都要把它们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且二者需名位一致方能实现礼以“制中”的目的;叶国良《〈仪礼〉各礼典之主要礼意与执礼时之三项基本礼意》(《岭南学报》2015年第3期)指出,《仪礼》中各礼典的执行均有想要表达的主要礼意,且通过恭敬、肃静、洁净三项基本“礼意”得以呈现;武勇《江永的三礼学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指出历代对三礼的诠释均以推求“礼意”为重;邹远志《礼意重诠与制度开新——论先秦原始儒家对为旧君服礼制的层累诠释及其意义》(《青海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指出历代儒家学者对旧君服制中的“礼意”进行了层累的重新诠释,通过对此一制度变迁的考察,表明中国古代经典诠释对于制度重建具有重要意义;龚建平《意义与生活世界的建构:以“礼意”为中心》(《孔子研究》2022年第4期)指出“礼意”的内在结构包含了事实与价值的内在紧张,且具有中性化的特点。,但涉及清代“礼意”的内容较少
顾迁《清代礼学考证方法研究》(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指出,清儒通过文献考证来阐释“礼意”,“礼意”等同于圣人之意;张丽珠《清代学术思想史》(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一书指出,清儒治礼是为了推求“礼意”,“礼意”系制礼之目的所在。,尚有不少可继续探讨之处。有鉴于此,本文拟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基于有清一代学术发展的宏观视野,探讨清儒如何解读“礼意”及其在不同阶段所呈现出的特征,以及共同具有的通过探求“礼意”以“通经明道”的治礼旨趣。
一“以礼经世”与“礼时为大”
历经明清鼎革的社会大变动,一些士人将社会风气的败坏、明朝的衰亡归罪于王学的空虚。为扭转此一世风日下的局面,清初诸大儒遂起而反思学术,着力重振经学,顾炎武等所开创的“以经学济理学之穷”因之而兴。在此新学术取向之下,对礼的关注和研究,成为复兴经学的先导。值得注意的是,士人们不仅试图通过探研礼学以解决现实问题,而且借由探索“礼意”,彰显了自身的复礼追求及“通经明道”的立学旨趣,希冀回归与落实孔子的礼治思想。这一经世思潮大背景下的礼学研究,呈现出“以礼经世”与“礼时为大”的显著特征。
清初的礼学研究中,继承宋明学者治礼方法的同时有着“回归郑注”的趋势,即通过训诂考证来寻求“礼意”。面对“残山剩水”的时局,大儒孙奇逢率先起而倡导对礼的“躬行实践”,进而希望恢复古礼。他将对礼的认知上升到天的高度,认为“礼者,天地之节义,所以美教化而定民志,故三王不异礼而治”[4]613。作为“承天之道,治人之情”[4]839的礼,有常亦有变,尽管“礼教陵夷,已不可言”,但是“礼之意终古难晦”。因为“殷因夏,周因殷,总此一礼,不得不损益于其间,继周者百世可知”[4]161。陆世仪指出,对礼的探求无须是古非今,“礼者,天理之节文,故有一代则有一代之制作,皆有意义,不必是古而非今也”[5]43。在他看来,“凡礼皆以义起”[5]86,先有“义”后有“礼”,“礼”缘于“理”而兴,是天理之具体体现,即其所谓:“礼者,理也。礼本乎理,理为体,礼为用。故礼虽未有,可以义起。”[5]180基于此,他强调对“礼意”的探求不必拘泥于“礼文”:“是虽不尽泥礼文,而实得礼之精意。”[5]87
“清学开山”顾炎武虽然没有专门的礼学著作,但本着“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治学理念及“治经复汉”的主张,提出“礼者,本于人心之节文,以为自治治人之具”[6]81的观点,并指出“义”系礼之所生的本源:“义者,礼之所从生也。”[7]421在他看来,对礼的探求需以学问为基础:“‘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是所存者,非空虚之心也。夫仁与礼,未有不学问而能明者也。”[8]331探求礼实际上也是追寻“圣人之道”的重要方法:“圣人之道,未有不始于洒扫应对进退者也。故曰‘约之以礼,又曰‘知崇礼卑。”[7]418-419期冀通过对礼的探求、对“礼意”的阐发,来“明道救世”,挽救颓风。在顾炎武的影响下,徐乾学认为“礼以义起,亦与时宜”[9]6,遂主持编撰《读礼通考》,通过详考历代丧礼以寻“礼意”。这体现了清初礼学研究中“礼时为大”和“以礼经世”的显著特色,为此后的礼学研究,尤其是对“礼意”的探求,奠定了基调。
在清初思想家中,王夫之著《礼记章句》彰显了其对“礼意”的探求。在他看来,“‘义者,礼之精意”[10]539,“礼”与“义”需相合而不可分离,由“义”方可知“礼”,“礼为义之实,而礼抑缘义以起,义礼合一而不可离,故必陈义以为种也。”[10]572关于二者之间的关系,他还强调:
“义”者,礼之质;“礼”者,义之实也。“制度”,宫室、车服上下之等。“田里”,井疆之制也。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制度、井疆,皆待礼义以行于天下,谋作兵起,强者干犯之而弱者不能自尽,故圣人为修明之。[10]539
概言之,“‘礼义者,因义制礼,而礼各有义也。”[10]565正是因为“礼”是有“精意”的“礼意”,所以需加以躬行实践。于个人而言,礼是修己治人的重要准则:“礼者,修己治人之大纲而治乱之准也。”[10]256“修己治人之实,礼而已矣。”[10]1213对“礼”的追求、对“礼意”的认知,也是君子区别于他人的重要标准:“礼者,大中至正之矩,君子以自尽,而非以矫时矜异者也。”[10]244更为重要的是,对礼的探求,对“礼意”的寻求,实际上是個人识道,进而“通经明道”的重要手段与方法。因此,王夫之主张通过“礼文”探求“礼意”:
礼著于仪文度数,而非有恭敬之心、撙节之度、退让之容,则礼意不显。君子知礼之无往不重,而必著明其大用,使人皆喻其生心而不容已,故内外交敬,俾礼意得因仪文以著,而礼达乎天下矣。[10]17
王夫之又进一步指出,对“道”的体认,是经由对“礼”的认知而来的,且需以“器”为基础。识“器”可达“礼”,进而可以明“道”:“形而上者道也,礼之本也;形而下者器也,道之撰也。礼所为即事物而著其典,则以各适其用也。”[10]579这与姚际恒“就器数中论其义理”[11]7的观点不谋而合。姚际恒在《仪礼通论》中指出:
《礼记》言义理者也,《仪礼》言器数者也。然言义理者,稍轶于中正之矩,即旁入二氏,是反不如言器数者之无弊也。夫言器数而误,则止于一器一数,言义理而误,则生心害政,发政害事,其患有不可胜言者矣。[11]7
由此,礼学中“义理”与“器数”是互为依托,不可分离的:“苟非义理,器数焉行?苟非器数,义理焉托?”[11]7若是缺少了“器数”,那么也就难以通晓“礼意”。故而姚际恒强调:“以其规规于器数之末而少之,是乌知礼意?”[11]2那么,“礼”自何来?在王夫之看来,“礼所自生,存中而发外,因用而成体。其用者天之德,其成而为体则效地之能,是本于天而动于地也。”[10]570也就是说,“礼”隐于心而不能著之于外,对“礼意”的认识是需经由个人内在修养而达到的。因此,王夫之认为,治礼最为重要的目标是探求“礼意”,并以此来体悟礼具有“人禽之辨、夷夏之分、君子小人之别”[10]10的重要意蕴。
黄宗羲认为六经之中的《礼》具有载道的意蕴,“《六经》皆载道之书,而《礼》其节目也”[12]311。并指出“礼”最初的意蕴就是躬行实践的“实治”与“实行”:“当时举一礼必有一仪,要皆官司所传,历世所行,人人得而知之,非圣人所独行者。大而类禋、巡狩,皆为实治;小而进退、揖让,皆为实行也。”[12]311-312此一认识,展现了通过探求“礼意”进而求“道”的目的。作为黄宗羲的高足弟子,万斯大在《学礼质疑》中推崇《仪礼》《礼記》二书:
礼之为礼,发为恭敬辞让之心,而将之以俎豆玉帛,行之以登降拜跪。在淳古之世,人皆学礼,毋或自外,然犹恐其徒习乎末而不得其原。故又戒之曰:“礼之所尊,尊其义也。其数可陈也,其义难知也。”于乎!先王之礼教如此。三代而降,圣人不作,礼制废阙,义固不明,数亦难考,赖《仪礼》《礼记》稍存一二大概,而诸经诸传有可以旁通而互见者,先儒立说不能通贯,往往拘文牵义,杂以告谶纬。又其陋者于周说穷即推为殷、夏,就其所见,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得乎此而不可通乎彼。嗟乎!礼数之未知,何足以明礼义?[13]359-360
在万斯大看来,“礼意”最为重要的就是礼具有“恭敬辞让”之意。三代时,人皆学礼,三代以降,因为圣人不作,遂导致礼制的废阙,因此“礼义”不可明,“礼数”也难以考究。“礼义”与“礼数”依靠《仪礼》《礼记》二书得以保存部分内容,就《仪礼》与《礼记》二书的内容来看,“考仪文则《仪礼》为备,言义理则《礼记》为精。”[13]176对“礼义”的认知是建立在“礼数”与“礼文”的基础上的。“在圣人,即吾心之义礼而渐著之为仪文。在后人,必通达其仪文而后得明其义理。”[13]176-177圣人依“礼义”而撰写“礼文”,后人则需通过圣人所撰“礼文”反求“礼义”。万斯大之弟万斯同则指出:“古礼不明,传注淆乱,释经者非纬书不谈,制礼者非纬书不信,是则三代以后,但有纬而无经也。”[14]368由此观之,“礼”与“礼意”均是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研治古礼时需对其中的“礼意”做新的诠释。颜元、李塨师徒就主张以“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作为治礼思路来倡导古礼,进而反思古礼,寻求“礼意”。颜元尝言:
三代之际,《礼经》备矣,然其存于今者,官庐器服之制、出入起居之节,皆已不宜于世。世之君子虽或酌以古今之变,更为一时之法,然亦或详或略,无所折衷,至或遗其本而务其末,缓于实而急于文。自有志好礼之士,犹或不能举其要,而困于贫窭者,尤患其终不能有以及于礼也。[15]317
追求“礼意”实际上是出于现实考虑,即所谓“治平之道,莫先于礼”[15]669。之后,李塨又提出学礼的重要性:“博文,学礼也;约礼,行礼也;齐明,内养以礼也;非礼不动,外持以礼也。”[16]102由此观之,“礼意”就在于“博文”“约己”“齐明”“外持”。进而言之,礼的意蕴就是“自治”与“及人”:“学礼则为博文,行礼则为约礼。以礼自治,则为明德,以礼及人,则为亲民。”[17]984
对“礼意”的探求,并不仅仅是出于关照现实的目的,更展现了清初士人“道在《六经》”的价值预设。张尔岐就曾指出:“盖闻圣人之道备在《六经》,大人之学首先格物,格物莫切于穷经,而穷经要归于体道。前有孔孟,后有程朱,轨辙如新,遗篇可考。”[18]142又强调:“尽《六经》之说,而后可以究《礼》之说,而后可以究《中庸》之说。《中庸》者,礼之统论约说非其详者也。而孔子之告颜渊曰:‘克己复礼为仁。仁不得礼无以为行,并无以为存也,礼之所统不既全矣乎!吾故断以《中庸》为必有所指,而其所指,断乎其为礼而非他也。汉儒取以记礼,为得解矣。”[18]24由此观之,圣人之道皆在《六经》之中,对“经”的研究最终是要归向于对“道”的体悟,通过对《六经》的认知方可探究“礼”。“礼意”就在于“抑人之盛气,抗人之懦情”[18]23。在此基础上,张尔岐反复申说:“礼者道之文也。”“礼者道之所会也。”“礼者道之所待以征事者也。”[18]24也就是说,“礼”不仅仅体现了追求“礼意”时所具有的“道在《六经》”的价值预设,“礼”本身就具有“道”的意义,是载“道”之文,会“道”之所在。
李光地、李光坡兄弟亦著文寻求“礼意”。李光地对《礼记》中蕴含“礼意”的篇章分析道:“《礼运》《礼器》以下,《学记》《乐记》以上,或通论礼意,或泛设杂文,或言君子成德之方,或陈王者政教之务。要于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靡所不讲,为《礼记》外篇。”[19]271由此可见,“礼意”就在于“陈王者政教”“修身齐家”“平均天下”,正是因为“礼”有此“意”,遂能够成为三代治天下之法:“三代以礼治天下,如此其盛也。虽当千百载之下,湮灭断烂之简编,仅有存者,而宏经大要,可考而知。以正圣功,以兴太平,取诸此焉足矣。”[19]271基于此,其弟李光坡就指出,对“礼意”的探求要“缘其文,求其义”[20]1。
在清初礼学渐趋兴盛的背景下,官方也致力于对礼学的阐发。乾隆初叶,三礼馆的诏开、《三礼义疏》的纂修,是一件关系乾隆一朝政治、社会和学术演进的大事。《三礼义疏》的编纂本身就蕴含了“修道设教”与探求“礼意”的目的,清高宗在《御制三礼义疏序》中即表明:“夫礼之所为,本于天,殽于地,达之人伦日用,行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斯须不可去者……故言礼者,惟求其修道设教之由,以得夫礼之意而已。顾其教之不泯,道之所由传,未尝不赖于经。”[21]1-2本着“盖治经者,求其义之明而已”[22]82的态度,三礼馆副总裁方苞在对“礼”学的研究过程中指出“先王制礼,有迹若相违而理归于一者,以物之则各异,而所以为则者,无不同也”[22]24。后世的“注疏之学,莫善于《三礼》”[22]81。在对《仪礼》进行一番研究后,方苞认为:
《仪礼》志繁而辞简,义曲而体直,微周公手定,亦周人最初之文也。然其制惟施于成周为宜;盖自二帝、三王彰道教以明民,凡仁义忠敬之大体,虽氓隶晓然于心,故层累而精其义,密其文,用以磨砻德性而起教于微眇,使之益深于人道焉耳。[22]23
也就是说,用于保存“礼意”的《仪礼》“志繁而辞简,义曲而体直”,“礼意”更是经过层累的构建而愈精,“礼文”经过层累的构建而愈密。而经由清初诸大儒和三礼馆的积淀和影响,清中期学人对“礼意”的寻求,转向“礼在器物”与“即器明道”的为学路径。
二“礼在器物”与“即器明道”
从乾隆初叶诏开三礼馆纂修《三礼义疏》,至乾隆三十八年诏开四库全书馆,研究《三礼》的方式由义理逐渐转向以训诂、考证为特征的汉学,考礼、释礼、注礼之风蔚为大观,展现了“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意”“由文字训诂以求经书义理”从而达到“训诂明义理自明”的治学思路。《钦定仪礼义疏》提要中即已指出:“《仪礼》至为難读,郑注文句古奥亦不易解,又全为名物度数之学,不可空言以骋辨,故宋儒多避之不讲。”[23]11这对此后礼学研究的思路与方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清初“以礼经世”与“礼时为大”的“礼意”追求也逐渐转向为“礼在器物”与“即器明道”,并呈现出由“器”以明“礼意”,由“礼意”以达“道”的特点。
清中期学者延续了顾炎武所开创的“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治学路径,将考据训诂作为探求“礼意”的一种重要方法。在清初实学思潮向18世纪汉学转变的过程中,惠士奇所撰《礼说》即已有通过考辨《周礼》以“递求周制”“阐其制作之深意”的目的,以其子惠栋为首的吴派学者更是大力提倡尊汉崇古,由此确立了汉学的地位。惠栋所主张的“宗郑”思想及维护郑注的立场,深刻影响了清中期治礼者追求“礼意”的思路。鉴于“《诗》《书》虽残缺,而迹其遗文,尚皆有义理可据”[24]58的情况,秦蕙田就曾指出:“三礼自秦汉诸儒抱残守阙,注疏杂入谶纬, 车翏车葛纷纭。”[24]60而就三礼所记载的内容来看,“《仪礼》载其事,《礼记》明其理”[24]68-69。且“《仪礼》所载谓之礼者,礼之经也。《礼记》所载谓之义者,训其经之义耳”[24]67。因此,本着“礼无本不立,无文不行”[24]73的治礼态度,秦蕙田撰《五礼通考》意在阐发《礼经》中所蕴含的义理。与秦蕙田治礼思想类似,戴震也认为对理义的追求应以经文为基础:“夫所谓理义,苟可以舍经而空凭胸臆,将人人凿空得之,奚有于经学之云乎哉!惟空凭胸臆之卒无当于贤人圣人之理义,然后求之古经。”[25]214由此建立了“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25]183的治学方法。据其弟子段玉裁记载,戴震常言:“为学须先读《礼》,读《礼》要知得圣人礼意。”[26]714在《孟子私淑录》中,戴震认为:
礼义者,心之所通也,人以有礼义,异于禽兽,实人之智大远乎物。然则天地之气化,生生而条理,生生之德,鲜不得者;惟人性开通,能不失其条理,则生生之德,因之至盛。物循乎自然,人能明于必然,此人物之异,孟子以“人皆可以为尧、舜”,断其性善,在是也。[25]429
又在《绪言》中强调:
礼者,天地之条理也,言乎条理之极,非知天不足以尽之。即仪文度数,亦圣人见于天地之条理,定之以为万世法。礼之设所以治天下之情,或裁其过,或勉其不及,示之中而已矣。[25]384
在戴震看来,知“礼”最为重要的就是明晰“礼”中近于“天地之德”且由心所通的“天地之条理”。因此,他说:“观于其条理,可以知礼;失条理而能生生者,未之有也,是故可以知义。”[25]333“条理”是为“礼”,“察条理之正而断决于事”是为“义”[25]333,即求得“礼意”的方法。因此,对“礼”中“义”的追求实际上就是治礼中更为重要的一步,也是求“道”的重要方法。对“道”的追求在于两端,一是仁,一是礼义,“使仁必无憾于礼义,礼义必无憾于仁,故曰‘修道之谓教。”[25]335概而言之,戴震是希望通过对“礼意”的追求来寻求道,体现“道在《六经》”的价值预设。诚如段玉裁在《戴东原集序》中所强调的:“圣人之道在《六经》,不于《六经》求之,则无以得圣人所求之义理以行于家国天下,而文词之不工又其末也。”[25]452主张“六经皆史”“以史明道”的章学诚,也强调通过探索名物制度以考察“礼意”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名家者流,出于礼官,辨方正位,循名考实,必深于经曲礼意,乃合于天理节文,是其义矣。沿其流别,可以知言,可以论文,盖先明乎制度精微,因以达乎文章体要。”[27]150
及至《四库全书》的纂修,更进一步彰显了以训诂考证探求“礼意”的治学取向,并对此后一段时期内礼学的研究产生了官方的导向性影响。四库馆臣就“三礼”问题在《钦定礼记义疏》提要中指出:
《周官》《仪礼》皆言礼制,《礼记》则兼言礼意。礼制非考证不明,礼意则可推求以义理。故宋儒之所阐发,亦往往得别嫌明微之旨。[28]566
又在康熙御制《日讲礼记解义》提要中阐发道:
盖《仪礼》皆古经,《礼记》则多志其变;《仪礼》皆大纲,《礼记》则多谨于细;《仪礼》皆度数,《礼记》则多明其义。故圣贤之微言精意,杂见其中,敛之可以正心修身,推之可以齐家、治国、平天下。自天子以至庶人,莫不于是取裁焉。是编推绎《经》文,发挥畅远,而大旨归于谨小慎微,皇自敬德以纳民于轨物。[28]566
由此观之,圣贤制礼时即已蕴含“礼意”,《周礼》《仪礼》二书多偏重于“礼制”,“礼意”更多保存在《礼记》之中,由考证可明“礼制”,由“义理”可求“礼意”。就推寻“礼意”的方法而言,虽然官方并不反对以“义理”来推求“礼意”,但更主张通过对礼文的训诂考证来寻求“礼意”,如四库馆臣评价元代陈澔所撰《礼记集说》时强调:
澔所短者,在不知礼制当有证据,礼意当有发明,而笺释文句,一如注《孝经》《论语》之法。故用为蒙训则有余,求以经术则不足。……特《礼》文奥赜,骤读为难。因其疏解,得知门径,以渐进而求于古。于初学之士,固亦不为无益。[28]561
此一评判,展示了官方的礼学意识,即注重通过对“礼文”的考读、文句的笺释,作为考证礼制的证据,由此发明“礼意”。在清中期考据学大盛的背景下,治礼者多以训诂考据“礼文”来寻求“礼意”,致使对“礼意”的发明显得“未至”。作为寻求“礼意”的手段,考据一途虽经四库馆臣加以推崇,但义理也并未完全湮灭。也正是鉴于陈澔《礼记集说》详于考证礼制,未能完全发明“礼意”的情况,孙希旦遂起而撰《礼记集解》,在考据的基础上以义理来发明“礼意”。他认为,“礼之数,见于事物之末,礼之义,通乎性命之精。故其数可陈,其义难知。知其义而又能敬守之,以体其实焉,则所谓‘能以礼让为国者,虽先王所以治天下,其道不出乎是。此礼之义之所以为尊也。”[29]707也就是说,探求“礼意”的本质是求“道”,追溯古之圣人撰写《礼经》时的“礼意”。不过,由于“谶纬百家杂说”等外力因素在儒家经典流传过程中产生“惑人心”“淆人听”的干扰,致使“礼意”晦暗难知。有鉴于此,孔广林在《禘祫觿解篇》中强调:
慨自政焰肆飞,姬籍半毁,《礼经》沦亡,礼制缺佚,虽有作者,末究厥蕴。汉京通人达士,掇拾余烬,师承传说,多以鲁礼推周礼,已不能溯镐、洛之源。加以谶纬百家杂说错迕,重惑人心而淆人听,先圣王之礼意滋晦矣。其尤汩乱纷拏、胶车葛而不可解者,莫甚禘祫也。汉魏以后,郑、王异义,徒以两家相持,从违参半,迄未有能破其谬舛、出其范围者。唐河东赵匡伯循始见得禘祫本义,一洗群障。宋儒从而发挥之,其说类不能不互有出入、互有失得焉。[30]1
这一现实情况,使得对“礼意”的探求并非易事,也并非所有的儒士能够做到,一如孔广森所指:“俗儒不知礼意。”[31]478孙锵鸣在为《礼记集解》所作序中就已指出历来单以考据或义理来探寻“礼意”均有失偏颇:“自元云庄陈氏《集说》出,明人乐其简易,遂列学官,至今承用,然于礼制则援据多疏,礼意则发明未至,学者弗心厌也。”[29]1又称:“宋、元以来诸儒之说,靡不博观约取,苟有未当,裁以己意。其于名物制度之详,必求确有根据,而大旨在以经注经,非苟为异同者也。至其阐明礼意,往复曲畅,必求即乎天理人心之安,则尤笃实正大,粹然程、朱之言也。”[29]1-2因此,孙希旦将考据与义理结合起来阐明“礼意”,彰显了其在考据基础上通过义理治礼的新特点,亦为晚清“会通汉宋”的治礼特点奠定了基础。
在“道在《六经》”的价值预设下,“礼意”的探讨显得格外重要。本着“圣人之道,至平且易”[32]31的观点,凌廷堪指出依“礼”方可探寻圣人之道,圣人之道也正是依“礼”而显:“道无迹也,必缘礼而著见,而制礼者以之;德无象也,必借礼为依归,而行礼者以之。”[32]30概言之,“圣人之道,一礼而已矣”[32]27,即“圣人之道本乎礼而言者也”[32]32。然而,作为彰显着圣人之道的“礼”是因其“义”而生的,“义”又是因“仁”而生的:“义因仁而后生,礼因义而后生。”[32]29因此,“圣人不求诸理而求诸礼,盖求诸理必至于师心,求诸礼始可以复性也。”[32]32就探求“礼意”的方法而言,凌廷堪本着“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32]312的态度,认为“礼意以为器”,亦即:“礼之器数仪节,皆各有精义存乎其间。”[32]145又强调:
禮也者,不独大经大法悉本夫天命民彝而出之,即一器数之微,一仪节之细,莫不各有精义弥纶于其间,所谓“物有本末,事有终始”是也。格物者,格此也。《礼器》一篇皆格物之学也。若泛指天下之物,有终身不能尽识者矣。盖必先习其器数仪节,然后知礼之原于性,所谓致知也。[32]30
礼的“器物”与“仪节”中均有“精义”所在,如此就需要对礼进行“格物”与“致知”,“以古人之义释古人之书,不以己见参之”[32]312的态度来明“礼意”,体现了“即器明道”的治礼理念。石韫玉也强调:“道也者,寓于器而后长存者也。若谓执乎器不足以言礼乐,则舍乎器又何以知礼乐哉?”[33]672阮元在“圣贤之道存于经”[34]547的价值预设下,以“表章六经,修复古学”[34]246为治学旨趣,本着“古今义理之学,必自训诂始”[35]423“有训诂而后有义理”[34]547的理念指出“礼明而文达”,主张通过“器”来求“礼”。在他看来,“器者所以藏礼”[34]632,“先王所以驯天下尊王敬祖之心,教天下习礼博文之学”[34]632。他还将考证礼制、阐释礼意结合,认为忠孝即“理”,亦即礼意:“朱子中年讲理,固已精实,晚年讲礼,尤耐繁难,诚有见乎理必出于礼也。古今所以治天下者礼也,五伦皆礼,故宜忠宜孝即理也。”[34]1062由此得出了“理必附于礼以行”的结论。焦循亦指出:“理足以启争,而礼足以止争也。”[36]183“以礼止争”也为晚清“会通汉宋”与“以礼明道”的“礼意”追求奠定了基础。
三“会通汉宋”与“以礼明道”
鉴于清中期愈演愈烈的汉、宋之争及时代环境的改变,晚清士人开始从儒家经典中去寻找可以调和汉、宋的路径。在学术层面上,他们一方面继承了乾嘉考据学的传统,坚持由“训诂以明义理”和“实事求是”的治学原则,另一方面也在考据的基础上以义理来探求“礼意”。以“礼”来调和汉、宋之争一时成为较为普遍的现象,而对“礼意”的探求在彰显了汉、宋会通的时代特点的同时,亦展现了晚清士人“通经明道”的立学旨趣。
在“通经明道”乃至“以礼明道”的价值预设下,林伯桐撰《礼意说》,以宋儒为治学之法,以汉学为治经之宗,通过阐发“礼意”来调和汉、宋之争。他就“礼文”与“礼意”的关系辨析道:
有礼文,有礼意。文者,可见也;意者,可知不可见。贱事贵,幼事长,文也;不贵而尊,不长而重,意也。至于以贵敬贱、以长敬幼,其礼愈厚,其意愈隐,浅人未必知,而劝善之道微矣……意之所在,不爵而贵,不禄而富,不言而罚,不怒而畏。在上者有荣辱,意通于上而风俗成焉;在下者有趣舍,意通于下而风俗移焉。然则意也者,所以通礼文之穷也。[37]24
相较于可见的“礼文”而言,“礼意”可知而不可见,是蕴藏在“礼文”背后的义理,通“礼文”之穷方可达“礼意”。“礼意”最为重要的意蕴就是“劝天下之士”,使之“自立”,从而达到“以礼经世”的目的:
礼文未足,而礼意存,天下之士就之矣;礼意不足,而礼文存,天下之士去之矣。天下之人贱之,而一二君子贵之,中人之才犹不忍为恶也;天下之人贵之,而一二君子贱之,有中人之志,不敢不勉为善也。不知礼意,无以劝天下之士,士不知礼意,又何以自立哉![37]24
如此,就使得对“礼意”的探求显得格外重要,而探求“礼意”也正是胡培翚撰写《仪礼正义》的原因:
念《仪礼》实为周公所作,有残缺而无伪托,其中冠、昏、丧、祭,切于民用;进退、揖让,昭明礼意。若乡邑中得一二讲习之士,使众略知礼让之风,即可消兵刑于未萌。此翚所以急欲成书也。[38]489
他还指出,在实际生活中要践履“礼”:“礼者,履也;礼者,体也。使人约其心于登降、揖让、进退、酬酢之间。”[39]1实际上是希望通过探讨礼的具体形式,来寻求礼仪背后的“礼意”与圣人制礼原则,进而借以阐发“礼意”、落实“礼意”,彰显“以礼经世”的功用。
黄式三、黄以周父子亦通过研治《礼经》来调和汉、宋之争。黄式三著《约礼说》《复礼说》《崇礼说》三篇文章阐发“礼意”,提出“礼者,理也”的观点。他认为“礼”系圣人所作:“礼也者,制之圣人而秩之自天。当民之初生,礼仪未备,而本于性之所自然,发于情之不容已,礼遂行于其间。”[40]24就“礼仪”与“礼义”之间的关系而言,他指出:“《中庸》曰:‘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礼仪当作礼义,据《周官·肆师》注,古者书礼仪作礼义。”[40]21 “古之所谓礼义,遗编犹在,即为‘经礼。”[40]22尽管“古今之礼虽异,而由质而文,其本则一”[40]25。这个“本”就是贯穿于礼学发展过程中“别仁义,明是非”的“礼意”。“礼文”显而易见,“礼意”却是难见之理:“博其显而可见之礼,曰‘文;约以微而难见之理,曰‘礼。”[40]23在黄式三看来,通过对“礼文”的考据方可探求“礼意”,这实际上也体现了由“道问学”以达“尊德性”的治礼方法。因此,他说:“君子崇礼以凝道者也,知礼之为德性也而尊之,知礼之宜问学也而道之。道問学,所以尊德性也。”[40]26黄式三之子以周,将对“经”的研究集中于礼学,并展现了“通经明道”的治礼旨趣。他说:“经者,圣贤所以传道也。经之有故训,所以明经而造乎道也。”[41]529对“道”的追求离不开“经”,对“经”的追求则离不开“故训”:“离故训以谈经而经晦,离经以谈道而道晦。”[41]529在他看来,对“礼意”的探寻需要以训诂为基础,“训诂不明,有害《礼》义”[42]411-412。因此,他在撰写《礼书通故》一书时通过考证具体的礼仪内容来判断是“合礼意”抑或“非礼意”,比如他在考证“肆献祼馈食礼”时就指出:“古文之义不明而《经》旨晦,‘易爵之义不明而《礼》意爽矣。”[42]775要之,其撰写《礼书通故》乃“志在发明经意”[41]594。本着“礼根诸心,发诸性,受诸命,秩诸天,体之者圣,履之者贤”[41]525的认知,黄以周提出“礼学即理学”的观点,“理”蕴藏于圣人之“礼”中,借助“礼”而存在。就“礼”的功用来看,“古人言学,近之以治其身心,远之以治其国家,不越乎礼。礼也者,诚正之极则,治平之要道也”[41]590。
秉持“礼者,为治之道”的观点,林昌彝撰《礼意》一文,强调道:
天下不可以意治也,故有其事、有其文,意著于事而敬行,事筦以文而仪立,敬与仪合而礼成。六经之籍,唯《礼》独繁,固圣学之枢、百王之轨也。世降民迷,论者以为有其事而无其意,不若事不足而意有余也。[43]272
为治之道,不在多言。说礼之家,有如聚讼。然亦有其时焉,世质则济以文,世文则返诸质;累治之世其礼备,积乱之后其礼简,此天地自然之数,存乎权而已。夫礼之用无有穷也,修身者所以治人也,修意者所以修身也。天下未尝不可以意治,意与事相周,事与文相足,敬与仪一者昌,意与治反者亡,信斯言也,虽百世不变礼,可也。[43]273-274
由其所述,探求“礼意”的目的在于“修身”,而修身的目的则在于“治人”。“礼意”虽无法治天下,却贯穿在“事”之中,“事”则体现于“礼文”之中。因此,治礼需从“礼文”所记载的“事”中去反求“礼意”,使三者相足方为治之道。
陈灃更进一步探讨了“礼文”与“礼意”之间的关系。
罗检秋先生在《学术调融与晚清礼学的思想活力》(《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5期)一文中指出,陈灃注重礼意,并以之融入全部经学,带有以礼解经的倾向。基于“宋儒轻蔑汉儒者,非也。近儒尊汉儒而不讲义理,亦非也”[44]11的融合汉、宋的治学旨趣,陈灃通过具体的学术实践,以考据为基础,来阐释汉学的微言大义与宋儒的义理学说的一致性,从而强调经学要以义理为归宿。他认为,“《仪礼》,礼之文也。《礼记》,礼之意也。”[3]106“礼文”与“礼意”的关系就在于:
礼文之中有礼意焉,不可不知也。不明礼文,不可以求礼意;然明礼文而不明礼意,则或疑古礼不可行于后世,不知古今礼文异而礼意不异。礼意即天理也,人情也,虽阅百世不得而异者也。[3]105
对“礼意”的探求需要建立在对“礼文”的了解之上,作为记载礼学内容的实体文本即“礼文”,在礼学的流传与演变过程中其内容虽然有所改变,但贯穿于礼学中的“礼意”则不曾改变。“礼意”之所以不会改变是因为“礼意”本身就是“天理”,是“人情”。明“礼文”只是第一层次,明“礼意”则是更高的层次:
既明礼文,尤当明礼意。朱笥河以《仪礼》难读,欲撰释例之书;又以礼莫精于丧礼,欲撰礼意之书。释例则凌次仲为之矣,礼意则郑注最精,非独丧礼也……其深微至此,得郑注而神情毕见,可谓抉经之心矣![44]150
陈澧还指出,考索“礼文”是解经的“内传之学”,而探求“礼意”系通经致用的“外传之学”:
凡治经者当以内传为先,而又不可无外传之学。内传者,解经之学也。外传者,通经致用之学也。若不为外传之学,何以诵《诗三百》则能达于授政而专对于四方乎!为《礼》学者当知礼意,为《诗》学者当知诗意,即外传之学是也。[44]368
因此可以说,探求“礼意”既是治礼的一种方法与手段,更是一种治礼的目的与理念,展现了礼学家“通经致用”的目的。比如,郭嵩焘以《家礼》为例,通过对朱子《家礼》文本的阅读来反求“礼意”,以期于实践中推崇家礼。在《校订朱子家礼本序》中,他表示:
嵩焘读《家礼》之书,反而求之礼意,以推知古今因革之宜而达其变,稍仿秦溪杨氏《家礼》附注之例,发明所以异同,条次于后,以靳合乎人心之安,而通乎事变之会,使人不敢疑礼之难行,以乐从事于复古。[45]624
又主张明“礼意”即可“理万事”:“窃论《礼》者征实之书,天下万世人事之所从出也,得其意而万事可以理,不得其意则恐展转以自牾者多也。”[46]2唐文治也认为,朱子《家礼》虽历代多有用之,文本虽多有损益,但“礼意”却千古不变:“今世礼学扫地无余,士君子无所遵守,有能本朱子之意斟酌古今之宜续为家礼者,其有功于世道,实非浅鲜。《易传》言:‘变则通,通则久。盖礼制当随时变通,而礼意则千古不变,通人达士必不以此论为迂也。”[47]129晚清士人多将考据与义理结合以研究礼学,以考据“通礼文之穷”,并在此基础上以义理阐发“礼意”,一如曹元弼所讲:“凡经文仪节极繁密处,礼意尤精。”[48]31“礼意,天下之至精也;礼文,天下之至变也。”[48]31通过辨别“礼文”与“礼意”之间的关系,明晰“礼意”的重要作用,晚清诸儒在一定程度上会通了汉、宋,践履了“以礼经世”的理想。
四结语
清代经学的复兴以礼学为先导,并遵循着顾炎武等所开创的“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路径向前发展。清初,在明清鼎革的社会大变动中,对“礼意”的寻求展现了士人的复礼追求及“通经明道”的立学旨趣,及其希望回归与落实孔子礼治思想的目的,呈现出“以礼经世”与“礼时为大”的特征。而后,在清中期考据学大盛的背景下,乾隆初年三礼馆的诏开与《三礼义疏》的纂修,使得對“礼意”的寻求逐渐转向了“礼在器物”与“即器明道”的途径,并呈现出由“器”以明“礼意”,由“礼意”以达“道”的特点。作为寻求“礼意”的手段,考据一途虽经四库馆臣加以推崇,但义理也并未完全湮灭。晚清礼学家继承了乾嘉考据学的传统,坚持“由训诂以明义理”和“实事求是”的治学原则。因此,晚清学者多关注于对“礼文”的研究,以此来辨析“礼文”与“礼意”的关系,主张“通礼文之穷”来寻找蕴藏在“礼文”背后的义理。他们在考据的基础上以义理阐明“礼意”去调和汉、宋之争,呈现出“会通汉宋”与“以礼明道”的新特点。
《礼记·郊特牲》曰:“礼之所尊,尊其义也。失其义,陈其数,祝史之事也。故其数可陈也,其义难知也。知其义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49]3153孔颖达将对礼的义理的阐发,视为“礼义”,即“礼意”,并在注疏中反复强调,“若不解礼之义理,是失其义”[49]3154,“言礼之所以可尊重者,尊其有义理也”[49]3154。近代学人黄侃也将“礼义”等同于“礼意”,并指出礼学的研究应该包括礼之意、礼之具、礼之文三个方面。[50]373陈戍国曾指出:“礼之义,即礼意,乃是礼最重要的组成部分。”[51]18徐复观亦尝言:“礼意是藏在礼的形式后面的精神。”[52]59“礼意”源自“礼义”,可看作是对“礼”的义理或意蕴的诠释,是礼学家“通经明道”的重要方法。从个人角度而言,“礼意”是对内在德行的一种探求,可“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53]4;从国家角度来说,可“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54]82。因此“礼之所兴,众之所治也;礼之所废,众之所乱也”[53]708。鉴于言“礼意”者虽多,但“《礼》之难言,久矣”的情况,黄侃先生提出了明“礼意”之法:“德俭而有度,登降有数,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知此义也,则《三礼》名物,必当精究;辨是非而考异同,然后礼意可得而明也。”[50]374在儒家经典的流传过程中,“礼文”经层累的构建而愈密,“礼意”因外力因素“惑人心”“淆人听”而晦暗却经层累的构建而愈精。作为记载礼学内容的“礼文”在流传与演变过程中虽然有所改变,但贯穿于其中的“礼意”则有不变者在。因此,在礼学研究大盛的时代背景下,清儒也格外关注“礼意”,并将对“礼意”的寻求与阐发作为治“礼”的手段、理念与目的,展现了其“通经明道”的立学旨趣及“以礼经世”的礼治思想。而其所具有的承上启下意义,也很值得关注。
[参考文献]
[1]程灏,程颐.二程集[M].上海:中华书局,2006.
[2]朱熹.朱子语类[M]//朱子全书:第1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3]陈灃.东塾集[M]//陈灃集: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4]孙奇逢.孙奇逢集[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
[5]陆世仪.思辨录辑要[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2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6]顾炎武.亭林诗文集[M]//顾炎武全集:第2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7]顾炎武.日知录集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8]顾炎武.日知录[M]//顾炎武全集:第1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9]徐乾学.读礼通考[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0]王夫之.礼记章句[M]//船山全书:第4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
[11]姚际恒.仪礼通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12]黄宗羲.黄梨洲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9.
[13]万斯大.万斯大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
[14]万斯同.群书疑辨[M]//万斯同全集:第8册.宁波:宁波出版社,2013.
[15]颜元.颜元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7.
[16]冯辰,刘调赞.李塨年谱[M].北京:中华书局,1988.
[17]李塨.李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18]张尔岐.蒿庵集[M].济南:齐鲁书社,1991.
[19]李光地.榕村全集[M]//榕村全书:第8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3.
[20]李光坡.周礼述注[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21]钦定周官义疏[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22]方苞.方苞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23]钦定仪礼义疏[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6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24]秦蕙田.五礼通考[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5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25]戴震.戴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26]戴震.东原年谱订补[M]//戴震全书:第6册.合肥:黄山书社,2010.
[27]章学诚.校雠通义通解[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
[28]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29]孙希旦.礼记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9.
[30]孔广林.禘祫觿解篇[M].光绪十六年山东书局刻本.
[31]孔广森.春秋公羊经传通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32]凌廷堪.校礼堂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8.
[33]石韫玉.独学庐四稿[M]//续修四库全书:第146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34]阮元.揅经室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3.
[35]阮元.揅经室续集[M]//续修四库全书:第143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36]焦循.焦循诗文集[M].扬州:广陵书社,2009.
[37]林伯桐.修本堂稿[M]//丛书集成三编:第58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6.
[38]胡培翚.研六室文钞[M]//续修四库全书:第150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39]胡培翚.仪礼正义[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40]黄式三.儆居集一[M]//黄式三黄以周合集:第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41]黄以周.儆季杂著五[M]//黄式三黄以周合集:第1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42]黄以周.礼书通故[M]//黄式三黄以周合集:第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43]林昌彝.林昌彝诗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44]陈灃.东塾读书记[M]//陈灃集:第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45]郭嵩焘.校订朱子家礼[M]//郭嵩焘全集:第2册.长沙:岳麓书社,2012.
[46]郭嵩焘.礼记质疑[M]//郭嵩焘全集:第3册.长沙:岳麓书社,2012.
[47]唐文治.紫陽学术发微[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48]曹元弼.礼经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49]礼记正义[M]//阮元.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09.
[50]黄侃.新辑黄侃学术文集[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
[51]陈戍国.先秦礼制研究[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
[52]徐复观.两汉思想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53]王锷.礼记郑注汇校[M].北京:中华书局,2017.
[54]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