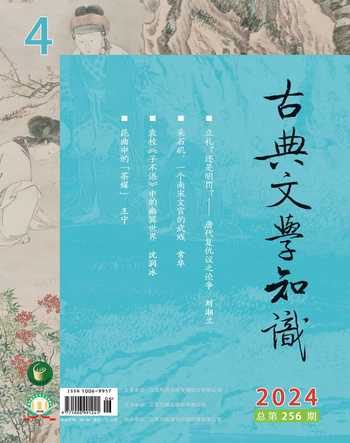王孝伯的名士观漫谈
林宪亮
名士一般是指有名望而未做官的人,而魏晋名士与传统意义的名士又有所不同,他们大多有官职,但不拘礼法、不重实务,乃至特立独行、恃才放达。魏晋时期,哪些人可以称为名士呢?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见解。东晋大名士王孝伯提出了令人感到匪夷所思的三个条件。他说:“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世说新语·任诞》)虽然王孝伯的名士观看起来有些荒诞,也有许多批评的声音,但在魏晋名士群体中也有一定依据。
常得无事
王孝伯所说的“常得无事”,是指如果想成为名士,需要有空闲时间,不能为俗务所累,这是成为名士的必要条件。
魏晋名士经常进行的活动有清谈、畅饮、放逸、郊游、吟诗等;他们活动时或孑然一身,或三五成群;活动的地点有时在河边,有时在山林,有时在官邸;持续的时间或长或短,有时是整日,有时至三更。无论名士以何种方式聚会,地点在何处,持续的时间有多长,都必须以有大量的闲暇时间作为保障,也就是“常得无事”,否则根本无从谈起。
魏晋名士大都是有官职的,其官位有高有低,所承担的责任有大有小,但都应兢兢业业、恪尽职守。事实上,魏晋的大名士基本都是身居高位,在社会上影响颇大。然而,“常得无事”,实际上是要求名士要从政治、军事等俗务中解脱出来,做到心中无俗事,才能心无旁骛地从事名士的清谈等活动。换言之,做名士与做官是相冲突的。“常得无事”的官员势必无所事事、尸位素餐,辜负朝廷的重托,有的甚至给国家和个人都造成了巨大灾难,最为典型的就是王夷甫。王夷甫在西晋末年位高权重,不思报国,却热衷于做名士,倡导清谈,改变了当时的社会风尚。“衍既有盛才美貌,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贡。兼声名藉甚,倾动当世。妙善玄言,唯谈《老》《庄》为事……累居显职,后进之士莫不景慕放效,选举登朝,皆以为称首。矜高浮诞,遂成风俗焉。”(《晋书·王衍传》)王夷甫的名士作风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灾难,自己也身败名裂,为世人所嘲笑。“夷甫虽居台司,不以事物自婴,当世化之,羞言名教。自台郎以下,皆雅崇拱默,以遗事为高。四海尚宁,而识者知其将乱。”(《世说新语·轻诋》第十一则刘孝标注引《八王故事》)王夷甫兵败被俘,向石勒开脱自己的责任,石勒对其嗤之以鼻,最后将其处死。王夷甫对自己执着于清谈而没有担负起国家的责任而感到懊悔,他对一同被执行死刑的同僚说:“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晋书·王衍传》)
对于这种无所事事的清谈,即使是当时的人也有反对的声音。晋穆公永和十二年(356),桓温率兵北伐,进入中原,看到国土沦丧、生灵涂炭,感叹王夷甫等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说:“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虚,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世说新语·轻诋》)这其实也是变相地抨击了名士的清谈误国。王羲之与谢安曾经就清谈是否误国展开过辩论,“王右军与谢太傅共登冶城,谢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王谓谢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谢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世说新语·言语》)对这种于国于民无实际意义的清谈,王羲之是极其不赞成的,他认为官员就应该勤于政事,积极进取,有所作为,而谢安却持完全相反的态度,他否认清谈与国家的安危存有联系。尽管清谈受到了桓温、王羲之的抨击,但总会有人对清谈为之辩护,且振振有词,可见,清谈在当时已经形成风气,积重难返。
痛饮酒
名士常常不拘礼法,不顾世俗,放浪形骸,“痛饮酒”就是其重要表现形式,王孝伯把“痛饮酒”列为名士的条件之一。在魏晋时期,几乎所有的名士都是喜欢饮酒的,有的甚至把饮酒上升到人生十分重要的位置,王佛大号称:“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世说新语·任诞》)张季鹰自叹:“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世说新语·任诞》)
在魏晋名士中,最能体现“痛饮酒”的典范是刘伶。《世说新语》中记载的刘伶的故事,基本是描写他嗜酒不羁的场面。刘伶自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世说新语·任诞》)刘伶的饮酒属于为了饮酒而饮酒,又通过饮酒而放浪形骸,对于别人的评价亦不以为意。有一次,刘伶饮酒后,在屋内脱光了衣服,有人嘲笑他,他便说:“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世说新语·任诞》)刘伶把天地当作房子,把屋子作裤子,反问那些嘲笑他的人为什么跑到他的裤子里来!其纵酒放达可见一斑,这也最终成就了他一世的酒名。
阮籍是魏晋名士中另一个极爱饮酒的名士。阮籍本来不愿做官,但听说步兵厨营人擅长酿酒,贮美酒三百斛,便请求做那里的校尉,“籍闻步兵厨营人善酿,有贮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晋书·阮籍传》)。阮籍的饮酒不拘礼法,他的邻居是卖酒的,女主人年轻漂亮,阮籍常在那里喝酒,喝醉了便卧在女主人身旁睡觉,但并没有非分之举。阮籍的母亲去世,按照礼法,守孝期间不能饮酒吃肉,然而他完全藐视这些规定,既吃肉又饮酒,但他并不是不孝,他对于母亲的去世是极其痛苦的,甚至因之口吐鲜血,昏厥过去。阮籍又常因醉酒而避祸,“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晋书·阮籍传》)。阮籍对现实政治不满,又蔑视礼法,胸中有块垒,内心有郁结,故通过痛饮酒麻痹自我,“王孝伯问王大:‘阮籍何如司马相如?王大曰:‘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世说新语·任诞》)阮籍表面上开怀畅饮、放縱洒脱,其实内心却又常常十分苦闷,正如宋代叶梦得《石林诗话》所说:“晋人多言饮酒,有至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酒,盖时方艰难,人各惧祸,惟托于醉,可以粗远世故。”
还有些名士的饮酒方式也是标新立异的。阮咸及其宗人皆好饮酒,他们不是每人一个酒杯独酌,而是拿一个盛满酒的大坛子,众人围坐在一起,相向直接在这个坛子上痛饮,此时一群猪也围拢上来,共同饮这坛酒,令人不得不惊叹他们的豪放与不羁。刘公荣与人饮酒,不在乎同饮者的身份与地位,他自称比自己强的人不能不与他们喝,不如自己的人也不能不与他们喝,与自己同等地位的人又不能不与他们喝,所以刘公荣整日处于喝酒、醉酒的状态。
名士过度饮酒,自然会影响到他们的工作,也就有负自己的职守和朝廷的重托。周伯仁作为朝廷重臣,肩负重要的政治责任,然而他以名士自居,常年沉湎于饮酒,因而疏于政务,曾因醉酒三日不醒,被称为“三日仆射”,这其实是莫大的讽刺。
“痛饮酒”是一种身体上的放纵,也是一种精神上的麻醉,以逃避这个无力改变的社会现实。更为重要的是,酒是由粮食酿造的,在中国古代生产力落后且物质上极不丰富的情况下,“痛饮酒”实是一种较为奢侈的行为。因此,“痛饮酒”需要有物质条件,也就是做名士需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
熟读《离骚》
在读书方面,名士各有其偏好,并非集中在某一部书上。王孝伯所说的“熟读《离骚》”,实质反映了名士要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彼此才能进行交流。文化修养不仅体现在读书方面,还要能够进行文学创作或学术研究。魏晋名士各有所长,有的出口成章,有的妙笔生花,有的别具慧眼。在《世说新语·言语》中,描述了一群名士一起去洛水游玩,归来后乐广问王夷甫:今天游玩,快乐吗?王夷甫回答说:裴仆射擅长谈名理,滔滔不绝,有高雅的意趣;张茂先谈论《史记》《汉书》,动听得让人心旷神怡;我和王安丰谈论季札、张良,也超凡脱俗。在这里,裴頠、张茂先、王夷甫、王戎四位名士展现了他们在文化修养方面的专长,且发挥得淋漓尽致。
正始三名士夏侯玄、何晏、王弼,开魏晋玄学之先河,他们在老庄学说方面皆有很深的造诣,例如何晏,除了有文集十一卷以外,另外有《论语集解》十卷和《老子道德论》二卷。“竹林七贤”都以诗歌著称,其中阮籍的《咏怀》八十二首成就最大。即使不以文学见长的士大夫,也表现了对于学问的向往,甚至著书立说以求认可。钟会身居要职,以军事见长,但也精通玄学,撰写了一部《四本论》,想得到嵇康的肯定,但又害怕嵇康的驳难,便把这部书从他家屋外投掷其家中,便匆匆离开了。王敦为东晋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他除了是一个野心家之外,同时也是一个名士,喜好清谈,精通《左传》。“敦眉目疏朗,性简脱,有鉴裁,学通左氏,口不言财利,尤好清谈。”(《晋书·王敦传》)
王孝伯认为“名士不必须奇才”,但需要有一定的学问或文学修养作为基础,如果仅仅是有空闲时间和能饮酒,这不但不是名士,反而只是被人嘲笑的酒徒而已。
王孝伯认为名士有三个条件,即“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这些条件要求名士要有空闲时间、能够放纵饮酒、能熟读《离骚》,但本质上却是要求名士不能为俗事所累,同时需要一定的经济条件和文化修养。这三个条件是相辅相成的,不能仅仅满足某一个条件就称之为名士。虽然王孝伯是大名士,但他的名士观也只是一家之言。冯友兰先生在其《论风流》中就明确反对这种名士观,“只求常得无事,只能痛饮酒,熟读《离骚》。他的风流,也只是假风流”。通过观照魏晋名士,可以发现王孝伯所说的名士的三個条件,与魏晋名士有相符之处,但这些绝不是魏晋名士的全部,魏晋名士有着更为丰富的内涵,例如崇尚自由、热衷清谈、追求风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