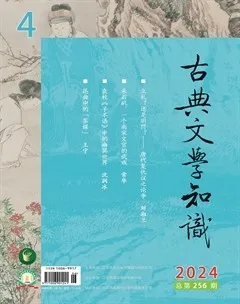《大宗师》1
王景琳 徐匋
【题解】
以篇义命题。
“大宗师”就是值得尊崇且有建树的老师,字面意思并不难理解。但究竟谁是《大宗师》中的“大宗师”就有争议了。自从崔譔、郭象以来,绝大多数庄学家都认为大宗师就是道。
这种说法并非没有根据。《大宗师》中说,曾在儒门修炼的意而子,不知是由于受儒家约束太紧,心里不舒坦,还是真心向往庄子世界的自得,找到无意功名的许由,欲改换门庭,投其门下学道。起初,许由拒绝了他,但意而子却坚持请求他。许由最终为意而子的诚意所动,感慨道:“吾师乎!吾师乎!齑万物而不为义,泽及万世而不为仁,长于上古而不为老,覆载天地刻雕众形而不为巧。”后四句话显然描述的是道的特征,于是解《庄子》者就把“吾师乎!吾师乎”解成了“我的大道啊!我的大道啊”。这样一来,“大宗师”也就成了“道”,“道”也就成了“大宗师”。
可是,此“师”非彼“师”。许由所说的“师”并不是“道”。《庄子》中的“道”也从来没有具体落实到老师身上。做老师,就要教书授徒,可“道”怎么教人呢?对此,《庄子》内篇特别是《大宗师》中论“道”的那段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自古以来,教书育人者才是老师。所谓“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韩愈《师说》),无论韩愈的“道”与庄子的“道”是不是一码事,“道”无疑都是要通过老师传授给学生的。《庄子》中有不少被树立为标杆式人物的老师,如《逍遥游》中尧在藐姑射之山见到的“四子”,《德充符》中的王駘、伯昏无人,《大宗师》中的许由、女偊以及在诸多篇章中现身的诲人不倦的孔子等。这样的老师都是具体的人,所以“大宗师”也应当是人,而不是看不见、摸不着、存在于万物之中的“道”。
那么,到底谁才是《大宗师》中的“大宗师”呢?或者说,《大宗师》中最受尊崇的人又是谁呢?读罢《大宗师》自然会豁然明朗。除了“真人”,还能是谁!整篇《大宗师》,记述的就是一部自古至今的真人发展史。它既是一首真人的赞歌,又是一部真人的悲怆曲。从对古之真人的声声礼赞开篇,到在快要饿死的子桑哭天抢地的悲戚哀鸣中结束,庄子的寓意再明显不过了:那些承接古之真人的纯粹的大宗师,在眼下已经濒临绝迹,再无生存的空间了,代之而来的,不过是些不学无术,整天虚张声势、自我吹嘘、毫无廉耻之心的所谓“师者”罢了。
庄子说
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矣。知天之所为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养其知之所不知,终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
虽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后当,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讵知吾所谓天之非人乎?所谓人之非天乎?
今译
知道自然可以做什么,知道人可以做什么,这是认知的最高境界。知道自然可以做什么,就知道天地万物都是自然而生;知道人可以做什么,就可以凭借自己所掌握的知识,去顺应人的认知尚无法企及的自然,这样也就可以尽享天年而不致中道夭折了。认识到这个程度,也就达到了认知的极致。
虽然如此,仍然存在着弊端。知识是根据所凭借的对象产生的,并由此判断知识是否正确。然而,知识所凭借的对象时时处于变化的状态。那么,如何去判断我所说的自然之所为不是人之所为?或者我所说的人之所为不是自然之所为呢?
说庄子
从《逍遥游》开始,庄子笔下大凡写到“知”似乎都是负面的,特别是《齐物论》中那一大段对大知小知的挞伐,“知”简直就成了人类最大之“恶”。而对那些追求“知”的文人士子,庄子在《养生主》一开篇,便明确地指出,人生有限,而“知”无限,以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限的“知”,那太危险了。既然如此,还一定要去求“知”,最终必然陷于深深的危险之中。在《人间世》中,庄子更直接把“知”比作“凶器”:“德荡乎名,知出乎争。名也者,相轧也;知也者,争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尽行也。”由此看来,庄子是不主张人类有“知”或者去探索“知”的。那么,为什么在《大宗师》中,庄子一反常态,忽然对“知”有所褒奖了呢?
其实,庄子并不笼统地否定“知”,也并不对所有的“知”都大加讨伐。在庄子的心目中,“知”就是“知”,并无善恶之分。但是“知”离不开人,而人也离不开“知”。所以庄子重视的是用“知”的人,他根据人如何去用“知”而作出评判。如果有人从《庄子》一书中得出了庄子彻底否定“知”的结论,那么不妨再仔细品味一下,庄子每每否定“知”的时候,是否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的是用“知”、求“知”、有“知”的人,而不是“知”本身?
如此看来,问题不是出在“知”上而是出在了与“知”相关的人身上。那么,有“知”的人又有哪几类呢?
大体上说,庄子把有“知”的人分为了三类。第一类是以“知”来搬弄是非、混淆视听的,如《齐物论》中被庄子骂得体无完肤的大知小知。这些人不能不说是聪明人,但“聪明反被聪明误”。他们把“知”用到了极致,最终却是害人害己。一向重视个体生命的庄子对这类人甚至说出了“你们去死吧”这样的话。对于这样的人以及他们用“偏”了的“知”,庄子是彻底否定的。
第二类的有“知”之人是庄子在《齐物论》中所说的“知止其所不知,至矣”的人,庄子说,“孰知不言之辩,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谓天府”。庄子认为能有这样的“知”的人是最有智慧的人。这样的人也就是《大宗师》中所说的“以其知之所知以养其知之所不知,终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的有“知”之人。对照《齐物论》与《大宗师》中的描述,两者惊人地相似,显然,对这样的“知”,庄子非但不加以否定,反而是赞赏的。
第三类人是《德充符》中的王骀、伯昏无人以及支离疏、哀骀它。这类人表面上看整天不哼不哈,甚至就是从事“舌耕”,也“立不教,坐不议”,个个都像“闷葫芦”一样。可是又有多少人能进入这样的境界?这样的“知”必定是远远超乎常人的。否则的话,怎么可能做到“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想来后世多少高僧、高道就是读多少书、修炼多少年也未必能接近其皮毛。你说这样的人没有“知”,傻子才信。这样的“知”可以说是“大智若愚”之“知”的极致。
庄子不齿于第一类有“知”之人,骂过之后也就再懒得搭理他们了。第二类人属于有资质做王骀等人的学生的人。而第三类才是庄子要在《大宗师》中大书特书的。他们就是《大宗师》中的主人公“真人”,也是名副其实的“大宗师”。现在,答案才终于揭晓,原来庄子在《大宗师》开篇拎出《齐物論》中的“知止其所不知,至矣”的人作为引子,就是要引出本篇的核心人物“真人”与庄子所尊崇的“真知”。由此可知,对所谓“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看上去庄子是给了他们不少的褒奖,可他们的“知”还不是“真知”,这样的人还配不上“真人”,庄子从写他们入手,只不过借此做个陪衬,通过对他们的肯定而把“真人”与“真知”隆重地推到台前。
庄子说
且有真人而后有真知。
今译
先有真人而后才有真知。
说庄子
这句话字面上不存在任何歧义:先有真人,才有了真知,真知来自真人。只有真人所传授的“知”才可称之为“真知”。对此,庄子已经说得十分明确了。可就是这么一句话,还是很让人琢磨一番的。
首先,真人是从何而来的呢?
或许我们可以从下面紧接着说的“古之真人”一语下手,寻出些端倪。“古之真人”是古代的真人,古到什么时候呢?庄子没有说。但《齐物论》中有一段关于“古之人”的描述:“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恶乎至?有以为未始有物者,至矣,尽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这段话,为我们打开“真人”与“古之真人”以及“真知”之间关系的大门提供了一把钥匙。
真人最大特点之一便是有“知”。“古之人”也有“知”。其“知”的精髓便是理解“未始有物”这一有关人类认知发展的“真知”。“古之人”是怎么认知这个世界的呢?概括起来说,就是物我不分,物与我之间不存在任何分别,物是我,我也是物,物我一齐。能把世界认知到这个地步,“古之人”已经达到认知的极致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古之人”对世界的认知也随着外在世界的变化而改变,人与物之间的区别越来越清晰,人不再是物,物也不再是人,人与物逐渐分道扬镳,最后进入了“是非”的时代。
“是非”的出现,导致“知”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标志,便是“知”从此分裂成为两种不同的“知”,一种“知”是人们用来区分“是非”的“知”,也就是“大知小知”那样的“知”;而另一类则是传承“古之人”的“知”,视万物为一的“知”。后者,庄子又称之为“真知”,而那些具有“真知”的人就是“真人”。真人与“古之人”一脉相承,真人之“知”来自“古之人”,所以庄子说先有“真人”而后才有“真知”。而“真知”又来自“真人”,源于“古之真人”。
那么,庄子为什么在论说“古之人”时,不点出他们就是“真人”呢?道理很简单。古之人的时代,人人都是真人,人人都有“真知”。这是一个不存在虚假,一切都是纯真、无虚饰的时代,自然用不着冠以一个“真”字。而到了“真人”的时代,有关“是非”的“知”出现了,“大知小知”你方唱罢我登场,到处弥漫着与“真”相对的虚假的东西,只是在这样的社会状态下,才有了区分“人”与“真人”、“知”与“真知”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