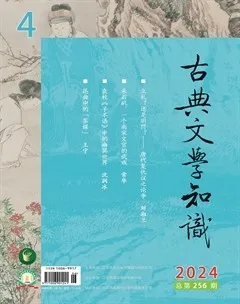“儋耳夜书”中东坡何笑?
罗宁
《东坡志林》是苏轼留给后世的一部小说,其中不少条文以其洁净隽永的魅力,成为明代小品文选本和今天文学选本中的名篇。我最近在注释全书时,发现“儋耳夜书”一条文末的表达不易理解,此前注家解释并不能令人满意,乃撰文讨论,以便加深对苏轼尤其是对其晚年思想的理解。
“儋耳夜书”条见于《东坡志林》卷一《记游》篇,又见《苏轼文集》卷七十一《书上元夜游》,文字略有不同(见后)。这里先列《东坡志林》的原文:
己卯上元,余在儋耳,有老书生数人来过,曰:“良月佳夜,先生能一出乎?”予欣然从之。步城西,入僧舍,历小巷,民夷杂揉,屠酤纷然,归舍已三鼓矣。舍中掩关熟寝,已再鼾矣。放杖而笑,孰为得失?问先生何笑,盖自笑也,然亦笑韩退之钓鱼无得,更欲远去,不知钓者未必得大鱼也。
元符二年(1099)的上元夜,苏轼应儋州当地人之邀,外出到城西的僧舍、小巷中闲逛。当时的儋州地处僻陋之海外,上元节(元宵节)的风俗应不如大陆地区热闹,不过大约还是有一点节庆的气氛,否则就不会是“民夷杂揉,屠酤纷然”了。苏轼游玩到三更时才回家,回来见家人皆已熟睡,“已再鼾矣”。这里说一下“再鼾”,有人解释为“鼾声一声接着一声传来”,似乎不准确。我的理解是,此前苏轼与家人已經睡下,有人来邀约外出,也惊醒了家人,苏轼走后他们又躺下,苏轼回来时,他们便“再鼾”了。这时苏轼进入家门,放下拄杖,忽然便笑起来。苏轼为何而笑?有人说:“苏轼到儋耳已近半年(应为一年半—笔者注),看到不同民族和睦相处,安居乐业,同庆佳节,觉得政通人和,是以欣然自喜。”(王晋光、梁树风译注《东坡志林》)这自然讲不通。苏轼的笑显然针对的是自己,后面也说是“自笑”,怎么会是因为一次夜晚出行、看到热闹纷杂的儋州“夜市”而高兴以至于笑起来呢?
文章最后又引出韩退之钓鱼无得、钓者未必得大鱼的话题,这是要表达什么意思呢?有人说:“这话并不好理解,他是在就自己眼下的情况主张什么样的人生智慧呢?在另外一种文本里,结尾的那句话是‘不知走海者,亦未必得大鱼。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有些消极的意味了,好像就是说钓不钓到大鱼本身是一件不确定的事情,所以抱有非要钓到不可的思想的人是愚蠢的,这最终在他和读者的心上掀起了一阵酸楚的宿命感。”(王连文《东坡志林:天才的游戏之笔》)意思是说,苏轼认为那种执着于钓上鱼的人是愚蠢的。还有人解释最后一句说是“指韩愈不懂得钓鱼的乐趣”(赵学智校注《东坡志林》);或者是“笑韩愈欲摆脱科举仕途去别求功业,终觉仍是世俗之累”(唐玲玲《“寄我无穷境”—苏轼贬儋期间的生命体验》);又或是“苏轼见到日常生活情景而顿然感悟,‘鱼自在我心中,欲求大‘鱼,何必走海远去,汲汲寻觅者未必能得‘大鱼。于是似拈花微笑,心境一片悟然澄明”(唐崛《“生命终站的境界”—苏轼贬儋期间的思想及创作》)。都不得要领。下面谈谈我对此篇的理解。
“儋耳夜书”条的前半部分比较好理解,难点在“放杖而笑”以下直至文末,这是全篇要表达的关键所在。疑难处有三:(1)苏轼为何要笑?因何而引起“得失”的话题?(2)“自笑”是笑自己的什么?(3)笑韩愈又是笑什么?“钓者未必得大鱼”是什么意思?
众所周知,上元夜在宋代是一个很重要的节庆日子,苏轼也多次在这个节庆日作诗。实际上就在儋耳夜游的上一年,元符元年(1098)的上元夜苏轼也写了一首《上元夜过赴儋守召独坐有感》,当时昌化军使张中召苏过饮酒赴宴,苏轼独自一人留在家中“守舍”,“静看月窗盘蜥蜴,卧闻风幔落蛜蝛。灯花结尽吾犹梦,香篆消时汝欲归”,可见其孤独悲凉,最后结句“搔首凄凉十年事,传柑归遗满朝衣”,诗人忆起了元祐年间上元夜宫中宴近臣,贵戚宫人以黄柑相赠的场面。通过这样的对比我们就可以知道,元符二年上元夜的夜游,对于苏轼来说是一次难得的经历,这一晚有良月佳夜,有老书生数人相伴,经过人声鼎沸的集市,必定驱遣了上一个上元夜那样的孤凄之感,而海外异乡的上元节民俗和风貌,应该也会让他生出一种新鲜感。
由此我们再来思考“放杖而笑”。苏轼带着几分夜游的新鲜感和兴奋之情回到家中,看到家人入睡,为何忽然而笑呢?“放杖而笑”后面紧接的是“孰为得失”,也就是笑的内容,可这里说的“得失”是指什么呢?我想,当苏轼看到熟睡的家人们时,极可能在心中产生了一种得意之感:自己获得了一次难得的上元节儋州夜游的经历,而家人则错过了这一“良月佳夜”。更进一步想,这种“得失”到底是我得彼失,还是我失彼得(得一酣睡)呢?然而他转念一想,自己为何要为此种“得失”而计较?自己身处儋州,却算计得与失,实在是无谓而可笑。这便是他的自笑。苏轼由上元夜夜游的得失,瞬间想起人生得失的问题。实际上,关于人生之得与失,苏轼没少思考和谈论。
早在熙宁三年(1070),苏轼送落第的安惇回四川老家时作《送安惇秀才失解西归》诗就涉及这个话题,诗开头四句是勉励安惇,接下来写自己:“我昔家居断还往,著书不复窥园葵。朅来东游慕人爵,弃去旧学从儿嬉。狂谋谬算百不遂,惟有霜鬓来如期。故山松柏皆手种,行且拱矣归何时。万事早知皆有命,十年浪走宁非痴。与君未可较得失,临别惟有长嗟咨。”自己本来在家乡读书问学,却因“慕人爵”而“弃去旧学”,结果机关算尽却百事不顺,现在唯有鬓霜相伴。当时苏轼在熙宁变法中被疏远,故回顾自己应制科以来的经历,以为万事皆有命,这十年来全是“浪走”。安惇科举不利固然是某种意义上的“失”,而自己当年虽有科举之“得”而进入仕途,现在看来难道不是一种“痴”?所以,计较我们二人孰为得失,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说苏轼此诗表达的是命运难知、得失难计的思想,他在《送杭州进士诗叙》中强调的又是“得而以其道”:“士之求仕也,志于得也,仕而不志于得者,伪也。苟志于得而不以其道,视时上下而变其学,曰:吾期得而已矣。则凡可以得者,无不为也,而可乎?”此文写于熙宁五年(1072),杭州太守陈襄为送杭州举子入京参加礼部试作诗,苏轼作此叙,意在劝诫举子们不要为了“得”而变其学(从新学)。这篇文章体现出苏轼一贯秉道行义、不曲学阿世的风骨。
在给前辈的文章中,苏轼常常夸赞他们忘得丧、齐得丧的人生境界。如为韩琦作《醉白堂记》,称赞他“齐得丧,忘祸福,混贵贱,等贤愚”(《醉白堂记》);给欧阳修写贺启,称赞他“自非智足以周知,仁足以自爱,道足以忘物之得丧,志足以一气之盛衰”(《贺欧阳少师致仕启》)。如果说这些文章里的话还有几分恭维和客套的成分,那么他给后辈的文字说到人生之得失,更带有深深的个人感悟。元丰八年(1085)《与千之侄》信中说,“人苟知道,无适而不可,初不计得失也”,劝勉侄子“慎勿动心,益务积学而已”。绍圣三年(1096)苏轼在惠州写给侄婿王庠的书信里,又说:“应举者志于得而已。今程试文字,千人一律,考官亦厌之,未必得也。如君自信不回,必不为时所弃也。又况得失有命,决不可移乎?”(《与王庠书三首》)再次表达了“得失有命”的思想。这种命定论的表达,实际是劝人不必以得失为念,而应秉持自己的道与学。至于苏轼本人能否做到忘得丧呢?他虽然说过“进退得丧,齐之久矣”的话(苏轼《与杨元素十七首》其十七),但有时候又承认自己的境界还差一点点,《送杭州杜戚陈三掾罢官归乡》诗中说,“老夫平生齐得丧,尚恋微官失轻矫”,认为自己因杭州通判的“微官”而如拘囚(用韩愈《同冠峡》中“囚拘念轻矫”之意),后面又说“徇时所得无几何,随手已遭忧患绕”,是说自己或其他做官之人实际所得无多,却饱受忧患。
了解了苏轼在其他诗文中提到的得失,我们就可以理解苏轼夜游后为何因念及“得失”而自笑了。苏轼夜游回来后先是因见家人熟睡,而引起我与彼“孰为得失”的念头,继而想起自己这样的仕途和人生,孰为得失?他的自笑实际上来自进一层的反思:一次简单的夜游竟引出自己如此的联想和回忆,说明自己还是没能摆脱得失休戚之感,不能做到像前辈那样“忘得丧”啊,何况自己早已说过“得失有命”,就在不久前来海南的路上给苏辙的诗,还说“我少即多难,邅回一生中。……老矣复何言,荣辱今两空”(《次前韵寄子由》)呢。想到这里,苏轼便哑然失笑了,这是笑自己尚计较于得失,笑自己自寻烦恼。
在这自笑的同时,苏轼又联想到另一件好笑的事情,那就是“韩退之钓鱼无得,更欲远去”,这来自韩愈《赠侯喜》诗中讲的事情和道理。此诗是一首七言古诗,前面大段是描写侯喜邀约韩愈钓鱼的经过,平明就出了洛阳都门,行走在荆棘丛中,下午来到温水(洛河)边,“温水微茫绝又流,深如车辙阔容輈。虾蟆跳过雀儿浴,此纵有鱼何足求”,看起来就不像是能钓上鱼的地方,但是既然来了,还是“盘针擘粒投泥滓”。两人从“晡时坚坐到黄昏,手倦目劳方一起”,终于有鱼上钩了,“举竿引线忽有得”,结果,“一寸才分鳞与鬐”,令人丧气,“是日侯生与韩子,良久叹息相看悲”,两人相视苦笑。这一部分描写活泼,语言风趣。最后十二句是韩愈的感慨:“我今行事尽如此,此事正好为吾规。半世遑遑就举选,一名始得红颜衰。人间事势岂不见,徒自辛苦终何为。便当提携妻与子,南入箕颍无还时。叔□君今气方锐,我言至切君勿嗤。君欲钓鱼须远去,大鱼岂肯居沮洳。”意思比较清楚:我一生行事就像今天钓鱼,忙活半生(当时三十四岁),始得一出身(进士),但此前数年在汴州、徐州的幕府中“辛苦”从事(而且两次侥幸免于军乱),后入京调选却未果,便到洛阳闲居。因此,韩愈当时萌生了携妻子远去箕颍(像许由、巢父那样)隐居的想法。《赠侯喜》诗最后说,“君欲钓鱼须远去,大鱼岂肯居沮洳”,有两层意思,字面义是劝侯喜不要在这洛水钓鱼了,这里没有大鱼,大鱼怎么会在这浅水之中;隐含义是劝他(也包括自己)不要再追求仕途功名了,不要像很多两京之间的隐士那样“以隐待仕”,而应远遁他处。然而有趣的是,后人对此诗的结句理解却又有一种,大鱼被理解为高官显爵,钓大鱼就变成汲汲于求官之意了。
宋人樊汝霖(《韓昌黎诗系年集释》引)在注解韩愈此句时就是如此,还引出了苏轼的话:
苏东坡《记儋耳上元》:“放杖而笑,过问何笑?曰自笑也,然亦笑韩退之钓鱼无所得,更欲远去,不知走海者未必得大鱼也。”盖公作此诗时年三十四,去徐居洛,方有“求官来东洛”之语。而东坡则晚岁儋耳,发于忧患之余。览者无以为异。
在分析樊汝霖的注释前,先说一下苏轼原文的版本异文。《东坡志林》的《儋耳夜书》与《苏轼文集》的《书上元夜游》文字略异,前者的“问先生何笑”,后者作“过问先生何笑”,前者的“钓者”,后者作“走海者”。樊汝霖所据苏轼文字版本显然近于后者。樊汝霖认为,韩愈作诗时正当盛年的三十四岁,居住在唐代两京之一的洛阳,说过“求官来东洛”(《县斋有怀》)的话,正欲有所作为,而苏轼当暮年(六十四岁),经历过各种忧患,故有此说。樊汝霖的这段话提供了宋人对韩愈诗句的一种解读,实际也是苏轼的理解。在二人看来,韩愈在洛阳附近仅得小鱼,而欲往远处钓大鱼,是一心求官、欲求大官的意思。二人实际上对韩诗的原意都有误会。正如清人王元启所说:“公欲远去,盖有高隐之思,指尘世为沮洳耳,非欲驰逐于名利之场别求厚获也。樊谓公年三十四云云,以此为两人所见之异,岂非错会韩公主意。”樊汝霖专门解释韩愈那时三十四岁而且正当“求官来东洛”,意谓韩愈的行为应予理解,以免览者因苏轼之语而看低韩愈。但这样一来,樊汝霖和苏轼一样,都是“错会韩公主意”了。
苏轼想起韩愈“君欲钓鱼须远去,大鱼岂肯居沮洳”的话,正是建立在这种误会之上,这让他哑然失笑:我如今已经“远去”来到这极远的海外之地,可我这个“走海者”未必能得到大鱼啊!苏轼写下这句话的时候,除了想起韩愈的诗感到好笑外,可能还想起《庄子·外物》篇里记载的任公子在东海钓大鱼的故事,在那个故事里,任公子是钓上了大鱼的,故事也说,“揭竿累,趣灌渎,守鲵鲋,其于得大鱼,难矣”。但苏轼想说的重点自然不是钓鱼,也不是嘲讽韩愈的求官热情,也不是宣扬《庄子》的通于至道,而是想到自己“走海者”的身份和不得大鱼的巨大反差。苏轼将自己的现状和被误解的韩愈诗猛然联系到一起,造成一种奇特的诙谐效果,在前面自笑之外,又生出一层笑意来。
再总结一下苏轼在儋耳夜游后的笑:他先是生出自己和家人此夜得失不同的念头,一转念间便想起自己的仕途风波,连续贬谪惠州、儋州的经历,这是得(“兹游奇绝冠平生”),还是失(官场失意)呢?本来自己早已知晓“得失有命”的道理,说过“荣辱两空”的话,这时却为是否夜游而计较“孰为得失”,实可自笑。既而他又由“得”联想起韩愈说过欲得大鱼要远去,这又是一个笑意(笑点),我如今已来到这天涯极远之处,又哪有大鱼可得?韩愈他不知道,“走海者未必得大鱼也”!事实上,苏轼将韩愈诗和自己的处境相联系,正呈现出一种幽默的效果。在外人看来贬官儋州是九死南荒的厄运,苏轼想到的却是来此未必得大鱼、韩愈在胡说,他那淡然的微笑,忽然消解了前面想到人生得失而生出的焦虑感。读者在领悟到苏轼的这些心理活动之后,一定会随他一起发出会心的微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