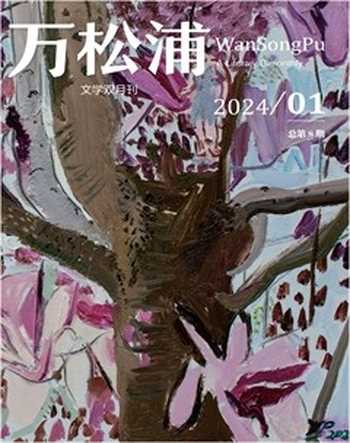彼时此刻
今天不是问问题的一天,
不是在日历上的一天。
今天是自觉的一天。
今天是爱者,是面包,是温柔,
是显现:超出能言之外的显现。
——[波斯]鲁米
一怀盈香
在南方的公路上行驶,绿树葱茏。打开车窗,闻外边的花木气。忽然,一只迎面来的蜜蜂冲进车窗撞到我脸上。我们都带着速度,它借天生的翼翅,我靠人类发明的机器。是瞬间的撞击,继而,它落进我怀里。晨光下,它细长的翅膀丝帛般晶莹,战栗、翕动,甚至能看到它肚腹的急促起伏。它一定给撞晕了。对它来说,那是个再平常不过的早晨,太阳刚刚升起,展雾正在散去,竞相开放的花儿期待着各路蜂蝶。我是交通肇事者,太突然了,它甚至来不及本能地伸出自卫之剑。我定定看着怀里的它,渐渐苏醒、努力、努力,抖开了薄翼。振翼之声在我耳边竟震耳欲聋,多么欢悦的声音。摸索了片刻方向,它飞出了车窗。短暂的一两分钟,事件跌宕起伏。是我和它之间的事,身旁坐着的人懵然不知。大约发生在几年前。我惊奇的是,当它从我怀里飞走,我忽然想起它撞到我脸上的那一刹那,我闻到的花香,凝结在那一个撞击点上,针尖一样大小的花香,却异常浓郁分明。一个带着花香飞行的精灵,我们遭遇,又倏然各奔东西,两个物种,大小迥异,但在同一个世上,看似没有千系,却在被众人熟视无睹的唇齿间的甜蜜时刻交集——对人类而言的单向度的交集。之前一刻,它落在哪朵花上?之后,它又飞过哪些花丛?
很多年前的冬日,在宁夏西吉县的芦子沟,一家农人院落,白净的黄土崖畔布满整齐的野蜂巢。那是个能被干涸刺疼眼睛的地方。农家阿婆拿出油饼,抹上蜂蜜给我吃。浓稠金黄的野蜂蜜,小小地舔一下,除了甜蜜,满嘴漾开的还有花香,多么神奇,就在那个干坼的芦子沟。阿婆说,一年里的一定时日,蜂儿们结伴飞进院子,住进蜂巢,蜂儿认人,不是每家都有这样的野蜂巢,至于花儿,开花的时候,芦子沟的沟底和两边山坡上,满眼睛都是。梦幻一般,我想起阿婆家那头口渴的骡子,解开牵绳后,疯了一般飞奔到芦子沟沟底那个细小的泉眼旁,脚下轰然腾起的黄土,能迷人眼目。但是,在那个草木完全蛰伏的枯黄的冬日,我眼前看到的却是满眼的花儿,还有那些带着花香飞行的微物之神。在苦焦的黄土地上,匆忙的小天使,早出晚归,追着不多的开花时日,酿造甜蜜,就在那辽远而又遍布细节的时光里。
告别时刻
和我们生活了二十年的“老虎”要走了。它是一只猫先生,我叫它“老虎”。它已腾空肚子,不吃不喝半月有余。它曾经时时刻刻保持着猫科动物的优雅,能在任何杂乱的环境以最舒适的姿态安然卧眠,但现在,我得帮它做出它惯有的姿态。白天,我把它抱到电脑桌上,晚上抱它到床边。它的皮毛枯草般已尽失光泽。这天傍晚,天色将黑,我感觉告别时刻就要来临。我抚摸它,和它说不要害怕。我一直相信它能听懂我的话。在它还有力气说话时,我叫它一声,它应我一声。日常中,我们你一言我一语没有中断过。这一刻,我们只能用眼睛交流。它侧卧在沙发上,我坐在小凳子上,我们平视。它眼睛一眨不眨望着我。我把电视的声音调到如常,让它感觉它活过的世界没有变化。在它耳边放了音乐,那是我写东西时,和卧在电脑旁的它常听的乐曲。我静静看着它,心里万般感受。它静静看着我,眼角忽地滚出眼泪,泪珠越滚越大,凝固在眼角。它的肚腹不再起伏,身体渐凉,它走了,眼角挂着一颗对我滚出的眼泪。在它生前,我从未见过它流泪。那一刻,我再次想定,这小小的生命,定有灵魂。“谁说兽的灵魂要下地狱?”苏珊·桑塔格曾经的万里之远的反诘,现在变成了我与她的小声对话。
相框里,有一张它生前的照片。趴着,一只眼睛藏在爪后,另一只眼睛调皮机敏地偷看我。那时,它那么年轻,它的眼睛明净若琥珀,那时我未曾想到它琥珀般的眼睛里会流出眼泪。
小女孩思思所讲
小女孩思思转眼8岁了,想一想,时间过得真是又快又慢。晚上,临睡时,她侧向我,捋平长发,合着双手压在脸颊下。枕头边睡着她的“小花”,一条梅花斑点的棕黄色毛绒小狗。她若有所思地看着我,过了许久,说,我将来结婚后,想生一对双胞胎,将来,我长大了,用不着小花陪我了,我把小花送给我的女儿。弟弟将来应该也不喜欢他的变形金刚了,我就送给我的儿子。小女孩思思一脸憧憬。我说,那想好和谁结婚了吗?她说,暂时还没有。
“将来”,这样的词,小小的孩子最有资格说,“暂时”也一样。很快的,小女孩思思睡着了,我看着她,一直在想,多美的小仙女呀。
小女孩思思哄妹妹睡觉
小女孩思思、思思四岁的妹妹、我,三个女生一起睡觉。妹妹前一晚挨着我睡在中间,今天还要。我知道她是胆小害怕,但思思不依,说该轮到她睡中间。妹妹大哭,说自己是宝宝。思思坐起来问,难道我不是宝宝?两个人都哭。我说,姐姐能哄妹妹睡觉吗?两人不哭了。思思说,我可以试试。她开始唱摇篮曲,那么好听深情的摇篮曲,不像一个八岁的女孩唱的。“北风吹过浪卷起,有一条河充满着回忆,安心睡吧小宝宝,一切的答案能找到……”思思像妈妈一样,一只手跟着节拍轻轻拍着妹妹。她的动情的歌声在关了灯的屋子里亮亮的,似乎窗外林立的高楼上,将要安睡的人们都能听到。接着,她们都睡着了。妹妹的小手还搭在我脸上。我的耳朵里一直响着思思的歌声,直到现在。
后来,小女孩思思说,摇篮曲的名字叫《阿塔霍兰》,是一个电影里的歌儿。她说,阿塔霍兰是一条河,这条河很神奇,能在这条河里看到往昔。我问思思什么是“往昔”,她说就是过去的时间,比如昨天,还有前天。
小女孩思思的一幅画
小女孩思思在她小书桌前的墙上用不干胶粘了一幅她自己画的画。
是不同颜色的彩笔画出的或直或弯的线条,线条有时重合有时各自路线清晰。画满了一张白纸。我看不懂,问她画的是啥,她说是全家福。
画上有两个深色的圆点,思思说,一个点是家,一个点是小区里爸爸的工作室。爸爸是一条粗粗的黑线,这条线很简单,基本两点一线。妈妈是红线,这条红线一直绕到白纸边,思思说妈妈常常要去外边,做很多事,這些螺旋一样绕到很远的一个个圈圈还是妈妈做的事。弟弟是黄线,线条跳跃得最厉害,因为弟弟还没上学,他很自由,可以到小区的好多地方和小朋友们玩。思思是粉色线,因为她最爱粉色。粉色线条和爸爸的黑线基本重合,因为被疫情封控在小区的时候,思思和爸爸一样,不是在家就是在爸爸的工作室,写作业看书。妹妹呢?思思哈哈大笑着说,你看这些黄线是妹妹,这些线最乱,跑得也最远,因为她一分钟都不安静,每天阿姨要领她到小区外的公园玩很久,走很远很远的路。那些黄线一直画到了白纸外边。
活着的颜色
什么样的颜色最难以描述?
有光泽的颜色。
比如禽鸟的羽毛。生命力旺盛时,羽毛熠熠生辉,并与周遭的光亮呼应。我多次惊诧于动物园里看到的各种美艳的鸟的羽毛,微妙的色泽在人类制定的色谱上找不到对应的名称。
花儿盛放时,缤纷的颜色自然也能好看到极致,但少了流转。
有一天,在一家野生动物园,看到美洲红鹦,红鹦是特立尼達的国鸟。除了细长弯曲的喙,它全身,包括腿和脚趾都是美艳的红,无法描述的红。红色中的万千种红,如同所有色系中的万千种色,如同人和树叶,绝无雷同。红鹦喜欢结群,它们在公园里的人造岩石上站成艳美的一排,左顾右盼,嘀嘀咕咕。太阳落山时,我走下山坡,再次看到那群红鹦,吃了一惊,这一刻,我发觉它们仿佛换了一身羽毛,用另一种无法描述的红色,在黄昏中明媚着。
有光泽的颜色,是有生命的颜色,在时序的渐变中会暗自流转。包括白色的羽毛,一根飘落的白鸽的羽毛,我曾拿它和飞鸽身上的羽毛比较,依旧洁白,但不是那种活着的白。
红鹮喜欢在沼泽地生活,据说它们在沼泽地的大树上成群结伴地过夜。月光下,那种浓艳的红又将是怎样难以描述的红呢?还说它飞翔起来,叫声高昂而忧伤,这声音和着那身红色,会不会有些凄绝?
开会的猫
已是子夜,和几个好友小聚,喝了点儿酒。总觉得酒能让人内心温热,让世事柔软。街上人影稀落,回到小区,拐到楼角时,看到一群猫,至少七八只,围拢着,像在开会。那晚是刮过不小的风的,杨树上的枯叶被吹下一半,我踩着落叶,咔嚓咔嚓地走过来,警觉的它们不会听不到,但它们丝毫没有被我惊扰。它们半蹲着,围成一圈,似乎在议事,这事儿似乎又很合适在夜深人静时商讨。也许,它们都瞄了我一眼,不动声色地瞄了我一眼。但我确定的是,路过它们时,我一定笑了,我在心里,一定和它们一一打过招呼了。
不要在过早的黎明打扰它们
一次采风活动,住在山林里。
一棵老山楂树正花团锦簇,木屋散着柏木的香气。一整夜,耳畔都是不远处小溪的水声。晨曦微露时,几人结伴,听着水声到了溪旁。空气沁人心脾,杂花生树。大家愉快说笑,突然,我觉得撞进了一团黑雾。惊叫。头上身上罩满网丝,方知冲破了一张蛛网。一只落地的大蜘蛛惊慌地跑进草丛。我们彼此受了惊吓,但我很快恢复了平静。
那个蜘蛛,它编织了多久,才织成这样一张铺天盖地的丝网。
太阳尚未升起,大自然还是它们的。那些昼伏夜出的鸟儿、打着灯笼的萤火虫、夜色里悄悄绽开的花儿和配合着花儿们传播花粉的蝇蛾。那个蜘蛛呢,天色尚早,它还没打算收丝回巢。
一天,在电视节目里,借助摄像镜头,看到了晨曦将明时的一角微观世界。纵横交错的蛛丝,借助植物,拉开晶莹闪烁的天罗地网,就等着那些不谙世事的小飞行者蒙头撞入。只是人类视力太差,看不到丝网。于人而言,它们太过纤细,冲撞了它常常又无察觉。我后来就想,生物为着生存,都有自己的作息。大自然有着适者生存的严明律令,暗夜到来,人就应该待在人的巢穴里,即便东方将白,也不要在过早的黎明去打扰旁的世界。
狐仙
在河北怀柔的一个小村子里,听小席讲狐仙。小席是当地农民,喜欢讲故事,给当地农民做了一档名叫“满庭芳”的广播节目。小席说是她亲见的,就在土地庙门口。夜晚,月光很亮,一只白狐在村里的那条土路上走着。是夜晚,但小席说真切地看到了白狐的妖媚。狐的妖媚在眉眼间,月光里,小席也搞不懂怎么能把狐的眉眼看得那么清亮,细长的脸,细长的眉眼,似乎含笑。狐就那样含笑着回头望了一眼她,然后不急不慌婀婀娜娜地走远了。狐的媚,还在那妖娆的走路姿态里,小席扭着腰身说。
狐的听力极好,所以稍有窸窣的响动都要回头。我常见的纤细的小席,走路的样子也是风摆柳,窸窸窣窣的,似乎脚不落地。我笑说她们是狐仙相遇。
黑泽明的电影《梦》,颜色极是绚烂。好几个梦境组成的片子,其中一个梦叫《太阳雨》。晴朗的天,却下着亮晶晶的雨,小男孩很好奇。妈妈说,狐狸常常在下太阳雨的时候娶亲,这时候人一定不能去树林打扰,如果惹得狐狸不高兴,会给自己带来麻烦。妈妈的话让小男孩更加好奇。他偷偷跑进森林,树木间,突然升起一团白雾,雾里,远远走来两队狐狸,打头的果然是衣着华丽的新郎新娘。小男孩躲到大树后面,胆怯又好奇地看着。狐狸们两步一顿,再走三步,倏然停下,然后整齐地倏然扭头旁顾,睁大眼睛,定睛片刻,继续前行。我明明从狐狸面具上含笑的眼睛里看到它们发现了男孩,但它们仿佛又没有看到他。我每每看到这个镜头,看到狐狸们定睛看着小男孩的那一片刻,忍不住要笑。良善可爱的狐狸们在偷笑,并非男孩妈妈所言的那般叫人骇怕。但小男孩回到家时,妈妈把他堵在门外,说狐狸送来一把刀,说他偷看了不该看的事,狐狸要他拿刀自裁。小男孩不想死,妈妈说,除非求得狐狸原谅。可是,狐狸们去了哪里呢?妈妈说,有彩虹的地方。男孩踩着一地茁壮的野花向远处的田野走去,天上正弯着半轮巨大的彩虹。
《水经注》写到“河”,开篇不久就说到狐狸。说盟津河天寒时结冰,河结冰后,人们先要偷偷看看狐狸是否肯过河。狐狸耳灵,它们俯身听河,若听不到冰底的水声才会过河。“人见狐行方渡”。也因而有了“狐疑”一词。我想,这么看来,狐多疑能疑过人吗?黑泽明的《太阳雨》的镜头一直到那个小男孩看到横跨在田野上的半轮彩虹为止。咦,狐狸们早忙它们的喜事去了。
背道而驰的颜色
想不出颜色里还有什么比它们如此对立:白和黑。
白是渐渐亮起的黎明,是呈现,是孩童,是一望无际的理想,是嘹亮的声音。黑是幽咽,是结论,是老人,是对无尽的包纳,是沉默,是地上的果实或者地下的骨骸。
白是一种危险的颜色,它清浅摇曳,纯洁脆弱短暂,叫人疼惜。稍不小心,便被破坏。黑色深厚到亘古无边,如同坚硬的陨石,包纳万象,无法洞穿。万千言说万千悲喜凝滞。
白和黑,彼此无法拯救,它们行驶在无法相遇的路上,世间还有哪两种颜色,这样背道而驰,又这样被人们给予无尽的隐喻?
岔道口的路牌
岔道口,高蓝的天空下,路牌矗立。像沉默的智者,它高瞻远瞩。用箭头做手势,果断、明确、不容置疑。在路牌下环顾,着迷似的想象各个方向。卓尼、临潭、合作、赤壁幽谷、亲昵沟、新城。这些名字有些熟悉、有些陌生、有些看上去是人们活出来的地方、有些是大自然的栖居地。但不管怎么,这些名字靠在一块路牌上,它们就像紧挨着的邻居。
扛着风走
一个小镇的下午,大道笔直无人。我用伞扛着风走。风有时很沉、有时很轻,我觉得风在和我玩,它有时压弯我让我下起苦力。我知道,在我目之所及之处,风散布得无边无垠。阳光下,道路白净,路上铺满树的影子,影子美得惊人。有那么一刻,我的伞里了然无物,我以为风停了,但我定睛树影,发现风正在树的细枝末节,你推我搡偷偷嬉戏,我还听到了它们最细小的耳语。
寂静的声音
一段日子,生病在家,不再早出晚归疲惫不堪。但躺在床上,夜夜难以入睡。我想起纳博科夫的话,人在闭合的眼睑上能看到想象的事物。果然能。我能看到生前的爸爸、妈妈在幽黑中亮亮的身影,他们的脸庞,样子,像在小小的幻灯片上。纳博科夫在书里写到,他能看到字母的颜色。我不能。睡不着,仔细辨听寂静的声音。寂静就是无声吗?我在万籁俱静中,听到很多很多气泡破灭的声音,寂静的泡沫,此起彼伏的破灭声,我有些心惊。
想跟着河一直走下去
那一天,有那么一刻,我内心忽然升腾起从未有过的渴望,我想跟着河一直走下去。那一刻,是一个边远小镇的安静的晌午。我深陷在一个巨大的山谷里。眼前的河在安详的小镇里波光粼粼地流淌。我想,一定是某种隐秘的东西一瞬间击中了我,让我有了这个强烈的愿望。那一刻,那是一条为我存在的河,那一刻,我只对这条河存在,这是那一刻,我和这个世界最单纯的关系。我想跟着这条河一直走下去,这是那一刻,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单纯的想法。
想起茶卡
想起茶卡,就觉得它大而远,其实,《汉书·地理志》里,茶卡“盐池”与家乡“金城郡”比邻而居。茶卡盐湖的大,绝非因为它有十几个西湖那样大而大,它的大和远很奇怪,听人唤它一声“达布逊淖尔”,就觉得它大,尝一粒风吹到脸上的盐,就觉得它远。就像家所在的很多地方,有了铜器陶器剑齿象的化石,就有了说不上的大和远。
那天傍晚,起初,月亮像一个薄薄的白纸灯笼,挂在祁连山这边,转过头看,夕阳马上要给那边的昆仑山收尽。站在分叉道上,一边通向小镇,一边通向盐湖,小镇上人影绰约,盐湖已隐入苍茫。月亮亮起来了,越来越亮的圆月旁边有颗星,像个金色的酒窝。我站在夜空下,这一边是祁连山,那一边是昆仑山,夜色里的盐湖就安睡在它们中间。山上的雪让月亮照得更白了,不知为啥,有一刻怔怔站在那里,有点儿想落泪。
我想,再到茶卡盐湖,一定穿浅色的素衣,不聒噪不乱行,最好披身雪或者盐,在湖边好好坐些时辰。
二人关于“弓”的对话
甲:那时候网站风行时,我在一群网名里一眼能认出你,你喜欢很动态的词,比如“箭在弦上”“马踏飞燕”“拓跋长风”等。
乙:你有一次起名“杯弓蛇影”,我也猜定是你。你喜欢的不是这个意思有些可疑的词,而是“弓”字。“弓”,满满地弯折着身子,满满的隐忍谦让,但当它打开身体,像将要凌空的猎豹的背脊,就等着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甲:你说的“弓”,韬光养晦,好像藏着心机,这我不大喜欢。但的确,当它被迫混同于浅薄甚至恶意,没必要时刻做出张弓拉弦的姿态,那和弓的理想不匹配。挂着的弓,即便蒙尘,也不能说明它在沉睡。弓的使命,弓心里清楚。
一些为证明虚妄而存在的事物
小时候,只有过年才能见到一样稀罕的物件,我们叫它“乒乒乓”。人工吹出的长颈的玻璃葫芦,轻薄透明。父亲带我们去城隍庙,寻着“乒乒乓”的响声,买到一个,然后对着小小的葫芦嘴一吹一吸,脆薄的葫芦腹底呼吸一样一起一伏,并发出“乒乒乓”的脆响。父亲也让我们吹,我们担心到颤抖,因为它是如此脆弱,声息太大它就震碎了,拿它时手稍重些也就碎了,它脖颈细长,不高高举着,稍不小心碰觸到别的东西,它也碎了。过年时,唯独它碎了,父亲不会心疼也不会觉得晦气,它好像就是为着人们听几声“乒乒乓”而存在的。父亲年年过年给我们买“乒乒乓”,但很快它就不见了,一点儿脆薄的玻璃碎片都找不到,好像它从来没有到过我们身边。它就是一样为证明人世的虚妄而存在的事物。和它相似的,还有惹得孩童欢快追逐的色彩缤纷的肥皂泡、一瞬即逝的耀眼的烟花……还有,一定还有许多想不起的相似的事物。
独一无二的酒
小镇广场一侧,有家“川味小馆”,是一对小夫妻开的,店里主营小吃,酸辣粉味道不错。墙上贴了一张巨幅海报,上面是看起来香味诱人的重庆烤鱼。我看到广告词里有个错别字,几次欲说又休。在这里,字是配角,错与不错,也都无妨。八张木桌,一个铁炉,店里暖和干净。再次去时,我叫上了外省来的朋友,要了麻婆豆腐、蒜蓉莜麦菜和回锅肉。其实,除了酸辣粉,我知道他们对川菜没有把握。妻子出出进进神色匆忙,买来豆腐、菜、豆瓣酱,半截门帘后的灶房一下子变得活色生香。
端上来的饭菜不是川味,但我们吃得开心。在这个寒意浓浓的深秋,我们从遥远的四面八方聚到这个偏远小镇的一个小店,应该感激这些热乎乎的饭菜。很晚了,小老板送我们一瓶用桑葚泡的青稞酒,瘦高的酒瓶,里面一半桑葚一半酒。把酒倒进四盏玻璃杯,都是浓郁的桑葚色。第二天,衣服上有几滴洇开的紫色,花儿一样。我忆起酒的味道,清冽直白的青稞酒,因了桑葚,滋味变得柔软深厚,还有些黏糯。
酒瓶里的酒,那些青稞,那些桑葚,那些田野里的事物,一次次被倒进四个亲密的杯盏里。多幸福呀,那个夜晚,我们喝到了这辈子独一无二的酒。
“青冈”和“橡树”
山坡上的树,多的是青冈。一个当地人说。
山坡上,青冈树的叶子正要变红。
很多年前的一个冬天,我到兰州郊区一个叫青冈岔小学的村小支教。那个通向远方的道路岔口,很适合长青冈。村小的老师指着校园里瘦凛凛光秃秃的树说,这就是青冈。在西北,落光了树叶的树,那么相似,我最终没能认清青冈的样子。
那天,我仔细察看了青冈,摘了几片青冈叶细看,像手掌,叶面覆盖一层蜡质。突然,我听到有人说,青冈就是橡树。啊,于我而言,这个没有被打通的树的名称在我的生命里横亘了那么多年。父亲年轻时手里常耍的一根白亮的棍,就是青冈木。父亲说,青冈木很硬,但也很韧,所以适合当棍耍。那时,在我眼里,青冈只是根棍,我心里,还没有青冈树的样子。
那天,我才知青冈就是橡树。作为橡树的青冈,让我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想到肖洛霍夫,想到西伯利亚,想到更远的东方和西方,甚至所有辽阔的世界。
一个鞋匠的脸
鞋匠是几条街上的人都熟识的。在排洪桥上的十字路口摆摊。他反复更换过好几个方位,西北角、东北角、西南角、东南角,跟着检查部门的要求。后来,为了不影响街面,他干脆把摊位摆进桥的护栏里约一米多见方的地儿上。
鞋匠一口四川话。矮个,圆脸,粗短手,一年四季,手指皴裂。多年前,鞋的质量普遍差,鞋匠很忙,有时小摊上围着的人需要排队。鞋呢,大抵是鞋底开了、缝线断了,或者鞋面破洞了等等。皮鞋、布鞋、球鞋、雨鞋,什么鞋都有。女人们让他在新高跟鞋的鞋跟上钉一层橡胶皮,这样,走起来不滑又没声响。橡胶皮大都是自行车或架子车的轮胎,内胎、外胎,有薄有厚。男人们有些时候让他在鞋后跟底上钉块铁片,像马掌一样,走起路来当当作响。后来鞋的质量越来越好,人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好,钉鞋的人渐渐少了,我也是偶尔注意到他,还坐在桥护栏后的犄角里,来修鞋的人显然少了。
有一天,我过马路时和他面对面相遇,我吃了一惊。他的脸变化很大,我才见过他不久,我一直想不出该怎么形容他的脸。有一晚,我躺着,忽然想到,他的脸,就像泄了气的气球,原本鼓胀饱满的气球,忽然就那样瘪下去了,皮肤、颜色、神情,全都那样瘪下去了。什么样的事,能让一个人的脸忽然变成这样?
宿命的阅读
有时,我发现,在众多等着阅读的书里,偶然打开的一本,很宿命。美国作家琼·狄迪恩的书在书架上很久了,有一天,忽然想读她。读完了《向伯利恒跋涉》,又打开了她的《蓝夜》。
去了陇东,这是多年后又一次去。在高高的董志塬上。一下车,先看到天空,正是琼·狄迪恩说的蓝夜,我想亲眼看到的蓝夜。蓝夜,白天和黑夜之间逐渐交替的那段时间,琼·狄迪恩说:“这种蓝夜时光接近尾声时,你会感到切实的寒意鸟对疾病的恐惧,惊觉蓝夜将尽,天光无多,夏日已去。”我看到的蓝夜,是那种无法形容的丝绸一样的蓝色,很高远,但又很温柔地笼罩着大地。蓝夜之后,塬上升起圆月,月光水一样冰凉。有个摄影家把那晚的月亮拍得很近,假的一样,我不喜欢。
琼·狄迪恩在《蓝夜》里写到她的亲人早逝后带给她的彻骨疼痛,正在她生命的蓝夜时段。读完《蓝夜》,正想读她的《奇想之年》,这时,看到她去世的消息。2021年西方的平安夜,在她送走了所有亲人的多年后,她离开了这个世界。《奇想之年》尚未打开,但蓝夜已尽,暮色四合了。
地底下的事情
甘肃甘谷县的大像山,俯视众生的大佛像在山巅。大佛正对着喧闹的县城。是厚厚的黄土山,白净的山崖,白净的寺院。正是桃花将开未开之时,垂柳蒙着一团团薄嫩的绿色烟雾。拾级而上,扭头看到几棵石阶旁的崖畔上长着的松树。因为给人開道,崖被陡陡地削了下去,露出了之前藏在地里的很深的切面。我之前看到不少这样的绽露树根的情形,但这次不同,是在很高的山崖上,没有水的黄土山崖。靠天生长的松树,枝杈瘦瘠矮小,但它的根,虬龙般粗壮坚硬,竭力伸展到四面八方。原来,看不见的根远比地面上的树木深长粗大得多。
这个疼痛的矗立的切面,像生物课本上印刷的剖面图,演示着地底下隐藏着的漫长的挣扎、苦斗。
日本作家和过哲郎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写:“的确,这座山被这激烈的生命力的苦斗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了。显然,我们的肉眼不能看见,但却感到一种灵气,一种饱含着的力量的威压,带着神秘的影子,令我们不能不肃然起敬。”这是他在看到露出的松柏的树根后的所感。
狗几岁了
6岁的小男孩小树,和我在街上走着,他看到有人牵着一条狗,过去问,狗几岁了?
牵狗的人笑,说,狗大的年纪,还问狗几岁了。我到现在一直不明白,为什么老人们说小孩的年纪时,总说是狗大的年纪。
小树好像对事物的年岁很感兴趣,但这个问题对他实在太深奥太抽象。他问我几岁了,问了很多遍,我回答了他,他很快就忘了,他说他记不住。
就像我们小时候学历史,几千年几百年甚至几十年,哪里有什么参照让你去深味时间的意义和分量。时间,对小男孩小树还是个巨大的谜。
(习习,作家,现居甘肃兰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