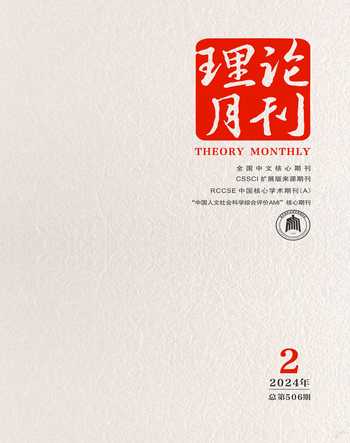数字下乡参与乡村振兴的实践逻辑与风险规避
[摘 要]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以数字技术应用为核心的乡村数字化探索推动了农业现代化的信息化驱动、乡土文明的媒介化发掘、乡村善治的智慧化构建、美丽乡村的可控化推进以及农民消费需求的精准化供给。数字乡村战略的顺利实施不仅是市场自发整合的结果,还受到诸如政府动员逻辑、乡村法治逻辑以及知识转化逻辑等非市场逻辑的影响。尽管乡村数字化建设符合乡村振兴的总体要求,但过度数字化依然会导致社会不平等在乡村场域的再生产、数字化实践与乡村社会的脱嵌、非理性意图在乡村社会的表达以及乡村数字化建设的“麦当劳化”。面对这诸多风险,数字下乡须明确从全面推进到靶向瞄准的问题意识;树立从形式合理到实质回应的需求宗旨;坚定从理论指引到研用结合的实践取向;完善从量化考核到综合评价的监督机制。
[关键词] 乡村振兴;数字下乡;数字经济;数字中国
[DOI编号] 10.14180/j.cnki.1004-0544.2024.02.013
[中图分类号] D422.6; F323 [文獻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544(2024)02-0108-08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强国[1]。自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提“实施数字乡村战略”以来,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被广泛应用于我国农业农村领域,对农业农村的全面发展起到了关键性、全局性的作用[2](p45-59)。事实上,乡村数字化建设不仅是“三农”工作的重点,也是推进乡村振兴的新举措与新方向,《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年)》等多个党和政府颁发的文件都强调要加快数字乡村建设。在全国上下的共同努力下,智慧乡村、智慧农业以及农村电子商务都取得了卓越成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指出,我国数字乡村建设已颇有成效,2017—2021年间,中国农业数字经济渗透率由2017年的6.5%上升至2021年的9.7%。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我国乡村数字化建设虽已积累了一些经验与做法,但不得不承认,继续推进数字乡村战略仍需作更为深入的理论探索。鉴于此,本文尝试对乡村振兴进程中的数字化实践、数字化逻辑、数字化风险、数字化路径作进一步探讨。
一、乡村振兴的数字化实践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从产业、文化、治理、生态以及生活五个方面对乡村振兴进行了规划与要求。乡村数字化建设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理应结合自身特点予以回应。
(一)产业数字化:农业现代化的信息化驱动
产业振兴夯实乡村振兴的经济基础。当前,乡村主要产业为农业,产业振兴的首要任务是完成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过渡与进阶。农业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农业的发展离不开信息技术的支撑,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信息化革命正成为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3](p2-15)。首先,信息化助推资本下乡。发展现代农业需大量投入人力、物力和财力,但以农村的广袤范围而言,仅依靠政府的财政投入显然不够,唯有注入市场与社会的力量才能有效纾解农业发展面临的难题。数字乡村搭建了招商引资的信息化平台,能够及时传达市场需求变化,为资本下乡与项目进村提供有效助益。其次,信息化保障农业高水平生产。数字农业采取信息化管理可降低经营成本,改善生产环境,合理使用资源,提高农作物的产量与质量。最后,信息化促进乡村产业的融合发展。借助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化平台,“互联网+”农业打破了农业与其他产业的固有界限,避免了过去因信息传输不畅导致的要素流动滞缓、不均与错配,从而为第一、二、三产业在乡村的产业融合增加了可能。
(二)文化数字化:乡土文明的媒介化发掘
文化兴,则乡村兴,数字媒介拥有传统媒介不具备的功能,赋予乡村文化以更多的潜能与活力。从文化传承角度看,数字化避免了书纸、音像制品等传统媒介因遭受物理性损坏而造成的文化缺失。通过数字勘测、数字复原、数字存档等手段,可对有价值的乡村文化资料进行技术化处理,从而最大限度地保留乡景、乡情与乡音。从文化传播角度看,数字化使乡村文化传播在主体、渠道与内容等多个方面经历革新。其一,传播主体的多元化。近年来,随着数字下乡渐入佳境,几乎人人都具备乡村文化广播站的潜质,传播主体因此不断扩大。其二,传播渠道的综融化。在乡村文化传播的过程中,短视频、网络直播等新兴媒介的兴起并不影响传统媒介继续发挥效用,两者相辅相成,形成了媒介融合的迭代优势。其三,传播内容的大众化。传播主体的多元化决定了乡村文化生产注定是一个去中心化的过程,大众成为创造、宣传乡村文化的主力。从文化创新角度看,数字化是未来乡村文化发展的新趋向。《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关于做好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工作的通知》等党和政府文件都提出了要大力发展数字文化产业,数字文化产业业已成为乡村振兴现在与未来的新着力点,而数字化也将成为乡村文化振兴的新阶段与新方向。
(三)治理数字化:乡村善治的智慧化构建
智慧化指向提质、增效与赋能,应用到治理领域可打破以往乡村治理在技术、层级以及职能上的障碍,构建智能、高效、安全的乡村治理新模式[4](p100-109)。目前,已有多地率先开展乡村治理的智慧化探索,如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的“智慧党建”[5],辽宁丹东的“平安智慧乡村”平台[6],江西宜春市奉新县的“雪亮工程”[7]等。从治理效能看,智慧化建设对乡村治理作出了如下优化。其一,提升村级政务水平。“村村通政务系统”“互联网+政务平台”等数字化政务平台的运营将原本繁杂的政务程序简约化,真正实现“群众不出门,数据来跑腿”的为民服务理路。其二,重塑村庄公共性。智慧化治理让村民外出后仍可通过“村民微信群”“乡村公众号”了解家乡事务,参与家乡建设,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被个体化与原子化趋势破坏的乡土社会基础,村庄公共性因此得以恢复与重构。其三,改善央地关系。乡村治理既是维护地方秩序的重要手段,也是国家治理体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智慧化治理可为央地在乡村治理层面提供数据、信息的衔接与匹配,从而实现上下联通的共治局面。
(四)生态数字化:美丽乡村建设的可控化推进
生态宜居是美丽乡村建设的基本遵循,其核心要义是调动政府、市场在内的多元主体的积极性,整合一切可用资源,有序地推进乡村生态面貌与人居环境的改善。然而,传统的乡村生态整治是一种压力型体制之下的运动式治理,缺乏长效性与能动性[8](p33-41)。而数字技术引导之下的乡村生态建设对于整治过程的系统把控效果更佳。首先,数字化转型打破了各层级、职能部门之间的条块分割,使各行动主体能够高效协同,按照整治所需随时进行职责任务的再优化、再调整。其次,乡村生态整治涉及清脏、治乱、增绿等多项任务,数字化技术的运用可将参与其中的各要素转化为可用于分析、描述、统计的数据代码,使整治过程化繁为简,清晰呈现,方便更新与追踪。最后,风险监管是乡村生态数字化建设的优势所在,通过风险评级、数字存档、动态监测、联合执法等手段,能够及时发现、化解可能存在的环境事件。
(五)生活数字化:农民消费需求的精准化供给
现阶段,消费品种类的极大丰盛与消费者偏好的繁复多样加大了我国乡村供需两端的匹配难度,精准性一度成为农民在数字化生活中追求的新特质。一方面,党的十九大以来,社会主要矛盾转变意味着包括农民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有了更高层次的消费需求,这迫切要求乡村供给侧升级到更高水准以应对农民对美好生活的期望。另一方面,数字赋能加强了个体与社会互动的频率与强度,人们的日常生活也随之迈入了智能化、个性化与便捷化的新阶段,农民因此拥有更多机会满足自身差异化的消费需求。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最新发布的数据,中国农村地区的网民规模已达3.09亿[9](p18-21)。借助互联网,农民在供需两端都可轻松完成精准配给。需求端,借助淘宝、京东、拼多多、亚马逊等电商平台,农民能够在海量购物信息中快速筛选出合适商品。供给端,商家通过对“产—销—运”环节的不断整合,构建出点对点配送的一体化供应体系,与需求端无缝衔接。总而言之,数字技术帮助农民在供需两端完成了精确定位、有效对接,实质性地提升了农民的生活质量。
二、 乡村振兴的数字化逻辑
從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的经济社会变革、乡村社会转型与技术运用更迭来看,乡村数字化建设的驱动力不仅有政府动员下的政策引领,法治保障下的立法规范,还有市场整合下的农企互动,科技创新下的智力支撑。
(一)政策引领: 政府动员逻辑下的顶层安排
数字乡村战略是乡村振兴迈入关键阶段的一次重大决策部署,作为一项新兴国策,在推进过程中难免遇到新问题新挑战。为此,党和政府及时推出一系列政策加以引导。诸多政策当中,尤以全国性的政策安排最为重要,其将一定时期内的国家战略、方针、路线转化为可对照施行的步骤条例、具体办法,实用性与前瞻性兼备。例如,《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和《2020年数字乡村发展工作要点》以及近三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均明确了数字乡村战略实施的现状、要求、任务、措施等,为乡村数字化建设指明了目标与方向。从现实情况看,数字乡村的政策实施过程也是政府发挥权威性主导作用的政府动员过程。在政策的执行过程当中,政府不仅负责制定、推广政策,还要营造相应的政策运行环境,约束相关政策主体的偏差行为,从而将政策执行对象整合进政策目标当中[10](p136-156)。这种行政主导的政策“输血”在学界通常被认为是上级权威过剩而导致基层社会活力不足的负面表现,但对于当前的乡村数字化建设而言显然具有更多的积极意义,能够在短时间内完成人员和资源的整合,助力政策目标的实现。
(二)利益联结:市场整合逻辑下的农企互动
学界对工商资本参与乡村振兴存在意见分歧。一种观点认为企业“上山下乡”只是借政策之便与农民争地、争利[11](p7)。而另一种观点认为企业逐利性固然存在,但不能因噎废食,人为设卡,无视其带来的资本红利[12](p23-30)。两种观点都有一定道理,但忽略了政府与农民的能动性。就当前的乡村数字化建设而言,市场利益驱动之下的政府与农民拥有自己的利益考量,可自由选择是否以及如何与企业合作,在利益受损时,也可及时调整甚至中止与企业的合作关系。此种情形下,企业不得不更多考虑政府与农民的意见,与之形成互惠共赢的利益联结,在自身盈利的同时帮助农村发展、农民增收,从而保证稳定、可持续的经营合作。目前,乡村数字化建设中农企所采取的利益联结类型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股份合作。该类型可解决农民资本禀赋不足的难题,以企业出让资金、技术,农民出让土地、劳动力的形式共同入股,共同分红。二是参与经营。农户参与到基础设施、智慧农业、电商平台、直播带货等乡村数字经济的经营活动中,获得工资性报酬。三是村级组织带动。企业与村级组织开展合作,成立合作社,按照“合作社+企业+农户”模式管理、经营与分红,合作社与农户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四是复合式联结。对于一些大型龙头企业而言,不会拘泥于某一种利益联结类型,而是根据实际情况作出适当调整,组合式选择。
(三)秩序保障:乡村法治逻辑下的立法规范
乡村法治是数字下乡的重要保证。一方面,作为一种新兴生产要素,数字下乡必然引起乡村利益格局的改变,若无相应法律、法规加以约束,则极有可能因市场恶性竞争而导致乡村秩序的紊乱,违背振兴乡村的初衷。另一方面,与法律相比,政策存在临时性、易变性以及惩治性不足等弊端[13](p84-95)。如仅依靠政策推进,则无法为数字下乡构建长效的规则环境。最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明确提出要“提升乡村公共服务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支持完善村级综合服务设施和综合信息平台”,这表明党和政府已开始关注数字乡村的立法问题。当下,短时间内构建起完整的数字乡村法律可能性较小,唯有采取央地结合、刚柔协调的立法方案,才能快速营造出对数字下乡有所助益的乡村法治环境。其一,央地结合,即中央立法与地方立法相结合。地方立法是中央立法的重要补充,与中央立法相比,地方所制定的法律、法规更具地方特色,适应性与可操作性也较强,央地结合的立法方案可使地方立法在中央立法的留白之处拾遗补漏,为地方的数字乡村建设打造良法。其二,刚柔并济,即刚性法律与柔性法律相协调。刚性法律是国家强制施行的法律,结构完整,法律效力强,但却无法变通,较为死板[14](p37-44)。柔性法律则恰恰相反,更具开放性与灵活性,但规范性、权威性却不足。刚性法律与柔性法律都存在固有弊端,只有采取刚柔并济的方法,才可为数字下乡提供最佳的法律援助。
(四)智力支撑:知识转化逻辑下的科技创新
数字下乡,既实现了数字技术的成果转化,也满足了乡村振兴的现实诉求。一方面,数字下乡为数字技术的知识成果转化提供了有利契机。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中国的科技创新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科研产出量质齐升,但绝大多数知识专利却被“锁在抽屉里”,难以有效转化[15](p5-17)。面对被搁置的潜在风险,各项技术创新都不得不积极寻求转化的机会与条件。对于数字技术而言,数字下乡是其实现知识成果转化的绝佳时机,不仅有稳定的政策支持,还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良好的科研氛围。另一方面,数字下乡满足了乡村振兴的技术支持诉求。科技创新推动乡村振兴,科技创新所具备的集聚、优化、倒逼功能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全方位的技术支持[16](p204-212)。从集聚功能来看,数字技术引发的产业集群在乡村形成了规模效应,致使周围生产要素向乡村流动,促成了乡村集约化发展。从推拉功能来看,新生产要素的注入必然推动或拉动产业链上其他生产要素的加入,这意味着数字下乡不仅会为乡村引入数字化产业,还会吸引其他相关配套产业进入乡村。从优化功能来看,数字下乡让乡村的基础设施、生产技术以及管理方法都经过一番调整、升级,产业结构与整体面貌也随之焕然一新。从倒逼功能来看,数字技术为乡村某一部分带来改观的同时也会激励其余部分向其看齐,例如,乡村的产业数字化取得进展后,乡村的生态、文化、治理、生活都会朝着数字化方向发展,从而跟进产业数字化的发展。
三、乡村振兴的数字化风险
尽管数字下乡符合乡村振兴的总体要求,在施行过程当中也拥有诸多有利条件,但这并不意味着数字下乡可毫无阻隔地融入乡村振兴实践。数字下乡是数字技术与乡村社会不断耦合适配的过程,数字技术在为乡村提供积极效应的同时也会产生诸多风险。
(一)分化风险:数字鸿沟与社会不平等在乡村场域的再生产
数字下乡意在最大化发挥数字技术的普惠性,让更多数字红利惠及农村农民。然而,不同地区、组织与个人对数字红利的机会把握具有差异性,存在所谓的数字鸿沟[17](p117-124)。数字鸿沟导致城乡差距、区域差距以及阶层差距的再扩大,形成“贫者越贫,富者越富”的两极分化局面,加剧社会不平等,阻碍数字乡村推进[18](p2-12)。从城乡差距来看,尽管数字乡村战略的实施可改善乡村数字化条件,但不可否认,农村地区对数字技术的接入、应用与创新仍无法与城市相提并论,城市在数字化建设中占据绝对优势。从区域差距来看,发达地区、东部地区的区位优势与资源优势明显,在基础设施普及率、宽带渗透率以及专业人才队伍等方面均远远超过不发达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从阶层差距来看,社会地位、经济条件、知识素养的不同使农民在数字资源的获取与应用上存在能力差距,由此促成了数字精英群体与数字贫困群体在乡村的产生。由于难以获取数字红利,数字贫困群体与数字精英群体的贫富差与社会地位差被进一步扩大,陷入从数字分化到经济分化、社会分化的恶性循环,而这也正是数字鸿沟阶层传递的结果。
(二)渗透风险:数字权力与非理性意图在乡村社会的表达
数字下乡拓展了乡村社会的权力表达机制。借助数字化转型,政府巧妙地将国家政权的意图传达至身处不同时空的村民,使国家政权可通过虚拟化策略实现对乡土社会的数字整合[19](p24-30)。这种自上而下的数字运作是不断理性化的国家机器在技术赋能下的外在表现,其实质为国家作为技术装置的隐喻[20](p97-105)。与政府理性化的数字权力表达不同,乡村场域的一些权力主体所表达的非理性主张会产生难以预料的后果[21](p62-72)。例如,村干部与普通村民对数字技术的权利主张往往是复杂的。对于村干部而言,他们有向国家、村民转化数字信息的权利与义务。在转化的过程中,村干部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可选择性地增减向国家或村民传输的信息内容。在基层“少出事、不出事”的逻辑引导之下,村干部通常报喜不报忧,而这可能导致国家、村民因信息掌握不全对真实情况作出错误判断。对于村民而言,数字赋权也让他们有了即兴发挥的机会。在一些利益纠纷上,村民采取常规措施无果后,往往会求助数字平台的力量进行曝光。不可否认,大多数村民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也不排除有村民刻意炒作或报复,通过数字网络引入外部力量,致使村庄内部矛盾公开化,破坏了村庄团结。
(三)内卷风险:数字扩张与乡村数字化建设的“麦当劳化”
目前,各地之所以对乡村数字化建设展现出高昂的参与热情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因素。其一,数字乡村的明星光环。在中国,上下级政府的信息不对称性促使下级官员不得不以资源密集型工程发出信号,让自己的政绩获得上级认可[22](p132-143)。数字乡村作为近年来最受关注的明星项目之一,理所当然地成为各地方官员竞相追逐的新政绩工程。其二,数字乡村的可复制性。数字乡村被冠以“数字”之名,但实质仍为行政、资本驱动的乡村建设运动,在人力、物力、财力均全力配合的情况下,数字乡村对于大多数乡村而言都不是一项难以完成的任务。这种在各地标准化、程式化地快速复制数字乡村项目的生产氛围正是乔治·瑞泽尔所描述的“麦当劳化”。“麦当劳化”的一个重要后果是生产系统内部的高度同质化[23](p160-163+169)。若各地为了指标考核片面追求效率,采取这种短平快的逐量式、批次化数字乡村建设模式,不注重实际发展质量,则可能出现无发展的增长,投入大量资源发展数字乡村,却不能为乡村数字化建设带来实质性的效果,陷入内卷化困境当中。
(四)悬浮风险:数字化实践与乡村社会的脱嵌
数字下乡归根结底是一种实践活动,从活动的主体、内容与形式对其进行考察,可以发现数字下乡仍存在数字下不了乡的数字悬浮化困境。其一,从数字下乡主体来看,党政部门与工商资本是积极推动者,而农民多为被动参与者。随着数字乡村战略深入推进,数字下乡被纳入政绩、业绩的绩效考核体系之内,各级政府部门与企业部门的参与积极性也随之提升,由此催生出一系列建设项目与援助任务。表面上,这有助于形成上下齐心、多方探索的共建局面,但实际上,行政主导的动员式参与虽可发动体制之内的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却无法激活体制之外的农民。其二,从数字下乡内容来看,目前以政策、技术、工商资本下乡为主,还需加强人才下乡与教育下乡。数字技术要求使用者有较高的数字素养,而整体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民显然无法满足条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数字下不了乡。其三,从数字下乡形式来看,仅采取自上而下的行政推动恐难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数字下沉。数字化代表一種新兴生活方式,意味着农民要放弃维持多年的生活方式与生活习惯,若数字下乡不能让农民切实受益,自发地认可、接受,且为之作出改变,则数字很难下得了乡。
四、乡村振兴背景下数字化风险的规避路径
数字下乡已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对乡村振兴中的数字化问题就要加以应对。对于这些问题,一是要以问题为取向,抓住乡村数字化建设的根本;二是要以需求为取向,克服形式主义弊端;三是要以实践为取向,实现学用结合;四是要以结果为取向,制定科学考评办法。
(一)明确问题意识:从全面推进到靶向瞄准
当前的乡村数字化建设,各地在收获成果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遇到难题,这些难题既是阻碍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靶向用力的突破口。首先,问题的出现表明数字乡村的政策安排可进一步改进。政策设计不可避免地存在主观臆断与理想设计的成分,在被执行的过程中也可能会出现文本领会偏差与实际操作偏离,但不管问题出在哪一环節,都为之后政策的调整与改进提供了方向。其次,问题的应对推动数字乡村的资源配置进一步优化。问题是乡村数字化建设中的痛点、难点,也是需要集中精力解决的症结所在,那些在计划时未被重视的环节,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也往往能够获得更多的资源倾斜,从而实现整体的资源优化配置。最后,问题的解决为乡村数字化建设的后续推进提供了有益借鉴。乡村数字化建设的探索过程也是经验再积累的过程,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从而使“问题清单”变为“经验礼包”,助力数字乡村战略的顺利实施。
(二)树立需求宗旨:从形式合理到实质回应
需求在数字下乡中不仅是推进各方合作的黏合剂,还是激发各方参与积极性的催化剂。一方面,以需求为宗旨的乡村数字化建设有助于克服形式主义带来的弊端。一直以来,自上而下的单向供给难免陷入以单一规格适配一切的程式化困境,在无端为一部分人提供不需要服务的同时漠视了另一部分人的真实需求,不仅无助于乡村数字化建设,反而会将大量资源消耗在各种形象工程、面子工程之中。而以需求为取向的乡村数字化建设则将形式供给与实质需求有机结合,通过有效沟通增加供需双方的匹配度,既能让政府的使命感得以发挥,继续为数字下乡提供支持,还能使乡村数字化的真实需求得到更多回应。另一方面,以需求为导向的乡村数字化建设有助于激发乡村公共性,推动持续参与与主动参与。基于需求而产生的参与能够让参与者感受到应有的关怀与尊重。此外,需求必然与参与者的自身利益密切相关,是参与者为了自己而努力,因此更容易促使参与者从私人领域走向公共领域,自愿地投入乡村数字化建设中去。
(三)坚定实践取向:从理论指引到研用结合
数字下乡的实践取向是在摆脱技术理性制约、回应数字乡村发展诉求以及消除乡村数字化建设中理论与实践二元对立的情况下形成的,其最终目的是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融通。其一,摆脱技术理性限制。脱离实践的数字化可能会引发技术霸权与数字暴政等隐患,加剧数字化中的不平等,产生“信息弱势群体”[24](p132-140)。数字下乡只有坚持为了实践、基于实践、融于实践,在实践中建设和发展数字乡村的方针,才能有效规避技术偏离实践带来的负面影响。其二,回应数字乡村发展诉求。数字乡村离不开数字技术的加持,但盲目迷信技术可能导致“技术治国”思维的蔓延,使决策部门在做重要决策时只重视少数专家、技术人员的意见,忽视大多数民众的声音,造成数字乡村发展的实际诉求无法得到回应[25](p87-93)。在此情形下,坚持以实践为取向的数字下乡就显得尤为重要,能够将人们从技术崇拜中解脱出来,正视数字乡村的真实发展诉求。其三,消除乡村数字化建设中理论与实践的二元对立。以实践为取向并不是要否定技术、否定理论,恰恰相反,强调实践正是为了在乡村数字化建设中更好地使用理论、改进理论,从而实现学以致用、研用结合,避免理论与实践的分割。
(四)完善监督机制:从量化考核到综合评价
考核评价机制是指挥棒,指引数字乡村的前进方向。与传统的量化考核机制相比,注重结果的综合评价机制更为适合当前的乡村数字化建设。首先,综合评价机制解放了数字下乡的规定性束缚。仅采取量化考核往往会忽略数字以外的内容,如在干部用人上,年轻化只看年龄不看经验,专业化只看文凭不看能力,这些硬性指标给乡村数字化建设的选人、用人带来极大困扰。其次,综合评价机制调整了地方官员的唯数字心态。过于注重量化使地方官员一味迁就考核任务,凡事都只想往指标上凑,把地方特色与人民需求晾在一边。综合评价机制能够给予地方官员更为客观、公正的考核,让地方官员一心一意聚焦于乡村数字化建设。最后,综合评价机制确保了数字下乡的长效安排。量化考核的重显绩轻潜绩使地方很少愿意为一些前景好但见效慢的项目投资,反而对那些没有发展潜力的“速效工程”“快餐工程”青睐有加,其结果必然无益于数字乡村的长远发展。因此,采取从注重阶段性到注重长远性、从注重过程到注重结果的综合评价机制,才能为乡村数字化建设提供全面性、针对性和有操作性的考评服务。
五、结语
乡村振兴历经诸多探索与调适,取得了众多成果,也遇到了不少难题,正是基于对这些实践经验的总结与判断,党中央适时提出了数字乡村战略。数字乡村战略的实质是推进数字下乡,即将数字技术作为一种新变量,注入乡村社会当中以推动其他变量随之改变。从推动效果看,数字技术为乡村社会带来的变化是全方位的,不仅响应了政策要求,还回应了居民需求,满足了市场期待,以此来看,数字下乡是乡村振兴的理想举措。然而,技术毕竟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其结果也是政治与社会共同作用的过程[26](p183)。若想充分发挥数字下乡的正向功能,不仅要关注数字技术本身对乡村社会产生的嵌入作用,还要注意乡村社会结构对数字技术带来的吸纳影响,只有调整好数字技术与乡村社会结构的内在关系,数字下乡才能规避下不了乡的困境,为乡村振兴提供应有助力。
参考文献: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N].人民日报,2022-10-26(01).
[2]王胜,余娜,付锐.数字乡村建设:作用机理、现实挑战与实施策略[J].改革,2021(4).
[3]夏显力, 陈哲, 张慧利,等. 农业高质量发展:数字赋能与实现路径[J]. 中国农村经济, 2019(12).
[4]何继新,何海清.城市社区公共服务智慧化供给治理:基本特质、靶向目标和推进路径[J].学习与实践,2019(4).
[5]王塔娜.“智慧党建”为乡村治理注入“智慧力量”[EB/OL]. (2023-05-28)[2023-05-30].http://nm.people.com.cn/n2/2023/0528/c347190-40433790.html.
[6]王卢莎.“平安智慧乡村”平台让乡村治理更高效[EB/OL]. (2022-02-15)[2023-05-28].http://ln.people.com.cn/n2/2022/0215/c400017-35133886.html.
[7]易来兵,胡涛,邓建刚.宜春奉新:“电”亮“雪亮工程”让治安防控“无死角”[EB/OL].(2022-09-22)[2023-03-22].http://jx.news.cn/2022-09/22/c_1129020563.htm.
[8]顾金喜. 生态治理数字化转型的理论逻辑与现实路径[J].治理研究,2020(3).
[9]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第47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2021-02-03)[2023-03-23].https://www.cnnic.net.cn/NMediaFile/old_attach/P020210203334633480104.pdf.
[10]张健明,黄政.“结构—利益—关系之网”与基层政策执行——对华北D镇散煤回收工作的考察[J].社会学评论,2021(2).
[11]陈锡文.不支持大资本与农民争耕地经营权[J].北京农业,2011(7).
[12]涂圣伟.工商资本参与乡村振兴的利益联结机制建设研究[J].经济纵横,2019(3).
[13]朱智毅.论乡村振兴立法的功能定位与基本原则[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
[14]尚希文.乡村振兴视域下绿色共享金融法律制度研究[J].河南社会科学,2021(2).
[15]刘瑞明,金田林,等.唤醒“沉睡”的科技成果:中国科技成果转化的困境与出路[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
[16]宋保胜,刘保国.科技创新助推乡村振兴的有效供给与衔接[J].甘肃社会科学,2020(6).
[17]胡卫卫,辛璄怡,于水.技术赋权下的乡村公共能量场:情景、风险与建构[J].电子政务,2019(10).
[18]陈潭,王鹏.信息鸿沟与数字乡村建设的实践症候[J].电子政务,2020(12).
[19]郭明.互联网下乡:国家政权对乡土社会的“数字整合”[J].电子政务,2020(12).
[20]沈费伟,陈晓玲.技术如何重构乡村——乡村技术治理的实现路径考察[J].学术界,2021(2).
[21]张丙煊,任哲.数字技术驱动的乡村治理[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3).
[22]周雪光.“逆向预算约束”:一个政府行为的组织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5(2).
[23]马玉阶.社会理性化的悖论及其破解——从麦当劳谈起[J].科学经济社会,2012(4).
[24]韩瑞波.敏捷治理驱动的乡村数字治理[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4).
[25]肖滨,费久浩.政策过程中的技治主义:整体性危机及其发生机制[J].中国行政管理,2017(3).
[26][美]白馥兰.技术与性别:晚期帝制中国的权力经纬[M].江湄,邓京力,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责任编辑 杨幸
The Practical Logic and Risk Avoidance of Empowering Rural Vitalization with Digital Technologies
Wang Zhen
[Abstract]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e rural digital exploration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as the core has promoted the informatization drive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the media discovery of local civilization, the intelligent construction of good governance in rural areas, the controllable promotion of beautiful villages and the precise supply of farmers consumption demand. The smooth implementation of the digital village strategy is not only the result of the spontaneous integration of the market, but it is also affected by non-market logics such as the logic of government mobilization, the logic of rural rule of law and the logic of knowledge transformation. Although the building of rural digitalization meets the overall requirements of rural vitalization, over-digitalization will still lead to the reproduction of social inequality in the rural field, the separation of digitalization practice and rural society, the expression of irrational intentions in rural society, and the “McDonaldization” of rural digital construction. In the face of such risks, we must make clear the problem awareness from comprehensive promotion to precise targeting; establish the purpose of demand from reasonable form to substantial response; firmly adhere to the practical orientation from theoretical guidance to combination of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and improve the supervision mechanism from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to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Keywords] rural vitalization; empower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digital economy; digital China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基层治理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机制与重构路径研究”(22YJA840016);合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返乡农民的回嵌困境及其破解路径——基于合肥市Z镇的实证研究”(HFSKQN202317)。
作者简介:汪振(1993—),男,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