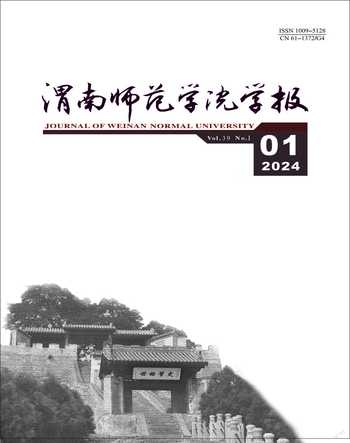论《世说新语》的“语料体小说”性质
摘 要:《世说新语》是中国古代“志人小说”的代表。相比于其他“志人小说”,《世说新语》具有独特的玄学文化特征。自东晋中期开始,世族阶层纯粹的思辨性的谈玄活动逐渐被其他形式的玄学活动取代,这个短暂的文化变迁时期和后来的文化追怀时期合称为“后玄学时代”。在“后玄学时代”,谢灵运的山水诗成为新的内容,而比谢灵运稍早,一种在世族中风靡的具有语料传播功能的作品应需而生,《语林》《郭子》正是这类作品的代表。这些“语料”迅速成为世族子弟领会玄学精神、学习名士风范的指南。《世说新语》正是对这种文化风尚的总结。结合现代文学意义的“小说”定义,《世说新语》可称为“语料体小说”。
关键词:《世说新语》;志人小说;语料体;文化生成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5128(2024)01-0079-06
收稿日期:2023-11-03
作者简介:陶成涛,男,陕西西安人,广州南方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教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作为“志人小说”的《世说新语》,在中国古代文学中与志怪小说并峙。可以说“志人”是鲁迅先生类比于“志怪”创造出的一个新概念。[1]317鲁迅先生将魏晋南北朝小说分为“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二者并举,清晰明了,便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当时的小说全貌。
宁稼雨《中国志人小说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是国内有代表性的“志人小说”研究的著作。日本学者林田慎之助《世说新语——志人小说の世界》(东京:大修馆书店1997年版)也反映了国外研究者对这一提法的接受。后来宁稼雨在《什么是志人小说》一文中总结:“自内涵来看,志人小说这个名称的使用自鲁迅始。他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一文中有‘六朝时之志怪与志人一讲。今天我们使用这个概念,既要尊重鲁迅使用这个术语时包括的内涵,又要考虑到历代目录学中小说分类沿革的事实。”[2]
学界在遵从“志人小说”的文学划分的基础上,也有一些将《世说新语》与其他笔记杂记小说进行贯通考察的意见。例如,陈文新先生在《六朝轶事小说综合研究述评》一文中提出了“六朝轶事小说”的概念,将《世说》体与“杂记”体及《笑林》体进行了综合述评。[3]
对鲁迅先生“志人小说”的提法,学界有零星质疑的声音。例如杨东甫《“志人小说”非小说论》就认为:“由鲁迅先生拟定而为现代学术界一致认同的中国古代小说类型‘志人小说,究其实质不能算小说,因为无论以古代还是现代的文体标准衡量,此一类文体都不具备完整的小说特征,而应属笔记野史性质。”[4]应该说,杨东甫运用的是传统文献学的考察思路,并非文学研究者的研究思路。对“志人小说”这个提法,从文学研究的思路讲,是应该加以贯彻的。但同时,作为文献学分类传统的子部文献,确实应归属于笔记野史。这两者并不矛盾,因为“志怪小说”依然属于子部。这是古代并无现代意义的“小说”概念、文人小说创作受到时代局限的历史结果。
以《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志人小说”或者“笔记野史”,确实是以记录魏晋名士的简短言行为内容的,反映了魏晋以来品藻人物的时代风貌。所以鲁迅先生冠以“志人小说”,属于现代文学史的话语开创;杨东甫认为依旧是“笔记野史”,是遵循了历史学或者文献学的话语传统。
但是,无论是鲁迅先生现代性的文学学术觉悟,还是杨东甫的坚持文獻学的传统看法,都忽视了一个潜在的问题,那就是,《世说新语》到底是在什么样的文化传统或者文化环境中才得以生成的?如果说,生成《世说新语》的文化环境不是为了“志人”而生成了“志人小说”,也不是简单地为了“笔记野史”而生成了“笔记野史”,那么,催生《世说新语》的文化土壤,就还值得深入考察。
一、“志人小说”的背后:《世说新语》
的文化土壤
考察以《世说新语》为代表的这一类作品的生成环境,我们就会发现,当时催生这种隽永简洁的记述文字的背后,首先是一种持续存在的文化风尚,具体包括魏晋以来的玄学环境和士大夫在乱世中表现出的所谓具有“魏晋风度”的不合作行为的社会流传。
魏晋士人在学术思想上开创了玄学的核心要义,并且和以“魏晋风度”式的不拘常格的行为艺术相结合,逐渐演化成为门阀世家的代表人物相互标榜其恺悌风流的时代风尚。玄学文化风尚由此进入鼎盛时期,即“中朝名士”时期。张华、王戎、裴楷、乐广、裴頠等朝中重臣发挥领衔作用,而宰相王衍及其家族士子以及官场同僚将这种风尚推上巅峰。
虽然王衍的空谈误国导致西晋最终被石勒攻灭,王衍也因此成了亡国罪人,身后骂名至今依旧,但是如果我们“不以成败论英雄”,那么,王衍是被当时的文化风尚选择的代表人物,得到了包括山涛在内的士人领袖的交口称赞,也是当时西晋后期世族子弟顶礼膜拜的楷模。
王衍的从弟王导,在西晋时期就追随王衍的洛水之游,后来因为他的功勋,便不被认为是空谈误国的一类人。但是王导实际上并未改变东晋世族谈玄的风尚:
旧云:王丞相过江,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然宛转关生,无所不入。[5]211
王丞相过江,自说昔在洛水边,数与裴成公、阮千里诸贤共谈道。羊曼曰:“人久以此许卿,何须复尔?”王曰:“亦不言我须此,但欲尔时不可得耳!”[5]631
在东晋衣冠南渡之初的种种艰难条件中,门阀世族对于这样的文化风尚的追求丝毫不减。其代表性的事例就是卫玠南渡,卫玠刚过江在扬州与谢鲲彻夜谈论玄理,王敦作为世族人物也终夜参与。卫玠之后到了建康,被其他已南渡的世族子弟围观风采,竟然心力交瘁一病而终。
玄学风气和人物风流在东晋上流社会的持续影响力是巨大的,东晋相对的安定繁荣局面也促使这样的文化风尚持续发展。在玄学上,以支遁为代表的天竺僧人将佛教义理引入对《逍遥游》等《庄子》篇章的新解,为玄学注入了新的理论生命力。在行为艺术上,涌现出刘惔、王濛这样具有代表性的名士,并且以王徽之为代表的门阀子弟将人的现实存在通过一系列意蕴风流高远的行为艺术表达出来。“江左风流”的盛况超越了“魏晋风度”,而其内核的文化精神则一脉相承并进一步发展,这便是《世说新语》能够生成的文化土壤。
玄学对上层社会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在当时诗坛上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玄言诗,正是以玄学精神为内核的文学衍生物。
当以谢灵运为代表的山水诗人逐渐引发诗坛瞩目的时候,玄谈的理论性被更有文学描述性的话语替代。同时,山水诗背后体现了一种玄学文化风尚的变迁,山水诗后面“玄言的尾巴”绝非多余,恰恰反映了诗人依然在追求符合玄理的哲学价值。
以山水为内容的玄言感悟诗开始风靡,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时代风气的变迁。纯粹以理论为核心内容的玄言诗被具有物象美的山水感悟诗逐渐压过了风头。在都邑的世族文化阶层中,与玄学相关的新的文化内容开始引起人们的兴趣。
如果为这种文化变迁举一个例子的话,那就是围绕着谈玄相关的或者名士相关的“话题”性质的语料类作品的出现。代表性作品就是裴启的《语林》。
从东晋中期开始,世族名士雅集,纯粹的哲学思辨的长篇长时的理论探讨的比重逐渐降低,而一起阅读山水诗、一起谈论过去的名士风流往事的内容逐渐加入进来。
这是一个典型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上流社会推崇的文化思想并未改变,依然是玄学。但是新的承载玄学的文学内容被创造出来。这一过渡时期一直持续到南朝宋初年。到刘宋政权取得对门阀世族政治和文化上的压制之后,玄学文化思潮彻底消退,这一过渡时期也就必然消亡了。但是过渡时期的这些文学作品没有消亡,并得以持续产生影响。
《世说新语》之所以在这个过渡时期产生,正是这种文化思潮和文化变迁的真实记录和总结。将《世说新语》放入整个笔记野史大类中考察,可以说它是一部最具玄学文化特征的笔记野史,在历代笔记野史的文献典籍系列中,恐怕也是最为独特的作品。同理,将《世说新语》放入整个“志人小说”大类中考察,可以说它是一部最集中以玄学人物为核心的“志人小说”,纵览整个中国古典小说史,恐怕也是最为独特的作品。
显然,这种独特性来自独特的玄学文化的土壤。《世说新语》正是生成于这样的文化土壤之中。
二、后玄学时代:话题转型
与“语料体”作品集
语料一词是本文从《世说新语》中对善于谈玄的名士的话语修养的赏誉之辞中概括总结而成的概念。《世说新语》中与语料相关的表述共有两处:“裴仆射,时人谓为‘言谈之林薮。”[5]430“庾太尉目庾中郎:‘家从谈谈之许。”[5]444第一则是称赞裴頠,第二则是称赞庾敳。“言谈之林薮”,即是玄学话语储备丰富之意。“談谈之许”,各家并未解释清楚。《世说新语全译》注此条云:“这句话各家无确解,很难讲通,可能句中有脱误。”[6]345实际上,《世说新语》中“许”作“住处、居所”讲,是普遍含义,而“谈谈”第二个“谈”是名词,正是“玄学话语”之意。两则表述结合看,一个名士具有深厚的谈玄的话语储备,是颇受赞誉的。而当纯粹谈玄的思辨逐渐被多元的名士与玄学相关话题取代之后,我们依然可以看到资谈性的话语的重要地位。我们将这类具有主题相关性的话语称为语料。
相对于主流文化形式的、纯粹以思辨性探讨为内容的“经典玄学时代”,我们可以将世族内部文化风尚变迁的时代和之后的文化追怀的时代合称为“后玄学时代”。
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显然是一个文化追怀者,他意识到过去正宗的经典玄学时代一去不复返,就在“后玄学时代”组织了一批编写者,完成了这部追怀经典玄学时代的玄学精神和人物风流的“旧闻轶事”的话题语料作品集——《世说新语》。
在“后玄学时代”,名士雅集的风气依然存在,但是一起谈论的内容正如《世说新语》所记载的,是用于传讲的具有资谈性质的语料类的人物轶事。
实际上,语料并非世族阶层独有的文化现象,每一个固定阶层都会产生独具特色的语料。邯郸淳(约132—221)的《笑林》可以说是一种俗文学的语料。这与世族高门的玄学语料迥然不同。很明显,《笑林》的受众是普通大众,而并非高雅的文人。《笑林》的编纂动机,当然是为了给当时中下层的受众作为娱乐的谈资,具有语料传播功能,并非自娱自乐。《笑林》之后,《隋书·经籍志》录有《笑苑》四卷,未录作者;又录有《解颐》二卷,北齐阳玠松撰。从题目来看,这些都是具有语料传播功能的笑话集。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论《笑林》:“遗文存二十余事,举非违,显纰缪,实《世说》之一体,亦后来诽谐文字之权舆也。”[1]66鲁迅先生在此将《笑林》与《世说新语》类比为“一体”是有合理之处的,但是也有明显的不当之处。
其一,二者在文化上有接受阶层的巨大差异。《笑林》是俗文学,而《世说新语》属于具有玄学精神的世族文学。二者不可视为一体。
其二,如果不谈雅俗之分、文化阶层的差异,那么二者确实有一个共通的文体属性,即都具有语料传播功能。所以,如果我们用“语料体”来概括它们的应用特征,那么鲁迅先生将其视为“一体”是有道理的。
在后玄学时代,核心的玄学理论和对具体问题的思辨探讨都没有再产生巨大突破或者持续贯彻,相反,世族子弟越来越注意在言行上向魏晋以来的名士学习。这样的环境下,原来哲学思辨的话题逐渐向谈论名士的话题转移。名士风流的故事,开始越来越受到世族的追捧。
正是东晋中后期门阀世族的谈论内容的变化,首先引发了袁宏撰写《名士传》的行为,谢安对此评论说:“我尝与诸人道江北事,特作狡狯耳!彦伯遂以箸书。”[5]272–273谢安的话颇值得玩味:一是谢安与诸人的闲谈,的确是与西晋名士相关的内容,但是谢安认为这些闲谈应该只停留在闲谈这个层次;二是袁宏撰写《名士传》显然出乎谢安的意料,似乎也获得了成功,谢安的戏谑之中或许还有为袁宏宣传此书之意。
而与《名士传》这样的严肃传记类不同的是,裴启开创性地完成了更为迎合这种文化转变的资谈性质的非传记类的、明确可以看出其语料应用性的著作——《语林》。
《语林》是直接为资谈而生的,明显具有“语料体”短篇文学的特征。《语林》所反映的正是后玄学时代谈论名士与玄学精神契合的逸闻趣事的文化风尚和需求。今天我们熟知的见于《世说新语》的文字很多实际是抄录自《语林》。在刘孝标注中,可以看到很多语料来自《语林》,而其中一些语料在《世说新语》中被加以语言和叙事上的修润。①
《语林》正是迎合了当时的文化需求,所以大受欢迎。《世说新语·文学》记载:“裴郎作《语林》,始出,大为远近所传。时流年少,莫不传写。”但是,由于谢安指责其妄造自己的言语,也由于裴启在此书中赞扬了与谢安有隙的王珣的《黄公酒垆赋》,引起谢安的鄙斥,使得此书在士林中的流传受到阻碍。②由于谢安是当时门阀世家的代表,且是重臣,谢安的品评导致裴启《语林》的传播受到影响,但是,《语林》的出现,标志着语料体文学正式进入世族文学。《语林》影响暗淡之后,当时还流传着郭澄之的《郭子》。《郭子》中的大多数语料故事,也被《世说新语》吸收。③
《语林》《郭子》之后,尚有郭颁《魏晋世语》、孙盛《杂语》,这些具有士林传播的语料功用的作品风靡的背后,正是世族子弟和清流名士雅集话题类型的转变。我们可以推测,当时应需而生的这一类作品应该还有很多不被著录或者影响未甚显著的。甚至可以推测到还有相当的语料,并不见于文字,而是流传于世族子弟的口耳交流之中。而且相当多的有资谈应用的相关语料被发掘出来甚至附会进来,形成了可以上溯至东汉的清流名臣和太学生、旁及妇女儿童的妙语警句的更为广泛的语料,以增加这种文化传统的渊源和影响程度。这样的具有持续文化传播力的语料,最终形成了集大成的语料体的文学汇编——《世说新语》。
三、“志人小说”的前身:语料体小说
我们依然以现代文学术语的“小说”来立论,不去溯源古代文献中的“小说”概念,因而概括魏晋南北朝文学中的小说作品,必然要将《笑林》《语林》《郭子》《世说新语》等作品归入“志人小说”。
正如前文所引,鲁迅先生将《笑林》与《世说新语》视为“一体”,但是《笑林》似乎并不具有明显的“志人”特征,《笑林》更多体现的是诙谐幽默的情节,其人物往往无名无姓,不为专门志人。如果我们向前追溯刘向的《说苑》《新序》,那么依然有所困惑,可以说《说苑》《新序》是“道理为尚”而非“志人为先”。而接下来如《西京杂记》,则明显属于杂记类、杂史类的作品,这又回归到了杨东甫文章所质疑的“志人小说”亦属于笔记野史类作品的路径中去了。
宁稼雨认为:“鲁迅先生所言的志人小说,实际是指刘知几所说的琐言一类小说。”[2]59刘知几在《史通·杂述》中将文献学和目录学中的“小说”分为十类,宁稼雨认为其中的“逸事”“琐语”“杂记”可以归入現代文学范畴的“小说”,并将“杂记”与“志怪小说”画上等号,而将“逸事”与“琐语(言)”归入“志人小说”。这样就可以“用志人小说之名,含《四库》所收杂事小说之实”。并且认为:“在志人小说内部,还有必要把逸事和琐言二者区分开来。因为从整体上看,逸事小说中的非小说成分要多于琐言小说。所以我们谈的志人小说,是以琐言小说为主,同时也兼及逸事小说中的小说成分。”[2]60
这是一种从文学角度对笔记野史类作品进行统揽全局的分类并从中获取“志人小说”文献学渊源的有效手段,在研究方法上对传统的依据文献学分类法的划分进行了现代学术意义的延伸,也是对杨东甫质疑文章的有效回应。
但是笔者依然试图强调《世说新语》的特殊性。因为不论“逸事”“琐言”“杂记”,都是没有办法标识出具有明确编纂主题与文化内核的特殊作品集。或者说,“志人小说”这个概念没有明确标识出从《语林》到《世说新语》的区别于其他“志人小说”的独立特征。
《世说新语》的编撰,我们可以明确看到其核心语料的文化标准。虽然每则故事都是独立的,但整体却让读者感知到了魏晋时代名士风流、玄学鼎盛的文化风貌。因为《世说新语》作为“志人小说”,背后还有一个特征已经被我们大致揭示出来,即追怀玄学文化风尚的以玄学人物为主的语料体轶事汇编,我们称之为“语料体小说”。
可以说,“志人小说”是《世说新语》从属于“琐言类”的普遍属性,而“语料体小说”则体现出《世说新语》中玄学和名士内核的独特属性。
具有话题传播属性的“语料”,不同于刘知几列出的“琐语(言)”,“语料”的话题具有一致或相近的文化主题属性,并且具备话语传播性和口语讲述性。不论是《笑林》中的笑话语料,还是《世说新语》中的名士语料,都可以体现出某一个阶层的文化休闲的特定应用需求。因此,“语料”具有特定群体的现场应用价值,这是无论纪言或纪事的笔记野史都不具备的文化属性。
以《世说新语》为代表的“语料体小说”,对当时世族文化中玄学名士喜闻乐见的“语料”进行了汇编性的收集与分类,而且也进行了文学的修润和改饰。从“语料”到“语料体小说”,是一种文学的提炼。因此,“语料体小说”成型要稍晚于“语料”的风靡和流传时期,先有“语料”,后有“语料体小说”,而且从《语林》到《郭子》到《魏晋世语》到《世说新语》,学者都认识到了前者对于后者的蓝本性贡献,这正体现了“语料”相对于“语料体小说”的先行特点。而之所以认为最终形成的作品集为文学意义上的小说集,正是由于编纂者对于这些语料进行了文学的分类和修润。
“语料体小说”的收集者和编辑者,有明确的对语料的文化属性的判断、甄选和取舍能力。《世说新语》体现的对于玄学精神和名士风范的明确推崇,正体现了这种能力。进一步说,后出的同类型和同主题的“语料体小说”合集一定是超越了之前流行本,这一点也是其传播属性和受众的选择决定的。正是因为《世说新语》具有此类文化殿军的性质,使得我们几乎可以一览东晋以来语料体小说的整体面貌。
《世说新语》之后,模仿其分类纪事风格的笔记野史一直延续。但是,《世说新语》所反映出的玄学精神、门阀名士引领的人物风流、高人雅士的言语风韵再也没有被复制出来。文化风尚完全消退、后玄学时代结束、政权更迭、阶层变动、文化土壤改换之后,再也没有一部可以让我们完全领略魏晋风度、江左风流的语料体小说了。后代纷纷效仿的“世说体”作品,绝大多数仅仅是零散无中心的逸事笔记与琐言笔记的集合。可以说,后世对《世说新语》撰述体式的模仿,是仅得其形而未得其神罢了。
四、結语
吴承学先生在《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中指出:“文体的特殊用途对文体风格起着制约作用……题材也制约着文体风格。‘体的含义,在古代除指文体、风格外,还可指题材,而题材与文体又有所联系。”[7]409《世说新语》具有“语料体”传播特征,即是当时玄学文化风尚催生的特殊用途,而作为语料传播功能的特殊用途的题材相同性,也促使《世说新语》此形成了“记言则玄远冷峻,记行则高简瑰奇”的整体性的文体风格。
一则被记述的材料是否属于“语料”或者“语料文学”,核心的考察应该在于其是否具有语料传播功能,特别是文人话题或文化话题的语料传播功能。除了魏晋时代的玄学精神与名士风范,我们认为在另一类文学作品集中也存在明显的“语料”属性,这就是宋代的诗话。欧阳修的《六一诗话》本来就是为了给文人提供谈诗论诗的语料而编辑的,之后宋人编写诗话之风盛行,这是宋代盛行谈诗的文化风尚直接促成的。宋代士大夫们陆续将他们谈诗的语料编纂成书,这便是如雨后春笋的林林总总的诗话了。诗话的“话”,正是对这种“语料”属性的直接说明。所以,我们可以戏谑一点地将宋代诗话都阐释为“语料体的诗歌评论集”。而我们以上关于“语料”属性的探讨,也反映了从口头到案头的文化话题的相通特征。可以说,宋代风靡于文人士大夫之间的谈诗的语料,完全不输于魏晋世族高门谈玄的语料,而中国的小说史和中国文学批评史,都是因为汇编了两种在文化上各有千秋的语料,才形成了令我们后世仰望的两座高峰。
参考文献:
[1] 鲁迅.鲁迅全集:第9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 宁稼雨.什么是志人小说[J].文史知识,2018(1):57-60.
[3] 陈文新.六朝轶事小说综合研究述评[J].齐鲁学刊,2003(1):11-13.
[4] 杨东甫.“志人小说”非小说论[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2008(1):62-67.
[5]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3.
[6] 刘义庆.世说新语全译[M].柳士镇,刘开骅,译注.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
[7] 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增订本)[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 王 萍】
On the Features of “Language-Material Fictions” in New Collections of Anecdotes of Famous Personages
TAO Chengtao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Media, Guangzhou Nanfang College, Guangzhou 510970, China)
Abstract:New Collections of Anecdotes of Famous Personages is a representative of ancient Chinese personal storie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the cultural environment which advocated metaphysics by distinguished families or aristocratic class during the West Jin Dynasty. Since the middle period of the East Jin, the absolute metaphysical analysis and debates among the aristocratic personages have gradually been replaced by other forms of philosophical activities. It can be referred this brief period of cultural change and the later period of cultural nostalgia as the “post-philosophical era”. In this era, Xie Lingyuns landscape poetry became a new content, and earlier than Xie, some popular texts with the function of language-material dissemination among aristocratic stratum emerged as needed. Yulin and Guozi are representative works of this phenomenon. These “language materials” quickly became a guide for aristocratic stratum to understand the spirit of metaphysics and learn the demeanor of personage. And New Collections of Anecdotes of Famous Personages is a summary of this cultural trend. In terms of the definition of “fiction” in modern literatur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refer to it as “language-material fictions”.
Key words:New Collections of Anecdotes of Famous Personages; personal stories; language materials; cultural gene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