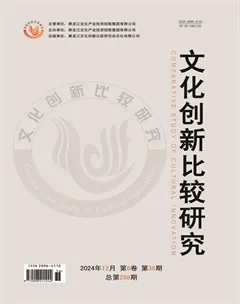J.G.巴拉德《摩天楼》中日常景观的陌生感
摘要:作为科幻新浪潮运动的先锋,J.G.巴拉德将科幻小说的风景从浩瀚太空转为日常的人造技术布景,深刻探讨了技术造物对人内在心灵的影响。《摩天楼》是巴拉德都市灾难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力作,小说中的“摩天楼”作为被间离的虚构物,在真实的推演与超现实的幻化中穿梭,产生了认知失调的陌生化效果,形成了滑流小说的独特感受。“摩天楼”这一日常事物在巴拉德笔下再度获得陌生感,它一边科学推演着城市现代性对住户的影响,一边动用大量超现实主义元素,将住户在压抑下的内在心灵外化为大楼自身。通过将摩天楼书写为内外景观的交汇面,巴拉德提供了一个陌生视角来重访日常的人造环境。
关键词:《摩天楼》;J.G.巴拉德;滑流小说;陌生化;新浪潮;城市
中图分类号:I712.06" " " " " " " " " " " "文献标识码:A" " " " " " " " " "文章编号:2096-4110(2024)12(c)-0010-06
The Estrangement of Daily Landscape in J.G.Ballard's High-Rise
HUANG Feiyu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207, China)
Abstract: As the begetter of New Wave movement of science fiction, J. G. Ballard transforms the landscape of this genre from vast outer space to everyday artificial technology environment, and delves deeper into the impact of technological creations on the inner human psyche. High-Rise is the last tour de force of Ballard's urban disaster trilogy, where the \"high-rise\" serves as an estranged fictive novum, traversing between realistic extrapolation and surreal fantasy, creating a sense of cognitive dissonance that constitutes to the sensibility of slipstream genre. In Ballard's portrayal, this everyday \"high-rise\" regains a sense of strangeness: it scientifically extrapolates the influence of urban modernity on its inhabitants, while incorporating numerous surrealistic elements which externalize the inhabitants' inner space of repression into the building itself. By depicting the high-rise as a convergence of outer and inner landscape, Ballard offers a estranged perspective to revisit the everyday artificial environment.
Key words: High-Rise; J.G. Ballard; Slipstream fiction; Estrangement; New Wave; City
詹姆斯·格雷厄姆·巴拉德(James Graham Ballard,1930—2009)是科幻新浪潮运动的重要奠基人。在这场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科幻革命中,巴拉德发出了“通向内空间之路”(“Way to inner space”)与“地球是唯一的异星球”(“The only truly alien planet is Earth”)[1]的宣言,并创作出了大量科幻杰作。这些作品一改科幻黄金时代浩瀚无垠的外太空景观,着重勾勒荒凉的人造景观,借助超现实主义的想象深入探索技术环境下个体的内在心理。其中,巴拉德的城市灾难三部曲《撞车》(Crash,1973)、《混凝土岛》(Concrete Island,1974)与《摩天楼》(High-Rise,1975)都将虚构的时空设置在熟悉的现代都市——伦敦。其中,《摩天楼》的场景设置在一座垂直的高层公寓,其玻璃外壳抵抗着外部光线,形成了一个内在天地,上演着城市现代性施压下人性的缺失。本文以滑流小说(slipstream)的视角阐释《摩天楼》中作为虚构新奇物(fictive novum)的“摩天楼”。小说借鉴了科幻的外推手法,将摩天楼置入文本场域进行推演,探讨了住户心理的逐渐转变;随着演绎的推进,小说融入了超现实主义元素,象征着住户内在心理从文明到野蛮的转变,最终指控城市现代性对个体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因此,巴拉德实现了科幻创作的目的:关注内空间,关注“现代技术所造成的灵魂领域”[2]。
1 滑流小说与巴拉德的“摩天楼”
“滑流小说”将后现代主义引入了科幻文类。滑流小说在科幻批评的话语中已经变得常见,甚至偶尔被书店使用,尤其是滑流本身不断作为叙事领域拓展的时候[3]。美国著名科幻小说家与理论家布鲁斯·斯特林(Bruce Sterling)最早提出了“滑流小说”这一新词,他在《科幻眼》(SF Eye)上发表了以“滑流小说”为标题的文章。其中,斯特林[4]归纳出滑流小说的特征:
这种文类并非科幻“类别”(category);甚至不属于科幻“文类”(genre);反之,它是一种与共识的现实背道而驰的当代写作。它有时是幻想的、超现实的,抑或推想的,但并非从严肃意义上而言……这仅是一种让你感到异常奇怪(strange)的写作。这种奇怪和生活在20世纪后期所感受到的奇怪如出一辙,如果你有一定的感受的话。可以称这种小说为后现代感性(postmodern sensibility)的小说……便于论证起见,我们将这些书称为“滑流小说”。
斯特林所定义的滑流小说风格明显,但缺乏内在于文类的清晰界限,因而引发了对滑流小说这一新词的定义、范围、与其他文类的纠缠等讨论。斯特林使用滑流小说的语境在于“要为科幻小说提供一个有益的、繁荣的竞争者”:科幻市场的作品粗制滥造,而一些频繁使用科幻惯例的外部作家却佳作不断,并在科幻专门奖项中夺冠。于是,斯特林将这些与科幻文类纠缠的作品置入滑流小说的范畴,这个范畴有着“科幻小说与其他文学领域交互的更广阔的背景”[5],滑流小说话语的建立始于斯特林与时俱进复兴科幻文类的目的。
因此,关于滑流小说的讨论注重滑流小说与科幻文类的亲属关系。凯利和凯塞尔在其编著的滑流小说文集《感到异常奇怪:滑流小说选集》(Feeling very strange: The slipstream anthology,2006)中提到,“在文类沟壑的另一面,有一些作家经常出现在阿西莫夫的《科幻杂志》和《幻想与科幻杂志》上,但他们与博尔赫斯的共同点多于与艾萨克·阿西莫夫的共同点”[6]。由此可见,滑流小说诞生于科幻的整体语境,但与阿西莫夫式的科幻惯例相偏离,有着倾向于幻想与超现实的文学风格。弗雷里克同样注意到了滑流小说所处的“文类沟壑的另一面”,他举出达科·苏文(Darko Suvin)将科幻大师布拉德伯里(Ray Bradbury)的杰作驱逐出科幻严肃分界的例子,认为这一事例证明了滑流小说从另类科幻作品中继承的遗产:“从被命名的那一刻起,科幻小说就一直存在着它的滑流小说——一类稳定的文本系列,它们无法将自己包含在科幻文类的设想边界内”。斯德勃则认为,可以将滑流小说视为科幻小说的延续:“其中科幻小说在滑流叙事中扮演着中心或边缘角色,并取决于作者意图、批评或读者接受”[7]。因此,可以认为滑流小说诞生于科幻土壤,它的幻想元素继承了科幻文类另类佳作的遗产,并具有向其他文类开放、杂糅的后现代文学特征。
也有学者参照“认知陌生化”(cognitive estrangement)的科幻诗学对滑流小说进行讨论。苏文提出科幻有两个主要诗学:“陌生化”与“认知性”。陌生化意味文本采用拟态现实对现实形成了间离效果;认知性则意味着科幻的陌生化遵循了认知性科学,文本最终演绎出具有科学性的结果,让读者获得对现实的认知。科学性认知含义广泛,既包括对科学学科领域的认知,也包括社会学、人类学、哲学等视野。基于“认知陌生化”的科幻诗学,斯德勃认为更符合滑流小说的诗学是“认知失调”(cognition dissonance),这恰是对认知陌生化诗学的延续:世界自身正由牛顿力学范式下的有序现实转向混沌理论与量子力学范式下的无序现实,文类对现实的再现也应由传统科幻转向滑流小说。凯利和凯塞尔也持有相同的观点:“我们认为滑流小说是时代精神的一种表达:它拥抱认知失调,并不尝试减缓它”。弗雷里克也赞成认知失调是滑流小说的主要效果,他归纳道:“如果科幻小说是认知性和陌生化的双重心理效果,那么对于凯利和凯塞尔而言,滑流小说是其中一半的效果,即它产生了陌生化效果,但无法生成通向认知的道路,而是将读者留在‘陌生感压倒一切’的屏息中。”
因此,滑流小说的陌生化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其一,和科幻文类一样,滑流小说对日常生活产生了间离,使得日常事物成为熟悉又陌生的文学意象;其二,滑流小说是科幻文类向魔幻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奇幻等文类开放的杂交产物,因而突破了常规科幻,产生了无法用单一文类惯例阐释的陌生感。无论是哪种原因,滑流小说认知失调的陌生化都反映了20世纪下半叶的“后现代感性”与复杂现实,为读者提供了通往无序现实的认知道路。因此,滑流小说可以被视为通过认知失调的陌生化实现了对后现代复杂现实认知的另类科幻。
巴拉德是重要的滑流小说作家,他的故事往往颠覆了科幻惯例,无法被称为常识意义上的科幻。在《摩天楼》中,摩天楼这一城市景观取代了“宇宙飞船”等传统科幻元素,成为承担认知陌生化功能的虚构新奇物(novum)。摩天楼为角色提供了一个故事发展的微缩社会。小说反复提示摩天楼与外界环境的分隔:“摩天楼内部自有一套时间,就好似人为制造出来的某种心理气候,循其自身的律动而动”[8]。摩天楼排斥着外部时空,为住户提供了一个与现实脱节的微缩宇宙,使得人物感受到“摩天楼里的种种,才是他生命里真实发生的事”。
2 外空间:摩天楼的外推式演绎
摩天楼首先是科幻虚构的新奇物。新奇物是科幻文本所创造的新事物,它们介入文本社会生活的常规进程,并探讨对历史轨迹的影响。小西瑟瑞-罗内认为“每一个科幻文本都提供着虚构新奇物,并据此作出回应”[9]。科幻文本围绕着新奇物进行推演,发展出与社会关系相关的叙事情节,演绎出新事物可能产生的社会启示。
虽然摩天楼在当今已屡见不鲜,但这种高层建筑实则是现代发明。城市的现代化要求“为市中心地区不断增长的白领劳动力提供最密集和最经济的住房”[10],在垂直空间上拓展疆域的摩天楼应运而生,成为典型的实用性现代主义建筑。作为早期最具影响力的摩天楼建筑师,沙利文(Louis Henry Sullivan)指出,艺术设计的理念应是“形式永远追随功能”,摩天楼的功能性摒弃了“希腊神庙、哥特式大教堂与中世纪的堡垒”等累赘的建筑艺术形式,成为满足办公室商务交易、大城市人口增长、市中心拥堵、地面价值上升的“现代办公楼”[11]。因此,作为现代化进程中的实用发明,摩天楼成为现代性的能指。汪民安指出,摩天楼展示了现代性的气质和禀赋,包括“对未来的乐观、成熟感、进步信念、超人式的力的奔腾、发展主义和唯科学主义等”[12],摩天楼体现了城市规划者对发展进程的美好愿景。但同时,规划者的乌托邦蓝图很快破灭,摩天楼加重了人们的隔阂与异化,它使得“个体的主体意识在工业资本主义下全面瓦解”[13]。
巴拉德正是将摩天楼这一日常事物创作为陌生化的虚构新奇物,演绎了城市现代化对住户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斯特林认为“滑流小说不倾向于‘创造’新世界,而是‘引用’(quote)它们,把它们从历史语境中切断,并让它们违反自身”。滑流小说所“引用”的是日常事物,而“违反自身”则意味着文本对这些事物的陌生化。在《摩天楼》中,摩天楼被外推为40层高、容纳了2 000户住户、配备规模庞大的配套服务的垂直小城。作为现实中摩天楼的增强版本,小说中的摩天楼以科幻的方式演绎着其对住户的影响。
摩天楼为住户提供自给自足的便利服务,使得个体与外界隔离,造成了人际隔阂。小说开头罗伯特·莱恩(Robert Laing)与前妻离婚,为了逃离人际关系和情感羁绊,决定搬入这座极其隐私化的公寓。摩天楼诸般便利让住户“尽享私密”:“整幢摩天楼就是一台庞大的机器,其设计目的就是服务于生活;其服务对象并非成群成堆的住客,而是分隔开来的逐个个体”。摩天楼的设计蓝图展现了人际隔阂的潜在后果,楼内的电子设备则加重了人际隔阂。电视屏幕、电唱机、电影放映机等日常配备满足了个体对于休闲娱乐的一切需求。塞拉斯在巴拉德采访集的引言中介绍道,巴拉德的作品探讨了“主动社会隔离”[14],摩天楼为这样的意愿提供了最理想的场景。
摩天楼建构了统一的中产阶级审美趣味,导致个体的均质化。摩天楼的住户由2 000名富有的专业人士组成。“这2 000名住户本质上是同一类人群,他们都是富有的专业人士,有若干律师、医生、税务顾问、高级学者、广告业高管,还有好几位飞行员、电影业技术员,以及合住一屋的三位空姐。”这些人属于新兴中产阶级,有着一致的审美,以及对休闲、消费的需求。摩天楼所提供的正是标准化的服务。“这样的一致,全都一览无余地反映在停车场上一时之选的各家车款、大厦内优雅得略显程式化的装潢陈设、超市里复杂考究的精选熟食和住客们自信的腔调口音当中。”住客满足于贴心的品质服务,却付出了牺牲个体性的代价。“简而言之,这样一个完美的背景,足以让莱恩融于无形。”莱恩融入标准化空间,大楼让所有个体都成为匿名者。
因此,人们生活在隔绝于世、标准单一的人造环境中,其后果是情感浓度的减退。巴拉德笔下的人物往往情感淡漠,有时甚至是超道德的(amoral),他们符合詹明信对后现代个体情感消逝的诊断:“今天一切的情感都是‘非个人的’、是飘忽忽无所主的。”[15]摩天楼中流淌着这样的气流:人们对暴力、死亡等极端事件无动于衷,并以刺激神经的强度替补情感的空缺。在作品的第三章叙述了派对进行中的死亡事件:“在第一排其中一辆车的车顶,砸进了一具身着晚礼服的男尸。……车前轮旁边的地面上躺着死者的眼镜,水晶镜片尚完整,折射出大厦的华光璀璨。”“水晶镜片”折射出了“大厦的华光璀璨”,死物的生机对比出生命的死气,展现了摩天楼的冷酷气氛,这种冷酷正是住户的内心特质。“莱恩抓紧了金属扶手,震惊且兴奋。摩天楼巨大的外墙墙面之上,几乎每一户阳台里都站了人;在这巨型的露天歌剧院中,每一位住客都在从各自的包厢里望出来,向下注视着同一个地方。”住客将命案当成景观,感到“震惊且兴奋”,这样的心理体现出住客情感的缺失。摩天楼经常上演的狂欢、无关爱欲的性行为、暴力后的兴奋等气流都属于“无所主”的强度而非情感。在楼内无菌的现代技术环境中,住户的心灵也融入了冷漠的特质。
住户逐渐滋生出紧张的敌意,并演变为人性缺失的暴力事件。敌意来自琐碎纠纷,“潜在于住户之间的情绪已经紧张到让人无法忽略”。在采访中,巴拉德提及关于楼内纠纷的描写源自其父母所居住的公寓楼中真实的邻里矛盾,这些纠纷和敌意往往滋生于“最不可置信的琐事”[16]。城市现代化所带来的不是邻里间的亲密认同,而是情感的缺失。作为科幻演绎的结果,这些基于个人琐碎利益的敌意逐渐发酵为死亡与暴力。
如史蒂芬孙所说,导致楼内居民精神堕落的催化剂是建筑本身,其干燥冷漠的环境滋生了居民的匿名性和孤立[17],小说将摩天楼本身作为“催化剂”演绎了城市现代性对住户造成的冷漠隔阂。巴拉德在与萨维奇(Jon Savage)的采访中描述了“自然人造灾难”,其中“人人家里都有一台电脑终端,以满足他们所有需求、所有室内之家的需求”,摩天楼中上演的正是这样的自然人造灾难。小说将摩天楼进行了科幻式的外推,对当下的现代化社会展开了预演:情感的需求被手边设备所填补,紧张的敌意则在琐碎之末酝酿。
3 内空间:住户心理的超现实象征
斯特林认为滑流小说杂糅了其他文类的“幻想”和“超现实”元素,并且,这些元素“都不是那类‘未来主义的’或‘超越可知范畴’”,而是“倾向于讽刺地将‘日常生活’的结构撕裂”。斯特林澄清了滑流小说中的幻想元素与奇幻等非认知性文类中“超越可知范畴”的幻想元素的关系,滑流小说中的幻想元素更倾向于借助超现实笔触书写现实。
摩天楼作为科幻新奇物被演绎后,逐渐融入象征住户心理的超现实主义元素,从而将演绎结果呈现为个体的心理内空间。在著名的“内空间”(Inner Space)宣言中,巴拉德宣示,“未来立即面临的最大进程不会发生在月球或火星,而是在地球上,并且在其内空间,而非外部,这也是指待探索之处。地球是唯一真正的异星球”。内空间指涉内在的心理维度,这是科幻领域颇具革命性的转向。如普林格尔所指说的,在巴拉德的作品中“高速公路、电视屏幕、广告牌、医院和停车场等客观的外部环境变得‘内化’——一个充斥着符号编码和潜在意义的领域,就像梦境”。摩天楼、混凝土岛、公路车祸等意象都是对内空间的外化,成为内空间和外部环境的交汇之所。
为了实现这样的效果,巴拉德常使用异文并置的隐喻,将人工环境与人的大脑、心脏等意识器官联系起来,形成技术与超现实梦境交织的风格,这些文体标识也是摩天楼陌生感的来源。试举几例:“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远方的城市天际线——它参差零落得如同一张患不明精神疾病的人的脑电图,还被干扰了波形”,城市楼群的天际线被喻为精神病人的脑电图波形,暗示城市发展和居民心理疾病的内在关联;“黑暗更亲切,至真的幻象会焕发于其间”,摩天楼的黑暗与心灵的幻象相勾连,黑暗的潜意识溢出主观边界,如有实质地成为大楼的部分;“连成一片的礼堂屋顶,蜿蜒的堤道和由直线构成的幕墙组成了一幅令人着迷的几何拼图——迷人得不像用来居住的建筑,更像是在某个神秘的通灵仪式中被人无意识画出的画”,“通灵仪式”“无意识”等禁忌的心灵维度与楼内装潢勾连,熟悉的家产生了暗恐感,表现出人们对城市环境家园感的丧失。
《摩天楼》中的异文合并来自作者对超现实主义的借鉴。超现实主义的创始人之一安德烈·布勒东在“超现实主义宣言”中强调“我相信梦境和现实这两种看似矛盾的状态,能在将来被中和为一种绝对现实,一种超现实”[18]。换言之,超现实主义把现实与人的本能、潜意识和梦境相糅合,以达到超现实情境。对巴拉德来说,超现实主义意象表现了内空间的图景,人们内在生命的幻想产生了“一种超越我们视觉或感官所熟悉的更高的或另类的现实”[19]。《摩天楼》便借鉴了这种超现实主义美学,使得外在的摩天楼环境成为人物内在心理的象征。
在整体叙事上,摩天楼从起初的科幻演绎场所逐渐向超现实场所过渡。楼内根据楼层高低形成了等级制度,楼层之间产生了凌驾与反抗,前期积累的敌意逐渐发酵为以争夺资源等名号为由的暴力战争,住户从现代文明状态退化为原始野蛮状态,小说的文类风格也由科学演绎转向超现实想象。小说这段话出现的时间节点标志了摩天楼的转变:“尽管他已经忘了确切是几点几分,这块坏掉的手表却用指针保存了留给他的那一刻有限的时间,如同抛在海滩上的一枚化石,将发生在一片已不复存在的海洋里的一小串瞬息往事永远结晶了起来。”这段话提示读者,楼内时空已完全扭曲,完全脱离了现实原则。从此刻起,超现实主义的笔触更为浓厚。
摩天楼自身的光明与黑暗在文中作为超现实的象征元素出现:光明象征着文明,黑暗则象征着混沌。起初,摩天楼的黑暗来自供电故障,这时的黑暗滋生了社会野蛮的另一面,“住低层的要回家,坚决要往下走;住高层的嫌人多,坚决要往上走,于是黑灯瞎火里,爆发了相当数量的、可笑却并不愉快的争执”,而适时的光明使得秩序回归:“光明适时回归,昭彰了见不得光的勾当,令它无法再似某类贪婪的植物品种一般在黑暗中欣欣向荣起来”。当摩天楼停电的楼层越来越多时,楼内越来越混乱,住户对这类事件也越来越漠视。楼内的黑暗不再是因为无力供电,而是住户刻意行为导致的结果,因为“也没有什么人想过要把坏灯泡更换掉”。
由此可见,摩天楼的黑暗、混沌逐渐演变为摩天楼自身的特性。小说这样叙述了摩天楼在暗色中的荒废景象:“银行和超市下午3点关门,小学则因教室毁损而迁到了7层的两间公寓。已经没什么小孩会出现在10层以上,更别提天台上那个罗亚尔专为他们精心设计的雕塑园。10层的泳池已经半空,剩下的半坑黄水上漂着碎片杂物”,精心设计的设施变成了废墟。并且,这片荒废的楼内景象与“大脑上散布着的坏死层”并置:“一到夜里,那几条黑杠横贯了摩天楼的整个外墙,像那颗衰竭的大脑上散布着的坏死层”,表明黑暗、无序的摩天楼是对住户文明退化的象征。因此,黑暗中的摩天楼与住户的内心一同涌动着混乱、野蛮的气息,直到整座大楼都完全失去供电,人们的心灵最终抵达了野蛮的国度:“如今的摩天楼居民,就好似在没有光亮的动物园里的一群生物,一同蛰伏在阴郁的沉寂中,时不时暴起,急促又暴戾地彼此撕咬一番”。
最后,摩天楼变成了尸骨坑:“池里很早就水干见底了。然而现在池底斜坡上满是骷髅、白骨和从数十具尸体上离断下来的四肢残骸。于这被弃之处,它们彼此纠缠着,闲散无聊得就好似这是一片热闹海滩上的住客们遭遇了瞬息突至的大屠杀”。“大屠杀”凝结了住户的集体记忆,“残骸”不仅意味着人们厮杀后的身体创口,还象征着住户长期的心灵创伤。这幅景象彻底超越了都市现实的边界,大楼的残骸与住户的残骸纠缠着,摩天楼完全成为人们心灵创伤的外化。小说结尾处,内外一片的荒凉景象极具超现实感,为前期的科幻演绎画上了句号,表明城市现代性压抑着个体深不可测的心理伤痕。
4 结束语
本文以滑流小说的视角阐释了巴拉德《摩天楼》中的摩天楼,将其视为与日常事物形成了间离的虚构新奇物。小说通过摩天楼演绎了城市现代化过程中的人际隔阂与冷漠。随着演绎推进,小说融入了大量超现实元素,以心灵废墟景象回答了前期的科幻演绎,表明了作者对于现代技术环境影响下人类心灵的关注。正如小说所述,“从这陌生的视角看这个厨房,它变得多么破败”,滑流小说为勘察现实提供了“陌生的视角”,使得巴拉德的科幻成为面向当下日常事物的深度洞察。
参考文献
[1] BALLARD J G. Which Way to Inner Space? [C]//BALLARD J G. A User's Guide to the Millennium:Essays and Reviews. New York: Picador USA,1996:195-198.
[2] PRINGLE D. Earth is the Alien Planet:J. G. Ballard's Four- Dimensional Nightmare [M]. San Bernardino:Borgo Press,1979:11.
[3] HOLLINGER V. Contemporary Trends in Science Fiction Criticism,1980-1999 [J].Science Fiction Studies,1999(26):259.
[4] STERLING B. Slipstream [EB/OL]. [2024-01-01]. https://www.journalscape.com/jlundberg/page2.
[5] FRELIK P. Of Slipstream and Others: SF and Genre Boundary Discourses[J]. Science Fiction Studies,2011,38(1):20-45.
[6] KELLY J P, KESSEL J. Slipstream, the Genre That Isn't [C]// KELLY J P, KESSEL J. Feeling Very Strange:The Slipstream Anthology. San Francisco:Tachyon, 2006:vii- xv.
[7] STEBLE J. The Role of Science Fiction Within the Fluidity of Slipstream Literature [J].Acta Neophilologica,2015,48(1-2):67-86.
[8] J.G.巴拉德. 摩天楼[M].陈醉,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9] CSICSERY-RONEY I. The Seven Beauties of Science Fiction [M]. Middletown: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2008.
[10]KLEIN S. Skyscraping Frontiers:The Skyscraper as Heterotopia in the 20th-Century American Novel and Film [M]. Berlin, et al.:Peter Lang International Academic Publishers,2020:12.
[11]SULLIVAN L. The Tall Office Building Artistically Considered [J].Lippincott's Monthly Magazine,1896(57):403-409.
[12]汪民安. 现代性[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47.
[13]刘英.摩天楼与美国现代主义文学[J].外国文学,2013(6): 125-131,160.
[14]SELLARS S. Introduction:A Launchpad for Other Explorations [C]// SELLARS S, O'HARA D. Extreme Metaphors:Selected Interviews with J. G. Ballard,1967-2008. London:Fourth Estate,2012:xvi.
[15]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陈清侨,等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449.
[16]SAVAGE J,BALLARD J G. 1978:Jon Savage. J.G. Ballard [C]// SELLARS S, O'HARA D. Extreme Metaphors:Selected Interviews with J. G. Ballard,1967-2008. London:Fourth Estate,2012:107.
[17]STEPHENSON G. Technological Tartarus:The Atrocity Exhibition, Crash, Concrete Island, High Rise [C]// STEPHENSON G. Out of the Night and Into the Dream:Thematic Study of the Fiction of J G Ballard. New York:Greenwood Press,1991:81.
[18]BRETON A. Manifesto of Surrealism [C]// BRETON A.SEAVER R, LANE H R, trans. Manifestoes of Surrealism.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72:14.
[19]BALLARD J. The Coming of the Unconscious [C]//BALLARD J G. A User's Guide to the Millennium: Essays and Reviews. New York:Picador USA,1996:84.
基金项目: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四川城市形象与跨文化宣传研究——以成都市‘科幻之都’国际传播为例”(项目编号:SC23BS027)最终成果。
作者简介:黄飞宇(2000-),女,湖南衡阳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