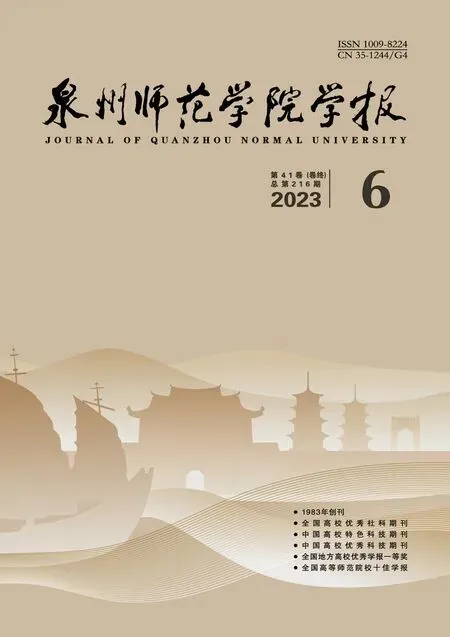场域与象征:两岸宋江阵演武文化视角
王伯余,林小红,魏太森,郭学松
(1. 泉州师范学院 体育学院,福建 泉州 362000;2.泉州东海湾实验学校,福建 泉州 362000;3.曲阜师范大学 体育科学学院,山东 曲阜 373100)
宋江阵是我国集体性民间武术文化,历经300余年的岁月洗涤,已成为两岸最具代表性的民间体育事项[1]。20世纪以来,学界对宋江阵进行广泛的研究,期间有大量研究者参与其中,如台湾地区的吴腾达、黄文博、谢国兴,祖国大陆的谢军、周传志、郭学松,以及日本的片冈岩等。他们分别从宋江阵本体论、发展史、社会治理、现状与对策、个案比较等方面进行系统的研究。据笔者调查,宋江阵是以传统武术技击为主要特征,以军事战斗及民间械斗为主要形成场域,在传承过程中融入乡土宗教、宗族、节日等传统文化内涵,是一个共生性的武术共同体[2]。
宋江阵能在两岸乡土社会存续数百年,不仅源自其在冷兵器时代的技击价值,更重要的是在发展过程中与乡土宗教祭祀、宗族祭祀、庆典活动等相互融合,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寻找到自我与社会契合的场域,拥有可持续发展的生存土壤。笔者调查发现,2010年以来福建现存宋江阵阵头20余阵、台湾地区存续200余阵。台湾地区的宋江阵主要出演于宫庙建醮庆典、宗族祭祀和大型庆典场域中;闽台两地的宋江阵出场场域相似,主要参与庆典和庙会的演出。能在乡土宗教祭祀、庆典仪式等场域出场,不仅表征宋江阵的时代发展需求,同时隐含这些场域对宋江阵出场的需要,因而这种民间武术在场现象的背后必然隐藏着许多社会“本相”。如此,探索现象背后的本相,不仅对学科理论建设具有积极意义,同时对体育项目的保护、传承、发展与弘扬更具实践价值,这就构成本研究的逻辑起点与最终立意。
一、乡土宗教仪式场域中的宋江阵演武文化
(一)宋江阵在乡土宗教仪式中的社会存在
宋江阵并非某一历史时期所创造,而是一种集体智慧的凝聚。其源头可追溯到远古时期,然而可考究的材料却源自明朝年间的唐顺之所创的鸳鸯阵。宋江阵真正成型是在戚继光抗倭时期,当时名为“鸳鸯阵”,后来在南少林反清复明、郑成功收复台湾、民团自卫和民间械斗等历史斗争中因假借梁山好汉之名,故而称之为“宋江阵”[2]。可见,宋江阵的武术特质是在特殊社会背景下型塑的。伴随岁月更迭,宋江阵的武术技击功用逐渐失去社会“市场”,转而为乡土宗教祭祀场域出演。1909年8月4日,“本岛乡村迎神,仍循旧例,多用狮阵、宋江阵,使用利器,实为维厉之阶。如客月三十日,打狗支厅前金庄,恭迎天后,附近庄多备旗子锣鼓,狮阵、宋江阵,以助闹热。有盐埕庄陈、林二姓者,出狮阵、宋江阵各一”[3];同年10月6日,在迎后盛况中,“一送一迎,宋江阵及狮阵,共计四五十,总共信徒有二万余人,殊呈盛况云”[4]。这是宋江阵较早出现在庙会中的文献记载,说明宋江阵的出场并非局限于搏斗场域。
清末以后,因社会发展和自身生存需要,宋江阵演武活动一直在福建和台湾地区的乡土宗教祭祀中持续发展。在台湾地区,比如1964年甲辰科,参与西港香绕境的庄头共72个,出神轿36顶,各式阵头35阵(没有艺阁),其中宋江阵的武阵共14阵[5]375;1991年辛未科,西港刈香庄头78个,神轿68顶,艺阵60组,宋江阵阵头14阵[6];1992年慈济宫刈香绕境,共有各式阵头73阵,包括艺阁16座,宋江阵8阵[7]64-78;2003年,西港庆安宫的香境跨越台南县市曾文溪两岸,共有96个庄头参加,神轿79顶,阵头68组,其中宋江阵武阵17阵[8]。这种现象说明我国台湾地区宋江阵参与宗教祭祀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在福建地域也有类似宋江阵的演武活动,比如明末清初,同安一带的农民好习武术,逢有庙会,他们便装扮成梁山泊英雄,游乡串社,表演各种武打艺术,俗称“套宋江”[9];每年北辰山王审知祭奠的二月十二前后,同邑士民冒雨迎寒,上山行香,络绎不绝,至今如此;旧时还在庙前搭台演戏,“套宋江”以娱神[10]。据统计,福建省和台湾地区存续200多阵宋江阵,且大多与乡土宗教活动相关联(表1)。福建和台湾两地宋江阵现象的存续有其社会因素使然,透过这种社会现象背后,说明其蕴含着两岸民众共同的历史心性。

表1 两岸乡土宗教仪式中的宋江阵
(二)宋江阵展演在宗教仪式中的象征
作为技击本质的演武活动,宗教象征具有凝聚共识与认同的作用,宗教认同往往是人群联系的重要方式,并由此产生具有归属感的社群[11]。正因如此,闽台诸多民间民俗体育事项皆会在地域乡土宗教仪式活动中寻找一席之地。宋江阵在闽台乡土宗教祭祀中的出演,不仅表征其在地域社会的重要影响,同时作为一种武阵,宋江阵的出演更多地体现出勇武本质,是一种“保护伞”的象征,“宋江阵系一业余的巫术团体,以言语、行为、符簶与器械等为方法来压制邪魔,达到驱鬼的目的”[12],“英魂若成厉鬼作祟人间,需要宋江阵之类武术技艺高强的神明禁卫军才足以镇压化解”[13]17-21,“宋江阵参与乡土宗教仪式场域的展演,以类似‘神兵神将’(六丁六甲)的角色护卫神明执行‘代天巡狩’(驱邪逐煞)的工作”[14]。在乡土宗教祭祀活动中,宋江阵队伍一般走在前面,是开路先锋,又是整个仪式的护驾“保护神”。宋江阵这种象征性功能源自对武术技击本质特性的继承,因而“武阵”也就成为宋江阵在台湾地区的代名词。
宋江阵在体现尚武特质的基础上,还在某些自我仪式环节中融入乡土宗教祭祀的元素。董芳苑调查高雄市林园、大寮一带的宋江阵,发现其表演形式为头旗(宋江)指挥排阵(后),队员每人手持香柱三柱,金钱三百,替身一个,一百纸钱,先予祭拜焚化,而后由持双斧的李逵踏七星步(叫“步罡踏斗”),跃进室内向四方,劈走邪魔,使室内室外清静[15]308。笔者调查发现,台湾地区宋江阵演武前有一些特殊的科仪,是为了祭拜相应的保护神(田都元帅、谢府元帅、五谷先帝等)及开基祖;宋江阵演武过程一般分为行阵、单练、对练等;行阵以打圈为基础,打圈主要是圈出一个圆形空地,留作对练和单练使用,被圈出来的地方是一种“神圣”地带[1]。演武过程凸显宋江阵武阵的驱邪、保平安之功用。在单练过程中,持双斧者要完成“开斧”仪式(双斧中间燃烧符箓,抛于空中,开始展演双斧武艺)。这种“开斧”仪式是假借演武的精气神及功力来实现净化展演场域的目的。福建地域的宋江阵出演虽有相似的过程,但并未形成圈,而是面向站立的两列横队,型如古代两军主将作战或两军对垒之势,其目的也是凸显宋江阵的武阵特质。比如每年厦门同安北辰山王审知祭奠的郭山村宋江阵出阵表演,其开基祖郭镕为王审知的十八部将之一,在开闽圣王东征西讨中立下汗马功劳,是该村的“英雄先祖”,正是这种英雄先祖崇拜的历史心性,促使他们一直参与王审知祭祀科仪;又因其开基祖是位武将,宋江阵演武活动凝结了开基祖的武术睿智,今之宋江阵武术及相关内容得益于开基祖的传授而被继承和发展;因而王审知祭日中展演的宋江阵,不仅凸显郭山村郭氏后裔对英雄先祖尊崇的历史心性,同时也表达了宋江阵是英雄祖先创造历史的记忆和文化象征。总之,作为先祖文化象征的演武活动,闽台宋江阵文化凝聚了共同先祖们的心性与智慧,其经由身体、语言、象征与文化论述来描述社会事实,反映理想与价值,或成为一种传递文化意识形态的工具[16]203。
二、村落宗族仪式场域中的宋江阵演武文化
宗族是由父系血缘关系建构起来的家庭单位,他们在祖先崇拜及宗法观念的规范下生成的社会群体,因而又称为家族。正如费孝通所指出的,“所谓的族,由许多家所组成,是一个社群的社群”[17]39。宗族通常只是村落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在福建和广东地域,宗族与村落两者有着明显的重叠现象,以致诸多村落只有单个宗族[18]1。在这些以村落为宗族的群体中,往往会形成独特的族祭仪式,表演常以象征的方式实践崇拜家族祖先的制度化设计,达到维系家族的团结、实现敬宗收族的祭祀目的。弗里德曼认为,“在家族祭祀中,人们与他们‘熟知’的逝者或多或少地取得联系,且通过祭拜的仪式或身体运动向他们进献,使其在不同的世界获得快乐。在宗族或族群的层面,亲属体系所要求的分化在仪式过程中得以表达和强化”[19]90-91。族祭仪式的展演内容是实现目标的重要方式。作为地域化象征记忆的宋江阵往往是闽台地域族祭的主要构成部分(表2)。

表2 两岸村落宗族中的宋江阵
(一)福建村落宗族仪式中的宋江阵
福建宋江阵以宗族或族群为主要传承载体,形成以村落为归属感的共享场域。Olwig认为,“归属感的共享场域”是探讨族群的适宜方式。族群在今日是一种文化建构,具有极强的象征意义。因此,她强调透过分析生命史的材料,分析个人的生活经验与归属感,才能了解族群所处的具体社会关系,族群的文化价值才能被其成员想象与实现[20]124-127。宋江阵在这样的归属感共享场域中存续,是以参与人员拥有或享受文化价值为前提的。因此,宋江阵要展示的象征寓意,远远不止其创造的武技价值。
笔者考察得知,目前福建宋江阵阵头约20个。在以某一姓氏为主体构建的宗族村落中,宋江阵在村落宗族延承过程中发挥积极的社会功能,成为村民重要的历史记忆。这些记忆通过循环往复的身体展演逐渐形成宗族独特的象征符号。即便宋江阵不是本村落宗族创建的,也是同一祖先的分支宗族传播延承下来的。正因为他们的祖辈凭借宋江阵参与保家卫国的壮举,使宋江阵在世代传承中逐渐成为“英雄祖先的历史记忆”。应该说,早期宋江阵在这些村落中的存在,发挥了保卫乡村的重要功能。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功能逐渐消退,转而成为一种宗族集体记忆,就像姓氏宗族群认同神明一样,成为该自然村落和族群的村神。此时,宋江阵与村神一样成为一种象征,被视为各村不同族群认同的角色[21]。村落宗族祭祀是福建地域最为盛行的民间仪式活动,族人往往会在一些具有重要纪念意义的日子里操弄。在族祭过程中,族人会将先辈传承或创造的文化作为展演项目以娱先辈。宋江阵被视为先辈们光辉事迹的映照,便在族祭仪式场域中被搬上展演舞台。在该仪式场域中,村民试图用身体运动来诠释先辈不怕牺牲、勇于抗争、奋勇拼搏等精神。通过对祖辈所传承身体文化的认同,可以更好地调控该村落的社会秩序,增强族群的向心凝聚力,实现族群认同,进而为其争夺社会生存空间提供必要的“人和”条件。宋江阵演武活动在以村落为基本单位的宗族或族群中存续,无形中成为族群延续的理性工具。
(二)台湾村落宗族仪式中的宋江阵
移民所型构的新族群环境,不仅能提供结构性失忆促生的温床,也能促使原来没有共同历史的群体,以寻根的方式发现或创造新的集体记忆,以便凝聚新的族群认同[22]29。正因为如此,特殊时期的台湾地区,大批福建移民将祖籍地的民俗事项(宋江阵、扒龙舟、攻城炮等)搬上生活舞台。在此期间,对祖先的纪念仪式成为许多台湾村落怀念先辈的重要方式之一,先辈留传下来的习俗文化自然成为族祭中的重要内容和诠释思念的媒介,宋江阵武术文化便是其中的例证之一。宋江阵演武活动在族祭场域的展演,勾勒先辈开拓台湾、落地生根的历史记忆,这种历史记忆逐渐衍化为台湾同胞的集体记忆。台湾民众的集体架构将这种集体记忆用来重建对于过去意象的工具,而在每一个时代,此意向符合社会的优势思潮[23]40,这也是台湾存续200多宋江阵阵头的原因之一。
聚族而居是台湾早期移民的重要特征。这种群居形成如今宗族性的村落族群体,他们将祖籍的风俗习惯带入新的地域,逐渐与当地文化结合,形成独具特色的村落族群文化。宋江阵文化是福建移民随迁传入,在宗族祭祀中以宗族繁衍文化的象征登上族祭舞台,逐渐被型塑为“英雄祖先”的历史记忆,是一种类似“回复式的乡愁(Restorative Nostalgia)”[24]153。宋江阵的身体实践在这种“回复式的乡愁”的固着意念中,仍然会在召唤(calling)的行动中,转化成为当下的体现与创造[25]。这是宋江阵在不同宗族部落中为了实现部落需求乃至社会需求,而或多或少存在差异的缘故。因此,宋江阵在台湾村落被赋予宗族文化及先祖文化的象征内涵。
宋江阵在台湾地域根植,不仅是先祖文化的象征,也是宗族繁衍历史文化的象征。早期,宋江阵武术组织在台湾社会更多的是承担保卫乡村的特殊使命,“我国台湾同胞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人和身家安全,成立了宋江阵,传承昔日族人的狩猎遗风和地方团练”[26]。连横曾指出:“闽、粤之聚居者可设族团,族长主之,凡团内之壮丁皆注于籍,分为义勇、练勇、团勇。义勇常住局中,逐日操练。无事皆农,有事皆兵,使盗贼无容身之地。”[27]229-230这些宗族将宋江阵作为先祖遗存文化的同时,也将其视为宗族延续的力量工具。“茄萣中角宋江阵,百年前由史姓家族组成,其目的在团结家族之力量,延续史姓从大陆来台后之传统。各姓角的武阵,尤其是各宗族的宋江阵更是早期乡勇团练组织的延伸,除抵抗外敌的宗族武力组织外,并有展现各宗族的力量意味”[28];“在闽粤移民之间、漳泉移民间甚至泉州移民内部,为了争夺资源经常发生械斗事件”[29]342-380。可见,宋江阵等武术成为宗族或村落械斗乃至争夺社会生存空间的重要工具,这是闽南地区村落多尚武的重要原因之一。总之,无论是抵御外敌侵略,还是乡土社会的械斗,都推动了宋江阵在村落宗族中的延承与发展,甚至成为宗族繁衍兴盛的一种象征。因此,在宗族祭祀仪式展演中,宋江阵是对族群文化的深度记忆与表达,是一个宗族或村落族群体生存与延续的象征。
闽台以宗族为基本单位构建村落群体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宋江阵在闽南和台湾中南部的广泛存续与宗族式的村落群体的存在密切相关。在宗族群体繁衍过程中,宋江阵涉及地方宗族的保卫、建构、发展,甚至牵涉到存亡之问题,是宗族部落发展史的特殊历史记忆。在宗族式群体的族祭仪式中,宋江阵不仅增添祭祀活动的氛围,同时表达了人们尊崇、感恩与怀念先祖的思想,且让先辈的英雄事迹代代相传,让族群文化延续推广,以不断增强族群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形成新的族群或宗族认同。因此,台湾地区宋江阵在宗族祭祀仪式中的展演,不仅有宗族群体层面的象征寓意,还有对自己身为华夏子孙的身份认同。
三、地方庆典场域中的宋江阵演武文化
(一)作为地域传统文化的象征
福建宋江阵不仅在一些民俗节庆中演出,同时参与地域社会的庆典活动。同安地区在春节、元宵、北山庙会、香山庙会、西山割香、吕厝送王等民俗活动中表演宋江阵[30]235。这些展演主要呈现宋江阵是祖辈们所根植的一种传统文化,其与传统节日形成共生体,凸显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记忆。宋江阵用身体运动形式将人们内心的文化认同观展示出来,表达广大民众一贯的传统文化观。同时,宋江阵还赋予节日装饰的象征文化符号,具有增添节日愉悦氛围的作用。另外,在一些特殊的庆典活动中,如赵岗的庆典活动、同安的文化节展演、莲塘村的海峡两岸武林大赛等,宋江阵作为地域传统文化的象征开始登上展演的舞台。
(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
我国台湾民众多源自大陆移民,许多节日习俗皆同于祖国大陆,特别是台湾南部的乡土村落。内门地区是大陆民众早期的主要迁徙地,他们过着中国大陆农村型的朴实生活,一年当中,地方、乡土神祇等祭典很多。虽然岁时节俗浪费时间和金钱,甚至浸于迷信,但其具有慰藉人心的作用。在农村生活上,岁时节俗不仅没有与农业生产脱节,反而把农村的劳动及休闲时间做适当的调配,实有调剂农村终年辛勤耕作之单调刻板生活的作用[31]156。宋江阵在岁时节俗操演,并与节日庆典文化相互融合,是台湾民众将其作为“母文化”的象征而传颂,寄托他们以身怀乡的情感。
台湾宋江阵在岁时节庆场域中的展演,是作为一种象征的文化载体,凸显台湾民众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我国台湾地区的余庆活动,宋江阵演武活动颇具多重象征寓意。大正十二年(1923年)日本东宫殿下(昭和天皇)到台湾巡视,台南地方士绅许廷光、黄欣、石秀芳等献上“御览”台湾“名产”——宋江阵和八爷、九爷等[32]。1925年,大正天皇第二子秩父宫殿下到台湾游览,台南地方官员、士绅安排余庆表演节目,场地位于台南州厅前广场,30余人演练宋江阵[33]69-70。这种特殊的“余庆”场域,宋江阵作为首个节目操弄给日本具有影响力的人物观看,凸显我国台湾民众对演武文化的认同性。对日本人来说,宋江阵文化是余庆场域的助兴方式;对我国台湾民众来说,宋江阵演武活动既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象征,又是中国传统文化实力与魅力的展示,更是民众引以为豪的历史心性诠释。日据时代,我国台湾不禁止宋江阵的演练,足证中华文化的不可抗御[34]23。
四、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1)在乡土宗教祭祀场域中,宋江阵表征勇武本质。宋江阵以武术对练、单练和行阵为主体内容,始终保持最原初的特质,成为保家护院的工具,并延生到乡土宗教祭祀场域中。因此,宋江阵在乡土宗教祭祀场域的出场,是保护神的力量与精神的象征,能发挥武阵功能,为祭祀活动顺利开展提供保障;同时又蕴含神人共娱、祖先尊崇等文化。正是这种多元一体的象征文化因素,推动了宋江阵演武文化在乡土宗教祭祀场域的可持续发展。从中可以发现,民族传统体育在乡土宗教祭祀场域的在场是一种身体运动与精神信仰的契合。
(2)宋江阵演武活动在村落宗族祭祀场域的出场,展示其蕴含的宗族文化象征与族人的血缘理性。在宋江阵参与者的话语叙事中,将这一民族传统体育与村落开基祖相互关联,构成村落宗族文化延续的组成部分,表达了村落族群后裔对宋江阵在宗族繁衍过程中所发挥作用的认同,并成为村落宗族文化的象征,成为勾勒族群后裔与先祖的媒介。在村落先祖祭祀为场域中,宋江阵已成为村落宗族先祖形象代表,并通过身体运动及话语叙事形式,传递族群后人对先祖们的尊崇,诠释他们基于先祖的血缘理性。这种血缘理性认知对于宗族凝聚、族群认同、身份认同的实践达成是有用的,对村落及两岸血缘共同体建设是有益的。
(3)宋江阵演武活动在庆典场域的出场,是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展示与象征,表达广大民众基于传统认知的文化自信。宋江阵在地域庆典活动中的出场,突显其地域文化象征性及代表性,展示广大民众对这种文化的地域化认同。将宋江阵作为一种象征文化,在特殊场域中向外国人展示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精髓,宣示广大民众的文化自信。这种文化自信是我国民族传统文化屹立世界之林的根基,为当下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国际化发展提供支撑,同时也成为打造民族传统体育国际话语权的内生动力。
(二)启示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大多发源、发展于乡土社会中,并在社会变迁中逐渐与广大民众的生活、习俗相互融合、协同发展,从而建构为多元一体的共生体系。当下,要做好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保护,必须充分认知民族传统体育传承境况与发展规律,在保持民族传统体育原生态特质的情形下,维护好民族传统体育与乡土习俗的共生体系,这是我国民族传统体育保护与传承的根基所在。在城镇化建设、农村人口流动等社会变迁境况下,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确实遭遇生存与发展的阻碍。因此,民族传统体育被“开发”、被改头换面,可能脱离或者正在脱离原有的生存土壤,原生态特质面临逐渐流失的境况。虽然,我们看到短暂的保护成效,但现实民族传统体育传承困境仍无法有效地解决。民族传统体育是历史进程的产物,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需要尊重传统、依托传统,而不是撕裂传统,因此保持原生态特质是民族传统体育生存与发展的最基本需求,是广大民众型塑文化自信的源头活水。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自信不是喊几句口号就能够实现的,而需要通过其自身的文化内涵与象征特质,以及依托共同建构的文化体系,并通过身体展演与口头叙事等形式实践达成。保持原生态并非与现代化发展相悖,从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历程来看,不同历史时期因社会需要及民族传统体育自身发展的需求,广大民众的生活、习俗文化会逐渐与之相互融合,共生发展,促生民族传统体育多元化文化内涵与象征寓意,推动民族传统体育的可持续发展。基于此,我们可以预见,民族传统体育在当下或未来发展中,因社会发展及自我完善需要,必然会融入一些新的文化元素。对此,我们不必过渡解读、苛求、排斥,一切应在保持原生态的基础上,秉承顺势而为、适者生存的传承思路,只有这样,才能促成其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