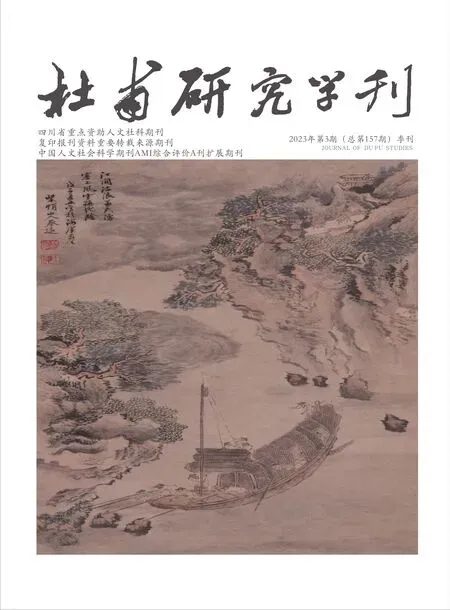走向下层:明代科举视域下韩愈古文的流播
莫 琼
一、问题的提出
明崇祯元年(1628),浙江仁和人刘士鏻重辑历代古文并付之梨枣,命名为《兰雪斋增订文致》。在说明《文致》选文宗旨的《纪凡》中,有两条凡例尤其值得注意:“一、文有以习厌而弃者,如《归去来词》《醉翁亭记》《北山移文》《吊古战场文》之类,自是风雅之宗,然耳目太熟,割爱置之。二、《文章轨范》一书,童习已久,凡经所选,不复再入,故即原选有《后赤壁赋》《送李愿序》及《祭十二郎文》,亦皆从删。”①〔明〕刘士鏻:《兰雪斋增订文致》卷首,上海图书馆藏明崇祯元年刻本。据此可知,刘氏选文,“耳目太熟”者不选,宋代谢枋得《文章轨范》中的文章也因“童习已久”,属于“耳目太熟”一类,不再选入,诸如陶渊明《归去来词》、孔稚珪《北山移文》、李华《吊古战场文》、韩愈《送李愿序》《祭十二郎文》、欧阳修《醉翁亭记》、苏轼《后赤壁赋》等名作皆在割爱之列。由此可以看出,由于文章选本的广泛传播,上述古文篇目,流传范围极广,已不再是精英阶层独占的文化读物,而流向下层群体。究其原因,不断完善并走向成熟的科举制度在其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桥梁作用。
明代是科举与教育这两种制度的关系越趋紧密的时代。明廷在南北两京均设国子监,地方府、州、县均设儒学,各都司卫所也设有学校,形成了较为完整与严密的学校系统。在这一时期,学校教育日益以科举考试为导向,负责教育的地方学官在实施具体教学措施的过程中,是如何将他们自己的教育理念贯彻其中,并进而影响文学发展以及文化走向,是颇值得探讨的议题①例如,师海军、张坤曾特别关注教育、科举与明代中期关陇作家群形成之间的关系,并重点提及杨一清(1454-1530)在弘治四年(1491)至弘治十一年(1498)间任陕西按察司副使时,“创办书院,亲自督教,培养了关陇作家群的许多核心人物,直接导致了关陇作家群的形成和发展”。参见师海军、张坤:《教育、科举的发展与关陇作家群的兴起——明代中期关陇作家群形成原因探析之一》,《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此外,叶晔也同样关注到杨一清提学陕西与弘治北地文风的兴起的关系,以及“七子”提学经历与郎署、地方间的文学互动等问题,进而认为提学制度“既是连接郎署文学与地方文学的制度纽带,又是郎署文学得以在师承上与馆阁相抗衡的重要利器之一”,“依赖于这一制度,他们将复古文学思潮从京城带至地方,扩大其流布的范围,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地方上的文学风气。与此同时,还在地方上培养了一批年轻作家,将他们提前带入复古文学的阵营,借此与馆阁文学的庶吉士培养模式相抗衡,保持阁、部文学在发展规模上的相对均势状态”。参见叶晔:《提学制度与明中叶复古文学的央地互动》,《文学遗产》2017年第5期。。在明代文学复古运动中,以“前后七子”为核心的中上层文人,提出了“文必先秦两汉”②〔明〕王九思:《明翰林修撰儒林郎康公神道之碑》,《渼陂续集》,《明别集丛刊》第1 辑,黄山书社2015年版,第86册,第65页。的文统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韩愈古文在主流文坛的生存空间。然而,韩愈古文乃至唐宋古文一脉并未由此而绝断。在重新将唐宋八家嵌入古文统绪,使得韩愈重新成为这个文统中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的过程中,“唐宋派”起了重要的作用。此外,在明人所选的众多通代或断代古文选本中,有相当数量的选本是由地方学官编选并主持刊刻的。在这些作为府、州、县学诸生习作古文的范本中,韩愈乃至“唐宋八大家”的古文多在必选之列,并且数量可观,这对促进韩愈古文以及“八大家”古文在地方上的流播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亦为后人研究韩愈古文在下层知识群体中的流播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此处所云“下层知识群体”,主要是指明代府、州、县学中存在着的数量巨大的生员群体,在进入地方各级学校之前,他们已在“小学”阶段完成了启蒙与识字教育③识字教育一般以《三字经》《千字文》等教材为主。相关研究参见吴宣德:《中国教育制度通史(明代卷)》第四章《明代的小学》,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63-342页;刘晓东:《明代的塾师与基层社会》第四章《馆塾日课与师道兴替》,商务印书馆2010 年版,第148-185页。。此生员群体,一般被认为是最低科名的拥有者,甚至被视作下层绅士①张仲礼认为:“绅士的地位是通过获取功名、学品、学衔和官职而获取的,凡属上述身份者自然成为绅士集团成员。……士人得到绅士地位的最低一级学品就是生员,这一学品的获得也需要经过一系列考试。‘生员’一词确切的意义是‘官办学校的学生’,它指的是在州、县学或府学里的学生。……许多通过初级考试的生员,捐监生以及其他一些有较低功名的人都属于下层(绅士)集团。”张仲礼著,李荣昌译:《中国绅士——关于其在十九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6页。。总体而言,“生员层慢慢从绅士层游离出来,成为相对独立的一个社会阶层”,不仅属于传统士大夫阶层,也是下层文人群体的一部分②参见陈宝:《明代儒学生员与地方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2页。。本文即以明代科举等相关制度与文化为媒介,探讨韩愈古文在此下层文人群体中的流播情况。
二、明代地方学校藏书楼的建设与韩文的流播
韩愈古文,自宋代起,便与科举考试联系在一起,成为考生模拟的对象,朱子即有云:“今日要做好文章者,但读《史》《汉》、韩、柳而不能,便请斫取老僧头去!”③〔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321页。明中期文人王文禄也曾指出:“唐韩昌黎已开课试之文之端。”④〔明〕王文禄:《文脉杂论》,《文脉》卷二,王水照编:《历代文话》,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册,第1697页。随着明代科举制度的成熟与生员人数的增加,对相关考试用书的需求也必然随之增加。明代初期,普通民众想要获取书籍十分不易,“靠钱财就能够得到书籍的例子实在太少,甚至是微乎其微”,此一阶段,“相比宋代而言,明代藏书更是凸显一种特权性质”,此外,“从弘治末年到嘉靖前半期,举业书的出版并不值得一提”⑤[日]井上进著,李俄宪译:《中国出版文化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第139页、第154页。。在这种情况下,一般的生员想要接触到包括韩文和其他举业书等考试用书在内的书籍,绝大多数时候,必须依靠学校的藏书,因此,建设藏书楼并添置书籍也就成为明代地方学官的重要任务之一。
明代地方学官,主要包括专门提督府、州、县各级地方的提学院道与巡按御史,以及具体负责府、州、县各级学校教育的学官。其中,明代于正统元年(1436)专设提学官员,总揽各省的学校教育,而府、州、县官员作为提调官则与儒学教官一起负责具体的日常管理与教学任务⑥有关明代地方学官制度、提学制度的发展情况,参见陈宝良:《明代学官制度探析》,《社会科学辑刊》1994年第3期;郭培贵:《试论明代提学制度的发展》,《文献》1997年第4期。。他们的主要工作和任务,概而言之,即“兴学养士而化民成俗”;分而言之,则包括修缮学校的设施、保障生员的食膳、培养生员的德行与考教生员的文艺等①关于提学官、提调官、儒学教官的工作和任务,明人薛应旂在其《浙江学政》中言之甚详,收入《方山先生全集》卷四十七,《明别集丛刊》第2 辑,黄山书社2016 年版,第55册,第502-514页。。
早在洪武二年(1369),朝廷就颁布了《立学设科分校条例》,令各处学校镌于碑石上,共9条,其中第四条云:“生员习学次第:侵晨,讲明经史,学律;饭后,学书,学礼,学乐,学算;未时,学习弓弩,教使器棒,举演重石。学此数件之外,果有余暇,愿学诏、诰、表、笺、疏、议、碑、传、记者,听从其便。”②〔明〕汪心:《(嘉靖)尉氏县志》卷二,《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本,上海古籍书店1963年版,第33b-34a。据此可知,明初开国之时,学校教育所重并不在“文艺”,生员也只是在学有余暇的时候学习诏诰等实用文体的写作。随着洪武十七年(1384)科举取士程式的确立,学校教育越来越向科举靠近,对提高生员文艺素质的要求也越来越迫切。明廷先后于正统元年、天顺六年(1462)与万历三年(1575)颁布了《提学敕谕》,为勉励生员进学,《敕谕》中均规定生员考试“不谙文理”者,或充吏,或罢黜为民③正统元年颁布的《敕谕》中规定:“生员有食廪六年以上,不谙文理者,悉发充吏。增广生入学六年以上,不谙文理者,罢黜为民,当差。”(《明英宗实录》卷一七“正统元年五月壬辰”条,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第346页)天顺六年的《敕谕》则在时间的限制上有所松动,曰:“生员考试,不谙文理者,廪膳十年以上,发附近去除充吏,六年以上,发本处充吏。增广十年以上,发本处充吏,六年以上,罢黜为民。未及六年者,量加决罚,勉励进学。”(《明英宗实录》卷三三六“天顺六年正月庚戌”条,第6866-6867 页)万历三年的《敕谕》基本继承了天顺六年的规定。,处罚颇为严厉。因此,各级学校对于能提高生员文艺水平的相关书籍的需求也与日俱增。
在明代,朝廷会向各级学校颁发书籍,因此,学校一般都设有尊经阁用以藏书。关于所颁降书籍的性质,洪武二十五年(1392),朝廷定礼射书数之法,其中第一条即云:“朝廷颁行经史、律诰、礼仪等书,生员务要熟读精通,以备科贡考试。”④〔明〕申时行等修:《学校·儒学·学规》,《(万历)大明会典》卷七十八,《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89册,第413页。可见,所颁书籍偏于性理、律诰等书,如洪武十四年(1381)颁《周易本义》《书经集注》《诗经集注》《春秋胡传》《礼记集说》《四书集注》各一部于县学⑤〔明〕李希程:《(嘉靖)兰阳县志》卷五,《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本,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5年版,第13b页。;永乐十五年(1417)颁《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于两京国子监及天下郡学⑥《明太宗实录》卷一八六“永乐十五年三月乙未”条,第1990 页。此条颁书令的实效在《(嘉靖)兰阳县志》得到了印证,见此书卷五。,又颁《为善阴骘》《孝顺事实》《劝善书》等书;嘉靖年间颁《明伦大典》《敬一箴》《四箴解》等书①参见《(万历)重修寿昌县志》卷三,第190 页;〔明〕周凤岐、张寅:《(嘉靖)太仓州志》卷四,《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本,上海书店1990年版,第312页。。这些书籍,或偏于说理,或重在说教。万历三年颁布的《提学敕谕》亦有规定云:“国家明经取士,说书者以宋儒传注为宗,行文者以典实纯正为尚。今后务将颁降《四书》《五经》《性理大全》《资治通鉴纲目》《大学衍义》《历代名臣奏议》《文章正宗》及当代诰律典制等书,课令生员诵习讲解,俾其通晓古今,适于世用,其有剽窃异端邪说、炫奇立异者,文虽工弗录。”②《学校·儒学·风宪官提督》,《(万历)大明会典》卷七八,第418页。这些书籍试图规定生员在思想方面的“纯正”以及教育的合法性③本杰明·艾尔曼在《明代政治与经学:周公辅成王》之《明初经、传及典籍之编纂》中说到:“除了对历史记录的‘修正’外,朱棣政权也需要教育的合法性。……这些文化上之努力……于1415年三部经典计划之出版发行时达于高潮。三部书分别为《四书大全》、《五经大全》,以及《性理大全》。”参见[美]艾尔曼著,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译:《经学·科举·文化史:艾尔曼自选集》,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7页。,至于如何作文,除《文章正宗》外,尚缺乏必要的文章范本。地方学校虽然有朝廷颁书,但是藏书的数量有限,而且种类较少,加之兵燹、火灾、水灾等原因,许多藏书楼所藏之书或残缺破损,或散佚不存④实际上,不惟地方官学缺乏书籍,就连两京国子监也面临缺书的危机。弘治五年(1492),时任内阁大学士丘濬上疏言:“今天下书籍尽归内府,两京国子监虽设典籍之官,然所牧掌,止是累朝颁降之书及原贮书版,别无其他书籍,其官稽于虚设。”(《明孝宗实录》卷六三“弘治五年五月”条,第1212页)。因此,建设藏书楼并添置书籍就成了地方学官的重要任务之一。学官捐俸购买与学校刊刻书籍是地方官学藏书的重要来源⑤如周士佐、张寅《(嘉靖)太仓州志》卷四《学校》“书籍”条记载:“嘉靖十五年,提学御史闻人诠命学正朱邦彦收采官给百金四十两,邦彦自以囊赀买之,得书数十种。金还官。”(《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本,上海书店1990年版,第312页)学官所买之书,应是当时坊刻,如杨维岳《(万历)忻州志》(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三十六年刻本)卷一“书籍”条所记载的藏书分为官板与坊板,坊板有《四书》《五经》《易经大全》《书经大全》《礼记大全》《礼记》《性理》《资治通鉴》《通鉴集要》等书,或即是从坊间购买而来。,许多古文选本,包括韩愈文集,即得以这种方式进入官学藏书楼,并成为生员的写作范本⑥卜正民在研究明代中期藏书楼的建设时提到:“颁书的方式却切实而有效。它成功地将大部分宫廷刻书颁发到全国的县学,从而在某种意义上也就决定了一个学校应该拥有什么样的书籍。”卜正民将明代藏书楼建设的历史看成一种社会运动,“在这项运动中,知识获取渠道逐渐开放,并在刺激中得到发展。然而,尽管为构建官学体系出现了各式各样的保守主义,但是一些人的心智却已然得到充分开放,就像公元6世纪那些放诞的心灵一般。有些人的心灵,通过到藏书楼阅读,至少也推开了那么一小点”。参见[加]卜正民著,陈时龙译:《明代的国家与社会》,商务印书馆2014 年版,第160 页、第175 页。地方学官以不同的方式将不同于朝廷颁书的书籍带到地方官学,也就有了“推开心灵”的作用。。
以韩愈文集为例,弘治十六年(1503),时任太和(今安徽太和)知县的戴鳌,将自己童年时期从真德秀《文章正宗》中手抄之75 篇韩文,加上不见于《文章正宗》之13篇韩文,分为上下卷,刊刻成册,是为《韩文正宗》。戴氏在《锓韩文正宗序》中录其好友汪子荣之语云:“举世学韩者也,子盍锓之与多士共?”①〔明〕戴鳌:《韩文正宗》卷首,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弘治十六年刻本。《韩文正宗》是明代现存最早的韩文选本,弥足珍贵。此外,据戴鳌的序,可知此本的刊刻地是在太和县,此县在明代隶属于南直隶凤阳府。可见,《韩文正宗》刊刻的目的在于为“多士”(即县学生员)提供学习的范本。嘉靖十六年(1537),时任巡按直隶监察御史的游居敬奉命巡按至宁国,即与宁国知府黎晨、宣城知县吴悌商定并校刻《韩文》《柳文》。游氏《刻韩柳文序》云,“取苏、闽旧刻,稍加参校,付之命工梓焉。……音切存其难解者,利习也。时本间有一二脱讹,取善本厘正焉,崇古也”,又云“司校刊则教谕陈思诚、训导陈嘉宾也;比襄厥成,教授郑富、训导何伟与有事焉”②〔明〕游居敬校刻:《韩文》卷首,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嘉靖十六年刻本。。可见,此次刊刻《韩》《柳文》是利于初学者,而发起此次校刻活动的是负有提督学校之责的巡按御史,参与者既包括当地的地方守官等提调官员,亦包括直接负责学生教育的教授、训导、教谕等儒学教官。至嘉靖三十五年(1556),时任巡按直隶监察御史的莫如士又重刻了游居敬所刻《韩》《柳文》。据《(万历)宁国府志》记载,宁国郡斋藏书中即有《韩》《柳文》③〔明〕陈俊:《(万历)宁国府志》卷一十二,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刻本,第1b页。。另据周弘祖《古今书刻》著录,南直隶苏州府、江西布政司、福建布政司等处皆刊刻有《韩文》④〔明〕周弘祖:《古今书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37页、第351页、第359页。。
此外,在出版业相对发达地区的官学藏书楼,亦往往藏有韩集等书籍供生员阅读使用,如《(嘉靖)建阳县志·学校志》“儒学尊经阁书目”条著录有《韩》《柳文》⑤〔明〕冯继科:《(嘉靖)建阳县志》卷五,《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本,上海古籍书店1962年版,第21b页。,《(嘉靖)宁波府志·经制志》记载奉化县学藏有《韩》《柳文》⑥〔明〕周希哲、张时彻:《(嘉靖)宁波府志》卷七,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嘉靖三十九年刻本。。值得注意的是,出版业相对落后地区的藏书楼,亦不乏相关藏书,如《(嘉靖)获鹿县志·学校》“书籍”条著录有“《韩文》,六本”⑦〔明〕赵惟勤:《(嘉靖)获鹿县志》卷六,《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本,上海书店1990年版,第631页。,《(嘉靖)普安州志·学校志》“书籍”条著录有“《韩》《柳文》,各一部”①〔明〕高廷愉:《(嘉靖)普安州志》卷三,《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本,上海古籍书店1961年版,第42b页。,《(嘉靖)河间府志·艺文志》“府学收藏书目”条著录有“《韩文》二部”②〔明〕樊深:《(嘉靖)河间府志》卷二十八,《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本,上海古籍书店1964年版,第58b页。,《(万历)来安县志》卷四“书籍”条著录有坊板《韩文》一部③〔明〕周之冕:《(天启)来安县志》卷四,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天启元年刻本,第2a页。,等等。何炳棣指出:“在贫穷与边远的地方,学校经常是唯一提供基本图书设备的场所。”④参见何炳棣著,徐泓译注:《明清社会史论》,台湾联经出版社2013年版,第211-212页。明代地方学官将书籍购至学校藏书楼,使得处于相对落后地区的生员有机会接触到一些基本的读物。这些地区分布范围较广,由此可见韩愈及其古文在下层知识群体中有着颇为广泛的受众。
明代官学藏书楼是对外开放的。叶德辉(1864-1927)在《书林清话》“宋元明官书许士子借读”一条中即说到:“刻书以便士人之购求,藏书以便学徒之借读,二者固交相为用。宋、明国子监及各州军、郡学,皆有官书以供众读。”⑤〔清〕叶德辉著,吴国武、桂枭整理:《书林清话》卷八,华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219页。除有藏书可供生员阅读之外,学官与生员还会在藏书楼中进行教学活动⑥如严汝麟于隆庆六年(1572)任全椒知县,继建尊经阁,并于此“校士课业,士子翕然宗之”。〔明〕戴瑞卿、李之茂:《(万历)滁阳志》卷一十二,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四十二年刻本。,生员主动接触书籍的机会也由此得到增加。在理想的状态下,生员或可以直接进入到藏书楼阅读相关书籍。
除了具有存藏书籍与提供教学空间之功能的藏书楼之外,在明代地方官学的建筑群之中,主祀孔子的先师庙具有崇高的地位。而在这象征着道统传承的先师庙中,韩愈得以“春秋以来诸儒”的身份从祀,接受师生的拜谒。在内,明代翰林院等处均以韩愈为祠祀对象,其原因在于明代官方对于韩愈的推崇以及韩文自身所具备的类似于“馆阁气象”的“廊庙气”⑦潘务正:《明清翰林院祠祀韩愈考》,《中华文史论丛》2011年第2期。。在外,除上述各官学藏书楼存藏韩集外,韩愈曾经仕宦或仕宦经过之地,大都建有“韩文公祠”“韩文公书院”等祠堂或书院以示尊崇。如袁州(今江西宜春)有韩文公祠,每岁春秋两祭⑧〔明〕严嵩撰:《(正德)袁州府志》卷五,《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本,上海古籍书店1963年版,第3a页。;潮州、阳山等地既有韩文公祠,又有韩山书院或尊韩书院⑨分见郭春震《(嘉靖)潮州府志》卷二,《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 年版,第190 页;戴璟《(嘉靖)广州通志初稿》卷一十六,明嘉靖刻本,第33a页、第31a页。;郴州有景贤祠,本在州学之内,遭毁后建在社学之东,祀韩愈及周敦颐①〔明〕胡汉:《(万历)郴州志》卷一十二,《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本,上海古籍书店1962年版,第5b页。。可以看出,从中央到地方,韩愈得以各种方式被推崇与祭祀。在此氛围下,韩愈及其道德文章一同得到传承与流播,并成为明人共同的文化记忆。
三、明代提学官的迁移与韩文的流播
明代地方学官中的提学官专一提督各方学校,其督学理念与政策将会直接影响一地的教育实践与文化风气。在明代“科举必由学校”②〔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六十九《选举志一》,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675页。的现实背景下,随着提学制度发展走向成熟,提学官在地方官僚社会中的地位也逐渐提高,并在正德(1506-1521)以后,以撰写试录序文与代作程文的方式参与到将科举理念具体化的乡试现场③[日]三浦秀一:《明朝提学官与各省乡试》,《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各提学官的学术背景虽然有所不同,但在搜集购买或者编辑刊刻相关书籍之时,其中所体现出来的文章观念仍然有其趋同性,即多崇尚以韩愈为代表的唐宋大家的古文。
顾潜(1471-1534)于弘治十七年(1504)以监察御史提调北直隶学校④《明孝宗实录》卷二一二“弘治十七年五月辛亥”条,第3978页。,其间曾颁布《申严条约事》,共21条,其中第十条云:“作文贵纯正明白,戒用尖新险怪之语。又须博学强记,《四书》《五经》之外,旁及诸子、诸史,并唐韩、柳,宋欧、苏、曾、王诸家之文,庶几临文资取不穷,或用其事,或师其意,或仿其格,无不可者。若徒记诵近时刊印时文并讲义活套等书,苟应考校,则其立志不远,取法已卑,验出必行惩责。其州县或因僻远,前项书籍艰得,提调官宜悉心访求,或翻刻,或抄写,各发该学,以便诸生。候本院按历之日开报。”⑤〔明〕顾潜:《提学公移》之《申严条约事》,《静观堂集》卷八,《明别集丛刊》第1辑,黄山书社2013年版,第84册,第148页。可以看到,作为提学官的顾潜,为生员开列了一份阅读书单,这份书单除了《四书》《五经》等必读书目之外,还包括子部、史部与集部书籍,而集部书籍则明确以唐代韩愈、柳宗元及宋代欧阳修、三苏、曾巩、王安石等八家为主,并令偏远州县的提调官访求刊刻或者抄写,以便生员使用。顾潜为弘治九年(1496)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当时教习庶吉士者为少詹事兼侍讲学士张升以及侍读学士王鏊⑥〔明〕谈迁撰,张宗祥点校:《国榷》卷四三“弘治九年闰三月”条,中华书局1958 年版,第2688-2689页。,因此,从顾潜为生员所开之书单来看,他无疑是深受永乐以来所形成的台阁文统观影响的,这个文统观即以唐宋文为文章的正宗①黄卓越:《明中后期文学思想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关于台阁文统观的问题,又可参看黄卓越《明永乐至嘉靖初诗文观研究》第一章《明代的台阁体及其早期思想基础的形成》(尤其是前两节)的相关论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7页)。。
同样具有台阁文学背景的还有嘉、万时期的胡汝嘉。胡汝嘉为嘉靖三十二年(1553)进士,改庶吉士②〔明〕王世贞撰,魏连科点校:《弇山堂别集》卷八十三《科试考三》,中华书局1985 年版,第1578页。,三十四年(1555)官翰林院编修③《明世宗实录》卷四百二十七“嘉靖三十四年十月己巳”条,第7384-7385页。,于万历元年(1573)十月起任河南右参议④《明神宗实录》卷一十八“万历元年十月甲子”条,第523-524页。,后改左参议,至万历四年(1576)四月任山西副使⑤《明神宗实录》卷四十九“万历四年四月壬辰”条,第1140页。。胡汝嘉在任官河南期间,主持编刻了《文章正宗钞》一书,其《刻文章正宗钞引》云:“怀守贾君以职事试诸□子员,既得其笃者,则录其文以示,余亟赏其才,……大抵尚高古者取秦汉,而或不宜于时好;务简便者取唐宋,而或未溯其本源。惟真氏所选《文章正宗》,体裁最为完备,而纵横变化一裁之以理,学古之士莫先焉。顾其篇帙浩瀚,诸生方务明经,不暇遍览,而诗词叙事又□□□所急。箧□偶有钞本,仅百篇,乃命梓于分省之公署,以与同志共之,非谓真氏之选有未工而有所去取于其间,亦非谓《正宗》之美者尽于此而已也,第欲使初学之士便于诵法云尔。若夫博雅君子则兼收广畜,虽西山旧本尚在包括中,而又何取于此……”⑥〔明〕胡时化:《文章正宗钞》卷首,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明万历三年刻本。按,引文中漫漶不清处,皆以□表示。据此可知,胡汝嘉编选《文章正宗钞》,令守令刊刻,是为了方便“初学之士”诵法。这里的“初学之士”,即指怀庆守“贾君”所说的儒学生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胡汝嘉说诸生所作习文存在两种倾向:以风格高古的秦汉文章为法,不为时宜所好;以风格简便的唐宋文章为法,又未能溯本清源。从有利于科举的角度来说,取法唐宋无疑是最佳选择,只不过需要溯源至秦汉之文。因此,《文章正宗钞》在选文上,前两卷选秦汉文48篇,后两卷选唐宋文49篇。在唐宋文中,卷三选唐文24篇,其中王勃文1篇、骆宾王文1篇、韩愈文17篇、柳宗元文5篇;卷四选北宋文25篇,其中欧阳修文5篇、范仲淹文1篇、王安石文1篇、李觏文1篇、苏洵文4篇、曾巩文2篇、苏轼文10篇、李格非文1篇。可以看到,除苏辙没有作品入选外,其选文范围基本在所谓的“唐宋八家”之内,其中尤以韩愈古文入选的数量为最多。这与前述台阁文统观具有一致性。另外,还需特别指出的是,《文章正宗钞》是在宋代真德秀《文章正宗》的基础上编选而成,而《文章正宗》不仅是万历三年所颁《提学敕谕》中所规定的各地方学校生员的必读书目,而且还是馆阁教习庶吉士的规定范本①参见黄卓越:《明永乐至嘉靖初诗文观研究》,第34-35页。另参叶晔《明代中央文官制度与文学》中《明代庶吉士教习范本与馆阁文学传统》的相关论述(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4-155页)。,故而具有馆阁背景的胡汝嘉以《文章正宗》为模本来重新编辑选本以供诸生学习,亦是将台阁文风带至了地方。胡汝嘉在任官河南之前,曾分别任广西按察司佥事、浙江按察司佥事②《明穆宗实录》卷五十四“隆庆五年二月丙申”条、卷六十九“隆庆六年四月甲戌”条,第1330页、第1666页。,在此之后,又升任山西按察司副使,长期掌管着一方学校的教育。尽管没有资料表明胡汝嘉在广西、浙江、山西等地也主持编刻了古文选本,但是可以推测的是,他的学术观念必定会影响到当地学官对于生员的教育理念,而《文章正宗钞》或曾随着胡汝嘉的升迁而被传至山西。曾任怀庆府推官的敖鲲,在万历八年(1580)以巡按福建监察御史的身份视学建州时,刊刻了《古文崇正》作为生员的举业法程,而《古文崇正》乃是敖鲲根据胡汝嘉《文章正宗钞》重新考订选辑而成的。《古文崇正》共选先秦汉魏唐宋文262篇,“唐宋八家”古文数量超过全书二分之一,其中韩文31篇③〔明〕敖鲲:《古文崇正》,明万历八年临江敖氏建州刻本。。唐宋古文的传统在建州地区得到了延续。
又如与胡汝嘉同年登第并同选庶吉士的孙应鳌(1527-1584),于嘉靖四十年(1561)始任陕西按察司副使提督学校④《明世宗实录》卷四百九十七“嘉靖四十年闰五月丙午”条,第8237页。,在任期间,孙应鳌因课士的需要,令诸生以宋人吕祖谦《古文关键》为习作模本。孙应鳌在《古文关键叙》中云:“诸生学文章于予,予愧无有所知以答诸生。尝闻古人能文章者,曰韩退之氏、柳子厚氏、欧阳六一氏、苏老泉氏、东坡氏、颍滨氏、曾南丰氏、陈宛丘氏,则固文章家之飞卫、泰豆者。而吕东莱氏所辑《古文关键》,则固亦退之诸氏承挺倒锥之形、趋走往还之迹也。诸生惟于所趋与不瞬者,以终身如一日之心求之,则至精之微,诸生将悟而得之。”⑤〔明〕孙应鳌撰,赵广生点校:《孙应鳌集》卷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年版,第21 页。按,《古文关键叙》收入孙应鳌《孙山甫督学文集》卷一,《明别集丛刊》第3辑,黄山书社2015 年版,第42 册,第509 页。据胡直作于嘉靖四十五年十月的《孙山甫督学文集序》(《孙山甫督学文集》卷首),可知此书所收文章时间断限也应在此之前。《古文关键》收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张耒等八家之文(《古文关键叙》中所云“陈宛丘氏”或为“张宛丘氏”之误),虽然王安石并不在列,但仍然是现存较早的以选本的形式确定“唐宋八家”古文统绪的文本。可见,曾以庶吉士的身份在翰林院读书的孙应鳌,亦将自己的阅读经验从中央馆阁传至了地方官学。
如果说具有台阁学术背景的提学官将韩愈古文乃至唐宋古文由中央传至地方,还在情理之中,那么作为明代中期复古文学运动核心人物的何景明,在其提督学校时将韩愈古文列为生员的必读篇目,就颇为耐人寻味了①何景明在《与李空同论诗书》中认为“古文之法亡于韩”,又将韩文列为学生的必读篇目,个中原因,应与何景明所具有的不同身份有关。作为复古派核心的何景明,论文主先秦两汉,贬斥韩文;而作为提学副使的何景明,在某种程度上还要兼任“举业师”(何景明《师问》)一职,出于举业的考虑,何景明让学生读韩文,亦在情理之中。。
何景明(1483-1521)中弘治十五年(1502)进士,于正德十三年(1518)五月至十六年(1521)六月任陕西提学副使②金荣权:《何景明年谱新编》,《信阳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在此期间,何景明有《学约古文》之作,其《学约古文序》云:“余初入关中,作《学约》示诸生,已成材者,经书、子、史,自宜罔贯,不为程限。其未成材者,令学官量资作成,以相授习,兹越二岁矣。……今复列为程,始自十六年春,按季考省。经书,每岁一周;性理、史鉴而下,则接年续去,期三年而卒其业。正诵之余,复读名家文字数篇,要取其虽非全编,而实览大义。于是究心则古人作述之意,源流可窥,而斯文经纬之情,变化俱见矣。”③〔明〕何景明著,李淑毅等点校:《何大复集》卷三四,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599页。按,本段引文句读与点校本稍有不同。据此可知,《学约古文》至少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正诵”的部分,即“经书、性理、史鉴”;二是名家之文。因为提学官的任期为三年,所以《学约古文》是以三年为一学程。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一部《何大复先生学约古文》,十二卷,题何景明辑,明岳伦增订,崇祯五年(1632)苟好善刻本。据苟好善刻本可知,《学约古文》共选韩愈古文3 篇,即《进学解》《平淮西碑》《毛颖传》,其中《进学解》被安排在第一年的秋三月学习,《平淮西碑》则在第二年的秋三月,《毛颖传》在第三年的夏三月。
除《学约古文》外,何景明在陕西提学副使任上,还曾有《古文集》之编。按,《古文集》四卷,有上海图书馆藏嘉靖十五年(1536)刻本。与《学约古文》相比,《古文集》只收名家之文,无“正诵”部分,所收之文均包含在《学约古文》中,因此,有理由相信《古文集》是将《学约古文》中的名家之文单独析出并刻梓以流传,以此来看,二者实际上是同书异名。孙应鳌在任陕西提学副使时,曾访求《古文集》全本并付梓,孙氏在《古文集序》中说:“大复何子择古文合于法者,凡四卷,梓诸秦之学台。”④《孙应鳌集》卷二,第31页。可知,《古文集》同样是用以教学的。
《学约古文》问世后,流传很广。先是,岳伦在嘉靖七年(1528)出任山东齐东县簿之时,将《学约古文》带至此处,复有增订,编为三卷,用以教学。其后,《古文集》经过张士隆(嘉靖初年为汉中守备副使,四年卒于任上)校订,在嘉靖十四年(1535)由时任巡按浙江监察御史的张景携至浙江,并在浙江布政司左参政洪珠的主持下,由嘉兴知府郑钢刊刻,时在嘉靖十五年①〔明〕何景明:《古文集》,上海图书馆藏明嘉靖十五年刻本。。此外,在嘉靖年间的直隶河间府、云南寻甸府、贵州普安州等地方学校的藏书楼里,《学约古文》也往往在列。可以看到,《学约古文》的流动经历了由西北向东、向东南、向东北、向西南等几条路线,空间分布广泛,韩愈古文也由此得到了广泛的流播。
同样因其流动的广泛性使得韩愈古文得到流播的,还有万历初期问世的《名世文宗》。《名世文宗》最初由时任合肥县令的胡时化奉南直隶提学御史褚鈇之命而选,用以课士,初刻是在万历四年(1576)七月,刻于合肥。同一年的十月,褚鈇将此书带至苏州,命苏州知府吴善言据以翻刻②〔明〕胡时化:《刻名世文宗序》,《新刊名世文宗》卷首,上海图书馆藏明万历四年刻本。。万历五年,褚鈇又将其携至池、宁(即池州府与宁国府),命冯叔吉与郭子章参订并付梓,共二十四卷(其中《外集》四卷)③〔明〕褚鈇:《名世文宗序》,胡时化《名世文宗》卷首,上海图书馆藏万历四年四明冯氏刻本。。万历七年,时任巡按御史的胡时化巡按至于苏州,将《名世文宗》重加汇择之后,交由苏州知府李充实刊刻,共三十卷④〔明〕王锡爵:《重刊名世文宗序》,胡时化《新刊名世文宗》卷首,美国柏克莱加州东亚图书馆藏明万历七年李充实刻本。。万历八年,胡时化任河南佥事,出万历七年本《名世文宗》,命怀庆府、卫辉府与彰德府等地分别刊刻⑤〔明〕郭朴:《重刊名世文宗序》,胡时化《名世文宗》卷首,上海图书馆藏明万历八年刻本。。无论是三十卷本,还是二十卷本的《名世文宗》,所重均在先秦两汉唐宋文,在唐宋文中又特重“八家”文,甚至有“独详于韩、苏者”⑥〔明〕胡时化辑,〔明〕郭子章参辑:《刻名世文宗议例》,《名世文宗》卷首,上海图书馆藏明万历五年四明冯氏刻本。之倾向。
随着提学官的迁移,韩愈古文的受众也得以随之扩大。这里主要有三条路径:第一,如上文所述,具有台阁学术背景的提学官将韩文从中央带至地方,再在各地之间流播,胡汝嘉《文章正宗钞》即是一例;第二,由在文坛上具有声望的提学官将韩文编入教程,而后韩文得以在各地之间流播,何景明《学约古文》即是一例;第三,由任科举发达地方的提学官将韩文编入古文选本,而后将其传至科举欠发达的地方,胡时化《名世文宗》即是一例⑦同样的例子,还有万历五年,时任江西道监察御史的虞怀忠奉命巡按四川时,因蜀中乏书,故编选《历代文宗》,命四川右参议范崙校订付梓,以供诸生学习。参见虞怀忠《刻文宗序》,《历代文宗》卷首,上海图书馆藏明万历五年刻本。。这三条由提学官的迁移而形成的传播路径,构成了一张书籍流传的网络,韩愈古文乃至唐宋古文的传统即循着这张网络得到了流播与延续。
四、余论
综合上述,明代地方学官特别是提学官员在主导地方教育时,因与科举考试适配的需要,多搜集购买或编辑刊刻韩愈文集或相关古文选本作为生员模写的范本。随着提学官员的迁移,这些书籍包括韩文也得到流播。这些书籍面向的是地方学校的广大生员,主要是在下层知识群体之间传播,因而,就有别于明代中上层文人中“文必先秦两汉”的主流文学取向。此外,以提学陕西的孙应鳌为例,他一方面在任上“为多位陕西作家刊印文集,以延续关陇的复古文脉”①叶晔:《提学制度与明中叶复古文学的央地互动》,《文学遗产》2017年第5期。;另一方面,如本文所论,他同样也将唐宋古文的传统由中央传到了地方。因此,如果说提学制度在实现明代中期复古文脉的传承中具有重要作用,那么,不应忽视的一点是,提学制度在传承唐宋古文的文脉上也同样具有着重要的作用。此条文脉通过下层群体来传承,或许有比主流文坛与文化场域更为广泛与深远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是以不断完善的科举制度与教育制度作为保障的。
如本文开篇所引刘士鏻《纪凡》之言,韩愈等人的文章名篇早已是童而习之,造成这一现象的,正是由于《文章轨范》(共收文69篇,其中韩文30篇,占总数的一半弱)等面向科举、面向下层群体的文章选本的广泛传播。王阳明(1472-1529)在《重刻文章轨范序》中说:“宋谢枋得氏取古文之有资于场屋者,自汉迄宋,凡六十有九篇,标揭其篇章句字之法,名之曰《文章轨范》。盖古文之奥不止于是,是独为举业者设耳。世之学者传习已久,而贵阳之士独未之多见。侍御王君汝楫于按历之暇,手录其所记忆,求善本而校是之;谋诸方伯郭公辈,相与捐俸廪之资,锓之梓,将以嘉惠贵阳之士。”②〔明〕王守仁著,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等编校:《外集四》,《王阳明全集》卷二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964页。这篇文章作于正德三年(1508),王阳明谪贵阳之时。王阳明《序》中云《文章轨范》“世之学者传习已久,而贵阳之士独未之多见”,其中原因乃是贵阳偏于一隅,社会文化与出版业都相对落后之故。作为地方官员的王汝楫手录一本,求善本校定,并与“郭公”捐俸刻梓,亦可知《文章轨范》作为举业范本,在明代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除《文章轨范》之外,吕祖谦《古文关键》、楼昉《崇古文诀》、真德秀《文章正宗》等宋人文章选本,实际上已在社会上构成一种公共知识,并对形塑明人的文学记忆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主流层面,经过明代文坛宗“先秦两汉”还是宗“唐宋古文”等主张的激烈碰撞之后,以韩愈为代表的唐宋文统在清初得到重构,重构后的文学典型具有强化意识形态的独特功能①郭英德:《唐宋古文典型在清初的重构》,《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而在下层,以科举制等作为制度保障,此条文脉在我国古代社会后期长期地延续下来。在清末光绪三十一年(1905)诏停科举之后,此制度保障被切断。在此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文学革命”派倡导白话文学,其矛头直指桐城古文与六朝骈文,钱玄同直斥之为“桐城谬种”与“选学妖孽”②钱玄同:《赞文艺改良附论中国文学之分期》,《新青年》1917年第2卷第6号,收入《钱玄同文集》第一卷《文学革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而桐城派推尊以韩愈为代表的唐宋古文,韩愈等人的地位因此再次受到挑战,以至于民众已不知“唐宋八家究指何人”③《申报》1930年6月20日刊载俞剑华《会考珍闻》一文,其中提到由上海市教育局举行的初中毕业会考中,有测验题为“唐宋八家究指何人”。。为改善这种境况,在民国时期学校国文教育中,韩愈等人的文章往往会被选入当时的中学国文教科书之中,如林纾(1852-1924)《重订中学国文读本》等。王汎森指出:“如果我们想了解的是每一个时代大多数人历史意识的形成,则目前史学史方面的著作显然有很大的局限。常民有他们自己的历史世界,一样侃侃而谈历史,而其知识来源往往不是出自史学史中常见的历史著作。当他们与历史学家辩论时,也不轻易退让,令人觉得历史记忆的世界似乎没有最高仲裁者。”④王汎森:《历史教科书与历史记忆》,《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香港三联书店2020年版,第347页。如同常民的历史世界往往不是来源于严肃的史学史著作一样,常民的文学世界亦往往与主流文学场域有别,这一点,在我国古代近世社会转型的背景下,结合经学等传统学术在科举制度与雕版印刷术等因素的推动下出现通俗化的倾向来看⑤传统经学的通俗化,可参看顾永新:《经学文献的衍生与通俗化——以近古时代的传刻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文化下移的脉络当能看得更为清晰明了。
——以明代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