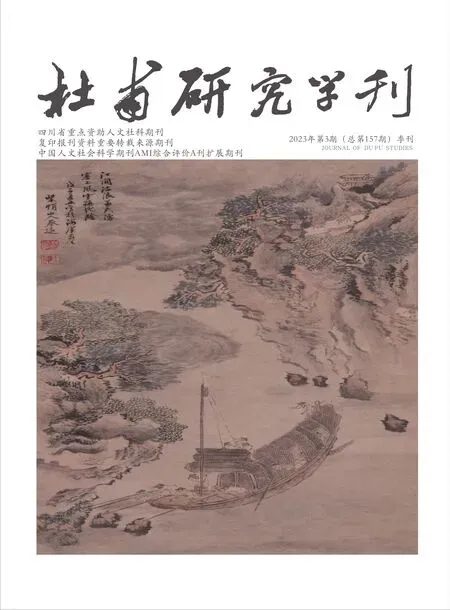“昔”与“忆昔”:杜甫往事书写的文学史意义
傅绍良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①〔唐〕杜甫撰,〔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163页。本文所引杜诗均以仇注为底本,后文不再另行出注。这是杜甫《忆昔二首》其二中的名句,是杜甫送给唐王朝最好的礼物,也是他留给后世的最美好的记忆。在中国诗歌史上,这是“忆昔”第一次作为诗歌题目出现,也是“忆昔”书写第一次承载重大的时代主题。所以,杜甫的“忆昔”诗,在诗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联系杜甫生平我们还会发现,杜甫的忆昔书写与其谏官经历所形成的朝班意识又密切相关,是杜甫朝班意识中的天下思维和谏诤精神,使他改变了传统“忆昔”的时空维度,把唐王朝的过去与现实对应起来,表达自己强烈的今昔感慨,反映王朝的盛衰之变,具有鲜明的“诗史”特征。
一、唐前诗歌中的“昔”与“忆昔”
忆昔,即回忆往昔,这本是文学创作中最普遍的题材来源和表现手法,但翻检唐前诗歌,我们发现,先秦和汉代的诗歌中,回忆往昔的题材书写虽然很多,但没有以“忆昔”的句式出现。《诗经》篇章中的往昔书写,没有直接带“忆”字的诗句,忆昔题材的书写用“昔”字的诗句也不多,只零星出现,如《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①〔西汉〕毛亨传,〔东汉〕郑玄笺,〔唐〕陆德明音义,孔祥军点校:《毛诗传笺》,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219页。又《楚茨》:“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为,我蓺黍稷。”②《毛诗传笺》,第307页。《楚辞》中的往昔书写,直接用“忆”字的诗句没有,但有“昔”字句的篇目及段落。其中,往昔书写最集中的篇章是《离骚》和《九章》。东汉王逸云:“屈原执履忠贞而被谗邪,忧心烦乱,不知所愬,乃作《离骚经》。”“屈原放在草野,复作《九章》,援天引圣,以自证明,终不见省。”③〔南宋〕洪兴祖撰,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页。《离骚》《九章》都是屈原追忆往昔的作品,应该在我们的研究视野里。而受选题的限制,我们这里仅录其中带“昔”字的往昔书写。经翻阅发现,屈原带“昔”字的往昔书写有两种类型。
一是单句式。如《离骚》中“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④《楚辞补注》,第40页。以下所引楚辞原文均出自此书,不再一一出注。。这种用法与《诗经·采薇》之句相似,昔与今对举,构成明显对比,语言简洁,修辞特征明显。
二是段落式。这种方式是以“昔”起头,展开对往昔回忆式叙述,所述内容比较多,所抒发的情感也比较复杂,昔与今的对比更加强烈。由于篇幅较长,“昔”的书写能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叙事结构。这在《惜诵》和《抽思》中表现得比较明显。如:
昔余梦登天兮,魂中道而无杭。吾使厉神占之兮,曰有志极而无旁。终危独以离异兮?曰君可思而不可恃。故众口其铄金兮,初若是而逢殆。(《惜诵》)
昔君与我诚言兮,曰黄昏以为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憍吾以其美好兮,览余以其修姱。与余言而不信兮,盖为余而造怒。(《抽思》)
《惜诵》:“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杼情。”《抽思》:“结微情以陈词兮,矫以遗夫美人。”作为两首抒情长诗,屈原在作品中抒发了自己被放逐时的忧愤和孤傲,而“昔余梦登天”的记梦和“昔君与我诚言”的往事,构成了其抒情的重要环节。“昔”字所引起的往事追忆,或虚拟了一个对话场景,或忆写了一段君臣旧契,曲尽作者内心的期待和矛盾。“昔”的忆写对“今”的情感抒发起了极大的反衬作用,这既是作者情感的自然流露,又使得诗歌的结构更加曲折。诚如洪兴祖评曰:“(《惜诵》)言己以忠信事君,可质于明神。”“(《抽思》)言己所以多忧者,以君信谀而自圣,眩于名实,昧于施报。己虽忠直,无所赴愬,故反复其词,以泄忧思也。”⑤《楚辞补注》,第128页、第141页。
可以看出,以“昔”字引出的忆昔书写在《楚辞》中运用得虽不太多,但段落式的忆昔书写具有比较特殊的意义。首先,“昔”与“今”对写既是反衬,又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章法结构,它的抒情作用大于“昔”与“今”的单句对比,是一种表现力更丰富的抒情手段。其次,“昔余”“昔与某”的表达方式,比较贴合忆昔的口气,能提升独立叙写的辨识度,利于忆昔书写的展开。
《九章》中还有一篇《惜往日》,主要写了两个内容:其一,忆“往日”受君王信任时所建之功,“奉先功以照下”“国富强而法立”;其二,感慨自己被谗害,“君无度而弗察兮,使芳草为薮幽”。从忆昔书写的形式来说,《惜往日》虽然未以忆昔为标题,其实就是忆昔书写,可以作为以“忆昔”标目的先声。
汉魏晋南北朝期间,忆昔书写基本沿续屈原的路数,“昔”字所直接引起的单句书写大量增加的同时,段落式的“昔”字也运用得很广泛,“昔余”“昔我”“昔有”“昔为”“昔闻”“往昔”“昔在”等词组搭配,比比皆是,而赋中用得较多的是“昔者”,限于篇幅,不一一列举。诗人在“昔”字的单句书写方面,有些只是作为“今”的对应体而出现,内容比较简单;有些则成为忆写主体,“昔”字引发诗人追忆往事、叙写过去,叙事因素增加了许多。如阮籍《咏怀》其二十九:
昔余游大梁,登于黄华颠。共工宅玄冥,高台造青天。幽荒邈悠悠,凄怆怀所怜。所怜者谁子?明察自照妍。应龙沈冀州,妖女不得眠。肆侈陵世俗,岂云永厥年!①〔三国魏〕阮籍著,陈伯君校注:《阮籍集校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01页。
又张协《咏史》:
昔在西京时,朝野多欢娱。蔼蔼东都门,群公祖二疏。朱轩曜金城,供帐临长衢。达人知止足,遗荣忽如无。抽簪解朝衣,散发归海隅。行人为陨涕,贤哉此大夫。挥金乐当年,岁暮不留储。顾谓四座宾,多财为累愚。清风激万代,名与天壤俱。咄此蝉冕客,君绅宜见书。②丁福保编:《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93页。
相对于《楚辞》中段落式的忆昔书写,这两首诗的“昔”侧重叙事,几乎完整地讲述了“昔余”和“昔在”某地的经历,只在结尾处点出忆昔之由,揭示主题。所以,诗歌虽然没有在标题上用“忆昔”,其实是以忆昔为主体进行写作的。
而就在这个时期,出现了“忆昔”句式。据丁福保编《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检索,共有以下4首:晋无名氏《从者歌》、宋鲍照《代挽歌》《代少年时至衰老行》、陈江总《怨诗》。与几百年历史相对比,这4首诗的数量是少了一些,且几首诗的内容和主题也比较集中,2首为挽诗,1首叹衰老诗,1首为怨诗,似乎都与伤感情绪有关,是通过忆昔之美好伤今之亡衰,抒写一种生命的悲忧。如:
可怜司马公,作性甚温良。忆昔水边戏,使我不能忘。(无名氏《从者歌》)①《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第556页。
忆昔好饮酒,素盘进青梅。彭韩及廉蔺,畴昔已成灰。壮士皆死尽,余人安在哉?(鲍照《代挽歌》)②〔南朝宋〕鲍照著,丁福林、丛玲玲校注:《鲍照集校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616页。
忆昔少年时,驰逐好名晨。结友多贵门,出入富儿邻。……今日每想念,此事邈无因。寄语后生子,作乐当及春。(鲍照《代少年时至衰老行》)③《鲍照集校注》,第220页。
采桑归路河流深,忆昔相期柏树林。奈许新缣伤妾意,无由故剑动君心。(江总《怨诗二首》其一)④《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第1410页。
“忆昔”句式所引领的往昔回忆,以今日的衰损和终结对应当年的另一面,从这个角度来说,“忆昔”句式的出现似乎具有一定的偶然性。诗人们忆昔书写的整体习惯还是以“昔”字句领起咏怀、咏史等,叙写“昔余”“昔在”的经历。所以“忆昔”句式仅在挽歌、伤悼等情感抒发时偶尔用及,所表现的内容并不深刻,所叙及事情也不复杂。
二、杜甫有“昔”字诗歌的往事忆写
“忆昔”句式较少的局面在唐代诗歌中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唐代诗人继续用“昔”字表现往昔,“昔”字句的往事书写不胜枚举,同时也大量使用“忆昔”词组。据《全唐诗》检索,唐诗中“忆昔”词组引领的诗句多达140 余条。从初唐到晚唐,几乎每一位大诗人都有以“忆昔”领写的诗句,尤以杜甫、李白、白居易、元稹居多,杜甫13 条,李白7 条,白居易12 条,元稹5 条。从诗歌创作的质量来说,也许这种统计没有太大意义,但在这些数字的背后,我们能看到诗歌语言表达习惯的改变,以及这种改变所带来的诗歌忆昔书写的新变化。杜甫的忆昔书写既产生于这种背景,又把古代的忆昔书写提升到了更高的境界。
不可否认的是,在忆写往事方面,杜甫的“昔”字句要多于“忆昔”词组,他在人生不同阶段的往事回忆与书写,也多用“昔”字。据《杜诗详注》检索,杜甫“昔”字句有200多条,不仅运用范围广泛,涵盖了其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昔”字所能搭配的词组几乎都用上了。所以,讨论杜甫如何使用“昔”字,其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在此,我们仅从三个方面重点谈谈杜甫“昔”字句运用的特色。
第一,杜甫特别喜欢而且擅长用“昔”“今”对举句,强化今昔对比。杜甫的这种对举句式具有极大的时空跨越度,而在这个时空中的变化和遭遇也往往表现得格外有感观冲击力。如他写自己晚年的处境和心态,“昔如纵壑鱼,今如丧家狗”(《将适吴楚留别章使君留后兼幕府诸公得柳字》),让人强烈地感受到了他飘零的悲苦。写郑虔:“昔如水上鸥,今为罝中兔。”(《有怀台州郑十八司户》)其“想像郑公孤危之状,如亲见,亦如亲历”①〔明〕王嗣奭撰:《杜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85页。。叹时光之飞逝:“伊昔黄花酒,如今白发翁”(《九日登梓州城》),“关内昔分袂,天边今转蓬”(《寄司马山人十二韵》),“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此句暗含了‘今’字)”(《赠卫八处士》)。述自己的游踪:“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登岳阳楼》)写自己的避乱心态:“昔去为忧乱兵入,今来已恐邻人非”(《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其五),“昔遭衰世皆晦迹,今幸乐国养微躯”(《岳麓山道林二寺行》)。除了这种两句对举句式外,杜甫还有一句诗中昔今对举的,如《哀王孙》:“昔何勇锐今何愚。”也还有四句式的,如《草堂》:“昔我去草堂,蛮夷塞成都。今我归草堂,成都适无虞。”杜甫昔今对举的句式运用得很自如,他在不同的句式中,都能高度概写昔与今的状态,对仗工稳,具有很强的感情色彩。
第二,杜甫晚年追忆自己往昔的游历,常用“我昔”和“昔我”这样的字句引起,展开较详细的叙事,角色明确,阶段性强,细腻地表达自己不同时期的情感和心态。“昔我”和“我昔”这类昔字书写与昔今对比句最大的区别是突破对偶式的昔今对举法,用较长的篇幅追忆往昔的自我,与今日的自我形成明显的对照。
杜甫“昔我”和“我昔”的往昔追忆多写于夔州时期,与下文要谈的“忆昔”背景相同。其中有3首诗比较集中,即《杜鹃》《遣怀》和《又上后园山脚》。这3首诗都是基于自我所居所闻而引起的往昔叙事,由叙述“我昔游锦城”“昔我游宋中”“昔我游山东”时之所历,转而表达今日之所忧。这是一种从微观感事到宏观议事的怀旧,是杜甫晚年表达社会关怀的基本模式。如《杜鹃》:
我昔游锦城,结庐锦水边。有竹一顷余,乔木上参天。杜鹃暮春至,哀哀叫其间。我见常再拜,重是古帝魂。杜甫对杜鹃十分留心,多次题咏,除这首诗外,还有两首同题的《杜鹃行》。杜甫着笔于杜鹃的感情动机是“君不见,昔日蜀天子,化作杜鹃似老乌”(《杜鹃行》),也就是他在这里所说的“古帝魂”。所以,他在云安听到杜鹃声,唤起了他在锦城的经历,然后感叹道:“圣贤古法则,付与后世传。君看禽鸟情,犹解事杜鹃。”(《杜鹃》)寓意十分清楚,“讥世之不修臣节者,曾禽鸟之不若耳”②《杜诗详注》引赵次公语,第1251页。。
又如《遣怀》叙“昔我游宋中”时的豪兴,更忆写了与李白和高适的交游:
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两公壮藻思,得我色敷腴。气酣登吹台,怀古视平芜。芒砀云一去,雁鹜空相呼。
前人对这段描写十分赞赏,称:“知己胜游,终身怀抱,故屡形之篇什,不厌其烦。”①〔唐〕杜甫撰,〔清〕杨伦笺注:《杜诗镜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703页。其实这并不是作者的愁怀所在,他所愁的是唐玄宗时期的拓边战争所造成的社会动荡以及友朋在动荡中的飘零:“拓境功未已,元和辞大垆。乱离朋友尽,合沓岁月徂。吾衰将焉托?存殁再呜呼。萧条益堪愧,独在天一隅。”杜甫“愧”什么呢?答案在篇末:“常恐违抚孤。”或许是当年朋友间互有抚孤之托,而今高、李已逝,自己却流落天涯,难践昔约,心有愧意。故宋赵次公评曰:“盖恐违戾抚养高、李二公之孤也。此其为朋友之义矣。”②〔唐〕杜甫著,〔宋〕赵次公注,林继中辑校:《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修订本)己帙卷之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313页。
再如《又上后园山脚》:
昔我游山东,忆戏东岳阳。穷秋立日观,矫首望八荒。朱崖著毫发,碧海吹衣裳。蓐收困用事,玄冥蔚强梁。逝水自朝宗,镇石各其方。平原独憔悴,农力废耕桑。非关风露凋,曾是戍役伤。于时国用富,足以守边疆。
作者曾作有《上后园山脚》,感叹道:“故园暗戎马,骨肉失追寻。时危无消息,老去多归心。”而今“又上”,思绪宕开,由山脚小园追忆山东平原。“到今事反覆”,一切都变了,流落到江峡的老诗人,忧心万分,“肺萎属久战,骨出热中肠。”王嗣奭说杜甫此诗“为性情之诗也”③《杜臆》,第306页。。原因有三:其一,忆昔之真;其二,忧世之悲;其三,伤己之深。作者两上后园,忆昔伤己,悲切感人。
杜甫晚年回忆性的诗歌很多,虽然他多次用“我昔”和“昔我”回忆往事,而触发他回忆的媒质其实就是他身边的自然场景。“杜鹃”的啼鸣、巫峡的风浪、居所小园后的山岗都能让他的思绪回到当年某个特定的时刻,以回忆书写,重现昔日的情景,构成伤感今日的对应体。“我昔游锦城”“昔我游宋中”“昔我游山东”诸句,地域色彩明晰,时空跨度极大,体现了杜甫晚年内心世界的深厚宽广。
第三,时代的昔今之变。“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昔时。”(《秋兴八首》其四)杜甫作为一个个体,其于整个时代也许微不足道,但他晚年的忆昔书写,则赋予了自我情感和经历巨大的社会意义。他的忆写,构成了一种难得的时代参照,也使他笔下的昔与今,不再是他个人的,而是时代的。“百年世事”,是杜甫自觉地担当起了描绘时代变化的使命,而“异昔时”则是杜甫描绘时代变化的主要材料。
基于这种情感寄托,杜甫“昔”字句的往昔追忆,常常很自然地集中指向玄宗时代。杜甫的《忆昔二首》其二这首诗,我们将在后面讨论,这里只论其“昔”字句中所涉及的玄宗时代的往事追忆。杜甫在夔州时期写了一组无题诗,每篇以首句二字为题,有《洞房》《宿昔》《能画》《斗鸡》《历历》《洛阳》《骊山》《提封》八首。这是杜甫忆写玄宗朝的名篇,仇兆鳌曰:“《秋兴》及《洞房》诸诗,摹情写景,有关国家治乱兴亡,寄托深长。《秋兴》八首,气象高华,声节悲壮,读之令人兴会勃然。《洞房》八章,意思沉郁,词旨凄凉,读之令人感伤欲绝。此皆少陵聚精会神之作。”①《杜诗详注》,第1529页。他以“昔”字句所引起的玄宗朝的记忆有《宿昔》和《洛阳》两章。但与他的亲历性追忆不同,杜甫这两章所写的都不是自己之亲历,而是用想象叙事的方式,对开元、天宝年间的那些皇家秘事进行叙写,也近乎史笔。《宿昔》云:
宿昔青门里,蓬莱仗数移。花娇迎杂树,龙喜出平池。落日留王母,微风倚少儿。宫中行乐秘,少有外人知。
仇兆鳌云“此追叙明皇逸豫之事”②《杜诗详注》,第1521页。,虚实结合,寓讽于事。以追叙者的清醒,讽玄宗当年的昏聩。“行乐”二字,笔力千钧,道出了千古兴亡的要害。《洛阳》云:
洛阳昔陷没,胡马犯潼关。天子初愁思,都人惨别颜。清笳去宫阙,翠盖出关山。故老仍流涕,龙髯幸再攀。
“天子初愁思”,用笔十分巧妙,既写了玄宗在安史之乱初的心理活动,又暗讽了他耽于享乐而离京失国的狼狈。正如前人所云:“‘初’字妙,盖向不知愁者。”③《杜臆》,第261页。“‘初’字,微词,至是始‘愁’也。”④〔清〕浦起龙撰:《读杜心解》,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513页。杨伦《杜诗镜铨》引张綖语说得更直白:“一‘初’字,便见平日歌舞荒淫,全不知备意。”⑤《杜诗镜铨》,第826页。杜甫不是皇家秘事的目击者,但他的追忆却真实重现了玄宗的当年,在追忆中暗讽玄宗的所为,在追忆中痛惜国运的衰落。
杜甫晚年时常见到玄宗朝的旧人或旧迹,也以“昔”字领起往事书写,写得十分真切感人。杜甫有《殿中杨监见示张旭草书图》《杨监又出画鹰十二扇》(此诗将在下文讨论)《送顾八分文学适洪吉州》《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等诗,分别从开元年间张旭的草书、顾戒奢的篆书、公孙大娘的舞剑器等入手,以他们杰出的才艺作为开元时代的象征,从不同的角度,倾注了自己的多种昔今感慨。
这几首诗的主角似乎都与开元时期尚在青壮年的作者有着某种特殊的因缘,所以当杜甫晚年流落江峡再睹其迹、其艺、其人,不由得让自己与他们一起都带上“开元故人”的印迹,一起重现当年盛景:
念昔挥毫端,不独观酒德。(《殿中杨监见示张旭草书图》)
昔在开元中,韩蔡同贔屭。玄宗妙其书,是以数子至。(《送顾八分文学适洪吉州》)
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
杜甫在悲忧的心绪中怀旧,将自己的盛衰之感投印到了这些“开元故人”的符号上,因而,这些“开元故人”也都以不同的形态,寄托了作者对那个时代的怀念与感伤。杜甫与张旭应为神交,早年写《饮中八仙歌》,为张旭书草写神:“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晚年再睹草圣书迹,杜甫喜中有忧:“斯人已云亡,草圣秘难得。……未知张王后,谁并百代则。”张旭是杜甫壮年时期书酒才气的偶像,也是杜甫盛世长安的幻影。百年之后的草圣能有他这样的知音,而杜甫诗歌百年之后又如何呢?这是杜甫的自负和自伤。杜甫与顾戒奢应为至交:“文学与我游,萧疏外声利。追随二十载,浩荡长安醉。”晚年在公安再遇,二人一样颠沛,“我甘多病老,子负忧世志。胡为困衣食,颜色少称遂”。所以,感叹“才尽伤形骸”,这是他们的不幸遭遇,是被盛世抛弃的无奈。而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更是一段让杜甫感伤的场景。杜甫在此“感时抚事”的感伤有三:其一,时代的巨大变化,“五十年间似反掌,风尘澒洞昏王室”;其二,开元盛事的凋零,“梨园弟子散如烟”;其三,开元故人的飘泊,“老夫不知其所往,足茧荒山转愁疾”。
张旭、顾戒奢、公孙大娘的忆写,既是偶然,又是必然。怀旧是晚年杜甫诗思的重要感发点,盛衰之变的经历,让他形成了一种较稳定的心理结构,任何一种媒质都可能触动他的这种心结,尤其是“开元故人”的出现,能打开他内心久藏的盛世影像。媒质是偶然,忆旧是必然。他的往昔叙事就是用不变的怀旧与偶遇的人或事相组合,形成一种稳定的昔今对比和感伤。
三、杜甫有“忆昔”词组诗歌的往事忆写
如前所述,“忆昔”一词因为杜甫而成了往事忆写最重要的方式,以至于世人对开元盛世的概括也多用他的《忆昔》诗和“忆昔开元全盛日”这样的名句。解读杜甫的“昔”字句诗歌的往事书写,为我们分析其“忆昔”词组的诗和以《忆昔》为题的诗做好了充足的准备。杜甫有“忆昔”词组诗句的作品共11 首,即:《哀江头》《彭衙行》《垂老别》《韦讽录事宅观曹将军画马》《夔州歌十绝句(其八)》《杨监又示画鹰十二扇》《羌村三首(其二)》《八哀诗·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病橘》《寄薛三郎中琚》《别李乂》。以“忆昔”为题的诗3首,即《忆昔二首》《忆昔行》。宋赵次公曰:“忆昔者,追忆往昔也。两字出鲍照《少年时至衰老行》云:‘忆昔少年时,驰逐好名晨。’故公有《忆昔》之作,止摘句首两字为题。”①《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修订本)己帙卷之二,第1354页。此拈出“忆昔”二字的来源,于我们理解杜甫的“忆昔”诗创作似乎没有太大帮助。我们只有联系杜甫有“忆昔”词组的诗歌进行分析,才能真正理解杜甫诗歌创作的动机及意义。
杜甫带“忆昔”词组的诗歌集中出现于安史之乱爆发之初。《哀江头》作于至德二载(757)陷贼长安时,《羌村三首》其二、《彭衙行》作于同年在鄜州时,《垂老别》作于乾元二年(759)在华州时。相对而言,杜甫用“昔”字句的忆旧要早很多,其《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作于天宝七载(747),那是杜甫求仕长安时期,可以明显看到,“昔”和“忆昔”两个时段杜甫所忆的往事不一样。《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云:“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忆写自己的过去,以为干谒求仕之资。这是一种自我书写,具有较强的个人功利。但是在几首带有“忆昔”词组的诗歌中,杜甫所忆的往事均涉国运,以他者书写为主,具有极强的社会关怀。
杜甫以“忆昔”写往事,不仅仅是词语音节的变化,更是叙事视角的转变。《哀江头》,“忆贵妃游苑事”②《杜诗详注》,第330页。,主旨很明显。《羌村三首》其二中有:“忆昔好追凉,故绕池边树。萧萧北风劲,抚事煎百虑。”看似忆己,实则象征性地忆时代。昔日天下太平,追凉绕树,何其自得;而今天下大乱,北风啸啸,让人煎虑难安。此四句重点在“抚事”,他所抚者不仅是个人,更是社会。《彭衙行》虽写自己“逃难之苦愈真”③《杜诗详注》,第416页。,然从开篇之“忆昔避贼初”到末尾之“胡羯仍构患”,都是将自己之难与时代之难揉杂在一起,“时艰”是自我与时代共同的背景。《垂老别》:“势异邺城下,纵死时犹宽。人生有离合,岂择衰盛端。忆昔少壮日,迟回竟长叹。”诗中的“少壮日”为兼指,既言自己身体强壮时,又言国家安泰之时。这是垂老从军者忆昔的痛苦,也是作者的忧苦,诚如前人所云:“《新安》《石壕》《新婚》《垂老》诸诗,述军兴之调发,写民情之怨哀,详矣。”④《杜诗详注》引胡夏客语,第537页。
杜甫“忆昔”句诗歌叙事视角的变化,在他晚年的往事追忆中又基本定格在开元时代。《忆昔二首》的第二首以“忆昔开元全盛日”开篇,满怀深情地忆写了开元盛世,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记忆: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百余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
这段文字,几乎将古代盛世的基本元素都囊括进去了,如仇兆鳌云:“此追思开元盛事。当时既庶而富,盗息民安,刑政平,风俗厚,制礼作乐,几于贞观之治。”①《杜诗详注》,第1163页。对“开元盛世”理想化记忆书写是杜甫晚年社会关怀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开元记忆书写尽管有盛衰之变的感伤,但“忆昔”句所展开的开元风物,总能让人联想到那个时代的盛景。如《韦讽录事宅观曹将军画马》:
忆昔巡幸新丰宫,翠华拂天来向东。腾骧磊落三万匹,皆与此图筋骨同。
又《杨监又出画鹰十二扇》:
忆昔骊山宫,冬移含元仗。天寒大羽猎,此物神俱王。当时无凡材,百中皆用壮。粉墨形似间,识者一惆怅。
显然,画马和画鹰就像是一个神奇的魔镜,让杜甫照见了开元时的皇宫。其实玄宗时代的杜甫没有到过皇宫,但他在画马和画鹰的神彩中找到了盛世的符号,他用想象,将这个符号所蕴含的奔放和雄健的时代精神彰显出来,这种精神与他开元年间在《房兵曹胡马》和《画鹰》诗中所抒写的精神是一致的。
与从绘画中所展开的盛世想象相似,夔州风景之美,也让他想到了当年太平时节在长安市集中所见到的山水画,其《夔州歌十绝句》其八云:
忆昔咸阳都市合,山水之图张卖时。巫峡曾经宝屏见,楚宫犹对碧峰疑。
杜甫喜用“咸阳”代指长安,如《壮游》:“快意八九年,西归到咸阳。”此“咸阳都市”即长安都市。这首诗在虚实之间,让人觉得不知是眼前的山水让作者想起了当年的画,还是当年画让作者更欣赏眼前的山水。但夔州山水的神奇和大气之美,还是极好地诠释了盛世艺术的阔大气象。杜甫同时创作的《咏怀古迹五首》其二有:“江山故宅空文藻,云雨荒台岂梦思?最是楚宫俱泯灭,舟人指点到今疑。”这里让人生发的是幻灭感,而《夔州歌》中的这首诗,则借自然山水与画中山水的互喻,既显巫峡风景之壮美,又显当年都市之繁华。作者以夔州山水与当年的山水画相类比,思绪飞扬,想象奇妙,令人回味无穷。
尽管杜甫的宗教信仰在学术界还未有定论,但杜甫诗中写佛和道的情感是真切的。清人杨伦曰:“太白好学仙,乐天专学佛,昌黎仙佛俱不学,子美则学佛兼欲学仙;要亦抑郁无聊,姑发为出世之想而已。”②《杜诗镜铨》,第918页。所以,他有一首《忆昔行》,详细书写了他当年学仙访道的经历,读来“真带仙灵之气”③《杜臆》,第361页。。追忆部分的文字如下:
忆昔北寻小有洞,洪河怒涛过轻舸。辛勤不见华盖君,艮岑青辉惨么麽。千崖无人万壑静,三步回头五步坐。秋山眼冷魂未归,仙赏心违泪交堕。弟子谁依白茅屋,卢老独启青铜锁。巾拂香余捣药尘,阶除灰死烧丹火。玄圃沧洲莽空阔,金节羽衣飘婀娜。落日初霞闪余映,倏忽东西无不可。
和“忆昔开元全盛日”的宏观式表述与“忆昔骊山宫”的想象式表述不一样,杜甫《忆昔行》中所忆写的往事是具体的、亲历的,而且他之所以用自创歌行体来写,亦体现了他对这种感觉的重视。
这段忆昔文字比“忆昔开元全盛日”那一段还长了4 句,是杜甫忆昔性诗句最长的,从描写的细腻与情感的投入来看,一个道教徒的虔诚也许不过如此。李白喜欢写仙景,用想象把仙景描绘得缥缈虚幻,变化无穷。而杜甫则用写实之笔,描写了他当年与李白等到王屋山寻华盖君不遇的往事,情感真诚,意境真实,与李白的游仙诗相映成趣。诗歌最后说:“更讨衡阳董炼师,南浮早鼓潇湘舵。”更点明自己的心愿。赵次公曰:“公在关塞时有《昔游》篇,与今篇大意相应,更相发明,具列于逐段之下。公往寻华盖君而不见,故前篇谓之昔游,今篇谓之忆昔也。”①《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修订本)己帙卷之二,第1354页。细读两诗,赵说值得商榷。《昔游》只是以与高适和李白昔日之游起笔,落笔在揭露天宝年间之弊政,并无求仙访道之愿。而《忆昔行》则以昔日学仙未得起笔,落笔在再往南岳学仙,求仙意图明显。所以说二诗“大意相应,更相发明”,恐不符实。
《忆昔行》的学仙求道之愿应该符合杜甫晚年追求心灵安抚的情感真实,是人到痛苦之极时的精神寄托。这种心理活动杜甫在夔州期间经常出现,他还有一首《寄薛三郎中琚》,也借用“忆昔”一词,表达了自己寻求村野式自在的精神追求:
人生无贤愚,飘飖若埃尘。自非得神仙,谁克免其身。与子俱白头,役役常苦辛。虽为尚书郎,不及村野人。忆昔村野人,其乐难具陈。蔼蔼桑麻交,公侯为等伦。
杜甫谈玄的作品不多,但这首诗开篇4 句把人生之悲说透了;而“村野”之乐的阐释,也把如何在人间获得精神自在的途径说透了。人生的悲与乐,其实在于自我的生活选择,只是很多人明白了其中的道理,却做不出适合自己的选择,也许杜甫就是如此。读到这类诗歌,我们说杜甫与李白在精神上有相通之处,就不是虚谈了。这里的“忆昔”可能不一定指盛唐时代,但那是作者理想的生活状态,是与“役役”人生相对应的精神世界,是一种基于盛世的生活理想。
综上所述,杜甫的“忆昔”心态与“昔我”“我昔”“甫昔”等往事书写有所不同,他用“忆昔”词组所追忆的往事,似乎具有集体记忆的特征,“忆昔”词中的“昔”是一个特定的历史单元,有时是一个值得留恋的时代,有时是一种值得向往的状态。所以他用“忆昔”词组和诗题所创作的诗歌,比较集中地指向了自己求而未得的人生经历。晚年的杜甫,盛世远逝,壮年远逝,只有“忆昔”方可唤起自己生存的希望,给自己的人生增加动力。这就是杜甫在痛苦和失落中“忆昔”的深层心理。
四、杜甫“昔”和“忆昔”的“三朝同写”
杜甫“昔”和“忆昔”诗歌中的往事书写是重现其人生经历的重要形式,但从写作动机上来说,忆“昔”主要是为了写“今”,或讽今,或伤今,所以,晚年的杜甫在用“昔”和“忆昔”书写往事时,常将唐玄宗、唐肃宗、唐代宗三朝同写。杜甫在玄宗朝并未真正入仕,但有政治梦想;在肃宗朝入仕为官,但先疏后贬,并不得志;在代宗朝羁旅蜀楚,流落江湖,但其政治胸怀十分宽广,羁旅漂泊中依然关注时局和民生,颇有屈原之风。所以他的往事追忆也继承了屈原《惜诵》和《抽思》的忆昔手法,打破时空界限,以其现在的处境为基点,将玄、肃、代三朝的所历所思所感融为一种特殊的政治情怀,这就是杜甫晚年多“书怀”“咏怀”“遣怀”等诗的原因。
杜甫“昔”和“忆昔”诗歌中的玄、肃、代“三朝同写”的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自我角色的自塑。作为一个三朝为臣的诗人,杜甫在晚年的三朝同写中是如何描述自我角色的呢?请看他的《夔府书怀四十韵》:
昔罢河西尉,初兴蓟北师。不才名位晚,敢恨省郎迟?扈圣崆峒日,端居滟滪时。萍流仍汲引,樗散尚恩慈。遂阻云台宿,常怀《湛露》诗。翠华森远矣,白首飒凄其。拙被林泉滞,生逢《酒赋》欺。文园终寂寞,汉阁自磷缁。病隔君臣议,惭纡德泽私。扬镳惊主辱,拔剑拨年衰。
作者以“昔”引起往事叙写,描述了一个三朝同境的时空场域。这一段的时间跨度很大,在这个时间段内,杜甫的政治角色各不相同,描述的重点也不一样。“罢河西尉”是玄宗时代,“罢”字很有深意,他在玄宗朝所授的官是右卫率府胄曹参军①杜甫《官定后戏赠(时免河西尉,为右卫率府兵曹)》:“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老夫怕趋走,率府且逍遥。”,但点出“河西尉”,其实是暗写他在玄宗时代求仕之艰难。而“初兴蓟北师”,则引出安史之乱爆发后天下局势的艰难,诚如清浦起龙所云:“首二句,直为全篇引端。以‘河西尉’领遇之穷,以‘蓟北师’领乱之始也。”②《读杜心解》,第766页。所以,他在玄宗朝的角色是国家由盛转衰的见证者。“扈圣崆峒”是肃宗时代。叙肃宗朝的角度十分独特,作者回避了在朝中被疏被贬的叙述,以“端居滟滪时”点明自己的处境,然后回忆自己昔日的朝班经历。他在肃宗朝的角色是朝政的亲历者。“扬镳惊主”是代宗时代。叙代宗时代时,作者以“惊主辱”和“拨年衰”形成对应,抒发自己济时伤己的情怀,这是作者“抒怀”的现实寄托所在。他在代宗朝的角色是王朝中兴的梦想者。杜甫以他的三种角色对应了唐王朝历史中的三个特殊时代,他以“昔”字忆写开篇,将自我的往昔与玄宗、肃宗朝的往昔融为一体,有忆有讽,有悲有盼,息息相关。对杜甫而言,“昔”的忆写已不只是一种写作手法,而是他不同时期不同角色的再确认,“三朝同写”中包含了他在三朝的追求与遗憾。
杜甫“三朝同写”的忆昔形式,寄托了他的政治梦。他的“三朝同写”是以王朝的盛衰变化表现自己的社会思考,所以在“三朝同写”中常带有三朝对比。杜甫进行三朝对比的依据是自己的朝班视角,他在代宗朝时曾除京兆功曹①杜甫《奉寄别马巴州》原注:“时甫除京兆功曹。”仇注系于广德二年(764)。,所以他在《忆昔二首》其二中说“朝廷记识蒙禄秩”。他虽然没有入朝,但还是有强烈的朝班意识。《忆昔二首》就是杜甫以缺席朝臣身份的追忆和感讽,其中玄宗、肃宗、代宗三朝的朝政和治乱形成了鲜明对比。仇兆鳌说此诗“于理乱兴亡之故,反覆痛陈”②《杜诗详注》,第1165页。,所言即此。
《忆昔二首》所忆写的往事,是作者站在朝班视角对肃宗朝和玄宗朝的概括性书写。“忆昔开元全盛日”那一段文字,已成为公认的盛世符号,兹不赘言。其忆写肃宗的一段,亦被王嗣奭誉为“诗史”③《杜臆》,第185页。:
忆昔先皇巡朔方,千乘万骑入咸阳。阴山骄子汗血马,长驱东胡胡走藏。邺城反覆不足怪,关中小儿坏纪纲,张后不乐上为忙。至令今上犹拨乱,劳身焦思补四方。(《忆昔二首》其一)
这段文字有两个突出特点:其一,对“先皇”宏大叙事与生活细节的对比,颂讽分明;其二,斥“关中小儿”的罪恶,背景清晰,控诉力强。有史家之严谨,谏臣之大义。夸张而不失真实,义愤而略带调侃,锋芒犀利,感情悲沉,体现了杜甫对肃宗的态度,从而也与“开元全盛日”形成了对比。
而对比意识最强的应该是“忆昔开元全盛日”之后的现实描写:
岂闻一绢直万钱,有田种谷今流血。洛阳宫殿烧焚尽,宗庙新除狐兔穴。伤心不忍问耆旧,复恐初从乱离说。(《忆昔二首》其二)
这是杜甫最伤心的现实。“岂闻”二字所形成的昔今转折,体现了作者对昔盛今衰的痛惜。浦起龙评曰:“前说开元。‘岂闻’四句,直说目下。中间隔一大段时光,故用‘伤心’二句搭连之。意以其间乱离之事,不忍再提。”④《读杜心解》,第287-288页。的确,作者所设置“不忍问耆旧”这一环节特别耐人回味,“耆旧”应该就是像杜甫一样经历过安史之乱的玄宗旧臣,杜甫虽然未入玄宗朝的朝班,但他对玄宗朝的想象书写,早已将自己置于虚拟朝班之列了,所以他的“伤心”就是作为玄宗旧朝班的痛苦记忆和现实伤感,而本诗的主体结构,恰恰是一个经历盛衰之变的“耆旧”忆昔伤今情感的呈现。
在杜甫“三朝同写”的忆昔书写中,还有一种“三朝类写”的情形。所谓“类写”就是把三朝中相同的社会和政治问题放在一起书写,以寄托深刻的盛衰思考。杜甫晚年,唐王朝面临的最大的社会问题是战乱和赋敛。他在《夔府书怀四十韵》就表达了自己的这种忧虑:“使者分王命,群公各典司。恐乖均赋敛,不似问疮痍。万里烦供给,孤城最怨思。”在《病橘》中,他更是借用“忆昔”的追忆,将代宗朝的战乱与赋敛问题延伸到了玄宗时代,“再征一影子以警醒之”①《读杜心解》,第92页。:
尝闻蓬莱殿,罗列潇湘姿。此物岁不稔,玉食失光辉。寇盗尚凭陵,当君减膳时。汝病是天意,吾愁罪有司。忆昔南海使,奔腾献荔支。百马死山谷,到今耆旧悲。
诗中的“耆旧”,也借指像他一样的玄宗旧臣。“尝闻”是想象之词,描写目下宫中享橘的情形。而他借如今“贡橘”和当初“献荔支”相类比,意在揭示一种现象:不体恤民众的君王,哪怕是在战乱频仍之时,也不会减少自己对异域风味的奢欲。作者用“忆昔”引起玄宗朝的旧事,与当今代宗朝的乱世形成对应,警告当政者,君王劳民伤财、穷侈极欲,会给国家带来巨大的灾难。这是杜甫晚年一贯的政治理性,其在大历四年所作的《咏怀二首》其一诗中阐发得更加直白:“本朝再树立,未及贞观时。日给在军储,上官督有司。”蒋寅评《病橘》说:“末尾‘忆昔’四句引述天宝进荔枝故事,并不是用作比拟,而是引为佐证,说明某些现象之恶,与世道的盛衰无关,只能归结于君主制和君主德行的厚薄。”②蒋寅:《绝望与觉悟的隐喻——杜甫一组咏枯病树诗论析》,《文史哲》2020年第4期,第92页。可备一说。《杜臆》引谭元春评“吾愁罪有司”云:“念头非为有司也,恐有司又罪及百姓耳。”③《杜臆》,第137页。此说似更可取。可见,经历了盛衰之变的杜甫,在君王与治乱的关系上,认识还是很深刻的,这也是他“三朝类写”的动机。
杜甫忆昔书写中的“三朝同写”,是其政治生涯的自然回味,往昔与今日,相反也罢,相类也罢,都体现了他“伤乱思治”④《杜诗镜铨》,第497页。的政治思维,这种思维的终极目标是中兴王朝,而实现王朝中兴的策略,就是资鉴贞观政治,诚如其在《夔府书怀四十韵》所云:
议堂犹集凤,贞观是元龟。
“贞观”是杜甫最高的政治理想。安史之乱初,他途经昭陵时写道:“文物多师古,朝廷半老儒。直词宁戮辱,贤路不崎岖。”(《行次昭陵》)晚年,他在《往在》中写道:“中兴似国初,继体如太宗。端拱纳谏诤,和风日冲融。赤墀樱桃枝,隐映银丝笼。千春荐陵寝,永永垂无穷。京都不再火,泾渭开愁容。”这是多么美好的梦境啊!
忆昔书写是杜甫怀旧伤时的重要表现手法,“忆昔”,不止是情感之源,更是政治评判的手段。“昔”和“忆昔”诗歌的“三朝同写”体现了杜甫内心的盛衰忧思,也许只有借助忆昔的情感推动,杜甫才能将自己的现实关怀更痛快淋漓地抒发出来,自己的往昔、王朝的往昔也都在这“三朝同写”的艺术空间里碰撞,并构成了他沉郁伤感的抒情特质和深广宽厚的社会情怀。
五、余论
如上所述,杜甫的“忆昔”诗句和诗题,把古代的往昔书写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境界,这是杜甫往事书写在主题和艺术上的重大突破。正因为如此,中晚唐诗人在忆开元旧事时,“忆昔开元”近乎相对固定词组,如鲍溶《温泉宫》“忆昔开元天地平,武皇十月幸华清”①〔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四百八十六,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5519页。,温庭筠《过华清宫二十二韵》“忆昔开元日,承平事胜游”②刘学锴撰:《温庭筠全集校注》卷六,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585页。,羊士谔《乱后曲江》“忆昔争游曲水滨”③《全唐诗》卷三百三十二,第3712页。,薛逢《金城宫》“忆昔明皇初御天”④《全唐诗》卷五百四十八,第6326页。等等。当然,杜甫有“忆昔”诗句的作品,还有两首未涉及开元时期的重大题材,其一是《别李义》,诗中有:“忆昔初见时,小襦绣芳荪。”其二是《八哀诗》之《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诗中有:“忆昔李公存,词林有根柢。”这种现象说明杜甫的“忆昔”书写具有唐人“忆昔”的共性,同时,更反衬了杜甫以“忆昔”诗句或诗题书写重大题材的文学追求,更体现了其“忆昔”诗的文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