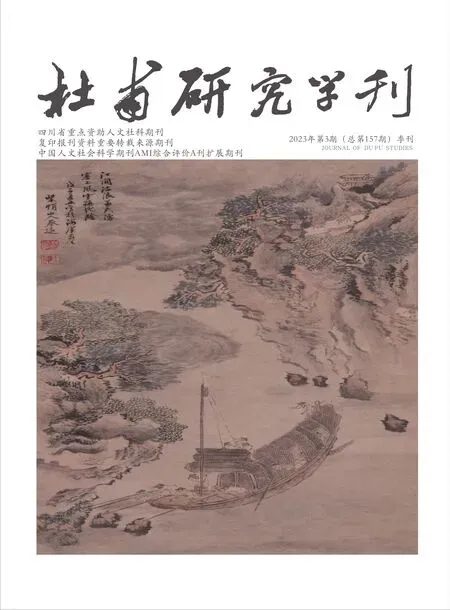“集大成”作为诗歌创作理论的建构
——宋诗话的杜诗接受
黄爱平
宋代诗坛经过初期的摇摆震荡和删汰抉择,北宋中叶最终确定杜甫为一代宗师①本文所言宋诗话主要包括郭绍虞先生《宋诗话考》所载现流传的42部及部分流传的如《蔡宽夫诗话》《王直方诗话》,他人辑录的《东坡诗话》《侯鲭诗话》《童蒙诗训》等近50部诗话,同时参考了《宋诗话辑佚》。笔者据此统计并删去重复,宋诗话论杜甫1055 则,韩愈543则,李白420则,柳宗元175则,白居易164则,元稹124则,韦应物、刘禹锡超出100则,王维、孟浩然、李贺、孟郊、李商隐、杜牧等约50则以上100则以内,其他诗人譬如王勃等初唐诗人均50则以下。这个数据既说明宋人对唐代诗人的整体关照性,也表明杜诗是宋代诗坛关注的焦点。后文提到的宋诗话,没有特别注明的,即以此为范围。。宋人在研习追摹杜诗的过程中,“集大成”是其关注重点。
杜诗“集大成”观念源自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其言:“上薄《风》《雅》,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昔人之所独专矣。”①〔宋〕计有功撰,王仲镛校笺:《唐诗纪事校笺》,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467页。其对杜诗风格、体式包容古今的特点进行了生动描述,突出了杜诗的伟大成就。其后宋祁、秦观皆本元稹之说,只是秦观还指出杜诗之所以能融汇万状在于“适当其时”②〔宋〕秦观撰,徐培均笺注:《淮海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751页。。明确用“集大成”评价杜诗的是苏轼,他说:“子美之诗,退之之文,鲁公之书,皆集大成者也。”③〔宋〕陈师道:《后山诗话》,〔清〕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上册,第304页。此后,“集大成”成为宋诗话对杜诗艺术的主要评价。
但是为什么宋诗话集中于杜诗“集大成”而不是“沉郁顿挫”这个特质?“沉郁顿挫”最早出现于杜甫《进雕赋表》④“臣之述作,虽不足以鼓吹六经,先鸣数子,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而扬雄、枚皋之流,庶可跂及也。”参见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6271页。,宋元之后逐渐成为杜甫诗歌风格的典型概括,但宋诗话罕见论列。现代学者对“集大成”的研究则从“集大成”概念出发,追源溯流,探讨“集大成”在哲学、文学、美学等方面的内涵、产生背景及其诗学影响等等⑤关于“集大成”的研究,主要有以下论文:程千帆、莫砺锋:《杜诗集大成说》,《文学评论》1986年第6期;马承五:《诗圣诗史集大成——杜诗批评学中之誉称述评》,《杜甫研究学刊》1997年第3期;韩经太:《宋诗学阐释与唐诗艺术精神》,《文学遗产》2011年第2期(其中一节主要讨论“集大成”艺术哲学底蕴);林继中:《论杜甫“集大成”的情感本体》,《福州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杨胜宽:《杜诗“集大成”义解》,《杜甫研究学刊》2014年第3期。涉及到“集大成”的杜诗研究专著,如莫砺锋《杜甫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梁桂芳《杜甫与宋代文化》(山东大学2005年博士学位论文)、李新《宋代杜诗艺术批评研究》(河北大学2011年博士学位论文)等。,极少讨论“集大成”对宋诗人创作的影响。本文从读者接受角度出发,试图探讨宋诗话中“集大成”作为诗歌创作理论的诗学背景,描述宋诗话杜诗接受的具体细节,展现诗歌创作理论与时代风气、创作实践之间细致的互动过程,由此讨论“集大成”用来指导创作的可行性、可操作性及其局限性。
一、集大成与创作焦虑
“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面对唐代诗歌经典,宋诗人陷入集体焦虑之中,创新成为他们的首要课题。王荆公言:“世间好语言,已被老杜道尽;世间俗言语,已被乐天道尽。”①〔宋〕胡仔编撰,廖德明校点:《苕溪渔隐丛话》前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年版,第90页。《扪虱新话》曰:“世间所有好句,古人皆已道之。”②〔宋〕陈善:《扪虱新话》卷九“韩文杜诗用字有来处”条,毛氏汲古阁校订本,第2a页。《诗人玉屑》言:“唐杜工部,如周公制作,后世莫能拟议。”③〔宋〕魏庆之辑录,王仲闻点校:《诗人玉屑》,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5-26页。在似乎无可创新的情况下,黄庭坚说:“文章最忌随人后”④〔宋〕黄庭坚:《赠谢敞王博喻》,刘琳、李勇先、王蓉贵校点:《黄庭坚全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04页。,“随人作计终后人。”⑤〔宋〕黄庭坚:《以右军书数种赠丘十四》,《黄庭坚全集》,第1249页。《苕溪渔隐丛话》云:“文章必自名一家,然后可以传不朽;若体规画圆,准方作矩,终为人之臣仆。”⑥《苕溪渔隐丛话》前集,第333页。这就是明知创新难,偏向难中行,也是宋代诗人追求独创性、以此建立诗坛地位的心声。但是正如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所言,任何一个诗人想树立自己的诗人地位,首先必须选择一位师法对象一样,唯恐被唐诗的光华掩盖,在勘比斟酌中,宋代诗人集体选择杜甫作为师法对象。
但是,杜诗又并不是宋诗人唯一的取法渊源。在宋诗人中最能发扬杜诗的黄庭坚,其《黔南十绝》中7篇是点化白居易诗歌而作⑦〔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一,《历代诗话》,下册,第489-490页。;他也推尊李白,认为“李白歌诗,度越六代,与汉魏乐府争衡”⑧〔宋〕蔡振孙:《诗林广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2页。。所以黄庭坚虽然学杜甫,但是不废他人。东坡、王安石也同样如此。“东坡常教学者,但熟读《毛诗·国风》与《离骚》,曲折尽在是矣。”⑨《扪虱新话》卷六“苏黄文妙一世”条,第3b页。东坡早年学李、杜,晚年在惠州尽和渊明诗⑩〔宋〕惠洪:《冷斋诗话》,吴文治主编:《宋诗话全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年版,第2453-2454页。。其创作可谓“胸有洪炉,金银铅锡,皆归镕铸”⑪〔清〕沈德潜:《说诗晬语》,〔清〕王夫之等撰:《清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544页。。王安石则“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⑫〔宋〕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中,《历代诗话》,上册,第419页。。朱熹也说:“须先识得古今体制,雅俗向背,仍更洗涤得尽胃肠间夙生荤血脂膏”⑬〔宋〕罗大经撰,王瑞来点校:《鹤林玉露》甲编卷六“朱文公论诗”条,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13页。。吴可《藏海诗话》倡导:“看诗且以数家为率,以杜为正经,余为兼经也。……如贯穿出入诸家之诗,与诸体俱化,便自成一家,而诸体俱备。若只守一家,则无变态,虽千百首,皆只一体耳。”⑭〔宋〕吴可:《藏海诗话》,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33页。这都是说要广博学习才能融会创新的意思。严羽言:“博取盛唐名家,酝酿胸中,久之自然悟入。”①〔宋〕严羽著,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其“悟”即指“作者在创作上下过功夫后所得到的洞晓诗歌创作诀窍的认识”②王运熙:《中国古代文论管窥》(增补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51页。。而妙悟的前提即是“博取”。宋人这种广博取法的眼光当然有时代基础,如宋代书籍印刷的发展,为知识的广泛传播打下基础;另外科举竞争也激发学子寒窗苦读,造就了宋代人以博学相尚的时代风气③《宋代诗学通论》,第143-144页。。而杜诗“集大成”在杜诗的众多特点中被拈出来,除了上述背景,还在于宋诗创作主体是文人学士,具备接触文献典籍的条件;也在于杜诗是诗歌创作积累至唐代而辉煌的典型代表,其“兼取众妙”的特点使宋诗人取法杜诗而有所得成为可能。
在这样的背景下,再来读苏轼这段有名的评论:
予尝论书,以谓钟、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而钟、王之法益微。至于诗亦然。苏、李之天成,曹、刘之自得,陶、谢之超然,盖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然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李、杜之后,诗人继作,虽间有远韵,而才不逮意,独韦应物、柳宗元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非余子所及也。唐末司空图,崎岖兵乱之间,而诗文高雅,犹有承平之遗风。其诗论曰:“梅止于酸,盐止于咸。”饮食不可无盐、梅,而其美常在咸、酸之外。盖自列其诗之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韵,恨当时不识其妙,予三复其言而悲之。④〔宋〕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2019 年版,第2124-2125页。
一般认为这是苏轼对韦、柳的发明⑤“前人论诗,初不知有韦苏州、柳子厚,论字亦不知有杨凝式。二者至东坡而后发此秘,遂以韦、柳配渊明,凝式配颜鲁公,东坡真有德于三子也。”(〔宋〕曾季狸《艇斋诗话》,《历代诗话续编》,上册,第292页),是对“简古”“澹泊”之风的提倡,对诗歌“远韵”的追求,对李、杜凌跨百代后“高风绝尘”、古意流失的叹惋。笔者认为这也是苏轼在广泛研习有宋之前诗歌、艺术基础上对“集大成”的再思考。颜、柳作为书法界的集大成者,极尽书法之变,融会古今笔法并尽力发扬,成为后代取法的宗师,但是钟繇、王羲之所具有的“笔法”之外的“萧散简远”之意渐渐式微了。李、杜卓绝千古,让所有古今诗人黯然失色,但是魏晋以来“高风绝尘”的古意与超绝世俗的意味渐渐没有了。无论颜、柳还是李、杜,他们的“集大成”都具有金声玉振、卓响天际的成就,并能垂范后世,然而他们的“集大成”却不再有魏晋以来那种高古风貌。那么,苏轼是否定他们“集大成”的意义吗?也不是,他只是认为颜、柳、李、杜的“集大成”也有缺憾①当然苏轼还是非常推崇他们的,如:“颜鲁公书雄秀独出,一变古法,如杜子美诗,格力天纵,奄有汉、魏、晋、宋以来风流,后之作者,殆难复措手。”(苏轼:《书唐氏六家书后》,《苏轼文集》,第2206页)“故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苏轼:《书吴道子画后》,《苏轼文集》,第2210页)“尝评鲁公书与杜子美诗相似,一出之后,前人皆废。”(苏轼:《记潘延之评予书》,《苏轼文集》,第2189页)。李、杜的缺憾,对于其他诗人,也就是机会。就诗歌而言,李、杜之后挺特出众的诗人是韦、柳,因为韦、柳“发纤浓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的风格承接了魏晋以来的那种高风远韵;司空图提倡要有“美在酸咸之外”的诗歌韵味,这使其诗在经历兵乱动荡后还能保有高雅承平之风,也是非常难得的。苏轼在这里把李、杜的“集大成”与韦、柳的简古澹泊并列讨论,有两重意味:一是指出韦、柳是李、杜之后具有创造力的诗人,“才逮其意”,创造了不同于李杜“集大成”之外的另一种风貌;二是韦、柳之风与“集大成”二者并非非此即彼,而是可以并存的。也就是说,李、杜的“集大成”并非无所不备,无所不包。如何来解释这个矛盾?就李、杜的“集大成”来说,他们自身具有圆满自足、和谐统一的特性,但是放在更宽广的历史角度来看,李、杜的“集大成”也只是“集大成”长河中的某个“集大成”。所以“集大成”是一个“适时”的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它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这与苏轼对人生短暂与时空永恒矛盾的破解一样,具有学理上的一致性,如“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②〔宋〕苏轼:《赤壁赋》,《苏轼文集》,第6页。。站在变的角度,天地不能止于一瞬;站在不变的角度,人生的永恒与无尽也是可能的。苏轼也从哲学角度谈“变”与“定”的问题:“夫刚柔相推而变化生,变化生而吉凶之理无定。不知变化而一之,以为无定而两之,此二者皆过也。天下之理未尝不一,而一不可执。知其未尝不一而莫之执,则几矣。”③参见《苏氏易传》解《周易·系辞传上》“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刚柔者,昼夜之象也”条,此则材料转引于韩经太《宋诗学阐释与唐诗艺术精神》,《文学遗产》2011年第2期。对于万事万物,没有看到变化,认为都是一样的,或者只看到变化而不知道他们的统一性、确定性,这都是不全面的;天下的道理也一样,有一个统一的理在,但是我们不能执着于这个统一的理,只有明了这个统一的内在道理但是又不是执着或者固执的理解,则可以达到对“变”的理解。这种思想移之“集大成”也成理,即任何一个“集大成”的个体,包括李、杜,都具有自身的和谐完备之处,但是在诗歌发展流变之中,这些“集大成”个体也不是无所不备的,会有新的“集大成”个体出现,这样的诗歌史才充满了突破和无限创造的可能。对于宋代诗人来说,这种观念是他们在唐诗的高峰面前不用止步叹息,而是继续向前、创造出新的“集大成”的理论前提。这种解读正如伽达默尔所说的“每一时代都必须按照它自己的方式来理解历史传承下来的文本”①[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著,洪汉鼎译:《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419页。一样,苏轼对杜诗“集大成”的解读也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做出的解释,即蕴含希望自己的创作能够成为新的“集大成”的意味或者就是开创出新、不落唐人之后。虽然“集大成”是苏轼明确提出的,但是这种思想观念是宋人都有的,只是苏轼做了总结提炼而已。
“集大成”以其广学博取、镕铸会通、在继承中推陈出新的创作精神让宋代诗人继承下来。宋诗也在唐诗之后走出了自己的创新道路,成为与唐音相并的宋调,影响后世。宋代开明通达之人已称苏黄为“集大成”,如“余尝谓开元之李、杜,元祐之苏、黄,皆集诗之大成者”②《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序,第1页。。当然对于宋诗的新风格,也有人从“本色”角度提出批评,比如说“唐文人皆能诗,柳尤高,韩尚非本色。迨本朝,则文人多,诗人少,三百年间,虽人各有集,集各有诗,诗各自为体,或尚理致,或负才力,或逞辨博,要皆文之有韵者尔,非古人之诗也”③〔宋〕范晞文:《对床夜语》卷二,《历代诗话续编》,上册,第416页。。主要批评宋诗缺乏韵味。但是反观其言则可见宋诗已自成一种风格,就是“尚理致”“负才力”“逞辨博”,清人④如沈德潜云:“元遗山云:‘只知诗到苏黄尽,沧海横流却是谁?’嫌其有破坏唐体之意,然正不必以唐人律之。”(沈德潜《说诗晬语》,《清诗话》,第544页)以及今人缪钺先生、钱锺书先生都认为这就是宋诗的姿态,别有特色,不可以唐诗绳之。另外,也可见宋诗创作数量之多,而巨大的创作数量⑤参见[日]吉川幸次郎著,郑清茂译:《宋诗概说》(第三版)序章第二节“诗在宋文学的地位”,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6-7页。该节比较了唐宋诗创作的诗人数量及作品数量,宋诗数量很大。,正是宋诗取得成就的一个有力保证,也是宋诗取得成就的表现。
综上所述,宋人拈出杜诗的“集大成”特点,在于其代表了一种广博取法、山包海涵、融会万状、变创出新的诗歌创作精神,所以宋人宗杜又不局限于杜,终能变创出新,自成一格。同时,“集大成”作为诗歌创作发展过程中的生产系统,是开放的、推陈出新的,使宋代诗人在唐诗的高峰面前开辟新境具有了理论前提,即宋诗也有可能成为整个诗歌史的卓越代表,宋诗人的创作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
二、集大成是“再写”与“个性建立”的结合
那么“集大成”如何处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从文本继承角度而言,“文学是在它与世界的关系中写成,但更是在它同自己、同自己的历史的关系中写成的。文学的历史是文学作品自始至终不断产生的一段悠远历程”①[法]蒂费纳·萨莫瓦约著,邵炜译:《互文性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引言第1页。。所以文学作品“在原则上有意识地互相孕育,互相滋养,互相影响;同时又从来不是单纯而又简单的相互复制或全盘接受”②《互文性研究》,引言第1页。。从这个角度讲,“集大成”的杜诗即是在前人“写”的基础上的“再写”,但同时又逐步形成作者的独立品格,建立个性。
饱读诗书的宋诗人是杜诗的用心读者,他们在杜诗的字里行间敏锐地捕捉到“前人”无处不在的影响,看出杜诗所用的词汇语言被传递和转换的途径,所以他们感叹杜诗“无一字无来处”③〔宋〕黄庭坚《答洪驹父书》:“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黄庭坚全集》,第475页。),“好言语都被其道尽”。宋人由此对杜诗用语渊源做了非常细致深入的研究④参见李新《宋代杜诗艺术批评研究》第七章《宋人杜诗艺术渊源论》、黄爱平《宋诗话与唐诗学》第四章《宋诗话中的唐诗学诗法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他们发现杜诗用语出经入史,摘《诗》取赋,雅俗并承,古今并用,一切皆可为己驱使。本节立论即从诗歌是语言的艺术着眼,从关注语言这“一斑”来窥探诗人在用语来源方面的继承与创新。下文只是举一例百,从不同用语来源考察宋人从中窥探出的杜诗如何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表现出独特的那个“自己”。
(一)杜诗用语来自经书。“子美多用经书语,如曰:‘车辚辚,马萧萧’,未尝外入一字。……皆浑然严重。如入天陛赤墀,植璧鸣玉,法度森严。然后人不敢用者,岂所造语肤浅不类耶”⑤《诗人玉屑》,第439页。。“车辚辚,马萧萧”是《兵车行》首联,解诗者认为“车辚辚”来自《诗经·秦风·车邻》首句“有车邻邻”。“邻邻”即“辚辚”,指车轮声,《诗经》这首诗写贵族或诸侯相见,先从车声写起,写出驾车奔驰之状。“马萧萧”来自《诗经·小雅·车攻》“萧萧马鸣”,“萧萧”指马鸣声,《诗经》这首写诸侯田猎归来马儿欢鸣场景。杜甫用《诗经》语写出征兵之际一派车鸣马啸的离乱景象,场景很悲壮,与后文写征兵之苦、民不聊生之景完全贴合。“车辚辚,马萧萧”作为《兵车行》的首句,可以说杜甫是在直接描写当时的情形,但是解诗者认为其来自《诗经》,因此增加了诗歌庄重谨严之感,这是读者将自己的阅读经历添加到文本解读之中,但是其说也成立,毕竟杜甫是饱学之士,随手引用《诗经》也是可能的。杜甫借用《诗经》描绘车马欢愉之声的词汇,描写了战乱之中的悲壮离别,改变了词汇运用语境,但与诗歌主题浑然相融。正是这样的解读,让后来者看到《兵车行》对《诗经》语言的创新应用,领悟文学创作可以这样延续与变创。
(二)杜诗用语来自六朝诗歌。《东观余论》云:“何逊集中若‘团团月隐洲’,‘轻燕逐飞花’,‘绕岸平沙合,连山远雾浮’,‘岸花临水发,江燕绕樯飞’,‘游鱼上急濑’,‘薄云岩际宿’等语,子美皆采为己句,但小异耳;故曰‘能诗何水曹’,信非虚赏。”①《苕溪渔隐丛话》后集,第9-10页。何逊“岸花临水发,江燕绕樯飞”,老杜作“岸花飞送客,樯燕语留人”;何逊“薄云岩际宿,初月波中上”,老杜作“薄云岩际宿,孤月浪中翻”,取景造语确实极其相似。何逊这些诗本身境界清远、情景相生,而且对仗工整,音韵和谐,非常接近近体诗,但老杜袭用而有变化。“岸花临水发,江燕绕樯飞”出自何逊《赠诸旧游诗》,整首诗充满感怀和迟暮无奈之感,这两句写出江岸之花在水边自开自放,江上燕子绕着船桅飞舞的自然之态,虽然有“发”和“飞”这两个动词,但是蕴藏的情感却是静态的,是“春物自芳菲”,我又奈何!“岸花飞送客,樯燕语留人”出自杜甫《发潭州》第二联,写离别潭州时所见的景物:岸上飞舞的落花似乎是在为诗人送行,船桅上春燕呢喃,似乎在亲切地挽留,诗人却仍然漂泊无依,一股浓重的落寞伤感之情溢于言表;飞花、语燕写得越动人,诗人的哀感越深沉,可谓“一切景语皆情语”。所以杜诗虽然承袭了何诗的词汇和情景,但是表达的情感要浓烈得多。要表达浓烈的情感,杜诗对何诗进行了增容,即增加诗歌的容量。“岸花临水发”,只写一物“花”,“岸花飞送客”,写了两物“花”与“客”;“江燕绕樯飞”,也只写一物“燕”,“樯燕语留人”写了两物“燕”与“人”。另外,杜诗增加了动词,何诗每句只一个动词,即“发”与“飞”,“临水”、“绕樯”是状语,是来修饰“发”与“飞”的;杜诗每句有两个动词,岸花“飞”是来“送”客的,樯燕“语”是来“留”人的,这样杜诗每句都有主客交流,情感自然也变得丰富起来。因此,看似与前人相同的词语与情景,杜甫却自有变创,让诗意更饱满。
(三)杜诗用语来自民间。一般认为方言俗语入诗,会让诗歌显得粗俗,但是用得好则另当别论。如“数物以个,谓食为吃,甚近鄙俗,独杜屡用。‘峡口惊猿闻一个’,‘两个黄鹂鸣翠柳’,‘却绕井栏添个个’;《送李校书》云‘临岐意颇切,对酒不能吃’,‘楼头吃酒楼下卧’,‘但使残年饱吃饭’,‘梅熟许同朱老吃’。盖篇中大概奇特可以映带者也”②〔宋〕黄彻:《䂬溪诗话》卷七,《历代诗话续编》,上册,第379页。。“峡口惊猿闻一个”来自七古《夜归》,全诗用语口语化,写夜深归来,家人已眠,只见北斗沉江、明星当空,回到家,庭前两只明烛,似乎给人安慰,然而听到峡口惊猿的啼声,不多,只有一声两声,并不连续,用“一个”来形容,更见猿啼的突兀,衬出夜晚的寂静。如此寂静深沉的夜晚,诗人晚归,惊听猿啼,内心颇不宁静;紧接着写“白头老罢舞复歌,杖藜不睡谁能那”,头白老去,无可奈何,且歌且舞,夜不成眠,“谁能那”也是俗语,且用反问句式,以故作豪壮之语加重无可奈何之意。所以此诗虽然用俗语,但是篇章奇特,前后有呼应,浑成一体。“两个黄鹂鸣翠柳”也有此妙,写景如画、声形毕现,让人根本不觉其用了俗语。阮阅说:“句法欲老健有英气,当间用方言为妙。奇男子行人群中,自然有颖脱不可干犯之韵。”①〔宋〕阮阅编,周本淳校点:《诗话总龟》前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8页。就是用俗语而奇的意思。张戒评老杜用俗语:“世徒见子美诗多粗俗,不知粗俗语在诗句中最难,非粗俗,乃高古之极也。自曹、刘死至今一千年,惟子美一人能之。”②〔宋〕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历代诗话续编》,上册,第450-451页。子美诗粗俗中有高古,这是众人不及处,原因在于老杜作诗是从胸臆中流出,并非有意于语言工拙。宋人从杜诗对俗语的化用中看到杜甫对语言的强大表现力,用对比鲜明的词汇“粗俗”“鄙俗”与“高古”“奇特”来描述这种语言张力;同时也展现了宋人作为博学的读者对杜诗的玩味,从中体现出对语言的过人敏感。
宋人对杜诗用语渊源的着力探讨,既是从读者角度,也是从创作者的角度着眼的。就杜甫来说,他前面也有高峰,《诗》《骚》传统、汉魏古诗、子建、渊明等,都不易超越。详读杜诗,宋人发现无处不在的古人身影,悟到杜诗就是在前人“写”的基础上的“再写”,立足于已有的基础,着力创造;但杜诗“无一字无来处”的地方,都在有意无意地避免与前人重复或者重蹈前人窠臼,就像普鲁斯特谈自己对前人进行仿作时说到的在模仿的过程中进行了“净化”:“对我来说……应该从一味模仿和偶像崇拜的天然病毒中净化出来。与其不露声色地仿效米歇雷(Michelet)或龚古尔(这里还可以写上我们整个时代最受欢迎的任何名字),然后签上自己的大名,还不如索性堂而皇之地仿作,而后等到我回头写自己的小说时,我便仅只是马塞尔·普鲁斯特了。”③《互文性研究》,第45页。杜甫虽不是模仿写小说,但是道理是一样的,他也在不断学习前人,但创作时就“只是杜甫”了,也就是元稹、秦观等人所说的在兼容并包中与古为化,镕铸出新,不只是前人的简单集合,而是在汲取过程中发生了化学反应,成为了“杜甫”。所以作为读者,尽管无比哀怨地看到前人“尽言矣”,但是同样可以看到一个作者仍然可以是与众不同的④《互文性研究》,第69页。。尽管前人“尽言矣”,但是“我以己言言之”,作者可以通过一种新的排列或者未曾有过的表达称其为话题的“所有者”⑤《互文性研究》,第60页。,避开重复、抄袭之名,披上创造的新装。从这个角度来审视继承杜诗的宗主黄庭坚提出的“点铁成金”“脱胎换骨”,我们则可以明白为何在宋代恰恰是黄庭坚扛起了杜诗传承的大旗,并且振臂一挥,应者如云;也可以明白正是“集大成”蕴含着镕铸前人而自出新意,给了宋人更大的信心。
三、集大成的文本创新与对创作天才的忽略
前文主要从语源角度论述杜诗在“无一字无来处”中表现出的语用创新,但是这种创新的底子仍然是继承,即要有学问,要对前代经典烂熟于心。如果杜诗仅仅只是有这方面的成就,还不足以被宋人称为“集大成”,宋诗话还非常关注杜诗中其他具有鲜明特点的创新之处,比如杜诗炼字、格律等方面的创新,以及他对传统体裁、风格的融会及变创。
诗歌是语言的艺术,宋诗话尤其强调炼字,自然极关注杜诗用字方面的因难出新。如云“虚活字极难下,虚死字尤不易,盖虽是死字,欲使之活,此所以为难。老杜‘古墙犹竹色,虚阁自松声’及‘江山有巴蜀,栋宇自齐梁’,人到于今诵之。予近读其《瞿塘两崖》诗云:‘入天犹石色,穿水忽云根。’‘犹’、‘忽’二字如浮云著风,闪烁无定,谁能迹其妙处。他如‘江山且相见,戎马未安居’,‘故国犹兵马,他乡亦鼓鼙’,‘地偏初衣袷,山拥更登危’,‘诗书遂墙壁,奴仆且旌旄’,皆用力于一字”①《对床夜语》卷二,《历代诗话续编》,上册,第418页。。所举诗中“犹”“自”“忽”“且”“亦”“更”等,皆是“虚死字”,相当于现代汉语的虚词,因为这些虚词本身没有什么“生命力”,即不能直接描景、状态、传情,所以称为“死”字,但是用得好能极好地辅助摹物象形,增添著物之妙,使诗歌显得更加灵动。如“入天犹石色,穿水忽云根”,来自《瞿塘两崖》第二联,整首诗主要写瞿塘两崖山高水险,四联都在反复摹写这一主题,但是最精绝、最生动还是这一联:前句写石崖高入云天,仰望天表,“犹”见两崖之石色,“犹”写出了石崖与青天同色,更显得石崖之高与天齐;后句中“云根”即指石崖,古人认为云多起于高山悬崖之间,故称之为云根,此句写俯视江水,只见两崖倒影入江,犹如倚天双剑穿入江心,与白云之倒影相叠,形成云生于崖之倒影,故这“忽”字,写出诗人一抬头一低头之间,处处都是山高水险,满眼都是崖高水深,两崖雄奇险峻之气势就出来了,全联因之而飞动腾跃。叶梦得分析了另外两联:“诗人以一字为工,世固知之,惟老杜变化开阖,出奇无穷,殆不可以形迹捕。如‘江山有巴蜀,栋宇自齐梁’,远近数千里,上下数百年,只在‘有’与‘自’两字间,而吞纳山川之气,俯仰古今之怀,皆见于言外。《滕王亭子》‘粉墙犹竹色,虚阁自松声’,若不用‘犹’与‘自’两字,则余八言凡亭子皆可用,不必滕王也。此皆工妙至到,人力不可及,而此老独雍容闲肆,出于自然,略不见其用力处。今人多取其已用字模放用之,偃蹇狭陋,尽成死法。不知意与境会,言中其节,凡字皆可用也。”②〔宋〕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中,《历代诗话》,上册,第420-421页。老杜这些虚字之妙,实在是意与境会,信手拈来,并不是求文字之奇,所以出于自然,又能开阖变化,叶梦得借此给当时学习者建议:学习不要只是借用这些字,而是要使字与整首诗意、诗境结合。
不能说这种表达方式前人从未使用过,但是将其形成一种风格,是老杜的创造。杜诗语言锤炼达到精深处还有很多,无论是一字之妙还是双字之奇,无论是实词还是虚字,杜诗都能随意驱遣,为写景表意造境服务。所以吴沆说:“大抵他人之诗,工拙以篇论;杜甫之诗,工拙以字论。他人之诗,有篇则无对,有对则无句,有句则无字;杜甫之诗,篇中则有对,对中则有句,句中则有字。他人之诗,至十韵二十韵则委靡叛散而不能收拾;杜甫之诗,至二十韵三十韵则气象愈高,波澜愈阔,步骤驰骋愈严愈紧,非有本者,能如是乎?宜乎《唐史》有言:‘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浑涵汪洋,千汇万状,兼古今而有之也。’”①〔宋〕吴沆:《环溪诗话》,《宋诗话全编》,第4册,第4339-4340页。
其次是杜诗格律的变创。杜甫常常打破格律常规而自出新意,创出“拗句”“变体”等等律式,形成一种拗峭、劲健的诗风。如“五言律诗,固要贴妥,然贴妥太过,必流于衰。苟时能出奇,于第三字中下一拗字,则贴妥中隐然有峻直之风。老杜有全篇如此者,试举其一云:‘带甲满天地,胡为君远行?亲朋尽一哭,鞍马去孤城。草木岁月晚,关河霜雪清。别离已昨日,因见古人情。’散句如‘乾坤万里眼,时序百年心’,‘梅花万里外,雪片一冬深’,‘一径野花落,孤村春水生’,‘虫书玉佩藓,燕舞翠帷尘’,‘村春雨外急,邻火夜深明’,‘山县早休市,江桥春聚船’,‘老马夜知道,苍鹰饥著人’,用实字而拗也。‘行色递隐见,人烟时有无’,‘蝉声集古寺,鸟影度寒塘’,‘檐雨乱淋幔,山云低度墙’,‘飞星过水白,落月动沙虚’,用虚字而拗也。其他变态不一,却在临时斡旋之何如耳”②《对床夜语》卷二,《历代诗话续编》,第418页。所举诗例“村春雨外急”的“春”经杨明师提醒应该是“舂”,所引版本有错误。。之所以要变格,是因为格律用得烂熟,诗歌声律太妥帖则因久成俗,诗歌的生命也就衰落了。上文所引的那首完整的诗即《送远》,该诗奇数句即出句第三字“满”“尽”“岁”“已”本应平声,但均用仄声字,偶数句即对句除“君”“霜”两字,其他也为仄声;“草木岁月晚,关河霜雪清”,“岁月”本该都用平,出于内容的考虑,此两字全用仄,此句全是仄,整首诗读来确有“峻直之风”。宋诗话大量分析了杜诗的“拗字”“拗句”“失粘”“拗救”等语例,为宋人追求创新提供借鉴,特别是对黄庭坚、江西诗派在格律、风格等方面的新变有很大影响。
再次是杜诗对乐府的革新。元稹最早注意到这一点:“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有倚傍。余少时与友人白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遂不复拟赋古题。”③《唐诗纪事校笺》,第1554页。《蔡宽夫诗话》说得更具体:“齐梁以来,文士喜为乐府辞,然沿袭之久,往往失其命题本意,《乌将八九子》但咏乌,《雉朝飞》但咏雉,《鸡鸣高树巅》但咏鸡,大抵类此。而甚有并其题失之者,如《相府莲》讹为《想夫怜》,《扬婆儿》讹为《杨叛儿》之类是也。盖辞人例用事,语言不复详研考,虽李白亦不免此。惟老杜《兵车行》、《悲青坂》、《无家别》等数篇,皆因事自出己意立题,略不更蹈前人陈迹,真豪杰也。”④《苕溪渔隐丛话》前集,第5页。乐府在流传过程中,因种种原因失其题意甚至连题目本身也非本来面目,那么所谓尊崇古意则成了一句空话,杜甫索性自出己意立题,不事蹈袭,此举相当大胆、有创见,所以为“真豪杰”。比如《丽人行》从《丽人曲》演化而来,由“曲”变为“行”,篇幅更长,《乐府广题》对《丽人曲》的解题说:“《刘向别录》云:‘昔有丽人善雅歌,后因以明曲。’”①〔宋〕郭茂倩:《乐府诗集》,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976页。此篇《乐府诗集》收在“杂曲歌辞”里。因此《丽人行》原意只是写美人,杜甫《丽人行》前半段表面是写“丽人”,实则是写时事,写出当时杨贵妃姐妹及其兄弟的奢侈荒淫生活和不可一世的气焰,后半段对时事进行描写和评论,结句“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更是直接讽刺,这种主题离此题原意已远。杜甫不拘于乐府古题的限制,继承乐府诗歌的精神实质而自创新辞,在乐府革新过程中直接启发了中唐元白的“新乐府运动”,发扬了乐府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
杜诗善于融会,打通了各种风格,元稹对此早有评论,秦观进一步申说:“杜子美之于诗,实积众家之长,适当其时而已。昔苏武、李陵之诗,长于高妙。曹植、刘公幹之诗,长于豪逸。陶潜、阮籍之诗,长于冲澹。谢灵运、鲍照之诗,长于峻洁。徐陵、庾信之诗,长于藻丽。于是杜子美者,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澹之趣,兼峻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作,所不及焉。”②《淮海集笺注》,第751页。严羽则概说杜诗“宪章汉魏而取材六朝”,“至其自得之妙,则前辈所谓集大成者也”③《沧浪诗话校释》,第171页。。杜诗风格上的融会贯通,汪洋海涵,树立了诗歌史上的最高典范,此点也不断为后世诗论反复论及④如胡应麟说:“盛唐一味秀丽雄浑。杜则精粗、钜细、巧拙、新陈、险易、浅深、浓淡、肥瘦,靡不毕具。”(〔明〕胡应麟:《诗薮》,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70页)虽然胡应麟觉得“参其格调,实与盛唐大别”,但是仍然赞叹“正而能变,变而能化,化而不失本调,不失本调而兼得众调,故绝不可及”。(《诗薮》,第73页)。
无论如何,做出这么多创新,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杜甫的创造力是明显的⑤赵翼认为杜甫是有意与前人较力的:“盖其探源泝流,自《风》、《骚》以及汉、魏、六朝诸才人,无不悉其才力而默相比较,自觉己与白之才,实属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清〕赵翼《瓯北诗话》卷二,郭绍虞编选,富寿荪校点《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版,上册,第1154 页)另外,赵翼不满前人只以“学力”称杜甫,认为杜甫也是有“才”的,因为“思力所到,即其才分所到,有不如是则不快者”。(赵翼《瓯北诗话》卷二,《清诗话续编》,上册,第1151页),但是,这种明显的才华横溢,突出的创作才能,宋人却吝于说出。环溪说:“杜甫长于学,故以字见工;李白长于才,故以篇见工。”⑥《环溪诗话》,《宋诗话全编》,第4343页。李杜各有所长,杜甫学问好,所以炼字炼句,以字见工,学诗者可以从中学其句法、字法;但是李白才气纵横,篇章浑融,不可拆断,要说哪个字好,找不出,只是一气儿的好。朱熹题太白诗后:“李太白天才绝出,尤长于诗。……今人舍命作诗,开口便说李、杜,以此观之,何曾梦见他脚板耶?”①《诗林广记》,第51-52页。朱熹强调李白才气天纵,所以出语便高,今人就是拼了老命作诗,只显得拙劣。所以李白诗歌之妙与他本身的才气分不开,并且他的才气在诗歌中化为无迹可求的形态。但是这种“天才”评论与杜甫无缘。刘克庄评价宋代诗人说:“放翁,学力也,似杜甫;诚斋,天分也,似李白。”②〔宋〕刘克庄著,王秀梅点校:《后村诗话》,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3页。即在他的心目中,杜甫之长在于学力,李白之长在于天分,即天生之才。换言之李白才气是天纵,杜甫乃后天所学得来。再如葛立方论李杜:“杜甫、李白以诗齐名,韩退之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似未易以优劣也。然杜诗思苦而语奇,李诗思疾而语豪。杜集中言李白诗处甚多,如‘李白一斗诗百篇’,如‘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何时一尊酒,重与细论文’之句,似讥其太俊快。李白论杜甫,则曰‘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为问因何太瘦生,只为从来作诗苦。’似讥其太愁肝肾也。”③《韵语阳秋》卷一,《历代诗话》,下册,第486页。葛立方通过对李杜互赠之诗的解读来说明杜诗“思苦而语奇”,白诗“思疾而语豪”的特点,隐含之义也是李白才思迅捷,犹如天纵,杜甫做诗需要花功夫琢磨,精思苦研。其实,李白和杜甫,都有对前代的继承,也都是天才,只是他们的天才表现形式不同,迟速异分而已。因为如果杜甫没有创作才能,只是有学问就成为了“杜甫”,那么宋朝多的是有学问的人,怎么没有都成为“杜甫”呢,但是宋诗话只是反复强调杜甫的学力。
与不关注杜甫的“天才”相关的是,宋诗话更关注杜诗的可法性,如“杜之诗法,韩之文法也。诗文各有体,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故不工尔”④《后山诗话》,《历代诗话》,上册,第303页。。 此条第二句批评了韩、杜诗文均不“得体”,非本色;但第一句“杜之诗法,韩之文法”,就是说杜诗与韩文在法度上有相近之处,就韩愈文章来说,开阖抑扬、波澜壮阔,如长江大河,滔滔不绝,因此杜诗之法也具有汪洋浩瀚的特点,取法不尽。又“学诗当以子美为诗,有规矩故可学”⑤《后山诗话》,《历代诗话》,上册,第304页。。《雪浪斋日记》也说:“欲法度备足,当看杜子美。”⑥《苕溪渔隐丛话》前集,第11页。严羽曰:“少陵诗法如孙吴,太白诗法如李广。少陵如节制之师。”⑦《沧浪诗话校释》,第170页。李广之师,出奇制胜,没有法度可依,而孙吴之师最讲法度,所以少陵诗法似之。他们都认识到杜诗有法度,也就是杜诗的可学性,所以对杜诗进行具体分析时,围绕杜诗篇章结构、用词用字、对偶押韵等做了详细阐发,从而模仿学习。诗话中范例甚多,此处不详举例。
强调杜诗的可法性,可能与杜甫自言“为人性癖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有关,再说杜诗对语言的锤炼讲究也确实堪当楷模;但有意强调杜诗的“功夫”,忽略其天才创造性,原因在于“功夫”才有可学性,而天才是不可学习的。所以,勤奋、注重“功夫”的杜甫就更适合作为取法对象,而注重杜诗的“可法性”则形成了宋人从文本出发对杜诗研读和学习的特点。
简言之,宋人选取杜甫为宗师,在于杜甫与他们推陈出新的需要切合,也与他们尚学、博学的自身特点切合。正如迪贝莱所说,一个作家“必须时时注意自己的天分,设法模仿他觉得与自己最为相近的作者”①[法]J. 迪贝莱(J. Du Bellay),《保护和发扬法语》(La defense et Illustration de la langue française),1549年。转引自《互文性研究》,第122页。。所以宋人对杜诗具体作品的创作分析中,突出了杜诗在用字、格律、体式等外在形式方面的创造性、创新性,重视其诗歌文本中所呈现出来的后天的学问与功夫,强调其可以借鉴学习的一面,但是遮蔽了杜甫的创作天才,在某种程度上也忽略了杜甫表达自我以及诗人自身经历与诗歌创作的互动关系。因此,宋代诗坛以学问为诗的风气,是时代的催化,也是宋诗人的主动选择,这促进了他们对文本演变的关注,间接导致对创作主体本身以及其能动性的忽略。
四、结语
从理论建设角度讲,宋人拈出杜诗“集大成”的特色,使宋诗创新有了理论前提,并通过对杜诗语言的详细分析,揭示了文学如何在自身基础上孕育自己的细致理路:文学是在“写”的基础上的“再写”,但是在“再写”的过程中,作者运用各种变创手法,逐步形成自己的个性特点,由此在文学史上获得独立地位。萨莫瓦约说:“对书籍的记忆、有意识地重复和套用他人的范例,这些仍然是很多文学技法的根本。”②《互文性研究》,第69-70页。这与“集大成”强调对传统的继承意脉相通。也如布托尔(Tutor)所说,在每个作家的身边都围绕着众多存在或不存在、他读过或未读过的其他作家,文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进行拼接,但是作家脑中永远有一块空地,被他正写着的作品明显地填补③参见乔治·佩雷克(Georges Perec)《当代法国小说家的权力和局限》(Pouvoirs et limites du romancier français contemporain),选自《佩雷克浏览》(Parcours Perec),里昂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6页。转引自《互文性研究》,第52-53页。。文学也就是这样在继承中不断开辟着新的未来,“集大成”作为诗歌创作理论的指导意义正在于此。然而,宋人对“集大成”的杜诗,主要从文本角度强调其可法性,关注其变创性,对作家创作主观能动性有一定程度的忽略,认为诗歌创作就是在学问之下的运作,创作天才似乎只表现在“融会”传统的能力之中。这种对作家天才的窄化理解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创作主体的能动性,把创作主体看成了一个封闭于文本知识体系的主体,而不是与现实生活关联的主体,所以也就极少关注创作主体是如何运用从传统中习得的文本创造技能来表达他正在经历的现实处境的。这种创作思想与宋诗尚理致、负才力、逞辨博的风貌是一致的。在这种诗学背景下,江西诗派的出现是必然的,其衰落也是必然的。
综上所述,宋诗话的杜诗接受是精心挑选了角度,选择了方向的,“沉郁顿挫”作为杜诗风貌概述过于个性化,宋诗话不予论列;而以“诗史”评杜诗主要关注诗歌内容,只是影响宋诗的某个具体特征,不具有创作理论指导性。只有当时代风气转换,创作需求发生变化,杜诗的这些特点才会逐渐进入诗学视野。但是“集大成”自从被宋诗话拈出,其创作精神的内核一直有形无形地影响着此后的诗歌创作,并成为中国诗歌创作最具指导性和操作性的创作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