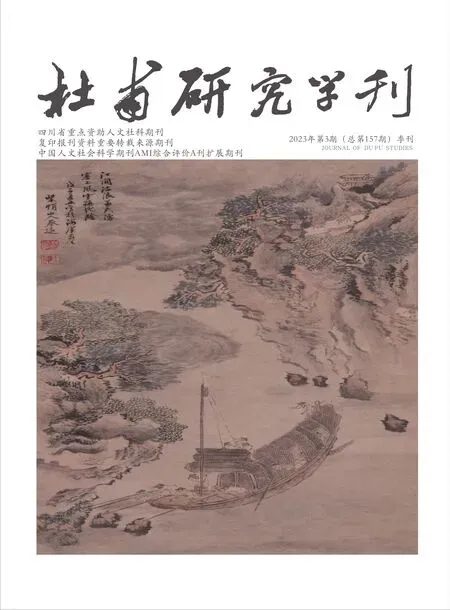京畿空间与中唐吏隐诗学的体系建构
徐贺安
“吏隐”是唐代文人特殊的生活方式与隐逸形态。从“吏”的角度讲是仕宦之风,从“隐”的角度讲是隐逸之风,两者碰撞、融合不仅是仕与隐的叠加,还产生了新型的生活方式、诗歌艺术、诗学思想。关于吏隐主题诗歌的发展定型,国内外学者多有论述①国内学者研究如蒋寅的《大历诗风》(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大历诗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百代之中:中唐的诗歌史意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年版)、《“武功体”与吏隐主题的发展》(《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 年第3 期)、《古典诗歌中的“吏隐”》(《苏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葛晓音《中晚唐的郡斋诗和“沧洲吏”》(《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外国学者研究如[美]宇文所安著,陈引驰、陈磊译《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唐文学文化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美]杨晓山著,文韬译《私人领域的变形:唐宋诗歌中的园林与玩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尤其是蒋寅先生考证出姚合“《武功作》是吏隐主题真正定型的标志”②蒋寅:《百代之中:中唐的诗歌史意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32页。。姚合,“调武功主簿,世号姚武功”③〔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四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49页。。这里的“武功”具有三重含义:地理上的唐代京畿武功县,职官上的武功县主簿,文学上的组诗“武功体”。可见,地理与职官是探究姚合“武功体”、吏隐诗歌发展定型的重要因素。由“武功体”上溯,可以发现活跃在安史之乱前后的钱起、韦应物、白居易、姚合等畿县诗人不约而同地写出数量众多、富有个性的吏隐主题的诗篇。但是,对于以上诗人的创作地域——京兆府畿县①关于唐代京畿研究可参看徐畅:《长安未远:唐代京畿的乡村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版。该书多从历史角度研究唐代京畿社会。,学者却少有细致考论。吏隐主题不仅是特殊的文学题材,还反映了独具个性的文学思潮,从思想史、长时段考察吏隐诗学是以往研究忽略的视角。群体性、地域性恰是文学思想史研究的重点,正如罗宗强先生所云:“文学思想史还要研究文学思想的地域色彩问题。”“活动于同一个地域的作家,往往在创作倾向上相近或相似,如何解释这种现象,文学思想史也必须作出回答。”②罗宗强:《宋代文学思想史·序》,张毅:《宋代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2页。从文学理论的角度,以上诗人并未提出过系统的吏隐诗学理论,但中唐吏隐主题诗歌已然表现出了很多吏隐诗学思想。左东岭先生从文学实践的角度提炼诗学思想的观点,正可弥补中唐吏隐诗学研究的不足:“其实,从作者的题材选取、文体使用、创作格式、审美形态等方面,均能体现作者对于各种文学问题的看法。”③左东岭:《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方法的再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第18页。所以,研究中唐吏隐诗学群体创作心理,考察中唐吏隐诗学的演进过程,才是吏隐心态史研究的应有之义。本文探讨的重点——中唐京畿空间中的吏隐诗学,是唐代京畿诗学与唐代吏隐诗学在特殊环境中融合的产物。就空间而言,中唐京畿吏隐诗学是唐代京畿空间诗学的一部分;就主题而言,中唐京畿吏隐诗学是唐代吏隐诗学、中国古典吏隐诗学的一部分。姚合的“武功体”既是中唐京畿吏隐诗学发展的产物,也是唐代吏隐主题诗歌发展定型的标志。基于此,京畿空间对中唐吏隐诗学建构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下面从三个角度探讨京畿空间与中唐吏隐诗学的双向互动过程:其一,中唐吏隐诗学产生的地理因素与政治因缘;其二,京畿空间视野里的中唐吏隐诗学体系涉及作者的身份特征与仕宦心态,诗人的情感表达与创作心态,诗体、诗题的选择与呈现,审美的具体形态与发展演变④中唐吏隐诗学体系结构内涵丰富,内容多样。本文仅就几个突出的面向展开论述。题目涉及的“建构”并非文学理论性的“建构”,仅是中唐吏隐诗学产生、构成、影响的概括。;其三,中唐京畿吏隐诗学与中唐吏隐诗学之间衍生、转变、发展的关系。
一、中唐京畿吏隐诗学产生的地理因素
《说文解字》释“畿”曰:“天子千里地。以远近言之,则言畿也。”⑤〔汉〕许慎撰,〔宋〕徐铉校定:《说文解字》卷一三下,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91页。畿县指天子所在京城的外围县域,既临近京城又在京城之外。《旧唐书》曰:“凡三都之县,在内曰京县,城外曰畿。”①〔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四三《职官二》,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825页。唐代畿县又分布在三个府内,《旧唐书》曰:“京兆、河南、太原所管诸县,谓之畿县。”②《旧唐书》卷四四《职官三》,第1920页。可知唐代畿县指京兆府、河南府、太原府直接管辖的县。本文主要研究唐代京兆府管辖的蓝田、鄠县、盩厔、武功四县及在四县任职的钱起、韦应物、白居易、姚合四位诗人。由人索地,以地系人,因人论诗,探究诗人在京畿奥壤中孕育出的艺术作品与文学观念。
长安是唐朝的首都,文人墨客为功名多奔走于此。尚颜《赠村公》就用“名利处”评价长安:“也笑长安名利处,红尘半是马蹄翻。”③〔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增订本)卷八四八,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9668页。京畿之地靠近名利场,又因多山水,为士人提供幽栖之所。钱起写蓝田县如同世外桃源,其《初黄绶赴蓝田县作》曰:“居人散山水,即境真桃源。”④〔唐〕钱起著,王定璋校注:《钱起集校注》卷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62页。不仅诗歌,地理类书籍也可参考。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记载:
蓝田县,畿。蓝田山,一名玉山,一名覆车山,在县东二十八里。
鄠县,畿。终南山,在县东南二十里。美陂,在县西五里。周回十四里。
盩厔县,畿。山曲曰盩,水曲曰厔。
武功县,畿。旧县境有武功山。斜谷水亦曰武功水。……是则县本以山水立名也。⑤〔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一《关内道一》,中华书局1983 年版,第16页、第29页、第31页、第32页。
可见,蓝田县有玉山。终南山经过鄠县,县境内有美陂。武功、盩厔都因山水得名。山地对人类文明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认为:“山是一种障碍,同时也是自由人的一个藏身之地。因为文明(社会和政治秩序、货币经济)强加的一切束缚和统治,在山区不再压在人们头上。”⑥[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唐家龙、曾培耿等译,吴模信校:《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7页。同理,山水为京兆畿县营造了幽深之境,也为诗人提供了藏身之地。唐代京畿地处关中,而关中地域广大,“多相当于三辅,有时相当于三秦”⑦李浩:《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9页。。关中文化精神,具有浓郁的地域特点。李浩先生将关中文化精神总结为“雄深雅健”,“雄侧重指雄浑浩大之气,健侧重指刚劲孔武之力”⑧《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第34页。。李浩先生的观点极具纵深讨论的价值:首先,关中是广大的文化区域,雄深雅健只是关中地区宏观的、显性的审美,还应有微型的、隐性的审美;其次,长安“名利处”与畿县“真桃源”形成了对比,长安都市审美与京畿县域文化之间也有差异;最后,京兆府畿县文化有别于“雄深雅健”式的刚性审美,还有清幽闲僻的柔性审美。唐代京畿县域毗邻长安,辖区多山水,特殊的地理与政治区位,成为影响中唐吏隐诗学思想形成的地理因素。
二、中唐京畿吏隐诗学产生的政治原因
畿县诗人既包含畿县籍诗人,又包含在畿县创作的诗人。戴伟华先生曾呼吁,地域文化研究应该“将过去主要以诗人籍贯为主的地域文化与文学创作的分析,转换为以诗歌创作地点为主的地域文化与文学创作的研究”①戴伟华:《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4页。。基于此,探究在畿县任职并在畿县创作的县官诗人,才是中唐吏隐主题诗歌研究的重点。从诗歌数量、艺术价值的角度讲,畿县县官诗人以钱起、韦应物、白居易、姚合较有代表性。具体表现在:钱起②钱起活跃于盛唐向中唐过渡的时期。蒋寅先生将中唐分为“从安史之乱爆发到德宗贞元前期约四十年”与从贞元到长庆时两个时期。参见蒋寅:《百代之中:中唐的诗歌史意义》,第5页。在天宝十三载(754)秋任蓝田尉,广德元年(763)改授章陵令,创作诗歌50余首③〔唐〕钱起撰,王定璋校注:《钱起集校注》,第472-487页。;韦应物大历十三年(778)秋为鄠县令,次年六月离职,创作诗歌20余首④〔唐〕韦应物撰,孙望编著:《韦应物诗集系年校笺》,中华书局2002年版,目录第8-9页。;白居易在元和元年(806)四月至元和二年(807)十一月任盩厔尉,创作诗歌30余首⑤朱金城:《白居易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5-38页。;姚合在元和十五年(820)罢魏博幕职,任武功主簿,长庆三年(823)春罢,创作出《武功县中作三十首一作武功县闲居》⑥陶敏:《姚合年谱》,《唐代文学与文献论集》,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87-288页。。京畿县官诗人的任职地域集中、任职时间衔接连贯、诗歌创作数量众多。天宝末至长庆末,京兆府畿县县官潮汐般地出现,形成了京畿县官诗人创作群体。
从史料和诗歌的互证中,可以发现京畿县官的制度品级与工作状态。《旧唐书》载京兆府县官曰:“京兆、河南、太原所管诸县,谓之畿县。令各一人,正六品下。丞一人,正八品下。主簿一人,正九品上。尉二人,正九品下。”⑦《旧唐书》卷四四《职官三》,第1920页。京畿县令、县主簿同地办公,品级相差甚远。县尉品秩虽低,但前途光明:“赤县和畿县的县尉,由于地处京城大邑,地位最崇高。唐史料也常称京畿县尉为美官,为士人竞求的对象。”⑧赖瑞和:《唐代基层文官》,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07页。“畿县约八十多个,其中又有十多个常出现在史料,最为要紧的计有蓝田、渭南、咸阳、鄠县、澧泉、美原、盩厔等,临近长安,其县尉常是校书郎、正字和州参军等迁官的美职。”①《唐代基层文官》,第116页。可见,畿县与畿县官具有地理与职官的优势。但是书面的规定和京畿县官的工作状态并不重合。下面结合四位诗人的不同官职,论述其工作状态与创作心理,以补史学家研究之不足。
韦应物曾任正六品下的鄠县令,生活处境较为优越,能够主持鄠县郊外的游宴。如其《对雨赠李主簿高秀才》:“吏局劳佳士,宾筵得上才。终朝狎文墨,高兴共徘徊。”②〔唐〕韦应物撰,孙望编:《韦应物诗集系年校笺》卷三,第172 页。本文引用韦应物诗皆出此书,不再一一出注。这与他任职洛阳丞时的心情差别很大,《任洛阳丞答前长安田少府问》曰:“数岁犹卑吏,家人笑著书。告归应未得,荣宦又知疏。”
钱起、白居易分别任蓝田尉、盩厔尉。在唐代,并不是所有的县都有县尉,如韩愈在《送区册序》中谈及阳山县:“县郭无居民,官无丞尉。”③〔唐〕韩愈著,刘真伦、岳珍校注:《韩愈文集汇校笺注》卷十一,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139页。京畿县尉比京畿县令品级低,但职责重要。日本学者砺波护研究县尉曰:“白居易是担当仓曹等事务的司户尉。”④[日]砺波护:《唐代的县尉》,刘俊文主编,夏日新、韩昇、黄正建等译:《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4卷,第568页。虽然白居易一再感叹县尉卑微,但是其盩厔生活较闲适,如《官舍小亭闲望》:“日高人吏去,闲坐在茅茨。”⑤〔唐〕白居易著,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79页。本文引用白居易诗皆出此书,不再一一出注。身为蓝田尉的钱起在《县中池竹言怀》中也书写知足心态:“官小志已足,时清免负薪。卑栖且得地,荣耀不关身。”⑥〔唐〕钱起撰,王定璋校注:《钱起集校注》卷六,第185页。本文引用钱起诗皆出此书。这种知足又有怨言的情感正是畿县县官的普遍心态。
姚合任武功主簿。关于县主簿的地位,可从韩愈为县丞崔立之写的《蓝田县丞厅壁记》窥探:“官虽尊,力势反出主簿、尉下。”⑦《韩愈文集汇校笺注》卷三,第373页。可见,有的县主簿的实际地位要高于县丞。县主簿工作繁琐,据《唐六典》载:“主簿掌付事勾稽,省署抄目,纠正非违,监印,给纸笔、杂用之事。”⑧〔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三〇,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753页。县主簿的职责之一就是“勾稽县政府中出入的各种文书。唐代文书,又称文案或案,即各级官府每日处理的问题按程式记录的文件”⑨张玉兴:《唐代县主簿初探》,《史学月刊》2005年第3期,第43页。。“勾检官员位卑而权重”①杜文玉:《唐代地方州县勾检制度研究》,《唐史论丛》2013年第1期,第14页。,主簿纠正不合程式的文件,其承担的文字工程量可谓浩大。因此,姚合在《武功县中作三十首》中多次提到簿书:“簿书销眼力”②文章引用姚合诗皆出自《全唐诗》(增订本)卷四九八《武功县中作三十首(一作武功县闲居)》,第5702-5703页。如无特殊说明,皆据此书,不再一一出注。,“簿书多不会”,“簿籍谁能问”。姚合在工作过程中因文字潦草,招来同僚官吏的不满:“吏人嫌草书。”县主簿有监印信的职责,这在姚合诗中也多有体现:“野客嫌知印,家人笑买琴。”“谁念东山客,栖栖守印床。”“今朝知县印,梦里百忧生。”“印朱沾墨砚,户籍杂经书。”“主印三年坐,山家百事休。”印作为县舍里的意象,代表功名与仕进,与官印相对的是“东山客”“野客”“经书”“琴”。印与琴、仕与隐形成对比,表现出官的书面规定性与吏的现实工作的矛盾。
唐代县尉、县主簿有具体的工作职责。史书记载、史家论述畿县官前途光明,但在诗歌创作中却透露出诗人卑微的心态。这种矛盾出现的原因,除了畿县官仕途前景与现状的时间差,还要从官吏分途、中央官与地方官之别两个角度考察。张广达先生指出唐代官与吏有明显的区别:“唐代之吏实相当于秦汉胥吏、郡县掾属和乡官。”③张广达:《论唐代的吏》,《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2期,第1页。而县尉、县主簿品级都在正九品上下,身处流内官的末位:“流内第九品官实际上常常仍被视为流外。”④张广达:《论唐代的吏》,《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2期,第9页。京畿县官不免从事吏职,感叹为“吏”之难。不仅有职官品秩的原因,京畿县官所处政治空间的特殊性也造就了他们的矛盾心态。京畿县域临近京师长安,京畿县官交游圈涉及京城中央官。张荣芳先生认为京畿县令“兼具地方官与中央官之双重性格”⑤张荣芳:《唐代京兆府领京畿县令之分析》,黄约瑟、刘健明编:《隋唐史论集》,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93年版,第128页。。京畿县尉、县主簿虽比京畿县令品级低,也不可避免地与中央官僚有交往。如韦应物归京朝请有《朝请后还邑寄诸友生》:“宰邑分甸服,夙驾朝上京。”钱起归京登览有寄中书侍郎李揆《乐游原晴望上中书李侍郎》:“遥想青云丞相府,何时开阁引书生。”白居易在元和二年(807)与京城杨氏交往,后任进士考官:“春,与杨汝士等屡会于杨家靖恭里宅。”“秋,自盩厔尉调充进士考官。”⑥《白居易年谱》,第37页。一言以蔽之,特殊的地理位置、书面的制度规定、紧要的工作环境是畿县官矛盾心态形成的政治原因。
三、中唐京畿吏隐诗学的群体表达:文以饰官,隐以淡吏
身为“官”却还要从事“吏”的工作,所以诗人通过文学的手段抬高自身的地位,向世人宣示京畿县官是清流官而不是浊吏①葛晓音教授指出“沧洲吏”:“尽量淡化吏的世俗色彩,强化‘隐’的清高姿态。”参见葛晓音:《中晚唐的郡斋诗和“沧洲吏”》,《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第99 页。葛教授定义的“沧洲吏”多指“在京外郡县任职的官吏”,与本文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不尽相同。。这就有情感体验与情感表现的区别:一是“人们内心深处感受到的情感体验。二是人们以语言、表情、手势以及眼神等各种方式所表达的情感,即情感表达”②孙一萍:《情感表达:情感史的主要研究面向》,《史学月刊》2018年第4期,第20页。。京畿县官在情感体验上感叹官卑,在情感表达上用诗歌抒发隐逸的喜悦。因此,“文以饰官”是情感表达的方式,“隐以淡吏”是情感表达的主题。这种情感表达体现在宦情与隐逸的对比、审美空间的位移、诗人对隐士的崇拜、日常交往的心态四个方面。
其一,宦情与隐逸的对比。在京畿县官诗人笔下,“仕”与“隐”两种情感同时存在。诗人将隐逸思想提升到“性”与“志”的高度。如钱起《幽居春暮书怀》:“自哂鄙夫多野性,贫居数亩半临湍。溪云杂雨来茅屋,山雀将雏到药栏。”诗歌以“野性”总领全篇,以下数亩田地、茅屋、药栏等意象都是“野性”的象征。韦应物在《答徐秀才》中表露“铅钝”本性:“铅钝谢贞器,时秀猥见称。”白居易《官舍小亭闲望》表达知足的乐趣:“人心各自是,我是良在兹。回谢争名客,甘从君所嗤。”钱起一方面享受县官带来的经济实惠,另一方面却厌恶追求功名。如《县中池竹言怀》:“官小志已足,时清免负薪。卑栖且得地,荣耀不关身。”“卑栖”是诗人真实的情感体验,“志”是诗人的情感表达。诗人的文学策略是将“吏隐”描写“脸谱化”:将“隐”的部分重点描写,“吏”的部分压缩略写;将“隐”的部分外化,“吏”的部分内敛;将“隐”作为兴趣爱好,“吏”作为忽视的对象;“吏”是谋身手段,“隐”是品格象征。“情感体验与情感表达相互影响、互为因果”③孙一萍:《情感表达:情感史的主要研究面向》,《史学月刊》2018年第4期,第20页。,卑微的情感体验与吏隐主题诗歌的情感表达是相互影响、彼此渗透的。
其二,审美空间的位移。畿县区域按照与“吏事”的紧密程度,可以分为不同层级区:县衙讼堂、县舍凉亭和书斋、县舍以外的地区④欧美学者雷迪指出:“有时人们为了避免情感痛苦,还会寻找能够自由地表达情感的场所或机构甚至某种仪式,即所谓情感避难所。”参见孙一萍:《情感表达:情感史的主要研究面向》,《史学月刊》2018年第4期,第21页。。在第一层级区,畿县官将讼堂县衙描绘成隐逸之所。钱起《题张蓝田讼堂》曰:“角巾高枕向晴山,讼简庭空不用关。秋风窗下琴书静,夜景门前人吏闲。稍觉渊明归思远,东皋月出片云还。”在钱起笔下,蓝田讼堂成为隐士隐逸的场所。县舍官亭也是诗人休憩的场所,如白居易《官舍小亭闲望》:“数峰太白雪,一卷陶潜诗。”官舍小亭为诗人“闲望”提供了展现自我的契机。这就形成了山峰、诗人、陶诗三者合一的境界。自然景物、历史人物将县官形象雅化,愉悦的情感掩盖了官卑的尴尬。在县域之中,有竹亭送别、寺院独宿等生活场景,如钱起《酬王维春夜竹亭赠别》:“山月随客来,主人兴不浅。今宵竹林下,谁觉花源远。”王定璋先生释“竹林”曰:“钱起为官蓝田时,常与王维、裴迪等人宴饮酬唱,故以‘竹林七贤’取喻。”①《钱起集校注》卷一,第30页。钱起借竹林七贤、桃花源的典故表达对桃源生活的向往。钱起在蓝田尉任内写有多首登山诗,诗题如:《自终南山晚归》《登秦岭半岩遇雨》《天门谷题孙逸人石壁》《独往覆釜山寄郎士元》《仲春晚寻覆釜山》《登覆釜山遇道人二首》《登玉山诸峰偶至悟真寺》《夕游覆釜山道士观因登玄元庙》。诗人以山为中心,拉开了与县舍俗吏的距离。鄠县令韦应物写有多首游宴诗,诗题如《西郊游宴寄赠邑僚李巽》《扈亭西陂燕赏》《任鄠令美陂游眺》《西郊游瞩》《乘月过西郊渡》《再游西郊渡》《东郊》。这里的“郊”是隐逸思想的空间呈现,与“讼堂”“县舍”相对。
其三,诗人对隐士的认同。畿县县官对陶渊明的诠释有三:一是作为辞官归隐的陶渊明。如韦应物《东郊》:“吏舍跼终年,出郊旷清曙。”“终罢期结庐,慕陶真可庶。”表达了诗人对归隐的美好愿望。二是作为诗人的陶渊明,如白居易《官舍小亭闲望》:“数峰太白雪,一卷陶潜诗。”表达了诗人知足、安贫乐道的情感。三是作为被超越者的陶渊明。钱起《题张蓝田讼堂》:“稍觉渊明归思远,东皋月出片云还。”还有刘伶、嵇康的形象出现在姚合诗中:“更师嵇叔夜,不拟作书一作诗题。”“长羡刘伶辈,高眠出世间。”诗人以嵇康之懒、刘伶之旷写闲适乐趣。在钱起眼中,亦官亦隐的王维堪称前辈,两人在蓝田的交游对其畿县诗歌创作、吏隐心态的展现都有影响。蒋寅先生认为钱起只是“在形式上取代王维位置的继踵者”,“还在与大诗人王维的交游酬唱中直接领受到亦官亦隐的生活作风的熏陶”②《大历诗人研究》,第164页、第156页。。不过,钱起继承了王维的生活作风,但两者又有区别:钱起以县官的身份写人塑景,既有隐逸之乐的情感表达,又有为吏之卑的情感体验。这种意内而言外的创作策略与王维空寂清高的创作心态有着本质的不同。从庄园题材的情景交融诗到山水题材的行旅言志诗,诗人的主体形象更加突出,诗风更加清新巧媚。县官身份拓宽了钱起的视野,有助于钱起摆脱王维式的写作惯性,走向独立的创作道路。
其四,日常交往的出世心态。县官诗人通过交往对象消除俗吏的痕迹。钱起的诗题多次出现野叟、野老③“‘野客’是《武功作》里经常出现的重要角色。”参见蒋寅:《姚合“武功体”对“吏隐”主题的开拓》,《百代之中:中唐的诗歌史意义》,第129页。其实在钱起诗中已经出现过很多野客形象。,如《同严逸人东溪泛舟》《蓝田溪与渔者宿》《题玉山村叟屋壁》。诗人在李叟家中享受田园乐趣,如《玉山东溪题李叟屋壁》讲述钱起与野老交往:“野老采薇暇,蜗庐招客幽。麏麚突荒院,鸬鹊步闲畴。偶此惬真性,令人轻宦游。”白居易与处士王质夫的交情密切,如《招王质夫》:“濯足云水客,折腰簪笏身。”《祗役骆口因与王质夫同游秋山偶题三韵》:“平生烟霞侣,此地重徘徊。”韦应物与处士交往,诗题极具叙事特色:《紫阁东林居士叔缄赐松英丸捧对欣喜盖非尘侣之所当服辄献诗代启》:“一望岚峰拜还使,腰间铜印与心违。”韦应物与僧道交往,《县内闲居赠温公》曰:“虽居世网常清净,夜对高僧无一言。”山水为县官提供了表演的舞台,山野村夫则是他们吏隐主题创作中的配角。
综此四点,畿县县官诗人通过共同的情感表达将畿县县域由近及远塑造成融合仕与隐的私人天地。恰如宇文所安先生所说:“这是中国上层社会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它标志了一种转变,从中古的‘隐逸’主题——对于私人性,它纯粹从拒斥公共性的负面加以界定——转向‘私人天地’的创造——‘私人天地’包孕在私人空间里,而私人空间既存在于公共世界之中,又自我封闭,不受公共世界的干扰影响。”①[美]宇文所安著,陈引驰、陈磊译:《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唐文学文化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73-74页。新型的隐逸文化可以使县官不必辞官,就地取材便可成为隐士。沿着宇文所安的内在理路,私人空间可看成实体化的物理空间,而私人领域是艺术化的、虚化的私人空间。园林就好比私人空间,而在园林里的文学活动如同诗人的私人天地。同理,京兆畿县诗人在公共空间之中营造夜间的讼堂、休假时的官亭、畿县的寺庙都是充满隐逸之乐的私人领域,是交杂着吏与隐的壶中天地。以上诗人的情感表达“都不是单纯地描述个人的内心体验,必须把它和外部的社会关系联系在一起理解”②孙一萍:《情感表达:情感史的主要研究面向》,《史学月刊》2018年第4期,第20页。。特殊的情感表达源于特殊的社会环境。历史性地考察,京畿县官的吏隐是新型的隐逸文化、清流文化,是出身科举、跻身清流的文人厌恶吏职、有意远离浊流的文学化呈现。诗人对隐逸空间的书写与想象,以文学作品装饰日常生活、突出隐士身份、表现隐逸情怀正是他们强化清流身份的艺术手段。“官”与“吏”杂处的生活环境和“吏”与“隐”融合的诗歌主题,是互为表里的。
四、中唐京畿吏隐诗学的审美特征:“幽”与“闲”
“一个作家,一个流派的创作,美在哪里,反映了什么样新的审美趣味,乃是文学思想中最为核心的问题。”③左东岭:《中国文学思想史的学术理念与研究方法——罗宗强先生学术思想述论》,《文学评论》2004年第3期,第173页。中唐吏隐诗学审美趣味的产生空间、具体形态、发展演变都是值得考察的问题。诗人在特定区域创作出特殊风格的文学作品,其审美情趣的形成是自然地理、人文地理两重合力作用的结果:“诗人受自然地域景观的熏陶……从而产生一种与地理风貌相似的审美理想。”①吴承学:《江山之助——中国古代文学地域风格理论》,《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增订本),中华书局2022年版,第317页。在地理环境与吏隐文化影响下,催生出的审美字眼是“幽”与“闲”。如钱起《独往覆釜山寄郎士元》:“胜事引幽人,山下复山上。”《杪秋南山西峰题准上人兰若》:“向山看霁色,步步豁幽性。”《秋夜梁七兵曹同宿二首·其二》:“如何此幽兴,明日重离群。”《春夜过长孙绎别业》:“含毫凝逸思,酌水话幽心。”韦应物《扈亭西陂燕赏》:“公堂日为倦,幽襟自兹旷。”《晦日处士叔园林燕集》:“始萌动新煦,佳禽发幽响。”白居易《酬王十八李大见招游山》:“自怜幽会心期阻,复愧嘉招书信频。”以上诗人都具有尚“幽”情结,钱起、韦应物更热衷于表现幽情。“幽”风格包含以下四方面:一是终南山中的幽境、幽响;二是诗人的幽性;三是因幽境、幽性衍生出的幽心;四是诗人与畿县人物的幽会,饮酒享乐。可见,幽境、幽性、幽心、幽会涵盖客观环境与主体性格两方面。“幽”不仅是地域性的审美,还具有时代意义。蒋寅先生认为:“吏隐心态成为韦应物异于陶渊明的特征……‘幽’就是陶诗不具备的趣味。其实,清幽乃是大历诗人共同的审美趣味。”②《大历诗人研究》,第89页。钱起、韦应物清幽风格的生成与京兆府畿县幽静的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分不开。京兆畿县的地域性审美促进了大历诗歌风格的生成。
“一个社会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会创造或让某一个表达情感的词汇特别流行。”③王晴佳:《拓展历史学的新领域:情感史的兴盛及其三大特点》,《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第89页。四位诗人笔下的“幽”与“闲”亦是如此。如果说天宝、大历时期的钱起、韦应物的艺术功绩在于写“幽”的话,那么元和、长庆时期的白居易、姚合表现在写“闲”。“幽”是诗人对自然环境的直接汲取,“闲”是县官对吏役生活的反向回应。姚合“武功县中作三十首”诗题又作:“武功县闲居”。“闲居”既表现出京畿县官的创作心态,也是诗人创作的重要题材。钱起《玉山东溪题李叟屋壁》:“麏麚突荒院,鸬鹊步闲畴。”韦应物《任鄠令渼陂游眺》:“屡往心独闲,恨无理人术。”《县斋》:“闲斋始延瞩,东作兴庶氓。”白居易《病假中南亭闲望》:“始知吏役身,不病不得闲。闲意不在远,小亭方丈间。”《游仙游山》:“暗将心地出人间,五六年来人怪闲。”姚合《武功县中作三十首》出现“闲”字更多:“闲行懒系腰”“爱闲求病假”“凭客报闲书”“闲行只杖藜”“闲披野客衣”“闲书不著行”“闲人得事晚”等。
通过以上几例可以发现“闲”的内涵有三点:一、与吏役忙碌相对,悠闲是诗人偏爱的词语。二、诗人借闲书、闲披、闲行的动作,衬托懒散无拘束的生活。三、诗人借闲心、闲兴表现生活品味。闲适是白居易创作的重要题材:“又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一百首,谓之闲适诗。”④《白居易集笺校》卷四五《与元九书》,第2794页。“退公独处”成为诗人诗歌分类的标准。白居易将闲适的居官心态转化为诗人品格,由诗人品格提炼为诗歌风格,由诗歌风格实体化为诗歌门类即“闲适诗”。可以看出“闲”的审美趣味不断物化,衍生出不同的诗体,最终形成“闲适诗”。姚合《武功县中作三十首》出现“闲”字的次数更多。“闲”和自然环境、生活场景、创作心态都有联系。不过姚合武功县中诗更多描写荒凉之景,如《唐才子传》评价:“盖多历下邑,官况萧条,山县荒凉,风景凋弊之间,最工模写也。”①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册,第124页。姚合“武功体”的“闲僻”风格还与地理环境有关。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武功县距京兆府较远:“东至府一百四十里。”②《元和郡县图志》,第32页。所以,姚合《武功县中作三十首》才有:“县去帝一作京城远,为官与隐齐。”“歧路荒城少,烟霞远岫多。”“作吏荒城里,穷愁欲不胜。”工作环境还影响姚合的性格与诗风:“养生一作闲宜县僻”,“自知狂僻性”,“还往嫌诗僻”。武功县的荒凉氛围使得姚合的诗歌“闲”中有“僻”。这种闲僻风格是偏离了“闲”的病态审美。从幽独到闲适,从地理空间上的逃避到心境情绪的自适,审美形态的流变象征着诗人情感的变化与处世态度的成熟。
钱起、韦应物、白居易的以上诗作也有审美上的缺点,如描写视域狭窄,题材率意重复、风格浅俗骨弱。刘克庄评钱起:“钱起与郎士元同时齐名,人谓之‘钱郎’。二人诗骨体弱而力量轻。”③〔宋〕刘克庄撰,王秀梅点校:《后村诗话》,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03页。姚范评韦应物:“韦自在处过于柳,然亦病弱。”④〔清〕姚范:《援鹑堂笔记》卷四四,顾廷龙主编:《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149册,第114页。许学夷评价白居易五古:“盖以其语太率易而时近于俗,故修词者病之耳。”⑤〔明〕许学夷著,杜维沫校点:《诗源辩体》,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73页。受京畿县域、县官身份的束缚,诗人的创作空间与眼界心胸都存在限制,创作风格难免走向率意、俚俗、荒僻、纤弱。可见,地域文化对诗人和诗歌的影响是正反两面的。
钱起、韦应物、白居易、姚合四位诗人,在拥有共同情感表达的同时,审美偏向不断变化。就诗体而言,钱起多用五言排律,韦应物、白居易多用五言古体,姚合多用五律组诗,四位诗人的创作,经历了律体——古体——律体、精巧——古淡——纤巧的循环发展。就内容而言,钱起、韦应物在天宝隐逸之风的基础上另开幽境,渐入俗调,更贴近日常生活。诗人身份、山水野趣、园林构建等诗料散落到诗篇中,使京畿县官的诗风摆脱了盛唐空灵悠远的审美束缚,朝向境幽骨弱的方向发展。元和、长庆时期,白居易、姚合取材更加世俗化、描写更加碎片化、情景更加日常化、人物形象更加个性化、诗意分布更加集中化,创立了“闲适”的审美格调。闲适成为吏隐主题诗歌普遍的创作心态,闲适诗成为一种诗型被后人学习、效仿。就京畿吏隐主题诗歌创作实绩而言,钱起是四位诗人中创作量最多的,体制完备⑥据王定璋先生注本统计,钱起表达吏隐乡野生活的诗歌,五古如《赠东邻郑少府》,七古如《题张蓝田讼堂》,五律如《县城秋夕》,七律如《题郎士元半日吴村别业兼呈李长官》,五言排律如《东溪杜野人致酒》,诗体多样。,但诗人身处盛唐、中唐之交,没有形成独立的风格,创作还带有过渡时期的痕迹;韦应物、白居易诗作数量较少,但创作主体的个性突出,艺术形象鲜明;元和末、长庆初,姚合以京畿县官的形象,闲辟①周衡先生指出姚合“武功体”经历了从清僻到清雅的内化。参看周衡:《姚合武功体和吏隐观的嬗变》,《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第66-69页。的审美风格,以组诗的形式将“吏隐”诗歌集中展现,使得吏隐主题进一步强化,《武功县中作三十首》成为吏隐主题“真正定型的标志”②《百代之中:中唐的诗歌史意义》,第132页。。唐代诗歌的吏隐主题由隐到显,从萌芽到定型,都与京畿县官的政治身份,京畿空间的自然地理、文化环境相联系。
畿县地理与县官身份共同激发了唐代吏隐主题诗歌的定型,使得吏隐主题形象化,正式成为创作风尚。在“幽”与“闲”的律动中寻绎,可以按切出中唐吏隐主题诗歌跳动的时代脉搏,从中挖掘出京畿县官创作的时代意义。“幽”与“闲”的吏隐之趣恰恰是中唐吏隐主题诗歌的审美注脚。
五、结语:中唐吏隐诗学思想的演进特点
地域文化与政治身份是中唐吏隐诗学发展定型的充分和必要条件。比起盛唐时期的“以隐为仕”、白居易大和时期的“中隐”等鲜明的诗学主题,天宝至长庆段的吏隐主题发展轨迹较为模糊。吏隐主题诗歌产生的区域、创作主体的政治身份常常被后人忽略。通过分析可知,以吏隐为主题的唐代京畿诗歌具有萌芽性、间歇性、持久性的特点。萌芽性是指诗人处在创作早期,艺术风格刚形成或尚未成熟。诗歌立意多重复、风格偏孱弱,还只是实验性练笔。在韦应物任职苏州以后,白居易任职苏杭、退居东洛以后③白居易退居东洛以后,“展现职业官僚的宦情与意趣”,“表达了一个职业官僚对常态化生活的肯定”。参看查屏球:《从科场明星到官场隐士——唐宋转型与白居易形象的转换》,《文学遗产》2019年第1期,第57页。,“吏隐”主题诗歌创作才形成规模,逐渐成为时代风尚。间歇性是指诗人会因为官职的迁转、空间的迁移,创作兴趣发生转变。大历时期,钱起回到长安以后,艺术贡献集中在酬赠诗、送别诗等题材。如高仲武评曰:“右丞以往,与钱更长。自丞相已下,出使作牧,二君无诗祖饯,时论鄙之。”④〔唐〕高仲武:《中兴间气集》卷下,傅璇琮、陈尚君、徐俊编:《唐人选唐诗新编》(增订本),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494页。元和初,白居易回到长安后,虽然也写了不少闲适诗,但创作重心已转移到讽喻题材⑤参看杜学霞:《朝隐、吏隐、中隐——白居易归隐心路历程》,《河南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第130-133页。。诗人对吏隐主题的选取受地理、职官的影响具有很大的灵活度。持久性是指不同代际的畿县诗人在诗歌体制、创作数量、艺术风格、审美趣味等方面对吏隐主题不断开拓。虽然他们的政治地位暂时卑微,文学创作稍显稚嫩,但“草蛇灰线,伏脉千里”,为之后白居易在洛阳创作的“中隐”诗歌、苏东坡的吏隐诗奠定了基础①参看张玉璞:《“吏隐”与宋代士大夫文人的隐逸文化精神》,《文史哲》2005年第3期,第48页。。诗人情感体验与情感表达的张力推动着诗歌史的发展进程,诗人们的集体化情绪固化为群体心态进而转化为时代风尚引领文人创作。在吏隐主题的引领下,诗人居官如隐,享受隐逸乐趣,吏隐成为诗人的生活方式、文学的创作思潮,渐渐成为时代风尚。要之,京畿空间中的吏隐诗学是不断建构的:从产生的角度讲,吏隐思想的萌生受地理环境、政治条件的制约;从体系构成上讲,包含作者身份、诗人群体情感表达、诗歌文体选择、诗歌审美特征及其变化等诸多面向;从概念的发展转化看,诗人创作的县居诗、行旅诗题材不断外化、变化,大而扩之为郡斋诗、闲适诗,变而化之为都市诗、讽喻诗。吏隐主题诗歌会因时、因地、因人、因官而发生变化。“吏”与“隐”的张力角逐促进了吏隐诗学产生原因的多维性、表现形态的多样性、发展演变的曲折性。要之,中唐吏隐诗学不仅具有地域性的审美价值,还具有思想史意义,在绵延中发生蜕变,在转型中走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