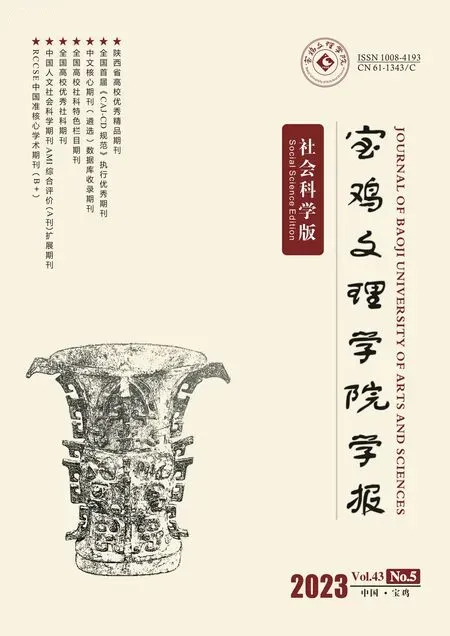金末政治生态与文人心态略论
——以杨奂仕行为中心
李 梅
(宝鸡文理学院 图书馆,陕西 宝鸡 721016)
金王朝气运由盛至衰急转而下的转折点开始于宣宗贞祐南渡(1214)。金朝疆域缩减,蒙古铁蹄之下的金代颓势毕现。宣、哀二宗也想励精图治,重振金王朝。国政之策由世宗、章宗时期重文轻吏而转向重吏轻儒,由此导致政治生态的转变走向不利于儒士生存和发展的局面,进一步激化了儒吏之间的矛盾,儒士的精神心理状态也随之转变。学术界对于金末政治生态的专题性研究较少,大多作为论述文学风格或文化等其他方面的一个背景加以叙述,而未真正展开对此针对性的研究。对儒士心态的研究则多以群体笼统述之,对其形成的具体原因及其复杂的政治背景等方面都还有待深入剖析。本文以“关西大儒”杨奂作为个案,通过对其科考仕途履历的具体分析,展示金末王朝政治生态的多方面影响,及由此导致这一时期儒学士人的生存状态及其心态之转变。
一、杨奂的早年经历与文人心态之养成
作为金末元初的关西大儒,杨奂早期是为进入仕途实现理想抱负的准备阶段。此时的心态正如他在《至日》诗中写道:“怒鲸一夕掀洪浪”[1](P443)般豪迈与昂扬。
杨奂的豪迈性格与政治品格的养成主要源于早年的经历与家学传承。杨奂之母程氏,“其家藏书数千卷,皆奁具易之。”“夫人姿淑媛,有识度。课诸子读书,必盈约始听休舍。尤善援引故实,因事指诲。”[1](P452)程氏对子弟的儒学教育甚严。如果说母亲对杨奂的教育是言传,那杨奂之父更多地便是身教。其父杨振公“幼喜读书,与同里张子文善,尝手抄经传,尤爱王符诸论。与宾客谈,时称诵之。”[1](P450)杨奂之父从小便手抄经传,可见他的儒学喜好与政治理想。这一具有儒家特征的政治品格也影响到了其子杨奂。
史载杨奂之父,“弱冠,仕州县,为属掾。复兴郡王括陕西民田日,知公名,选之以从,甚重信之。公因为王言‘军与民皆吾人,夺彼与此,其利安在?’”“当官公廉,所平反甚多。”[1](P451)从中可以看出其父杨振公虽为吏官却有儒行,故而受到名流人士耀人(耀,今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李安国的敬重,赠诗曰:“纯夫吏业而儒行,家贫而好客,居今之世而好古,贱金帛而贵砚墨,是四反也。”[1](P451)此言鲜明生动地体现出杨振公儒雅好古、不重产业而重学问修养之品行。
正是得益于优良的家庭儒学教育和父母的言传身教,杨奂16岁时,州倅宗室永元对其父言:“‘若老矣,守佐重以案牍相烦,闻若有佳儿,姑欲试之。’即檄,君为仓典书。时调度方殷,君掌出纳,朱墨详整。迄岁终,无圭撮之误。倅爱之,为他日必有大用者,劝之宦学,师乡先生吴荣叔,指授未几,□迥出伦辈。”[1](P455)由此可见,杨奂早年便体现出优于同龄人的吏治才能和儒行学识,受到了长辈的首肯和赞誉,并寄予厚望。
来自家庭的优良教育和社会士人的肯定激励,杨奂的人生前期可以说是充满雄心壮志的。而此时又正是世宗、章宗两朝重文轻吏、文治繁盛的良好政治时期,因此杨奂积极入世,希冀通过科考进入仕途,实现自身的政治抱负。即使他在章宗到卫绍王时期(1190—1213)前后历经三次科考失败,却仍然没有熄灭心中的政治理想。“以天下为己任”,希望通过进入仕途来实现自己的儒家之道。许纪霖在论述中国古代士大夫之儒道精神时,认为此种沉重的社会使命在世界文明史上也是罕见的[2](P66)。杨奂这一阶段体现的正是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3](P104)的儒道精神。故而是其人生最充满积极进取的前期,虽然科考之路多舛,但他对自己的儒道仕途仍充满希望,对金朝的政治社会寄予深切关注。
二、杨奂兴定科考所见政治生态及影响
(一)杨奂兴定五年科考下第之遭遇
宣宗兴定五年(1221),杨奂在经历了前四次的科考失利,心中入仕之火不灭,仍然参加了这一年的科举考试,此时他已32岁。而这次科考他依然遗误下第。这背后又透露出怎样的时代政治讯息?只有充分探究其科考失利的原因,才能够更深层次地挖掘金末的政治生态环境以及所处其中的儒学士人所面临的困境和心态转折的形成。
关于宣宗兴定五年的这次选举,《金史·宣宗本纪下》记载:“三月,省试经义进士,考官于常额外多放乔松等十余人。有司奏请驳放,上已允,寻复遣谕松等曰‘汝等中选而复黜,不能无动于心。方今久旱,恐伤和气,金特恩放汝矣。’庚子,赐林州行元帅府经历官康琚进士及第。”[4](P356)而宣宗之所以应允多取十余人,以特恩赐第,可能也是因为人数不多的缘故。[5](P499)《金史·选举志一》载:“五年,上赐进士斡勒业德等二十八人及第。上览程文,怪其数少,以问宰臣,对曰:大定制随处设学,诸谋克贡三人或二人为生员,赡以钱米。至泰和中,人例授地六十亩。所给既优,故学者多。今京师虽存府学,而月给通宝五十贯而已。若于诸路总管府、及有军户处置学养之,庶可加益。”[4](P1143-1144)“五年”即指兴定五年(1221),而这一年学者减少,除了因为赡给减少的原因外,金朝随着宣宗南迁,政权日益衰弱,社会动荡,战乱频繁,统治疆域也日益缩减,应举之人减少则是必然。《深州金石记》记载兴定二年(1218)经义词赋进士总共才录取75人。[6](P536)根据都兴智的统计,从承安五年(1200)到哀宗天兴二年(1233),总共进行了十一次科举考试,而平均每年的录取人数只有45.9人,总体的录取人数呈下降趋势。[7](P59-64)兴定五年的科考录取人数由上面的资料也看出人数之少,宣宗才特赐了一些人,将乔松特赐为经义科进士。从直接的原因来看,似乎是取士人数的有限而可能导致杨奂遗误下第,但是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却更为复杂。
元好问所撰《杨公神道碑》中载,杨奂“赴廷试。兴定辛巳,以遗误下第,同舍庐长卿、李钦若、钦用昆弟惜君连蹇,劝试补台掾。台掾要津,士子慕羡而不能得者。君答书曰:‘先夫人每以作掾为讳,僕无所似肖,不能显亲扬名,敢殆下泉之忧乎?’”[1](P455)杨奂以母之训,以孝为由含蓄地回应了这次的劝告。杨奂之母曾经提及,“今幸无他,使吾儿无废学,如次充植业士林、乡里称善人足矣,荣仕非所望也。”“尝抚奂辈戒之曰:‘士立身行己,教亦多术,何必尔耶?汝曹若不改图,吾饭含不瞑矣。’”[1](P453)杨奂拒绝补台掾,除了受重儒学轻吏学的家教学风影响外,也反映出当时以儒学为业士人的吏员观念以及与吏宦之间不曾间断的冲突和对立。我们不可否认杨奂的这次选择不无受其母亲的影响,但更为复杂的政治背景和时代观念才是导致杨奂遗误下第并拒绝补台掾的主要原因。而这次科考失败以后,杨奂不仅没有试补台掾,甚而直至金亡国,再没有参加科举考试。其背后的原因绝不简单。
(二)儒吏之争与杨奂科考下第
贞祐二年(1214)宣宗南渡,金朝的政治版图一缩再缩,军事态势呈守势。宣宗却任用权臣高琪,“高琪自为宰相,专固权宠,擅作威福,与高汝砺相唱和。高琪主机务,高汝砺掌利权,附己者用,不附己者斥。”“琪喜吏而恶儒,好兵而厌静。”[4](P2345-2347)排异己,拉帮结派之风已成。刘祁在《归潜志》里也记载:“贞祐间,术虎高琪为相,欲树党固其权,先擢用文人,将以为羽翼。已而,台谏官许古、刘元规之徒见其恣横,相继言之。高琪大怒,斥罢二人。因此大恶进士,更用胥吏。彼喜其奖拔,往往为尽心,于是吏权大盛,胜进士矣。”[8](P71)吏权大盛,文人士子只能通过科举一路进入仕途,而科举之路却不可能不受到这些当权胥吏的横加选择和干涉。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宣宗兴定五年的这场科考无疑凸显了政治斗争对其选拔人才的影响和干预。关于这次科考,《金史·李复亨传》记载:“五年三月,廷试进士,复亨监试。进士卢元谬误,滥放及第。读卷官礼部尚书赵秉文、翰林待制崔禧、归德治中时戬、应奉翰林文字程嘉善当夺官降职,复亨当夺两官。赵秉文常请致仕。复亨罢为定国军节度使。”[4](P2218-2219)可以看到,除了进士卢元因谬误乱选及第而受处分致仕之外,赵秉文、翰林待制崔禧、归德治中时戬都受到了不同程度夺官降职的处分。《归潜志》卷六还载:“李君美,河中人。……兴定末,坐监试进士失取人,出镇同州。”[8](P59)李君美也在这次兴定五年的科考中受到了惩处。这么多人受到牵连和处分,很显然不仅仅是卢元滥放及第这么简单。“兴定初,某(元好问)始以诗文见礼部闲闲公。公若以为可教,为延誉诸公间。又五年,乃得以科第出公之门。公又谓当有所成就也,力为挽之。奖借过称,旁有不平者,宰相师仲安班列中倡言,谓公与杨礼部之美、雷御史希颜、李内翰钦叔为元氏党人,公之不恤也。”[9](P70)因为赵秉文(1159-1232)对元好问的赏识与推奖而被目为元氏党人的事件中,杨之美、雷希颜以及李钦叔都一并划入元氏党人。杨之美即杨云翼(1170-1228),他与赵秉文一起代掌文坛多年,时称“杨赵”。关于此次被一起称为元氏党人的赵秉文、杨云翼以及雷希颜还有时戬等,其实在政治交往中也是有些端倪的。《金史》列传第四十八载:“时右臣相高琪当过,人有请榷油者,高琪主之甚力,召集百官议,户部尚书高夔等二十六人同声曰:‘可。’云翼独与赵秉文、时戬等数人以为不可,议遂格。”[4](P2422)这里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朝堂之上,以高琪为代表的胥吏与以赵秉文为代表的文臣之间各自站队相左的政治生态局势。
宣宗朝重用胥吏,更进一步地加大了吏官与士人之间的对立。整个朝堂上弥漫着大臣之间互相攻怵为党,人人自危自保之境。刘祁在《归潜志》卷七中言:“南渡为宰执者,多怯惧畏懦不敢有为,凡处一事,先恐人疑己。如宰执本进士,或士大夫得罪,知其无辜,不敢辨言,恐人疑其为党也。”[8](P74)所以,杨云翼和赵秉文等被攻击结党在金末南渡的如此政治环境背景中,确是难免,也从侧面反映出刘祁所言非虚。而杨奂同赵秉文亦有多年的交情,赵长杨奂27岁,二人经常书信相通,既有儒学经义的学术探讨,也有生活上的互相帮助,可谓亦师亦友。赵秉文在《与杨焕然先生》的一封书信中写道:“中前道过京兆,承不远相从,谈话终日,极有开发。违别以来,不胜倾向。意想秋尽复得会面……”“某眼疾如昨,承遣人玺足千里外送眼药,良感意动。伏蒙赠以柳义假子,悚愧!悚愧!《论语》未有印者,钦叙西行,不知有余者否?《孟子解》先寄去,《中庸》《大学》相次了毕,续当继呈。足下高才博学,留心经学,研究圣心宜矣。”[1](P463)从这段书信记载中体现出二人关系深厚,互相激赏,在学术和生活方面都有不断的交流。杨奂被划入赵氏一党也在情理之中,而赵秉文“为人至诚乐易,与人交不立崖岸,未尝以大名自居”[9](P2429),这也正是其受到儒学士人拥护的缘由之一。然而此时吏风正盛,儒吏之间矛盾激烈之时受到攻击在所难免。这里除了“攻击者以科举利禄计、以升斗活妻子的观念来看待元好问和赵秉文等人”[5](P500)的原因外,更深层次地反映出朝廷胥吏与文臣之间的力量拉扯和政治斗争。所以,兴定五年的这次科举反映出:因宣宗重用胥吏而导致的胥吏之权扩大,从而严重挤压了文士的生存空间,进一步激化了二者之间的矛盾斗争,而杨奂落第只是当时政治斗争的生态环境在科举方面的反映。
故而我们看到,兴定五年的科考结果就是杨奂、麻九畴等士人落第。元好问虽中选亦弃去。郝经《遗山先生墓志铭》载元好问:“登兴定五年进士第,不就选,往来箕、颖间,数年而大放厥词。”[10](P1365)此外还有麻九畴,《归潜志》卷二载:“麻九畴知己……幼颖悟,善草书,能诗,好神童。……兴定末,试开封府,词赋乙,经义魁。再试南省,复然。声誉大振,南都妇人小儿皆知名。及廷试,以误绌,士论惜之。”[8](P14)麻知己试开封府夺魁,是最有实力和希望夺第的人选之一,结果却和杨奂一样,以误绌落第,之后“已而隐居,不为科举计。”[8](P73)赵秉文还专门作《答麻知己书》表达了他深深的同情及爱才惜才之心。
值得深思的是,在这次科举中,杨奂和元好问以及麻九畴都受到了赵秉文赏识,文人间的交情深厚。杨奂和麻九畴却都以误绌落第,元好问虽然中选,但却因受到朝中胥吏之攻击而失望弃归。而担任此次科举的阅卷官正是时为礼部尚书的赵秉文,同他政见颇为一致的翰林待制崔禧、归德治中时戬、应奉翰林文字程嘉善以及进士卢元、李君美都受到了牵连和处分。从中透露出宣宗朝整体形势的变化和当政者政治喜好的改变,使得儒士与吏员之间的紧张关系成为一种常态。在此背景下,不论杨奂的落第还是此后对补台掾的拒绝,包括其他士人被误绌落第,更深层次的原因,正是宣宗朝不利于儒士仕进生存之政治生态所结出的恶果。
(三)以杨奂为代表的儒士之心态转变
兴定五年的这次廷试,反映出宣宗时期在人才选拔方面的某些弊端和不利因素。虽然面临着内忧外患,“播越流离,官职多缺”的局面,而且“兵兴以来,百务烦冗,政在用人。”[4](P1196)但是在具体的选拔人才过程中,由胥吏与士人之间的长期矛盾导致的不良政治生态,在宣宗朝达到了一个高峰,故而切断了很大一部分儒学士人的入仕之途,造成了文士们对科举的失望和人才的流失。
在如此政治背景和选举制度下,杨奂兴定五年的这次廷试宣告失败。在历经前后五次的科考后,杨奂的心情必将是失望且失落的。而此时他与金朝廷的情感,也由最初的充满关切担忧的状态逐渐走向了离心状态。从同时期元好问的登进士第而不就选和麻九畴的落第隐归、不为科举计的选择上,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士人群体对朝廷选拔人才的失望以及与整个政府的隔阂心态。故而,杨奂表面上是因为顺其母“每以作掾为讳”的训戒,实际上是朝堂之上,胥吏当权,官宦之间互相攻怵,文士不得重用的局面所造成的。所以,杨奂在兴定五年的这次廷试落第,我们不能看作是杨奂的个人事件。
总体而言,在金末贞祐南渡日益衰落动荡的时局中,在胥吏与士人矛盾激化内耗的不利政治环境下,文人群体想要投身江山社稷,以“介入”的方式参与到金代政治建设之中的想法几乎化为泡影。而杨奂作为金元易代之际文人群体的代表之一,他的遭遇显然带有强烈的时代悲剧性色彩。以上是我们对杨奂中期的仕宦履历及心理状态做出论述。如果说此时他还处于对金朝政治失望且有所徘徊的状态,那么接下来发生在金末哀宗时期的上万言策一事,则是杨奂对整个金朝态度的一个大转折,也促成了他人生的另一种方向和选择。
三、万言书事件与文士心态的转变
(一)上书万言策之政治生态与权力格局
杨奂上万言书绝不是一时兴起之举,而是有着很深层的社会政治背景。想要对岌岌可危的金政权有所救治,体现了他作为金代成长起来的儒士还保有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早在宣宗朝时,金廷已经内忧外患。宋、元、夏的不断袭击攻打,再加上红袄贼、花帽军、黑旗贼还有各地土寇的侵扰,金政权风雨飘摇,急需要人才力挽狂澜。宣宗也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诏诸职官不拘何处出身,其才可大用者尚书省具以闻。”[4](P311)然而实际情况却是职官往往不赴任就职。“户部侍郎奥屯阿虎言:‘国家多故,职官往往不仕。乞限以雨季,违者无复任用。’上嫌其太重,命违者止夺三官,降职三等,仍永不生注。”[4](P312)兴定元年(1217)冬十月丁未“丙寅,订职官不求仕及规避不赴任法”[4](P331)。宣宗的应对策略是设定了“不赴任法”,通过降职、夺官等惩处手段来达到目的,从侧面反映出当时职官不就任的情况应该不止一两处。这显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出现这种职官不上任的原因是什么,显然宣宗并没有认识清楚。
刘祁在《归潜志》中,将金代明昌、泰和间(1190-1208)的养士用人之风与宣宗时对比,可谓抓住了问题的根本。“士气不可不素养,如明昌、泰和间崇文养士,故一时士大夫争以敢言、敢为相尚。……南渡后,宣宗奖用胥吏,抑士大夫,凡有敢为、敢言者,多被斥逐。故一时在位者多委靡,为求免罪,罟苟容。迨天兴之变,士大夫无一人死节者,岂非有以致之欤?”[8](P73)宣宗朝,吏权大盛,胥吏高琪手握大权。“抑士大夫之气不得伸,文法棼然,无兴复远略。大臣在位者,亦无忘身徇国之人,纵有之,亦不得驰骋。”[8](P137)《金史》列传四十九赞曰:“金自胡沙虎、高琪用事,风俗一变,朝廷矫宽厚之政,好为苛察,然为之不果,反成姑息。将帅鄙儒雅之风,好为粗豪,然用非其宜,终至跋扈。牙吾塔战胜攻取,威行江、淮,而矜暴不法,肆侮王人,此岂可制者乎?”[4](P2461)南渡后,有名的谏官如许古和陈规,在一次次切中时弊的箴诫中,真正能落到实处的没有多少,原因之一也正在吏权大盛,阻碍了宣宗的改革兴政之举。吏儒权利的失衡使得宣宗虽“知其为直,而不能用其言。”[4](P2418)“上初欲行之,而高琪固执以为不可,遂寝。”[4](P2410)权臣胥吏位高权重,此风俗之转变,甚而影响到普通民众对人生仕途的选择。刘祁在《归潜志》中言:“自高琪为相定法,其迁转与进士等,甚者反疾焉。故一时之人争以为此进,虽士大夫家有子弟读书,往往不终辄辍,令改试台不令史。其子弟辈即习此业,便与进士为雠,其趋进举止,全习吏曹,至有舞文纳赂甚于吏辈者。”[8](P72)由此可见吏权影响之大,也更从侧面体现出此时的儒吏矛盾之激烈。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下,士大夫无地位无权力,还受到胥吏的排挤压迫,士人势必同朝廷产生疏离。再加上金代又是异族统治, “偏私族类,疏外汉人,其权密谋谟,虽汉相不得预”[8](P137)。如此,汉人文士同金朝异族在本来就黏连不紧的情况下,就更加的隔离和疏远了。朝廷又特别保护女真人,尤其是宗亲贵族。女真人反过来压抑汉人,也是其政权失去汉人支持的一大原因。[11](P135-161)宣宗也只能感叹“天下之广,缓急无可使者,朕安得不忧?”[4](P342)在动荡混乱的战争局势下,金朝政权岌岌可危,汉族文士不愿出来做官则成必然。
再到哀宗朝,“元光二年十二月庚寅,宣宗崩,辛卯,奉遗诏即皇帝位于柩前。”哀宗完颜守绪初即位就有励精图治、振兴基业的理想。即位的第二日(壬辰)就“诏大赦,略曰:朕述先帝之遗意,有便于时欲行而未及者,悉奉而行之。国家已有定制,有司往往以情破法,使人罔遭刑宪,今后有本条而不遵者,以故入人罪而罪之。草泽士庶,许今直言军国利害,虽涉讥讽无可采取者,并不坐罪。”[4](P373-374)从这道诏书中,可以看到在金末面临蒙宋的巨大压力下,完颜守绪初即位不出三日,就下诏锐意改革,想从制度和用人两大方面入手,鼓励积极进言献策,即使“虽涉讥讽无可采取者,并不坐罪”。这也正是杨奂慨然草创万言策准备上书言事的一个契机,然而还没成行就作罢归乡里,一腔心血付诸东流。
(二)上万言书流产之原因
关于杨奂上万言书的事件,元好问在《故河南路征收课税所长官兼廉防使杨公神道之碑》中记载:“正大初,朝廷一新弊政,求所以改弦更张者,君慨然草万言策,诣阙将上之,所亲谓其指陈时病,辞旨剀切,皆人所不敢言,保为当国者所阻,忠信获罪,君何得焉?”“君知直道不容,即日出国门而西,教授乡里者五年。”[1](P455-456)明代学者冯从吾在《关学编》卷二也记载:“先生名奂,字焕然,号紫阳……金末。尝作《万言策》,指陈时病,辞旨剀切,皆人所不敢言者,诣阙欲上之,不果。”[12](P453)可见杨奂在面对哀宗朝准备一新弊政、励精图治的感召下,他仍旧一腔热血地草创万言策,指陈时病,希望能够对处于水深火热的金朝廷有所裨益。正如余英时所言:“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所恃的‘道’是人间的性格,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是政治社会秩序的重建。”[13](P119)然而,“道”与“势”的冲突和对立阻断了他的上言之路,儒家“士志于道”的政治使命感几乎无实现之可能。杨奂彻底失望归乡,开始了他五年的教授乡里生涯,直至金代灭亡都再没有出仕。
如果我们将杨奂上书万言策流产的原因归咎于受亲戚朋友的劝告,则太失之于草率和表象化。上文讨论过宣宗朝已经形成胥吏当权,汉族文士逐渐远离朝堂,职官不赴任的朝野局势。到了哀宗时期,权倾一时的胥吏高琪虽然被宣宗杀掉,但是“上下通风,只以苟安目前为乐,凡有人言当改革,则必以生事抑制”[6](P70)的朝堂风气仍然存在。正大九年(1232)又下诏求言“于东华门接受陈言文字,日令一侍从官居门待,言着虽多,亦未闻有施行者。盖凡得士庶言章,先令诸朝贵如御史大夫裴满阿虎带、户部尚书完颜奴申等披详,可,然后进,多为诸人革拨,百无一达者。”[8](P121)可见其实际收效微乎其微,几乎沦为一纸空文。而杨奂上书,来自族亲“保为当国者阻”[1](P455-456)的劝告,更能深层次地体现整个朝堂之上的颓败无能之气已经在民间迅速蔓延。
《金史·哀宗本纪上》中有一段很有意味的记载:“有男子服麻衣。望承天门且笑且哭。诘之,则曰:‘吾笑,笑将相无人。吾哭,哭金国将亡。’群臣请置重典,上持不可,曰‘近召草泽诸人直言,虽涉讥讪不坐。’”然而“法司唯以君门非哭笑之所,重杖而遣之。”[4](P374)从这段记载透露出,宣宗朝时期,朝廷不得士人之心,将相无人的局面到哀宗时无根本改观,甚至面临更为严重的局势。而胥吏朝贵内心虚颓,对皇帝则是采取掩耳盗铃之法,以此来掩盖政权核心深处的腐烂和摇摇欲坠。刘祁在《归潜志》中言及:“在位者临事,往往不肯分明可否,相习低言缓语,互推让,号‘养相体’。吁!相体果安在哉?又,宰执用人,必先择无锋芒、软熟易制者,曰‘恐生事’。故正人君子多不得用,虽用亦未久,遽退闲。宰执如张左丞行信,台谏官如陈司谏规、许司谏古、程、雷御史,皆不能终其任。”[8](P70-71)
皇权孱弱,大权都掌握在女真贵族和胥吏手中,而士人却被排挤出了权力中心,甚而罢官免职的也不在少数。刘祁在正大九年(1232)准备上书,求见口陈,结果翰林修撰李大节劝言:“今朝廷之力全在平掌、副枢,看此一战如何?”[8](P121-122)刘祁只能无奈作罢。奇士王郁京城被围时,同样上书不报。高永上书言事而不报。[8](P27)可见,杨奂上书一事还未成行就半路夭折的境遇并非仅他一人。而有研究者认为金末宣哀两朝,因女真作战能力的削弱和抗蒙形势的日趋恶化,而导致这一时期的汉族士人成为治理国家和抵御蒙古的核心,从而形成汉族士人的势力有加强的趋势。[14](P99)此结论没有详细个体的论证过程,而只是以蒙古入侵、女真作战势力削弱,必将倚重汉人的推论提出结论,似显草率。事实上,此时因蒙古的入侵,女真政权确实需要更多更有力的抵抗势力,但汉族士人并没有因此而进入权力的中心,一部分处于权力边缘的汉人儒士在此时期更多是以一种工具的角色出现。金末文士张德辉在向忽必烈阐释金朝灭亡的原因时评价道:“辽事臣未周知,金季乃所亲见。宰执中虽用一二儒臣,余则武弁世爵,若论军国大计,又皆不预。其内外杂职,以儒进者三十之一,不过阅簿书,听诵理财而已。”[15](P214)由此可见此时儒士文人群体地位之低下。
金哀宗完颜守绪即位后,在急剧恶化的政治生态背景下,儒学文士群体已经被排挤出权力中心。处于极度边缘化的以杨奂为代表的儒士群体想要通过上书言事来实现他们的政治秩序建设,已然失去了落到实处的基础。因此,杨奂、元好问、刘祁、麻九畴等人才会有相同的遭遇。这也正是杨奂上万言书流产的根本原因。
(三)杨奂后期心态之转捩

如果说杨奂早年还怀着儒士兼济天下、入仕治国的儒家理想,那么在宣宗朝政治生态的转变,儒士群体的仕进之路变得十分困难的情状下,此星星之火几乎快要被浇灭。杨奂兴定五年的科举失败即反映了这一时期整体政治生态的变化,此后拒绝台掾和科考仕进,也透露出此时儒士群体心态的转变。再到哀宗朝上万言书事件的流产,更是反映出面临金朝不断恶化的政治危局,儒士群体秉恃着儒家强烈的天下责任感和使命感,做出了最后的努力和挣扎,结果则彻底摧毁熄灭了以杨奂为代表的儒士群体对于金代的最后期许,撕裂了其对金王朝的家国感情。至此士人与金朝多数离心,此为金亡不远的一个信息。
余论
在外受蒙宋各方夹击,内耗于女真贵族与胥吏对汉族文士排挤斗争的金末政治生态环境下,杨奂仕途之路的失败代表了金末士人普遍的遭遇。文人群体在世宗、章宗“文治烂然,金朝之盛极矣”局面下形成的积极入世、充满儒家治国政治理想与抱负的心态受到挫伤。杨奂前后五次参加金代科考失败到上万言书事件的流产,是金末文人遭遇的典型事件。然而,在大蒙古国太宗窝阔台时期(1229-1240),杨奂就参加为了编定僧、道、儒户籍而举行的戊戌举选(1238),[16](P65)且两中赋、论第一,并受到了耶律楚材的赏识推荐,授以河南路征收课税所长官兼廉防使。《杨公神道碑》中记载:“君初莅政,招致名士,如蒲阴杨正卿、武功张君美、华阴王元礼、下邽薛微之、渑池翟致中、太原刘继先之等,日与商略,条画约束,一以简易为事。”[1](P456)此时杨奂才算是第一次真正地进入仕途,他也已经58岁,距金灭亡(1234)也仅仅4年。杨奂在此职位上,除了揽招了包括同乡张美君、王礼元等名士之外,还有河南、山西等地的士人一同参议政事。
如果我们将杨奂等人视为金代遗民,那么他们又具有不同于那些在王朝更替中持节守志而不愿与新朝合作的前朝遗老。他们生长在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更迭变换的时代,其本身那种强烈的“华夷之辨”的文化心理可能已经不复存在。杨奂在《正统八例总序》中说:“王道之所在,正统之所在也。”[1](P395)这种政治文化认同与郝经类似,郝经在《与宋国两淮置使书》说:“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10](P1365)他的正统论与杨奂可以说是一脉相传。所以,金末士人在经历了战乱纷争、流离失所的痛苦境遇后,面对新王朝的建立,在本就与旧王朝情感疏离的情况下,他们的情感心态更多的是一种时事风云变幻的历史沧桑感与人生无常的感伤,以及儒家那种救世济民的“家国天下”情怀,而没有太多传统道德观念中的抱节守志、不仕二姓的历史包袱。所以,在元世祖忽必烈潜邸时期,他知人善任,尤其重用汉族儒士,能行仁政,这极大地契合了金末文人心目中明君的特点。[17](P2)这种有利于汉族儒士发挥儒家经世致用、积极入世的政治生态,对金末士人来说是生命中难得的机遇。故而很快就形成了一批拥护忽必烈政权的金末汉族儒士群体,其中就有杨奂、赵良壁、许衡、郝经、董文用等人。他们在蒙古时期的宦海浮沉与文学创作,体现的则是一个新时代的政治生态与文学文化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