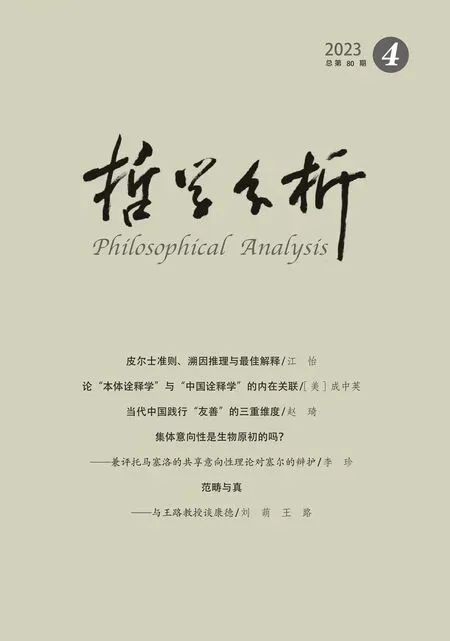康德与莱布尼茨主义形而上学的告别
——沿“实在性”问题而行的三步
谢裕伟
由莱布尼茨哲学奠定基础、沃尔夫和鲍姆嘉登等人加以体系化和学科化的“莱布尼茨主义”学院形而上学,是康德由之出身的哲学体系。先验哲学正是通过对莱布尼茨主义形而上学的多维度反思而逐渐建立的。本文拟以“实在性”(realitas)概念为线索来对康德这一反思的过程进行探索。这一概念的关键之处在于,它一方面是莱布尼茨主义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存在者的所有肯定的规定性都借助它来刻画,甚至连“上帝”概念也是从“全部实在性之大全”来理解的;而另一方面,康德的先验哲学也明确地以时空形式的“经验实在性”和先天概念的“客观实在性”等问题为其主要议题。就此而言,“实在性”概念可构成连接莱布尼茨主义形而上学和康德先验哲学的一个线索,线索的两端可用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①本文所引康德原文, 除《批判》 (以文内注形式标注为KrV 并配以1781/1787 版即A/B 版页码)以外,皆以文内注形式标注科学院版《康德全集》的缩写AA,列出卷次与页码(如AA 02: 72 即为《全集》第2 卷第72 页),不再另标出康德的名字。相关中译文参考了李秋零教授译注的《康德著作全集》 (第2 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不再逐一说明。中所提出的“本体实在性”与“现象实在性”(realitas noumenon/realitas phaenomenon)的概念对子来描画:“本体的实在性”指的是“以肯定的方式(positiv)展现在我们的纯粹知性中的东西”,它描述的是莱布尼茨主义形而上学所理解的实在性;而“现象的实在性”则是那些“以肯定的方式展现在我们的感官中的东西”②这一概念对子出现在KrV, A 264/B 320,并在康德的形而上学讲稿中大量使用(cf. AA 28:502, 560,634, etc.)。这里引述的是《形而上学讲稿L2》中更清晰和完整的表达(cf. AA 28: 560)。此处的“纯粹知性”亦可译为“纯粹理智”,它是一个更宽泛的用词,与传统哲学中的intellectus(理智)概念基本重合。康德也将“本体的实在性”称为“智性的实在性”(realitates intellectuales, cf. AA 28: 1162)。,它是被康德批判哲学承认为唯一合法的那种实在性。
不过,“本体实在性”与“现象实在性”之间看似轻巧的区分,实际上是在康德对莱布尼茨主义形而上学的复杂的反思过程中才得以逐渐成形的,其中涉及多种概念要素之间的纠缠和联系。但也正是这一复杂反思过程,使得康德最后能够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将“感性”看作知性之外的另外一个实在的而非虚幻的知识来源,甚至将其看作使先天概念获得其有效意义的唯一基础。本文将根据三个关键时间节点来剖析这一反思过程,并由此将康德“告别”莱布尼茨主义形而上学的历程分成三个层叠推进的步骤,即:(一)1762—1763年的“实存”(existentia)与“实在性”的分离和“实在冲突”(Realrepugnanz)概念的提出;(二)1768—1770年从实在性自身中区分为出一种“非智性的实在性”;(三)1775年前后的“实在性”之根据的“主体化”。本文第二到四节将详细阐释这三个步骤的基本内容。在此之前,笔者将在第一节中先对莱布尼茨主义形而上学中的“实在性”概念的基本含义和理论地位进行说明,以为后文研究作准备。③尽管国内学界对康德的“范畴的客观实在性”“自由的实在性”等问题讨论甚多,但直接针对康德“实在性”概念的研究尚不多见。国外学界较早注意到相关问题,如Anneliese Maier, Kants Qualitätskategorie(Berlin: Pan-Verlag, 1930);Heinz Heimsoeth, „Christian Wolffs Ontologie und die Prinzipienforschung Kants.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r Kategorienlehre“,in Heinz Heimsoeth, Studien Zur Philosophie Immanuel Kants.Metaphysische Ursprünge und Ontologische Grundlagen, Köln: Kölner Universitäts-Verlag, 1956, S. 57—61;Ludger Honnefelder, Scientia Transcendens. Die formale Bestimmung der Seiendheit und Realität in der Metaphysik des Mittelalters und der Neuzeit (Duns Scotus-Suárez-Wolff-Kant-Peirce), Hamburg: Meiner 1990,皆关注了康德的“实在性”这一范畴与莱布尼茨主义学院形而上学的思想关联。而海德格尔的《现象学之基本问题》 (丁耘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一章则明确将康德的“存在不是实在谓词”的论题与“实在性”问题联系在一起。就国内学界而言,伊凡(《论康德的实在性概念》,载《南京社会科学》2000年第12 期)较早探讨了“实在性”概念在康德批判哲学体系中的意义。近年来,国内学界对康德关于存在论上帝证明的批判的讨论也引发了人们从“实在谓词”“实在性之大全”等维度关注康德的“实在性”概念,典型的如李科政:《拨开“存在”谓词的迷雾——康德存在论题的第三种诠释》 (载《哲学动态》2020年第9 期);胡好:《康德对本体论证明的系统批判》 (载《哲学研究》2020年第11 期)、谢裕伟:《何谓“实在”?何以“必然”?——康德的“存在神论”批判及其形而上学要义》 (载《哲学研究》2022年第9 期)等。不过上述研究未就康德前批判时期对“实在性”问题的反思作充分探讨,而这正是本文的任务。
一、莱布尼茨主义形而上学中的“实在性”概念
在莱布尼茨主义诸家的形而上学著作中,康德最为熟悉的当属鲍姆嘉登的《形而上学》 (Metaphysica),因康德至晚自1755年起就研读该书,并以之为教本在哥尼斯堡大学讲授“形而上学”课程。在该书中,鲍姆嘉登为“实在性”一词提供了一个完整的且具有标准化意义的界定:
“通过规定而在某物中被设定(ponuntur)的东西,就是规定性(determinationes),而诸规定性中的一些是积极的和真正地肯定的(positiva, et affirmativa, quae si vere sit),就是实在性;而其他的那些真正否定的,则是否定性。”①Alexander Baumgarten, Metaphysica, Halle:Hemmerde, 41757, § 36. 强调为原文所有。之所以强调“真正”,是考虑到如下情况:有些规定性尽管在表述上是否定的,但它本质上是肯定性的,例如“无限”(unendlich)。康德也曾在这个意义上将“诸实在性”解释为“真正肯定性的谓词”(wahrhaftig positive Pradikäte,cf. AA 17:240)。
简言之,“实在性”指的是在事物中的真正肯定地被设定在事物之上的那些规定性。按照这个定义,存在物所具有的所有肯定性的普遍谓词——本质、属性、样态、关系等——都属于实在性。甚至整个形而上学的两条首要原则即“矛盾律”和“充足根据律”,其内涵与意义都是以实在性为基础,因为所谓“矛盾”指的是某种实在性与其反面(否定性)在同一个事物身上被设定时出现的冲突,而所谓“根据”,其实质则无非是一种实在性对另一种实在性的关系。这些都表明了“实在性”作为莱布尼茨主义形而上学的框架性基本概念的地位。不过,人们今天通常将“实在性”(或者英语的reality 以及德语的Realität)一词理解为“某物在外部世界中实际存在”或者说“外部世界本身实际存在”那样的意思,这样我们似乎很难理解为何“实在性”能够在存在论中具有上述那种的基础性作用,甚至无法理解鲍姆嘉登为何如此定义“实在性”。为此,我们有必要先对其词义作专门的辨 析。
“实在性”一词的起源一般追溯到邓·司各脱以及其同时代的根特的亨利(Henri de Gand, 1217?—1293),并主要通过司各脱而对后世哲学产生影响。据法国学者库尔廷的研究②Jean-François Courtine, “Realität”, in Historisches 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e, Bd. 8, Basel:Schwabe,1992,pp. 178—184. 笔者以下的论述从库尔廷的研究中借鉴了一些材料,特此说明。,该词从含义上并不追溯到realis 或者esse realis(“实在的存在”)——后者表示被设定在原因之外而实存,而是直接与宽泛意义上的res(事物)一词相关,是对每一个res(事物)本身的本质规定性(essentialitas)进行刻画的一个抽象概念。这样一种含义是在司各脱关于“形式规定性”(formalitas)的学说的语境中确立的。这里的“形式规定性”指的是那构成事物之本质的东西,它指向某种可以在理智中被把握的、用以阐明事物的本质或者“是什么”(quidditas)的统一而协调的规定。①参见Duns Scotus, Ordinatio II, dist. 3, par. 1, q. 6, n. 12, n. 15, in Opera Omnia, Vol. 7, Vatican City: Typis Polyglottis Vaticanis, 1973, p. 479, pp. 483—484。因而“实在性”在司各脱这里也可被看作“本质规定性”和“形式规定性”的同义词来使用,但相比之下它更强调与事物(res)本身的内在关联。此时,“实在性”并不具备任何独立于事物的存在,也不刻画任何存在论上的状态(是否现实存在),而是必须在事物中作为事物的实在性(realitates rei)而出现。
作为对事物的本质规定性的刻画,“实在性”可以并经常以复数realitates 的方式出现,因为事物的本质规定性并不止一种。故而同一个事物可具有多种实在性:“每一个共同的但可被规定的东西,就其是一个事物而言(quantumcumque sit una res),都可以在形式规定性上(formaliter)被区分为多种实在性,它们之间彼此不同。”②Ibid., p. 484.这些实在性都从其自身所特有的那种形式规定性出发,共同构成事物的完整本质。
司各脱对该词用法的显著影响体现在17 世纪哲学家米克雷利乌斯的流传甚广的《哲学词典》中:
实在性是事物中的某种东西。因此,在任何单个事物中都能够有多个实在性被设定(multas realitates poni)。此时,各种实在性应该与它们居于其中的那个事物(res)区分开来。于是,在人(homo)之中便包含了理智性、动物性和实体性等实在性。③Johann Micraelius, Lexicon philosophicum terminorum philosophis usitatorum, Stettin, 21662, p. 1203.
这段引文以标准化的方式呈现了当时人们对“实在性”一词的普遍理解。当然,在比照司各脱(主义)的“实在性”概念与后来的人(特别是鲍姆嘉登)对“实在性”的使用,我们会发现“实在性”一词的使用范围在逐渐变得宽泛:在司各脱主义者,甚至到笛卡尔、斯宾诺莎那里,“实在性”主要还是指那些本质性的规定性,或者至少是那些可以从本质中必然地推衍出来的规定性,但在鲍姆嘉登这里,则不仅本质和属性,而且包括样式和关系等,只要是正面的、肯定的规定性,都可被纳入“实在性”的指称范围内。这样一个变化很可能肇始于沃尔夫。在《自然神学》中,沃尔夫将“实在性”理解为“任何真正内存于某个存在物之中的东西”(quicquid enti alicui vere inesse intelligitur)。①Christian Wolff, Theologia naturalis, methodo scientifca pertractata, II, Frankfurt/Leipzig:Renger, 21741, § 5.按此界定,不仅本质,而且包括“实存”(existentia)都被理解为一种实在性,不管这种实存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
至此,我们大致上刻画了莱布尼茨主义学院形而上学对“实在性”一词的基本理解:“实在性”标识的是那些被设定在事物自身之上的各类肯定的规定性,它们要在理智中被把握。这实际上也是康德用“本体的实在性”一词所指称的东西,只不过他在大部分情况下并没有将所有这些含义维度都考虑在内。接下来,本文将按照三个关键理论步骤来分析康德在其“前批判时期”对这一实在性概念进行反思的思想过程。
二、步骤一:“实存”与“实在性”的分离和“实在冲突”概念的提出(1762—1763年)
康德迈出的第一步是将实存和实在性相分离,并引入“实在冲突”的观念。这是他经过“长期的反思”(AA 02:66)后在1762年完成写作的《演证上帝存有的唯一可能的证明根据》 (出版于1763年,以下简称“《证明根据》”)中提出,并在几乎同时出版的另一篇文章《将负量概念引入尘世智慧的尝试》中加以完善的基本思想。
在《证明根据》中,康德在反思过往上帝存在证明的过程中,提出了“存有”(Dasein)不能作为一种“实在性”来理解的思想。当康德明确地意识到“实有”(亦即“实存”“存在”②在目前的问题语境中,康德基本上将“实存”(Existenz)、“存在”(Sein)、“存有”(Dasein)三者当作同义词来使用。)无法作为一种“实在性”或者实在的规定性而被理解时,他与莱布尼茨主义的分离便正式开始了。当康德在《证明根据》中开宗明义地讨论何谓“存有”,并且在标题中直接提出“存有根本不是某一事物的谓词或规定性”(AA 02:72)时,他显然已经明确地将对实存(存有)与实在性之间的关系的反思作为自己哲学探索的一项基本任务。
康德看到,对于何为“实存”这一问题的讨论,直接关乎的是必然存有和偶然存有这一与传统神学的上帝证明有关的问题,而可惜的是,哲学家们在不考虑上帝存在问题时,对于“实存”或者“存有”这些语词,是以非常模糊的方式来使用的。由此,康德认为,必须从存在论的一般层面上澄清“普泛意义上的存有”(das Dasein überhaupt)。在这个要求下,康德直接提出了自己的命题:“存有根本不是某一事物的谓词或规定性。”这个命题显然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康德后来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的那个表达:“存在(Sein)显然不是一个实在的谓词。”(KrV, A 598/B 626)尽管康德此处还不包含后来表述中的“实在的”这一概念要素,但根据我们在本文第一节对“实在性”和“规定性”等概念在莱布尼茨主义存在论中的使用的分析来看,康德此时的表达显然完全可以替换为“存有根本不是某一事物的实在性”。
康德对“存在不是事物的实在性”这一思想的论证是从一个简单的思想实验出发的:对于某个具体的存在物,例如尤里乌斯·恺撒,我们去设想他的全部可能的谓词,但在这种情况下依然可以进一步设想,这个具备了所有这些规定性的存在物既可能实存,也可能不实存。当然,我们可以反驳说,对于人类理智而言,要设想某个具体存在物的全部可能谓词,是做不到的,由此而质疑这种思想实验的可行性。不过康德对此反驳早有准备,他引出上帝或者说一种神性的理智,它完全有可能认识这位恺撒的所有谓词,但即便如此,神性理智也仍然只把恺撒看作一个“仅仅可能的”、离开了上帝的那种创造的“决断”(Ratschluss)就不实存的东西。也就是说,即使对于上帝来说,仅仅从理智上把恺撒这一存在物的所有可能的谓词都设定在恺撒身上,也不足以让恺撒实存;这种实存依赖于理智以外的某种东西,也就是这里称之为“决断”的那种东西。虽然康德的这一想法与中世纪的神性理智和神性意志(创世的决断)之间的区分有着明显的关联,因而带有一定的神学色彩,尽管如此,康德的整个论证及其要素在哲学上还是清晰可解的——我们关于某个事物所能设想的一切实在谓述,都不能让这个事物具有实存。实存是有别的基础 的。
康德这一区分带来一个明显的效果,即除了与实在性相对立的“否定性”以外,还有一个东西是在“智性的实在性”所描画的范围之外的,是实在性所无法容纳的,那就是“实存”。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如何理解“实存”或“存有”?康德尝试用“绝对设定”(Position 或Setzung)的思想来对它进行解释:“存有是对一物的绝对设定,并由此区别于任何只有当一物与另一物相关时才被设定的谓词。”(AA 02: 73)这里的“物”(Ding)是宽泛而言的,指一切的“东西”(不一定是我们日常意义上的个别物,也可以指物的一些规定性),与经院哲学中的“存在物”(ens)是类似的。因而,康德所说的后一种谓词,实际上可以被理解一种“相对设定”,也就是在与某事物的关系中去设定某些东西,它通过判断的联结词“是”来表达。而“存有”表示的是一物的绝对设定,不关乎该物与其他东西处在什么关系中。相对设定和绝对设定的区分,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实在性”和“实存”之间的差异的描述。在前一种情况下,某个东西在与事物的关系中被设定,通过联结系词“是”而成了该事物的一种肯定的规定性,即“实在性”;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并不是任何别的东西,而是这个事物本身是被设定的,这时我们是在谈论事物的“存有”或“实 存”。
我们应该如何评估康德在1763年提出“实存不是实在性”这一命题时所取得的成果?“存有不是一种实在性,而是一种设定”,这一点是否就足以使康德与莱布尼茨主义形而上学区分开来?既然“实在性”是指一切“真正肯定的规定性”,那么,如果“实存”或“存有”并不是一种实在性,它到底又处在什么位置上?难道它竟是实在性的反面即“否定性”?这显然不是康德的意思。康德提出“存有是一种设定”,当然是为了让“存有”一词超出“实在性”和“否定性”所划定的范围。然而,到底这里的“设定”是什么意思?根据前文的探讨,在莱布尼茨主义形而上学中,任何“实在性”之为“实在性”,恰恰就在于它是被肯定地“设定”(ponere)在事物之上的东西。由此可见,仅仅用“设定”一词并不足以真正地将“存有”和“实在性”区分开来。这一点也不会因为康德在“设定”之前加了“绝对的”这一形容词而得到根本改善,因为“绝对的”和“相对的”在实际的思想运作过程中究竟有何不同,这一点并未得到充分的阐明。所以,康德在1763年“实存不是实在性”这一命题中所达到的成就是有限的,可以说,这时候他虽然明确地意识到要与莱布尼茨主义形而上学的思想方式拉开距离,但他此时还缺乏足够有力的思想手段和概念工具来对莱布尼茨主义的整体机制进行反 思。
尽管如此,《证明根据》一文中还出现了一些与“实在性”问题相关的思考,指向了另一个突破的方向。这便是康德在该文第一章的“考察三”的第六小节“必然存在物包含着最高实在性”中所提出的“实在冲突”(Realrepugnanz)的思想。这一思想主要针对传统形而上学中关于“实在性之大全”的概念。按照莱布尼茨主义形而上学的理解,实在性只与相应的否定性相冲突,而实在性之间是彼此没有对立的,都可以相互共存。这是因为,凡实在性都是真正的肯定,而肯定与肯定之间并无冲突。但康德则认为,各种实在性之间只是在逻辑上没有冲突(因而不会导致矛盾和绝对不可能性)而已,但并不排除它们之间可能存在“实在冲突”,他说:“任何时候,当作为根据(Grund)的某个东西借助一种实在的对立(reale Entgegensetzung)取消了别的东西的结果(Folge),那么就会出现实在冲突。”(AA 02: 86)康德的这一想法源于他对运动、静止和力的关系的如下思考:物体向一个方向运动的力和以同等强度向相反方向的趋势之间并不产生矛盾,它们完全可以现实地共存于同一个物体中,只不过其中一个力否定了另一个力的结果,使得在这个物体之上并不会出现两种真实的运动,而是出现了静止,而静止本身是不矛盾的,是可能的。不过,实在冲突虽然对于有限世界中的物体是可能的,但不应该出现在上帝或者绝对必然存在物之上,因为如果上帝包含了一些相互冲突的实在性,这种冲突的结果将会是一种阙失,而阙失是与最高实在性相矛盾的,有损上帝的完善性。而在康德看来,像“不可入性”“广延”等实在性,与“知性”“意志”等实在性之间是有实在冲突的,因而它们不应该都一起共存于上帝的概念之中——尽管它们或许可以一起共存于有限的存在者如人类身上。所以,所谓的“实在性之大全”的概念本身是不合法的。
在《将负量概念引入尘世智慧的尝试》中,“实在冲突”的思想得到了专门的探讨。在传统形而上学中,“否定性”要么被理解为“绝对的不可能性”,即矛盾,要么被理解为“实在性的阙失(privatio)”,例如,生病是健康的缺乏,黑暗是光明的缺乏。而在这篇文章中,康德提出要引入一种新的否定性概念,即标题中所说的“负量”(negative Größe)。这种负量“不是对量的否定(Negationen von Größe),而是某种自身真正肯定的东西(an sich selbst wahrhaftig Positives),只不过它跟别的东西有对立而已”(AA 02: 169)。康德举例说,像“不愉快”就不仅仅是快乐的阙失,而是我们内心直接感受到的一种实在的情感,是能够充当根据来发挥作用的。这种不愉快与我们的愉快情感之间构成的就是实在的冲突,二者尽管相互对冲,但可以共存而不导致矛盾。(Cf. AA 02: 180)
康德关于“负量”和“实在冲突”的思想,构成了对莱布尼茨主义形而上学的框架性概念“实在性”的一次冲击,因为围绕实在性概念而展开的一些关键思想要素如“实在性之间可共存”“实在性之大全”等都由此而被动摇了。当然,这还只是一种有限的冲击,因为实际上改变的并不是“实在性”概念本身——特别是,实在性中的“设定”还没有被触及,而只是对实在性之反面亦即“否定性”的一种新理解,而这一新理解的实质乃是在于对各种实在性与否定性相互共存的可能性与方式的一次新的探 索。
不过,我们也可以看到,康德在引入“负量”和“实在冲突”概念时所设想的许多内容,例如不同方向的力之间的冲突、不愉快作为一种实在的情感等等,本身就已超出了传统上用“智性的实在性”所能够刻画的范围;相反,它们都是必须在感性层面上来描述的。如果感性层面的一些内容可以在“实在冲突”的名义下谈论,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负量”,那么是不是也意味着,不仅只有理智性的东西可被看作“实在”的?接下来我们将看到,康德告别莱布尼茨主义形而上学的第二步,正是朝这个方向迈进 的。
三、步骤二:“非智性的实在性”的出现(1768—1770年)
第二个步骤是首先在18 世纪60年代末期开始明确出现的。在1768年,康德发表了一篇短文《论空间中方位区分的最初根据》 (Von den ersten Grunde des Unterschieds der Gegenden im Raume,以下简称“《空间方位》”)。康德在这篇文章中反思了其一贯坚持的与莱布尼茨立场接近的空间概念——后者否认绝对空间、认为空间只不过是事物之间相互关系,而对牛顿式的绝对空间的构想重新有所同情。学界对这篇文章多有关注,认为它体现了康德在时空问题上面临的困境,并由此导向了他在1770年的教职资格论文中区分可感世界和理知世界的形式及其原则的思想。①Cf. Klaus Reich, „Einleitung“, in Immanuel Kant, De mundi sensibilis atque intelligibilis forma et principiis,Hamburg: Meiner, 1958, S. XIV.在这篇文章中,康德通过一个关于“不全等对称物”(inkongruente Gegenstücke)独特的思想实验而质疑莱布尼茨的所谓相对空间的概 念。
所谓“不全等对称物”,指的是“一个与他物完全相等和相似(völlig gleich und ähnlich),尽管并不被[包围他物的]同一条边界所包围的有形体”(AA 02: 382)。康德所举的例子是人的手。人的左手和右手在大小、形状和结构上都是一致的,但它们占据的是不同的方位(即不被同一条边界所包围)。康德的思想实验的内容是:假设我们世界的第一个创造物是一只人手。这时,按照莱布尼茨的理论,唯一现实的空间就是这只唯一的手所占据的空间。尽管这只手“必定要么是一只右手要么是一只左手”(AA 02: 383),但由于只凭着手的大小、形状和结构是完全不能判定它到底是左手还是右手的,而且,目前唯一的空间就只有这只手所占据的那个相对的空间了,也无法从这个空间出发进行判断,这么一来,这只手将既适用于身体——当一个身体随后被创造出来的时候——的左边、也适用于身体的右边,也就是说,它究竟是一只左手还是一只右手,是“完全不确定的”。但这个结果是不合理的,因为这只手必然确定地要么是一只左手要么是一只右手。由此,康德推出结论说,莱布尼茨的相对空间概念是有矛盾的,它没有办法解释这个思想实验中的困难。因而,必须有某个“绝对的、原初的空间”作为左手和右手的确定区分的基础(cf. AA 02: 383)。
初看起来,在这篇文章中,康德似乎重新主张了一种牛顿式的绝对空间。不过很难说康德真的能够坚持这个实际上多年来都被他批判的观点。因为在这篇文章中,康德虽然指出了莱布尼茨主义的相对空间无法提供事物方位区分(如左手和右手之间的确定区分)的“内在根据”(AA 02: 382),但他同样没能表明,牛顿式的绝对空间是如何提供这种内在根据的。①Eckart Förster, Die 25 Jahre der Philosophie. Eine systematische Rekosntruktion,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22012, S. 20 指出了这一点。实际上,康德很快走向了莱布尼茨和牛顿以外的第三条道路,后者最终将康德引向了关于《纯粹理性批判》中时空作为认知主体的感性直观的形式的学说。在此,笔者暂不详细讨论康德在时空绝对性和相对性问题上的态度,而是进一步分析,康德在这篇文章中通过对莱布尼茨主义空间观的批判为他对“实在性”概念的思考提供了何种新的视角和资源。就此而言,这篇短文的最后一段话非常值得我们进一步深 思:
一位深思的读者不会——像几何学家所设想或者敏锐的哲学家们将之纳入自然科学的学科概念之中时所做那样——把空间概念视为一个单纯的思想物,尽管当人们想通过一些理性理念(Vernunftideen)来把握空间的那种对于内感官来说足够直观(anschauend genug)的实在性的时候,并不缺乏围绕这一概念的困难。但是,只要人们还想对我们认识的最初材料进行哲学思考,那么任何时候都会出现这种麻烦的[……] (AA 02: 383)
这段话中出现了很多后来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使用的概念,例如“单纯的思想物”“理性理念”“内感官”,不过我们不能简单地按照《纯粹理性批判》的用法来理解这些概念,毕竟这些同样也是当时学院中流行的说法。这里“单纯的思想物”指的是通过理智去把握的东西,并不是后来《纯粹理性批判》所批评的那种“空洞之物”;“理性理念”并不是后来说的那种关于“无条件者”的总体性概念,而只是理智进行思考时所使用的概念;“内感官”也不是后来那种以时间为其形式、与外感官和空间相对的东西,而是一种非智性的感受方式。在莱布尼茨主义的认识理论中,虽然有理智和感官的区分,但所谓感性的表象只不过是理智的模糊形态,可以通过反思、抽象等方式变得清晰,进而化归为理智表象。换言之,除了一些纯属理智的天赋观念以外,理智表象和感性表象之间并没有截然的区分,感性表象只不过是理智表象的初级样态。②典型的表述参见Alexander Baumgarten, Metaphysica, 41757, §§ 520—521。对莱布尼茨主义诸家在此问题上的观点的系统性概述参见Falk Wunderlich, Kant und die Bewusstseinstheorien des 18. Jahrhunderts, Berlin/New York: De Gruyter, 2005, S. 7—12, S. 18—68。因此,康德说,“敏锐的哲学家们”把空间概念视为一个单纯的思想物,也就是一个纯粹理智的对象,这是由于不管我们在感官中“模糊地”知觉到了空间的什么东西,一个纯粹的空间本身却始终是理智性的表象。而现在,不全等对称物的思想实验却透露了关键的一点:不全等对称物之间的区别没有办法通过任何理智性的、概念性的方式来把握,因为两个对称物在任何概念层面都是完全一致的,但二者又必然是有区分的,因此这个区分只能是某种非概念、非智性的东西。康德此时把这种非概念、非智性的东西称为“绝对的、原初的空间”,并表示对于这种空间的实在性,我们是“足够直观的”。这也就表明了,存在着某种在直观中可以充分通达却无法化归为理智表象的东西。尽管康德此时也承认,要去把握和言说这种纯粹直观性的、非概念的东西是很困难的,也没有能够明确地给予它一个理论位置。但是这种东西却显然通过不全等对称物的思想实验而以不容置疑的方式呈现出来了。
从这里显然可以引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感性的直观(Anschauung)与理智性的—概念性的思想(Denken 或Gedanke)之间是有根本区别的,而不只是层级上的区分。如果说,在莱布尼茨主义形而上学中,由于感性表象只不过是理智表象的初级形态,因而感性本身无法给出任何能够被称为“实在性”——也就是对物进行真正肯定性的谓述——的东西,一切实在性之为实在性都来自智性的“设定”,那么现在在《空间方位》一文的结论之下,就出现了一种无法通过理智来设定的“实在性”了。它之所以是一种“实在性”,是因为它确确凿凿地提供了空间中方位区分的“内在根据”。这种直观的或者感性的实在性,意味着一种不同于理智实在性、但仍然能够对事物进行肯定性谓述的规定方式,但在莱布尼茨主义形而上学的框架下,无法给这种实在性以相应的理论位置。
康德提出的这种新的、不同于“理智设定的实在性”的“感性实在性”,在其接下来的思想发展中逐渐地得到确证和展开。其1770年的教职资格论文《论可感世界与理知世界的形式及其原则》 (以下简称《教职论文》)就是这项工作的一个重要节点,因为在这篇以“说明感性知识与理性知识的区别”(AA 02: 395)为任务的论文中,康德给出了感性的领域和理智的领域各自的形式和原则,因而可以让两种“实在性”之间的区分具有实质性的内涵。这一点尤其对于“感性实在性”的问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在莱布尼茨主义的框架内,感性的东西仅仅只有依附性的地位,而不可能具有自身独立的“形式与原 则”。
在《教职论文》中,感性世界与理知世界的区分同时也被描画为现象与本体的区分,也就是事物“如其所显”(uti apparent)和“如其所是”(sicuti sunt)的区分。这种区分是以其各自的形式为基础的。现象或者感性世界的形式是时间和空间。这里的时间和空间并不是如《空间方位》所暗示的那样被理解为一种牛顿式的实在的绝对时空(cf. AA 02: 400),而是明确地被看作某种“观念性的东西”(ideale,AA 02: 403)和“想象存在物”(ens imaginarius,AA 02: 401)。据此,时空似乎不是什么实在的东西,但康德通过将时间和空间与理智性的东西相区分来展示出时空的独特性,因而能够将时空看作“极为真实”(verissimus)的东西(cf. AA 02: 401, 404)。在此,康德延续着《空间方位》中的思路,从时间中的差异和空间中的差异无法通过“理智”来把握的方式来论证这一区分。这里,我们仅以空间问题为例展示康德的基本论证思 路:
在一个给定的空间中,什么朝一边放着,什么转向对面一边,这不能以论理的方式(discursive)予以描述,也就是说,不能被任何敏捷的精神(mens acies)还原为理智的特征。即便是那些完全相似和相同、但并不全等(discongruentes)的固体事物,例如左手和右手(如果仅仅按照广延来设想它们)、由两个对立的半球构成的球面三角形,对它们来说,也还是有区别,由于这种区别,虽然它们能够通过一切以那些对于精神来说可以借助语言来理解的标志而得到表达的东西来互换位置,但它们的广延的边界却是不可能重合的。由此可知,这里只有通过某种纯直观(intuitio pura)才能说明这种区别,即不全等。①参见AA 02: 403。时间问题上的类似讨论参见AA 02: 399。
在这段引文中,我们再次看到了关于不全等对称物的说法,这一点表明了《教职论文》对《空间方位》的延续和发展。②实际上,这个例子还反复出现在康德后来批判时期的著作中,例如在《未来形而上学导论》 (AA 04:285—286)和《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始基》 (AA 04: 484)中,它始终作为直观——特别是空间——与概念性表象有根本区别的直接而明确的证据。康德想表明的是,空间的方位差别没有办法直接在理智中以论理的方式来把握,而只能通过直观的方式来加以说明。二者之间的区别是严格的,是根源上的差异,而不是像莱布尼茨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只是认识的不同层级。因此康德明确表示,像沃尔夫那样从模糊与清晰(confusus et distinctus)之间的那种“逻辑上的区别”来理解感性之物和理智之物的不同,是“不幸的”,因为这会导致现象与本体的区分被引导到一些“经常是鸡毛蒜皮的逻辑问题”之上(cf. AA 02: 394—395)。
虽然康德在1770年的《教职论文》中给了感性和直观的领域以专门的形式,使之能够从实质上区别于理智的领域,并在此意义上进一步推进了1768年的《空间方位》中关于“感性实在性”的新构想,但我们也必须看到,他在这里所能达到的成果是有限的,特别是就“实在性”问题而言,从根本上还不能与《纯粹理性批判》中的“先验感性论”相提并论。这主要是因为,此时康德还是认为,感性世界中的所有东西,包括其中最为“真实”的时空纯直观,在真实性上也无法与理知世界中的事物相比。根据他的说法,理知世界是实体的世界,它们在一个单一的神性存在根据的作用下结合在一种和谐的交互关系中(cf. AA 02: 407—408),这种交互关系是“唯一有资格叫作实在的(reale)的,并且由之出发,[本体的]世界整体也有资格叫作实在的,而不是观念性或想象的(ideale aut imaginarium)”(AA 02: 407)。这也意味着,理智或者理知世界中的东西的实在性才是根本的实在性,而感性世界中即使是最真实的东西也只不过是“观念性的东西”。二者仅仅是相互区分,各自处在自己的领域中,而毋需相互关联起来。在这种理解下,《教职论文》最终成为了“现象与本体”两个世界划分的柏拉图主义传统图景的回响。在这种图景之下,一种“感性的实在性”的地位是难以得到充分肯定 的。
综而言之,在《教职论文》中,虽然康德通过对时空本性的辨析而进一步肯定了感性之物的一种无法被理智之物所解释和取代的独特地位,但感性本身尚未被建立在一个确定的根据之中,因而“感性的实在性”只能停留为一种空疏的构想,无法得到独立的规定。这是康德走出莱布尼茨主义的第二步骤的限度所在。在第三个步骤中,康德将通过对实在性之根据的思考,为“感性的实在性”问题提供新的理论可 能。
四、步骤三:实在性之根据的主体化(1775年)
自《教职论文》发表以后,康德处在了一个长达十年有余的“沉默期”,在此期间几乎没有发表哲学类的文章,直至1781年其鸿篇巨制《纯粹理性批判》出版。目前,我们只能是依靠康德遗留下来的笔记手稿以及书信来探寻康德在这“沉默的十年”里的思想发展足迹。在这些文字中,写于1775年的被称为“杜伊斯堡遗稿”(der Duisburg’sche Nachlass)的一批笔记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也备受学界关注。①“杜伊斯堡遗稿”收录科学院版《康德全集》第17 卷第643—673 页。它们是编辑者在杜伊斯堡市的一家人手上取得的,故如此命名。
“杜伊斯堡遗稿”的主题是范畴以及与之相关的主体性问题,处于中心位置的是“统觉”(Apperzeption)的概念。②“统觉”概念由莱布尼茨所发明,其目的是通过“统觉”和“知觉”(perceptio)之间的区分来避免笛卡尔主义者因为混同了“知觉”和“思”(cogitatio,具体来说是指“我思”)而导致的形而上学谬误(参见《以理性为基础的自然与神恩的原则》,载《莱布尼茨后期形而上学文集》,段德智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232—233 页)。莱布尼茨主义者如沃尔夫、鲍姆嘉登以及沃尔夫的批评者克鲁修斯等都在“自我觉知”“自我意识”的意义上使用“统觉”这个概念(尽管有很多细节上的重要差异)。康德正是通过他们的著作而熟悉这一概念的传统用法的(cf. AA 16: 80)。此时,康德关于“统觉”概念的使用还不够清晰,有时接近于一种“对自身的理智性直观”,有时又接近于一种“内知觉”(区别于对外部事物的感知),这一点表明了康德此时还没有清楚地明白“统觉”——也就是后来他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称为“原初的、先验的统觉”的东西——到底是如何发挥其作用的。不过,在其中的一则笔记里,康德明确表达了他想借助这个概念达到的目 的:
所有被思考为感知对象的东西,都处在统觉(Apperzeption)的、亦即自我感知(Selbstwahrnehmung)的某项规则之下。显象(Erscheinung)因为被思考为包含在自我感知的某个标题之下而变成客观的(objektiv)。因此,领会(Apprehension)的那些原初的关系(ursprüngliche Verhältnisse)乃是对显象中的实在关系的感知的条件,而正是通过人们说“某个显象归属于这些条件”,这个显象便从这种普遍的东西出发而被规定和被客观地表象,也就是被思考。①参见AA 17: 658。引文中的德语单词拼写根据新正字法作了改正。
康德在这段话中表明,这个被他以“自我感知”来字面直译的“统觉”提供出一些规则,让显象置于这些规则之下,使得显象被思考和被规定,也就是被表象为“客观的”。这些规则便是所谓的“范畴”。康德此时主要是从“关系”的维度上来理解范畴的综合方式,因此他将统觉的这些作为规则的范畴称为“原初的关系”。之所以他在这里要将它们标识为“原初的”,是因为它们构成了客观性的依据,也就是使得单纯的显象能够成为“客体”。在这一意义上,康德说:“自我是一切客体中的原初者”(Ich bin das original aller obiecte, AA 17: 646)。他在同时期写下的笔记中也有类似的表达:“所有一切都建基在一个原初的知性之上,后者是世界的完全充分的根据(der allgnugsame Grund der Welt)。”(AA 17: 707)
尽管康德此时还没有清楚地阐释,统觉或者自我意识是如何达到这种为一切客观性奠基的目的的,甚至从其行文来看,似乎还只是停留在那种被他后来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称为“自我意识的分析统一性”(analytische Einheit, cf. KrV, B 133 f. n.)的角度来理解自我意识的运作方式,而未能达到“统觉的原初的综合统一性”的层次,但这种以统觉的运作为客观性奠基的基本思路,已经初具《纯粹理性批判》中“先验统觉”学说的雏形。而对于本文主题来说更为关键的地方在于,“杜伊斯堡遗稿”中的康德实际上第一次明确地将对事物和对象的一切客观规定性的“根据”回溯到了对显象进行认识的主体的自我意识机能之中,由此让显象处在一种“实在的关系”之中。这实际上体现了康德的一次明确的尝试:存在物的各种规定性的“根据”不再放置在该物的“本质”或某个原始存在者(上帝)之中,而是放置在自我之中——具体来说,是自我意识的运作之中。不过需注意的是,这里的“根据”概念并不是在传统的“充足根据”的意义上说的;换言之,自我并不是事物的一切规定性由之生成的根源,而只是让各种显象方式能够在一个客体之上被确定因而成为该客体的规定性的那个依据。因此,统觉和自我意识实际上是一种形式的、“客观性”上的根 据。
这一点具有关键意义,因为正是“根据”关系的这一变迁为“实在性”概念的变化提供了新的维度。其根本原因在于,莱布尼茨主义者所认为的使实在性被设定到事物身上的那个“根据”现在已经不再起作用了——事物的规定性不能仅仅通过事物的本质,或者通过一个原始存在物,而智性地以肯定的方式设定在一个存在物之上。在“杜伊斯堡遗稿”中,康德已经明确表示:“实在性必须在感觉中被给予。”(AA 17: 646)这意味着,实在性来自理智以外的其他地方——即“感觉”,而且“必须”如此。这是前面自1762—1763年通过引入“实在冲突”的概念而动摇了“实在性之大全”的传统观念,在1768—1770年又通过区分直观与概念而提出“感性的实在性”以来的思路的延续。现在,由于实在性在理智中得以被“设定”的那些“根据”关系被抛弃了,事物的规定性仅仅在其 “客观性”的这一形式上而不是在其内容上以“自我”或者主体为“根据”,那么实在性之为实在性,就必须以理智之外的东西——也就是感性和直观——为其根源。就此而言,虽然在“杜伊斯堡遗稿”中,康德关于感性和“感性的实在性”的谈论不多,但从学理上来看,将事物规定性的根据关系从“本质”和“上帝”那里抽离出来,确实为“感性的实在性”的最终确立提供了充分的理论空间。对于康德走出莱布尼茨主义形而上学的过程而言,这一步可以说是至关重要——尽管直到1781年《纯粹理性批判》出版,这条道路才到达其终 点。
五、结语
至此,我们考察了康德沿着“实在性”问题而逐渐与莱布尼茨主义形而上学拉开距离的思想过程,指出了他反思莱布尼茨主义“智性的实在性”概念的三个主要的理论步骤及其意义:首先,通过将“实存”或“存有”置于实在性的范围之外,康德打破了“智性实在性”对存在物的所有谓述领域的统治,同时也为将来先验哲学在“现实性公设”(Postulat der Wirklichkeit)的名义下将“存有”与经验性的“感觉”(Empfindung)关联起来的做法提供了准备;此外,在同一时期所提出的“实在冲突”的思想,也指引了一种从感性的角度思考实在性问题的方向;其次,通过指出空间(进而还有时间)不被理智和概念所完全规定这一点,康德为直观和概念作为两种不同知识来源的区分作了准备,并借此提出了一种不同于“智性实在性”的“感性实在性”的思想;最后,通过打破事物的“本质”以及上帝作为实在性之根据的传统设想,并将显象的客观性的根据奠立在主体自我意识运作之上,康德为其后来的先验哲学将显象的实在内容的来源和根据放置在感性能力之上的工作准备了相应的理论空 间。
不难发现,康德沿着实在性问题告别莱布尼茨主义的过程,就是一个逐步与“智性的实在性”(本体的实在性)脱离而建立“感性实在性”的原则与根据的过程。先验哲学对“实在性”的理解,便是以“感性实在性”的构想为基准的,如《纯粹理性批判》中所谈的时空的“经验性的实在性”(KrV, A 28/B 44, A 35/B 52)、先天概念的“客观实在性”(KrV, A 156/B 195),甚至“实在性”范畴本身——就其有意义地得到运用而言,都以“感性的实在性”这一基本思想为出发点。可以说,从感性能力出发来理解实在性之为实在性的本性和根据,正是先验哲学在思想模式上区别于莱布尼茨主义形而上学的主要特征之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