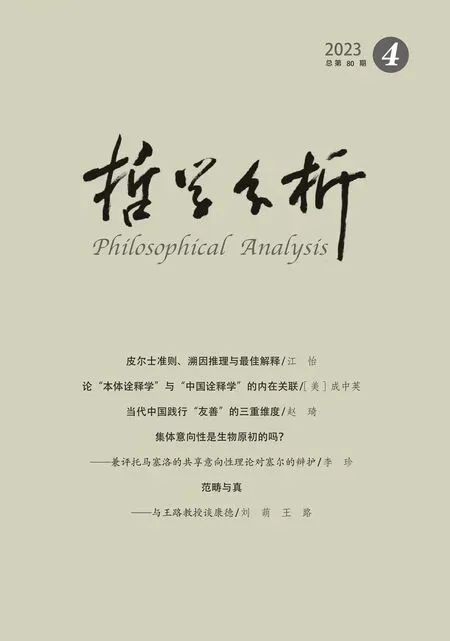超人类主义与人类物种同一性
钟焕林
一、引言
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一种被称为“超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的思潮在西方国家逐渐兴起。这一思潮并非一种统一的和固定的理论或观点,而是一种“被宽泛定义的思想运动”①Nick Bostrom, “In Defense of Posthuman Dignity,” Bioethics, Vol. 19, No. 3, 2005, p. 202.或“生命哲学”②Max More, “The Philosophy of Transhumanism,” in Max More & Natasha Vita-More (eds.), The Transhumanist Reader, New York: Wiley-Blackwell Publishing, 2013, p. 3.。这种生命哲学关注人的完善和未来,并主张在人类所珍视的价值引导下,使用科技手段增强①所谓“增强”,是指通过科学技术(特别是生物技术)的应用对人的一种有意的干预,其旨在以直接作用于人体的方式,改善大多数或所有正常人通常都拥有的能力,或创造一种新的能力;参见Allen Buchanan,Beyond Humanity?: The Ethics of Biomedical Enhance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23。值得注意的是,也有学者主张通过与“治疗(treatment or therapy)”的对比来定义“增强”(其背后的目的是反对超出治疗限度的对人体的增强);但正如很多学者所指出的,“增强”和“治疗”的区分是缺乏充分根据的;参见 David B. Allen, Norman C. Fost, “Growth Hormone Therapy for Short Stature: Panacea or Pandora’s box?”, The Journal of Pediatrics, Vol. 117, No. 1, 1990, p. 18; 吕克·费希:《超人类革命》,周行译, 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年版,第7 页。人的体力、智力和情感能力,减轻不必要的痛苦,延长人的寿命,以超越人各方面的生物极限和现有存在形式。②例如,通过基因工程修复人类基因中的缺陷来增强人的体力、智力和情感能力,并改变由“自然彩票”的随机分配而来的人类个体间自然禀赋的不平等;使用纳米技术修复或合成人体组织和器官,克服疾病和衰老过程;用再生医学帮助肢体残疾患者重获新生;甚至通过“上载(uploading)”来实现永生。
超人类主义这种对超越的追求,旨在从根本上改善人的境况,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存在性风险(existential risks)”,并尽可能地为未来生活提供保障和拓展可能的生存环境。这种超越并非宗教式的,它并不预设任何超自然力量或彼岸世界,而是肯定人的地位和价值,特别是肯定人自我完善的自由和能力;因此,通常被认为继承了人文主义强调理性、强调进步、强调自我塑造和依靠人自身的力量建立更美好未来的优秀传统③参见Nick Bostrom, “A History of Transhumanist Thought,” Journal of Evolution and Technology, Vol. 14,No. 1, 2005, pp. 1—25; Max More, “The Philosophy of Transhumanism,” in Max More & Natasha Vita-More(eds.), The Transhumanist Reader, New York: Wiley-Blackwell Publishing, 2013, pp. 3—17;吕克·费希:《超人类革命》,周行译, 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年版。,并受到普遍欢迎——毕竟有谁不想变得更健康、更聪明、更美丽,并拥有更好的感知能力和更长的寿命呢?更不用说在极度痛苦折磨下的人们对改善自身境况的渴 望。
超人类主义的目标的实现十分依赖技术的进步。现代高新科技的蓬勃发展,特别是生物技术的进步,让我们看到了超人类主义的主张由理想变成现实的可能性,但也正是这些能够直接增强人体的技术的进步,让人们感到担忧。其中忧心尤甚者被称为生物保守主义者(bio-conservatives)。在他们看来,作为人(being human)是一种道德义务。他们担心增强技术(例如基因技术)的运用会打破物种之间的界限,并带来人类本质的改变,而这种改变是“对我们现有的物种同一性(species identity)④在哲学话语中,一物的本质通常被认为是使该物成其为该物并区别于他物的东西,而一物是其自身而非他物的这种性质(或者说,一物与且只与其自身之间才具有的那种关系)即是该物的同一性,因此一物的本质决定了其同一性。如果承认有所谓人类的本质,那么人类的本质的改变意味着人类将不再成其为人类(或者说存在的将不再是人类)。换言之,这意味着人类物种同一性的丧失,即人类这一物种的灭亡。的背离”⑤John Harris, Enhancing Evolu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39.。换言之,他们担心“极端的增强有把我们变成完全不同的存在者的危险,以致我们将不配再被称为人类。它将使我们成为‘后人类’”①Nicholas Agar, Humanity’s End: Why We Should Reject Radical Enhancement,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2010, p. 2.。
本文旨在回应生物保守主义者的这种担忧并力图证明:超人类主义的方案并不会危及人的本质和人类物种的同一性;并且,对人类个体的同一性和道德地位而言,人类物种的同一性(或者说我们的物种成员身份)并不重 要。
二、超人类主义的计划不会损害人类物种的同一性
生物保守主义者担心增强技术会改变人类的本质,并直接导致人类的灭亡。例如:乔治·安纳斯(George Annas)、洛里·安德鲁斯(Lori Andrews)等学者认为,“生物保守主义”一词应当严格地从字面上去理解,其真正的含义就是要保存和守护人类这一物种,使其免于灭亡。②参见George Annas et al., “Protecting the Endangered Human: Toward an International Treaty Prohibiting Cloning and Inheritable Altera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Law & Medicine, Vol. 28, No. 2—3, 2002, p. 173。在他们看来,克隆和对人进行可遗传的基因更改是一种特别形式的“反人类罪”。他们说:“通过将人类的进化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并将其引向一个有时被称作‘后人类(posthuman)’的新物种的发展,这些技术可以改变人类自身的本质。”③Ibid., p. 153.无独有偶,福山也说:“当代生物技术带来的最大威胁是,它可能会改变人类的本性(human nature),从而使我们进入‘后人类’的历史阶段。”④Francis Fukuyama, Our Posthuman Future: Consequences of the Biotechnology Revolution,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2, p. 7.
我们认为,虽然极少有超人类主义者主张对人进行克隆,但安纳斯和福山等人的观点无疑代表了生物保守主义者的典型看法和深层担忧——对人体的增强将改变人类的本质,进而直接导致人类物种的灭亡和新物种的产 生。
准确地说,一个事物的本质是无法改变的。所谓“改变一个事物的本质”只是一种不严格的表达,它的真正意义是使该事物不再存在,并让另一个本质上不同的事物取而代之。因此,我把生物保守主义者的上述担忧改述为:由于增强对人的改变,人类将演化成不再是人的新物种(或“后人类”);换言之,人类将丧失其物种同一 性。
为了回应这种担忧或反驳,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到隐藏在这种担忧背后的如下预设或信念:每一个物种都有固定的、唯一的本质,物种之间存在基于自然而非人为建构的、清晰的、固定的界限。简而言之,每个物种的同一性是确定的。但是,“物种”概念出了名地难以定义(包括不能从基因的角度来定义)。①参见Jason S. Robert, Françoise Baylis, “Crossing Species Boundarie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Bioethics, Vol. 3,No. 3, 2003, pp. 1—13; Steve Clarke, Julian Savulescu, “Rethinking our Assumptions about Moral Status”,in Steve Clarke, Hazem Zohny & Julian Savulescu (eds.), Rethinking Moral Statu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1, pp. 1—19; Marc Ereshefsky, “Species”,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Summer 2022 Edition, Edward N. Zalta (ed.), https://plato.stanford.edu/archives/sum2022/entries/species/。正是因为这种困难,“言必称人性”的福山不得不用一个未知数“X 因子(Factor X)”来指代人性或人的本质②参见 Francis Fukuyama, Our Posthuman Future: Consequences of the Biotechnology Revolution, pp. 149—150。——这颇具讽刺意味。在人类和后人类的物种界限确立起来前,我们没有理由说人类被增强后就已然是一个新物种 了。
实际上,任何物种都不是一成不变的,生物的演化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生物的演化是一个过程或连续体(continuum),一切生物都从其他物质或生物演化而来,经由变异和自然选择又演化成其他生物。一个物种与其说是生物界在共时性上的一个横截面的一部分,不如说是众多相互交织的演化过程中的一个演化过程的历时性阶段。从一个演化过程或连续体中任意截取一段称为“人类”,并把另一段称为“后人类”,难免失之武断。“人类”这一概念具有很大的弹性,这个概念至少在理论上能够容纳对人的生物性增强。从早期人类到今天的人类,人类的情况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这并不能否定他们都是人类。同理,人类中的被增强者和未被增强者,虽然存在十分大的差异,但仍然可以同属人类。当然,人类物种的同一性能够耐受住多大程度的增强还有待进一步探讨。但是,问题并非像生物保守主义者们想象的那样简单,我们绝不能一概而论地说对人类的增强必然会损害人类物种的本质和同一 性。
退一步讲,即使我们承认人类有固定的本质和物种同一性,超人类主义的计划的实施也未必会伤及人的这种本质和同一性。生物保守主义者要保证他们选定的人的本质特征被人类普遍共有(如果这不是不可能的),那么他们就只能把这些特征锁定在类似于理性、道德选择能力、语言、社会性等被人普遍例示的特征上。③Ibid., p. 171.也就是说,他们只能给人的本质一个十分宽泛的定义。对人的增强并不会伤及这个被宽泛定义的人的本质,例如:认知能力增强带来的结果是人的理性能力的提高,而不是对这种据称是人的本质性能力的损害。如果超人类主义的计划并不会损害人的本质,而是有利于人的本质的保存,那么它恰恰是巩固了人类的物种同一性,而不是相反。并且,由于各方面能力的增强,人类将能够更好地应对各种对人类生存造成严重威胁的风险,进而保存人类这一物 种。
再退一步讲,即使对人体的增强和改造势必会伤及人类的本质,这也需要在种群尺度上大规模地对人类个体进行增强才会威胁到人类物种的同一性①参见Norman Daniels, “Can Anyone Really Be Talking About Ethically Modifying Human Nature?”, in Julian Savulescu and Nick Bostrom (eds.), Human Enhance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41。;否则至多只会产生一些新的非人类个体、人类亚种或新的非人类物种。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物种同一性的丧失或整个人类的灭亡;也就是说,即使产生了不再是人类的“后人类”,后人类的出现和存在本身也并不意味着不再有人类存世,后人类和人类有可能共 存。
但很多生物保守主义者并不这么认为,他们担心世界将从此分裂为分别由被增强者和未被增强者构成的两个彼此对立的集团,这两个集团的对立和冲突最终将导致人类的灭亡。例如:安纳斯等学者认为,为了使人变得更好的基因修改一旦成功并广泛实施,“一个新的物种或人类亚种就会出现。这个新的物种或‘后人类’,可能会把旧有的‘正常’人视为劣等人甚至野蛮人,并认为可以奴役或屠杀他们。另一方面,那些正常人可能会把后人类视为威胁,并且如果做得到的话,可能要在后人类杀死或奴役自己之前先发制人地杀死他们。最终,正是这种可预测的大屠杀的可能性,使能造成物种改变的实验成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使不负责任的基因工程师成为潜在的生物恐怖分子”②George Annas et al., “Protecting the Endangered Human: Toward an International Treaty Prohibiting Cloning and Inheritable Alterations”, p. 162.。
这与担心整个人类不知不觉地逐渐演化为后人类不同,而是担心人类和后人类之间的冲突直接导致人类的灭亡。他们担心的这种可能性值得我们严肃对待;但是,他们对后人类未来的构想过于简单化了。鉴于超人类主义尊重每个人选择自身存在形态的自由③参见Anders Sandberg, “Morphological Freedom—Why We Not Just Want It, but Need It”, in Max More & Natasha Vita-More (eds.), The Transhumanist Reader, New York: Wiley-Blackwell Publishing, 2013, pp. 56—64。,如果我们暂时假定对人的增强必然会损害人类的本质,那么当超人类主义的计划被实施,在人类之外肯定会出现因自主增强而产生的新物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世界将分裂为两个对立的物种或集团。基于一种简单的二分法把整个世界划分为两个对立的物种的做法,得不到经验证据的支持。这一点已有论者指出,例如:尼克·波斯特洛姆(Nick Bostrom)认为,跟未被增强的人的能力的自然差别类似,被不同程度增强的个体在能力方面构成一个连续体,世界因此分裂成截然对立的两极的情况不太可能出现;并且,即使在今天,原则上人口中身高较高的90%的人完全有能力消灭或奴役另10%的人,但在一个被很好地组织的社会里这并未发生。④参见Nick Bostrom, “In Defense of Posthuman Dignity”, Bioethics, Vol. 19, No. 3, 2005, pp. 207—208。我们赞同波斯特洛姆的上述看法。安纳斯等生物保守主义者构想的这种情况并非什么“可预测的可能性(predictable potential)”,而只是一种未能得到证据支持的抽象的可能性或臆 想。
另外,即使真的出现非人类物种,这些物种也极有可能不止一种。换言之,后人类也可能有很多种。这些新物种(以及人类)将不仅在某些能力上表现出不同程度,还将彼此拥有完全不同类型的能力和存在形态。如果说波斯特洛姆主要是通过指出能力的更多“程度”来反对生物保守主义者对世界的简单化的二元划分,而我在此要强调的则是我们还可以通过指出更多的“维度”(即更多种类的能力和存在形式)来反对这种对世界的简单化。如果对人类进行增强的最终结果是一个人类和后人类共存的世界,那么那个世界也将是一个更加多元的世界,而不会是个两极对立的世界。智能生物将以多种形态存在,而不仅仅是以人这种形式存在,他们甚至不再是生物有机体。他们的能力、需求、利益和生存条件也将与我们的不同,并呈现出极大的多样性。多样化的后人类物种将与人类千差万别,例如:他们可能不会再追求功名利禄,没有饮食需要,甚至可能不需要呼吸,生活在水中或另外一个遥远的星球。这种多样性将更有助于后人类与人类的和平共处。人们常常以为一个趋同的世界更有利于稳定,但实际上一个多元互补的世界才可能真正和谐。彼此相同的诉求可能导致冲突,因为能满足这种诉求的资源是有限的,但多样化的诉求将避免这种冲突。人类和后人类可以长期共存,直至由于自然演化过程或其他原因人类退出历史舞台为 止。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超人类主义中有一个被称为“生物控制超人类主义”的激进的流派。这一流派与“生物性超人类主义”不同,它认为当前人类的保存和完善并非目的,创造一个新的超级物种才是目的。这一激进的流派含有一个人机混合的控制论计划,是真正意义上的后人类主义。这种后人类主义不仅依赖生物科学与技术,更重视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的运用,其目标是创造超越生物人的几近永生的超级人工智能物。①参见吕克·费希:《超人类革命》,周行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年版,第38—43 页。
但是,即使这种激进形式的超人类主义也不仇视人类,且尊重每一个人选择自身形态的自由,它在理论上允许人类和后人类的共存。“后人类(posthuman)”的概念跟“死后的(posthumous)”没有关系,它并不意味着人类历史终结之后的存在,而仅仅意味着后于人类产生的智能物。②参见 Humanity+ (World Transhumanist Association), “Transhumanist FAQ”, https://www.humanityplus.org/transhumanistfaq,访问日期:2023年6 月6 日。也许未来有一天某种超级智能生命形式将产生,他们的存在可能会构成对人类的“存在性风险(existential risk)”。但是,首先,这多半不会是因为他们像生物保守主义者说的那样认为人类是劣等的或野蛮的,可以被屠杀或奴役。他们可能既不爱人类,也不恨人类,而只是不在乎人类,就像我们不在乎一块没有智力的石头一样。①参见Eliezer Yudkowsk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s a Positive and Negative Factor in Global Risk”, in Nick Bostrom and Milan M. Ćirković (eds.), Global Catastrophic Risk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308—345;Nick Bostrom, Superintelligence: Paths, Dangers, Strateg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其次,他们是否真的会对人类造成威胁还不能断定。超人类主义者已经意识到超级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风险,在未有安全和妥善的方案之前超人类主义者并不主张贸然行动。②参见Humanity+, “Transhumanist Declaration (2012)”, in Max More & Natasha Vita-More (eds.), The Transhumanist Reader, New York: Wiley-Blackwell Publishing, 2013, pp. 54—55。并且,超级智能生命的时代还未到来,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只能在发展中解决,我们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未来,不忽略可能的风险,也不错过可能的机遇。超人类主义也不是一个具体的行动指南,而只是一个框架性的构想,它将不断地进行细化和完善。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需要更强的自身能力来解决这些问题和应对各种风险,而对人的增强是达到这一目的有效方 式。
生物保守主义者可能要反驳说,虽然后人类灭亡人类的可能性比较小,但这种风险毕竟存在,为什么要冒这个险呢?对此,我们要说的是,绝对安全的事情是没有的,世界本身充满着不确定性。能够造成人类灭亡的风险远不止对人体进行增强这一种。天文灾害、地质灾害、气候变暖、全球性传染病、大饥荒和核战争等等,都可以造成人类的毁灭。人类如果不增强自身、不断超越自身极限并提高应对风险的能力,将难以处理这些已知的和尚未知的存在性风险。如果我们不是谨慎但又勇敢地向前走,我们将有可能错失适应变化和战胜危险的机会。更不用说,对于处在痛苦中的人而言,我们错过的每一天都是莫大的损 失。
我们看到,即使我们为了论辩的需要一再让步,仍然不能得出超人类主义计划的实施必将导致人类灭亡的结论。实质上,我们甚至可以论证超人类主义的实践有利于人类物种的保存,因为对人的增强有利于提高人类应对各种已知的和尚未知的各种“存在性风险(existential risk)”的能力。总之,对人的谨慎的生物性增强导致人类灭亡的可能性很小;即使对人的增强促生了后人类,后人类的存在与人类的保存也并不冲突,因为新物种的产生和存在并不需要以一个旧物种的灭亡为前 提。
三、人类物种的同一性并不重要
我们知道,在浩瀚的宇宙中,人类的存在极其偶然和渺小,并且按照自然规律,任何一种生物最终都要灭亡。那么我们不禁要问,生物保守主义者为什么执着于保存人类这一物种?我们为什么一定要作为人而存在,如果我们虽然不再是人类却在各方面胜于人类?简而言之,人类物种的同一性为什么这么重要?
这显然不能仅仅从生物多样性或生态保护的角度去理解,否则我们只要给生物保守主义者划定一个自然保护区(可能是整个地球)就可以了,而且我们只需要谈生物学或动物行为学就够了,而不用涉及复杂的哲学争 论。
生物保守主义者的主张和诉求背后显然另有原因,即他们心中的如下信念:第一,我们都是人,人类整体的灭亡意味着每个人类个体的死亡,但这并非我们所愿——每个人都希望他那个最亲爱的自我能够继续存在;第二,“人”或“人类”这个概念具有道德意义,人是万物之灵长,正是我们的人类物种成员身份赋予我们独特的道德地位和价 值。
现在让我们先来讨论第一个原因。人们对人类物种同一性的关切,有时是源自对全人类命运的考虑,“但我们对同一性的兴趣也是出于更加个人化的原因。因为我们并不是一般地以人的方式去生活;而是作为我们自己,作为个体,去愿望、行动、繁荣和衰落”①The President’s Council on Bioethics, Beyond Therapy: Biotechnolog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Washington,DC: PCB, 2003, p. 293. http://hdl.handle.net/10822/559341,2023-06-06.。美国前总统小布什的生物伦理委员会(主要由生物保守主义者构成)的上述看法表明,他们对人类物种同一性的重视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人类个体同一性②在本文中我们用“个体同一性(identity of individuals)”表示(人类或非人类)个体的同一性,以区别于“人的同一性(identity of human beings)”和“人格同一性(personal identity)”。后两个术语通常被不加区分地被使用(并用“personal identity”一词指代),但实质上二者是有区别的:“人格同一性”这一术语背后隐含着一个关于人的形而上学预设,即把人(human being)看作在本质上是(拥有)人格者(person),而不是人类动物(human animals);但“个人同一性”这一个术语没有这种预设,它在形而上学上是中立的,只表示人的同一性,而不管人是否在本质上就是人格者。的关切。这很好理解。人们担心人类的灭亡,往往是因为担心作为人类个体的“我”的灭亡。即使不是担心自我的灭亡,也是担心其他人类个体的灭亡,因为人类无非是人类个体的集合。也就是说,在生物保守主义者对人类物种同一性的重视背后,隐藏着他们的如下看法:人类整体的灭亡意味着每个人类个体的死 亡。
在有的情况下,他们的这种看法是没有问题的。比如说,由于宇宙中某种有害射线暴的强烈辐射,地球上的所有生物被瞬间灭活——在这种情况下,整个人类的灭亡无疑意味着每个人类个体的死亡。也就是说,此时人类物种同一性的丧失意味着所有人类个体同一性的丧失,因为前者以后者为前 提。
但是,人类物种的灭亡本身并不蕴含着每个人类个体的死亡。认为前者必然蕴含后者的观点,实际上预设了(人类)个体同一性的保存必须以其物种成员身份的保有为前提。换言之,它预设了人在本质上就是人(homo sapiens)。①参见Mark Walker, “Cognitive Enhancement and the Identity Objection,” Journal of Evolution and Technology,Vol. 18, No. 1, 2008, p. 112; Allen Buchanan, “Human Nature and Enhancement”, Bioethics, Vol. 23, No. 3,2009, p. 144 (note 7) 。但这个预设是十分可疑的,因为一个个体有可能改变其物种成员身份,即它有可能先归属于某一个物种随后又变成另一个物种的一员。通俗地说,人类的灭亡并不意味着作为人类个体的“我”不能从中幸存,因为“我”可以不是人(例如可以变成后人类)。也就是说,人类物种的灭亡这一事实本身只意味着不再有“人”存在,而不意味着一个人类个体不能变成其他物种的成员而仍然是其自身。②反之亦然。即使所有人的个人同一性同时丧失,也不意味着整个人类物种同一性的丧失。一个人的“个人同一性”的丧失意味着不再有此人,但不意味着不再有人(即某人的“个人同一性”的丧失不意味着其“个体同一性”的丧失)。一个个体有可能先后作为不同的“人”存在。简而言之,没有人不意味着没有“我”(虽然我不再是人),没有“我”也不意味着没有人(虽然那个人不再是我)。
这种观点得到我们的直觉和经验的支持。在神话故事(例如《聊斋志异》和《西游记》)中,某一个体转变其物种成员身份仍保持其同一性的情节比比皆是:一只狐狸、一条蛇、一只乌龟或一只鸟,甚至一个琵琶或一株牡丹花,都可以修炼成人而仍不改其为同一的个体;反过来,一个神或得道的人可以变鸟、变蛇、变鱼,甚至变成一座庙。我们虽然认为这些故事和情节不是真的,但很自然地接受了这类虚构故事,我们并不觉得这是完全不可想象的。这即是说,我们的直觉并不反对个体事物改变其物种成员身份的可能 性。
并且,经验事实也不反对这种可能性。例如,当一只蝌蚪逐渐变为一只青蛙后,我们认为彼时的蝌蚪就是此时的青蛙,它原来是蝌蚪,现在变为青蛙了——蝌蚪和青蛙都是同一的个体的不同存在阶段和形态。(同样的分析也适用于昆虫化蝶的过程。)从生物形态上看,一只蝌蚪和一只青蛙相差很大(例如蝌蚪用鳃呼吸,青蛙主要靠肺呼吸)。虽然现有生物学并不把它们当作两个物种,但它们的差别之大并不亚于两个物种的差别。但是,这并不妨碍它们是同一的个体这一事实。同理,我们认为一个人类个体改变其生物形态和物种成员身份后,仍然完全有可能保有其个体同一性。换言之,一个人有可能先作为人类存在,然后又作为后人类继续存 在。
如果我们预设了人在本质上就是(具有)人格者(person)并在同一性问题上持一种“还原论观点”③参见 Derek Parfit, Reasons and Person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6, p. 210。,那么毫无疑问人类个体同一性的保存并不需要以其人类物种成员身份的保存为前提。一个人格者完全可以保持心理上或物理上的连续性和联系性并因此仍然是同一的个体,即使在被增强后他不再是人类(homo sapiens)。
即使我们不作关于人的本质和同一性的上述预设,而是持一种生物观点或动物主义立场①参见Eric T. Olson, The Human Animal: Personal Identity Without Psycholo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 pp. 16—21。,这也依然不会影响我们的结论。例如,在同一性问题上持生物观点的德格拉兹亚(David DeGrazia)也认为我们有可能改变我们的物种成员身份。他说,对于保持我们的个体同一性而言,重要的不是隶属于某一特定的生物物种,而是隶属于某个生物种类(biological kind)。②参见 David DeGrazia, Human Identity and Bioeth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pp. 48—49。也就是说,我们只需在本质上是某种活着的动物或生物有机体就足以保证我们的个体同一性,而并不需要在本质上就是人类。例如,我们可以成为某种(新的)人科动物(hominid species)的一员而仍然保持我们的个体同一性,尽管目前人科动物仅存一属一种(即人 类)。
总之,人类物种同一性的丧失并不必然蕴含着每个人类个体的同一性的丧失。也就是说,即使对人的增强的结果是整个人类的灭亡,这也不意味着每个目前属于人类的个体的灭亡。生物保守主义者试图把人类物种保存的重要性嫁接在人类个体同一性的重要性之上的做法是徒劳的,因为人类物种同一性的保存对人类个体的同一性的保存不是必需 的。
更何况人类个体同一性的重要性本身也存在争议。众所周知,德里克·帕菲特(Derek Parfit)曾雄辩地指出个人同一性并不重要,重要的只是“关系-R”(即心理上的联系性和连续性)。③参见 Derek Parfit, Reasons and Persons, chapters 12—13; Derek Parfit, “The Unimportance of Identity,” in Shaun Gallagher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Self,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419—441。即使我们承认个人同一性是重要的,超人类主义的计划也并不会损害个人同一性。对一个人各方面能力的增强如何能够使其不再是其自身呢?除非我们认为人在本质上必须是人,并且超人类主义计划会使人不再是人——但这两点都已被我们证明是十分可疑 的。
在结束我们这一节的讨论之前,还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我们这里谈论的同一性是指“号数上的同一性(numerical identity)”;但正如德格拉兹亚所指出的,人们经常混淆“号数上的同一性(numerical identity)”和“叙事同一性(narrative identity)”这两个概念。前者指一个事物和其自身之间的关系,它决定一个事物历经变化之后是否幸存的标准;后者指一个个体的自我概念,即他如何定义和看待他自身,它涉及的是一个个体对自我的形象、角色、经历和价值观的认同。前者是关于形而上学或概念的,后者则是有关价值和内在心理的。④参见David DeGrazia, “Enhancement Technologies and Human Identity,” Journal of Medicine and Philosophy,Vol. 30, No. 3, pp. 264—266。
人们对同一性的关切通常并不是关于号数上的同一性的,而是关于叙事同一性的。例如,当一个人在经历青春期迷茫或中年危机时,他内心中那个“我是谁”的追问并不是关于号数上的同一性的,而只是关于叙事同一性的。他不是对自己在经历各种变化之后是否还活着这个问题有所疑惑,而是存在一个自我认同的危机。我们希望保有我们号数上的同一性,绝大多数时候只是希望将来会有一个个体和我保持叙事上的同一性——他把我认同为自己,拥有我的记忆、情感和价值观等等,并去实现我的愿望和追 求。
生物保守主义者对同一性的关切也主要是对叙事同一性的关切。虽然他们认为在被增强后“我们有‘变成另一个人(turning into someone else)’的风险”①参见The President’s Council on Bioethics, Beyond Therapy: Biotechnolog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p. 300。,但这主要是说增强会使我们对自我的认知产生困惑,而不是说增强真的会使我们成为另一个个体。也就是说,他们把“同一性”和“自我认知(sense of self)”(也就是“叙事同一性”)当作相同的概念。②Ibid., p. 215.
毫无疑问,一个人的叙事同一性至少对其自身而言是重要的。但对人的增强如何会损害人的叙事同一性呢?生物保守主义者认为,这是因为在被增强后“我可能会更好、更强、更快乐,但我不知道这是如何做到的。我不再是自我转变的动因,而是造成改变的力量的被动承受者”③Ibid., p. 294.。也就是说,我们可能会有更强的体力、智力和情感控制能力并因此获得更大的成就和更好的状态,但这不是由我们的“真实经历”得到的,我们不能理解这种更高的能力和更好状态的意义,因而这种好的东西是“廉价的”。总而言之,他们认为“极端增强提供不了对我们而言很有价值的经验,同时它也往往会损害那些经受它的人的同一性。这种损害表现为对自传式记忆中的联系构成威胁,这种记忆解释了何为人的历时同一性或者一个人对历时的自我的理解”④Nicholas Agar, Truly Human Enhancement: A Philosophical Defense of Limits,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2014, p. 55.。
生物保守主义者的这种看法似是而非。首先,通过增强获得的能力和状态与天然获得的能力和状态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对于自己的天然禀赋我们也同样不能理解其来源和作用机制,但这不妨碍我们凭借自己的天赋能力获得非凡的经历和成就。在被增强后,我们只是在更高的层次上面向更多的可能性去愿望、去经验、去行动。被增强也不意味着无所不能,我们同样需要发挥我们的主动性,我们不会成为被动的承受者,而仍然是自身生活和意义的创造 者。
其次,只要增强是一种自主选择且不是特别突然和剧烈,我们的叙事同一性就不会受到损害。这种能力的增强至多只会成为一个奇特的体验(就和平常生活中某种新奇的非凡体验一样,我们能够适应这种新的变化),而不会损害对叙事同一性至关重要的所谓自传式记忆。也就是说,我们将能够把增强前后的经验和记忆结合在一个统一的自我叙事之中。另外,即使增强会损害自传式记忆,认为对自传式记忆的损害会导致人历时的同一性(号数上的同一性)的丧失的看法仍然是可疑的,因为它预设了个人同一性问题上的记忆标准或心理标准(其正确性在形而上学仍有待证 明)。
再次,即使是生物保守主义者,他们也承认生物医学技术有时有利于同一性的保存,例如通过延缓阿尔兹海默症的侵蚀而保留我们的完整记忆,或通过控制抑郁来恢复我们正常生活的能力。①参见 The President’s Council on Bioethics, Beyond Therapy: Biotechnolog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pp. 293—294。完整的记忆和正常的情感能力是维持叙事同一性的关键因素。生物保守主义者总是倾向于把超人类主义改善我们情感能力和情绪的计划想象成一个可怖的“美丽新世界”②参见 Francis Fukuyama, Our Posthuman Future: Consequences of the Biotechnology Revolution, pp. 4—7。,但这实际上是一种对超人类主义构想的歪曲。我们相信,只要稍微了解一下抑郁症患者对控制自身情绪的渴望就会同意这一点。被抑郁情绪折磨的人通常认为在被药物治疗后的状态才是“更真实的自我”,而不是相反。最后,叙事同一性虽然重要,但并非不能改变。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对自我的理解和认同经常发生巨大变化,如果这种变化大体说是好的,那就值得欢迎。事实是,随着生活的变化和自我的成长,每个人的叙事同一性都在不断地打破和重建中。这也正是自我塑造和成长的题中之 义。
接下来,让我们来考虑生物保守主义者认为人类物种同一性之所以重要的第二个原 因。
生物保守主义者普遍相信,“人类”这个概念具有道德意义,并且人类物种的成员这一身份是我们能够享有道德地位和权利的理由和根据;因此,保证人类物种的同一性和我们的物种成员身份十分重要。例如,安纳斯等学者认为,“人类物种成员身份是人权之含义及其实现的核心”③George Annas et al., “Protecting the Endangered Human: Toward an International Treaty Prohibiting Cloning and Inheritable Alterations,” p. 153.。这实际上是把人权等同于“人的权利”,即把人权看作是专属于人的东西;换言之,他们认为只有人类物种的成员才配享有完全的道德地位(full moral status)并得到平等的尊重。这种认为个体的道德地位取决于其所属的物种的观点被称为“物种主义(speciesism)”④或译为“物种歧视”。由于“歧视”一词本身蕴含着否定和贬义,这里我们采用“物种主义”这一更为中性的表达。。
物种主义的困难在于很难说明为什么物种概念具有道德相关性,特别是很难说明为什么人类这一物种具有高于其他物种的道德地位。正如德格拉兹亚和米拉姆所指出的,成为人只是成为同属一个生物演化系列的一群动物的一员,这一生物事实本身并不是人的道德地位的合理根据;并且,“每一个人都是无数个种类(包括生物种类)的成员。例如,一个人既是人类的一员,又是人科动物、灵长类、哺乳动物、脊椎动物、动物、生物有机体等生物种类的一员。把物种单独挑出来作为与道德地位相关的生物种类的做法是武断的”①David DeGrazia and Joseph Millum, A Theory of Bioeth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1,pp. 181—182.。
生物保守主义者要避免这种困难,使自身免于“物种歧视”的指责,就必须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他们的解释通常诉诸人类物种的独特性,即人所特有某些能力。例如,福山说:“物种主义未必就是人类无知和自私的偏见,而是一种关于人类尊严的信念,这一信念可以基于对人的独特性的实证性观点得到辩护。”②Francis Fukuyama, Our Posthuman Future: Consequences of the Biotechnology Revolution, p. 147.换言之,他认为“人类身上有某种独特的东西,它赋予这一物种的每个成员高于自然世界其他成员的道德地位”。③Ibid., p. 160.
这种对物种主义的解释或辩护显然不能成功,即使我们承认人类如其所言地具有某些独特的性质或能力(例如意识、理性、语言,等)。首先,并非所有人类个体都具有这些能力。有的人(例如婴儿、残疾人和某些病人)并不具有(或完全具有)这些能力,但我们仍然把他们当作具有同等道德地位的人来尊重。即使我们像物种主义者经常辩解的那样,只要求大多数人类个体具有(或潜在地具有)这些能力,问题仍然挥之不去:“如果一个物种的成员的道德地位被证明是基于该物种成年的普通成员碰巧拥有的那些能力,那么仍然不清楚的是为什么该物种中缺乏这些能力的成员应该被赋予完全的道德地位。”④Steve Clarke and Julian Savulescu, “Rethinking our Assumptions about Moral Status,” in Steve Clarke, Hazem Zohny and Julian Savulescu (eds.), Rethinking Moral Statu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1, pp. 6—7.其次,这些能力有可能被其他物种的成员所具有,没有理由认为被增强后的人类个体或后人类个体不能具有这种能力。由此看来,人类物种成员身份对享有完全的道德地位而言并非必要 的。
更为严重的是,生物保守主义者把一个物种具备何种典型能力这一点设立为裁定其成员应该被赋予何种道德地位和权利的最终标准的做法,会允许根据不同物种和一个物种内部不同个体具有(或不具有)某些能力的程度来划定道德地位和权利的等级。①生物保守主义者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例如,福山说:“乍看起来,把人的尊严建基于人类具有某种独一无二的特征这一事实之上的自然权利理论,似乎会允许根据这一物种的所有单个成员享有那些特征的不同程度来划分权利的等级。”参见Francis Fukuyama, Our Posthuman Future: Consequences of the Biotechnology Revolution,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2, p. 174。这无异于在价值领域建立起一种基于能力的丛林法则。正是出于他们内心所执有的这种根据能力的有无或大小来划定道德地位和权利的法则,生物保守主义者担心“超人类主义的第一个牺牲品可能就是平等”②Francis Fukuyama, “Transhumanism”, Foreign Policy, No. 144, 2004, p. 42.——这正是他们所持有的这条法则的逻辑结论。因为,被技术所增强或改变者在能力上可能高于或低于人,按照他们的法则,这些在能力上与人不平等的新物种或人类亚种就会相应地在道德地位上与现有人类不平等。他们担忧,一方面,在能力上低于人的物种将“受到不平等的待遇或被剥夺人权”③George Annas et al., “Protecting the Endangered Human: Toward an International Treaty Prohibiting Cloning and Inheritable Alterations,” p. 154.;另一方面,在能力上高于人的物种将声索高于人的地位和权利。④参见 Francis Fukuyama, Our Posthuman Future: Consequences of the Biotechnology Revolution, pp. 9—10; Francis Fukuyama, “Transhumanism”, Foreign Policy, No. 144, 2004, p. 42。
生物保守主义者的这种担忧或理论困境完全是作茧自缚。正如道德个体主义(moral individualism)所揭示的那样,“能力的差异对权利产生影响的方式,不是由此创造一个重要性或价值的等级,而是决定对某个生物而言,什么是好事,什么是坏事”,而物种成员身份本身则完全是不重要的。⑤参见 Martha C. Nussbaum, Frontiers of Justice: Disability, Nationality, Species Membership,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2006, p. 360。这就是说,一个物种的成员身份和一个物种的典型能力本身并不是其成员所享有的道德价值、地位或权利的根据,而只是规定什么对其成员而言是利好或伤害,或者说规定什么对其成员而言构成一种权利。只要放弃其物种主义立场(但这显然不是他们所乐意的),生物保守主义者的困境就迎刃而解 了。
其实,在道德地位这个问题上,我们并非只有物种主义这一种选择。对道德地位问题的合理解释,可以以一种与物种同一性和物种成员身份无涉的方式回应生物保守主义者对平等的关切。我们这里试举两例:首先,正如布坎南(Allen Buchanan)所说,道德地位(moral status)和人权(human rights)都是“门槛概念(threshold concept)”。一旦在能力或其他方面的某个门槛被达到了,达到这个门槛的个体都应享有完全平等的道德地位和权利,不管这些个体在能力方面表现出多大程度的差异,即使这些能力是构成那个门槛的关键因素时也是如此。⑥参见Allen Buchanan, “Moral Status and Human Enhancement”, 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 Vol. 37, No. 4,pp. 357—359。此外,还存在另一种意义上的“门槛”:道德地位和基本权利都具有不可让渡性和不可侵犯性,一旦获得,其他具有更高道德地位的物种或个体的存在也不能对其构成挑战。①参见Allen Buchanan, “Moral Status and Human Enhancement”, 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 Vol. 37, No. 4,pp. 364—369。也就是说,被增强者或后人类并不拥有比现有的人更高的道德地位;并且,即使被增强者或后人类具有更强和更多的能力并因此享有比现有人类更高的道德地位和更多的权利,也不代表现有人类已然获得的道德地位会受到损害或其享有的权利会相应减少——这里不存在一个此消彼长的关 系。
其次,大多数道德理论(包括物种主义)都认为一个事物是什么决定了它应该享有什么样的道德地位和权利,但正如贡克尔(David Gunkel)在讨论机器人的道德地位和权利问题时所指出的,这里还存在一条与此完全不同的理论道路。他沿着伊曼努尔·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所倡导的“伦理学先于本体论”的思路前进,认为在道德生活中我们首先面对的是一群进入我们生活的匿名的他者,我们有义务在对他们是什么有所了解之前就做出回应。道德考虑不应该基于预先决定好的本体论标准或能力,而应该直面实际的社会关系和互动。也就是说,道德地位问题并不取决于我们所面对的他者在本质上是什么,而在于他/它出现我们面前时我们应该如何回应;不在于他者的内在性质,而在于我们和他者的外在关系。②参见 David Gunkel, “The Other Question: Can and Should Robots Have Rights?”, Ethic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Vol. 20, No. 2, pp. 95—97。贡克尔的这一思路对我们的启示是,当我们考虑应该赋予一个对象怎样的道德地位时,首要的问题不是追问这一对象是否是人类,而是要看它与我们处在什么样的关系或互动中。简而言之,拥有完全的道德地位并不要求以拥有人类物种成员身份作为必要前 提。
当然,我们承认个体的道德地位问题本身十分复杂,限于主题和篇幅本文无力给这个问题一个决定性的答案。但是,我相信上文所举的两种对道德地位问题的合理解释足以说明物种主义并非我们的必然选择。并且,鉴于物种主义的理论缺陷和它所面临的理论困难,我们有理由认为生物保守主义者基于物种主义立场在道德地位问题上对我们的物种同一性(或物种成员身份)的关切和担忧没有充分的理论根据和必要。
综上所述,对人的个体同一性和道德地位而言,人类物种的同一性并不重要。当然,我们并没有说人类物种的同一性或人类的延存在其他方面也不重要。超人类主义者并不期待或愿望人类的灭亡,他们和生物保守主义者一样希望人类能尽可能长久地生活在这个世界 上。
四、结论
超人类主义计划的实施并不会危及人的本质和人类物种的同一性,它并不会加速人类的灭亡;相反,它将增强人类应对各种存在性风险的能力,有利于人类物种和人类文明的保存。并且,对人的个体同一性和道德地位而言,人类物种的同一性并不重要,生物保守主义者基于这方面的考虑对人类物种同一性之执着缺乏合理的根据。超人类主义者可以理解生物保守主义者对我们这个物种的留恋,既不希望人类的灭亡,也不恐惧人类的灭亡,更不促使人的灭亡。超人类主义者只是认为,既然人类终有一天要退出历史舞台,就不如顺应变化并保存人类最珍视的东西,而不是沉迷于为人类唱挽歌,因为真正重要的并非人类这个物种的保存,而是人类文明和价值的延 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