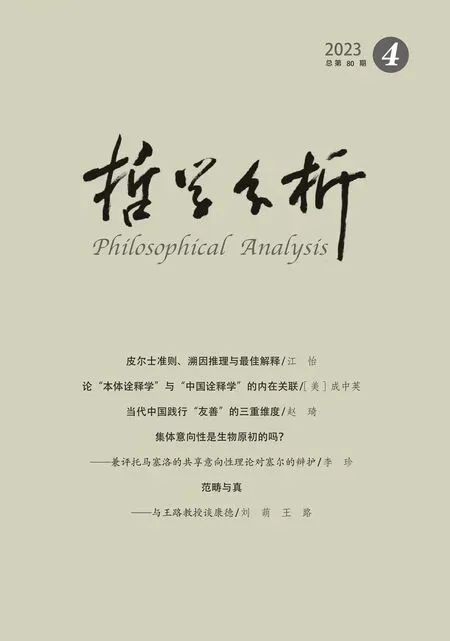范畴与真
——与王路教授谈康德
刘 萌 王 路
刘萌(以下简称“刘”):王老师,最近几年您发表的文章开始越来越多地涉及康德哲学,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①参见王路:《论关于认识本身的认识》,载《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5 期;《“表象”的使用和意义——弗雷格与康德比较研究》,载《学术月刊》2022年第6 期;《研究还是读后感——关于邓晓芒〈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句读〉的几点看法》,载《河北学刊》2017年第6 期;《为什么要区别真与真理——回应邓晓芒教授的批评》,载《河北学刊》2018年第2 期;《逻辑判断是“消极的”吗?——与邓晓芒教授商榷》,载《河北学刊》2019年第4 期。我曾多次听您谈论康德,您在以前的著作中也多次提到过康德,比如他对“形式逻辑”的命名,他对上帝存在的反驳,您还仔细分析过他的“是(Sein)显然不是真正的谓词”这个论题,以及他的判断表和范畴表。②参见王路:《逻辑的观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是”与“真”——形而上学的基石》,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逻辑与哲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一“是”到底论》,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但是,像您近几年这样连续写文章专门谈论有关康德的问题,有些文章还带有一些论战的性质,这都还挺让人感到意外的。所以,我想就此专门向您请教几个问题,听一听您的想 法。
王路(以下简称“王”):好 的。
刘:您早年在《逻辑与哲学》中就系统讨论了康德的先验逻辑和“形式的”逻辑,您认为,康德的先验逻辑是一种哲学,这种哲学是以逻辑为基础的,这个观点也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国内学界对康德形式逻辑与先验逻辑关系问题的讨论。而近几年,您又开始谈论康德关于“真”(Wahrheit)的论述,算上一开始提到的“是显然不是真正的谓词”、判断表和范畴表等内容,这些论述看似松散,其实还是有联系的。“是”与“真”是您长期以来研究的重点,其实质则涉及逻辑与哲学的关系。我是不是可以认为,您所有关于康德的论述,都是围绕着逻辑来谈论的或者说是从逻辑出发的?这与国内学界普遍做法显然是不同的。如果我的看法是正确的,您能不能说一说,这是为什么 呢?
王:你说的是对的。康德的著作我只熟悉《纯批》,这也是我一直读的主要著作之一,其他的读得不多。你可以看到,我关于康德的谈论也只限于《纯批》。而从这部著作看,谈论逻辑或者围绕逻辑来谈论康德哲学就是自然的事情了,因为康德自己就是这样做的。我最近的讨论主要集中在《纯批》中“先验逻辑的理念”这一章。它属于开始部分,分四节,第一节“普遍逻辑”谈的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逻辑。康德将通常所说的逻辑称之为“普遍的逻辑”或“形式的逻辑”,这样就说明了逻辑的一些性质,比如它只研究形式,不研究内容,它是纯粹的科学,与质料无关,然后基于这样的说明提出一些不同的性质,比如仅与“Verstand”(知性)相关,与对象相关等等,由此形成他说的“先验(的)逻辑”。所以,不是我要围绕逻辑来谈论康德,而是康德本人就是这样谈论的。或者退一步说,围绕逻辑来讨论康德是可行的,至少是有文本依据 的。
除了文本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根源于对逻辑与哲学关系的看法。逻辑研究薄弱,对逻辑重视和把握不够,是国内哲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对《纯批》的研究也是如此。我并不专门研究康德,但是这一点还是看得很清楚的。我讨论康德,主要围绕逻辑来讨论康德,强调逻辑在康德思想中的作用,其中含有一个意思,是希望这个问题能够引起学界的重视。在我看来,这是研究康德哲学的必要条 件。
刘:您认为“是”与“真”这两个概念是把握西方逻辑与形而上学思想的核心。然而相比康德研究中像“范畴的先验演绎”这样的核心话题,对康德思想中“是”与“真”的研究却算不上真正的热门,您如何看待这样的研究状况?此外,您认为“是”与“真”这两个概念在理解康德的批判哲学中应当发挥怎样的作 用?
刘:我也发现了这个问题。“真”这个概念很重要,但是却没有出现在康德的范畴表中。您能谈一谈这是为什么 吗?
王:很简单啊,他的范畴表怎么会有“真”这个概念呢?我强调康德的范畴表来源于他的判断表,要认识二者之间的关系,这一点你是知道的。康德的判断表是依据逻辑构造的,而且主要是依据逻辑的句法构造的。这从量、质、关系和模态这四个分类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它们都是句法方面的分类。“真”不是句法概念,而是一个语义概念。虽然康德时代对这一点尚缺乏充分的认识,但那时人们对逻辑句法的认识还是清楚的。所以,“真”这一概念无法放入这个判断表中,而是需要另做说明。此外,康德关于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的区别所作的说明是明确的,关于这一原则的使用是贯彻始终的。这一区别和原则显然是围绕着“S 是P”这样的句式说的。所以,“是”与“真”的对应,“是”与“真”的联系,在康德思想中无疑是存在的,只不过在范畴表中没有而已。而且在我看来,这一点也是非常清楚 的。
刘:许多现当代学者在争论,康德在真理问题上究竟是“符合论”,还是“融贯论”,抑或是兼而有之,您刚才也提到您读过许多有关康德的真之理论的论文,那么您能不能谈一谈您对康德关于“真”的论述的理解,或者说,您认为康德对“真”的看法对于理解他的批判哲学有着怎样的价 值?
王: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近几年我讨论了有关康德关于“Wahrheit”是知识与对象的符合的论述。它涉及两个问题,一个是康德称这个说法是关于“Wahrheit”的名词解释,另一个是康德说还要追求有关知识的“Wahrheit”的普遍标准。在相关研究中,一种观点认为,前一个问题表明康德是符合论,另一种观点认为,后一个问题表明康德是融贯论。当然也有人认为这两种看法康德都有。我认为符合论的说明是自然的,康德从这个观点出发来探讨这个问题也是自然的,这也是塔尔斯基的真之理论产生之前人们的普遍看法。所以认为康德有这样的看法并不奇怪。融贯论的意思是说,“真”乃是相对于某一种知识系统而言的。所以将康德(根本不可能有关于知识的“Wahrheit”的普遍标准)的看法归于融贯论,也不能说没有道理。我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对“Wahrheit”一词的理解和翻译上,因而没有就这个问题本身展开讨论。在我看来,无论是从符合论出发还是从融贯论出发,也就是说,无论怎样解释康德对“Wahrheit”的看法,将“Wahrheit”译为“真理”都是有问题的。“真理”与对象不同,与知识或认识却是相似的,但是,“真”不仅与对象不同,与知识和认识也不同。因此将“Wahrheit”译为“真”还是译为“真理”乃是完全不同的。我认为康德是在“真”的意义上谈论认识与对象的符合的,而且主要是在“是真的”这种意义上谈论“真”的。基于这样的认识来解释康德,比如将他的论述解释为符合论,“真”就是知识或认识与对象之间的关系。无论这样的看法是不是对的,不管这样解释康德是不是有道理,“真”显然是与知识和对象不同的东西,我的意思是说,它们是不同种类和不同层次的东西。这样的说明与说“真理”是知识与对象之间的关系无疑是不同的,至少是有重大区别 的。
至于你说的这样解释康德思想的价值何在?我认为至少有两个层面。字面上看,这样的解释至少更清楚。即便认为这样的解释会有问题,它也提供了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是从“真”的角度,一种是从“真理”的角度。我们至少可以而且也应该思考一下,这两种角度的理解是不是一样,哪一种理解更有道理。而就理解康德本人思想而言,我们应该看到,康德关于“真”的讨论是在区别出形式和内容之后提出的一种思考方式。他认为逻辑是纯形式的,与内容无关,而他所期望的先验逻辑不是这样的。在撇开形式的考虑之后,他提出“真”及其相关问题,希望可以通过相关讨论来说明内容或与内容相关的东西。知识或认识显然是有内容的,因而与内容相关。那么它们如何相关?“真”是不是也与内容相关呢?它与内容又是如何相关的呢?这些都是康德讨论中所涉及的问题。今天我们知道,逻辑有句法和语义两个方面,“真”乃是其语义的核心概念。那么句法是什么呢?对照起来看就会发现,康德所说的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就是或者就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句法,而他说的“真”,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就是或者就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语义。所以康德可以谈论形式,可以依据判断形式构造他的范畴表,并通过这样的谈论使他所说的形式与内容区别开来,并通过这种形式方面的刻画对内容方面的事情作出说明。但康德同时也可以谈论“真”,并试图通过“真”来谈论与内容相关的事情,从而为他从形式方面作出的说明提供补充说明和论证。只不过他那时的逻辑没有今天成熟,没有关于句法和语义的明确区别和说明,没有一个清晰的语义学。所以康德的区别不是非常清楚,论述也不是特别清楚。可以看到,他关于句法方面的说明还是明确的,有条理的,因为有亚里士多德逻辑所提供的句法作参照,但是他关于“真”的论述基本上还是常识性的,即依据人们对“真”这个概念的直观认识。所以,从语义的角度来看康德对“真”的论述,其实还是可以看到它们与句法论述的对应性的。这也是今天人们研究康德的一个基本认识,无论是符合论还是融贯论,在这一点上,差不多都是一样 的。
刘:您认为康德是从逻辑出发构建出他的先验逻辑的,然而国内许多康德研究者似乎并不赞同您的这种观点,他们认为康德实际上是以先验逻辑的范畴来为形式逻辑的判断形式奠定基础的。您的观点主要以康德对普遍逻辑等内容的一般说明,判断表、范畴表等部分的文本为论据,而持相反观点的学者则主要以范畴的先验演绎部分作为文本支撑,并认为您所依赖的文本只是康德“表面上”的说法。您如何看待这样的分 歧?
王:我认为这里至少涉及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看待逻辑,一个是如何理解康德。当然,二者合一就要问:康德是如何看待逻辑的?康德认为逻辑是普遍的,是纯粹的科学。仅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如果还可以找出可以为逻辑奠基的东西,那么这样的逻辑就一定不会是普遍的,也不会是纯粹的。原因很清楚,因为它还会依赖于其他科学。但是这与康德关于逻辑的看法显然是相悖的。所以,这里的问题实际上是如何理解康德的问题,但是在理解康德的过程中又涉及如何理解逻辑的问题。我认为康德的先验逻辑依赖于逻辑,这一点是自明的,用不着多说什么,我只就你说的论证方式说一说我的看法。我之所以要谈康德关于逻辑和判断表的认识,主要是因为我认为它们很重要,它们对于康德的先验逻辑很重要。而且我认为,它们与康德关于先验逻辑和范畴表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但是这一点并没有受到充分的认识。不是说不可以从范畴的先验演绎部分来论述和论证康德关于逻辑的看法,问题是,是不是应该认真研究和理解康德关于逻辑和判断表的论述,并由此出发理解康德关于逻辑与先验逻辑之间关系的论述。即使仅从文本的角度说,逻辑和判断表也是在先的。换句话说,在尚未读到后面的论述之前,我们该如何理解康德关于逻辑和判断表的论述,如何理解康德关于逻辑与先验逻辑、判断表和范畴表之间关系的论述?仅从阅读的角度说,康德的思想有一个延续性的问题,即我们依据他在先的论述来理解他后面的论述。即便我们在后面的论述中获得了与先前不同的认识和理解,是不是也应该思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这是康德本人表述的变化,还是他的论述过程的变化,这是他的思想的变化,还是仅仅是我们理解出来的变化?我只讨论康德在“先验逻辑的理念”这一部分的论述,并不意味着我不能讨论康德后面的论述。我强调在这一章读不出康德关于先验逻辑为逻辑奠基的思想,是因为这一章有康德关于逻辑与先验逻辑之间关系最明确的论述。反对者可以提出自己的论证,但是不对康德这一章的论述作出说明,不针对我围绕这一章所作出的论述作出反驳,只是笼而统之地谈论是不行的。所以,这里既有理解康德思想的问题,也有如何阅读文本和进行讨论和论证的问 题。
刘:众所周知,您研究最多的两个人物是亚里士多德与弗雷格,一位是逻辑的创始人和形而上学的奠基人,一位是现代逻辑的创始人和分析哲学之父。所以您强调逻辑与哲学的关系是很自然的。康德的先验逻辑或先验哲学非常重要,但是他的逻辑似乎并没有那样重要。您在论述康德时这样强调逻辑的作用,强调康德关于逻辑的看法,这会不会有问题啊?或者我换一个问法,你认为康德的思想在亚里士多德和弗雷格之间大概处于一种怎样的位 置?
王:这是一个好问题,直接涉及逻辑与哲学的关系。亚里士多德和弗雷格在逻辑和哲学中有崇高的地位,他们的逻辑与他们的哲学是密切联系的,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康德的哲学地位没有问题。但是他在逻辑史上没有什么地位,他最出名的大概就是他关于逻辑说的那句话:逻辑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就已经完成了。但今天人们知道,这句话是不对的。那么在他的思想中,逻辑与哲学是不是有密切地结合呢?强调对逻辑的认识和把握,这对康德研究是不是必要的呢?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既然你提到亚里士多德和弗雷格,我就从比较的角度说一 下。
调蓄水池的主要作用,是用来调节供水量与用水量的不平衡情况,以及发生事故检修时的备用水量。由于工程规模较小,并且选择水泵、管材均易于检修,所以水池容积按检修4 d考虑。项目区共11 120人,标准为40 L/(人·d),共计需水量2 000 m3,最终确定蓄水池容积为2 000 m3。
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与《形而上学》是完全不同的著作,弗雷格的《概念文字》和哲学论著比如《算数基础》 《论涵义和意谓》等等也是完全不同的。在《形而上学》等哲学论著中,你可以看到逻辑理论和方法的应用,还可以看到后者确实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个事实是,在这些哲学论著中,几乎看不到专门关于逻辑本身的论述。但是人们承认,如果没有相应的逻辑理论背景,读懂它们是有困难的。康德的《纯批》不同,国人说它难懂,主要是因为它的语言表达方式。确实是这样。但是如果你对照康德的《逻辑学讲义》和《纯批》,你会发现,《讲义》中导论部分的内容几乎都在《纯批》中出现了。也就是说,《讲义》和《纯批》有许多内容是重合的。所以我强调,把握逻辑或者把握康德对逻辑的认识对于理解《纯批》是至关重要的。大体上说,康德与亚里士多德有一点不同,他谈论哲学的时候总是小心翼翼地基于逻辑作出区别。比如,他将逻辑称为普遍的或形式的,基于这样的说明他称自己建立的东西为先验逻辑。他将逻辑分为分析的和辩证的,称前者为真之逻辑,与真之普遍标准相关,称后者为逻辑的应用,因而包含一些与真之标准不同的东西。他区分出感性和“Verstand”(知性),逻辑与二者相关并且只与形式相关,他的先验逻辑只与知性相关,并且还会涉及相关的对象等等。我说这些不是要谈论它们,我要说的是,这些无疑都是《纯批》的内容,但它们同时也是《讲义》导论中的内容。这样的情况显示出康德与亚里士多德和弗雷格的不同,但同时不也恰好说明,他的逻辑与哲学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吗?
刘:那么关于康德在亚里士多德和弗雷格之间的位置 呢?
王:这一点我说不好。就谈谈我自己的直观认识吧。亚里士多德是形而上学奠基人,分析哲学被称为当代形而上学,因此弗雷格可以被看作是当代形而上学奠基人,所以在形而上学上他和亚里士多德是一脉相承的。康德是近代哲学家中明确提出建立形而上学科学的人。我认为,如果形而上学有两个阶段,那么一个是从亚里士多德到弗雷格之前,包括康德及其以后的哲学家,另一个是自弗雷格以来到今天。如果有三个阶段,那么康德就是第二个阶段的开启者。我这样说是因为,在重视逻辑,应用逻辑的理论方法来从事哲学研究这一点上,康德与亚里士多德和弗雷格显然是一致的,而且他使用的逻辑理论和方法本身与亚里士多德的是相同的,与弗雷格的却是不同的。弗雷格的逻辑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不同,因而导致哲学形态和成果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有一种观点认为,近现代哲学的所有问题都是从康德那里来的。假如这种观点成立,那就还可以继续问,康德的问题又是从哪里来的?所以我认为,研究康德,固然可以谈论他本人的思想,但是也可以将他放在哲学史上去看,这样他就不是一个孤立的个 体。
刘:您的说法让我想起康德提出范畴表时的一句话,“我们想依据亚里士多德把这些概念称为范畴,因为我们的意图(Absicht)原本与他的意图是一回事”。我觉得这句话很能说明康德对亚里士多德的继承关系,特别是他那些先验哲学范畴。但是“范畴”这一概念到了现代以后似乎消失了,比如弗雷格构造的“概念文字”就不再谈论范畴了,这样我们就看不到他们之间的继承关系了,至少字面上看不到这样的关系了。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呢?
王:我明白你的意思。继承关系,一种是字面上的,一种是非字面上的。前者是清楚的,说起来也比较容易,后者似乎不是那样清楚,说起来似乎也要费些力气。我认为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到弗雷格的继承关系,大体上说,他们都是哲学史主线上的人物,他们都是研究先验的东西的,他们都是开创性的人物。具体一些说,在他们的哲学著作中,逻辑的理论和方法的应用是显然的,因而他们应用逻辑的理论方法来探讨哲学问题的方式对后人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些也可以看作是他们的继承关系,即他们共享一种哲学研究的方式。但是一定要看到一个重大区别,这就是逻辑在弗雷格这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我们一般说,亚里士多德逻辑是形式的,但不是形式化的,而弗雷格逻辑是形式化的。这一区别其实在我看来还只是表面的。重要的是,弗雷格改变了逻辑的基本句式,他使逻辑从“S 是P”这样的主谓句式变为“Fa”和“∀xFx”这样的函数结构,结果使逻辑的理论和方法在应用于哲学时的解释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而使现代哲学的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康德之所以在字面上也可以显示出与亚里士多德的继承关系,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使用的逻辑还是亚里士多德逻辑。而在弗雷格的哲学及其以后的分析哲学中,“范畴”,或者说亚里士多德和康德意义上的“范畴”概念不再是核心概念,不再在讨论中占据主要位置,这是很自然的事情:逻辑的理论和方法完全不同了啊!但是即便如此,人们仍然发现并在努力研究和试图进一步发现弗雷格受到的康德影响以及他与康德的关系,比如弗雷格关于算数定律是先验综合的还是分析的论述,关于“Bedeutung”(意谓)的论述等等。你刚刚提到弗雷格的“概念文字”。一些研究认为,弗雷格之所以这样称呼他的逻辑,是因为“概念”一词自康德以来就与认识相关,特别是与“Verstand”(理解)相关,所以弗雷格的逻辑实际上是一种关于概念、关于理解的逻辑。还有人认为,弗雷格的概念文字引入的第一个符号含有一条横线,弗雷格称之为“内容线”,后来他从这条内容线区别出涵义和意谓,即思想和真值。所谓“内容线”中的“内容”与康德区别形式和内容时所说的“内容”是一样的,这样似乎也就可以看出,弗雷格关于逻辑的考虑乃是与内容相关的,他关于“真”的考虑也是与内容相关的,但是他考虑的结果则比康德要前进了一大步。当然也有人认为弗雷格的思想是开创性的,没有受到他之前的德国哲学家和德国哲学的任何影响。对弗雷格和康德关系的研究很多,有些研究也比较深入,这你是知道的。我一再说我不是康德研究专家,我也没有做过关于康德的专门研究。就我一直关注的问题而言,我认为逻辑与哲学的密切联系在康德著作中是显然的。所以,说他对亚里士多德思想的继承没有问题。但是说弗雷格对康德的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笼统地说一下肯定是可以的,但是提供明确的说明和具体的论证就需要下功夫了。
刘:我发现,您在探讨康德时有一个特点:您经常是从翻译入手的。关于“Sein”和“Wahrheit”,您的讨论很多,也很出名。这些我就不问了,我只问一下其他的。在近几年,您专门探讨了“negativ”一词的翻译。您认为应该将“negativ”译为“否定(式、性)的”,而不应该译为“消极的”。您批评“消极的”是错译,由此形成对康德思想的误解,而产生这种错译的原因则在于对逻辑的偏见。我赞同您的看法,但是读到这部分内容时感到有些奇怪。这个词并不是一个重要的用语啊。以我对您的了解,您平时都是读外文的,您怎么会注意到这个译文的问题呢?
王:你是对的:我发现“negativ”的翻译问题确实是偶然的。读德文著作当然是看不到这个问题的。最近由于讨论康德关于真的论述,我读了中译文,一下子就看到了这个问题。(刘:怎么是“一下子”?)我要讨论的是与“Wahrheit”相关的问题。你知道我认为应该将它译为“真”,而不是译为“真理”,因此查看与“真理”相关的中译文。我看得比较粗。但即便是一目十行,“是一切真理的conditio sine qua non[必要条件]、因而是消极的条件”这一句的问题也是跑不掉的。原因很简单。这里的“因而”表示推论。前提“必要条件”是褒义的,结论“消极的条件”是贬义的。这显然是一个不符合逻辑的推论:从褒义的怎么能推出贬义的来 呢?
刘:您的意思是说,一个符合逻辑的推论是:如果前提真,那么结论必须真。如果结论假,而前提真,就是不符合逻辑的。而您将这样的推论方式应用到康德这里所说的“因而”上,所以您发现了问题,是这样吗?
王:是啊。逻辑是二值的。但是应用到日常思维和其他学科的思维上,我们会遇到很多不同情况,比如对错、好坏、合适不合适、恰当不恰当,甚至黑白、高矮、美丑等等。而就推论而言,前提和结论的关系也是同样。从假的前提可以得到真的结论,也可以得到假的结论,但是唯独不能从真的前提得到假的结论,这才叫符合逻辑。你想一下,从好的能推出坏的来吗?(刘:推不出来。)看到这个问题,我也有些惊讶,于是去看了一下其他译本,结果发现这是一个普遍问题,于是我就做了一些讨 论。
刘:谢谢您,逻辑的学习和应用还真让人受启发。我注意到,您在访谈过程中多次特意用德文词“Verstand”替代了中文词“知性”,巧合的是,“范畴”也是康德对“纯粹知性概念”的简称,这就不得不让我联想到您在之前《是“知性”还是“理解”?》一文①参见王路:《是“知性”还是“理解”?》,载《社会科学报》2018年2月8日。中的观点,您认为将康德所说的“Verstand”译为“理解”会比现在通行的“知性”更好。确实,如果从“理解”来看待范畴,您刚才所说的弗雷格的“概念文字”受到了康德的影响这种观点似乎就更说得通了。而在另一篇文章中,您又说您只关注“理解(知性,Verstand)”,因为既然是与理解相关,那么逻辑当然就是非常重要的。②参见王路:《逻辑判断是“消极的”吗?——与邓晓芒教授商榷》,载《河北学刊》2019年第4期。可惜的是,除此之外我再没有看到您关于“理解”这个词的谈论了,您能不能简单谈一下您为什么会这样看呢?特别是,您为什么会认为逻辑对于“理解”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呢?
王:那篇小文章是为了参会而写的,不是正规的论文。但是这个问题却还是有意义的。康德说的“Verstand”是接着培根的“understanding”说的,这在《纯批》和《讲义》中都提到过。培根的书在前,被译为《人类理解论》。当然,“understanding”这个词的字面意思也是理解。而从德文本身来说,“Verstand”是名词,它的动词是“verstehen”,字面意思也是“理解”。所以,采用“理解”这个译名不仅符合其词义,而且也与培根的表述相一致。否则,国人还会以为他们说的是不同的东西。至于说逻辑与“理解”相关,至少可以有几个意思。康德谈的东西很多,包括感性、理解(知性)、理性,但是他所谈的主要是“理解”(知性)。康德在谈论“理解”的过程中有许多与逻辑相关的论述,这一点,仅从康德对感性和理解(知性)作出的区别,并由此展开关于“理解”(知性)的论述即可以看出。此外,我们探讨康德的思想,最基本的就是对康德的理解,这包括对康德著作的阅读和解释,对自己观点的说明和论证,对不同意见的批评和反驳。在这一过程中,当然会涉及逻辑,而且逻辑会起重要的作用。比如对前面所说关于“因而”的理解。超出康德,在现代分析哲学讨论中,“理解”(understanding)也是非常重要的概念,它与“意义”,与“真”直接联系起来。所以,仅从字面上即可以看出,这一概念在西方哲学中,至少从培根以来,一直是一个重要概念。所以,这个词既是一个术语,也是日常表达用语。我对它的翻译只是简单说一下,我说我只关注理解,这只是借用这个说法,有些一语双关的意思,但也仅此而已。因为在我的研究中,“是”与“真”才是重点。关于它们的讨论会给我们带来关于西方哲学完全不同的认识。这样说吧,像与“negativ”“Verstand”相关译名的讨论,可以是一次性的,但是关于“being”和“truth”的讨论,却是可以一直进行下去 的。
刘:围绕康德,和您谈了逻辑与哲学,也谈到了“being”和“truth”,最后我想听您谈谈哲学对于逻辑的影响。后人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称作“工具论”,似乎只认为它是一种工具。康德在谈论逻辑的时候也总是区分纯粹的、分析的和应用的、辩证的,似乎暗示我们逻辑是有局限性的。海德格尔写过《逻辑的形而上学基础》,似乎直接说明哲学对逻辑的作用。按照您的说法,逻辑在哲学中应用,逻辑对哲学有影响。那么哲学对逻辑有影响吗?我赞同您说的逻辑是讨论哲学问题、构建哲学体系不可或缺的工具,但是哲学家们在进行哲学研究的时候难道不需要合理地使用这种逻辑工具吗?而所谓“合理地使用”难道不需要以某种哲学思想为指导吗?还是回到康德。他最先提出了“表象与对象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何种根据之上”这个哲学问题(康德致赫尔茨的信,1772),只是在解决这个哲学问题时,逻辑才作为一种工具参与了进来,并以此为哲学体系的建构提供基础。这难道不是说明哲学研究对于逻辑的使用具有指导作用 吗?
王:你问了一个很大的问题。说实话,我还真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直观上说,逻辑是在哲学研究中产生和发展的:在哲学研究过程中,人们发现有这样一些独特的东西,将它们的性质和内容揭示出来,形成了专门的理论。亚里士多德称之为“分析”,后人称之为“工具”,再后又有了“逻辑”之名。在这种意义上,你可以说没有哲学就没有逻辑,这大概就是哲学对逻辑的作用。既然没有认真思考过,我就不便多说什么了。这样吧,我回答你的几个具体问题。一个是“合理地使用”逻辑。我认为,与其说需要靠某种哲学思想的指导,不如说取决于对逻辑的正确认识和把握。这是因为,逻辑毕竟成为一种具有专门性的东西,如果不懂或者没有很好的把握,那肯定是无法正确运用的。另一个是康德所说的表象与对象的关系。这无疑是康德考虑的基本问题。对象与感觉相关,感觉与“Verstand”(理解)相区别。这些是康德讨论的基本区分。“表象”则是他讨论中用以说明这些区别的东西,比如他明确说过,感性是通过被对象刺激而获得表象的能力,判断是对象的一个表象的表象。“获得表象的能力”与“表象的表象”,显然是不同的说明,而且还是区别出不同认识层次的说明。那么为什么逻辑会与判断相关呢?即便我们不作进一步的讨论,也还是可以看出,这一认识当然有赖于对逻辑的认识,或者至少有赖于对逻辑的认识,否则凭什么说逻辑与判断相关呢?这样就可以看出,讨论中在什么地方引入逻辑,需要基于对逻辑的认识。至于为什么要引入逻辑,大概就不必说了吧。或者,我们是不是至少可以认为,在逻辑的重要性以及由此在哲学讨论中需要引入逻辑这一点上,我们也许不清楚是不是需要依赖于某种哲学认识,但是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在这一点上,对逻辑的认识一定是最起码的条件。如果我们不知道逻辑是什么,对逻辑的理论方法认识得不是特别清楚,那么用什么样的哲学认识来指导也是没有用的。
达米特有一本书叫《形而上学的逻辑基础》,从书名上看,它与你说的海德格尔那本书似乎是对着干的,其实它们没有什么关系。这两本书我都读过,在这里就不展开评价了。不过我倒是建议你读一读达米特的这本书,关于逻辑与哲学的关系,我觉得它说得更有道理。
刘:我会认真读一下这本书的,您今天所说的观点对我很有启发,非常感谢您的耐心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