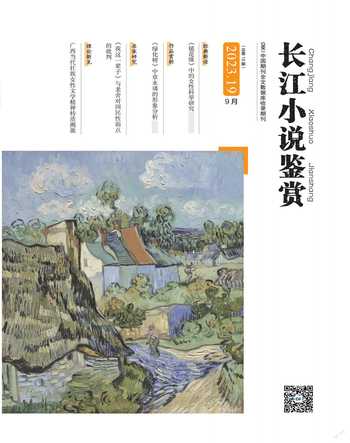论伊迪斯·华顿《纯真年代》中的怀旧情结
[摘 要] 美国女作家伊迪斯·华顿的作品《纯真年代》聚焦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纽约上流社会,讲述阿切尔、埃伦与梅三人之间的情感纠葛。小说对阿切尔祖先画像、传家宝等物件的描写以及博物馆这一特殊地点的选择都表明了华顿在经历一战爆发的创伤后对当下动荡、冷漠的社会环境的不满,从而转向追寻记忆中那个纯粹、安定、讲究体面与诚信的“纯真年代”——19世纪70年代。但同时,她的怀旧又并非完全理想化过去,而是始终以客观公正的态度看待传统与现代化,不仅表达其在面對传统精神理念消逝与中断时,对于旧秩序的怀念及留恋,同时批判了老纽约旧秩序的压抑和苦闷。
[关键词] 伊迪斯·华顿 《纯真年代》 怀旧 老纽约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2881(2023)19-0039-04
《纯真年代》讲述了老纽约贵族青年纽兰·阿切尔与两位女性梅·韦兰及其表姐埃伦·奥兰斯卡之间的情感纠葛。小说横跨三十年之久,华顿在文中以大量笔墨描写了19世纪末的老纽约社会,直到小说最后一章,才将时间推移到三十年之后。三十年前的纽约,等级观念根深蒂固,上流社会不断抵制新兴阶层;三十年后,当博福特的女儿范妮进入纽约社交界时,“上流社会非但没有不信任她或惧怕她,反而高高兴兴接纳了她”[1]。表面上看,在这三十年的浮沉与变迁中,纽约社会变得更加开放与宽容。但事实上,当时社会环境的断裂与剧变却引发了华顿的怀旧情结,她逐渐开始反省并重新评价传统的价值与意义,并将过去视为简单、纯粹、有序、安逸的理想家园。
《纯真年代》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这场战争给华顿带来了巨大的伤痛。一战期间,她曾在法国参加救护工作,目睹了战争的残酷以及当时人民的悲惨生活。在这样的背景下,华顿开始创作《纯真年代》。在其自传中,华顿坦言:“在这(一战)期间,我找到了一个逃离现实的方法,那就是回到消失许久的纽约,回到我童年的美国,于是写下了《纯真年代》。”[2]由此可见,尽管三十年后,“长途电话已经变得跟电灯和5天内横渡大西洋一样司空见惯”[1],但这些进步似乎并没有触动华顿的内心。她认为现在和过去的实质差别并不在于技术的发展,而是欧洲传统文化遭到摒弃:“我(华顿)幼时那样精致优雅的世界已经退入了历史之中,只有最勤奋的考古学家才能挖掘出一小部分;而即使是其中的小小碎片也变得值得收藏,应当在最后几个还留着旧时记忆的人和它们一起被时间淘汰并遗忘之前,将它们重新拼凑。”[2]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华顿开始对她童年时代的纽约社会——她曾觉得它是十分局限的——怀念起来。在她看来,传统与现实生活严重脱节,社会早已被金钱与权势所侵蚀,人际关系也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下被不断疏离、物化。而怀旧则具有情感方面的抚慰作用, 可以充当理想主义遭遇现实撞击时缓解人们痛楚的软垫[3]。因此,文中反复出现的老祖先画像、作为传家宝的箭形胸针、阿切尔对东湖牌家具的执念以及博物馆所特有的凝固时间的内涵都在表达华顿对传统秩序的眷恋,她试图从逝去的文明中探寻并传承一些她认为稳固安全的东西,从而与过去和解并改善当下的困境。
一、物的书写:抒发怀旧
怀旧常与物紧密相连。霍克(Derek Hook)认为,相当一部分怀旧具有恋物癖性质[4]。营销学视角的怀旧研究多围绕物展开,目的在于揭示如何借助商品中凝结的怀旧情感,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而社会学者则更关注物作为怀旧课题所蕴含的生命意义[5]。《纯真年代》的情节并不复杂,但是其中充斥着大量关于物件的书写,如纽约贵族的衣着服饰:埃伦出场时,“身穿低领深蓝色丝绒晚礼服,还用一个很大的老式别针系着一条很夸张的腰带”[1],由此,埃伦无拘无束、脱离传统的形象便呼之欲出了。
除此之外,小说也刻画了不少具有深厚历史沉淀的物品,这些物品或许并不像交通工具、服饰以及建筑那般显眼,但却不时透露着作者对历史以及记忆的传承与延续。文中阿切尔祖父的相片、梅在赢得射箭比赛时获得的胸针以及阿切尔钟爱的东湖牌家具都经历了时间的洗涤,承载着历史的风貌与文明的积淀。记忆越少在内部被体会,它对外部支持和有形提示物的需求就越多。这样的记忆除了拥有记忆的身份以外,已经不存在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会迷恋档案,它标志着某一时代,我们不仅试图在其中保存所有的过去,也试图在其中保存所有的此刻。因此,从这些看似不经意的书写中,华顿对那个旧时代的怀念便跃然纸上了。祖先的肖像以及为了传给后代而制作的胸针便成了诺拉笔下的“记忆场”,即“被作为社会记忆之焦点的象征化的物件”[1],而对这些物件的强调也是华顿对现代社会担忧的另一种表达。
小说对阿切尔祖父相片的描写虽然只有寥寥几字,但暗含着华顿对历史与过去的深切怀念。当久居欧洲的埃伦突然来到纽约社会时,人们对她的经历充满好奇,因此阿切尔太太便邀请“有着收藏家一般的耐心与博物学家一般的知识”[1]的老杰克逊先生前来家中共进晚餐,然而阿切尔一家却对饮食极不关心,将其视为“粗俗的享乐形式”[1]。这引起了老杰克逊先生的不满,于是便借用阿切尔祖父吃大餐一事来暗讽餐食的简陋与寒酸:“杰克逊抬眼看一看烛光下挂在昏暗墙壁上深色相框里的阿切尔、纽兰以及范德鲁顿家族先人的画像……画中人系着宽领带,穿件蓝外套,身后是一所白色柱子的乡间别墅。”[1]从这一描写中,我们可以窥见阿切尔将已逝祖先的画像悬挂于家中,而这一行为有效防止了后代对于过去的淡忘。纪念的意义在于提醒,这一画像似乎是在提醒人们曾经存在过的稳定和谐的老纽约旧社会。将祖先画像悬挂于餐桌之上,这一纪念行为能“确保那些需要记住的东西总是靠近意识的表层,并处在道德认知的核心”[6]。墙上挂着的这幅祖先的肖像画不仅反映出阿切尔家族对其祖先的缅怀,也映射出华顿对老纽约传统秩序的留念。而这一情感在小说结尾对于过去的感慨中也有迹可循,“以前在纽约,最快速的通讯方式是靠穿铜纽扣制服的信差的那两条腿,这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1]。“一去不复返”正体现了华顿对于19世纪70年代纽约的眷恋。
此外,对胸针及东湖牌家具的书写也强调了华顿在小说中传达出来的怀旧情结。当阿切尔与梅最终成婚,来到纽波特度假时,梅凭借着其高超的射箭技术,赢得了一枚“钻石包头的箭形胸针”[1],对于这一价值不菲的奖品,明戈特老太太称赞道:“这可真是传家宝呢,亲爱的,你一定要把它传给你的大女儿。”[1]物件的传承也有助于个人记忆的加强,传家宝能让人想起与它们有关的祖先,或者至少是它们传承过程的最近阶段[6]。同时,尽管时过境迁,阿切尔始终不舍得丢弃他那张东湖牌书桌。三十年前,在与梅结婚后,她便全权操持着新家的装修,而纯正的东湖牌书桌是阿切尔唯一能自己决定的家具,三十年后,他仍保留着这张书桌,尽管它早已过时,显得陈舊老气。在阿切尔眼里,这张书桌是他三十年经历的见证,他在这里阅读新奇有趣的人类学书籍,注视书桌上梅在恋爱初期送给他的照片。对阿切尔来说,这张书桌也有着厚重的历史感。华顿不仅把自己看成一个具有忧患意识的历史学者,还把自己当成是可以转换阶级和改变礼仪的历史学者,她的作品也被看成20世纪复杂的文化和政治环境中的一部分[7]。因此,华顿对这些怀旧情节的安排也表达了其对当下的忧虑,以致其发出“传统的生活方式也有其好的一面”的感叹。
二、空间的选择:缅怀历史
小说中,阿切尔与埃伦在博物馆的最后一次单独见面将故事推至高潮。而博物馆这一场景的选择也暗含深意,它具有扭转时空的功能,将历史永远定格,而从空间上来看,它又能将归属于某一地方的珍宝掠夺而来,机械地将其置于完全陌生化的环境之中。因此在书中,华顿便借主人公埃伦对博物馆的批判表达了其对历史的怀念与留恋。
在得知埃伦将留在纽约后,阿切尔迫切地想要与其见面,因此他们便相约于艺术博物馆,“穿过走廊来到一间无人问津的房间,里面陈列着的‘查兹诺拉古代文物在孤独中渐渐消逝”[1]。为躲避外界的眼光以及流言蜚语,阿切尔选择了人烟稀少的纽约艺术博物馆。但事实上,阿切尔参观过巴黎美术展览会,认识不少画家,而埃伦也对艺术颇感兴趣,因此,对处于上流社会的阿切尔与埃伦来说,博物馆绝不是一个隐蔽之处。此外,学者米尼奥指出这一博物馆并不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小说始于19世纪70年代初,而阿切尔收到伦敦书商寄来的新书《米德尔马契》则于1872年首次出版,同年阿切尔与梅结婚,而后文又提到阿切尔在“他们结婚已经快两年了”时对这不冷不热的生活感到厌倦,由此可以猜测两人的见面大约是在1874年到1875年之间。但在那个时候,纽约艺术博物馆位于西14街的道格拉斯大厦里,直至1880年才搬至中央公园。这绝非华顿的失误,在弗雷德里克·韦格纳编纂的《一个小女孩的纽约》一书中,曾提到华顿的叔叔弗雷德-莱茵兰德有在中央公园建立艺术博物馆的宏伟梦想[7],并于1902年担任该博物馆的董事会主席。此外,华顿在自传中也表明自己与1910年担任董事会成员的爱德华·罗宾逊相识。因此,华顿对纽约艺术博物馆的历史应该十分熟悉,即使是在回忆往事时也不会犯这样的错误,故而博物馆这一意象似乎意有所指。
首先,从华顿对馆藏物品的描写及埃伦对此的评价中,可以看出作者对被遗忘的历史的惋惜。“玻璃搁板上堆满了破碎的小物件——几乎无法辨认的家用器皿……褪了色的铜制品,还有因年代久远根本看不出什么东西做的小物件”[1],埃伦从这些馆藏品中感受到时光的流逝与无情,这些对“那些已经被遗忘的人们来说”[1]必要的物品却在时间的冲刷中被贴上了“用途不详的标签”[1]。学者潘宝曾指出,所有物品都有其物品表征与展品表征,物品表征体现固有的文化属性,而展品表征则是将其置于博物馆这一特定空间之后产生的,博物馆为物品表征创造了新的场域,这种场域赋予物品脱离其原有文化生境的力量[8]。当物件被摆到博物馆后,其过去与现在被割裂,而由于受到技术的限制,其原始功用也就不得而知了。或许对当下来说,博物馆有助于传承文化遗产、了解文明进程,但对处于过去的人群来说,这是一件“残酷的事”,这些物品最终只能被人们“放在放大镜下猜测”[1],而其原始价值在这一过程中被不断剥夺,最终只剩下展览价值。当华顿对一战后的社会秩序彻底失望之后,她试图通过怀旧以“返回到过去的历史当中,从既有的生存经验那里寻求帮助”[9],但那些承载历史与经验的物件却在博物馆的陈列之中被淡化了其原有的社会属性,如今仅仅作为几百年前的象征而展示于众。因此,埃伦对于馆藏文物的评论反映了华顿对历史与记忆的追寻,体现了其在迅疾飞逝的岁月中想要记住什么、留住什么或拥有什么的心理。正如学者尼古拉斯·丹姆(Nicholas Dames)所言:“怀旧是一种缺席,它所缺乏的正是以其最纯粹形式呈现的记忆。”[10]
其次,博物馆也表达了华顿维护旧秩序的愿景。阿切尔与埃伦身处的查兹诺拉古代文化是通过殖民掠夺而来,有着帝国主义历史背景。查兹诺拉曾任美驻塞浦路斯领事,并痴迷于当地文物挖掘,其在任职期间,从近7万座坟墓中收集了3.5万件文物,并出售给大都会博物馆[11]。对查兹诺拉来说,这些文物仅是战争的延伸与胜利的象征。文物的返还问题历来饱受争议,部分考古学家推崇博物馆的普世性价值,而另一些学者则对此持怀疑态度,认为这一观点掩盖了殖民侵略的事实,是对帝国主义的辩护。小说中,埃伦对博物馆的谴责也间接表明了华顿的反殖民主义倾向。在华顿看来,每一件物品都有其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语境,而用暴力手段进行抢夺并归为己用是一种粗鄙野蛮的行为。将文物归还给其所属国是为维护事物之间原有的和谐秩序,使其能在固有的、熟悉的文化语境中找到归属感与认同感。尽管华顿此时已经回到故土,但面对战争时,她和这些身在异处的文物一样,只觉颠沛流离,丝毫没有归属感可言。而归属感正是怀旧的核心,怀旧情结发端于归属感的缺失,终结于和谐人际纽带的重建。因此,华顿借博物馆这一富含历史意义的空间表达了其对逝去的旧秩序的缅怀。
三、结语
在目睹了当下纽约社会的混乱与无序之后,华顿意识到如今的现实社会与其回忆中的美好社会相背离,这引发了其对传统价值理念以及和谐融洽的人际关系的追寻。她把理想寄托于过去,以求缓和社会断裂与剧变带来的焦虑与伤痛,在对过去的怀念中重拾归属感与认同感。
参考文献
[1] 华顿.纯真年代[M].赵明炜,译.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
[2] 华顿.回眸一瞥[M].乐欢,译.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
[3] 梅丽.从《长日留痕》看英国“二战”后的文化困境[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8,41(1).
[4] Hook D.Screened History:Nostalgia as Defensive Formation[J].Peace and Conflict:Journal of Peace Psychology,2012,18(3)
[5] 戚涛.怀旧[J].外国文学,2020(2).
[6] 丘比特.历史与记忆[M].王晨凤,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21.
[7] 潘建.美国作家伊迪丝·华顿研究述评[J].外国文学研究,2002(1).
[8] 潘宝.空间秩序与身体控制:博物馆人类学视域中的观众[J].中国博物馆,2014,31(4).
[9] 赵静蓉.现代人的认同危机与怀旧情结[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5).
[10] Dames N.Amnesiac selves:Nostalgia, forgetting, and British fiction 1810-1870[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11] Tomkins C.Mercbants and Masterpieces:The Story of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M].New York:Dutton,1970.
(责任编辑 夏 波)
作者简介:朱菁菁,上海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