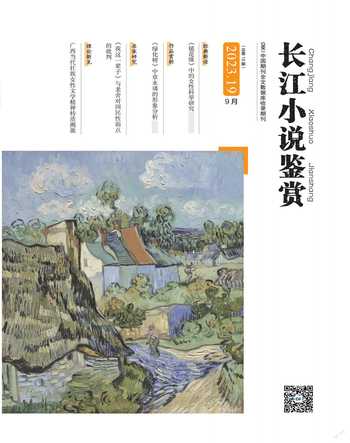后现代女性主义视域下马尔克斯小说中的 女性形象解读
[摘 要] 加西亚·马尔克斯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作品里都时常流露出对女性的赞美和肯定。他对女性的思考与后现代女性主义思想不谋而合。本文运用后现代女性主义思想分析马尔克斯《霍乱时期的爱情》《爱情和其他魔鬼》《百年孤独》三部小说中的三位女性费尔明娜、谢尔娃、乌尔苏拉,揭露拉美地区乃至全世界女性面临的共同际遇和命运。
[关键词] 加西亚·马尔克斯 后现代女性主义 女性形象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2881(2023)19-0073-06
在欧洲历史长河中,“女性主义”思想由来已久。柏拉图曾在《理想国》中提出男女平等的思想,并支持男女平等地接受教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想萌发,主张个性解放和男女平等。薄伽丘在《十日谈》中表达了男女平等的思想,提高了女性的地位。启蒙运动时期,伏尔泰提出“人人生而平等”的主张。
“女性主义”(feminism)一词起源于19世纪末的法国,与“妇女解放”同义,20世纪初传入我国被译为“女权主义”。李银河认为:“无论称这一种思潮和运动是‘女权主义还是‘女性主义,归根结底是对男、女两性客观上不平等现状的具体研究,女性主义理论就是对女性屈从地位的批判性解释,最终消除两性之间不平等。”[1]也就是说,女性主义首先旨在为女性争取与男性相同的平等权利,其次力求改变女性的边缘地位,同时反对以男性为主导的性别压迫与性别歧视。到目前为止,女性主义的发展共经历了三次浪潮,其中后现代女性主义(Postmodern feminism)作为第三次浪潮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受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思潮的影响,不同程度地接受了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福柯、拉康和德里达等人的思想,其中福柯对其影响最为深刻。后现代女性主义是一个新型的女性主义理论流派,但其理论思想并不统一,具有颠覆性、挑战性、观点众多且松散等特点。后现代女性主义的主要思想包括:反对一切宏大的理论体系,试图建立一种社区理论;受福柯的影响,对其话语即权力理论、标准化或正常化及惩戒凝视观点和有关身体的思想进行了吸收和借鉴,想要发明女性的话语,反抗被男权压迫的命运;反对二元对立,提倡多元化;反对本质主义和普遍主义,主张差异性,尤其注重区分阶级、民族、国家等的差异性。
拉美妇女运动萌芽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蓬勃发展。受女权主义运动的影响,拉美妇女运动也强调男女平等,努力争取女性各项权利。加西亚·马尔克斯从小就受到拉美民族文化的熏陶,他曾在《番石榴飘香》中指出拉美社会就是一个“母系社会”,也曾多次表示女性对他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他说过:“如果不充分估量妇女在我人生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就不能如实地了解我的一生。”[2]在《活着为了讲述》中,他认为:“母亲、妻子和家族里的其他女人,铸就了我的性格和思维方式,她们个性坚强,心地善良。”[3]马尔克斯也曾明确表示:“因为有了女人,历史才继续前进。表面看来,男人是历史的主角,但是如果说他们是历史的主角的话,那是因为在他们背后某个人在支撑着世界;而这某个人就是女人。”[4]因此,虽然他并没有明确表示自己对拉美妇女运动的支持,也没有明确表示支持女性主义思想,但是女权主义运动对他的女性观产生了间接的影响。马尔克斯塑造了众多女性形象,虽然其中不乏悲剧形象,但也有很多女性致力于追求男女平等。她们充满个性,又独立自主。马尔克斯在作品中体现男女性别差异性的同时,也更突出女性的独特价值。她们大多属于边缘人物,受性别、宗教、种族的压迫,但仍努力追求属于女性自己的话语体系和生命价值。马尔克斯笔下的女性群像也再现了现代拉丁美洲女性独特的精神面貌、生存现状以及社会地位。笔者将以后现代女性主义为研究视角,采用文本细读的方法,深入探讨马尔克斯作品与后现代女性主义思想的相似之处,以此来完善其小说对于女性形象的阐释。
一、争夺话语权力和主体意识的女性
“话语”和“权力”都是福柯哲学思想中很重要且较为复杂的词汇。在福柯的思想中,话语对于人类来说十分重要,因为它是一项重要的活动。“话语是人们进行思考、产生意义的方式,并且无论是身体、思想或是情感,它们只有在话语的实现中才有意义。”[5]可见,话语在社会生活中具有框架性特点,人类的一切劳动和思考都会受到话语的支配,它在人们的生活中具有决定性作用。同时,话语和权力密切相关。在福柯看来,权力和知识能够构成话语,而有权力的地方就一定有反抗,反抗会形成新的知识,进而拥有新的权力。后现代女性主义者受到福柯的影響,对话语中蕴含的权力力量感兴趣,进而提出重建女性话语权,重塑女性的主体意义。后现代女性主义者认为,目前世界上的话语只属于男性,主张女性要有自己的话语,有自己的声音。她们认为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要以自身的名义来讲话,而不是女性一直附和男人的话语。“迄今为止所有的女权主义文字一直是在用男人的语言对女人耳语。我们必须去发明 ,否则我们将毁灭。”[6]也就是说,后现代女性主义者认为,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中,妇女一直处于“失语”状态。女性往往围绕着男性霸权话语来表达自我,但这其实并不是女性自身的思维方式。女性若想寻找和认识真实的自我,就必须要掌握话语权,构建主体意识。
很多作家笔下的女性都在有意无意中被塑造成男性的附属品。她们是纯洁美丽的女性,却不是有独立意识的女性;她们是为男性奉献牺牲的女性,却不是热爱自我的女性。像《阁楼上的疯女人——女作家与19世纪的文学想象》中所描述的那样,“但丁笔下的贝雅特里齐、弥尔顿笔下的人类之妻、歌德笔下的玛甘泪到莫帕尔笔下的‘家中的天使等,都被塑造成纯洁、美丽的理想女性或天使,但‘她们都回避着她们自己——或她们自己的舒适,或自我愿望,即她们的主要行为都是向男性奉献或牺牲,而‘这种献祭注定她走向死亡,这‘是真正的死亡的生活,是生活在死亡中。”[7]这些女性就是男权控制下的典型女性,男权规训着她们的喜好,约束着她们的思想。无独有偶,在《霍乱时期的爱情》中,虽然费尔明娜是一个不甘屈服、坚守自我且具有反叛精神的女性,她反抗着父亲的命令、侯爵府的各种礼教约束和丈夫乌尔比诺医生去世后对她生活的约束,但是她依旧为他们的要求而妥协甚至牺牲自己。父亲看似随意地对她说“想想看,要是你母亲知道你被一个乌尔比诺·德·拉卡列家族的人看上了,她会是什么感觉啊”[8]。于是她牺牲了自己的婚姻,接受了乌尔比诺医生的追求。面对婆婆的指责,“我不相信一个不会弹钢琴的女人会是一个体面的女人”[8],她也选择了牺牲与顺从,而唯一争取到的也不过就是把钢琴换成了竖琴。面对丈夫的背叛,即使有过失望、有过离开,她最终只能回归家庭,顺从丈夫的喜好,牺牲自己的生活。只要费尔明娜在男权社会里生活,她就不得不回避着真实的自己,为父权夫权做奉献或牺牲,献祭着她的喜好和生命。
幸运的是,当费尔明娜义无反顾地决定与弗洛伦蒂诺踏上“新忠诚号”时,她便能够完全摆脱男权社会带给她的多重压迫,获得自己的话语权。“她亲自安排了这次旅行的细节”,“半打棉制衣服、梳妆和洗漱用品、一双登船和下船时穿的鞋子,还有旅行中穿的家用拖鞋,此外别无其他:这是她一生的梦想”[8]。就像福柯所说的,“那些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疯人乘客是去寻找自己的理性”[9]。费尔明娜在“新忠诚号”上能够轻松自在地寻找自己的理性,而这里的理性就是费尔明娜摆脱男性话语权的枷锁,成为话语的生产者。在这里,她成为轮船上的女王,拥有了自己的话语权。弗洛伦蒂诺以她为中心,她可以做任意想做的事情,“她以女主人和夫人的身份占据了总统舱”[8],甚至当她在返程的航船上看到熟悉面孔而感到沮丧时,弗洛伦蒂诺也是以保护她为己任,为她升起霍乱的黄旗,让她能够愉快地享受旅程。
但是,“新忠诚号”虽然能够净化费尔明娜的灵魂,将她带往平等、自在、充满自主权和话语权的世界,但是那个世界还只是一个桃花源,并没有让费尔明娜彻底摆脱现实社会带给她的枷锁。就如同福柯认为水域有净化作用,但是“航行使人面对不确定的命运”[9]。航行使她拥有的只是一种不确定的命运和权力,并不是恒久的。因此,虽然马尔克斯最终为费尔明娜的生活提供了一个乌托邦乐园——“新忠诚号”轮船,但是女性在现实生活里并没有摆脱男性话语权的束缚。费尔明娜向往的生活是拉丁美洲众多女性乃至后现代女性主义者们所向往的,但她的现状也是众多女性现状的缩影,她们追求的话语权还没有真正在现实社会中实现。
二、反抗多重压迫和性别歧视的女性
福柯的正常化思想是根据男性话语来制定的标准,以男性话语为尺度告诉社会何为正常,何为反常。后现代女权主义者通过对福柯的标准化和正常化理论的阐释,认为面对社会给予女性的枷锁,为女性设置的种种纪律规范,女性往往会无意识地去服从,“自己制造出自己驯服的身体”[10]。女性就是在这样的标准下受到男性社会的凝视和惩戒,女性的地位也长期受到男权的压制。对于凝视惩戒,福柯认为:“用不着武器,用不着肉体的暴力和物质上的禁制,只需要一个凝视、一个监督的凝视,每个人就会在这一凝视的重压之下变得卑微,就会使他成为自身的监视者,于是看似自上而下的针对每个人的监视,其实是由每个人自己加以实施的。”[11]在后现代女性主义者看来,女性长期受到来自性别、种族、宗教等的多重压迫和歧视。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女性会本能地遵从男性制定的规范,自我约束,自我管制。黑人女性主义代言人贝尔·胡克斯指出黑人妇女“忍受着性别歧视、种族歧视和阶级歧视的压迫”[12],在胡尔斯看来,生活中的女性,尤其是黑人女性都受到了来自性别、种族和阶级的多重压迫。因此,后现代女性主义致力于追求女性社会地位的平等,她们反对多重压迫和性别歧视,但并不意味着要用女性权力来压迫男性,而是要消灭创造了多重压迫和性别歧视的社会制度。
在《爱情和其他魔鬼》这部中篇小说中,修道院便集男权和宗教压迫、种族歧视、文化冲突于一身,它是女性受到多重压迫和种族歧视的集中营。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说到“隔离是实现彻底服从的首要条件”[13],圣克拉拉修道院仿佛监狱一般将修女们关在里面,与公共空间隔绝。“自从选择了安贫恭顺和守贞,她们和外面唯一的接触就是偶尔在会见室接受探望,那里隔着木头百叶窗,听得见声音,却看不见人。会见室设在大门口,规矩很多,管得很严,而且每次会见都要有监听的人在场。”[14]修道院里的女性被无情地关着,不仅要劳动生存,还要面临着管控与监视。马尔克斯利用修道院里牢房的空间,展现了女性面临种族歧视和宗教残害的集体命运。修女们面对种族歧视、宗教压迫、精神摧残和身体奴役的多重困境,她们的境遇就是整个拉美殖民社会下女性生活状况的缩影,其中主人公谢尔娃便是众多受害者之一。她虽然是卡萨尔杜埃洛侯爵的独生女,但是她从小被黑人管家抚养,除了肤色以外,她的语言、行为甚至生活习惯都秉承了非洲和印第安人的传统。谢尔娃在一次外出中不幸被疯狗咬伤,虽然没有出现患狂犬病的症状,但侯爵还是束手无策只能求助主教。“你可怜的女儿在地上滚来滚去,抽搐不已,嘴里狂吠异教徒的黑话,这已是人尽皆知的秘密了。这些不正是魔鬼附體的明确无误的症候吗?”“尽管你女儿的身体治不好了,上帝总还是给了我们办法来拯救她的灵魂。”[14]可见,主教在乎的并不是谢尔娃是否得了狂犬病,是否能够医治她的身体。所谓的魔鬼附体,也不过是谢尔娃的黑人异教徒言行受到了来自宗教、种族的歧视。最终在主教的旨意下,侯爵只能将年幼的谢尔娃送进圣克拉拉修道院,让主教为她实施驱魔活动。面对宗教压迫和种族歧视,谢尔娃的一切行为都被打上异教徒的烙印,无论是侯爵、主教还是修道院的修女们都一致认为她被魔鬼附身。只有不信仰宗教法庭的阿布雷农肖医生才认为谢尔娃是无辜的、正常的,“宗教法庭更喜欢把无辜的人放到刑具上肢解,或是当众架在火上活活烧死”[14]。
尽管谢尔娃被关在毫无人性的修道院里受着非人的虐待,但她并没有因此服从管控和压迫,她用自己的努力反抗着种族歧视和宗教压迫。面对修女们的欺负,她横冲直撞将一切清静打破,把修道院搅得混乱不堪。当主教为她驱魔时,她用高声叫喊表达自己的不满与反抗。谢尔娃想要获得自由,并要求德劳拉带她离开,可是对宗教的坚定信仰使德劳拉想要用合法的手段证明谢尔娃没有被魔鬼附身。当谢尔娃再也等不到爱人来看望她时,她便采取极端的手段,开始绝食,“她以一种撒旦的凶猛面对主教,嘴里说着各种各样的语言,不时发出地狱里禽鸟的悲鸣”[14]。最终她为爱而死,也得到了彻底的解脱,摆脱了性别、种族、男权对她的迫害。
虽然谢尔娃对社会给她的多重压迫和性别种族歧视进行了反抗,但是她的反抗却以生命为代价。无独有偶,小说中马尔蒂娜也是一位敢于反抗宗教、追求自由的女性。最终,她顺着下水管道逃离了修道院,获得了向往的自由。即使她逃脱成功,但是她仍身处拉丁美洲的社会中,依旧无法摆脱家庭、宗教和社会给她的压迫。因此,无论是谢尔娃还是马尔蒂娜,看似她们都反抗成功了,但实则她们都是采取极端和黑暗的手段获得了自由,并不是正大光明地摆脱了压迫和摧残。她们的悲剧命运意味着依旧有众多女性在多重压迫和种族歧视的社会下艰难生存。
三、打破从属地位和二元对立的女性
传统的二元对立将男性与女性区别对立开来。男性居前女性居后,男性是一切积极正面的标志,女性则是消极负面的存在。二元对立论贬低女性推崇男性,女性只能依附于男性而存在。二元对立论在西方传统文化中一直占據主导地位,后现代女性主义反对这一观念,反对将男性女性完全对立起来。她们用批判的眼光看待男性主导的二元对立,认为这对女性是不公平的,主张女性应该抵抗和摆脱男性施加给她们的从属地位和既定秩序。后现代女性主义提倡多元化,她们认为当下的社会仅仅局限于以男性为主体,女性的主体意识一直被排斥在边缘地带,从属于男性,不被社会承认。她们认为女性的主体意识不应该被历史遗弃,需要得到身份认同,改变从属地位。后现代女性主义并不是要消灭男性,而是旨在强调男女两性本是协调的统一体,改变男女二元对立局面,形成一个以差异为基础的两性关系和谐共存的社会。
在传统的二元对立论看来,男性是理性的,而女性是非理性的。而在马尔克斯看来,表面上男性是历史的推动者,是历史的主角,但其实在背后支撑着整个世界的是处于从属地位的女人。在他眼中,女性具有很高的地位和价值,“男人们不是沉迷战争,就是在情妇的裙子底下寻欢作乐,而女人们则固守家园,维护家族的稳定与团结”[15]。《百年孤独》中,乌尔苏拉是马尔克斯塑造的一位理想型女性,她伴随着整个布恩迪亚家族走过了近百年的历史,她是整个家族的灵魂人物。在她的世界里,不仅仅有家、丈夫、子女和房子,她还心怀整个马孔多。她为人民的稳定生活、家族的兴衰荣辱做着力所能及的事情,于危难之中多次挽救马孔多。乌尔苏拉既慈爱善良又细腻温柔,既坚韧勇敢又理智独立。她身材瘦小,却精明能干,用自己强大的生命力支撑着布恩迪亚家族,养育家族的子孙。在这个男性主导的社会里,她凭借一己之力,维系着家族的血脉延续,不仅改变了人们心中对女性的传统看法,还赋予女性新的价值。当丈夫醉心发明时,她是家中唯一的顶梁柱,支撑起养家的重担。当丈夫受吉卜赛人蛊惑时,她理智地“发动全村的人加以抵制”[16]。当丈夫异想天开地想要迁出马孔多时,她将村里所有女性联合在一起,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努力反对男人离谱的想法,“我们不走,就留在这儿,因为我们已经在这儿生了一个孩子”,“如果非要我死了才能留下,那我就去死”[16],勇敢坚定地保全了马孔多的稳定生活。除了顶撞丈夫,她还违抗神父的意愿为皮埃特罗·克里斯皮举行宗教仪式并将他葬在公墓里。她带领着家中的女人们经营糖果生意,将家宅进行改造,而家里的男人们却整天游手好闲,沉迷战争和女人。无论是蛮横无理的阿尔卡蒂奥在马孔多肆无忌惮地进行军事独裁、迫害民众,还是当奥雷良诺·布恩迪亚将军判决处死蒙卡达将军,她都挺身而出,干预他们疯狂的行为。哪怕当她老到被家族逐渐遗忘的时候,她还试图亲自教养孩子。在乌尔苏拉的世界里,她不被男权制的权威所束缚,敢于反抗男性,镇压他们的疯狂举动。她用自己的努力消解着男性中心主义,打破了二元对立对女性的偏见,为女性赋予价值,她比那些男性都更有魄力和远见。
但是,乌尔苏拉最终还是被遗忘了,她先前为家族所做的努力最后都付诸东流,因为她一直赖以维系的家族是靠乱伦建立起来的,而它最终也会在乱伦中消失。无论乌尔苏拉如何以超凡的生命力维护家族稳定与延续,一切终将化为乌有。就算乌尔苏拉有着男人所不能有的理性、坚强、智慧,但她依旧不能改变整个社会的传统文化。布恩迪亚家族在大陆上消失后,社会仍旧以它固有的姿态发展。女性还没有真正摆脱自身的从属地位和两性二元对立的状态。
四、结语
马尔克斯笔下的女性不是渺小的个体,她们虽处境艰难且总是感到孤独无力,但她们依旧有巨大的能量,她们代表着女性整体。“马尔克斯小说中的女性人物不是单纯的美学形象,而是一个民族的微观粒子,在她们身上浓缩着整个拉丁美洲社会存在的症结。”[15]马尔克斯在《番石榴飘香》中曾说妇女能给他带来安全感。在他的笔下,我们可以看到女性很多时候虽然不能掌握自己的话语权,但是她们一直在努力争取。她们能够有自己的意识和想法,能够努力去追求身体和精神的自由,即使失败了,也不曾放弃。虽然马尔克斯在女性主义思想上始终保持中立地位,但是我们可以从他塑造的女性形象身上,体会到他对女性自由意识、反抗精神的欣赏和肯定,同时也对社会现实给予她们的压迫和残害表示同情。马尔克斯在一些女性形象的塑造上也与后现代女性主义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处,尽管这些女性的反抗要么被人遗忘,要么是以离开流浪而告终,要么是以死亡告终,终究不能彻底摆脱男权社会和宗教世俗带给她们的禁锢和摧毁。
谢尔丽·桑德伯格曾说:“作为女性,我们需要感激自己拥有的一切,但不能满足于现状,因为这种不满足感会激励我们做出改变,我们应该坚持下去,为实现真正平等的行动还在继续,这么做不仅仅是为了曾经努力奋斗的数代人,也是为了继续奋斗的数代人。”[17]虽然后现代女性主义思想比较松散,理论观念并不完善,也受到了诸多质疑。但不得不承认,它为女性解放事业和男女平等观念做出了努力,提供了新的方向和动力。从马尔克斯的作品中我们能够了解到,女性解放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并没有彻底地实现,路途还很艰辛,需要我们数代人为两性最终平等和谐相处努力奋斗,因为这并不只是女性的真正解放,同时也是在解放男性,是为了实现两性真正的解放。
参考文献
[1] 乔蕤琳.女性主义的后现代转向与新型女性文化的建构[D].黑龙江大学,2014.
[2] 马尔克斯,门多萨.番石榴飘香[M].林一安,译.海口:南海出版社,2015.
[3] 马尔克斯.活着为了讲述[M].李静,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6.
[4] 尹承东,申宝楼.马尔克斯的心灵世界——与记者的对话[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
[5] 张国昌.福柯与女权主义文学批评[D].兰州大学,2010.
[6] Kourany J A,etal.Feminist Philosophies[M].Prentice Hall:New Jersey,1992.
[7] 朱立元.当代西方文学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8] 马尔克斯.霍乱时期的爱情[M].杨玲,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5.6
[9] 福柯.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10] 李银河.后现代女权主义思潮[J].哲学研究,1996(5).
[11] Ramazanoglu C.Up against Foucault,Explorations of Some Tensions Between Foucault and Feminism[M].Routledge:London and New York,1993.
[12] 胡克斯.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M].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13] 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14] 马尔克斯.爱情和其他魔鬼[M].陶玉平,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5.
[15] 沙丹.论加西亚·马尔克斯小说的女性书写[D].江苏师范大学,2020.
[16] 马尔克斯.百年孤独[M].范晔,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1.
[17] 桑德伯格.向前一步[M].颜筝,曹定,王占华,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
[18] 王淼.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
(责任编辑 夏 波)
作者简介:姚晓宇,内蒙古师范大学,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基金项目:内蒙古师范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2022JBXC004;2023年内蒙古自治区硕士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项目编号:S20231061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