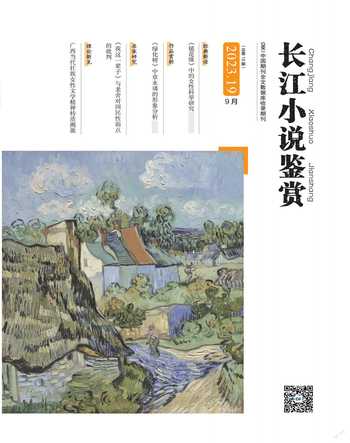论古尔纳《赞美沉默》中的阈限性
[摘 要] 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是一名围绕后殖民、流散、难民、记忆、身份等主题进行创作的作家,其作品大多借助个人早期经历,围绕难民主题,描述殖民地小人物的生存状况。本文旨在通过分析古尔纳的长篇小说《赞美沉默》中的阈限表征再现该作品的主题。作为一个游走在两种文化之间的“双重他者”,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陷入了身份认同困境的阈限人物。经历暴力革命后的桑给巴尔社会短暂地陷入了阈限。通过剖析革命爆发的原因,西方权力话语对殖民地国家的影响得以显现,并且人们在此背景下的生活体现了社会阈限阶段底层人物的无奈与痛苦。此外,古尔纳在小说中描绘了一个阈限性区域——“飞机”。在此空间中,沉默的个体平等地对话,形成了一个共同体——“我们”,诉说了边缘人物真实而苦痛的经历。古尔纳在《赞美沉默》中反思了殖民主义对非洲流散者身份建构和殖民地国家和人民前途命运的影响,书写了难民的记忆,呈现了个体眼中的历史。
[关键词] 《赞美沉默》 古尔纳 阈限性 身份危机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2881(2023)19-0051-06
《赞美沉默》(Admiring Silence)是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Abdulrazak Gurnah)于199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小说通过讲述一位无名的跨国难民的故事展示了流散者的生存体验。现有关于该作品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移民身份、叙述声音、“沉默”之作用等方面。本文旨在从阈限理论的视角出发再现小说的主题。通过分析该小说的阈限人物、社会和空间,本文挖掘了该小说的阈限性,认为该小说呈现了处于阈限状态的“双重他者”,短暂陷入阈限的桑给巴尔社会,和具有阈限性的间隙空间——飞机。古尔纳通过书写难民群体、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的命运,体现了对于身份认同、记忆书写和西方权力话语的深刻伦理思考。
一、阈限人物与身份认同
“阈限(liminality)”源自拉丁语的līměn,该词义为“门槛、通道”。在英文中意为“间隙性”。“阈限”一词最早出现在普通心理学中,指能引起感觉的最小刺激量,即“感觉阈限”。在人类学中,“阈限”是由比利时人类学家阿诺尔德·范热内普(Arnold van Gennep)首次提出的。范热内普在“过渡仪式”理论中融合了“阈限”的概念,以阐释人类民俗礼仪的总体模式,并分析前现代社会中仪式的机制和人类行为模式。范热内普提出的“通过仪式”分为“分隔(separation)—边缘(marge/transition)—聚合(aggregation)”三个阶段。处于分隔仪式和聚合仪式阶段象征着主体拥有明确的结构位置。而边缘阶段的主体则呈“阈限”特征,即通过者既不在原状态也不在新状态,而是处于无限定状态。他们置身于社会的稳定结构之外,未被结构化,没有清晰的身份地位,在分类上非此非彼或既此又彼[1]。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继承并发展了阈限理论,指出阈限是一种过渡状态,处于正常的文化和社会结构的缝隙。“阈限的实体既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他们在……指定和安排的那些位置之间的地方”;“阈限是仪式过程的核心,处于‘结构的交界处,是一种在兩个稳定状态之间的过渡和转换”[2]。王微认为,文学中存在大量的边缘品质、居间时刻、临界主体、矛盾身份与混杂意识等具备阈限因素的文学表征[3]。对处于阈限状态的阈限主体进行研究,可以更深刻地洞悉人物的生存处境、精神样貌和文化身份等,并有助于揭示文学主题。因此,从阈限视域出发研究主人公的处境,可以更全面地观照他的身份困境,从而挖掘古尔纳隐藏在此人物刻画之下的深层主题内涵。阈限性意味着主体无法被分类,主体也因此面临无法确认自己身份的危险。《赞美沉默》的主人公游离于殖民文化和被殖民文化之间,既不是一个真正的英国公民,也无法融入故乡,长久地滑入了阈限的真空,无法获得清晰的身份认同。
《赞美沉默》中的主人公迫于政治压力来到伦敦,他的非洲人背景使他成为英国人眼中的“他者”。即使他凭借努力成为一名教师,但是面对白人以自我为中心的优越感,主人公经常忍受着种族和文化偏见。小说伊始,四十多岁的主人公受困于心脏的痛苦去看医生,医生不假思索地把他的心脏病归结于加勒比非裔的种族特性,发表了隐含种族歧视观念的诸多评价。这是一种殖民者对被殖民者的刻板印象。此外,主人公还必须面临岳父岳母的不满与发难。“威洛比夫人并没有兴趣听我讲任何故事”,“她在必要时会客套上几句,似乎全然不理交谈中我说话的分量,而且几乎从不抬眼看我”[4]。这展示了威洛比夫人对主人公的轻视与疏离。“当我瞟一眼威洛比先生时,他的目光正在我身上打量,这让我想大喊一声,尖叫着跑入夜幕当中。他渴望听到一个帝国故事,但我的舌头早已僵化变色,我的脑袋也因愤懑而嗡嗡作响。”[4]在威洛比先生眼中,“我”只是他了解帝国故事的渠道。“我”也是一个工具,威洛比先生从“我”身上获取被殖民者在失去大英帝国的指引之后的混乱故事以满足他的白人优越感。同时,“我”不再是一个独特的个体,而是殖民地人民的代表。主人公不仅在生活上要遭受敌意,在工作上亦是如此。“我发现这份新的工作每天都是一种迫害,我则终日担心学生会造反,并最终逼我体会受辱的滋味。我时刻保持警惕,思忖着要在每一天、每一小时存活下来,并绝不沦为野蛮行径的牺牲品。”[4]殖民者对“他者”简单化、脸谱化的认识给被殖民者带来了精神创伤,迫使底层人物只能通过沉默和编造故事进行抵抗。在小说中,医生说“我”心脏有问题,“我恭敬地坐着没有吱声”[4];威洛比先生追问“我”的国家的形势,我尽力渲染混乱的氛围以满足他的想象;爱玛执着地询问“我”家乡的信息,“我”编造故事以满足她的兴趣。然而,这些沉默与谎言是行不通的,它们使主人公更加隐忍,越来越远离真实的“故事”,无法言说自己遭受的不平等对待和往日的苦涩和痛楚,丧失了话语权。“我”变成了“隐形人”,“不仅言语不清,而且羞于开口”[4]。“难民要想真正走向新的生活,就要释放出被压抑的过往,重构自我。”[5]因此,主人公在收到母亲的来信后,便踏上了返乡之旅,寻求自我拯救的方法并寻回自己的家族记忆,以恢复自身身份的完整性。然而,这次回乡之旅让他意识到自己在家乡也成为一个外来人,已不再属于桑给巴尔。
主人公回到家乡后首先面临的是亲人的不满和指责。桑给巴尔经过多年的混乱和恶意统治,只剩下贫瘠和匮乏。令人窒息的生活环境使主人公与亲人之间产生了隔阂。舅父哈希姆对主人公说:“有多久了?我们以为你忘了我们。”[4]经过二十多年的离家生活,主人公与家人仅有几次书信交流,在故乡亲人的眼中,“我”不了解故乡的变化和他们艰难的生活。他们是暴力革命的直接受害者,而“我”却在英国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并且,在“我”拒绝了安排好的相亲并不得已坦白了在英国的生活后,家人认为“我”的行为让家族蒙羞。此外,主人公在英国生活了二十年,他对故乡的记忆越来越模糊,故乡的文化与传统对他而言也变得越来越遥远。因此,他不得不变得小心翼翼,害怕被人当做“异类”和背叛者。“面对曾经熟悉的人们和地方发生的变化,我每天的生活充斥着冲击和纷扰。我觉得自己必须时刻保持警惕,似乎每个人都想抓我的毛病,揣摩我对自己的看法、我说话的方式以及我对礼节的恪守……”[4]当地政府官员邀请“我”参与重建国家的工作。但“我”因知晓当局政府的无所作为——他们以一种资本家的视角看待自己的土地和人民,并不關注人民真正的需求——而不愿与他们沆瀣一气。最终,“我”不得不仓皇逃离桑给巴尔。“小说中的空间环境是具有多重意义的多维存在。”[6]“房间里让人感觉拥挤不堪”[4],这不仅是“我”刚回到桑给巴尔的公寓,面对脏乱的环境时的感受,还描述了“我”对故乡的整体印象。这里的“房间”不仅指公寓,也是主人公关于“家”的心理意象。家园不再是带给“我”温暖的地方和“我”的栖身之所,而是变得“拥挤不堪”。此外,小说结尾“我”在与继兄阿克巴的通信中也表达了“我”对桑给巴尔真实的感受:“然而,那已经不再是家。”[4]
因此,主人公逃离了故乡,返回了英国,却发现被女友抛弃。他最终打算学习水暖课程并以外籍人员的身份为祖国工作。这体现了主人公身份的“混杂性”。正如Zohdi所说:“这些人在他们的生活中一直在两种文化中摇摆,这使他们拥有了融合的身份。”[7]主人公不依附于任何一种文化,无根无依,通过身份的“混杂”寻求着一种自己的生活方式,体现了古尔纳对“漂浮者”的希望与出路的探索和思考。
综上,主人公既不属于英国,也不属于桑给巴尔,他游离于两个国家和两种文化之间,变成了一个“流放者”,无家可归。特纳认为对于“阈限人”而言,“没有地位、财产、标记、世俗的衣物、级别、亲属位置,没有任何可以将他们在结构上界定区分于他们同伴的东西”[8],即他们具有一无所有的否定性特征。主人公正是一个在结构中一无所有的人,是一个被流放的人,在本族群和他者族群、在社会现实和心理意识上都被视作他者。这样的阈限状态不仅使他感受到文化归属上的失落,还强化了他的身份认同危机,因为认同要在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中产生[5],而不论是英国还是桑给巴尔的客观社会环境都缺乏作为认同基础的信任。主人公不止一次表达了自己身份的困惑:“我是个悲剧。这该死的世界充满了混乱,而我是一个迷失的人”[4],“我是一个可怜的流民,过着奴役和虚妄的生活”[4]。总之,通过对主人公这一“阈限人”的塑造,古尔纳展现了后殖民语境下难民的心理状态和生存状况,揭示了难民的归属感的缺失和身份危机问题。并且,通过人物身份的“混杂性”,古尔纳为他笔下的人物探索了一条出路,即不刻意建立对某一种文化的认同,而是在不同文化的影响下寻找适合自己的生存方式。
二、社会阈限与西方话语
结构与交融现象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关系模式,维克多·特纳基于此发展了阈限理论,使它走进了现代社会,给人们提供了从另一种角度理解社会矛盾、社会运作和身份转变的可能。“阈限”也因此成为文化人类学中的重要概念,旨在呈现一种社会文化从稳定的状态中脱离出来,同时向待建立的结构过渡的过程中模棱两可的状态或者过程。小说中的“我”在收到母亲的来信后返回了阔别二十多年的桑给巴尔,却发现故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桑给巴尔的政治、经济、人民的生活都在政治运动的影响下陷入危机。对一个社会而言,集体“面临突发事件”意味着一次社会性阈限[9]。桑给巴尔脱离英国殖民统治后的革命剧变引发了社会秩序的溃败,它从独立前的社会模式中脱离出来,但又没有形成一种稳定的社会结构,桑给巴尔社会短暂地陷入阈限之中。在阈限阶段,社会原有的秩序被重新审视、阐释和组合,社会混沌无序,充满着未知。
1963年12月,桑给巴尔政府宣布独立。桑给巴尔独立后,双重民族主义造成桑给巴尔社会的分裂。事实上,与桑给巴尔的双重民族主义伴随着的是桑给巴尔社会秩序的彻底崩溃。最终引发的结果便是独立一个月之后出现的桑给巴尔革命。这正是小说主人公返回家乡桑给巴尔的背景。小说并未采取宏大叙事来反映此次革命巨变,取而代之的是对故乡变化的描述和对散布在人物生活中的暴力事件的呈现。当局政府的无能以及强烈的种族排外情绪是暴力革命爆发和社会陷入阈限状态的主要原因。但是回顾桑给巴尔独立史,就会发现引起这次暴力革命的原因其实是占据主导地位的殖民权力话语。在英国殖民者来到桑给巴尔实施殖民统治之前,桑给巴尔由于自然条件,与外界交流的机会很少,也不需要建立复杂的社会劳动制度和划分清晰的人种界限。然而随着西方殖民者的入侵并开始以统治话语对殖民地进行种族划分时,原有族群内部的安宁就被打破了。当桑给巴尔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后,英国殖民主义意识形态下的人种身份,又在桑给巴尔内部政党斗争中被强化为政治身份,导致桑给巴尔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与暴力。由此可见,英国人在殖民过程中将自己的种族范式引入了非洲,最终引发了桑给巴尔革命。种族范式是一种被西方殖民者构建出来的模式,对人们的观念、认识和想象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这种范式在殖民地的引入是如此悄无声息,以至于当殖民地人民意识到它时,他们就已经要接受它所带来的后果和寻求应对策略了。因此,古尔纳说:
我们乐于把自己看作谦良温和的人民……文明人,这正是我们……事实上,我们已不再是我们,我们待在各自的院子里,封闭在历史的贫民窟中,自我宽恕并且满心都是偏狭、种族主义和怨恨……并非是我们不懂关于我们自己……当我们开始考虑今后的自己,我们说服自己认为遭受虐待的对象并未留意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或者他们已经原谅了自己并且现在乐意接受一种团结统一和民族主义的论调。[4]
古尔纳认为“我们”受到了言语和西方构建的身份模式的摆弄。“我们”的主体性受到了殖民历史、意识形态和话语权力的影响,“我们”被禁锢在权力营造的种族意识里,最终引发了种族暴力并使社会陷入混乱。
随着社会秩序的溃败,人们的生活也出现危机。首先,人们的物质生活陷入危机,“有些片区的房屋已经弃置坍塌,曾经喧闹的集市被封之后变成了阴暗的街道,破裂的管道把污水泄在狭窄的街道上,蜿蜒的臭水像小溪一样流淌,而人们只能迈步穿行其中”[4]。革命后的桑给巴尔,充满着后殖民时代的真实:房屋建筑被摧毁,基础设施残缺不全,水、电资源以及生活必需品短缺……作者描绘的一个典型是“堵塞的马桶”。通过这一细节,古尔纳向读者展示了恶劣的生活条件以及统治者的无所作为。政府正企图在废墟般的故土上虚构可以得到救赎的假象,而不是去改善堵塞的马桶和为人民解决实际的问题。“阿克巴开始谈论他正着手的项目,即旧殖民酒店的翻新以及周围欧式区域风貌的复原工作。”[4]“而且他俩说什么其实都不重要,因为反正这都可归结到同样的东西:项目、赞助方、聯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工作。”[4]作者讽刺了东非在后殖民时代腐败无能的权力机关。社会陷入短暂阈限还给人们带来了精神危机。首先,长期的政治不稳定导致人们对统治者和国家失去信心。“那是我们的大人物。对他来说任何事情都不过分;对他来说任何卑鄙手段都不足为奇。”[4]“我的继父漫不经心地点了点头,一边又为自己卷了一根烟。乞求施舍,这就是政府现在的样子,他说。”[4]在古尔纳的笔下,非洲对“我”来说不再是“家”,官员们的虚伪言行让“我”反感,故乡让“我”失望。非洲对“我”的家人来说也不再是提供温暖与安宁的港湾,无法给他们提供生存尊严。政府让人们的“生活陷入混乱状态”[4],让社会穷困不已。并且,它还企图遮蔽那段伤痛的历史,将人们“经历的牵强混乱推到看不见的地方”[4]。再者,社会陷入阈限使人们被猝不及防地推进一个陌生的环境中,人们无力应对其中的错综复杂,只能选择忍耐与挣扎。这种过渡状态表明了社会动乱下底层人物无奈的阈限生活。
通过探寻非洲暴力革命爆发的原因,得以窥见西方话语霸权对非洲的影响。正如古尔纳所说:“殖民史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腐败和暴政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是殖民遗产的一部分。”[10]因此,理解非洲问题应从非洲的范式出发,这是对文化和历史的尊重。此外,古尔纳描绘了处于社会阈限阶段的底层人物的生存经验,谴责了政府的无能与腐败,说明了社会动乱会导致人民对国家认同感的缺失和人民的生活也陷入不安与阈限之中。
三、阈限空间与记忆书写
霍米·巴巴在《文化的定位》(The Location of Culture)中,探讨了“居间”这一概念。巴巴论述到:“楼梯间作为阈限空间,居间在指定的身份间,成为符号交叉过程和构建上层和下层,黑色和白色之间区别的连接组织。楼梯间的东来西往,它允许的时间运动和通道,阻止了它两端的身份陷入原初的两级。这个在固定身份之间的阈限空间为文化混合提供了可能性。”[11]如果说楼梯间是一个阈限空间,那么连接两个城市的中间地带——飞机也是特殊的阈限性区域。《赞美沉默》中就描述了这样的间隙地带。主人公乘坐飞机从伦敦返回桑给巴尔。在飞机上,他打破了沉默,与另一位乘客进行交谈。“我发现自己竟然向他讲起自己的旅行以及在英国的生活,并且非常惬意地与他攀谈起来……”[4]“当得知我已离开家乡多年,他更是乐意提供建议和最新消息,而我也并未像自己设想的那样介意。”[4]之后,主人公离开故乡返回英国。在去英国的航班上,他偶遇了一位和自己有相似经历的印度女人艾拉。主人公与之交谈,了解了她的家族历史并讲述了自己在英国的经历。
飞机的物理意义是沟通两座城市,它处于对立双方的中间地带。它的两端分别是两座城市,只有它悬浮在空中,象征着悬而未决的状态。当主人公处于飞机这一空间内,他就正处于一个界限模糊、介于两种空间之间的阈限空间,他将面临生命的无数可能。而当他走下飞机,则又重新回到确定性的社会结构之中。正是飞机的空间阈限性允许主人公跨越边界,吸纳多种声音。因此,正是在飞机内,主人公能够与其他主体的声音发生对话。
在阈限阶段,由于社会法则的消失,个体处于稳固的社会结构之外,产生出了一种暂时平等的社会关系。特纳将这种缺乏社会组织结构的状态命名为“交融”,交融是阈限阶段的人类关系模式[2]。因而,有必要在文本中构建一个独特的阈限空间,以表现交融状态下的社会关系。相对而言,出现在飞机内的个体因为其彼此陌生而预设了身份的平等。飞机内的人可能来自社会各个阶层。飞机的这一特性使之成为最适合主人公的活动空间,因为主人公是一个敏感的“夹心人”,飞机内人与人间无差别的平等才能使他处之泰然。因此,飞机的社会属性支持它成为一个典型的体现交融的阈限空间。交融不仅意味着阶级界限的消失,而且也是一个所有二元对立的、有高下之分的概念壁垒消融的领域,在这一领域中,界限不再清晰,个体之间无差别,因此,在飞机内,主人公得以与其他沉默的个体平等地对话。这时的倾听是对他者他异性的承认,这时的讲述是自我声音的真实表达。在这种倾听与讲述之中,交谈双方因经历相似而短暂地构成一个共同体——“我们”。“我们”的记忆脱离传统的二元对立的文化空间,在裂隙中交织在一起,拼凑出整个难民群体生活的图画。在艾拉讲述自己记忆的过程中,主人公发现他们的感受是如此相似,他们一直都难以摆脱被视为异类的感觉,这体现了移民经历带给人物的创伤和身份认同困惑。古尔纳从历史的受害者的角度出发,将他们的心理状态呈现出来,以小见大,为难以发声的难民群体发声。
综上,飞机连接分离的双方,处于二者的断裂之处。因为它“居间”的位置,它才摆脱了对立双方的约束。最终,它被建构成为一个自由、开放、多元的阈限空间。在这一空间之中,结构性的界限开始消融,所有声音都获得了话语权。主人公因此可以倾听他人诉说自我经历和讲述自己的经历。此外,飞机的社会属性支持它成为一个典型的体现交融的阈限空间。交融意味着界限的模糊和关系的平等。因此,对话的个体们因经历相似而短暂地构成一个共同体——“我们”,“我们”各自的记忆共同编织起了一张大网,诉说着“我们”真实而苦痛的经历,呈现了历史的真相。
四、结语
《赞美沉默》的作者古尔纳以自身移民经历为基础,塑造了一个夹杂在英国与桑给巴尔两种文化之间的阈限人物。他因不被两种文化所接受而落入阈限的真空,他的身份也因此陷入危机。后来,主人公返回桑给巴尔。桑给巴尔社会因暴力革命短暂陷入阈限。通过分析革命爆发的原因,可以看到西方权力话语对殖民地国家及其人民的影响。古尔纳还通过刻画处于社会阈限阶段的人民生活和政府表达了对殖民地统治者的谴责和对故乡的忧虑。此外,作品中还出现了“飞机”这一阈限性区域。“飞机”的阈限特征使主人公可以平等地讲述自己的故事和倾听他人诉说自身经历。于是,具有相似经历的沉默的个体在这一空间内结合成了“我们”这一共同体。“我们”各自的记忆诉说着底层人物真实而苦痛的经历。通过书写难以发声的难民群体的记忆,古尔纳呈现了历史真相,在文学文本中构建了一个多元、混杂的广阔空间,展现了一部建构流亡者主体性的精神史,反映了他对夹杂在文化和地缘裂隙间的难民命运的关切。
参考文献
[1] 范热内普.过渡仪式[M].张举文,譯.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2] 特纳.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M].黄剑波,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3] 王微.文学阈限性社会学起源研究[J].大连民族大学学报,2019,21(2).
[4] 古尔纳.赞美沉默[M].陆泉枝,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22.
[5] 高文惠.古尔纳《海边》中跨国难民的身份叙事[J].外国文学研究,2022,44(5).
[6] 尹锐.划界与跨界:空间批评视域下的《郊区佛爷》[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2(2).
[7] Zohdi E. Lost-identity; A Result of “Hybridity” and
“Ambivalence” in Tayeb Salihs Season of Migration to the North[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and English Literature,2018,7(1).
[8] 特纳.象征之林——恩登布人仪式散论[M].赵玉燕,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9] Thomassen B.Liminality and the Modern:Living Through the In-Between[M].Burlington: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2014.
[10] 古尔纳,谢娟.从自发到自觉的写作——古尔纳获奖演说[J].世界文学,2022(2).
[11] Bhabha H K.The Location of Culture[M].London New York:Routledge,1994.
(责任编辑 夏 波)
作者简介:张雪沛,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