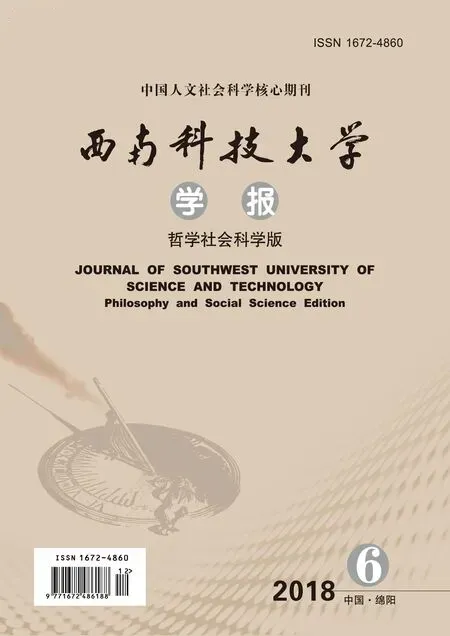西方伊迪丝·华顿短篇小说研究述评
易灵运
(西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四川绵阳 621010)
作为曾获得过一次普利策奖,三次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美国作家,伊迪丝.华顿的影响力是毋庸置疑的。她的很多作品在刚出版时就获得巨大成功,为她带来了财富和名誉。华顿的文学生涯始于1891年短篇小说《蔓丝缇夫人的景色》(Mrs.Mamstey’sView)在文学创作类权威期刊《斯克里布纳杂志》(Scribner’sMagzine)上的发表。其对于短篇小说的创作热情贯穿其一生,先后创作出版了83篇短篇小说。虽然学术界对于华顿短篇小说的研究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大幅展开,但她在世时评论界对其短篇小说的评论已经非常高。 1936年 4月25日出版的《芝加哥论坛报》上可以看到当时相当有影响力的文学评论家范妮.巴切这样评价华顿新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可能有人已经忘了《伊桑.弗洛姆》以及老纽约四部曲这些短篇小说有多精彩,他们总是以为华顿只是小说家。新出版的短篇小说集《那边的世界》(TheWorldOver)再次提醒大家华顿的短篇小说写作水平亦是无与伦比。该书的七个故事中至少有三个足以让任何作家嫉妒且几乎无人能及。”[1]
华顿去世后,她的作品曾一度被认为题材局限写法保守而无人问津。在20世纪60、70年代女权运动的影响下,其小说在英语文学中的经典地位再次得以确立。1983年“华顿研究会”在纽约成立,自1984年起研究会每年出版两期学术刊物《华顿评论》,这为学者们交流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平台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对华顿作品的研究,但华顿短篇小说获得的关注仍远低于其长篇小说。当人们谈到华顿时,想到的也都是她的长篇小说《纯真年代》 《欢乐之家》《伊桑.弗洛姆》等等。各种名为美国短篇小说选集的美国文学选集都将其作品排除在外。直到1989年著名学者保罗.劳特(Paul lauter)大胆的将华顿的四篇短篇小说收录在其主编的《希斯美国文学选集》中,学术界这才再度将视线投向她的短篇小说。1991年芭芭拉·怀特(Babara White)编写的第一本研究华顿短篇小说的专著《伊迪丝·华顿短篇小说研究》出版。这标志着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才出现了规模较大的华顿短篇小说研究。
西方学者们对华顿短篇小说的关注和研究有不同的侧重点,本文以大量文献阅读为基础,对华顿短篇小说研究主要成果和趋势进行归纳总结。
一、 彰显女性主义立场:鬼故事与婚姻故事
尽管华顿作品经典地位的确立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上世纪60、70年代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的兴起,但90年代后学者们开始认识到华顿的女权主义并不是可以被简单定义的。更有学者认为《母亲的赎罪》(1925)、《哈德逊画派》(1929)、《神来了》(1932)等晚期小说表达了她明显的保守主义倾向,对于女性母亲身份的强调“强化了传统的性别范畴,体现了一种被规驯和物化的内在逻辑”[2]。与其长篇小说相比,相当多的研究表明华顿的立场在其短篇小说中要明确得多,无论是其早期还是晚期作品都清晰的表现出了她坚定的女性主义立场。
在对华顿的短篇小说进行女性主义的研究过程中,评论界最关注的是她的鬼故事(Ghost stories)和婚姻故事。学者们主要从精神分析,女性主义,酷儿理论几方面对其作品进行分析。著名女性主义学者吉尔波特(Sandra M.Gilbert)认为[3]鬼故事使华顿能够允许她自己超越平常,解放当时文化环境中不允许存在的欲望。她以《科夫》(kerfol) 、《琼斯先生》(Mr.Jones)、《石榴籽》(PomegranateSeed)等故事为例指出华顿的多数鬼故事在表达 “女性欲望”这个主题的同时也以隐晦的笔触反映了女性被桎梏和物化的问题。在保守社会环境下不可言说的女性欲望或化身成动物(如kerfol中的狗成了女主人复仇潜意识的化身)复仇,或变身为鬼魂后获得生前所不能享有的权力(如《琼斯先生》中的被丈夫囚禁的结巴妻子在死后最终通过信件得以与外部世界交流,而这在她在世时是被严厉禁止的)。
简妮·戴曼 (Jenni. Dyman)在《潜在的女性主义:华顿的鬼故事》(Lurkingfeminism:TheGhostStoriesofEdithWharton1996)一书中重点探索了华顿鬼故事在一个传统框架下以不同方式展现的隐蔽的女性主义主题。她认为“华顿特意用鬼故事这种形式来探索女性以及男性的社会处境,包括性别角色,婚姻关系,交流形式。”[4]xii她也指出在华顿鬼故事中的男性角色大多都是自我中心的单身男性,他们具有明显的同性恋特征,想要逃脱自己被定义的性别角色。此书通过分析写于4个不同时期的11个鬼故事来说明华顿鬼故事展现了华顿的女性主义从简单反对男性主宰、父权符号转变到探索两性关系中的女性欲望、权力争夺以及安全但势微的传统行为想法和女性成长需求之间的矛盾而爆发的内心冲突[4]xvii。
在《华顿故事中的性别与哥特》(GenderandtheGothicintheFictionofEdithWharton)一书中,费多克(Kathy A. Fedorko)则将华顿的个人经历及对女性身份的认识与其不同时期的鬼故事以及少数含有哥特元素的长篇小说结合起来分析,认为她鬼故事中的女性主义经历了四个认识阶段: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与男性对其的压制,女性对自身艺术创造力的恐惧;对于理性思维局限性的认识;对于女性自身性欲更为正面的认识,以及男性对之的恐惧;对于性别角色的奋起反抗。总的来说费多克认为华顿四个时期的鬼故事展示了她对于自身女性及艺术家身份的逐渐深入的认识。
最有名的华顿学者列维斯(R.W.B Lewis)在1987年出版的《华顿短篇小说选集》(TheCollectedshortstoriesofEdithWharton)的前言中谈到他认为华顿最为擅长、连亨利.詹姆斯也未能匹敌的一类小说是婚姻问题短篇小说。他认为华顿的婚姻短篇小说主要分为六类:1.婚姻基础及婚前斡旋2.婚姻中的紧张焦虑无望以及被迫的自我调节。3.关于离婚生活的敏感问题。4.通奸带来的心理问题。5.非婚生子问题。6.孩子在婚姻中的价值[5]。在多达几十篇的华顿探讨婚姻问题的短篇小说中,有相当大数量的作品也和鬼故事一样表达了她的女性主义思想。芭芭拉·怀特 (Babara.White)在第一部研究华顿短篇小说的专著 《华顿短篇小说研究》(EdithWharton:AStudyOftheShortFiction)中特别研究了华顿短篇小说从早期的女性叙述者视角转向后来的男性叙述者视角与她要表达的女性主义观点之间的联系。她指出在《迟来的灵魂》(SoulsBelated)、《另两个》(TheOtherTwo)、《业余爱好者》(TheDilettante)等多篇婚姻问题短篇小说中,华顿都采用了男性叙述者来讲述故事,从而通过他们对女性人物毫无同情心的不可靠叙述间接表达了对男性虚伪自恋的反感以及对于他们要求女性谨遵自己的性别角色,死后也要成为“坟场里的天使”[6]的嘲讽。
二、短篇小说比较研究:摆脱詹姆斯的阴影
对于华顿这样一位重要作家,学者们自然会将其写作技巧、主题、内容等各方面与其他作家相对比从而达到深刻认识的目地。在她的写作生涯之初评论者就热衷于说她是亨利.詹姆斯的门徒或继承人,学者们在作比较评论时也通常将目光局限在她的作品与詹姆斯作品的比较上。詹姆斯的确是华顿生活中亲密的朋友,但她多次在给编辑和朋友的私人信件中很清楚地表达了对于“门徒”“继承人”此类说法的不满,“人们不停地说我是詹姆斯的翻版(虽然他是我最爱的朋友但他过去十年的书我根本看不下去)……这真的让我绝望。”[7]虽然随着近30年来华顿研究的大规模深入展开,尤其是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经意识到詹姆斯与华顿之间更多的是一种平等的同行而非师徒关系,但即便在21世纪,在说到华顿的《欢乐之家》《纯真年代》等长篇小说代表作时,很多学者仍然认为在结构、故事情节安排、人物心理描写甚至用词特点上华顿都是在模仿詹姆斯,在做华顿小说的比较研究时詹姆斯也是用于参照的主要人选。这一现象在人们研究华顿短篇小说时则明显较少出现。尤其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以来,学者们在华顿短篇小说的比较研究上引入了不少不同的作家,力求通过广泛的对比研究更深入地了解华顿的作品。
在研究华顿小说时,很多做对比研究的学者都忽略了除了詹姆斯以外的男性作家。与此不同的是,在研究华顿短篇小说时,评论家们则把目光投向了更多的男性作家。这其中被作为对比研究对象的第一类作家是作品被她大量阅读并深刻影响她写作的美国作家。其中的代表人物是爱伦坡。约翰.格茨(john Getz)认为《玛丽.帕斯科小姐》与《厄舍府的没落》故事框架相似,但华顿以反讽的方式使厄舍府中死去的女人不但复活且能开口为自己辩护;而《琼斯先生》中“被盗信件”这一重要情节也是来自于坡的《失窃的信》,除此之外一向对人物名字的选择相当讲究的华顿用了坡的岳母克莱门的名字来为故事中的管家命名,这些对于坡的作品以及生活的 “盗窃”[8],是华顿反映她对坡复杂评价的重要手段,同时也表达了她对于男性文学传统中女性角色被边缘化这一做法的不满。卡罗尔(Carole M Shaffer-koros) 也指出坡是《科夫》这个故事的灵感所在,而在《鹧鸪》一文中,鹧鸪这一形象则来自于《乌鸦》。
除了爱伦坡以外,研究者们指出霍桑对华顿的作品也有相当影响,例如瑞蕾.科内塔(Reiner Kornetta) 认为人们忽视了华顿广被讨论的一个故事《坟墓天使》其实在总体构思和内容上都与《七个尖角阁的老宅》相似。两个故事中的新英格兰地区的老宅子都代表着历史、父辈之罪和孤独,不同的是“霍桑表达了对巫术的错误信仰的终结,而华顿则埋葬了超验主义,转向了更加科学的理性主义。”[9]
第二类对比研究的对象则是一些对华顿产生影响的欧洲作家,其中广受关注的是尼采。沙瑞(Shari Benstock)称“在1907-1908年之间,华顿阅读了尼采的所有著作”[10]。 威廉(William Macnaughon) 指出尼采影响了华顿在1909-1914年之间的创作,其中最明显的是短篇小说《金色野兽》。此文不仅在题目上就使用了“金发野兽”[11]这一最先出现在尼采《道德谱系》中的术语,而且描绘了一个尼采式超人的故事。卡罗尔(carole M Shaffer-koros) 则以《罗马热》所体现出的哲学思想为例论证了尼采以及德国文化在华顿写作中产生的影响[12]。
除了尼采以外,有学者认为保罗.布尔热对于华顿的短篇小说创作也产生了较大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是相互的。作为一位与华顿同时代的法国作家,布尔热与华顿私交甚好。华顿曾在1936年所写的对布尔热的纪念文章中说到 “ 保罗的写作技巧与我完全不一样,因此我们决定闭口不谈各自的作品,但我们经常一起讨论下一个故事的内容。”[13]阿德莲(Adeline Tintner) 认为这种讨论的结果就是两者在短篇小说创作上产生了明显的互相影响,这种影响在两人1900-1908年这段时期的作品中尤其明显[14]。例如华顿在1901年出版的短篇小说《移动的手指》(TheMovingFinger)就与布尔热在1903年出版的故事《画像》(LePortrait)在情节安排上非常相似。
第三类研究对象是与华顿同时代的英美男性作家。冬娜(Donna Campell) 认为华顿的多篇短篇小说与舍伍德·安德森的短篇小说集《小镇畸人》在内容与主题上相似,“其后期作品例如《镜子》《丧葬之日》中的主人公对某种绝对价值的痴迷使得他们完全符合安德森对于“畸人”的定义。 ”[15]
埃尔博特(Monika Elbert)指出华顿虽然曾经公开贬低过推崇现代主义的作家,但故事《毕雷矿泉水》与艾略特的《荒原》在某些方面却出奇的一致。她认为这两个作品都属于“现代主义哥特”(modernist-Gothic)的范畴, “都描写了现代思维的碎片化以及都相信为了解决现代带来的问题人们需要回到遥远过去的某个时刻。”[16]
总的来说,与对其长篇小说比较固定的比较研究对象相比,华顿短篇小说比较研究的发展趋势是学者们越来越多的将她的作品与各个时代不同作者的作品进行多方面的深入比较。这能让读者们更好的了解华顿写作的多样性,打破对其写作特点的固有看法。
三、 现代主义问题辩驳:观点趋于一致
关于华顿的长篇小说是否体现了现代主义,或者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现代主义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热点。一方面有学者认为华顿的小说体现了广义上的现代主义,例如普雷斯顿(Clair Preson) 在其专著《伊迪丝.华顿的社会语域》(EdithWharton’ssocialregister)中指出华顿“总是有节制的评论、解释,避免派别之争……同时,她相信读者具有自己做出判断得出结论的能力”[17]而这些都是现代主义的明显特点。另一方面有学者认为华顿的后期小说连现实主义都谈不上,而更多的是被“感伤主义”影响。皮尔(Peel.Robin)认为华顿拒绝 “将艺术从历史、经济、政治的领域中抽离”,坚信艺术应该“在好的社会中扮演重要角色”[18]因此她最终是“背离了现代主义”。
作为一种20世纪才兴盛起来的较新的写作形式,与华顿的长篇小说中似有还无的现代主义相比,她的短篇小说中所表现出来的现代主义元素则要明显得多,因此争议也少得多。加之学术界开始关注华顿短篇小说的时间较晚,反而在研究之初就打破了一些对其作品缺乏现代性的固有看法。尤其是21世纪以来,研究者们对于华顿短篇小说展现的现代主义色彩少有异议。学者们认为华顿的短篇小说写作是“实验性”[19]“现代性”[20]以及 “颠覆性”[21]54的。
怀特赫德(Sarah Whitehead)在《华顿短篇小说中的现代主义实践》(MakeItShort:EdithWharton’sModernistPracticesinHerShortStories)中系统研究了华顿短篇小说中的叙述者、叙事视角、叙事空白以及顿悟的运用。她认为“华顿的短篇小说并不是19世纪传统小说的缩减版本,相反,由于她对于不可靠叙述等手法的运用以及她对读者在阅读中积极作用的期待,使得其作品与20世纪现代主义作品更加接近。”[21]1很多对于华顿写作现代性持怀疑态度的学者认为他们最有力的依据就是华顿于1925年出版的《小说写作》(TheWritingofFiction),他们相信华顿在此书中对自己写作的总结表现了她对于传统秩序和形式的推崇,而这些都与现代主义格格不入。对于这一观点诸多学者从不同层面进行了反驳,怀特赫德认为“尽管她的短篇小说不具有《尤利西斯》那样的混乱、随意、流动的特征,这些特点同样也并不存在于《都柏林人》这样的现代主义作品中”[21]11,相反,现代主义文学代表人物乔伊斯也和华顿一样相信应该通过传统形式在混乱的现代世界中创造秩序。埃尔博特(Monika Elbert)也认为《毕雷矿泉水》与艾略特的《荒原》在通过传统寻找秩序的主题表现上相当一致[22]。维尔( Michele S.Ware) 在《短篇小说的建筑:华顿的现代主义实践》(TheArchitectureoftheShortStory:EdithWharton’sModernistPractice)中指出“在将华顿的文学批评理论运用到她自己的作品中的时候我们应该谨记D.H劳伦斯的警告 ‘不要相信艺术家本人,要相信他的故事’。”[23]17她主要研究了华顿短篇小说在形式结构上与现代主义一致的地方,如频繁的分段以及叙事的碎片化,这些特点展示了“华顿对传统形式的抗拒而与现代主义的主张一致”[23]22。她认为短篇小说是华顿的写作实验,它们具有令人印象深刻的现代性,她在其中所运用的美学思想不是来自于其后期的文学批评理论,而是源于早期对于艺术、建筑和设计的理解。
在2008年出版的《伊迪丝.华顿与现代主义对话》(EdithWhartonandtheConversationsofLiteraryModernism)中,海托克(Jennifer Haytock)则另辟蹊径探讨了在形成现代主义的各股社会、文化、文学的浪潮中华顿所处的位置[24]。《“无中介的男性纽带 ”:短篇小说中男性的累积》(“UnmediatedBondingBetweenMen” :TheAccumulationofMenintheShortStories)这一章节运用伊芙.塞吉维克 (Eve Kosofsky Sedgwick) 关于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 ( homosocial desire)的酷儿理论结合华顿传记研究,特别是她与 “inner circle” 中男性成员的关系,对《上锁的门》(TheBoltedDoor)、《长跑》(TheLongRun) 、《毕雷矿泉水》(ABottleofPerrierr) 、《圆环》(AFullCircle)等短篇小说进行情节、主题以及叙事角度的文本分析,探讨了华顿隐秘的表达在短篇小说中的关于权力有可能完全不通过女性这一媒介而在男性之间直接传递、自己被男性成员排除在“圈外”的恐惧。海托克认为华顿在其短篇小说中常用的双重男性叙述者这一叙事角度也是在表达她对社会权力只在男性群体内部得以加强的认识。
21世纪以来对华顿短篇小说中现代性的肯定对于华顿的作家形象具有颠覆性的作用。如今的她不仅不是最初的“风俗作家”,也非“感伤小说”的作者,甚至不完全是一位“现实主义”作家,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和读者看到她短篇小说的现代性和实验性,因此我们在阅读研究她的作品时应该牢记不能简单的用那些陈旧的标签来定义华顿。
结论
综上,目前西方学者们对于华顿短篇小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女性主义、比较研究、现代主义这三个方面,对其长篇小说的研究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认为她短篇小说中的女性主义主要体现在鬼故事和婚姻故事里;在比较研究时极大加深了研究的广度;充分肯定了华顿短篇小说里的现代主义。在未来,对于华顿短篇小说的研究会更加深入和多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