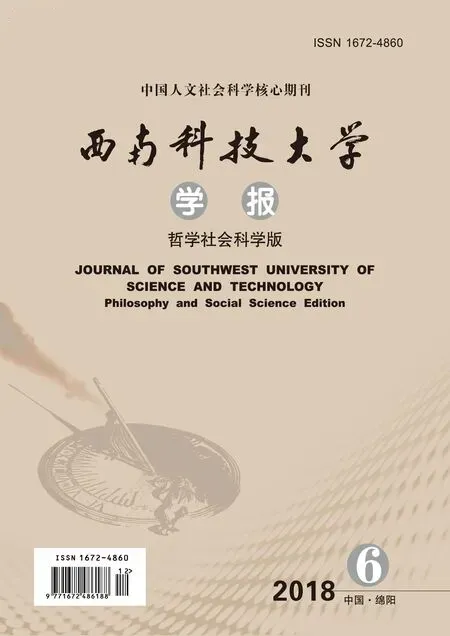英国浪漫派诗歌动物书写的互文性和现代性
——以休斯的“鹰”和劳伦斯的“鹰”为例
陈贵才 原一川
(1.滇西科技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云南临沧 677000;2.云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云南昆明 650500)
作为20世纪英国诗坛上的桂冠诗人,泰德·休斯(1930-1998)充分继承了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关注、歌颂和回归自然的文学传统。凭借敏锐的洞察力、超群的想象力、杰出的诗歌才能和渊博的人类学和考古学知识,休斯在畅游美丽而神奇的大自然的同时,一面与大自然中的动植物进行着密切的对话与交流,一面认真审视着充满危机和暴力的人类世界。这些最终在他的自然诗集《雨中的鹰》《牧神之地》和《乌鸦》等中得以有效刻录和充分展现。在这些诗集中,诗人通过鹰、狐狸、美洲虎、乌鸦、狗鱼等猛禽凶兽的动物形象向读者呈现了动物世界的弱肉强食、人类世界的血腥暴力和人的狂妄自大与唯我独尊。因此,与其把休斯的这些诗集称作动物诗集,不如把其称为“一部动物寓言集”。[1]307这种寓言性在其诗作《雨中的鹰》和《栖息的鹰》中所书写的充满活力和暴力的“鹰”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在动物书写方面,泰德·休斯受其前辈诗人戴·赫·劳伦斯的影响较深。事实上,“劳伦斯可能是除了莎士比亚之外对休斯影响最大的前辈作家。”[2]66这种影响可从休斯的《雨中的鹰》和《栖息的鹰》与劳伦斯的《新墨西哥之鹰》和《美国之鹰》之间的文本对话和文化对话中反映出来。它们之间的对话性或互文性又根植于英国浪漫派诗歌的自然书写传统。在广泛继承和充分发扬英国浪漫派诗歌自然书写传统的基础上,劳伦斯创设了他“艺术世界里的自然保护区”[3]38、植物王国和动物王国。在其精心创设的动物王国里,蜂鸟、蚊子、蝴蝶、蝙蝠、蚂蚱、萤火虫、火鸡、乌鸦、天鹅、孔雀、鹰、乌龟、蛇、鱼、蜥蜴、老鼠、毛驴、鹿、马、山羊、大象、袋鼠、鲸、狼、和狮子等被劳伦斯的前辈诗人赞美、鄙视或遗忘的动物全都进入了他书写的中心而获得全新的关注和普遍的认同。正如哈里·穆尔所言:“劳伦斯无限热爱自然,几乎为所有的动物写过诗或故事,从鲸和大象到豪猪和蝙蝠,都成为他描写的对象”。[4]23这种广泛的动物书写又深刻地影响和启迪着他的后辈诗人泰德·休斯的动物诗创作。
一、泰德·休斯的“鹰”文本和“鹰”形象
泰德·休斯的“鹰”文本主要存在于他1957年出版的第一部诗集《雨中的鹰》和1960年出版的第二部诗集《牧神集》中。这些“鹰”文本就是他第一部诗集的同名作《雨中的鹰》和第二部中的《栖息的鹰》。在这两个“鹰”文本中,诗人成功书写了一只多重形象之鹰。
首先,诗人书写了一只深受人类中心主义暴风雨之害的鹰。在《雨中的鹰》中,虽然身处暴风雨中的鹰仍能在高空自由翱翔,仍能心平气和、轻松自在、坚忍不拔、泰然自若地与自然搏斗,在搏斗中仍表现出超凡的掌控能力和驾驭能力,但在人类中心主义暴风雨的残暴肆虐下,这只万能之主的鹰从空中被重重摔下,摔成了肉酱,与地上的泥泞混杂在一起:“那鹰可能某时遇上不测风云,/ 遭遇强气流,被从空中重重摔下,/ 沉沉乌云从眼前滑落,撞击着他,地面束缚着他;/ 他天使般滚圆的眼睛被摔得稀烂,/他心脏流出的鲜血与地上的泥泞搅和在一起。”[5]19与这只万能之主的鹰相比,以“我”为代表的人类在自然灾害面前则相形见绌,在暴风雨和泥潭中无能为力、无所适从、不堪一击、惶恐不安、心急如焚,使尽浑身解数也不能从命运的沼泽和泥潭中脱身,只能丢弃尊严,拼死迈向高空自由翱翔的万能之主的鹰,但最终还是成了“大地之嘴最后时刻死死咬住的一块食物”。这就是以“我”为代表的病态而毫无生机的人类中心主义者的最终下场。尽管如此,骄傲无知、丑陋无度的人类仍不思己过,我行我素,处处以自我为中心,时时迷恋于征服自然,总把自己看作自然的主宰,总以为自己在自然面前无所不能、无往不胜,甚至万能之主的“鹰”最终也逃脱不了人类中心主义的魔爪。从这个意义上讲,《雨中的鹰》这首诗是休斯对病态和异化的人类世界的一种警醒,同时也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有力鞭策和辛辣讽刺,希望人类不要总是以自我为中心,不要迷恋于对自然的征服,否则,人类中心主义要么被“当空吹下,撕成碎片”,要么被“抽去脊梁,顷刻间倒下”。[6]104
其次,诗人书写了一只蓄势待发的自然之鹰。这只鹰见于他1957年写成的诗歌文本《栖息的鹰》之中。在这首诗中,诗人巧妙地运用动词的各种形式向读者呈现一只静态与动态相结合的自然之鹰。从诗歌题目Hawk Roosting中的“Roosting”一词来看,诗人似乎要向读者展现一只栖息着的静态之鹰,但从各诗节中展现鹰的众多动作行为的动词或动词化的其他词类如“排练”(rehearse)、“捕杀”(kills)、“吞食”(eat)、“监视”(inspection)和“紧紧锁住”(are locked upon)等来看,诗人呈现给我们的却是一只动态的鹰。这种静态与动态相结合的形象塑造不仅展现了诗歌的意象张力,而且凸显了鹰的生命活力和行动暴力。经过诗人暴力美学的诗学展现,一只具有强烈支配欲和占有欲的蓄势待发的鹰就呈现了出来。
再次,诗人书写了一只由自然层面向隐喻和象征层面转变的鹰。这只鹰在各诗节中呈现出不同的形象,并逐渐走向了隐喻和象征。诗歌第一节书写的是一只居高临下、目空一切、爪牙锋利和嗜血成性的捕杀者之鹰。第二节书写的是一只占尽天时地利、监视着地上万物的监察者之鹰。第三节书写的是一只地位极为稳当的叛逆者和支配者之鹰。第四、五节书写的是一只操控着地球、霸占着万物、掌握着生死大权、对猎物想捕食就捕食、捕食方式和捕杀行为极为凶残的、无法无天的霸权者、主宰者和残杀者之鹰。最后一节书写的是一只狂妄的秩序维护者之鹰:“太阳被我甩在身后。/ 自我有生以来什么都没变过。/ 我的眼睛不容许有任何变化。/ 我要让世间一切维持现状。”[7]365
综合以上具体形象来看,休斯的这只鹰首先是一只自然层面上的鹰。作为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鹰,它无愧于百鸟之王,不仅可以任意残杀自然界中的生灵,还可掌控它们的命运和决定它们的生死,甚至还维护着自然的秩序。从隐喻和象征层面上讲,这只鹰既是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在鹰身上的再现,又是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不断膨胀的恶果,因为诗中的“我”既是人类的一员,又是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实践者。从当时的社会历史语境和诗人的个人语境来看,休斯的鹰还可看作是法西斯独裁者形象的影射。1930年出生的休斯不仅亲身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亲眼目睹了二战的残酷,还从他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父辈们那儿了解到了许多残酷无情的战事。这些创伤记忆无形中催生了他战争叙事的冲动,使他有一种迫切的希望去寻找一种恰当的客观对应物来表现法西斯分子及其罪行,而这个客观对应物最终落到了这只象征独裁者和秩序维护者的“鹰”身上。诗人笔下的“鹰”性的法西斯独裁者的形象,便建立在“诗人战争叙事的主观冲动”,与“‘鹰’和法西斯分子的相似性与联系性”二者的巧妙结合之上。
尽管休斯的“鹰”形象呈现多重性,既有自然之鹰,又有深受人类中心主义之害的鹰,还有人类中心主义之鹰,甚至还有法西斯独裁者之鹰,它们还是与休斯的前辈诗人劳伦斯所书写的“鹰”形成了一定的沿袭性和统一性。
二、戴·赫·劳伦斯的“鹰”文本和“鹰”形象
作为文艺世界中动物王国的建构者,劳伦斯诗歌中所书写的动物既有西方文化语境中较为高贵的动物如鹰、夜莺和云雀等,又有如蝙蝠、蛇、蜥蜴、老鼠、蚊子等长期以来被人视为低贱的动物。无论高贵还是低贱,这些动物最终都进入了劳伦斯书写的中心而获得了全新的关注和普遍的认同。在以《新墨西哥之鹰》和《美国之鹰》这两个诗歌文本为主要载体去书写“鹰”这一高语境动物时,劳伦斯以鲜活的表现力为读者呈现了一只别具一格的鹰。
在《新墨西哥之鹰》一诗中,劳伦斯书写了一只人类中心主义操控下的自然之鹰。在该诗的前七节,诗人首先书写的是一只自然界中的王者之鹰。这只王者之鹰英勇无畏、敢于向炙热的太阳发起冲锋:“一只胸脯赤红色的鹰/挺身冲向太阳, 冲向西南。/一只胸脯赤红色的鹰,/ 像答案一样,像反击者一样挺身冲向太阳。”[8]304其次,诗人书写了一只高傲自大、唯我独尊和藐视太阳的鹰:“你从不用双眼正视太阳。/你只用你宽广的赤红色胸脯的内眼直视太阳。”[8]304再次,诗人为读者呈现了一只爪牙如坚硬而锋利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在高空翱翔时羽翼如横扫的镰刀、在捕杀中嗜血成性之鹰。这只鹰总是昂首挺立,身居高位,极目远眺。这些特质是诗人从远处静观得知的,是一只百鸟之王应有的特质,同时也是自然界中王者之鹰的特质。然而,随着诗人与鹰的距离逐渐拉近,诗人就“把现实里的鹰和想象中的鹰糅为一体”[9]76,在指称这只“鹰”时不再用先前的各种隐喻,取而代之的是人称代词“你”。这样,诗中的对话主角就成了“我”和“你”。从诗歌的对话来看,以“你”为代表的鹰总处于失语状态,而以“我”为代表的诗人却掌握着充分的话语权,因为诗人连续发出了10个想象性疑问。在这些疑问之后,诗人不仅表明了不会屈服于鹰的态度,而且还以祈使句的语气催促着它离开,甚至还表达了以“我”为代表的人类能够掌控自然和征服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
我不会屈服于你,大大的颚脸之鹰。
我既不会屈服于你,也不会屈服于你那嗜血成性的
吸血的太阳,
虽然你们让人惶恐不安。
飞走吧,黑背大鸟。
慢慢飞走吧,上天之鹰,
虽然你的尾巴闪烁着一丝火花,你依然如此之黑。
在人类的心中,即使是天空中的太阳
最终也要受到控制和惩罚。
更何况你这只大鸟,太阳的凝视者,又黑又大的鹰
也可能当作祭品送来者而被逐出天国。
这些想象性疑问和坚决的态度是诗人对百鸟之王的一种蔑视,是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在“我”身上不断膨胀的表现,是狂妄自大的人类中心主义者力求征服自然和主宰自然的行动宣言。
在诗歌《美国之鹰》中,劳伦斯书写的不再只是一只自然之鹰,而是一只极具象征性的鹰。这只鹰由自由女神之鸽孵化而成,然后在自然的淘汰选择中成了世界上唯一的鹰,但它开始变得烦躁不安起来:时而双脚来回移动,看上去就像一只摇摇摆摆、步履蹒跚的鹈鹕,时而从自己丰满的羽毛中拔出一些松散的羽毛去装饰世界上那些新诞生的、贫穷而弱小的共和国的巢穴。这只自由女神孵育的幼鹰正在成长为一只惊人的大鸟,栖落于世界之巅;她的母亲自由女神一直力图教它学鸽子咕咕叫,但它总以狂叫回应。正如猎豹不能改变其花纹,英国雄狮不会改变其胃口,这只冉冉升起的年轻雄鹰嘴里也永远不会叼着象征和平的橄榄枝。相反,它骄傲蛮横的态度、让万物臣服的决心和蚕食生灵的本性暴露无遗:
新建立的高傲的共和国
根基于自豪之神秘。
自负的人,满怀生命的力量,掌控着无数的臣民。
落基山之鹰, 主人之鸟,
叼起无数只鲜血淋漓的兔子, 在空中耀武扬威,扔下几根骨头。
张开巨大的双翼, 去迎面那即将失去羔羊的羞怯母羊,
喝着一点点的鲜血,向世界展示着无限的王威。
劳伦斯的这只“鹰”已成了象征美帝国等新兴殖民主义国家的强权之鹰。正如潘灵剑所言:“鹰的形象已远离了作为自然物的鹰的形象:它本质上不是指向肉欲的生存,而是通过形象的虚构获得思想的概括力, 走向象征。”[10]97它“象征着一个正在崛起, 将会对人类产生威胁的美国。”[11]2021776成立的美国孕育于自由的理念,奉行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然而,当这个孕育于自由理念之中的国家发展壮大并成为世界超级大国之后,他的“鹰”性本能就暴露无遗,不仅不遵守自由女神之母的意旨,而且还蔑视和践踏着自由的理念,竭力攀登到世界权力之巅,甚至总打着自由、民主和人道主义的幌子对弱小国家横加干涉,总想把世界上的弱小国家变为他的附属国或殖民地,总想让这些弱小国家成为其嘴边的兔子或羔羊。这就是劳伦斯所刻画的美国之鹰,一只象征美帝国等新兴殖民主义国家的强权之鹰。
劳伦斯书写的“鹰”不只是自然界中的百鸟之王,其身份还随着诗人视角的变化而处于一种动态的变化之中。在劳伦斯那里,鹰最初以自然界中的王者形象出现,随后成了人类中心主义支配下的他者,最后又以新兴殖民主义者的形象呈现出来。这些形象的变化既凸显了劳伦斯对自然世界和人类世界的关注和深思,又反映出他别具一格的动物书写策略和独具匠心的诗学隐喻。通过这些诗学策略和诗学隐喻,劳伦斯为他文艺世界里的动物王国添加了一只异类之鹰。这只鹰在劳伦斯的动物王国里虽然成了异类,但在某些方面却与其后辈诗人泰德·休斯所书写的“鹰”成了同类。
三、休斯之“鹰”与劳伦斯之“鹰”的互文性和现代性
虽然休斯的“鹰”与劳伦斯的“鹰”存在着一定的异质性,但他们的“鹰”文本却为读者搭建了一个文本对话和文化对话的平台。从这个平台可发现,休斯的“鹰”文本与劳伦斯的“鹰”文本既有沿袭性,又有创新性,还有统一性。这就是互文性理论家所说的狭义互文性和广义互文性。前者指的是“一个具体文本与其他具体文本间的关系,尤其是一些有本可依的引用、套用、影射、抄袭、重写等关系”[12]26,后者则指“文学文本对社会文本的阅读和重写”。[12]26互文性研究就是在阅读和阐释中探寻文本间既有的多维立体的内在联系和挖掘隐藏在文本之间共有文学性的同时,去追忆伟大的文学与文化传统和发现子文本对母文本乃至伟大的文学和文化传统的转换生成,从而让读者在领略个人才能的同时去追溯伟大的文学和文化传统,在文本对话、文化对话和价值观对话中获取新的阅读快感和审美体验,在文本的转化生成中见证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的演变和审视社会人文现实的变迁,最终恢复人们对文学传统和文化传统的集体记忆。
休斯之“鹰”与劳伦斯之“鹰”的互文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休斯的“鹰”与劳伦斯的“鹰”在浪漫主义层面上的互文性。作为英国诗坛上两位以书写动物而著称的诗人,休斯和劳伦斯笔下的鹰首先是一只自然之鹰。在书写自然界中的百鸟之王时,休斯不仅续写了劳伦斯笔下的自然之鹰,而且赋予了这只百鸟之王更多的新特质。劳伦斯笔下的鹰爪牙坚硬而锋利,羽翼丰满而有力,它总是身居高处、英勇无畏、高傲自大、唯我独尊、叛逆不羁、嗜血成性。在此基础上,休斯续写了其前辈诗人劳伦斯的鹰。这只百鸟之王的鹰临危不惧,在灾害降临时仍能在高空自由翱翔,在灾害面前仍能轻松自在、心平气和、泰然自若,在与自然的搏斗中仍能坚韧不屈、驾驭自如。另外,休斯的鹰还以捕杀者、监察者、叛逆者、支配者、霸权者、主宰者、残杀者和秩序维护者等形象展现出来。通过这些特质和形象的呈现,休斯不仅续写了劳伦斯的鹰,而且很大程度上重构了劳伦斯的鹰形象。在续写和重构劳伦斯之鹰的同时,休斯既突破了他前辈诗人劳伦斯所创设的以鹰为题材的文本语境和拓展并加深了鹰的书写维度,又丰富和发展了英国浪漫派诗歌自然书写传统的形式,从而为英国浪漫派诗人所创设的文艺世界中的动物王国增添了光彩和注入了活力。
休斯的“鹰”与劳伦斯的“鹰”在人类中心主义层面上的互文性。人类中心主义在西方由来已久。但近代以来,特别是20世纪以来,人类中心主义在西方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这主要是由于成功的西方工业革命和迅猛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背后暗藏的各种深刻危机: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文化危机、生态危机、心态危机和信仰危机等。在这些层出不穷、此起彼伏的危机作用下,人类已在信仰之海中迷失了方向,只知道一味地去征服自然和占有自然界中的各种自然资源。这种强烈的征服欲和占有欲扭曲了人性,破坏了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生态系统。当人类在信仰之海中普遍迷失方向的时候,在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不断滋生蔓延、行为愈演愈烈的情况下,劳伦斯和休斯为盲从和迷失的人类中心主义者点亮了明灯。“在人类中心主义的话语指涉里,动物被视为野性和蛮昧的化身,是对立于人类文明的‘他者’。”[13]96在人类中心主义的话语体系下,劳伦斯的鹰不但失去了与人类平等交流的话语权,而且被看作与人类对立的他者而被蔑视和虐待。休斯的鹰既成了人类中心主义的代名词而恣意妄为,又成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受害者而被撕成碎片当空扔下。虽然劳伦斯的“鹰”文本不及休斯的“鹰”文本那样令读者赏心悦目,但从人类中心主义这一视角来看,休斯确实在续写着劳伦斯的“鹰”,因为从劳伦斯的“鹰”到休斯的“鹰”这一文学发展历程既是人类中心主义从思想发展到行动的历程,又是英国浪漫派诗歌自然书写传统的现代性转向的过程。
休斯的“鹰”与劳伦斯的“鹰”在殖民主义层面上的互文性。在休斯和劳伦斯的“鹰”文本中,这只自然界中的百鸟之王已经突破了自然的界限而成了象征和隐喻。“没有隐喻,就没有诗歌”。[14]8这是美国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在论及诗歌之于隐喻时的重要论断。在劳伦斯的“鹰”文本中,鹰已成了美帝国等新兴殖民主义国家的隐喻和象征。这虽然是劳伦斯对正在不断崛起的美帝国的预言,但这种预言最后却变成了现实。在成为世界超级大国之后,美国总是以自由、民主和人道主义为幌子,以大棒和金元为武器,对世界上贫穷落后的弱小国家进行殖民扩张和统治。作为劳伦斯的后辈诗人,休斯不仅续写了劳伦斯的这只殖民主义之鹰,还以更隐含的方式把这只殖民主义之鹰的凶险、霸道、蛮横等特性展现了出来。从劳伦斯的“鹰”到休斯的“鹰”的过程既是殖民主义从预言到现实的过程,又是英国浪漫派诗歌自然书写传统从浪漫主义向现代主义的转向过程。
休斯的“鹰”文本与劳伦斯的“鹰”文本虽然在三个层面上存在一定的互文性,但这些互文性最终又统一于英国浪漫派诗歌动物书写传统的现代性。
劳伦斯是一位融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于一身的诗人。在以诗歌形式书写动物的时候,他不仅继承了英国浪漫派诗歌歌颂自然的传统,而且以现实主义的眼光来审视自然界中的动物和人类的本能。不仅如此,劳伦斯还将现代性所带来的危机和所呈现出的阴暗面融进了他的动物诗歌文本中。“现代性是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产物,是科技发展、工业革命和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15]107现代性这一概念既是“一个具有丰富历史内涵的悖论式的概念”[15]107,又是“一种双重现象”。[16]6现代性在给人类带来机遇和辉煌的同时,也使人类陷入到危机和阴暗之中。作为20世纪英国现代性的见证人,劳伦斯把现代性所带来的危机和所呈现出的阴暗面巧妙地融入到他的两个“鹰”文本中。在其中,劳伦斯把人类中心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失语症、疏离感、身份焦虑、人性异化、极权化、中心化、单一化、生态危机和环境危机等现代性的阴暗面充分披露出来。在续写现代性所带来的危机和所呈现出的阴暗面的基础上,劳伦斯的后辈诗人泰德·休斯也在其“鹰”文本中把人类身份的迷失、人类的极端脆弱性和人类的狂妄自大等现代人的问题展现出来。这样的续写不仅使英国浪漫派诗歌动物书写传统呈现出现代性转向的趋势,而且使该传统呈现出一定的审美现代性。
“审美现代性就是社会现代性过程中分化出来的一种独特的自律性表意实践,它不断反思着社会现代化本身,并不停地为急剧变化的社会生活提供重要的意义。”[17]70-71换句话说,审美现代性就是以审美的方式对现代性所带来的危机和所呈现出的阴暗面进行审视和反思,以期现代性能朝着健康和谐之道前行。“审美现代性的最终目的是要抵制现代性的负面影响,强调的是对现代性的反思和重建。”[15]108作为英国现代性的审视者,劳伦斯不仅“追根求源地看到了现代社会罪恶的渊蔽, 竭力寻求人类自我解放的出路,”而且“激烈地抨击现代工业文明, 描写扭曲的人性、本能, 希望通过人性的复归, 为死气沉沉的英国和当代社会找到一条再生之道。”[18]93虽然劳伦斯在其“鹰”文本中并未对现代社会的罪恶进行追根溯源,但他把人类中心主义和殖民主义等现代性所造成的恶果披露了出来。这种对人类中心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披露在其后辈诗人泰德·休斯那里又得到了较好的继承和发扬。
结语
泰德·休斯和戴·赫·劳伦斯同是英国浪漫派诗歌自然书写传统的继承人。他们在英国浪漫派诗歌自然书写传统的动态生成中起着重要作用。作为英国浪漫派诗歌自然书写传统之链上的重要一环,劳伦斯在深受其前辈诗人影响的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他的后辈诗人泰德·休斯。这种影响和继承在他们的动物诗创作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在创作他们各自的动物诗的过程中,劳伦斯为其文艺世界中的动物王国增添了一只异类之鹰,而休斯则在续写和戏仿劳伦斯之“鹰”的基础上重构了一只与劳伦斯之“鹰”同类的鹰。从休斯的“鹰”文本与劳伦斯的“鹰”文本的对话中可发现,它们在浪漫主义层面上、人类中心主义层面上和殖民主义层面上具有一定的互文性。这种互文性既是休斯和劳伦斯诗思和情思共鸣的结果,又是他们对英国浪漫派诗歌自然书写传统继承和创新的结果,同时还是该传统动态生成的原因。在休斯和劳伦斯的合力推动下,英国浪漫派诗歌的动物书写传统已呈现出现代性转向的趋势。
注释
① 文中诗歌除特别注明之外均为作者自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