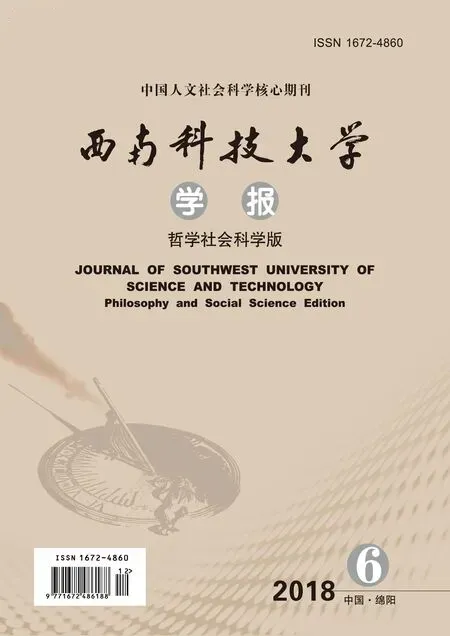宋代中秋节日内涵演变考
张舰戈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北京 100732)
中秋节是中国传承已久的民俗节日,在我国传统节日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在“阖家团圆”的主题和意境下,除春节以外,中秋节最具团聚之义。中秋节在唐、宋逐渐发展起来,已伴随中华文明走过了一千余年的漫长历程。中秋节并非从产生之时就以“团圆”为主题,而是在历史的不断发展中,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不断影响下,逐步加入了“月圆人亦团圆”的节日内涵。
一、明月曾经照古人——北宋以前的中秋节
关于中秋节形成的过程,学术界看法相对一致,中秋节的根基可以溯源到古人对月亮的祭祀和崇拜。周人就有“祭日于坛,祭月于坎”的记载,秦汉时期祭月仍是皇家重要礼制之一,这种祭月仪式后来以秋分祭月的形式一直保留到明清时期。既有朝廷大规模的祭月活动,也有民间对“月”的关注和崇拜。早在西汉刘安所著的《淮南子》中,就有了嫦娥奔月、吴刚伐桂的相关记载:“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羿妻嫦娥窃之奔月,托身于月,是为蟾蜍,而为月精。旧言月中有桂,有蟾蜍。故异书言:月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树创随和。人姓吴,名刚,西河人,学仙有过,摘令伐木。”[1]221魏晋时期,文人赏月、对月抒怀之作也大大增多。如沈休文《应王中丞思远咏月一首》写道“月华临静夜,夜静灭氛埃。方晖竟入户,圆影隙中来。高楼切思妇,西园游上才。纲轩映珠缀,应门照绿苔。洞房殊未晓,清光信悠哉。”[2]433
此时的咏月之作大多不限于八月十五日,诗中出现的“中秋”也和后来的“中秋节”有所区别。古代用孟、仲、季来表达季节的顺序关系,所谓“中秋”是为“仲秋”,即秋天的第二个月份。在中秋节兴盛以前,“中秋”一词更多地是用来表示秋天过半之意,而非某一节日的专有名词。除此之外,时人所著的节序书籍也并未将“中秋”与其他岁时月令并列记载,如南北朝宗懔所著《荆楚岁时记》中并未出现“中秋”一条。至唐代,虽然在律令格敕中没有明确记载八月十五的官方名称和相关规定,但从魏晋时期流传下来的赏月、拜月之风愈演愈烈,文人阶层在八月十五月圆之夜掀起一股“玩月”之风。
中唐以后,欧阳詹在《玩月》诗序中写道,时人于八月十五赏月的原因是“月之为玩,冬则繁霜大寒,夏则蒸云大热,云遮月,霜侵人,蔽与侵,俱害乎玩。秋之于时,后夏先冬;八月于秋,季始孟终;十五于夜,又月之中。稽于天道,则寒暑均;取于月数,则蟾兔圆。”[3]3910说明选择在八月十五夜玩月,是因为天气合适,不冷不热。此夜月又最圆最亮,最适合“玩月”也最容易让人浮想联翩、感慨万千。在中秋之夜流传下来的唐代文人玩月抒怀之作不胜枚举,如白居易的“万里清光不可思,添愁益恨绕天涯”。王建《八月十五夜玩月诗》记载“合望月时长望月,分明不得似今年。仰头五夜风中立,从未圆时直到圆。”中秋玩月在唐朝文人群体中已成为重要组成部分。《唐诗》中“清光凝有露,皓魄爽无烟”“泉澄寒魄冷,露滴冷光浮”这样的诗句随处可见,这虽是中秋之夜诗人对大自然的灵智感受,但从诗句中也可看出是作者独自一人在赏月,其赏月地点多在高楼和山水寂静冷清之处。
关于中秋节的具体起源时间,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中秋节最早起源于宋代,以宋人最早将八月十五日定为官方给假“节日”为证明;另一种认为中秋节起源于唐代,大致在中唐以后,起码文人阶层已经开始将八月十五作为一个特殊日子,用一些特殊表达方式来庆祝八月十五日。宋代提倡者大多认为,宋代以前国家政权未对“中秋节”做相关的解释,并且当时著作《荆楚岁时记》和《岁华记丽》等文献的岁时部也未出现“中秋”一条,直到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才将“中秋”单独列目。另外,宋说支持者多认为,即便唐代中秋已有赏月之风,也只是文人群体的单独行动,普通百姓并未大规模的参与其中,以此为依据,可见中秋节起源于宋代。
唐说支持者多数认为,唐代中秋玩月诗众多,因此唐代文人已把八月十五看做一个有一定意义的独立日期。“有一定数量的人会在这个日子里不约而同地举行某些相对固定的活动,那么中秋节确实在唐代已经出现了。”[4]150虽然二者在判断标准上有些许不同,但有一点相通之处,即在判断一个节日是否形成之时对大众百姓的重视。唐代说提倡者提出,在唐代八月十五玩月并非只是文人的喜好,并举出一些诗文以作依据。如王建的“今夜明月人尽望,不知秋思在谁家。”和张南史的“千家看露湿,万里觉天清。”以及刘禹锡的《奉和中书崔舍人八月十五日夜玩月十二韵》“远近同时望,晶荧此夜偏”[5]4103等词汇语句。如果仅凭诗句中的“人尽望”“千家看”“远近同时望”来证明唐代中秋节已被大众所接受是有失偏颇的。唐代文人阶层从前代承袭了仲秋望月吟诗的传统,但毕竟下层百姓没有如此的文学修养和欣赏水平,即使出现了百姓在八月十五日赏月的情况,也没有赏月以外其他的活动,查找唐代以前的民俗文献也没有出现对中秋民俗活动的记载。所以唐代的玩月只停留在文人圈里,因为这种对月吟诗之风只能让普通百姓望尘莫及。对这些普通民众来说,中秋赏月吟诗不能引起他们过多的兴趣,唐代中秋赏月已经深入市井之民的说法略有不恰当之处。到宋代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赏月的风俗加入更多娱乐气息,市井之民自然也极易接受,于是一股中秋宴饮娱乐之风从上而下蔓延开来,此时中秋之夜可谓真正繁盛起来,“中秋夜,贵家结饰台榭,民间争占酒楼玩月。丝篁鼎沸,闾里儿童,连宵嬉戏。夜市骈阗,至于通晓。”[6]814至南宋时期宁宗颁布假宁令,官员中秋休假一天,“中秋节”才真正列入国家政策和岁时节日之中。中秋节作为一个独立特殊的民俗节日,以宋代为开端更为合理,然而一个节日及其民俗的起源问题往往存在争议,因为民俗节日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不断传承创新。
二、千里共婵娟——北宋中秋节的大众化
北宋时期,中秋节已不再局限于文人士大夫阶层,它逐渐迈出了附庸风雅的高贵门槛,开始走向民间,成了文人唱和宴饮与民众饮酒娱乐双面并行的节日。
北宋的文人士大夫在继承唐代文人对月吟诗的基础上,安排了更加丰富的节日内容:宴请唱和,觥筹交错,曼舞轻歌,不一而足。中秋之时,气候最为适宜,在中秋之夜宴饮同僚、好友,赋诗唱和,成为北宋文人雅士必备之事。如晏殊,北宋文人领袖之一,与王君玉为同朝好友,以诗赋饮酒为乐,中秋之夜常有唱和宴饮的聚会。“尝遇中秋阴晦,公厨夙为备,公适无命。既至夜,君玉密使人伺公,曰,已寝矣。君玉亟为诗以入,曰‘只在浮云最深处,试凭弦管一吹开。’公枕上得诗,大喜。既索衣起,径召客治具大合乐,至夜分,果月出,遂饮乐达旦”[7]1。中秋这天,“公厨夙为备”,晏殊家的厨房一早就做好了中秋宴请的准备,而且宴请的人数应该比较多,由此厨房才要早作准备。无奈碰巧赶上天气阴晦,无月可赏,晏殊大为扫兴,很早就睡了。而王君玉则如往常一般来到晏殊家中准备参加中秋夜宴,并赋诗一首以劝诱晏殊。于是晏殊遂重新招徕宾客,请出歌舞乐妓奏乐唱和。又明道元年“遇中秋,晏殊启宴,召宋,出妓饮酒赋诗,达旦方罢。”[8]409由此可知,宾主双方都将在中秋之夜聚友宴饮视为平常之事。
再如北宋文豪欧阳修、梅尧臣等也常在中秋夜相聚玩月。庆历八年,欧阳修知扬州,中秋设宴,许发运、梅尧臣、王琪等好友前来。欧阳修以诗邀约“仍约多为诗准备,共防梅老敌难当。”梅和之曰“曾非恶少休防准,众寡而今不易当。”席上既有美酒珍馐,又有轻歌曼舞,“罗绮尘随歌扇动,管弦声杂雨荷干”就连水中池鱼都忍不住前来凑热闹,“听曲跃文鱼”“池鱼暗听歌声跃”,中秋夜宴的气氛是轻松欢快的。不仅晏殊、欧阳修、梅尧臣这几位文坛领袖的中秋之夜少不了歌舞夜宴、赋诗唱和,其他文人的中秋节也基本大同小异。如王珪的“夕宴中秋醉广寒,美人半夜歌明月。”[9]65李之仪的“玉琯传声,羽衣催舞,此欢难借。”黄裳作《中秋日宾兴宴》,陈舜俞作《中秋玩月宴友》等,宋代文人士大夫所作的中秋玩月宴饮的诗词不胜枚举。
在唐诗中体现出来的唐代文人的中秋意境多是孤寂清冷、文艺高雅,是让普通百姓望尘莫及的,唐代文人的中秋情节并没有过多地影响到百姓的生活。宋代文人雅士的中秋节已经脱离了唐代文人的轨道,从对月自赏发展为好友宴饮唱和,并以歌舞为伴,从唐代清冷孤寂的意境中解脱出来,向世俗娱乐的方向发展。
宋代文人以同僚好友赋诗唱和为主,辅以歌舞宴饮助兴的节日庆贺方式,更加世俗化、娱乐化,更加贴近市民百姓的生活,也更加便于百姓的理解和模仿。受文人士大夫的影响,中秋节宴饮娱乐之风扩大到普通市民阶层。但毕竟不同的文化层次有不同的文化追求和精神需求,他们在模仿的同时抛弃了唱和作诗的风雅,加入了自身对中秋节欢庆的理解和要求。北宋市民欢度中秋的情景,最具代表性的应属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中所描绘的景象:
“中秋节前,诸店皆卖新酒,重新结络门面彩楼花头,画竿醉仙锦旆。市人争饮,至午未间,家家无酒,拽下望子。是时螯蟹新出,石榴、漓勃、梨、枣、栗、孛萄、弄色枨桔,皆新上市。中秋夜,贵家结饰台榭,民间争占酒楼玩月。丝篁鼎沸,近内庭居民,夜深遥闻笙竽之声,宛若去外。闾里儿童,连宵嬉戏。夜市骈阗,至于通晓。”[6]814
中秋节前夕,各酒铺就开始重新装饰店面,挂起酒旗,吸引客人。市民也争相买酒畅饮,还没到下午,酒已经争抢一空。各种时令水果也琳琅满目。中秋之夜,富贵人家登上绵延至月中的台榭饮酒,撤去遮挡门窗的帘幕共赏明月。普通市民也一样在酒楼畅饮玩月,有管弦奏乐助兴。夜市的喧闹与儿童嬉戏一并,通宵达旦。不仅如此,在皇宫之内,也是丝竹鼎沸,直至深夜。又如,仁宗时期的陈舜俞所做《中秋玩月宴友》中讲到“都人尤侈盛,时节惜芳佳。楼台延晧魄,帘幕去周遮。交错宴子女,嘈杂鸣箫茄。”如此可见,北宋时期,中秋节已经具有了浓厚的节日气氛,尤其是在都城汴京地区,已经成为社会各阶层普遍参与、玩赏游乐的节日。
北宋中期以后,中秋节沿着唐代历史发展的轨迹出现了新的变化。
首先,宋代文人的中秋节气氛不再似唐代一般孤寂清冷,亲朋同僚间的唱和宴饮成为宋代文人庆贺中秋的习惯和主流。其中虽不乏对月感怀之作,但大多数道出的也是自己孤身在外,不能与好友唱和的寂寞和遗憾。这种变化的发生与北宋文人士大夫整体境遇和地位的变化息息相关。宋开国以后即确立了重文轻武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祖宗家法,文人士大夫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改变了唐代文人郁郁不得志的境地。因为可以在政治上发挥一定的作用,宋代士大夫的心态也随之产生了极大变化:他们不再消极避世,而是以天下为己任,“实现治国平天下的宏愿,体现出一种强烈的汲汲用世的外向追求。”[10]这种地位的优越性和满足感反映到文化生活中,自然不再以清冷孤寂的情调为主,更多地表现为积极参与政治和同僚交流的心态,因此中秋节轻快的歌舞宴饮之风也流行开来。
其次,由于文人中秋情节的娱乐化、世俗化,使节日的庆贺形式更贴近普通市民,玩月宴饮之风也逐渐渗透到普通市民阶层之中。宋代随着士大夫政治地位的提高,其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各种生活习惯、节庆方式也逐渐受到追捧和模仿。另外,北宋的社会经济在中期以后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普通百姓生活水平提高后,也需要一些精神上的娱乐和慰藉。但是他们本身又缺乏创造、精神食粮的创造力,于是,身份高贵的士人们亲和、世俗的过节方式逐渐侵染到社会各层。到北宋中期仁宗以后,无论是富商大贾,还是普通百姓,都要饮酒作乐以庆中秋。同时,他们又舍弃了文人作诗唱和、抒发情怀的风雅,极大地发展着宴饮娱乐的风气,将中秋节从文人吟诗作对中剥离出来,向大众化、普泛化的方向发展。
三、月圆人亦团圆——南宋中秋节的思乡情
北宋时期,无论对文人士大夫还是普通百姓来说,中秋节多展示出轻松、娱乐的一面,但到南宋以后,特别是在靖康之乱和蒙元侵宋这两个特殊时期,中秋宴饮之时记录对家乡亲人的思念和对国家破亡的伤感之作有所增加。以中秋圆月寄托情思,中秋节加入了对阖家团圆与山河重复的期望和企盼。
北宋时期的中秋节日,文人多与同僚好友共赏明月、宴游吟诗,与兄弟子女等亲人团聚的记载寥寥无几。从对《全宋诗》的搜索结果来看,较早提到中秋之夜与家人团聚记载的,应属孔平仲所作的《熙宁四年中秋》:“月满光尤好,秋殷气更清。频年苦阴雨,此夜独晴明。后阁罗甥妹,前堂合弟兄。团圆最相称,尽饮至深更。”[11]10902除此之外,其他涉及“团圆”的诗词多属送别兄弟之作,如晁补之送八弟无释到宝应赴任,对月而感“卷书帷寂静,对此伤离别。重感叹、中秋数日又圆月。问几时、清樽夜景共佳节。”[12]516这虽然也表达了对亲情团圆的期盼,但多属送别兄弟子侄外任之作,只是涉及到家族中男性成员的活动,对家人、子女的活动极少提起。除文人之外,孟元老在中秋一节的记述中,也只是写道“民间争占酒楼玩月”,并未涉及家庭内部的宴饮团圆,究其原因,大致是此时阖家宴饮之风尚未流行,家人团圆也并不是中秋主题。
南宋以来,虽然文人对同僚好友在中秋之时欢聚一堂的热情不减,但对家宴、阖家团圆的记载也有所增加。表现在诗词中主要有以下几处。李光于绍兴十四年作《临江仙(甲子中秋微雨,闻施君家宴,戏赠)》,诗人薛嵎作《中秋家人玩月》,女诗人朱淑真作《中秋夜家宴咏月》三首诗词,在题目中就明确道出中秋夜与家人玩月或中秋家宴的情况,中秋节不再只是男性亲属或朋友的团聚,妻妾女子也参入其中。尤其是女诗人朱淑真的诗词更表现出女性家庭成员已经参与到中秋家宴之中。另外,刘学箕在外宦游时思念家乡和亲人,作《安康中秋书》感怀去年中秋在家乡与众人把酒言欢,今夕却孤身在外。看到某处人家在中秋之夜家人团聚“妇翁欢喜婿远来,阿妇见爷双靥开”他人一家团圆喜笑开颜,作者自己也勉强振作,饮酒如故。并感叹“但愿吾身益强健,莫使骨肉叹南北”,从中也可以看出,对于普通百姓来说,中秋节最期盼家人团聚,只有家人团聚才会喜笑开颜。王炎在淳熙十三年作《丙午中秋夜》:“免与朋侪争翰墨,聊呼儿女具杯盘。”这些诗文虽然只有寥寥数语,但却体现了南宋中秋节日内涵的变化。上述几篇诗文中几乎都出现了“家宴”“家人”和“团圆”的字眼,并且这些诗词都是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所作,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在南宋以后,一些家庭出现了有女性家庭成员参与家宴的情况,家人团聚成为中秋节的一项重要活动内容。
除诗词之外,宋人笔记小说中也出现了一些关于中秋家人团聚宴饮的记载。最常见的应属吴自牧《梦粱录》中关于中秋节的记载:
“八月十五日中秋节,此日三秋恰半,故谓之‘中秋’。此夜月色倍明于常时,又谓之‘月夕’。此际金风荐爽,玉露生凉,丹桂香飘,银蟾光满。王孙公子,富家巨室,莫不登危楼,临轩玩月,或开广榭,玳筵罗列,琴瑟铿锵,酌酒高歌,以卜竟夕之欢。至如铺席之家,亦登小小月台,安排家宴,团栾子女,以酬佳节。虽陋巷贫窭之人,解衣市酒,勉强迎欢,不肯虚度。此夜天街卖买,直到五鼓,玩月游人,婆娑于市,至晚不绝。盖金吾不禁故也。”[13]48-49
如果将《梦粱录》和《东京梦华录》中“中秋”一条进行对比,二者除了都写到中秋欢乐节日气氛以外,最大不同在于对普通百姓过节的记载。《东京梦华录》中只是提到:中秋夜民间争占酒楼玩月,闾里儿童,连宵嬉戏。而《梦粱录》中则增加了普通人家也会登上小小赏月之台,安排家宴,团栾子女,共度中秋佳节。两文对比可以说明,到南宋以后,中秋节安排家宴、子女团聚已属寻常之事。而在孟元老所追述的北宋汴京,这一习俗显然并没有像饮酒赏月一般流行。
又如,张镃作《赏心乐事》排比十二个月宴饮游乐之事:八月仲秋在摘星楼赏月家宴团圆,到群仙绘福楼观月游玩。洪迈《夷坚志》记载“绍熙二年,中秋夜,周与妻侍母饮酒赏月,见母坐立艰辛,不觉墜泪。”[14]490这些和《梦梁录》的记载相互应和,说明中秋家宴、家人团聚不仅是文人墨客欢度中秋节日的形式,也是普通百姓欢度中秋佳节的主要习俗之一。
家宴流露出了对亲人团圆的希望和期盼,正如远在他乡之人对故乡和故国的思念。南宋偏安一隅,由月亮圆缺想到不能归乡,想到“金瓯已缺”家国何时能复?更引文人无限愁思。尤其是南宋在靖康之乱和蒙元攻宋以后,这种家国之思,在中秋月圆之夜显得更加浓郁。词人赵师侠“京华倦客难堪,羁思历尽愁边。寄语姮娥休笑,月圆人亦团圆”;辛弃疾作《太常引·建康中秋夜,为吕叔潜赋》“一轮秋影转金波,飞镜又重磨。把酒问姮娥:被白发欺人奈何?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斫去桂婆娑,人道是清光更多。”[15]34借中秋圆月,展现出靖康之后渴望收复故国山河的心愿。刘辰翁中秋作词《水调歌头》表达国家沦陷,故国已失的伤感之情。在中秋时节思念家乡、感怀故国的记载不胜枚举。
靖康之乱后,宋室失去了半壁江山,偏安一隅。为免于战火,北方士人和百姓随高宗大量南迁,成为南方的“异客”。即使是举家南迁,亦受安土重迁思想的深刻影响,对北国故乡和亲人产生深深思念。在中秋夜天上月圆之际,更加深了对家乡的思念之情,因此对家人团聚倍感珍惜。此时,一些文人士大夫壮志未酬,走出小家的界限,将月圆与山河破碎联系起来,用中秋诗词倾诉自己恢复旧山河的满腔热忱。经历了山河沦陷和骨肉分离之痛的南宋人民,在中秋之时不似北宋一般,只是一味地宴饮娱乐,以度佳节。他们在“歌舞升平”中加入了对家宴的重视和对家人团聚的渴望,因此对家宴的记载也更多地显现出来。
到宋室南渡、北人大量南迁以后,明月“团圆的特征和象征意义得到突出和强调,中秋节俗的内涵增加了阖家团圆的人伦涵义。”[16]中秋节不再是单纯的文人唱和、市民宴饮的娱乐性节日,它被赋予了自身独特的节日内涵“团圆”。
南宋中期以后,随着理学的发展,作为儒家伦理根基的“忠孝悌节义”也自然更加被提倡。理学家们在社会上宣扬和推行伦理道德时“并非一味倡导僵化极端的孝义形式,他们更多的是秉承合乎礼制的道德规范在基层社会中树立了大批彰显人伦、有益教化的孝悌典型。”[17]如前文提到的“周昌时孝行”即被树立为社会典范。“父母在,不远游。”中秋佳节陪伴家人,孝敬父母也更合乎理学家们提倡的社会道德规范,中秋家国团圆也具有了一定的伦理意义。
随着自身团圆意义的凸显,中秋节也日渐得到了朝廷和官方的认可,在官方文书和法律制度中也出现了中秋节的记载。南宋朝廷增加了中秋节官员放假的规定,表明了官方对中秋节作为一个独立节日的认可,统治者的倡导也推动了中秋节民俗文化的发展,家国团圆的思想在朝廷的倡导下越发重要,成为中秋节日风俗的核心内涵。
结语
中国节日民俗代代相传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中秋节由古代祭月、拜月之风演变而来,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完善,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联系到人间的悲欢离合。起初祭月、拜月之礼逐步演化为赏月、玩月之风,并不拘泥于八月十五这一天,直至隋唐时期,玩月之事才大致拟定在八月十五之夜,因为此时秋高气爽、明月最圆,最适合赏月。文人骚客对月感怀,中秋吟月也成为一时风尚,宋人承袭了唐代的方式。
民俗节日内涵的不断发展,在传承的基础上,受到不同地区文化、经济状况的影响,也会发生变化。“历史在进步,社会在发展,人类生活不断更新,节日风俗也不断被注入新的内容。”[18]29随着宋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宋代文人士大夫社会地位的提高,他们表现出更为积极的心态,中秋赏月走出了唐人孤冷凄清的氛围,向娱乐化、大众化方向发展,中秋宴请同僚、观歌舞、作诗词成为主流。受此影响,广大市井之民也参与到中秋宴饮之中。北宋时期,中秋赏月、宴饮、玩乐成为各阶层必备之事。中秋节在北宋时期表现出了参与阶层普遍化和节日形式娱乐化的特点。但值得注意的是,此时,中秋期盼“阖家团圆”和“山河无缺”的社会气氛并不浓厚。
靖康之乱宋室南渡以后,受家国破裂的影响,“团圆”逐渐被加入到中秋节中,家宴、团聚成为这一节日的核心内涵。中秋节由纯娱乐性活动转变为具有象征团聚意味的节日,表现出南宋以后人们价值观念的转变。这种变化不仅得到了民间的认可,也相应得到了朝廷的重视,在孝宗时期朝廷就有过是否将其纳入节日系统的讨论。到宁宗时,中秋节首次得到官方认可,加入到官员节假日的体系当中。南宋时期,中秋节“团圆”意义的加入在靖康和宋亡以后更加凸显,发展至明清时期成为中秋节的核心内涵,它表达了人们对亲情和国家团圆的希望,成为人们在异地他乡的精神支柱,也使中秋节日永葆活力,保证了它在中国传统节日中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