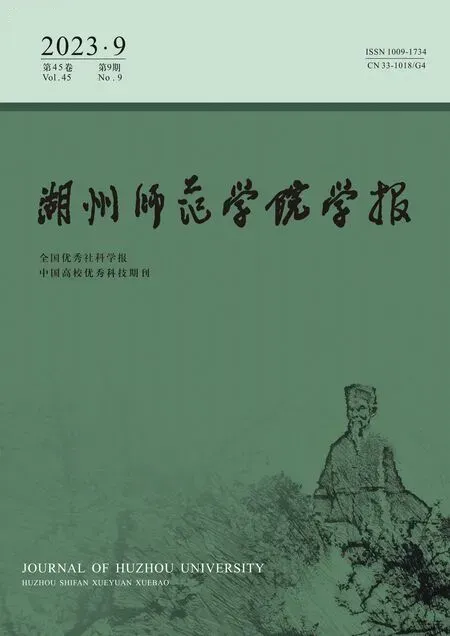吕祖谦《宋文鉴》的选赋特色及赋史意义*
华若男,杨许波
(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吕祖谦《宋文鉴》作为现存最早最全备的北宋诗文总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北宋各体文学发展的真实样貌。相对于诗文,《宋文鉴》的选赋尚未受到学界关注。事实上,《宋文鉴》收录了52位赋家90篇赋作,是现存最早且篇幅最大的北宋赋选集,对于北宋赋史的建构有着重要作用。刘培在《两宋辞赋史》开篇指出,“在宋代文学研究中,宋文研究是薄弱环节,宋代辞赋又是宋文研究的薄弱环节”[1]1,《宋文鉴》的选赋无疑值得我们进行深入探讨。《宋文鉴》的选赋在宋代独树一帜地呈现出某种程度的“异化”倾向:在宋代持续不断的诗赋与经义之争风潮下,依旧对赋体倾注了特别的情感,选赋数量多且有代表性,较为明晰地呈现了北宋赋的发展流变脉络;在宋代科考重律赋的大环境下,古、律赋兼收,且选录古赋数量远超律赋;在宋人辨体、破体意识强化的影响下,打破了《文选》开创的以类选赋的传统,首开以选本辨赋体的先河。可以说《宋文鉴》的选赋既是北宋赋坛生态的缩影,同时又表现出与北宋赋坛主流风气的疏离。基于此,本文试图以《宋文鉴》的选赋作为研究切入点,分析其选赋特色、背景及后世影响。
一、《宋文鉴》的选赋特色
宋之前专门的赋集很少,入宋以来赋集的编纂才蔚然成风(1)许结:《历代赋集与赋学批评》,《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第28页:“唐人专门赋集甚少,像王棨《麟角集》收律赋数十篇,乃是凤毛麟角。考《新唐书·艺文志》,见录有李德裕杂赋2卷、陆龟蒙赋6卷、李商隐赋1卷、薛逢赋集14卷、卢献卿《愍征赋》1卷、谢观赋8卷、卢肇《海潮赋》《通屈赋》各1卷、林绚《大统赋》2卷、高迈赋1卷、皇甫松《大隐赋》1卷、崔葆数赋10卷、宋言赋1卷、陈汀赋1卷、乐朋赋1卷、蒋凝赋3卷、公乘亿赋集12卷、林嵩赋1卷、王翃赋1卷、贾嵩赋3卷、李山甫赋2卷等。宋人辑选辞赋之风较唐人盛。”。《宋史·艺文志》记载的北宋赋集即有:徐锴《赋苑》200卷、《广类赋》25卷、《灵仙赋集》2卷、《甲赋》5卷、《赋选》5卷、《桂香赋集》30卷,杨翱《典丽赋》64卷、《类文赋集》1卷[2]5394,王咸《典丽赋》93卷[2]5402,李祺《天圣赋苑》18卷[2]5403等。此外,范仲淹亦主编有指导士子作律赋的《赋林衡鉴》,但仅序文得以流传至今。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五“总集类”亦载:“《后典丽赋》四十卷”,下行小字注“金华唐仲友编。……此集自唐宋末以及本朝盛时,名公所作皆在焉,止于绍兴间”[3]457;“《指南赋笺》五十五卷、《指南赋经》八卷”下行小字注“皆书坊编集时文,止于绍熙以前”[3]458。这些书大多都已散佚,我们仅能通过目录书的存目确定其曾存在,但无法进一步获知北宋赋收录的具体情况,颇为可惜。与此同时,宋人编选的文章总集所收北宋赋数量却并不多,《宋文海》虽收录赋,但根据祝尚书《宋人总集叙录》的爬梳(2)祝尚书:《宋人总集叙录》,中华书局,2004年,第97页:“《新雕圣宋文海》一百二十卷,宋江钿辑,存卷四至九,计六卷。……卷四古赋,卷五赋,卷六赋,卷七记,卷八铭,卷九诏。”,可知其留存下来的赋仅三卷(卷四至卷六):卷四为“古赋”,选录8篇,卷五、卷六为“赋”[4]97,分别选录7篇、1篇[5]107,共计16篇。佚名《宋文选》、魏齐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均未列赋体且未收赋作;王霆震《古文集成》、楼昉《崇古文诀》未列赋体但收录了极少量的汉赋,然而并未收录北宋赋;谢枋得《文章轨范》仅收录北宋苏轼赋2篇,林之奇《观澜文集》收录北宋赋6篇,数量均极少。而《宋文鉴》共选录了52位赋家的90篇赋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样本,通过总结其选赋特点可以大致勾勒出北宋赋的发展流变历程。
《宋文鉴》选赋横跨了整个北宋时期,历时一百六十余年,且选录赋的数量高达90篇,较同时代的大多数选集更为可观;其选录的赋作中,骚体赋、逞辞大赋、律赋、散体文赋各种体式兼备,同时,其所涉及的题材亦十分丰富,几可涵盖此前赋家的各类题材,并呈现出一些新特点;后世公认的北宋重要赋家如梅尧臣、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张耒等人的代表作,也尽数被囊括其中,因而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首先,《宋文鉴》选赋时期跨度大,选取了自赵宋王朝建国(960)到北宋灭亡(1127)这167年间52位赋家的90篇赋作,其中包括古赋71篇,律赋19篇。吕祖谦全面考量了不同时期赋作的选录标准及数量,简要勾勒了北宋赋发展流变的线索。郭维森、许结合著的《中国辞赋发展史》将北宋赋的发展划分为三大阶段:宋初太祖、太宗、真宗三朝(960-1022)是北宋赋在继承前代中求新变的时期,《宋文鉴》选录赋家11人,占比21.2%、赋作12篇,占比约13.3%。这一时期沿袭唐人科举考赋制度,故赋在体制上多沿袭前代,但在写作手法及赋作风格方面均表现出新气象,名家、名篇均较少。庆历(1041-1048)到元丰(1078-1085)年间是北宋赋由变革而繁荣的重要阶段,选录赋家20人,占比38.5%,赋作40篇,约占44.5%。这一时期抒情小赋、骚体赋创作颇为兴盛,文赋创作兴起,出现了文赋大家欧阳修和长于骚体赋的王安石,选录名家、名作数量较多。元丰以后为北宋辞赋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期,选录赋家21人,占比40.3%,赋作38篇,占比42.2%。此期散体文赋大兴,出现了以苏轼及“苏门四学士”为代表的辞赋名家,名家、名篇数量亦多。概括言之,《宋文鉴》的选赋大体上涵盖了整个北宋,且各个时期的选赋数量也大致合于赋坛发展的实际情况。
其次,《宋文鉴》开启了文章总集辨赋体的先河,透露出宋人对赋体认识的深化及强烈的文体自觉意识。与此同时,其选录赋的题材极为丰富,鲜明地呈现了北宋士人审美旨趣的多样性。许结《历代赋集与赋学批评》一文指出:“缘于唐人赋‘大抵律多而古少’(祝尧《古赋辩体》卷七《唐体》),赋学批评亦因创作变化而确立‘古赋’‘律赋’之名,尽管唐以后科举试赋与否,然此后赋论史的古、律赋之辨与赋体之争,实为其批评主潮。”[6]31此系针对赋学批评而言,赋体之辨在唐代并未体现于文体分类的实践层面。至宋代,文学总集才开始有意识地区分古赋与律赋,《唐文粹》专选古赋,以古为尊,而《文苑英华》惟取律体,以时文为尊。吕祖谦则采取了一种更为折中的态度:古赋与律赋兼收,且将其分别置于不同的编次,古赋在前,律赋在后,不偏废一方的同时亦更凸显二者间的差异,已然呈现出较为鲜明的“辨体”倾向[7]34。吕祖谦选赋还兼顾了题材的丰富性。根据清人陈元龙《历代赋汇》的分类,《宋文鉴》所收录赋的题材多达28个大类,涵盖宫殿、典礼、旷达、蒐狩、地理、草木、音乐、天象、性道、都邑、室宇、岁时、花果、仙释、情感、祯祥、怀思、览古、言志、人事、饮食、玉帛、鸟兽、鳞虫、行旅、武功、讽喻、治道等题材,其中典礼、地理、天象、性道、治道类赋选录较多。从这些丰富的题材中,我们既可以看出宋代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高度发达,还可在一定程度上看出宋代文化的某种转向:一是追求文学的经世致用,二是士人的政治参与热情空前高涨,三是士人的关注重心内转,注重个人修养的提升。
最后,《宋文鉴》选录的赋家、赋作均极具代表性,宋室南渡之前的重要赋家大多被选入其中,其所选赋作也多为后世赞誉的名篇,当代最重要的辞赋史北宋部分重点介绍的赋家皆出于《宋文鉴》。马积高《赋史》[8]北宋赋部分重点介绍的赋家有梁周翰、张詠、杨侃、王禹偁、范仲淹、叶清臣、宋祁、刘敞、司马光、王回、梅尧臣、欧阳修、王安石、沈括、蔡确、狄遵度、崔伯易、苏辙、苏过、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米芾、刑居实,多达25人,约占《宋文鉴》所选赋家总数的50%;郭维森、许结合著《中国辞赋发展史》[9]北宋赋部分设置专节或进行专门介绍的赋家即有:梁周翰、张詠、夏侯嘉正、杨侃、种放、杨亿、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邵雍、周敦颐、司马光、刘敞、刘攽、王安石、沈括、蔡确、苏轼、苏辙、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周邦彦、米芾、刑居实,共计26位,恰好占《宋文鉴》所选赋家的50%;刘培《两宋辞赋史》[1]北宋赋部分则重点介绍了王禹偁、晏殊、宋祁、宋庠、范仲淹、王安石、王回、梅尧臣、欧阳修、刘攽、刘敞、苏轼、苏辙、黄庭坚、张耒、晁补之16家,约占《宋文鉴》选录赋家的31%。由此可见,《宋文鉴》所选赋家大多都可独立名家,在北宋赋学史的地位得到学界公认。
与此同时,吕祖谦还能十分准确地挑选出最能代表宋赋特色且又最富于赋家个性特色的佳作,在入选的赋家中,苏轼赋选录最多,共8篇,其次是张耒(6篇)。唐子西评价苏轼最负盛名的文赋代表作《后赤壁赋》:“余作《南征赋》,或者称之,然仅与曹大家争衡耳。东坡之《赤壁》二赋,一洗万古,欲仿佛其一语,毕世不可得也。”[10]261浦铣称赞张耒的抒情小赋《鸣蛙赋》:“张文潜《鸣蛙赋》,熟读之使人矜平躁释,此宋文之胜唐人处也。”[10]399此外,后世所公认的宋赋名篇如钱惟演《春雪赋》、欧阳修《鸣蝉赋》《秋声赋》、王安石《思归赋》、苏轼《滟滪堆赋》《昆阳城赋》《秋阳赋》、崔伯易《感山赋》、黄庭坚《煎茶赋》、周邦彦《汴都赋》、秦观《黄楼赋》、刑居实《南征赋》、蔡确《送将归赋》、范镇《长啸却胡骑赋》(按入选《宋文鉴》所属卷数排列)等也大多为吕祖谦所选录,在当前通行的各类赋学专著中都均占有一席之地。
概括言之,《宋文鉴》的选赋在宋人总集中呈现了独特的风貌:时期跨度广,体量大;注重辨体,体式全备,题材丰富;所选赋家、赋作具备典型意义。
二、《宋文鉴》选赋的特定背景
《宋文鉴》的选赋在宋代无疑别具一格,在当时已然兴起的古律赋之争中采取了相对折中的处理方式,但其中还是明显透露出“重古轻律”的观念,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宋代赋坛主流风气的背离。
首先,唐代开创的以诗赋取士传统为宋人所继承,不同之处在于:唐人取士重于诗,宋人取士重于赋。欧阳修《六一诗话》已有记载,其中提到宋初“自科场用赋取人,进士不复留意于诗,故绝无可称者”[11]16。刘克庄《后村题跋·李耘子诗卷》对唐宋诗赋取士还作过一番比较:
唐世以赋诗设科,然去取予夺,一决于诗,故唐人诗工而赋拙。……本朝亦以诗赋设科,然去取予夺,一决于赋,故本朝赋工而诗拙。[12]1484
虽然北宋科举曾因诗赋与经义之争几度罢赋:熙宁四年(1071)罢赋,元祐元年(1086)恢复考赋,绍圣元年(1094)再罢,建炎二年(1128)再复,但赋在宋人仕进过程中依旧占据了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有人因具备优秀的作赋能力而名动一时,声名甚至远播异域,如《宋史·范镇传》记载:“(范镇)少时赋《长啸》(即《长啸却胡骑赋》),却胡骑,晚使辽,人相目曰:此‘长啸公’也。兄子百禄亦使辽,辽人首问镇安否。”[2]10790还有人因为杰出的作赋才能顺利跻身仕途,《宋史·崔公度传》记载:“欧阳修得其(崔伯易)所作《感山赋》,以示韩琦,琦上之英宗,即付史馆,授和州防御推官,为国子直讲,以母老辞。”[2]11152还有不少如今为我们所熟知的诗词名家也以赋闻名于当时,比如晏殊即是一例,《宋史·晏殊传》记载:
景德初,张知白安抚江南,以神童荐之。帝召殊与进士千余人并试廷中,殊神气不慑,援笔立成。帝嘉赏,赐同进士出身。宰相寇准曰:“殊江外人。”帝顾曰:“张九龄非江外人耶?”后二日,复试诗、赋、论,殊奏:“臣尝私习此赋,请试他题。”帝爱其不欺,既成,数称善。[2]10195
甚至秦观在北宋文坛崭露头角也是因为赋,浦铣《历代赋话》记载:“见苏轼于徐,为赋《黄楼》,轼以为有屈、宋之才。”[10]106其因杰出的赋才见赏于苏轼,最后成为苏轼最得意的门生。上述例子无一不说明赋在北宋文坛的重要地位。
其次,《宋文鉴》的选赋特点还与宋人辨体、破体意识的强化有关。元人祝尧《古赋辩体》卷八“宋体”序即云:
王荆公评文章尝先体制, 观苏子瞻《醉白堂记》曰:韩白优劣论尔。后山云:退之作记, 记其事尔。今之记乃论也。少游谓《醉翁亭记》亦用赋体。范文正公《岳阳楼记》用对句说景,尹师鲁曰“传奇体”尔。宋时名公于文章必辨体, 此诚古今的论。然宋之古赋往往以文为体, 则未见其有辨其失者[12]卷八。
由此可见,北宋各类文体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破体倾向,宋人就已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并开始有意识地辨体。祝尧更为明确地指出,学界鲜有针对宋人“以文为赋”这一破体现象的得失探讨。北宋总集的选赋已然呈现出较鲜明的辨体意识,比如《唐文粹》全选古赋,《文苑英华》则全选律赋,而《宋文海》已有意识地在区分“古赋”(卷四)与“赋”(卷五、卷六),《宋文鉴》则显然受到了《宋文海》的影响,将赋体分为“赋”与“律赋”。以上是总集的情况,别集亦然,因为宋代沿袭了唐代科举考律赋的传统,故宋人别集中大量收录律赋,如刘攽《彭城集》、王禹偁《小畜集》、文彦博《潞公集》等,甚至还有人在自己的别集中专门区分“古律赋”与“律赋”,比如杨杰《无为集》。根据目前所能了解到的情况,我们可以推知,宋人已有较为自觉的辨别赋体意识,且会在选赋过程中有意识地区分“古赋”与“律赋”,可以说《宋文鉴》选赋注重分体是赋体发展到宋代的必然趋势。
此外,《宋文鉴》选赋更为特殊之处在于,其选录古赋(还可再细分为骚体赋、仿汉大赋、骈赋和文赋)数量明显多于律赋,但宋代科举考律赋而非古赋,范仲淹《赋林衡鉴序》即有语云:
律体之兴,盛于唐室。贻于代者,雅有存焉。可歌可谣,以条以贯。或祖述王道,或褒赞国风,或研究物情,或规戒人事,焕然可警,锵乎在闻。国家取士之科,缘于此道。[14]508
他编选《赋林衡鉴》的初衷是为了襄助士子科考,虽然这一赋集已散佚,但律赋在宋代科考的地位我们于此序言亦可见一斑。吕祖谦选录古赋远多于律赋是出于何种考量,这又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或许这与古人的文体正变观念有关,明代吴讷《文章辨体·凡例》有语云:“四六为古文之变,律赋为古赋之变,律诗杂体为古诗之变,词曲为古乐府之变。”[15]10由此可以推知,吕祖谦应该也受到了文体源流正变观念的影响,视古赋为正体,律赋为变体。
最后,《宋文鉴》的选赋可能还与吕祖谦的教书先生身份息息相关。《吕东莱先生本传》记载:“乾道二年丙戌,丁母夫人曾氏艰。护丧归婺,庐于武义明招山墓侧,四方之士争趋之。”[16]319由此可知,吕祖谦于乾道二年(1166)回故乡浙江武义丁母忧期间开启了其教学生涯。吕祖谦《东莱吕太史别集卷第九·与刘衡州》记载孝宗乾道三年(1167):“近日士子相过,聚学者近三百人。”[17]453从这则材料可以看出,吕祖谦在当时的士子中有着非同一般的影响力,吸引了大批求学士子慕名而来。此外,吕祖谦还创办了专门的书院——丽泽书院聚众讲学,其年谱记载他于乾道六年(1170)闰五月:“八日,会诸生于丽泽,有《规矩七事》”[16]306。甚至连朱熹都将其长子朱塾送至吕祖谦门下受教,可见吕祖谦作为教书先生得到了时人的高度认可。
持续不断的废赋与复赋之争导致众多士子丧失了作赋能力,乃至到了哲宗元祐年间突然恢复考赋的时候,一度出现找不到考官、改卷老师的荒唐局面。《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丁骘所上奏章:
窃睹明诏,欲于后次科举以诗赋取士,天下学者之幸也。然近时太学博士及州郡教授,多缘经义而进,不晓章句对偶之学,恐难以教习生员。臣愚欲乞下两省、馆职、寺监长贰、外路监司各举二人曾由诗赋出身及特奏名入仕者,以充内外教官。盖经义之法行,而老师宿儒久习诗赋,不能为时学者,皆不就科举,直候举数应格,方得恩命。今或举以为教官,当能称职。[18]9963
这仅是北宋年间的情形。“赋荒”对南宋年间产生的影响,我们仅看宋人吴处厚所编《三元元祐衡鉴赋》及元祐赋在南宋科场受到的推崇便可见一斑,陈谠谓“举子词赋,固不敢望如《三都》,得如《三元元祐赋》足矣”[19]。正是因为几度罢赋造就的赋荒,才使得元祐赋在南宋大放异彩,最具代表性的即为“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这一佳话的广为流传,虽然不是专门针对赋而言,但从中亦足以看出以苏轼为代表的元祐文人文学创作(其中自然包含赋体)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吕祖谦在《宋文鉴》选录大量北宋赋固有存一代文献的考量,但也不排除有为科场士子树立赋作典范的特殊用意,毕竟在此之前,吕祖谦已有凭借自身科考成功经历为士子编选《古文关键》的经验。吕祖谦选录的赋家在当时几乎都可独立名家,并因作赋才能或在当时顺利跻身仕途,如王曾、崔伯易;或为名家所激赏并由此在宋代赋坛占据一席之地,如张耒、刑居实;其所选赋作也大多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或在艺术或在思想方面有可资借鉴之处,足资作为士子学习的典范。根据吕祖谦为士子编选《古文关键》的经历,不难发现他在文章鉴赏方面的卓越才能。该文集所选6篇北宋赋(苏轼《赤壁赋》《后赤壁赋》、苏辙《黄楼赋》、秦观《黄楼赋》、欧阳修《秋声赋》《憎苍蝇赋》)全为北宋大家手笔,且均为有较明显破体倾向的古赋或文赋,其选赋成因就更有迹可循了。
简而言之,《宋文鉴》选赋特点的形成,首先离不开当时科举重赋才的特定历史背景以及持续不断的罢赋与废赋的特定政治环境;其次还与它顺应了宋代文学发展的总体趋势,即“破体为文”的风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最后,还与吕祖谦个人独特的教书先生的身份密不可分,他自己就曾两度高中(3)杜海军:《吕祖谦年谱》,中华书局,2007年第304页。据记载,吕祖谦于孝宗隆兴元年癸未(1163)“春,试礼部(奏名第六人)。四月十二日,赐进士及第,改左迪功郎。又中博学鸿词科”。,积累了丰富的科考经验,而赋体作为重要的科场文体之一,其地位不言自明,吕祖谦重视赋体亦属于情理之中。
三、《宋文鉴》选赋的后世影响
吕祖谦凭借独特的选赋眼光,呈现出对古赋审美旨趣的回归,表现出对当时科场积弊已久赋风的纠偏;而《宋文鉴》的选赋在体裁与题材方面的齐备性,不仅为北宋赋选提供了范例,还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宋赋的经典化;同时由于《宋文鉴》选赋在数量和质量方面的独特优势,相对较为全面地展示了北宋赋的整体概貌,促进了北宋赋史的初步建构。
首先,《宋文鉴》首次以选本的形式开辨赋体的先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世古律赋之争中的“复古”倾向,表现出对科场赋风的有力反拨。
《文选》开启了总集选赋的先河,在它之后赋集的编纂都不约而同地以《文选》作为蓝本。同时,许结还指出:“由于赋‘类’的意识得以扩展,且受类书的影响,古人编赋尤其是编赋总集时,多以类相分,赋集的类编成为一种常态。”[20]256《文选》代表了以类选赋的滥觞,所以赋集的类编传统也一直得以延续,乃至到清代陈元龙编《历代赋汇》,依旧采用类编方式。而到吕祖谦编《宋文鉴》,采用的却是以体裁而非题材的分类方式,将所选赋划分为古赋和律赋两大类,虽不及诗体分类那般细致,但较类编无疑更为进步,反映出更为明晰的辨体意识。《宋文鉴》之后的赋集多数仍旧采取类编的方式,但其体类意识无疑较之前更为凸显,这在赋学批评著作如元人祝尧《古赋辩体》、清人陆葇《历朝赋格》等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四库总目提要》(集部)云:
其书(《古赋辩体》)自楚词以下,凡两汉、三国、六朝、唐、宋诸赋,每朝录取数篇,以辨其体格,凡八卷。[21]卷一百八十八
由此可见,祝尧已开始自觉地对赋体的源流正变进行专门探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鲜明的“祖骚宗汉”的赋体复古主张。陆葇《历代赋格》亦将赋格分为三大类,即骚体、散体、骈体(包含律体),呈现出较为自觉的辨体意识。
其次,《宋文鉴》选录了大量北宋赋名篇,涵盖逞辞大赋、骚体赋、散体文赋、律赋等各种体式,在囊括传统赋题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开拓,对扭转前代赋风起到了重要作用,并为后世北宋赋选提供了具有较高借鉴价值的范本,是宋赋经典化过程中的重要一环。翻阅当前通行的几部辞赋史,无论是马积高《赋史》,许结、郭维森合著《中国辞赋发展史》,还是刘培《两宋辞赋史》的北宋赋部分,都不难发现其重点介绍的赋家乃至赋作,均与《宋文鉴》选录情况存在高度重合。
最能体现宋赋特色的无疑是文赋,《宋文鉴》选录的欧阳修《秋声赋》、苏轼《后赤壁赋》无疑是北宋文赋最负盛名的代表作,即使后人对文赋这一文体颇有微词,也不得不承认欧、苏这两篇赋的出彩之处。元人祝尧《古赋辩体》即有语云:
今观《秋声》《赤壁》等赋, 以文视之, 诚非古今所及;若以赋论之, 恐坊雷大使舞剑, 终非本色。学者当以荆公、尹公、少游等语为法, 其曰“论体”“赋体”“传奇体”, 既皆非记之体, 则文体又果可为赋体乎?[13]卷八
祝尧虽是立足于赋体源流正变的角度,批评欧、苏文赋不合于正体,但另一方面他也承认欧、苏的文赋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若放置在更广义的“文”的范畴来看待,无疑是可独立名世的佳作。受欧阳修倡导的古文运动的影响,宋人的骚体赋创作亦别具特色。王安石、刘攽、刘敞、黄庭坚、晁补之等人都深于骚体赋的创作,且多有佳作流传,比如王安石《思归赋》《历山赋》,风格冲淡宁静,呈现出较为浓厚的诗化倾向,刘敞《离忧赋》《栟榈赋》、刘攽《不寐赋》则以骚体来说理,刘培认为刘氏兄弟的该类创作“反映了宋代骚体赋以理入情、以理节情的发展方向”[1]227。在北宋理学影响下兴起的哲理赋同样不可忽视,以王回《事君赋》《责难赋》《爱人赋》、周敦颐《拙赋》等为代表,其出现标志着北宋赋重说理、议论倾向发展到新的高度。而在传统的逞辞大赋领域,亦可看出宋人创作热情并不减退,反而有所增加,从侧面反映出宋代士人高度的文化自信,甚至出现了杨侃《皇畿赋》、周邦彦《汴都赋》、王仲旉《南都赋》等京都赋佳作。而作为科场文体的律赋创作虽然较唐代更趋于程式化,内容亦更趋于枯燥,但依旧出现了像范镇《长啸却胡骑赋》、苏轼《浊醪有妙理赋》、秦观《郭子仪单骑见虏赋》这样广受赞誉的名篇。以上论述所涉及的篇目,在各类辞赋史的北宋赋部分均成典范之作被屡屡提及。
最后,同时代的文章总集中,《宋文鉴》所选北宋赋无论是在数量还是质量方面无不占据压倒性的优势,对北宋赋整体面貌的呈现堪称最为全备,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建构了最早的北宋赋史。
当前通行的辞赋史都倾向于将北宋赋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北宋初期为宋赋的发轫期。这一时期赋家有从五代入宋的徐铉、梁周翰、夏侯嘉正等人,创作主要承袭晚唐五代骈俪赋风,其中,梁周翰《五凤楼赋》、夏侯嘉正《洞庭赋》为此期赋作代表;此期还有西昆体作家如张詠、杨亿、杨侃、钱惟演诸人,在赋作形式上依旧沿袭前代,但已呈现出不同于五代赋体的卑弱风格,别具雍容华贵的盛世气象,以张詠《声赋》、杨侃《皇畿赋》、钱惟演《春雪赋》为典型代表;还有开辟宋初辞赋新境界的王禹偁,开始在赋作中大量抒情、论政,《籍田赋》为其代表。北宋中期为辞赋新变期。这一时期赋家辈出,文人、学者、政治家、理学家等群体均有数量或质量较为可观的赋作流传,且无论是在体式还是风格方面,均呈现出多样化特征,宋赋面貌得以初步确立。这一时期赋的议论色彩更趋于强化,以范仲淹的《明堂赋》《金在熔赋》为代表;此外,此期宋赋的散文化、说理化倾向亦更为凸显,以欧阳修《秋声赋》、邵雍《洛阳怀古赋》为代表;梅尧臣、刘敞、刘攽、王安石、崔伯易、狄遵度等人也有佳作流传。北宋后期是宋赋成熟定型期。这一时期的赋家以苏轼及其周围的苏门文人群为代表,他们对赋境、赋艺多有开拓。这一时期赋的题材、风格更趋于多样,手法亦更臻于圆熟,比如,苏轼的《后赤壁赋》标志着文赋的成熟;苏轼《浊醪有妙理赋》、黄庭坚《煎茶赋》将士人日常生活引入赋域;苏辙《黄楼赋》、秦观《黄楼赋》、苏过《思子台赋》则反映出此期亭台楼阁赋的兴盛,进而体现出北宋士人喜“登高作赋”的高雅情趣;张耒《鸣鸡赋》《鸣蛙赋》、苏过《飓风赋》等均为此期涌现的佳作。而以上所列举的篇什均被选入《宋文鉴》,足以看出吕祖谦在选赋方面的杰出才能。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宋文鉴》的选赋大体上与北宋赋的发展历程相契合,其选所赋家在北宋具有相当的代表性,选录的赋也大多被视为北宋赋的经典在当前的各类辞赋史中屡屡出现。
《宋文鉴》的选赋一方面继承了《文选》重视赋体的传统,将赋列于首位,另一方面,它又打破了《文选》开创的赋的类编传统,尝试以体编次。吕祖谦在选赋时不仅能关注到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赋家,在注重题材的多样性,兼顾体式完备的同时,还能敏锐地选出最能代表宋赋特色的典范之作,并且能有意识地调和时下兴起的古律赋之争。《宋文鉴》选赋呈现的这些特点与当时科举考试大环境密切相关,宋代科考重赋故而吕祖谦给予了赋这一文体特别地关注;几度反复的经义与诗赋之争使得元祐赋的价值得以凸显,故而他大量选录元祐时期的优秀赋作;赋体发展到宋代各种体式均已趋于成熟,开始注重辨体与破体,为此《宋文鉴》首先区分了古赋和律赋,并且选录的赋作也多呈现出鲜明的破体倾向。《宋文鉴》古赋与律赋兼收且将古赋列于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元、明古律赋之争的倾向,带动了从重律赋到重古赋的转向;而选录大量北宋时期重要赋家的代表赋作又于无意间助推了北宋赋在后世的经典化进程;最后吕祖谦通过在选赋数量、体裁、题材、风格等方面的综合考量,建构了较为粗疏但与此同时亦是最早的北宋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