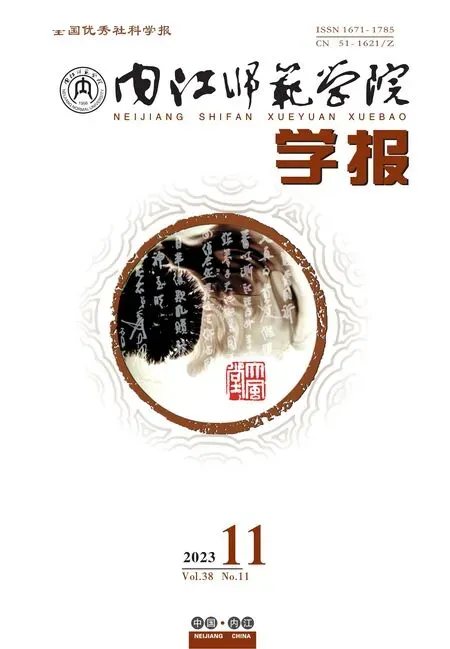近代汉语中的动源职事称谓
曾子涵, 陈练军
(闽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福建 漳州 363000)
动词转指可分为有标记转指和无标记转指。朱德熙强调,汉语里“凡是真正的名词化都有实在的形式标记”[1],姚振武进一步指出“汉语中有些谓词性成分不用加任何形式标记也可以名词化”[2-3],即无标记转指。当动词无标记转指施事时,职事称谓占有显著优势,由此引发了学者对职事类称谓的关注,如张博[4]、鞠彩萍[5]、马伟忠[6]等。不过,以往研究多基于现代的共时层面,对历时层面关照不足。本文以白维国等主编的《近代汉语词典》[7]为语料来源,从历时角度探讨动源职事称谓的结构、语义、义类优势等特征,考察其与现代汉语的异同。
张博将由从业或司事义动词直接转指施动者而衍生的称谓称之为动源职事称谓[4]。但与职事有关的称谓不仅包括由动词转指的施动者,也包括由动词转指的受动者。因此,本文将动源职事称谓定义为:由职事义动词直接转指为职事人员的称谓,且收集语料时排除以下几种情况:(1)属现代职事称谓而非近代职事称谓。一是相关词语与现代职事称谓为同形异义关系,如《近代汉语词典》中“编辑”的释义为:①组织编排(文字)。②组织编排(人员)。该释义显示“编辑”不仅没有发生动词向名词的转变,且与现代职业“编辑(对文字进行审评、整理和修改的文职工作者)”的含义不同。二是相关词语在近代汉语中仅表示人的身份,在现代汉语中才发展为职业称谓。如“主婚”指主持婚事的人,在封建社会中需依照宗法血缘关系的远近及尊卑长幼关系来决定,是存在于婚嫁礼仪文化中的一种身份。现代表示“主持婚事的人”的职业称谓不由动词“主婚”直接转指,需在后面附加词缀“-人”构成“主婚人”,是“主持”职业类别下的一个分支。(2)与同形动词意义无关的职事称谓。如名词“承受”是宋代监察地方的军政官职,而动词“承受”是指承袭或忍受,名词并非从动词义转指而来;动词“跳荡”是指跳跃、跳动,名词“跳荡”是指精锐的士兵,名动二义完全不同。(3)动词名词化词缀参与构词的职事称谓。这类词缀是构造职事称谓的常用语素,由动词名词化而来,不具备动词性质。例如动词“差”指差遣,后演变为名词,指官府差遣的官吏,因构词能力强逐渐变为表示官吏类职事称谓的构词语素。由词素“差”直接构造的“官差”“差尉”等职事称谓没有相应的动词来源,不是动源职事称谓。(4)不由动词直接转指,而是由其他词缩略而成的职事称谓。如动词“宣赞”指宣唱赞礼,表示职事称谓的“宣赞”不是由“宣唱赞礼”义动词转指而来,而是“宣赞舍人”的省称;动词“巡按”指巡行按察,名词“巡按”是由“巡按御史”缩略而成。(5)动词性语素参与构词但无法考察是否为动词来源的职事称谓。如“过卖”在词典中的唯一义项是指酒楼食店中的伙计,虽有动词性语素“过”和“卖”,但无法判定其成词时是约定俗成、固化而来还是由动词转指而来。
一、动源职事称谓的结构类型
经统计,《近代汉语词典》中共有104个动源职事称谓,其中以宋、明时期的数量居多①,具体词目见表1。
近代动源职事称谓除各时代数量分布不均之外,其构词结构类型的数量也有历时变化,具体情况见表2。

表1 《近代汉语词典》动源职事称谓的各时代数量分布

表2 《近代汉语词典》动源职事称谓的结构类型
表2显示,近代动源职事称谓来源有并列、动宾、状中、主谓、动补五种基本结构。其中并列式和动宾式具有较明显的转指优势,但在各朝代分布并不完全一致。就两者比较而言,除明代以外,各时期并列式的职事词数量要多于动宾式②。除此之外,本文将宋代最后一类列为“其他”,一是存在单音节词,即“哨”;二是从语义和语法上难以归入上述基本结构类型,如“小唱”动词指唱小曲,转指为名词指唱小曲的人,其动源形式的结构类型应为宾动式。
在所有结构类型中,动词在“施事—动作—受事”的典型语义框架下转指的是与动作行为相关、具有凸显性的论元,即施事和受事。动源职事称谓在施事转指上表现出明显倾向,因职事词是反映社会关系中特定行业、职业及身份的名称,具有表述功能和指称作用,其指称对象为人。施事是动作发出的主体和陈述的对象,两者在此基础上融合和统一。另一方面,职事词的动作行为一般是由承担该职业事务的人主动发出,而受事是受动作支配的对象,因此动词转指受事较少,在表1中仅有“差人”“雇工”“部卒”3个职事词。在职业中存在上下级关系的社会语境下,这类词在结构上表现为动宾结构,动词表示下级对上级所支配的行为,宾语表示上级所支配的对象,是动作行为的承受者。
二、动源职事称谓的语义和语法特征
近代汉语动源职事称谓的内部语义和语法特征存在历时的变化:一是指称形式不同,即“异形同指”;二是动词转指名词后,内部的结构和意义不同,即“同形异构”。
(一)异形同指
“异形同指”是指形式不同而意义相同或相近的一组称谓词,即反映“一义多词”现象。一是不同时代、不同形式表达相近含义,如唐代“步从”“参从”、宋代“拥从”、元代“跟随”、明代“参随”都是表示随行的人员,且都包含“随行”义动词性词根。不同时期使用不同形式表达随行人员的称谓反映了词汇的发展和变迁:从唐至宋,都含有动词性语素“从”,从元至明,则含有动词性语素“随”。二是同一时代相同含义用不同形式来表达,如元代用于指称掌管日常事务的仆人的职事称谓有“管家”“管事”“掌家”“勾管”等,动词性词根“管”“掌”都有管理、安排事物的意义。
(二)同形异构
“同形异构”是指动词转为名词时,其构词语素没有任何不同,但语素间的内部结构和语义重心发生了变化。如“差人”为动宾结构,动词义是指差遣人员;“雇工”为动宾结构,动词义是指雇佣工人;“部卒”为动宾结构,动词义是指统领军卒;“配军”是中补结构,动词义是指发配到军队。当上述动词名词化后,构词语素的关系都变为定中结构,动词性词根为限定语素。“差人”“雇工”“部卒”“配军”分别指向被差遣做事的人、被雇佣的工人、被统领的军卒、被发配的军卒。动词转名词后语义上的变化是,动作行为的发出者被弱化,在逻辑上不用补出确切的施事;同时受事得到强调,词所表示的被动含义更加凸显。
“同形异构”结构转换得以实现的前提是,两个构词语素一般由一个动词性语素和一个名词性语素构成,这样才能使转换后的语素内部关系存在定中式的可能。其次,转指对象“人”“工”“卒”“军”作为语素,在语言使用中逐渐演变为表征身份的类词缀,且常居于词尾,例如:
-人:舆人、僧人、矢人、梢人、炊人、车人、探人、礼人
-工:画工、花工、笔工、采工、土工、篦工、火工、伶工
-卒:递卒、探卒、塘卒、解卒、禁卒、监卒、轿卒、铺卒
-军:抚军、号军、巡军、解军、亲军、炮军、牌军、探军
这类语素在同一义项上的构词能力较强,且易为语言使用者所理解和接受,使得语义重心从关注动性成分如何影响受事,到关注受事在动性成分影响下有何属性;从关注表动作行为的动词性词根,到关注表类属身份的名词性词根中得到转移。
三、动源职事称谓转指的义类优势及语义限制
上文指出近代汉语动源职事称谓从语义和语法特征来看,存在“异形同指”和“同形异构”两种情况。但动源职事称谓在语义上的分布是否具有倾向性?动词无标记转指名词时有无语义限制?这些问题还需进一步探讨。
(一)义类优势
张博[4]的研究表明,现代汉语动源职事称谓的义类优势序列为特异职事>普通职事、高级职事>低级职事。本文根据《近代汉语词典》研究发现,近代汉语动源职事称谓的义类优势序列与之类似,但不完全相同,具体情况见表3。

表3 《近代汉语词典》动源职事称谓数量分布
观察动源职事称谓在各类职事中的数量分布,可以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展开。从纵向上观察到的是近代动源职事称谓的总体特征:处于行政体系、官僚体制下的职事称谓(官、吏)在总体动源职事称谓中所占比重较高,分别为33.7%(“官”类)和17.3%(“吏”类)。职事称谓数量较少、占比总数不足5%的职业多分布于市井生活中,如“厨师”(1%)“术士”(1%)“工匠”(1.9%)“艺人”(3.8%)。从横向上看,各时代的“官”类职事称谓与其他普通职事称谓相比,更占据优势地位。据此,可以根据横、纵分布的职事称谓特征得出近代动源职事称谓衍生的义类优势序列,即官僚职事>普通职事。这与现代汉语“身份类”动源职事称谓的特征具有一定相似性,即动源职事称谓的多少与“身份”社会地位的高低成正比[4]。封建社会强调等级制度,官员的社会地位通过等级制度规定,在整个社会体系中居于高位。因此,官员相较于其他职业,其社会地位更高,动源职事称谓的数量也就越多。
(二)语义限制
1.名词的语义限制
动宾式结构发生转指时,宾语既可以是抽象名词,也可以是具体名词。王冬梅[8]指出,现代汉语中作宾语的名词性成分越具体,动宾式越不容易转指施事,反之,作宾语的名词性成分越抽象,动宾式越容易转指施事。近代动源职事称谓中宾语为抽象名词的有“逻事、抄事、供事、管事、当事”,共计5个;宾语为具体名词的有“参军、当道、当家、射生、部卒、察官、贡声、呵殿、监酒、量酒、领班、押牢、该房、提牢、行财、行厨、押狱、拔禾徕、承差、差人、抽分、督学、管家、监场、监令、监试、写字、赞礼、掌家、雇工、盘头”,共计31个。
上述动宾式称谓中,作宾语的名词性成分只有“事”较抽象,相关职事称谓有“逻事、抄事、供事、管事、当事”,其他作宾语的名词性成分都很具体。这说明在近代动宾式职事称谓中,作宾语的名词性成分越具体,就越具有转指优势;反之,作宾语的名词性成分越抽象,转为职事称谓越受限。这一现象,与王文得出的结论是相左的。
2.动词的语义限制
《近代汉语词典》中动源职事称谓动词的语义特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动词所表示的动作行为若限定于特定职业,更易直接转为职事称谓。例如“赶趁、贡声、小唱、舌辩”都限于艺人行业。官职类称谓“写字”虽可以指书写文字的日常行为,但是作为近代职事词,其特指的是明代职司抄写的低级官员,而非泛指一般的写字动作。第二,不及物动词或弱及物动词较及物动词更具转指优势。动源职事称谓的动词,大多为不及物动词,如表“军士、士兵”一类的职事称谓中有不及物动词“射生、游奕、呵卫、部卒、配军”、弱及物动词④“哨(意为巡逻)、部署(意为管辖)”。第三,及物动词所搭配的宾语成分在语义上较为有限,则可以发生无标记转指。如“肩挑”“行贩”的对象一般只是货物、商品,“帅领”的对象基本限于军队,动词所搭配的宾语成分义类单一。
在归纳上述易发生转指的动词特征基础上,可以进一步概括近代汉语动词转指职事称谓的语义限制,即兼表非职事义的动词和受事义类丰富的动词发生无标记转指时会受限,这与张博[4]在考察现代汉语动源职事称谓所得出的语义限制是一致的。
四、结语
动词无标记转指是汉语中的一种普遍的语法现象,且动词转指施事时大部分都表示职事称谓。本文通过考察《近代汉语词典》中的动源职事称谓,发现近代汉语动源职事称谓与现代汉语动源职事称谓的特征具有一致性:在结构类型方面,动词转指在动宾式和并列式中更具转指优势;在义类优势序列方面,表现为高级职事>低级职事;在转指动词的语义限制方面,兼表非职事义的动词和受事义类丰富的动词发生无标记转指时会受到限制。同时,近代汉语动源职事称谓与现代汉语动源职事称谓又存在差异性:一是近代动源职事称谓有少量转指受事的情况。二是当动宾式职事称谓发生转指时,近代汉语中作宾语的名词性成分越具体,就越具有转指优势;现代汉语中作宾语的名词性成分越具体,则越受到转指限制。
注释:
① 《近代汉语词典》是一部反映近代汉语词汇系统面貌及其历时演变的词典,其收词尽可能选取文献中最早的用例,但后代沿用的情况不再标注说明。本文收集的语料虽以时代分布的形式呈现,但并不能反映词汇的使用频率及历代沿用的情况。从汉语词汇复音化的历时发展来看,唐代为初步形成阶段,复合词的结构类型较少;宋、明时期为发展的高峰阶段,用例呈现大幅增长;元代用例较少,或许与时代的特殊性有关(历史周期较短,汉文语料偏少);至清代中叶,语言内部差异并不显著,词汇的演变较为平缓,因而用例也较少。
② 明代并列式职事词虽少于动宾式,但仅相差5例。这可能与所选语料及词典收词有关,其具体原因不明。
③ 本文的普通职事还包括:密探(间探)、僧人(住持)、厨师(行厨)、农民(拔禾徕)、术士(克择),由于用例少,均只有1例(每类后面用括号加注),故表3不单独列出。
④ 弱及物动词不能带真宾语,有时可以带准宾语,如处所宾语、存现宾语等。
——针对对外汉语语素教学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