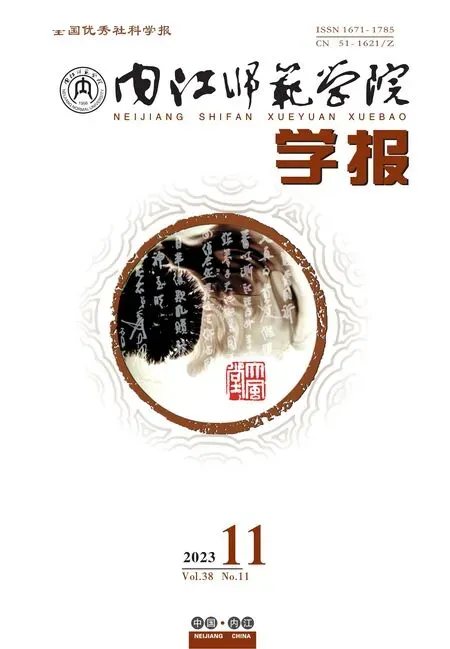清末至民国成都城市环境卫生管理及成效
黄文记, 李兆田, 曾鑫可
(1.内江师范学院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四川 内江 641100;2.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政府宝圣湖街道办事处应急办, 重庆 401120)
随着社会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国内史学界对公共卫生史的关注与研究不断升温①。然而,目前从环境卫生的角度探讨城市环境卫生管理的研究不足②,特别是对民国时期城市环境卫生管理的研究较少③。公共卫生是社会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环境卫生管理水平直接决定了一个城市的卫生事业的发展程度。成都历史悠久,卫生事业源远流长。近代以来,成都的环境卫生事业整体向前推进,有些方面还走在全国的前列。本文首次全面梳理近代成都城市环境卫生管理机构的历史,阐述成都市近代环境卫生管理的基本运行状况。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拓展城市卫生管理史研究的空间,推动近代卫生管理研究的深入开展。
一、清末至民国成都卫生管理机构的演进
(一)清末民初:警察机构兼管
清朝,成都卫生行政机构称“医学”。医官的主要职责是管理医疗诉讼,诊断、治疗工作人员和囚犯的疾病,检查尸体等。瘟疫流行期间,也需“劝募施救”。此外,医官还要出巡各地,考核医药真伪,审查医生[1]23。
鸦片战争后,清朝政治日益腐败,医疗管理机构和制度逐渐松懈,地方医学陷入衰落状态,医政事宜多无人过问。清末“新政”,巡警部警保司下设卫生科,卫生行政工作交由警保司管理。1909年,四川通省巡警道成立,下设警务公所。公所内设总务、行政、司法、卫生4科。卫生科“掌卫生警察,凡清道,防疫,检查食物,屠宰,考验医务医科及官立医院各事”。1910年,卫生科下又增设检查股和医务股。检查股掌理“关于省垣(指成都,华阳两县城厢)人物之有伤生理一切防杜事;关于省垣清洁街道,排除积污,统辖清洁队事;关于考核各州县有关前项事”;医务股掌理“关于省垣警务上之诊断健康及附设之病院一切疗察事;关于研究义务改良及考核医药事”。“成都华阳两县城厢系省区,所有关于巡警范围内一切卫生事项,均由省区巡警办。”④1909年至1910年,警务公所卫生科曾对成都街巷水井进行了1次检查,井水被分为“可饮”“不可饮”“制后可饮”3类,并钉牌标明,让汲水者周知。另对医生进行考试、考核,合格者准挂牌行医。还在成都城厢的六总区各设官办牛痘局1所,为儿童接种痘苗,预防天花。
辛亥革命后,四川军阀长期混战,成都大体延续晚清新政时期由警察兼管卫生事务的格局。
(二)民国前期:纳入省市政府系统
清末民初由警察兼理成都卫生事务的格局,到成都市政公所成立前后开始逐渐改变。1922年3月,在合并成都、华阳两县城区的基础上,成都市政公所成立。公所内设卫生科,掌理“清洁市街,经营市立医院,管理屠宰场,浴场,监督私立医院及处理有关防疫事项等”⑤。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在内政部下设置卫生司,掌管全国医政。1928年改为卫生部,内分总务、医政、保健、防疫及统计五司,分管各项卫生事宜。另设中央卫生委员会,并公布了《卫生部组织法》。至此,中央卫生体制建立。此时的四川,正处于“防区制时代”,军阀混战,并不在南京国民政府的实际控制之中,卫生管理格局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1928年,成都市政公所改组为成都市政府,初期设有卫生科,后卫生科被裁撤,又在民政科下设卫生股,处理日常卫生行政事务。同年,四川省会警察局改组为成都市公安局,隶属成都市政府,开始设有卫生科,不久又被裁撤,公共卫生业务并入总务科[2]。从此,四川的卫生管理工作正式纳入到省市政府系统。
1933年,成都市公安局改为省会公安局,隶属省政府。1934年,在局内设卫生科,科下又设保健股和防疫股,掌理“稽察清洁街道,沟渠,公私厕所,管理屠宰场和浴场,开展卫生宣传暨防治传染病,检查及取缔食物饮料,取缔剧毒药物以及管理传染病医院,疯院,狂病院,施药检诊,种痘,救治时疫等”⑥。
1936年1月,四川省会公安局改为四川省会警察局,下设卫生科。卫生科的职责是职掌省会成都市的保健、医药、防疫等事项。诸如居民生死调查统计,市区街道的清洁扫除及水井、厕所之管理等,均由该科负责⑦。
1936年12月26日,国民政府内政部公布的《省会警察局组织暂行规程》规定:各省会警察局不设卫生科。省会警察局向省政府提出“惟以省会(成都)日趋繁荣,人口已达五十余万,市府又无相当之卫生行政组织,恳请核准卫生科仍旧设置”⑧。省政府批准并报经内政部批复同意,四川省会警察局卫生科才保留下来。
这一时期,成都卫生行政管理的最大特点就是成都卫生事务由警察系统与省市政府系统共同管理。
(三)抗日战争期间:建立专业管理机构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由南京迁往重庆,四川成为国民政府统治的中心地区。同时,沦陷区的一些医疗单位及卫生人员迁入四川。出于社会及军事医疗的需要,1938年5月2日,四川省政府民政厅内成立“四川省卫生药员会”,统筹全川卫生事宜。同年,成都市政府下设卫生科,职掌关于公共卫生之计划及推进。
1939年,为“应付空袭救护燃眉之急”,四川省政府于5月16日成立四川省卫生实验处,处长陈志潜⑨。处内设秘书室、第一科、第二科、统计室、技术室、会计室六个科室。省卫生实验处同时直接负责成都市卫生行政组织建设、防空救护、霍乱防治等工作。
四川省卫生实验处成立后,成都的卫生事务实际上由省会警察局卫生科、省卫生实验处、市政府卫生科三方管理,事不专属,有相互掣肘之嫌。1941年,陈志潜处长同成都市政府、省会警察局协商,决定由三方共同设置成都市卫生事务所。1941年6月1日,成都市卫生事务所正式成立,所内设事务室、环境卫生室、卫生宣传室,另设清洁大队及1个诊疗所。
1941年冬,经省卫生实验所提议,报省政府决定,自1941年起,将卫生所划归成都市领导管理。1942年4月,王季槐接任卫生所所长,所内人员扩充至33人,机构重新调整,设置了环境卫生科(下设稽查队,队员8人)、防疫保健科、总务科。在此期间,市卫生事务所及其附属部门大多能够执行分配给它们的任务。
1944年,霍乱大流行,为迅速根除霍乱,提高工作效率,成都市政府报请省政府批准,8月份在市政府内部成立卫生科。凡与卫生行政有关事项,由卫生科办理,卫生技术和卫生防疫工作由卫生事务所负责[3]。实际上将卫生行政管理和具体的卫生事务分开。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发动内战,成都卫生行政机构建设停滞萎缩。1948年4月15日,成都市因财政极度困难,撤销卫生科,人事业务并入卫生事务所。同时,卫生事务所迁至新南门外龙江路市立医院办公,导致门诊工作停顿。此外,资金极其有限,货币贬值加剧,员工缩减,工作难以推进[3]。
二、环境卫生的管理
环境卫生管理是卫生行政管理部门的重要职责之一。成都的环境卫生,清末以前官府并未专设机构管理。街道、公共场所的环境卫生常由居民自行负责,环卫公共设施的设置等,常由居民自行承担。清末至民国,成都逐渐建立了环境卫生管理机构,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组建了一支清道夫队伍,持续开展街面的清洁与公共卫生管理。
(一)建立管理机构
1902年,四川建立警察总局,周孝怀提出警务施政方针为“采外、酌中、师古、保安、正俗、卫生”。其中的“卫生”即包括环境卫生工作。总局设卫生科,负责管理成都市卫生事务。1908年,卫生科更名为第四科,并设立卫生警察,检查成都的清洁情况,并聘请街道清洁工清除垃圾和污垢[4]。
民国初年,由于四川多年军阀战乱,成都的清洁工作倍受阻挠,市容脏乱不堪。1921年,市政公所设立后,公所开始注重街道卫生治理。每当炎热夏天,派令沿街住户给街道洒水降尘。市政公所在社会局设卫生科督管清洁卫生工作后,又制订各种清洁规则。1922年,市政公所设立第二科(次年更名卫生科),负责清洁卫生事务。1924年,市政公所规定卫生科职责为监督市街、屠场、浴室、餐馆、茶园清洁卫生。次年5月,市政公所委托载重车行成立总渣行,市各区设分渣行,负责组织清洁队清运垃圾。
1941年,成都市卫生事务所成立,内设环境卫生科,职掌市面清洁设计与清洁管理,饮食摊铺、公厕、公共场所、服务店馆、牲畜屠宰场、售卖场、工厂、学校等的环境卫生设计、监督、管理;负责卫生稽查员的监督管理与考核;指导警局办理垃圾除运、处理及其他有关环境卫生事宜。20世纪40年代,省卫生实验处还设有省环境卫生队,兼管成都市各种重要清洁卫生工程的设计和施工修建。
20世纪30年代中期,市政府推行以“简单朴素、整齐清洁”为内容的新生活运动[5]。除了政府设有清洁卫生机构外,历年政府与民间还共同组建一些临时管理或宣传清洁卫生的机构和组织。1933年,市政府、警察局会同各界人士组织“四川省会市民清洁运动委员会”。1938年,警察局又会同各界人士共同组成“成都市清洁检查委员会”。1939年,市政府机关组织卫生指导队,分为36个分队,分区倡导卫生活动。20世纪40年代中期,除在春季开展清洁运动外,在夏、秋季也各举办一次清洁卫生宣传周活动。由省市机关派员组成卫生检查队(或卫生指导队),督促检查清洁,开展清洁竞赛活动。如1947年夏令卫生运动竞赛检查中,获最优清洁奖者40余户,最劣受惩罚者886户,第二年检查,最劣者降为269户。卫生检查涉及街面及室内外环境卫生等状况。
(二)制定政策法规
1915年,警察署制定“违警罚法”,对妨碍清洁卫生的行为规定处罚办法。1924-1929年市政公所卫生科监管全市清洁,相继颁布一些清洁规则,并规定对清洁工作的检查办法。如《清洁队暂行章程》中规定清洁队每组每日应到该管区警局处登记核查工作情况,并明确奖惩办法。又如1926年《市民街面清洁规则》中规定:各街清除垃圾等脏物应由街正(政府委派的街巷管理负责人)稽查,如有乱抛洒脏水、脏物、粪尿,不受街正和各住户监督者,当拿送该管区警署处罚。1936年省、市政府制定《整理本市市容办法大纲》,并开展清洁卫生运动。
为加强环境卫生管理,20世纪40年代初,市卫生事务所修订了厕所、街道清洁维护办法。1942年市卫生事务所制定《卫生稽查员服务规则》,规定:卫生稽查员负责稽查全市清洁卫生,对饮食、户外环境、公共场所、商摊等进行卫生检查、督促、改造卫生情况,每日稽查情况填表汇报。从1942年起,市政府连续颁发《改善成都市市容交通秩序公共卫生取缔办法》《夏令卫生运动清洁竞赛暂行办法》《成都市清洁大扫除检查办法》。
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国民政府各机关相继迁离四川,新生活运动时期建立的定期大扫除以及军、警、宪联合监督检查,执行处罚等制度,逐渐中断或流于形式。由于卫生活动日益松懈,居民的不良习惯开始出现,各部门的监督管理工作日益懈怠,导致各街道的清洁度很差。城区的大部分街道肮脏不堪,路边的排水沟经常被垃圾堵塞,尤其是公共厕所,破旧、肮脏、难闻。垃圾堆积在厕所外,粪便和尿液溢出厕所。居民们经常把脏水泼在街上,把死老鼠扔在街上,把衣服挂在街边的横杠上,随地大小便。迎曦街整条街都积满了污水,又脏又臭。夏天,蚊子和苍蝇聚集在一起,没有人打扫街道。鸡和鸭在街上跑来跑去[6]。再如,城隍巷屠宰场的血水、污水遍溢街道,旁边臭水塘边空地上垃圾长年堆积如山[7]。其中以皇城坝一侧的“煤山”最为突出,堪称四川城市中的“垃圾山”之最[8]。
(三)组建清洁队伍
清末,四川警察局就开始雇用百余名杂役作为清道夫。1902年,警察机构开始将清洁卫生纳入其管理范畴。警察各分署启用百余名清道夫挑竹筐或使用“鸡公车”,清除城区街道垃圾,清洁夫的工作内容主要包括将街面及厕所内外的渣滓、死鼠搬运出城,街面洒水等。专业环卫工作,从此开端。清道夫大多来源于破产农民及城市贫民。民国时期,清道夫数量变化不大,长期维持在一百到二百人。此外,市卫生事务所和省环境卫生队,还有清洁卫生管理和设计人员数名。这一时期的清道夫,几乎全是文盲,只有市卫生事务所和省环境卫生队中个别担任高级技师工作的人,出自高等院校或为留学人员。
清道夫社会地位低下,穿着形同囚犯的黑底白字号衣工作。稍有疏忽,监管警察非打即骂。轻者用木板打手心,谓之吃“红烧鲢鱼”,重者罚作苦役[9]463-464。1937年,警署强行裁减清道夫定员三分之一。为了生活,被减人员并未离开警所,形成七八个人工作只能领三四个人的薪饷的局面,加上当时物价暴涨,清道夫的生活难以维持。迫于生计,清道夫联合举行罢工。同年4月,二百余名清道夫在“财神会”和“土地会”张先贵、蓝玉山、李志高等人的带领下展开罢工。罢工持续数天,城内大街小巷的垃圾因为无人清运,堆积如山。东门一带最为严重[10]。警察局同东门商会和“舵把子”协商解决堆放垃圾地皮的纠纷,并强令清道夫复工,在惩处违法者的同时市政府恢复了各警署原有清道夫名额,但薪饷数目照旧。罢工之事,不了了之。
警察局规定的清道夫每天的劳动量很大,而劳动条件始终不见改善。清洁工人经常感染疾病或中毒,患吐血病的不在少数。即便如此,清道夫的收入仍相当低下而且不固定。“其运渣车辆由清洁夫自备,渣筐由社会局发给。每六个月更换一次”,“月薪仅4元5角”。原因主要在于经费不足,民国初年,警察厅的清洁费一部分由各街居民筹措,称为“公益费”。1915年,警察厅开始征收“清洁费”,用作警察局购买清洁药品。1936年7月,市政府又改征“清洁捐”,但市政府清洁费支出不断增加,主要有:(1)日常管理费用与清道夫的薪饷。以 1925年的费用与1929年的费用相比,前者每年需 13 544元,后者增加 37%。(2)增补漏支项目。如官办渣滓场与渣滓船两项,每年共需支出 6 590元。(3)其他费用:如清洁运动会开支,洒水工作费用。经费始终处于紧张状态。清洁夫常被驻军“拉壮丁”,为部队从事义务劳动。据三分所呈称,“1932年6月16日午前9点,署员至状元街、青石桥南街见渣滓尚有堆积,未扫运净尽,转饬空长督饬清洁夫立即扫运,复于午前12点40分经过上述各街,渣滓堆积如故,派警员赴东门、南门觅清洁夫据去警称本日午前8点后,城口发现不知何部军人,强拉清洁夫而去”。1932年7月17日,四分所清洁夫被忠烈祠内驻军拉去推运河沙。1933年4月6日、7日,二分所清洁夫在街推运渣滓,被24军司令部拉去4人推运河沙,每晨7点至午后6点始返所。1935年10月21日,秋季清洁运动连日举行,异常整洁。逐日清洁夫各处洒扫,推运渣滓,不遗余力。25日清洁夫四名推运至通惠门,被特务团一并拉入该团,启泥填坑及洒扫一切,日夜不放,以致推行清洁运动停止工作。
(四)开展街面清洁
1.制定清洁规则
晚清时期,成都居民以街心为界,每天自行打扫门前,进行路边清洁[11]247。1902年,警务部门开始雇用百余名清洁夫收运垃圾,并负责城区内的空场坝或公共场所清扫。民初,四川战乱频繁,成都警务部门对环境卫生管理不力,沿街垃圾成堆,市容脏乱。1926年,市政公所颁布《成都市市民街面清洁规则》,规定居民除自扫门前街道外,还有责任整掏房檐石阶下污水沟和劝告行人不抛脏物。1928年,市政府重颁《成都市市街清洁规则》,规定早晨7时前为扫街时间,街巷、墙角有垃圾的,由居住在两旁的住户清扫,还令兽力车车夫带撮箕扫帚随车打扫畜粪。同年,成都市公安局为加强城市卫生管理,颁布《污物扫除条例施行细则》,在成都市政府与市公安局的共同努力下,城区街道卫生面貌自此开始有所改变。
2.开展卫生运动
自1929年开始,市政府在每年四、五月,经常举行清洁卫生运动会数日,邀各界人士参加,进行各种卫生宣传活动,会后由社会局清洁视察员、警察局卫生督察员、警卫队员等举帚游行,清道夫推渣车随行,巡回各街,号召、督促市民大扫除。1934年,省会警察局制定《四川省会清洁运动大会计划大纲》,积极推动卫生运动。1936年,四川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市政府、省会警察局等推行“新生活运动”,开展以“简单朴素、整齐清洁”为内容的移风易俗活动。同年9月,省民政厅、市政府、警察局及警备部、宪兵等机关负责人商讨整顿市容办法[12],通过《整顿市容办法大纲》,主要内容包括:禁止乱扔破布和标语,禁止在路上吸烟、吃东西、吐痰,禁止随地大小便,禁止乱扔垃圾、乱溅污水,禁止在街上晒衣服,需要随时清洁和安装门窗等[13]。以上各项由军、宪、警三机关派小组巡逻,随时负责监督纠正。运动初期宣传热烈,执行严格,如有随地便溺者,则罚其跪地,后来执行逐渐松弛。
3.街面洒水冲洗
街道清洁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街面的洒水、冲洗。市政公所成立前,成都没有专门人员负责对街道洒水、冲洗。1924年,城市街道扩建。在夏季,市政府命令扶贫工厂的学徒和工人使用木制水车在一些街道上洒水以减少灰尘。第二年,由于水车损坏,洒水停止了。1928年,市政府规定街道居民在清扫街道时要洒水。第二年,社会局定制了数百个浇壶,卖给临街居民洒水。1932年春,青羊宫劝业场开馆,通往劝业场的路上,每天尘土飞扬。从当年3月到9月底,市政府要求清洁工人每天上午10点和下午2点在重点路段洒水。20世纪30年代初,城区车辆数量逐渐增多,水壶洒街已不能满足降尘要求。1935年,警察局与航空汽车检查处协商,向市内有车的车主和单位购买一到两辆车,用于街道巡逻洒水。但由于资金不足,最终改为购买木制水车,由清洁工或其他人员轮流推着水车洒水。警察局还命令街道设置“太平缸”和水桶,里面的水不仅可以作为消防用水,还可以作为洒街用水。1937年夏令时节,“空气干燥,致扬尘蔽天,且劝业会即将开幕”,市政府令公安局责成各署所清洁夫役自3月1日至9月底,在每日扫除渣滓后于10点起,各街洒水一次,至午后两点再洒水一次,所有劝业会期间,南门及通惠门至青羊宫之马路尤需多洒,避免尘土飞扬,妨碍卫生。1938年又陆续增加木水车,把城区街道划分为76个段面,每段配备1辆洒水车和3名夫役洒水。但是,由于每年木水车损坏严重,且无专款修理和添置,各警署又监管不严,致使洒水办法不能持续实施。
三、厕所与粪便治理
(一)管理机构
如前所述,清末至民国成都建立了卫生管理机构,这些官方机构具有对厕所、粪业管理的职责。除此之外,民间还设有粪肥业行业组织。1912年9月,粪商为保护自身经济利益,在华阳县政府倡导下,集合九十余家同行联合成立“肥料培根会”,隶属四川省农会。肥料培根会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逐渐被肥料同业公会取代。1930年,成都近百家粪商以民间“财神会”“土地会”为基础,自发成立新的行业组织——粪便业同业公会。入会时担粪工人须交1元扁担费,粪商或厕主交帮底费三斗米。20世纪30年代,成都地区因军阀混战,粪商所雇运粪工人常被拉去充当军械运夫。停战后,粪便市场极其萧条,加上捐税太重,粪商时有破产,粪便业公会日趋衰落[9]320。
(二)经费来源
民国初年,警察厅的清洁费来源及数额不固定。1915年,警察厅以管理厕所和粪便为名,开始征收“清洁费”,清洁费用作警察局购置清洁药品。市政公所成立后,清洁费改由公所卫生科筹划。清洁费分经常收入与临时收入。经常收入包括:1.税捐类。粪商粪价捐,由粪商负担,甲等每厕每月1元,乙等每月8角,丙等每月6角,全市每月共收银800元;厕主粪价捐,由厕主负担,其税率为租金的百分之二十,每月共收银500元。2.证照工本费类。运粪证费每本征收1元,每月收银一百七十余元;其他费,如卫生营业执照费、运粪尿人力车牌照费、车夫执照费等。临时收入包括各种违章罚金等。20世纪20年代后期,市政府将各种清洁费合并称“毛厕捐”。1929年,为弥补卫生行政费开支的不足,市政府提高毛厕捐征收标准,按照市财政局《征收毛厕捐规则》,甲等2元,乙等1.5元,丙等1元,由粪商按月缴纳。除毛厕捐外,市政府还增开有其他新捐种,如厕所号牌捐等。1933年,仅粪商缴纳的各种捐款就超过1 700元。由于杂捐重叠,1936年7月,市政府又将各种捐综合改称“清洁捐”。20世纪30年代后期起,市政府清洁费支出不断增加,增加的项目有改建公厕和粪坑方面的开支等。如1937年,省政府拨款2 700余元作为市府迁移成都北门、南门外公路旁的大、小粪坑的费用,但粪池未见搬动。这些有关公共卫生设施的修建其实徒增支出,并未见公卫设施有何改变。
(三)治理措施
1.改良厕所的努力
成都居民旧时多用马桶作厕所,居民院落中较少设置公用厕所。公厕往往沿街夹于店铺之间修造,或在街道空坝的角落设置。民国初期,城区有街道公厕一千余座,分布不均匀,大部分属私人财产且从不设置女厕所,只在每年逢青羊宫花会时,在宫院内设置临时女厕数处,每厕派一中年妇女看守,备有洗手盆,如厕者须交铜币二百文[14]369。由于当时厕所建筑简陋,或以茅草盖顶,以竹笆为墙,粪坑为土坑,上搭木板作蹲位,经常因管理不善,而破烂脏臭不堪。
1928年,市政府规定改造的厕所图样(设有女厕),这些公厕,全是旱厕,一般间深(长)6米,宽2米;大的间深(长)10米,宽2.6米。1933年,市政府令警察局参照上海或日本式样设计厕所图样,以作为督促改造公、私厕所之用。1934年春夏之交,四川省会警察局令组织公厕工程队从事厕所的改良。工程队共8组,每组派员率警士1人,泥工2人,犯工4人(犯工是被拘留的罪犯),依照规定模式改造街道公厕。厕所的入口开留巷道,地面筑三合土,用砖造尿槽,隔扇置木门。泥工包定每个厕所给6元(银元)工资,监工委员、警士及帮工罪犯均不另给工资,罪犯食费每日由厕主或粪商津贴银洋1角,所需材料及其他维修费均以厕主八成、警察局两成分摊计算。警察局所需修厕费用从各街道居民处筹集。此外,也有厕主粪商自行改良厕所的。1940年底至1941初,市府调查城区大小街道公厕1 300-1 400座,限令将其中在主要街道旁的193座公厕改作铺房。其余各小街巷的公厕必须按照市政府要求的式样改良。一般厕所地基面积留足近40平方米,每厕所改建费大约需要法币5 000元。改良厕所一事,厕主事实上大都没有遵行,致使市政府一再申令。
2.封禁与启封厕所
1933年,市公安局颁布厕所取缔暂行规则以加强厕所管理。规则规定:第一,隔板、踏板应随修随补,不得任其破坏朽腐,并应每日洗刷洁净,自阳历4月1日起至9月底,按日以生石灰倾入粪池尿坑内;第二,厕所地下砖、泥水湿处,每日应以生石灰撒布;第三,厕所内不得囤积垃圾、瓦砾、余泥及各种不洁废物;第四,厕所内蛛网须随时扫除,内外墙壁不得标贴字纸;第五,各厕临街墙壁应用砖修,厕门须加安弹簧门,使能自关严密,免臭气外溢。
同时,市公安局对不符合卫生条件的厕所严加封禁。如3署8分所辖内祠堂街第20号周和兴有厕所一间,因其污秽不堪,臭气熏蒸被市公安局取缔整顿。少城仁厚街口一厕所坐东向西,“每日容纳各住户大小便几有外溢之势,兼之早晚妇女携便桶者从集期间,甚于观瞻有碍。该厕所有地当西晒,自尤奇臭无异常,有碍卫生,行人莫不掩鼻而过,为顾虑街户公共卫生起见遂将该厕所查封”。外东珠市街第1158号厕所,因不符卫生规定而被查封。五福街609号厕所因建筑不合,妨碍卫生被查封。董瓦寺街517号因污积不良空气,妨碍卫生被查封。长顺街三道街口第559号茅厕因狭小污积被查封。石灰上街640号,石灰下街650号厕所因夏季时疫流行,有碍卫生被查封。金家坝街603号茅厕因臭气外溢不合卫生被查封。陕西街乔公馆侧厕所接近公井,污积不堪被查封。
厕所被查封后,厕主大多呈请市公安局要求启封厕所。如3署8分所辖内祠堂街第20号周和兴有厕所被查封后,厕主呈请启封,理由是:
祠堂街约有300户人家,人烟稠密,倾倒马桶、便溺全赖此厕。近有不顾清洁之人,家中便桶所贮之粪水无处倾倒,侯深夜时,倾入阴沟内,时值春末夏初,热气渐烈,臭气熏蒸,恐受传染,妨碍安宁。邀集厕所附近街民,会议研究,对于公共厕所清洁事务再三讨论,唯周和兴厕所地点适宜。故望局长体恤街民便溺艰难,积气难净实惠于周和兴,垂怜家贫,素以肥料营生,别无他业,呈请谕令启封厕所,饬令周和兴遵照议案修理场所,以洁公共卫生而重观瞻。
又如:
王氏一家数口,幼年居,先夫故世。留厕所一间,而每月租金4元,王氏一家全赖此生活。前因公安局注重卫生,防患未然,首从卫生入手,清查本市公共卫生。查得外东街市4号茅厕过于狭小,不合卫生,令伤改建,严加清洁,务以适合卫生。王氏当即着手整理,再加修葺,使空气格外流通。
因此呈请市公安局启封王氏厕所。
类似的情况屡见不鲜。五福街609号厕所因建筑不合,妨碍卫生被查封后,厕主呈请启封,理由是“厕主前将五福街茅厕租与不重卫生之粪商,以致查封,现拟改良建筑,另行择佃,以重卫生,如蒙允许,即日动工修建,以后随时打扫清洁,若再蹈前辄,自甘受罚”。石灰上街640号,石灰下街650号厕所因夏季时疫流行,有碍卫生被查封后,呈请启封,理由是“惟民一家数口全赖茅厕以维生活,自封禁后生活无依,一家数口嗷嗷待哺,不得已邀同署正恳请准予揭封,照图改建,不致有碍卫生”。而金家坝街603号茅厕因臭气外溢不合卫生被查封后,厕主呈请启封理由是“厕主一家数口全赖此生活,其厕所修理改建数次。因厕主住家稍远,有不顾公益之辈常将臭积之物以及渣滓倾倒厕所,防备未周,以致臭气外溢,故被查封。现已雇人将渣滓搬运,并随时扫除,不致有碍卫生,故望启封。”一是作为全家糊口之用,二是作为改建厕所的费用。
3.成效甚微的粪坑治理
清末至民国初期,成都的街道厕所大多小、烂、脏、臭,夜间也很少点灯。沿街很远就能嗅到臭味。居民在家里,一般使用马桶或在庭院角落设置尿缸。事实上市政对尿缸,也缺乏管理。私人厕所业主只图利,用厕所粪便赚钱,很少对厕所保洁。此外,成都四城门外沿着公路两边历来有许多储粪坑,分为干粪坑和尿水坑两种。有的属于粪商,有的属于农民。粪坑一般深2米,常用熟石灰抹四壁,也有用青砖、石板镶壁的。坑口或方或圆,上面搭有棚盖透雨。有的坑上搭上木板以供运粪夫居住,称为“粪坑楼”。
储粪坑很少保洁。在省城四门外,泥泞狭窄的公路两旁,粪坑星罗棋布,都不加盖。每逢雨季或用肥淡季,经常出现粪便淤积,坑满为患的现象。蚊蝇飞舞,臭气熏天,河岸旁粪坑也是如此。公厕内经常屎尿遍地,入厕时根本无落脚之地。厕所、粪坑周围常堆积垃圾脏物,形成老鼠聚集地。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四川省会成都市对公共卫生日渐重视,认为公厕对卫生、观瞻均有妨碍。1940年5月3日、4日,市府督同警察,尽数查封全市大、小街巷厕所。结果当即遭到肥料公会及市民的反对。市民在封闭后的厕外随地便溺,厕所业主、粪商迫于生计也上书四川省府吁请解决。省府兼理主席蒋介石训令市府妥慎办理,查封整治厕所一事只得不了了之。公厕脏臭面貌依旧,直至国民政府统治结束,仍无多大改善。
总的来说,民国时期,市政府制定各种规章,对公厕进行管理,有时还采取严厉措施。如对擅在厕所门前随地便溺者,罚跪一小时以示惩戒。对污秽不堪的厕所,也规定了取缔办法。同时制定厕所建造样式,督造“模范”厕所,令各街厕所业主仿造,但均未见有多大成效。
四、结语
近代,成都与全国其他城市一样经历了改良、革命和军阀混战,社会一直处于剧烈变化的状态,城市公共空间被重建并纳入系统的市政管理体系。卫生事业作为现代城市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重要性日益凸显。卫生事业是城市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方面,与城市现代化有着特殊的关系。近代卫生事业的发展既是城市现代化的必然结果,又是城市现代化发展的推动力量。这是因为卫生事业既涉及市政基础设施的物质方面,又涉及现代文明的精神方面[15]。
近代成都卫生管理事业从无到有,努力发展,为卫生事业的现代化做出过积极贡献。主要表现在:其一,卫生行政管理机构的不断完善。成都的卫生管理机构明清时期为“医学”,清政府实施“新政”后创建新式警察,成都的卫生事业由警察机关管理。1921年6月5日,成都市市政筹备处成立,成都市卫生事业开始进入警察系统与省市政府系统双头管理的局面。但由于事不专属,权责难分,卫生管理过程中难免相互掣肘。抗日战争爆发后,四川成为国民政府统治的中心地区,为加强卫生管理,1939年,四川省政府成立四川省卫生实验处,职掌全省卫生行政事宜。1941年,省卫生实验处会同成都市政府、省会警察局共同组织的成都市卫生事务所成为全国省会城市中仅有的三所卫生事务所之一,曾为改善城市卫生状况做了不少具体工作。1944年,成都市霍乱大流行,市政府为迅速扑灭霍乱,提高工作效率,在市政府内设置卫生科,将卫生行政管理和具体的卫生事务分开。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发动内战,成都卫生行政机构建设停滞萎缩。其二,公共卫生管理得到一定加强。自清末至南京国民政府结束,成都市在街面清洁、厕所清洁、有关卫生各业等方面曾相续颁布一系列法规,在执行过程中虽然极其艰难,但也取得了一定成效。近代成都卫生机构的发生发展始终处在一个动荡的、战事频发的年代,国民政府也无法得到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由于诸种原因,卫生事业总体不尽如人意,但对前人和历史,我们应多一份“了解之同情”与客观辩证之评价。客观而言,在有限的条件下,近代成都卫生管理机构为成都卫生事业及城市的现代化曾做出了积极贡献。
注释:
① 这方面较早的代表性著作是余新忠的《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版),该书立足近世社会发展、清代国家与社会关系两大问题,较为全面地探讨了清代江南的瘟疫及瘟疫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另,2015-2019年,华中师范大学有7篇硕士论文是关于民国时期疫灾流行与公共卫生意识的变迁研究的,范围涉及全国大部分地区。
② 目前城市公共卫生管理研究的学术成果中涉及环境卫生建设的,其研究范围主要集中于几个开放较早的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天津等,而对于内陆的研究却相对缺乏,特别是对于抗战大后方的川渝地区,其论著较少,尚有较大的研究空间。现主要有5篇硕士论文:江帆. 民国时期成都公共卫生研究[D].成都:四川师范大学,2019;纪晓婷. 民国时期开封城市的公共卫生事业[D].开封:河南大学,2017;甘慧. 民国时期上海卫生运动大会研究(1928-1937)[D].温州:温州大学,2015;马红梅. 民国时期南京城市环境卫生管理(1927-1937)[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3;赵文青. 民国时期广州城市环境卫生治理述论[D].广州:暨南大学,2007.
③ 米晓燕在《公共卫生与都市生活——以成都市卫生事务所为中心的考察(1941-1949)》中,以20世纪40年代的成都市卫生事务所为中心,考察了现代卫生观念下成都市开展的一系列具体的工作,指出现代卫生管理工作是成都现代化、都市化中极其重要的表现。刘雪怡在《社会进步与社会矛盾:民国成都现代卫生管理中的官民冲突》中指出,在卫生治理方面,政府与公众舆论是一致的,但是涉及自身利益时,双方所占的立场便出现了分歧甚至是对立,致使成都的卫生治理效果显得短暂且无法长期维持下去。
④ 四川省政府(卫生)资料集:1910[A].成都:四川省档案馆(全宗113,目录4,卷宗15).(本文档案文献均为内部未出版资料,下同,不一一注出。)
⑤ 市政公所报告:1922[A].成都:成都市档案馆(全宗38,目录5,卷宗45).
⑥ 四川省公安局卫生科工作报告:1933[A].成都:成都市档案馆(全宗93,目录5,卷宗229).
⑦ 四川省公安局卫生科水井、厕所调查表:1936[A].成都:成都市档案馆(全宗93,目录5,卷宗22).
⑧ 四川省政府政绩表:1937[A].成都:四川省档案馆(全宗113,目录4,卷宗23).
⑨ 陈志潜,公共卫生学家。他提倡公医制度,积极开展健康教育。先后参与陶知行和晏阳初分别在南京郊区和河北省定县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农村卫生实验区建设。在定县创立了他构想多年的农村三级保健网,开展保健服务和健康教育。陈志潜在日本投降前的几年中,为四川省的卫生建设工作作出了较大的贡献。他利用担任四川省卫生实验处处长、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学教授和战时救济工作负责人的身份和机会,为四川省建立起综合医院,传染病院,妇婴保健机构,护士、助产士和公共卫生人员培训中心以及供医学生和护校学生实习用的温江农村卫生实验区。他还争取到当时省政府领导的支持,为四川省大部分市、县,建立起市、县公立公共卫生机构八十余处,这在当时全国各省中是绝无仅有的。(资料来源:讴歌. 协和医事 [M]. 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254-2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