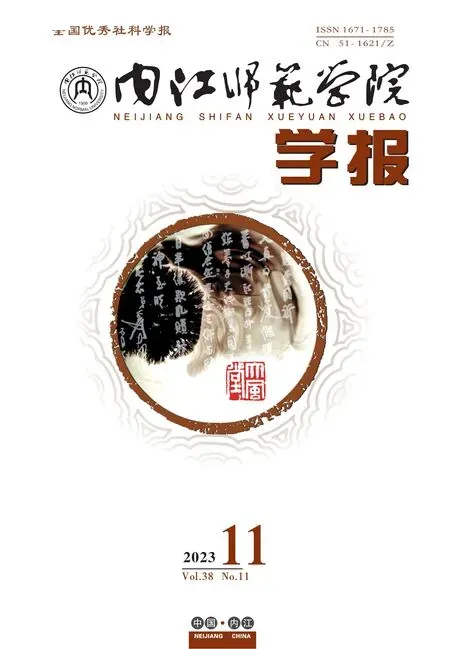清中叶百姓生活中的典衣现象
——以嘉庆朝刑科题本为基本资料
王 承 红
(山东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山东 济南 250000)
近年来,历史学的研究视角转向下层,关注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逐渐成为新的趋势。“清代档案刑科题本”系列丛书的出版为研究日常生活史、社会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刑科题本较为完整地记录了命案的审判过程,相关供词对涉案百姓的家庭、婚姻、身份、职业、社会关系以及案件发生的前因后果记载得十分详细,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涉案百姓当时的生存状态。从整体上来看,刑科题本中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命案审判记录,涉及地域范围广、各种类型的案件数量丰富,因此可供研究的问题和视角众多,相关研究成果也十分丰富。目前,以冯尔康、常建华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充分利用刑科题本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研究内容涉及社会经济史、日常生活史、法律史、妇女史等多个领域。其中就典当业的研究成果来看,学者们较多关注的是土地的典买和契约问题,对百姓典衣活动的关注和研究稍显不足,刑科题本中与典衣相关的内容还有待发掘和整理。
尽管目前运用刑科题本对典衣进行研究的成果还比较少,但不可忽视的是部分学者曾运用其他资料对典衣进行过研究。比如,王中良曾利用晋商书信资料《同光直隶大名府恒裕典东伙往来信稿抄本》,撰文分析了同治十二年(1873)至光绪三年(1877)恒裕典当衣业务的开展情况,论述了恒裕典当衣业务的主要对象、收当和赎当的影响因素等问题[1]。这篇文章在内容和方法上都对本文有较大的参考价值。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整理嘉庆朝刑科题本中与典衣相关的记载,以期进一步认识典当业中的典衣业务与百姓生活的密切关系,进而了解当时百姓的生存状态。
一、典衣行业的兴起与发展
所谓典衣,即以衣服做抵押进行借贷的活动。原始社会时期,衣服最初的功用是保暖防护、蔽体遮羞,人类开化以后有了爱美之心,衣服又增加了为美观而装饰的作用。随着私有制的发展,社会出现了阶级分化,随之形成了完善社会秩序的礼制建设,衣服作为个人私有财产的一部分,也成为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皇室贵胄有锦衣华服,平民百姓则穿粗布衣衫,尽管这些衣服的价值天差地别,但都具有一定的典当价值。
何为典当,清人郝懿行在《证俗文》中写到“典当,俗以衣物质钱谓之为当”,并以《后汉书·刘虞传》中所载的“虞所赍赏,典当胡夷,瓒复钞夺之”为依据,认为东汉时期已有典当[2]503。然而,今人学者经过研究多认为中国典当肇始于南朝佛寺寺库[3]。尽管典当起源于何时,学界仍存在一定的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早在西汉时期就出现了以衣服做抵押换取其他物品的现象。
西汉时,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夫妇“以所著鹔鹴裘就市人阳昌贳酒”[4]82。“贳”作何解,东汉时许慎在《说文解字》中作“贳,贷也”,“赊,贳买也”[5]130。清人段玉裁注之:“贳买者,在彼为贳,在我则为赊也。”[6]515换言之,受者曰赊,予者曰贳。从记载来看,抵押过程中并未出现一般等价物,也没有经过典当经营机构,有学者认为这只是私人之间的一种质贷活动[3],真正以衣服做抵押借贷银钱的典衣活动,则始于典当经营机构正式出现以后。
随着典当业的发展,典衣活动在民间逐渐普遍,许多诗词家的笔墨中都能看到“典衣”的存在。唐代诗圣杜甫多有酒债,以致典衣。唐肃宗乾元元年(758)暮春时节,他在诗中写道:“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7]77杜子美“日日典衣”,其中虽不乏夸张的成分,但也表明“典衣”在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很可能经常发生。两宋之交,山东诸城太学生赵明诚与女词人李清照夫妇酷爱金石学,遇到珍贵的碑石古玩时,不惜典衣换钱购买。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中写道:“每朔望谒告出,质衣,取半千钱,步入相国寺,市碑文、果实归,相对展玩咀嚼,自谓葛天氏之民也。”[8]257南宋爱国诗人陆游的《剑南诗稿》中也随处可见“典衣”,如《春前六日作》中“典衣沽酒莫辞醉,自有梅花为解酲”,《自贻四首其三》中“痴孙护雀雏,馋仆放池鱼。怀药问邻疾,典衣收旧书”[9]27等等。从这些诗词家的笔墨中,可以窥见典衣活动在百姓生活中之普遍。
实际上,典衣与中下层百姓特别是贫民的联系更加紧密。民国学者杨肇遇论及典当业之兴起时曾指出:
盖自货币兴,借贷起,有余资者不得其用,而无资者,欲假钱财,既无亲戚友朋之关系,则靳于情谊,又非空言所能取信于人,乃以物为质,约期赎回,贷资者因得物以为抵押,则不虞其贷资之无着落,借资者只须有物,则可质钱,不问其识与不识也。于是资金得以流通,各方均蒙其利,而于贫民尤称其便,贫民之信用薄弱,岂一纸借据,而能博人之信哉,故贫民欲得资金之融通,舍典当更无第二途径。[10]1-2
由此可知,典当为那些资金需求不大、信用薄弱、但尚有部分实物资产可供抵押的低收入群体提供了一种正当合法的应急途径,正如谚语所说的那样,“典当者,穷人之后门”[10]1-2。在百姓掌握的各种可典当的物品中,以人们日常生活中所必需的衣服最为常见,即使是贫民也有几件“褴褛衣衫”可供出典。换言之,相较于金银珠宝等其他较为贵重的物品,衣服是绝大多数百姓都持有的一种典当物。因此,典当业中当衣业务的服务对象范围更加广泛,典衣与贫民的关系更加密切。
从典当行的角度来看,衣服是当铺收押物品中的大宗。嘉庆朝刑科题本中有一起当铺被盗案可作例证。据记载,嘉庆十三年(1808)广东新兴县人罗亚宽等合伙从冯宰平的当铺中劫掠了番银六百一十两零、铜钱六十五千四百文、金首饰七件、银首饰三千余件,绸布衣裤共五百零两件、棉夹布被褥二十八张等等[11]1721。在这起盗窃案中,若将案犯更倾向于劫走贵重物品的因素刨除在外,可以发现衣服确实是当铺中收押和保存数量较多的物品之一。民国时人陆国香对山西当质业的调查报告也可以佐证。
当铺当入之物品,以衣服为最多数,皆在百分之七八十以上,当铺亦欢迎此项日用或生产必须品,因当铺营业,利在当户之赎当,赎当多则利息收入旺,营业亦发达,他方面,当户因系必需品,故有当必赎……[12]
从材料中可知,当铺盈利的主要方式是向当户收取赎当的利息。衣服作为百姓生活中的必需品,拥有相对较高的赎当率,因此也是当铺十分乐于收押的一种物品。除了收取赎当利息外,当铺还可以通过兼营估衣铺出售那些到期未赎成为死当的衣服,借以回笼资金。在这样的情况下,衣服既是百姓应急时方便出典的当物,也是当铺中流转率较高的物品,在商民双方的共同需求下,典衣行业的发展日益兴盛起来。
二、嘉庆朝刑科题本所见典衣的种类及其价值
典衣是普通百姓特别是贫民日常生活中较为常见的现象,那么百姓典当的主要是哪些衣服,当值如何?本部分即针对这些问题展开论述。
(一)典衣的种类
百姓的衣服在未被典当前,主要有两种来源:其一是自制成衣。或自己纺纱织布,或直接买布制衣。生活在乾隆、嘉庆年间的洪亮吉曾指出“一人之身,岁得布五丈,即可无寒”[13]16。其二是直接购买成衣。刑科题本中的相关记录很多,比如嘉庆五年(1800)五月,四川仁寿县人周代有向孟惠先赊买布衫一件,讲定价钱二百五十文[11]512;嘉庆七年(1802)七月,许老七赊买严礼顺棉被一条、棉袄一件,凭张老么作保,讲定钱二千文[11]830;嘉庆二十年(1815)十一月,广西龙州厅监生叶青松在裁缝邓宽惠处赊取羊皮马褂一件,该银六两二钱[11]1221,等等。这些案例表明清中叶百姓直接购买成衣的现象较为普遍,可以推测当时成衣业的发展较为兴盛。值得注意的是,百姓购买的成衣有新旧之分,其中的旧衣服主要来源于当铺中到期未赎成为死当的衣服,这些衣服一般经由当铺兼营的估衣铺出售,估衣能否顺利销售是影响典当业盈利与否的重要因素[14]。
就百姓出典的衣服种类而言,清代《浒墅关商税则例》中有“衣服小贩税则”,对各种典衣过关时的纳税要求进行了规定,其中开列的典衣种类有衣、帽、包头、兜肚、带、袜、鞋等等[15]222。相较而言,刑科题本的相关记录中,典衣的种类相对较少(如表1所示),主要是棉袄、棉袍、皮袄、布衫等。从衣服的质料上来看,主要以棉、麻为主。冬季百姓多穿羊皮袄,大体上符合清人黄卬所描述的康熙年间人们的居常服装,即“常服多用布,冬月衣裘者百中二三,夏月长衫多用枲葛,间用黄草缣……冬月富者服狐裘猞猁狲之属,服貂者亦间有之,若羊裘则为贫者之服矣”[16]16。嘉庆朝刑科题本中所见典衣的种类,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时下层百姓的穿着情况。
除了个人私有的衣服可以典当外,一些公共性质的衣服也可以用于抵押。嘉庆年间,山西太原府阳曲县向来有公置的社庙彩衣十件,每年正月十五灯节时扮演社戏穿用,平时由村民轮流经管。嘉庆十年(1805)灯节后,村民王世喜要出门看亲,因自己的衣服质当后没钱赎取,遂从经管人高清明手中借得彩衣顶出,并说定回家后赎还。但王世喜并未信守承诺,探亲回家后始终没有赎还。到嘉庆十一年(1806)正月十五日,村人要扮演社戏却无彩衣可用,经管彩衣的高清明被村人抱怨。次日,高清明又去讨要彩衣,不料失手将王世喜扎死。这件案子最后判定高清明拟绞监侯,秋后处决。王世喜顶当衣服钱文,身死勿征,其所顶当的彩衣乃是公置,仍饬令高清明名下备价取赎[11]594。

表1 嘉庆朝刑科题本所见部分典衣的种类及价值
(二)衣服的典当价值及其影响因素
分析涉及典衣的相关案件可以发现,被典当的衣服大多数是百姓穿过的旧衣服,这些衣服多多少少具有一定的典当价值。如表1所示,不同种类的衣服当值不同,即使是同一种类的衣服,其当值也有不小的差异。比如同样出典皮袄,山西灵石县人李三牛当了一千文钱,奉天宁海县人金文发当了市钱六千,直隶平泉县人李麻孔则当得一千五百文大钱。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清代实行银钱并行的货币政策,各地区流通使用的钱币种类又有所不同,所以出现了衣服的当值由不同的货币单位来表示的情况,而且钱币本身的价值时刻处于变动之中,各种货币之间的折算比例也不易确定,这就使对比各种典衣的价值产生了一定的难度。
不过,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制作衣服时投入的成本越高,其典当价值也越高。从整体上来看,百姓一年四季换穿衣物的当值由多到少分别是:皮袄—棉袄—夹袄—单衣,与谚语所说的“皮顶棉,倒找钱;棉顶夹,倒找嗄;夹顶单,倒拐弯;单顶棉,须加钱;棉顶皮,干着急”[17]2194一致。这也表明衣服的当值多少与其质料有关。如前所述,百姓衣着的质料主要以棉花、棉布为主,因此衣服的价格和当值受到棉布价格波动的影响。一般而言,棉布的价格越贵,制衣的成本越高,衣服的价格和典当价值随之而上升。
除质料外,还有许多其他因素也影响着衣服的当值,当铺在收押衣服时有一套详细的衡量优劣的标准。《晋商史料集成》中收录的《咸丰元年重订当谱》手抄本中即有“看衣规格”,教人分辨当衣的优劣和价值的高低,现摘录如下:
然当行中论衣之美劣愈真,看之必先看其大小、宽窄、颜色、高低。如衣之全美者,要身长袖入,看宽而下炸大,领口合其中做的时样上下里表相配,色道鲜嫩,乃谓之全美。如劣者,身长袖短,或小炸窄小、领口过大,或样不齐、花不对、不时样,或底巾频接,大面上沾渍,整衣补块,面好而里削薄,或做手不高,此皆衣服之大病也。[18]632-633
从中可见,衣服的大小、宽窄、做工、色彩、时样、是否有污渍补丁、磨损程度都是影响当值的重要因素,各种衣服的典当价值还需视具体情况而定。
另外,到清朝中后期,随着国门打开,洋货洋装涌入中国市场,对典当业中的当衣业务也产生了一定的冲击。针对这个问题,民国学者杨肇遇曾指出:
典当所受抵押之物品,衣服占其大宗,近年衣式翻新,变更迅速,随身裁剪,他人难穿,典当自受质之日始,至满期时止,须经一载或二载之久,在当时以为美观时式者,迨满当时,已成陈旧,价值跌落,亏本堪虞。[10]24
刘百闵也有同样的看法,他在为宓公干的《典当论》所作的序中也写道:“然近年来,外货倾销,物价陡变。都市好奇,衣服式样屡变。”[19]19从杨、刘二人的描述中可知,其一,清朝后期,随着价格更加低廉的洋布在中国市场的大量倾销,制衣的成本逐渐降低,普通衣服的价格和典当价值也随之而下降;其二,衣服的裁剪制作逐渐趋向贴合人的身材,量体裁衣,他人难穿;其三,受外来因素的影响,衣服款式更新迅速,人们更倾向于挑选美观时样的衣服。
这些变化的出现直接影响了当铺的收入来源,一方面,衣服的赎当率降低,当铺的利息收入减少;另一方面,那些因过期未赎而进入估衣铺销售的衣服,往往也因式样陈旧销路不畅,估衣的滞销无疑不利于典当业的发展。种种因素影响下,当衣业务逐渐衰落下去。现今的典当业中依然有衣服的典当,但仅限于价格昂贵、数量十分有限或者具有特殊意义的衣服,平民百姓穿用过的衣服显然已经失去了典当的价值,这与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和各种衣服的供求关系发生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三、嘉庆朝刑科题本所见百姓典衣活动的特点
分析涉及典衣的相关案件,笔者发现清中叶百姓的典衣活动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应耕作时令的“春当秋赎”
一般来说,百姓的冬衣“春当秋赎”,适应了耕种的时令。每年春季三四月份,典衣迎来一个小高潮,这时天气转暖,人们逐渐脱下棉袄、皮袄等厚重的衣物,换上轻便的衣装,不少人选择将厚重的衣物典当换钱,助力春耕。待到秋冬之时,天气转冷,又将典当的衣服赎回。典衣以助春耕的例子不在少数,比如明人熊人霖所说:“更喜天稍暄,絮衣聊可质,一以修耒耜,一以偿佣直。”[20]14还有清中叶诗人贝青乔的《浸稻种》写到“去年典谷赎冬衣,今日典衣赎稻种”[21]16等等。
“春当秋赎”在刑科题本中也可以看到相关的记录。嘉庆十四年(1809)三月,广东曲江县人朱贱科因春耕乏本,叫妻子朱江氏回娘家向母亲借取衣服十七件,当银使用,约定收割早稻后赎还。南方地区的早稻一般在清明前后(即4月初)插秧,到大暑前后(7月中下旬)收割。因此,朱贱科三月内借当衣服准备春耕,到七月底应收完早稻,赎还当衣,但因他嗜酒将赎衣钱花用,当衣过期未赎。八月初六,岳母寄信催赎衣服,朱贱科不满岳母和妻子逼催赎衣,双方发生口角,朱江氏将丈夫打伤致死[11]1065。这起案件表明,以种地为生的百姓可以通过典衣助力春耕,“春当秋赎”也使典衣行业的发展在时间上有一定的规律可循。
(二)“便民”又“伤民”的两重性
典当业包括典衣业务存在的初衷是扶困济贫、便民利民。在刑科题本的相关案件中,大多数典衣活动均出于应急目的。部分百姓为了筹集盘缠而将衣服典当,如嘉庆二十年(1815)七月,云南府禄丰县人戴升,因工食微薄,想去省城寻找新的雇主,临行前典卖衣物筹措盘缠[11]1089。嘉庆二十三年(1818)三月,甘肃河州府北塬汉人李希苍为筹措盘费,携带旧布衫一件、裤子一条、小铁锅一口、铁斧一把进城变卖[11]737-738。还有人为解决温饱而典衣,比如嘉庆十四年(1809)十二月,江西金溪县人江匹生在被拘押期间,因无钱买饭,将身穿布褂交给王魁三代为押钱[11]1067。一些百姓无力缴纳赋税时,也通过典衣换钱以补不足,清初浙江海宁人陈确写下七言律诗《己亥春正》:
己亥春正灯尚红,征粮县檄日数通。借衣出典典铺中,诸铺皆云银已空。十金典一非至公,犹言为我姑通融。嗟哉吾穷铺更穷,征输络绎将奚供。嗟哉民穷俗则丰,举世相耀以鲜秾。请君试看陌上佣,黑纱由里辉其躬。今日制衣明日典,还愧新衣制未工。[22]12
诗中描述了当地百姓典衣换钱以纳粮的情形。如此种种,都说明在底层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典当衣服是较为便利、迅捷的应急方式。尽管衣服的当值往往较低,但也可解燃眉之急。典衣为百姓提供了一条应急的“生路”,使贫困小农得以维系生产生活,也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
此外,在地方志中也有不少典衣以行善的事例。比如嘉庆《扬州府志》中记载扬州人栗本中听闻“里有累官钱而质女者,壻家来娶,其人惶惧,本中尽典衣物,赎而归之,有富家闻其义,因纳交延,誉为书佐,复以诚信见重于钜公”;扬州江都人江崑,性好施予,遇到族党之穷乏者随时周恤,“有亲串某某遭急难事,非万金不可活,崑罄所有为助不足,仍典衣饰补之,事始得解,而崑家坐是中落,几于日食不给,绝不向人道一字”;黄起杰也轻财好义,“人有急,不惜典衣应之”[23]27-38。这种典衣活动也是应急性质,其典衣的目的和动机是十分高尚的。
然而,随着典当业的发展,当铺重利盘剥、欺诈穷人的本质也逐渐暴露出来。清乾隆年间,李燧在游历山西各府州县时,已深感当铺盘剥之弊,他在《晋游日记》中写道:
汾(州)平(阳)两郡,多以贸易为生。利之十倍者,无如放官债。……其次,则设典肆。……吾辈八口嗷嗷,点金乏术,不得不倾箱倒箧,尽付质库。伊乘其窘迫也,而鱼肉之。物价值十者,给二焉。其书券也,金必曰淡,珠必曰米,裘必曰蛀,衣必曰破。恶其物,所以贱其值也。金珠三年,衣裘二年不赎,则物非己有矣。赎物加利三分,锱铢必较。名曰便民,实闾阎之蠹也。[24]70
李燧的描述揭露了典当业盘剥百姓的“真实面目”。但不可否认的是,贫民又对典当业有着较强的依赖性,当百姓求救无门时,舍此途径别无他法。面对典铺“便民”又“伤民”的两面性,清朝官府的态度是,既承认其合法性,又针对典当行业中存在的弊端出台相关法令进行制约。在当息方面,清廷明确规定:“凡私放钱债,及典当财物,每月取利,并不得过三分。”[25]416在典当行业的监督和管理上,清朝政府向地方官施加了更大的压力。比如,乾隆五十三年(1788)上谕:“台湾地方,如有开设小典,质押零星衣物,重利盘剥贫民,地方官任听开设者降一级调用,失察者降一级留任。”[26]373-374这些相关法令的出台,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典当行业走向规范。
(三)衣服出典、赎当权利的让渡及其弊端
在涉及典衣的相关案件中,常常可以见到“剥衣抵欠”的现象,如表2所示。当百姓之间产生小额的债务或借贷纠纷,欠债人又因种种原因无法还钱时,剥衣抵欠成为一种常见的方式,这表明百姓穿用过的旧衣衫仍有一定的价值,但其价值较为有限,只能用于小额债务的抵偿。债主剥走衣服后,可以将衣服占为己有,也可以将衣服典当换钱以抵欠款,在这个过程中,衣服的所有权和出典权实现了转让,不过这种权利的让渡是被迫进行的。
刑科题本中还有一些“借当”衣服的案例。比如,山西阳曲县村民王世喜通过同村村民高清明借得社庙彩衣典当、广东曲江县人朱贱科借得岳母衣服典当等等。在这种情况下,衣服出典权则是自愿转让的。“借当”衣服的对象一般是百姓的亲朋邻里,借衣者和出借者之间往往有着亲近的社会关系,只通过口头约定便将衣服借出,利息也常常不在考虑范围之内。衣服的“借当”展现了亲朋邻里之间的信任和温情,在“借”与“还”中也往往秉承着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这是中国古代百姓在社会交往过程中“讲人情”的生动体现。这种自发自愿的民间互助行为,有利于营造和谐稳定的基层社会环境。
但是,这种基于信任而达成的约定往往也需承担更大的风险,一旦有一方失信,双方之间原本亲近的关系便会随之转向破裂。在一些案件中,衣物的“借当”与随后的“催赎”往往是导致暴力冲突的导火索,比如山西夏县民师四娃因当衣未还谋杀小功服兄师佐致死案、甘肃平罗县民孙成立因赎衣纠纷伤伊妻王氏身死案、山西灵石县民杨九玉因索还皮袄扎死李三牛并杀己妻案,等等。这些命案的发生归根结底,还是百姓的信用薄弱,没能按时履行约定。这表明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人们的法律契约精神还比较淡薄,借贷双方达成的口头约定只能靠个人的信用来维持。正如英国学者科大卫所说:“约束着人们行为的并不是世俗的法律,而是带有信仰色彩的道德和良心。”[27]16这也昭示着“人情社会”中仅靠道德约束是不够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借贷契约无疑能使借贷双方更好地履行义务,从而保障双方权益。
“剥衣抵欠”和“借当”衣服的现象表明,在典当过程中当物的所有权、出典权可以进行转让,这种权利的让渡一方面为百姓应急提供了便利,但另一方面也给不法分子利用当铺销赃留下了可乘之机。在刑科题本中的抢劫、盗窃案中,衣服作为“赃物”常常通过当铺出手。比如嘉庆十一年(1806)正月,宁海县人金文发行凶杀人后,顺便将死者身边的衣裤带走,为了销赃,金文发将羊皮袄拿到当铺当得市钱六千,后又将皮袄当票转卖给李皮匠,得钱一千六百文[11]1609。当票是赎回衣服的唯一凭证,金文发为了销赃又将当票转卖给他人,有偿让渡了赎当权。
在利用当铺销赃的问题上,清廷规定“若诸色人典当收买盗赃及窃赃不知情者,勿论,止追原赔,其价于犯人名下追征给主”[28]377。即当商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收买盗赃并不需要负相应的责任,在案发后还能向犯人讨回当本。比如,嘉庆七年(1802)十二月,山东莱州府昌邑县人王小豹因索欠砍伤隋加爵,顺便带走了一件蓝布棉袍、一件蓝布大棉袄、一件蓝布小棉袄、一件白布小褂、一床棉被。王小豹恐怕赃物留在家中被人看破,案发次日拿到庄上典当换钱,不久被公差抓获。案件审理过程中,王小豹典当的衣物从当铺取出作为呈堂证物。莱州知府邓再馨指出:“该犯所当衣被业已起获,究非无故而取,应免追赔,仍追当本还商。”[11]545可见,在当时即使有人通过当铺销赃,案发后也并不会影响当铺的经营,朝廷对利用当铺销赃问题的处理长期处于一种“治标不治本”的状态。现代典当业较之古代典当业的进步就在于,对出典人身份的真实性和抵押物来源的合法性进行了严格要求,这就大大限制了销赃现象的膨胀与发展。
四、余论
刑科题本中关于百姓典衣活动的案例,为我们了解清中叶的社会情况提供了一个新的着眼点。
首先,从经济层面来看,清中叶百姓典衣活动的普遍存在,反映了当时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具体而言,小农将衣物“春当秋赎”以维持农业生产;贫民典衣以解燃眉之急;因贫从商者通过典衣筹集贸易经营资本;财资雄厚者则开设典铺、收押衣服以谋利。这一系列活动以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前提,反过来也构成了经济发展的推动因素。
其次,从社会史的角度来看,典衣活动展现了清中叶百姓生存状态的一个侧面,即当贫民在生活中遇到困境时,常常通过“典当”或“借贷”来维系其生产生活。在一些案件中,借贷关系和典当关系同时存在,衣服的“借当”即是典型的例子。“借当”“催赎”“剥衣抵欠”等现象反映了清中叶百姓对社会人际关系的经营与处理。
最后,由于刑科题本所反映内容的特殊性,我们得以通过“典衣”的相关案件管窥一些法律层面的问题。其一,刑科题本中数量庞大的命案审判记录表明,清中叶的司法审判程序已经相当规范和成熟,审判、量刑均有法可依;其二,清朝统治者出台了相关的法律条文,为典当行业的发展走向规范做出了努力和尝试;其三,信用薄弱的低收入群体常因未能履行约定而陷入借贷经济纠纷,最终酿成暴力冲突,人情社会更加呼唤法律契约的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