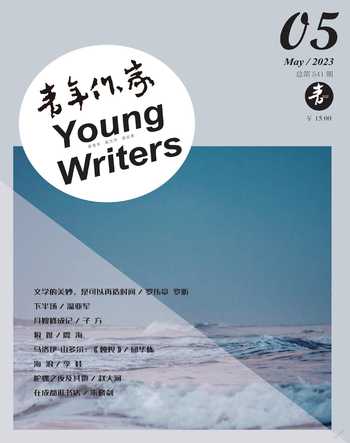西游天竺随笔
上篇 拉吉普特人的古堡
在我的印象中,印度是一个内部纷争不断的国家,种姓之间的藩篱、宗教之间的鸿沟,甚至语言之间的隔阂,遇到一点风吹草动,都可能引发冲突,酿成动乱,好像从来就没有消停过。2017年岁末,一部尚未公映的电影,又一次把南亚次大陆搅得鸡飞狗跳山河震荡。
这是根据16世纪苏菲史诗《帕德玛瓦蒂》改编的同名电影,情节主干完全可以视为印度版的《特洛伊》:拉吉普特(Rajput)人的契托国(Chittor)王后帕德玛瓦蒂(Padmavati)倾国倾城惊为天人;德里苏丹阿劳乌丁·卡尔吉(Alauddin Khalji)垂涎美色,不惜兵犯契托;契托国王拉坦·辛格(Ratan Singh)战死;城破之日,王后为守护清誉,率后宫女眷着结婚礼服集体自焚。
耐人寻味的是,尽管导演煞费苦心地在片头发布免责声明,连篇累牍地宣称人物、地点、场景、故事,包括对话、舞蹈、习俗均纯属虚构,声言断无对任何个人与团体的信仰、情感、情绪的无礼及贬损,甚至以印度动物保护协会的半官方名义,保证影片中的飞禽走兽均受到专业人士的善待,但仍然无法避免街头不断升级的骚乱。
引爆点在阿劳乌丁纯粹意淫的同王后的缠绵床戏,信奉印度教的拉吉普特人,无法容忍心目中的女神帕德玛瓦蒂,投入信奉伊斯兰教的德里苏丹怀中,哪怕是非分幻想中的场面也不行。在印度古老的种姓制度中,拉吉普特人属于血统高贵的刹帝利,向来以婆罗门文明的捍卫者自居,因此骚乱尤以拉吉普特人聚集的拉贾斯坦邦、古吉拉特邦、北方邦、哈里亚纳邦为甚,这背后显而易见是种姓的、宗教的情绪支配,而操纵民众情绪的,则是背后政客们看不见的手,印度种姓的政治化和政治的种姓化,也由此得窥一斑。
然而印度毕竟是大英帝国假东印度公司枪炮下190年的殖民地,英语和法治是女王陛下留下的两大遗产。2018年初,最高法院裁决一锤定音:“电影院是言论自由和表达自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影片遂略作技术处理后在世界各地热映,而我则得以通过网络资源一睹真容。这部电影对我个人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激发了我对印度,对拉吉普特人强烈的兴趣,带着一个个浓烈镜头堆砌的新鲜印象,在3月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中,取道香港,5个半小时后就抵达了新德里,然后阿格拉——斋普尔,一路走来。
旅游大巴泊在斋普尔郊外一块平坦的沙地。斋普尔的气温明显要高于阿格拉,男士一律换上了T恤,你能实实在在感受到印度次大陆阳光的热情。一头白牛踱着方步掺和进我们的小圈子。印度是动物的天堂,印度教(婆罗门教)的生命轮回转世信念,强化了印度人尊重一切生命的情感,牛更是独享尊荣,德里的大街上,也常能看到牛混在汽车、摩托和TOTO车的洪流中优哉游哉地闲庭信步。同团驴友不解地问地陪光辉,光辉操印度口音浓重的汉语,比我们还要困惑地反问:人和牛不是一样的吗?人能走,为什么牛不能走呢?在信奉印度教的地陪光辉眼里,世间任何生物,都是显示神的存在,是伟大生命链条中的一环。难怪虔诚的印度教徒都是素食者,牛乳制品只用于宗教献祭。不过打眼一望,那牛都是瘦骨嶙峋,而且脏兮兮的,不像中国的牛膘肥体壮,毛色光亮如缎面。
手机、相机和目光,全都仰对着前方。前方山峦起伏,依山就势逶迤着一道城墙,雉堞参差,宫阙巍峨,整体呈琥珀色,与“粉红之城”斋普尔谐调,这就是拉吉普特族卡奇瓦哈国的旧都——琥珀堡。
其实契托国也是有城堡留存的,就在拉贾斯坦邦,可惜不在我们行程之内,只能留作遗憾了。好在导演拍戏取景,一如鲁迅小说写人,“杂取种种”,不拘一地,我在《帕德玛瓦蒂》中,就看到了阿格拉红堡壮观的正门,而影片开头的一个空镜头,分明就是峥嵘眼前的古堡。
上山的方式有三:年轻的背包客安步当车,浪漫的情侣多选择骑大象,我辈既不年轻又不浪漫的老人团,是挤在6人吉普里。反正或快或慢,都能把你带进历史的深处。
黑格尔称“建筑是凝固的音乐,音乐是流动的建筑”,这句话尽管常被挂在嘴边,但是坦白地说,我很难达到这样高的审美段位,倒是雨果的那句话,“建筑是用石头写成的史书”,更切合下里巴人的认知水平。现在,我们走进的这座古堡,就是一部拉吉普特人用石头写成的历史。
何谓拉吉普特人?印度号称人种博物馆,次大陆人称欧亚群租房,自从公元前2000年,雅利安人越过兴都库什山与苏莱曼山之间的开伯尔山口入侵以来,波斯、希腊、阿拉伯、突厥……一个个纷至沓来,来的都不是善茬,漫长的人种混血过程就次第展开了,这可忙坏了今天的人类学家,从骨骼、血型、肤色、语言等等角度研究其来龙去脉已然不够,随着基因技术的进步,一个将分子生物学与人类学交叉产生的边缘学科“分子人类学”又登堂入室,试图通过研究人类DNA中所蕴藏的遗传信息,揭示各个人种以及整个人类的形成与演化过程。只是面对这些高深的学问,在科盲如我辈心里,会徒生一种“你不说我还明白,你越说我越糊涂了”的茫然感。
所谓拉吉普特人,据《百度百科》介绍,是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5、6世纪,贵霜、匈奴、古加拉等部族,以及安息人和希腊人大批移居印度,与当地居民融合形成的种族。这些在梵语中意为“王族后裔”的拉吉普特人,建立了许多独立王国,虽互不统属,在面对德里苏丹国穆斯林入侵时,却又能組成联军,为捍卫印度教婆罗门文明顽强抵抗,拉吉普特男人骁勇,女人刚烈,享有“印度武士”美誉。《帕德玛瓦蒂》中,便有许多宣示“战斗民族”性格的台词,掷地有声,令人闻之动容。
吉普盘旋而上,片刻抵达山腰,停在城堡侧门,当地称“月亮门”。山路狭窄,城门巍峨,矗立于峭壁高墙间,墙外环以护城河,据说水中还放有鳄鱼,以防敌人偷袭,属于那种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防御性设计,月亮门没有一点月亮的温柔。进得门来,四面建筑合围,围出一个大操场,半山腰辟出一块平地,宽广空阔,不知做何用途。正疑惑间,几头载客大象,披挂大红象衣,十分惹眼,正步态庄重,慢悠悠地从另一道大门踱进来,此门为太阳门,是城堡正门。操场实为游客集散地,一年到头热热闹闹,熙熙攘攘,像一个露天巴扎(集市)。
西谚说“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琥珀堡始建于1135年(这是我根据城墙上一块刻有“1135AD”的金属铭牌推断的,不知确否),公开的资料则显示为“建于1592年”,经历了不同历史时期,也不是一天建成的。时间在石头上留下的刻痕,显现在建筑群落的整体格局上,是自山腰动土垒石,以阶梯式建构,一层层向山巅堆叠开去。如同人种的混血,建筑上同样吸纳了多种文明元素,这也是时间在石头上留下的另一道刻痕。在城堡二层三面环合的楼台中央,建有公共会议大厅,应该是国王与臣属商讨国事的场所,这是一座开放式建筑,宽阔而厚重,庄严而华美,却只有立柱支撑,无一隔断,是典型的伊斯兰风格。但细瞅立柱,每根顶端都有一头小象支撑屋顶,而伊斯兰教是反对偶像崇拜的,网友便谓之拉吉普特建筑,或莫卧儿建筑。游客到此,喜欢伫立廊边,凭栏远眺。《帕德玛瓦蒂》电影里,放眼望去,是赤地千里,黄沙漫天,阿劳乌丁的军队纵马挥刀,如惊涛拍岸,席卷而来,那显然是导演另外选择的外景地。而今俯瞰前方,斋普尔静卧在低矮的丘陵怀抱里,民居错落,屋舍俨然,一派宁静和安详。
我同四海游客挤挤挨挨,坐在大厅廊檐下小憩。众人的注意力都被面前一座三层楼宇吸引,这座宫殿气象庄严,装饰华美,色彩明丽,顶层阁楼,却状似穹庐。细加推算,若以“建于1592年”计,彼时巴布尔在印度建立莫卧儿封建王朝,已歷数十载,而巴布尔是突厥化的蒙古人帖木儿的后裔,所以琥珀堡的整体风格,是印度教、伊斯兰、蒙古建筑风格的混搭。 作为琥珀堡的“标志性建筑”,这座宫殿吸引了众多游客拍照留念。地陪光辉用浓重印度口音的汉语,纠正了我的误判,原来这只是一道通往内宫的大门,叫“象神门”。举首仰望,门楣处果真绘有一具象头,有几分卡通造型,憨态可掬,十分可爱。印度教是多神教,号称有3300万个神灵,多神中以梵天、毗湿奴、湿婆为三大主神,但若论民间的亲和力,则以象头神(Ganesa)为最。象头神是智慧之神、破除障碍之神,象头人身,仁慈和善;独牙,持斧,战斗中则神勇无比。古代印度曾以象作兵,谓之“象骑兵”,试想千百头大象冲锋陷阵,如古德里安的装甲集群,横扫欧洲,所向披靡,那是何等一幅战争场景;当年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其先驱还曾以祭祀象头神动员民众,掀起反英殖民统治浪潮;而草根百姓每遇人生大事,也都会敬拜象神,以期破除障碍,诸事如意。大象在印度被视为祥瑞之物,乃至作为一个国家的图腾,也就毫不奇怪了。
拾级而上,穿过象神门,别有一番天地。但见庭院中央,绿草如茵,切割成规则的几何图形状,分明是一座花园,甚觉眼熟,一定是电影里掠过的镜头。行走至此,才明白了琥珀堡的整体布局。地陪缺乏宏观介绍,我则“说走就走”,缺少事先功课。琥珀堡的功能是综合性的:作为军事要塞,一层的广场是屯兵之处,平时习武操练,战时集结布阵;作为行政中枢,二层是“会议厅”及国王与高官办公之处;作为宫廷禁苑,三层是国王及嫔妃生活的“大内”。比之紫禁城,无非是把平面的功能区做了垂直的安排罢了。
走进“大内”,最有观赏性的建筑是国王下榻的寝宫,若论帝王寝宫的豪华,仅以法王路易十三开建的凡尔赛宫、俄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女皇开建的叶卡宫,其金碧辉煌,尽奢极艳,都足令世人叹为观止。琥珀宫的建造者无意于也不可能与之争锋,而是别出心裁,不做第一而做唯一:寝宫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全部采用切割细小的宝石和指甲大小的玻璃镜片,拼贴出繁密的图案贴面,日间美轮美奂,光彩照人;夜间一支蜡烛,即可繁星万点。倘若烛光摇曳,则流萤飞舞,寝宫顿作琼楼玉宇,天上人间。此番匠心,不独为美,更为国王安全,使刺客无从遁形,此宫遂得以“镜宫”名世。
地陪光辉再次用印度口音浓重的汉语,介绍镜宫对面,是国王的“12个老婆”居住的地方。这个在昆明学了几年汉语的印度小伙子,在他的词汇量中,还没有“嫔妃”“后宫”这两个比较高级的名词。“12个老婆”表达的生猛,刺激了在宫斗剧中浸泡得太久的中国女游客,一伙人前脚跟后脚,忙不迭钻进去,想一探宫闱秘史,镜宫再美,也不在心上了。
后宫和中国人心目中“宫”的概念相去甚远,整体建筑包括宫室、走廊、楼梯全由浅黄色石料筑就,浑然一体。楼梯既窄又陡,走廊幽暗,房间逼仄,所有的家具物件均已清空,徒留四壁,犹如监房号子,穿行其间,又仿佛在打地道战。据说国王就是借助这些暗道进出,临幸何人,其余11个老婆一概不知不晓。不过仍然有入戏太深的女游客,捡一靠窗处席地而坐,神思恍惚,不知穿越到哪块地盘,忘记了今夕何年。
地陪留下了足够的自由活动时间,之后就要打道回府了。地陪同时告诫:不可乱窜,琥珀堡建筑复杂,很容易迷路走失。我撇开后宫,顺一条狭窄通道,登上一座高台。登高望远,才看清琥珀堡整体布局。除了宫室建筑外,有城墙、瞭望台,沿山坡向左右两翼铺展开去,随山势起伏,十分壮观。无怪乎线上线下,驴友异口同声,呼为“印度长城”。不过在我看来,比起中国的万里长城,琥珀堡长城的格局明显不在一个量级上。这当然不奇怪,以一方土邦,怎么能与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大秦帝国同日而语呢?种姓文化自身的分裂性、排斥性,使印度从古到今,都没有形成统一的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虽然印度早在1947年独立之后,就以法律的形式废除了种姓制度,但是这种世袭的森严的等级制度,作为公元2世纪业已形成的印度教的核心教义,经历数千年积淀,已经成为集体无意识,深入到印度人灵魂深处了。国大党主席尼赫鲁清醒地认识到,“只要种姓制度仍然存在,印度就不能在世界文明国家中占据应有的地位”;但是他又同样清醒地认识到“在印度人们保持着种姓制度的条件下,印度终归是印度,但是从他们与这个制度脱离的那一天起,印度就不复存在了”。不知印度何时能走出这个两难怪圈。高台下,一群小学生在老师带领下游览琥珀堡,校服是清一色的,孩子的肤色却有黑有白,有深有浅。据说凭肤色、姓名、出生地便大致可以判断出各自的种姓来,我却衷心希望在这一代身上,能彻底抹去种姓的阴影。
沉思间,不知从哪个角落,呼啦啦腾起一群鸽子来,在古堡上空飞舞盘旋。泰戈尔的一句名诗倏然跃上心头:
天空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但我已飞过。
下篇 世间最美的陵墓
从新德里驱车5小时,就到了古都阿格拉。这是2018年的阳春三月,来时的武汉春服既成,正是踏青好时节,属热带季风气候的印度北方邦,天气已经炎热起来。此番拜谒的是莫卧儿王朝的圣地,印度共和国的名片——泰姬·玛哈尔陵。
正像一部宏大的乐章前面会有一段序曲,正戏开演前需安排一节热场,陵园的入口便气派不凡,以赭红色砂岩建筑的门楼,配以白色大理石图案点缀,厚重庄严,左右两侧墙体如双臂舒展,将整个园区揽入怀中。汹涌的客流将我裹挟进拱形门廊,甬道内光线幽暗,如晨昏颠倒。走着走着,忽然眼前一亮,那张无数次刻印在脑海里的二维图画有了生命,变为正前方的三维实景。连日的风尘和疲惫遂一扫而空,那一瞬间我被深深震撼了,这是每当慕名已久的标志性历史建筑扑入视野时,我从心灵深处迸发的一种生理性反应。都说没有到过泰姬陵等于没有到过印度,那么此时此刻,我的双脚才算是实实在在地踩在印度的土地上了。于是,咖喱、瑜伽、宝莱坞、圣雄甘地、诗人泰戈尔、柯棣华大夫、唐高僧玄奘取经之地、上海滩租界缠头巾的巡捕、儿童时代迷恋的《流浪者》《两亩地》、青年时代醉心的《罗摩衍那》《吉檀迦利》、改革开放初年倾动中华的《大篷车》,那些鲜明的画面动人的音符优美的诗句,混杂着隔三岔五种姓间教派间冲突引发的骚乱,以及我们同这个接壤千里的邻居之间难以避免的磕磕绊绊,一句话,关于印度的全部碎片化知识,一同潮水般涌来,又一同潮水般退去,眼前只有这座美轮美奂的陵墓——一个美丽女子的长眠之地。
在书写女人的美丽时,世界上最丰富的语言也会苍白无力,聪明的写作者总是采取侧面迂回的手段去接近她,从不敢贸然发起正面强攻。
海伦有多美?荷马没有描绘她的容顏,他只是告诉我们,为她整整打了十年特洛伊战争,当元老院的元老们终于见到她的那一刻,连这帮七老八十的老者也不由得怦然心动,叹一声这场大战打得值得。
杨贵妃有多美?白居易没有描绘她的五官,他只是告诉我们: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
那么,这个叫阿姬曼·芭奴(册封“泰姬·玛哈尔”,意为“宫廷的皇冠”)的波斯血统女子有多美,让一代君王沙贾汗如此倾心,虽征战南北而不离左右,倾一国之力也要兑现承诺,终至生死不渝而感天动地呢?泰戈尔未着一字,他只是告诉人们,好好端详这座陵墓吧,它有多美,她就有多美!
回应着诗人冥冥中的指引,我一时不敢唐突向它奔去,驻足廊下,放眼前瞻,一箭之地,越过长形水道,越过夹池绿树,越过青青草坪,中轴线末端,目光聚焦处,那座纯白的大理石建筑在丽日蓝天下熠熠闪光。宽阔台基上,呈八角形的殿堂,托举一个浑圆的中央穹窿,顶上升起一弯新月,四座高耸的宣礼塔拱卫四角;台基两侧,各有一座清真寺翼殿对称,朝向麦加,通体赭红,与陵墓形成鲜明色差,映衬得它如冰似雪。殿堂整体呈现是典型的伊斯兰风格,内凹拱门却是波斯风格,门户的透空又是印度教风格——极致的美是需要多方借力的,如同阿姬曼·芭奴的混血。于是,千头大象奔走于南亚次大陆,驮来阿富汗的青金石,斯里兰卡的蓝宝石,阿拉伯的玛瑙,中国西藏的绿松石、东海的水晶……世间珍宝,荟萃到亚穆纳河右岸。当然,同建材和珠宝一起来的,还有本国和外国的建筑大师、能工巧匠。22年的披星戴月,2万人的殚精竭虑,打造了这颗印度的明珠,世间最美的陵墓。
是的,泰姬陵绝对配称世间最美的陵墓。奥地利作家茨威格拜谒托尔斯泰墓,留下一篇传世散文,在他眼里,这座“只是树林中的一个小小长方形土堆”,是“世间最美的坟墓”。这两个“世间最美”,一是坟墓,一是陵墓,一个朴素到极点,一个华丽到极致,各据一端,极为具象地给我们普及了一个基本的美学知识:美的形态是多种多样的,世间万物,各美其美。
托尔斯泰坟墓的“最美”,外在的是它极端的朴素,而与朴素相依傍的,是一个建筑了现实主义文学顶峰,为人类精神文明作出了卓越贡献的伟大作家,又是一个毕生都在追求“道德自我完善”,不断地忏悔和赎罪的孤独的圣徒。这决定了托尔斯泰墓不是一个寻常意义上的“旅游景点”,而游客,或者更应该说是如茨威格那样的文人墨客,慕名前往,就不是寻常意义上的旅游观光,而是去贴近一个伟大的人格,去表达自己的仰慕和崇敬。
那么,泰姬陵的“最美”,又美在何处呢?试想以世界之大,帝王后妃陵寝何其多多,若要比庄严宏伟,恐怕莫过于埃及的金字塔和中国的始皇陵了。那巍然矗立的人造大山,劈面就给人一种威压感、沉重感,你可以敬畏它,膜拜它,但绝不会亲近它,而它也绝不会容许人去亲近。金字塔幽深的墓道里,刻着一句威严的咒语:谁打扰了法老的安宁,死神的翅膀就将降临在他头上。实际上,横死其间的探寻者代不乏人,诡异事件也层出不穷。始皇陵虽尚未发掘,但据说已测量出周边空气中,水银蒸气密度大于正常值,印证了《史记》“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的记载。
我曾踏访过京郊十三陵中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的定陵,这是中国唯一被打开的皇帝陵。深达九层的墓道,每走下一层,便多一分阴气。参观者无不敛声屏息,作毛骨悚然状。即便是上得地面,那古柏森然,昏鸦聒噪,触目皆肃杀之气,游人也多面目凝重,找不到一个喜笑颜开的人。
再看看泰姬陵吧,没有暗藏玄机,让擅入者步步惊心;没有生发诡异,以拒人于千里之外。世人用尽美好的词汇赞美它:圣洁、宏伟、壮观、典雅、高贵、端庄、肃穆……然而在我看来,首先应当是“明朗”,“明朗”是泰姬陵与其他陵墓区别开来的最显著的特点,以至于它可以开放夜游,票价虽远高于白日,游客仍络绎不绝。不妨想象一下,月光如水的良宵,星斗满天的子夜,泰姬陵倒影于水道,或清明澄澈,或迷离恍惚,若喷泉飞溅,水雾朦胧,倒影闪烁颤动,倏聚倏散,飘忽变幻,该是何等一幅风景?再问一句,有哪个少男少女愿意深更半夜跑到埋葬死人的地方去浪漫呢?无论是帝王将相的陵墓还是草民百姓的坟茔?除非是盗墓贼。
这就是泰姬陵,同样是为死者建造的安息之地,却超越了死亡,洋溢着生机。一代君王的功过是非,还是留给历史学家去评说吧。在芸芸众生眼里,泰姬陵只是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爱情的信物,正是这种人之为人的永生不灭的情感,触动了每一个游览者心中最柔软的部分。它超越了民族国界,超越了宗教信仰,超越了尊卑贵贱,超越了种种有形的无形的人造樊篱。罗密欧与朱丽叶如此,梁山伯与祝英台如此,沙贾汗和阿姬曼·芭奴也如此,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就是为什么戴安娜王妃与查尔斯王子婚姻危机时,要飞越重洋专程造访,面对泰姬陵而瞬间泪奔了;这就是为什么新郎新娘要特地来这里拍摄婚纱照,为的是让泰姬陵见证山盟海誓吧。人们从地球各个角落来到这里,只为瞻仰泰姬陵的风采,见证那份生死不渝的爱情。马克·吐温说得好:爱情的力量在这里震撼了所有的人。
此时此刻,南亚次大陆的太阳,正挥霍着灿烂与辉煌,把每一个男女老少都镀上金光。莎丽、奥黛、旗袍、契玛、长裙、筒裙、阿拉伯袍、牛仔裤、夹克衫……浓艳的、素静的、俏丽的、淡雅的,姹紫嫣红,五彩缤纷,泰姬陵俨然成为民族服饰的秀场;黑、棕、黄、白,每一张脸庞都洋溢着愉悦和友善。语言在这里不是障碍,一个微笑,足以让素昧平生的人互致问候;一个手势,就可以邀请萍水相逢的人合影留念。泰姬陵是印度的,也是世界的。正如巴黎圣母院是法国的,也是世界的;罗马万神殿是意大利的,也是世界的 ;红场圣瓦西里大教堂是俄罗斯的,也是世界的;万里长城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游客对每一处人文古迹的造访,都是对先哲前贤的敬仰,对人类文明的礼赞。在这些旅游胜地,也只有在这些旅游胜地,你才能真切感受到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愿景是多么美好,认识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曾经,我们梦见彼此陌生/醒来却发现我们,原本心心相通。”想起泰戈尔的诗句,我觉得心头一阵温暖。
【作者简介】吴平安,评论家,作品散见 《人民文学》 《中国作家》《文艺评论》《小说评论》《世界文学评论》《长江文艺》《作家》等刊,著有评论集《听那强弓响箭》、非虚构《中国光纤之父》等;现居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