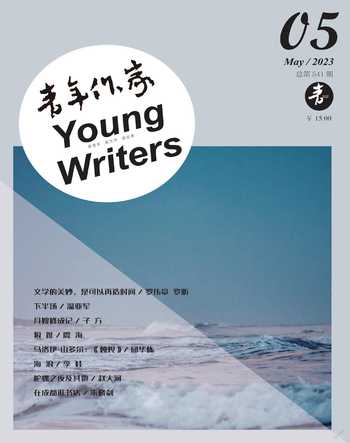斑马线
一
天还没有亮,张小鲁就起床了。迷迷糊糊之间,若兰觉得自己刚挨着他躺下不久。耳边盛开的窸窣声,淹没了她一肚子繁茂的私心杂念。她伸出光溜溜的手臂去摸,那个壮实的男人已跨过自己下床了。客厅里的灯亮了一下又灭了,像眨了眨蒙眬的睡眼。很快,楼下就响起了大货车的响声。
空气流淌着火,身体也流淌着火,整个世界就像一个被蓝焰包裹着的煤球,即使夜里也没有一点凉意。张小鲁刚坐进驾驶室里,就出了一身大汗。黑暗中的公路像一个幽深的煤窑,灯光打在上面闪着铁青色的光芒。他要把车开到百公里外的煤厂,那是方圆百公里唯一允许开采的煤矿。页岩砖厂需煤量大,拉煤的大车也多,只能按先来后到的顺序排队。去晚了,车子就会排到后面,等装好煤天就黑了,再拉到砖厂后回家就是半夜了,两头都不见天亮。多年黑白颠倒的生活让张小鲁觉得自己活得像个鬼一样。
今年夏天的气温高得离谱,很多司机就歇人歇车了。张小鲁还在坚持拉煤,运费是家里唯一的收入来源。
车窗外的树木、房屋还是一串黑影,远山是一张折痕不齐的黑纸,一齐向他涌来。张小鲁在这条路跑了十多年,他知道每一处的情况。他根本不在乎车窗外鬼魅般的黑暗,他心里想的是若兰。昨晚,她是几点回来的?有好长一段时间了,若兰都回得晚,有时候到了凌晨才回家。张小鲁辛苦了一天,回家倒头便睡,她回来的时候,他睡得正香。他们只能在黑夜里见面,在黑夜里相爱,他努力在脑海中翻找若兰的模样,可是只有一团模糊不清的样子。
张小鲁把车开到煤厂的时候,天空中才透出一层迷蒙的灰白色来。河谷仍然一片灰暗,只有橘黄的车灯错乱地在黑色的山谷里晃动着。货车沉重的喘息声此起彼伏,湍急的河水发出巨大的轰鸣,把原本宁静的大山吵成了一个热闹的早市。煤厂在河谷东边的大斜坡上,煤窑在陡峭的坡腰上,除了两根粗壮的滑索和黑洞洞的窑口外,就只能看见一面凹凸不平的黑乎乎的山坡。
从出煤口下来,横倒的M型黑泥路上已经排了十五六辆大货车,河对岸的公路上还有车灯在晃动,正朝山谷里开过来。他把车开上坡,赶紧排在那条粗壮的长龙后面。
“哧——”张小鲁拉起手刹,车子发出了刺耳的放气声,他打开车门跳了下来。淡蓝色的彩钢棚里早已坐了人,有的趴在黄色大圆桌上睡觉,有的坐在钢条椅子上抽烟,还有人精神头十足地相互开着玩笑。棚子靠着山体的一侧是三间简陋的厂房,住着掏煤工人和工头,当中隔着一间水泥空心砖砌起来的食堂。食堂里冒着腾腾的热气,胖大姐正在给大家煮面条,十块钱一碗。靠墙角的一个简易木架上有香烟、方便面、袋装卤味小吃等小商品,工人们早已吃完饭进窑出煤去了,她是在给司机们准备早饭。司机们起得早,几乎都没有吃早饭就开车上来排队了。等着装煤的时候,司机们就堵在那间彩钢棚里抽烟、打牌、摆龙门阵。
张小鲁用微信扫了十块钱,要了一大碗面条,又自己动手调了油辣椒、面条鲜、陈醋,还特意加了两个卤鸡蛋,才端到外面桌子上来坐下吃。往天,他通常只吃面条,有时也只买一袋方便面吃。今天算是奢侈了。但他胃口不好,觉得胸口有一股子浊气堵着,心情不舒畅。
他吃完面条才开始吃那两个茶色的鸡蛋,但手有些笨拙,挑了几筷子都没有捞起来,还差点掉到了地上。他把肥厚的嘴唇放到碗边,才把鸡蛋赶进嘴里。
“张胖子,你好久没有吃鸡蛋了吧?”
张小鲁白了麻杆一眼。麻杆身材瘦弱,叼着一支细杆烟,细直的烟雾从鼻尖升上去,把一脸嬉笑劈成了两半。
“不吃能长这么胖?”
“胖也是虚胖。干正事不行。”
“都像你?”
“看你鬼迷日眼的样子,昨夜肯定没有干成好事嘛。”
张小鲁心里陡然有些生气了,但他还是涎着脸笑了。
“都像你。”
二
“不打了。”
张小鲁斗了几把地主,输掉三十多块钱,赌气将纸牌扔在桌上。
“你咋是这个样子哟?平时赢我们那么多钱。”
“他不来,我来。”旁边早有人按捺不住,很快填补了空缺。赌场从来不缺人。
张小鲁没有回答,点了一支烟,径直向棚外出煤口走去。今天出煤慢,天气太热,工人少。麻杆和老工人正在装车,他在上面又蹦又跳,像笼子里一只找不到出口的長臂猩猩。随后又从老工人手里夺过铁锨在车顶使劲儿拍打。
“你看你哟,多装得了几斤?”张小鲁觉得麻杆整得太夸张。
“你没整过?”
张小鲁从地上捡起一个空烟盒,装了两支烟,又装了一块亮晶晶的煤在里面,向车顶抛了上去。麻杆伸手接住,递给老工人一支,吹了一口,也给自己点上了。
“这就走?”张小鲁问。
“不走,你管午饭啊?”
麻杆抓住车帮一跃而下,拍了拍手上的灰,又在屁股上搓了两把,便钻进了驾驶室。见张小鲁没有上车的意思,他又使劲按了一下喇叭,把张小鲁吓了一大跳。“上车啊。”
张小鲁一边掏车钥匙一边往棚子里跑去。转眼之间,他又跑回来上了车。
回程的公路顺河而下,阳光燎烤着大地,对岸山坡上的玉米地一片枯黄,公路两边的稻田里,谷子黄了,田埂都裂开了。灼热的风扑进驾驶室里,像是给人淋了一身开水。张小鲁戳了一下按键,打开空调,驾驶室里随即风声喧闹。麻杆看了他一眼,什么也没有说,要是他一个人的话,是舍不得开空调的。常年风里雨里,他们都习惯了。
煤、运输、页岩砖,形成了县内一条重要的产业链。这条公路去年刚刚整修过,水泥路面上标线清晰醒目,公路穿过小镇的时候,改成了漆黑的沥青路面。张小鲁跳下车,鞋子像是垫着海绵,太阳将沥青晒软了,黄色的中心线粘上了沥青黑斑和轮胎灰印,已经不太清晰。麻杆的车高高在上地碾过沥青路面,不时摇晃几下,又喘着粗气。他开得缓慢而小心,似乎比通过一段坑洼不平的泥泞路还要艰难。
小镇沿河而建,像一只庞大的腔肠动物,那条公路直通首尾,只在桥头有一条分岔公路向右延伸出去。路口设置着小镇唯一的斑马线,连红绿灯都没有安。那组白线油污不堪,“礼XX人”中间两个字看不太清了。斑马线右面,挂着清闲居茶楼淡绿色的大招牌,小镇上很多人在那里面闲度四季时光。今年天热,茶楼的生意特别火爆,空调从早开到晚,老板还管饭,如果晚上不想回家,还可以在房间的沙发上将就一晚。
若兰不在家。肯定又到茶楼去了。一开始,张小鲁并不想让若兰到茶楼去。
“我一个人在家,就是浪费。”
若兰抱怨她成天无事可做,要开空调,要买菜做饭。到茶楼里去,不仅能混时光,而且不做饭不费电,划算得多。张小鲁觉得若兰说得有道理,自然也不勉强,他也不敢勉强。
当初,若兰是看不上他的。若兰长得漂亮,苗条,是当地为数不多的美女之一。张小鲁胖,一动全身的肉都在抖动,但他实诚、顾家,跑了几年大货车,不仅还清了买车的贷款,而且还改造了临街的瓦房,建起一幢三层楼的新砖房。若兰的父母看中的正是这一点,如果女儿嫁过去,日子会过得衣食无忧。“帅气能当饭吃?还是找个老实人安稳些。”
若兰觉得自己嫁得勉强,心里总有一种失落感。要是继续外出务工,凭她的模样找个好工作不是多大的问题。但到了父母催婚逼嫁的年纪,她也只好将就了。
三
淘了一小碗米放到电饭锅里后,张小鲁拿出两个土豆削皮切片,又切了三个泡椒两根泡豇豆。一个人吃饭,他只需要做一个酸辣土豆片就够了。躺在沙发上看了一会儿手机,电饭锅就跳闸了。他把锅里的饭和菜全部盛在一个不锈钢大碗里,端到客厅沙发上吃起来,若兰是不会回来吃饭的。家里无所事事的日子,让她闲得无聊,她学会了打牌,而且一玩就上了瘾,没有时间给他做饭。最近,经常到了凌晨才回家。
张小鲁吃得满身大汗,肚子更加圆了。他没有开空调,一个人在家没有必要浪费电。再说,屋里比太阳下好多了。洗好锅碗,他就站在阳台上抽烟,目光慵懒地扫描着街面。对面人家的空调都在忙碌着,风机上积了一层黄土。一个月没有下雨,一个月持续高温,人行道上的小叶榕树精神不振,叶子软塌塌的。那条灰黑的柏油马路上面散落着白的红的黄的纸巾、雪糕袋、零食袋,在正午阳光的照射下,像是一片正在烧烤的海带,冒着滋滋的油光。路口那组白色的斑马线僵直地横躺着,脚印、轮胎印为它薄薄地盖了一层阴凉。张小鲁想把烟蒂扔到马路上,他又担心会把那条油滋滋的马路点着了,在阳台瓷砖上使劲地揉了一圈,才扔下了楼。他准备回到客厅,在沙发上睡个午觉。
这时候,他看见住在斑马线左面的杨三娃子从楼梯间下来了,那样子是要到对面的清闲居茶楼去。他穿了一件写满五颜六色字母的T恤衫,黑色西裤笔直坚挺,脚上是一双锃亮的高帮皮鞋。他洗了头,梳着整齐的分头,面容白净。他走路一阵风,衣袂飘飞,风流洒脱。
“手机里一千块钱都没有,潇洒个球。”
张小鲁历来看不起他。那是一个好吃懒做的二流子,除了像女人一样打扮自己,啥也不会干。看人嘛,体体面面的,但口袋比脸还干净,家里乱得像鸡窝。他那个苗条瘦小的老婆经常被他打得鼻青脸肿,很少有人看见她抬起头在大街上走过。
张小鲁见过一次她的脸。那是去年夏天一个下午,他从河边洗澡回来,那个女人端了一盆盐菜到河边去淘洗。他往上走,她往下走,错身而过的时候,女人看了他一眼。一缕头发从她窄瘦的脸上垂下来,半掩了女人的小嘴直鼻,那双眼睛透着半是春水半是桃花一样的忧伤,眼角似乎有一滴清泪随时会掉下来。张小鲁觉得那滴眼泪随时会砸在自己的心上。他故意向她那边撞了一下,女人有些惊慌,向旁边一闪,随即又抬起头來,眼睛里闪现出一丝被挤压的张皇。
杨三娃子并不喜欢那个女人,几乎天天都在清闲居茶楼里混,一日三餐也在茶楼里解决,他和一群年龄大小不一的女人们熟得很,大家都爱拿他开玩笑。再出格的玩笑,他都不生气不发火。他偶尔回家,不是洗头洗澡,就是换一身衣服,再回到茶楼来。张小鲁觉得他唯一的优点就是不抽烟。
小时候,街坊四邻常拿两人说事打趣,说到老实顾家的时候,就拿张小鲁做榜样。说长得俊秀,穿得干净,就拿杨三娃子做榜样。两人从小心里就较着劲,努力把自己的优点发挥得最好最明显。若兰最早是被媒人说给杨三娃子的,若兰倒也没有什么意见,但她父母不同意,认为长得再好看也不能当饭吃,过日子还是要实诚些好。媒人灵机一动,转头又把她说给了张小鲁。若兰有些不情愿,但父母喜欢。从此,两个男人心里又多了一层尴尬和戒备。
路口的斑马线,像一座悬在深渊上的吊桥,桥面高低不平,被惨白的光照得时隐时现,桥下地狱一般幽暗,闪烁着点点磷光。杨三娃子左右看了两眼,才将皮鞋轻轻放到那串白色的木板上,他怕沥青粘到了鞋底上。有一辆小车从他前面闪过,风卷起了衣衫,那桥似乎随着他的步子一左一右摇摆起来。张小鲁心里一阵发紧,生怕他掉进了无底的深渊。可转瞬之后,他又高兴起来。掉下去才好呢,免得看着心烦。
杨三娃子周周正正地走过斑马线,站在人行道上跺了跺脚上的沥青,又向左右看了两眼。看见张小鲁站在阳台上,他把头一扬,就踏进了茶楼升起的卷帘门里。
“神气个啥?马屎外面光,里面一包糠。”张小鲁也把头一扬,向路口吐了一口唾沫。
躺在沙发上,他热得睡不着,若兰吃饭了吗?若兰和杨三娃子说话了吗?他们开的什么玩笑?他一脑子疑惑。
四
火红的太阳落山的时候,张小鲁才把煤拉到砖厂,煤坑前堵着一面厚实的红砖墙,刚出窑的砖还没有来得及转运。张小鲁叹了一口气,只好把大货车停靠在一边,接着跳下了驾驶室。
“好久能搬完?”他生气地嚷了一句。
“估计要到晚上九点多。”
“咋把煤坑堵上了嘛?”
“天热,人手少,搞不过来。”
“搞快点哈。”说完,他给叉车师傅递了一支烟。
砖厂老板不在,他打开车门坐在驾驶室里给他打电话。“今天的煤34吨。”
“多4吨?”
“你要不来看一下。”
“不来了,我晓得了。”
挂掉电话,张小鲁就坐在驾驶室里刷视频。他只好等着,他要把煤卸完,把车开回去,明天早上才好早起去排队。
回到小镇停好车,已经是晚上十点了。张小鲁在楼下看到,客厅里亮着灯,挂在墙上的空调风机呜呜地转个不停。今晚回来得这么早?打开房门,一阵凉意,若兰果然在家。她穿着睡衣,盖着凉被,躺在沙发上看手机。听到门响,她眼睛向上翻了一下,目光从额头上滑过,又穿过蓬松的头发看过来,随即又收回去盯着手机。张小鲁看见她拉着脸不高兴的样子,心里倒是一喜。输了吧?这下可能要歇几天了。
“咋这么晚才回来?”若兰心里似乎有气。
“在砖厂等他们卸煤。”
“往天不是早就回来了吗?”
“煤坑腾不出来。对了,你今晚咋不打牌了?”
“打个铲铲。”
“哪个惹你了?”
“莫哪个。”
张小鲁不再过问。他起身到厨房里转了一圈准备做饭。
“你还没有吃饭?”若兰的话冷冷的,在张小鲁的心里惊起了一阵风。
“你吃了?”
“没有。”
“咋不做饭吃呢?”
“不想做。”
“你想吃啥?”张小鲁转身又向厨房里走去。
“别做了,我们出去吃吧。”
“好吧。”张小鲁犹豫了一下,心里有些凉意。
晚上睡下后,若兰说,今天在茶楼里,那一群娘儿们开玩笑,说他长得黑,像个掏煤的,她简直就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煤堆上。而且经常不在家,两人的夫妻生活肯定不好。不然,结婚都快三年了,她那肚子咋还不见一点动静呢。她们说话露骨,羞得她头都抬不起来,恨不得推倒了牌就走。但赌博场上,她不能这样做,否则以后就没有人跟她同场了。见她不说话,她们就更加放肆了。杨三娃子在另一个房间打牌,若兰有意不跟他同场。他和了牌,上完厕所手都没有洗就跑到她这边来看牌。若兰把牌全部扣了,不让他看。他又指挥她打牌,她偏不听他的,结果让对门糊了自己一个大番。若兰有些生气,说他给别人递眼色,联合起来欺负她。哪知那群娘儿们又拿她取笑,说她和杨三娃子才般配,是天生的一对好夫妻,哪有夫妻胳臂外拐的呢?杨三娃子肯定是真心帮她的。还说,当初她要是同意了杨三娃子,现在就名正言顺了。杨三娃子也嬉皮笑脸地跟她们一起说,如果跟他成了夫妻,他们就是一对革命同志了。说完,他把一只手放在她的肩上拍拍,又把手伸过来,想跟她来个革命同志式的握手。若兰生气,一巴掌打开了他的手,推了牌就走了。
若兰受了欺负,张小鲁觉得自己吃了哑巴亏。但这种事儿,找谁去算账呢?
“输了好多钱?”
“三百多。”
“输了就算了。以后少打吧。”见若兰埋着头不吭气,张小鲁又说:“我多跑一趟车就赚回来了。”
第二天,张小鲁照旧早早醒来了。若兰伸出光溜溜的手臂摸了摸男人壮实的脊背和宽阔的肚腹,偏头又睡了。客厅里的灯亮了一下又灭了,很快,楼下就响起了大货车的响声。
五
天气还是热得像火烤,张小鲁觉得昨晚开空调,一冷一热,中暑加重了一些,浑身烧得发烫,头脑晕乎。车窗外,玉米秸响起一阵焦黄的碎裂声,杨树叶在黑暗中低垂着,张小鲁来得早,抢到了一个好位置,比以前的排位前进了五辆车。他跳下车,来到食堂里,买了一袋方便面,又自己烧了一壶开水泡上。河谷里仍旧没有凉意,他撩起煤迹斑斑的衬衣,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敞露出鼓圆的肚子。
“狗日的张老板,挣了我们这么多钱,连电风扇都舍不得给我们整一个。”
沒人理他,来得早的司机们有的在驾驶室里睡觉,也有的来到彩钢棚里把两张椅子连起来躺在上面补瞌睡,还有的在山南海北地摆龙门阵。
张小鲁把方便面吃得山响,香气四散。躺在椅子上睡觉的人皱了一下鼻子,喉头一声轻响,痰水浓重地咳嗽了一声。
“我看你那个样子,昨晚肯定吃了一顿饱饭嘛。”
“饭都不吃够,哪有劲来挣钱嘛。”张小鲁说完,又要了一包方便面泡上。
湛蓝的天空里铺排着瓦块一样的白云,清澈地笼罩在河谷上。张小鲁望着天空,坐在棚子里悠闲地抽烟。煤厂这面坡还笼罩着一片蓝色阴影的时候,就该他装车了。
“师傅,你负责放煤,我来帮你装车。”
老工人把铁锹交给张小鲁,就爬到索道旁边的小煤车旁坐下了。张小鲁卖力地把他放下来的煤平铺到车厢里,又用铁锹拍打一遍,接着又撒上一层,再拍一遍。
“差不多就行了,别人看见不好。”老工人在小煤车旁边抽烟。张小鲁似乎没有听见他说话。
车厢装满后,张小鲁抬头对老工人说:“再放一车。”
他把那一小车煤均匀地洒开,再把四边的煤往当中赶了赶,又抡起铁锹把三面拍结实,才把铁锹递给老工人。
张小鲁开车到达小镇的时候,太阳还没有把沥青路面照全,靠河边的半边路面黑得似乎要把路面压翻。他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远远地看见了若兰,正向清闲居茶楼的方向走去。她穿了一件淡绿色的连衣裙,脚上的高跟鞋敲打着人行道上的青灰色地砖,苗条的身姿如风一样摆荡着。张小鲁加了一脚油,想上前跟她打个招呼。若兰没有发现张小鲁的车在身后,每天经过小镇的拉煤车多得让人熟视无睹。她看了一眼手机,又向公路对面看了看,继续往前走。来到斑马线的时候,她站在那里盯着手机,手指飞快地打着字。杨三娃子从楼梯上走下来,妖娆地向路口走来。若兰向对面看了一眼,脸上荡漾着一圈笑意,随即头一扬,快步向茶楼走了上去。杨三娃子也快步走过斑马线,把一座吊桥踩得左摇右晃。张小鲁加了一脚油,货车轰隆隆地叫了起来,向前窜了一下,轮胎在软软的路面滑了一步,车身晃动了两下,把散碎的煤洒到了路面上。张小鲁本能地踩了一下刹车,向右打了一下方向,又赶紧向左边打了一点方向。杨三娃子飞身向人行道上跳去的时候,庞大的车身就从斑马线上碾了过去。
张小鲁觉得自己烧得越来越迷糊了。
六
小镇来了一车警察。烈日下,全镇男女老少都出动了,把桥头路口拥得密不透光。漆黑的沥青路面更黑更重了,各式各样的鞋子掩盖了斑马线,掩盖了那座悬挂在深渊上的白板吊桥。
“让开,让开……”
警察一边轰赶着人群,一边拉起了警戒线,把一张薄薄的灰色床单覆盖的杨三娃子和一大摊乌红的血迹圈了起来。
“谁是车主?”
张小鲁赶紧跑上前去,“我是。”
“把证件拿出来。”
“在车上。我去拿。”张小鲁趴在车上,高高地撅着肥硕的屁股。
“说一下情况。”警察大檐帽下有一张鲜红的嘴,一口细密的白牙,上唇一抹淡青色。但字语清晰威严。
张小鲁简单陈述了事情的经过。这段时间,天气太热,把沥青路面晒软了,轮胎有点打滑。晓得这个情况,自己开车很小心,尤其是过场镇街道的时候,是小心了又小心,生怕出了事。事情怪就怪在,越小心越出事。这几天拉煤的人少,装好煤他还在河边休息了半个小时,洗了一个澡,抽了两支烟,整个人就感觉到很凉快。
“说重点。”
“我把车开到小镇的时候,就快要吃午饭了。我开得很慢,很小心。路面打滑,我不敢开快了。快要到这个路口的时候,我看见杨三娃子穿着一件五颜六色字母的T恤衫正在过斑马线,他想到对面的茶楼去打牌。我又不敢踩刹车,就使劲按了一下喇叭,我想提醒他有车。他转头看见我的车来了,还向我笑了一下,像是在给我打招呼。我们是街坊邻居,从小就认识。我又按了一下喇叭,示意让他快点走过去。哪个晓得,他又转身往回走,我又不敢刹车,就把方向盘往右打了半圈。可能他觉得跑回对面要远些,又折身往右边跑过来。我看见他跳起来想跳到人行道上去,可是来不及了。他被撞出三米多远,轻飘飘地落到了地上。眼看就要碾上他了,我又赶紧往左打方向,车子就冲进了那间商店里,右后轮胎就把杨三娃子扫上了。你看,车上的煤洒得到处都是,杨三娃子都埋进了煤堆里,证明我是采取了紧急避险措施的。但是,我们把他掏出来的时候,他就断了气。我吓慌了,还是他们提醒我,我才赶紧报了警也报了保险。”
“还有其他事情没有?”
“没有。”
事故发生后,那个懦弱的小女人把街面上的门面腾空,搭起了灵棚,又请人买了一副棺材装殓了残缺不全的尸首。张小鲁从派出所回来后,先和女人谈妥了赔偿事宜,又帮助女人把杨三娃子送上了山。小镇很快又恢复往日的宁静,只是若兰这段时间一直没有出去打牌,天天躲在空调屋里发怔,依然不买菜不做饭。张小鲁偶尔回来做好了饭叫她,她总说不饿,像丢了魂一样,人也瘦得肩胛窝能养金鱼。喊她睡觉,她也不睡,张小鲁就把她抱到床上躺下,但她整夜都睡不踏实,嘴里含混地嘀咕着什么。
警察出具了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张小鲁承担百分之六十的责任,杨三娃子承担百分之四十的责任,死亡赔偿可以参照这个比例。但是,张小鲁已经和那个女人谈妥了,他几乎承担了全部责任的赔偿。保险公司赔付了大部分,剩下20万元还需要张小鲁自己承担。张小鲁从银行里取出了10万元现金,又找人借了10万元送到对面女人的家里。
若兰仍是一副精神不振的样子,张小鲁照常出车,回家后还是小心照顾着她。晚上,张小鲁关切地问:“吓着你了?”若兰摇了摇头,张小鲁一声叹息。
“若兰,我们结婚已经两年多了,你跟着我受苦了。我没有别的本事,只会开车。我给不了你想要的生活。这次出事后,家里还要挣钱还账,往后的日子可能更加艰难。要不,我们离婚吧。我不能拖累了你……”
若兰怔怔地听着。
“以后你就可以去追求你想要的生活了。”
若兰哭出了声。
“好在我们还没有孩子。只要你同意,我们可以协议离婚。”
若兰倒伏在沙发上,裸露的肩背不停地抽动着。
“我们不争不吵,自愿离婚,办理起来快。”
若兰眼中泪水无声地滑落下来。
第二天早上,若兰收拾了一个行李箱,坐上了一辆长途车走了。小镇上的人都说,张小鲁扛得起事情,对若兰也好,是一条汉子。
晚上,張小鲁回家,站在阳台上抽着烟。暗蓝色的天空中云影飞动,月光下的沥青路面一片漆黑,路口的斑马线时隐时现,仍像是挂在深渊之上的一座吊桥。公路对面,杨三娃子的家里灯光昏暗,粉色的窗帘拉上了,上面固定着一个女人的身影。张小鲁看见,那身影低着头,脸庞窄瘦,小嘴直鼻,神态忧伤,像春天里粉色的桃花雨砸在自己的心上。
【作者简介】马希荣,生于1973年,四川通江人;作品发表于《青年作家》《草原》等刊;著有报告文学集《村上一棵树》;现居四川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