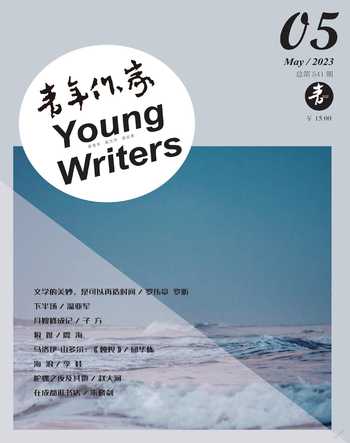下 山
李娃
一
仲夏的一个傍晚,人們围坐在屠夫家的小院里闲谈。屠夫的朋友问屠夫:“你那徒弟,什么时节下得山去啊?”朋友一边说,一边打着哈哈。
“莫说是我徒弟,我能有这号徒弟?莫烂了我的名声!”屠夫愤愤不平地应道,“跟在边上四五年了,昨日第一回拿点血刀。把猪架上屠凳,他的手打起了颤,钩子挂了几回才挂到那畜牲的下颌上。他的刀尖子尽戳到喉嗓上,那畜牲都起了躁(跳跃起来),他一脸死相。(我)对着他喊:‘扎啊,扎啊!他还是不动,像是被定了身一般。(我)又喊:‘你快来按着,我来杀!他鼓着眼珠子望直了,嘴巴里蹦出句:‘算了吧!——算了,那畜牲一蹿就起来了,撞得他刀一摔,差一点就飙(快速地刺)到老子的心口上!”
屠夫的妹妹接话说:“他给你拖尾、剐蹄、氽血、洗屠圈,做了这么多事,起先不是不要钱的吗?旧年就收十块钱一回了,师不师徒不徒的——总会有他嫌钱少的日子。”
“他叫什么?好大的年纪啊?”屠夫家新过门的弟媳突然出了声。她还很年轻,看什么都新鲜,在城里生长,家境富裕,经历的世事远比读的书要少,一脑门子稀奇古怪的想法。
屠夫娘说:“都喊他细妹子的……”
“呃!”朋友下意识地嚷了一声。一个男人打开了小院的栅栏门,目不斜视,伸直了脖颈往堂屋奔来。武短身材,赭褐油亮的肤色,像渍泡在酱缸里的人。一颗剃得能见到头皮的溜光的脑袋往前突着。狭眼睛,眼角耸拉,笑从下颌努力往上推,推到眼眶下边便推不动了。
“吃茶吗?”屠夫娘正在捣姜煎茶,男人嘿嘿地笑出声来,把一个塑料袋子放在凉棚下的立柱边,从袋子里掏出一只玻璃瓶子来。“啊呀,你是在哪里做了官了?不睬人了!”屠夫妹妹朝他喊道。他不做声,放了瓶子,转身就走。他从人们的眼皮底下溜过去,栅栏门外,他回过身,伸手去够内侧的门栓。“你走,你走……”屠夫妹妹朝他叫了起来,霍地挥了下手。屠夫也在朝他挥手。他像是被骇到,忙地把手缩了回去,嘿嘿地笑。
“他家在哪里啊?”弟媳问道。
“光身一个人。一个爹,死了有三十年了;一个娘,云里雾里的。一个姐姐,十八岁嫁到外乡,姐夫打工一年到头不回来,两头不走动,这样的人,还有什么家?”屠夫的妹妹说道,“爱赌钱,罩青蛙、摸泥鳅、捉黄鳝,那就是好手喽,得个钱就丢个在牌桌上,又好吃酒,横竖没人管的。”
“他为什么不成个家呢?”弟媳又问道。那位朋友指着屠夫对她说:“问他师傅,什么时候他下得山去,就成得了家了。”屠夫呸了一口,鬼师傅!人们哄笑起来。
二
一阵嗷叫惊起,新媳醒来。
叫声愈往后愈锋利,濒死的猪,嚎出“我啊”“我啊”,仿佛它就是个人了。哀鸣声声穿墙而来,在暗黑的顶端吊出一个灰白色的旋涡。年轻的女人睁眼看着,夜深处,灰白旋涡,归于沉寂。
女人走向了屠场。茅房连着猪圈,之间的一块平坦处,殷红的血四下流,曲曲折折都往墙角一块方砖大小的开口汇聚,淌向外头去。腥气臭味扑打过来,死去的猪侧在铁制的屠凳上,地下两个人,一人立着,一人蹲着,立着的是屠夫,蹲着的那个,是不被屠夫承认的徒弟。他们各自裸露着的身体,都在腾腾的雾气里——屠场的一个盛满滚水的木盆里血色淋漓,几截猪腿泡在盆里。
女人走过去,徒弟起身,向她哈着腰,往下拉出长尖角的凸囊囊的膛,一条洗得半红半白的化纤内裤勉强叉在那里。女人面无表情地说:“在杀猪啊?”
“嘿嘿,在杀猪呢。”徒弟咧开嘴笑,像一位殷勤的主人招呼突然登门的客人。他盯着她看,些许难堪都没有。他在逢迎她。屠夫骂了一句,模糊得很。女人听到嚓嚓的声音,那是皮肉分离时所发出的。屠夫手里有一把短刀,刀尖游在红白处,剔剥下来的那层皮子绷在猪身与人掌间,微微地颤。
“那是剐皮……”徒弟对女人说道,一边收了笑,抬起了下巴。他在为他的解说感到得意——屠场是他的地盘。
“你蛮骜(很厉害,很出色)嗒——那你来剐不咯?”屠夫喝斥道。徒弟像是被唬住了,呆了一下,勾了背,重又蹲下身去。
“杀猪?你杀得了么?你倒是杀头猪给我看下啊?”屠夫停了手,斜眼看着徒弟。徒弟不自觉地挪动双脚,越挪越近,整个身子蜷成一团。屠夫接着把短刀一撂,从身边的一个圆木凳上抄起一把尖利的长刀来,朝他举着:“看,这个你敢拿么?”
屠夫像尊神像。
徒弟看了一眼高高扬起的那把点血刀,旋即回过身,从木盆里捞起一截猪腿揉搓起来。他搓得着急,手掌和臂肘都在微微地颤,像是花了很大的气力。
“昨日你是吃了几口猫尿才夸口跟我说能杀的?崽啊崽,老子一条命差一点儿送到你手里!你就啜(骗)得了老子一回喽……还敢到外头讲跟着老子学徒弟,老子是能一手杀猪一手接血的,有几个做得到?你莫败了老子的名声!”屠夫越说越从容了。
女人蹲在茅厕。屠夫梆硬的声音撞着她眼前的一扇薄门板,像磕了一地的玻璃渣子。“我没有再讲过了……”徒弟终于说起话来,他说话,总是从第一个字开始,音量逐渐往下落,落到最后便听不见。屠夫没有声响,应该是一心对付那张他引以为傲的猪皮去了。
女人看到脚边,一只蛆横在灰扑扑的厕坑木板上,头尾胡乱地左右伸突,又做折滚,盲目仓皇。厕坑里头白花花的一群群,紧迫压塌,争相往浮起高处的秽物上爬,每一块高处都是扑探卷曲延宕踯躅。她的双脚麻了。
女人经过时,徒弟悄声说:“下不得手呢……”不迟不早,说在她的脚边。她低头看他,他用一个小工具在刨刮猪蹄,像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他是特地说给她听的,她假装没有听到。
一个不得志的学徒,人近中年,被人像小孩子那般叫唤,偏偏对一个陌生的女人带着家犬似的亲近。因她是个外人?因她生了个好看的相貌?两个几乎裸全了的男人,令女人有些慌,还有羞涩。可女人认为做出羞怯的举止是失礼的,也就装作不懂得。回到屠夫家的客床上,女人开始了她的浮想。
天光了,屠场离开了人,重回原样。蛆虫还在,屠事的痕跡一干二净。
三
夏末,屠夫支了一张小床,徒弟从此夜宿于此。
午后,女人独自睡在客床上。她听到声响,呼吸声,像是沉重的叹息,像是动物的喘息,一声一声。她想,是个男人。一个男人,就在近前。她屏息等待,时间从她的耳廓的血管里流过,呼,呼,呼。时间的声音是血流一样的声音,呼吸一样的声音。她猜想,是那徒弟吧?她一动不动,其实是不知如何是好。揣了忍气吞声的心情,她装作不知晓。
屠夫娘进门,招呼了一声:“细妹子啊,什么时候来的?”顿了一下,又唤女人起床。屠夫娘走了出去,那人还在屋里。屠夫娘又喊了他一声。
女人在屋檐下见到了徒弟,他与屠夫娘说话,并不拿眼看她。屠夫娘将徒弟指给女人,说他比东子(她丈夫的昵称)大五岁,她微笑着对他说:“细哥。”他张着嘴,像是被她吓了一跳的样子。她的客气,是理所当然的事,他却如此惊慌。她很意外,莫名惹出心底的那一点戚戚然。
屠夫娘说:“把猪脑壳剥了喽,给你师傅那边送过去吧。”凉棚底下,一道满是油渍的横梁,那里悬挂着一颗孤零零的猪头。猪的双眼,塌陷隐没。那颗头,扇子一样开着,凝固了的黑色血痂子贴在白森森的稀碎骨头上。
徒弟定定地看着那颗头,忽地直了一下背脊,头颈跟着昂了一下,像只久蜷的猫猛地撑起它的爪子。他把头慢悠悠地转过来,用一种心照不宣的眼神看向女人。屠夫娘似嗔似哄地呶起嘴来,说:“哦?”他把头转了过去,嘴角扬起一丝莫名的快意,伸手摩挲着他的那条粗壮的颈根子。接着,他默不作声地往前走,很快便走出了院子。
“教他做人都不做,怎么出得来?”屠夫娘叹息地说道。女人思忖,这个“出来”,说的是不是出师“下山”的意思。恍惚便记起他看她的那个眼神,还有她叫他时,他把眉眼低下来,讪讪地笑,那暗自欢喜的样子。尘世凉薄,没被好好对待过的人,得了一点点的好,便受宠若惊甘之如饴。女人有过职场的挫败,自知冷暖。还有她进不去的圈子。女人跟徒弟,实在很像。
四
小院里来了客人,两个熟客,一个生客。熟客们坐在院中央的靠背椅上,面生的老妇,蹲坐在堂屋外的阶沿。老妇双手攥着一根扁担,扁担的一头杵在地面上,就像随时准备倚仗它站起身似的。屠夫娘在煎茶,熟客们争相寒暄,老妇只在张望。女人望到老妇,老妇一笑,神色紧张。老妇的头极小,门齿缺了,皱纹纵横的脸如同一只豁了口的核桃。
女人问老妇:“您没有喝茶吗?”一位熟客说:“她不吃,你婆婆问了,她不吃的。”女人兀自将手里的那碗茶递了过去,老妇不接,攥着扁担的手指蜷曲了起来,只是憨笑。另一位熟客劝说道:“快接啊,吃啊。”老妇放开扁担,用双手托了,小心翼翼,有几分的虔诚。女人柔声道:“您慢慢的,不要烫了。”老妇下意识地将那碗茶托高了一点,喃喃地说:“嗯……”又抖抖索索地说:“哦……”老妇看着女人,眼里跳出两团小小的光。
屠夫娘说起老妇送来了马齿苋,就着露水扯下的,东西就码在了屋檐下的墙脚边。老妇就是徒弟的娘。女人忙道谢,老妇连声说:“没啊,没啊……”老妇很惊讶,还有一丝惊慌。女人记得听人说起过,老妇脑子有病,不禁悄悄地甄察着。
把茶吃过,老妇起身交还茶碗,挑上一对空竹篮走出小院,举止未有异常。“他娘不是有精神病吗?”女人疑惑地问道。人们摇了摇头,一个熟客说:“那样的崽,一世出不得声。”原来所谓的病,是他的没出息啊,她恍然,点了点头。
屠夫娘跟女人说,之前曾跟老妇说起马齿苋是她最喜欢的一道菜,又告知过老妇,她今天会从城里过来。老妇的家离此二十多里,靠着一双脚走来的。女人很奇怪,她与老妇并不相识,怎会如此特意。“你是喊他‘哥的人,他娘老子总要有点表示嘛……”屠夫娘呵呵地笑起来。屠夫娘的笑声使她暗生鄙夷。市侩、功利,凡此种种,她都看不起。
五
秋分后,再见面时,女人又叫了徒弟一声“细哥”。屠夫听到这声儿,将脸摇向背后,眼角一挑。女人的神情持重,对于屠夫便是一种警告。她不会漠视这个人,也不会轻贱他。屠夫立马收了那满是不屑的眼神。这番暗涌,徒弟自是感触不到。他亦步亦趋地跟着屠夫,探着脑袋,目不斜视地往前走,眼眶底下堆着笑。他径直走到凉棚底下,停住,躬下身子,往地上的那只玻璃瓶看。就是上回他来时,带来的那只瓶子。当时屠夫和妹妹驱赶着他,他连栅栏门都没敢拴。
屠夫叫了,徒弟不答应,只在自言自语道:“换水了吗?晓得长得大吗?”屠夫又喊了一声,他立起身,突然扭过头来看着女人,嘿地一笑。这一笑,显得很得意。因为屠夫要留他吃饭。这是从未有过的事。
“吃啊,吃啊……”饭桌前,屠夫用筷子指着菜碗说话。徒弟撒开了两个膀子,端着饭碗扒了两大口,把碗放在桌面上,细细地嚼。黄鳝、小龙虾、刁子鱼。屠夫开了一瓶酒,一人一杯。吃啊,吃啊,屠夫又说。徒弟慢条斯理地点着头。他咀着咂着,腊黄脸偏着,露出微醺的神色。
“吃得好吧?”屠夫拿眼瞟了瞟。徒弟抿了口酒在嘴里,抬了一下眉头。“我跟你讲,杀猪跟搞女人一个样,都是看有胆还是没胆,”屠夫黠笑道:“你搞过女人没?”徒弟吸了一下鼻子,呵地笑,头昂起来,说搞过。屠夫斜过眼去,嘴歪向一边:“搞过?老子是十六岁就拿点血刀的!没个胆,想都莫想!还搞过!”
“三三!”徒弟吐了口气似的说出一个名字。
“蕌头三三?说的像真的一样……”屠夫满是怀疑。
“我那天从她屋过身,她把瓜子壳吐到我的脚面上。”徒弟说着,跺了跺脚,用力地点了一下头。
“那长子(指特别高瘦的人),一脸的锅铁(指皮肤黑),像坨紫皮藠头,”屠夫很是不屑地说道,“你踮脚站着,还不齐她的下颌高!她男人瘫了那么些年,看不把你当马骑!”
徒弟愣愣地看着屠夫,似是寻找答复的话。屠夫哼了一声,掷了筷子,起身就走。徒弟从嘴里理出一根小小的刺,用指头捻了,粘在桌面上,把它粘牢了,端起酒杯,抿一口酒。
屠夫家的饭,屠夫娘是不上桌的,早就过了时的老传统,屠夫娘还在遵循着。一张桌子,就女人和两个男人。男人们并不与她说话,男人们的话,女人只听着。屠夫离席后,女人很快也离开了。屠夫站在屋檐下,见女人出来,问她有没吃饱,这是客套话。女人笑了一下。她不想跟屠夫有多的话说。
离开饭桌前,女人郑重地对徒弟说了声:“慢吃啊……”他微微地点了一下头。徒弟只有在女人的面前,才不把笑堆在眼眶底下。她像是他多年的故交,多余的话,不需要。女人不介意他表现出来这种随意,这使她感受到属于她的善良和宽容。
徒弟把屠夫家的饭吃成了独席,他走时连招呼都没跟女人打,离去的背影里,一种得胜的风姿。半晌之后,屠夫妹妹嚷嚷着进门,说见到那人坐在了街头卖爆竹的兰姑家前头,撩起一双脚杆,架着脑壳跟人讲,师傅请他家里吃饭,师傅还亲自滗酒给他吃。街坊都是明白人,都说他扯谎。他还把兰姑的孙子喊到身边,说起杀猪的事,兰姑骂他死了血(没羞耻),谁认过他是徒弟,莫教坏人家的人。
“这样说他,他会心里难过吧?”女人问道。
“咳,他啊,趋着兰姑一味地说:‘那是的,那是的……颠着他的脑壳,提着一张脸,就是那样地笑——他晓得什么难过喽?”屠夫妹妹答得满不在乎,细微地啐了一声,“今日吃的,都是他抓来的,大大(指屠夫)是不得收钱的喽。”
屠夫留他吃饭的原因就在于此。女人抿了一下嘴,想着徒弟得意的那个时刻。
六
立冬这天,徒弟蹲在屠夫家门口的一堆鹅卵石前。女人隔着栅栏门看着他。徒弟随手捏起一颗小卵石,把它抛往空中,在这小石子尚未落地的时候,又用同一只手抓取另一颗石子,然后飞快地翻过手掌来,接住刚才抛往空中的那一颗。他的手里有了两颗小石子。女人不禁瞪大了眼睛。徒弟又重复了上述的动作,直到他的手掌里同时出现四颗石子。在女人的孩童时代,也曾玩过这样的游戏。她静静地看着他,好在他没有接住第五颗。他扔了那些石子,游戏结束了。
女人等着徒弟开始新一轮的游戏。徒弟的嘴里念念有词,听声韵,应该是童谣。嗓音低微,她听不清楚。女人很稀奇,她从不知道,这个游戏还有歌谣。她问:“细哥,你在念什么?这个还有口訣的吗?”
徒弟睃了她一眼,站了起来,把手里的一颗小石头扔回卵石堆里。他不说话,也不急着离开,低下头,一直站在那里。女人犹豫了一下,问他要不要坐坐,他就往屋里去了。
屋里除了女人,没有别人。徒弟在她关上纱门的那一刻,一把拉住了门栓。
“细哥会抓鱼,这也是一个本事呢。”女人说道。徒弟呵呵地笑,拿他那双猫样的黄眼珠看着她,信任而又适意地看着。从捉鱼的方法谈到需要注意的方方面面,女人发现,徒弟原本是很能说的,并非口拙之人。
徒弟边说边微微地点头,女人的每一个反应都合乎了他的心意。世上的人分两种,有话说的,没话说的。恰巧女人是让他有话要说的人。然而,事实上,女人没料到徒弟有这么多的话。她的微笑、偶尔的点头、间或的哦与嗯,先是应付,再是敷衍。渐渐地,她就不耐烦了,只是不好意思打断他。终于女人想了个法子,问了他一句别的,但凡机灵点,都知道上个话题应该结束了。可他应了一声,又兀自将她打断的话头续上。
女人托着腮,想着一些杂七杂八的事,徒弟的声音,被她屏蔽了。女人从包里掏出一本书来,翻动起其中的张页。女人的书,跟她的工作毫无关系,从来形式大于内容,多数是做做样子。有时女人也跟旁人说说书里的字句,至于对方感不感兴趣,她是不在意的。她做这些旁人不做的事,倒也不是虚荣,只是这么做了,她才心安。她常常莫名地惶恐,时有漂泊无依的错觉,一点儿风吹草动就能惊扰许久。可她只在她的心里兵荒马乱。
“细哥,你怎么怕杀猪呢?”女人突然想起什么似的,抬起头来,认真地问他。她确实是好奇的。
徒弟懵怔住,哑巴似的看着女人。“也不是怕,看不得那个眼睛……”他艰难地说道。他的眼神僵直。一种复杂的表情在他的脸上漫开,疼痛的愧疚的或者怜悯的。女人发觉了自己的唐突,不知如何是好,就不再说话了。
徒弟走的时候,女人还在看书。他轻手轻脚地出去,在门外留了个声音,还是那句:“换水了没?晓得能长大吗?”没人回应,他又在自言自语。
四下无人,女人站在凉棚下,看着棚柱根的那只玻璃罐,里边有只乌龟,不及婴儿的手掌大。是徒弟捉来的。他常常去看这只瓶子,当着人们的面去看。她想起他的本事。从头到尾,他就想让人知道,他有本事。
七
除夕的白日,女人站在小菜园里。
菜地的小河边,一道陡直的土坎上,长着一溜的灌木,当中还有一株柑子树,树杈间挑着几个果子。女人指着那里,对身边的丈夫说:“啊,看那个,真想摘下来啊。”丈夫认为摘不到,她跑到了土坎边,仰头看树,向那些果子伸出手臂去。她的双臂向空中捞着,咯咯地笑。这不过是她的一个玩笑。
忽地一阵扑簌簌的声响,徒弟站在了树杈上,冲女人喊:“摘得到,摘得到的……”他往上攀缘,像只猴子。
女人担心徒弟摔下来,为了几个不值钱的柑子,惹上一场祸事,对他说快下来快下来,我不要的。他攀得更快了。摘下一个,朝她喊,让开一点,接着把一个柑子掷到她的脚边,接着是第二个、第三个……最后的那个,他朝她扬了一下,那是一树柑子里最大的一个。他攥在手里滑下了树,没有向她抛掷。她拾了地上的几个柑子,一抬头已不见他,她还想等一会儿,丈夫说回去吧。
出了园子,徒弟站在栅栏门前,把手向女人伸过来,他的掌心摊开,正是那只最大的柑子:“这个给你,怕丢烂了……”她的手腾不出空,他将它叠放在了她捧着的那几个小柑子上。她向他道谢,他看着她,他的眼球好像不会转动了。丈夫说:“走吧。”
丈夫不曾招呼徒弟,或者觉得尴尬,转过身,笑了一下。走出几步,丈夫沉下声对女人说:“莫那么贤惠,那个人,尽做些不该做的。”女人发觉到了异样。她分明认为,刚才那双盯着她的眼睛,是单纯的。她总是后知后觉。
暮色里,远近鞭炮在响。小孩子拿出自家的散碎烟花去小院里放。花花绿绿,噼噼啪啪。一个孩子发出尖利的声音:“鬼啊,鬼!”几个孩子跑进屋来。人们赶忙吐着口水,这是山南的古老仪式,常常用以消解不吉的话。是徒弟。他悄无声息地站在栅栏门外,黑咕隆咚的,像鬼一样。屠夫妹妹说他竟不会道个恭喜,屠夫说,骂你都轻了!屠夫娘碎碎念着,小童之言,百无禁忌,小童之言,百无禁忌。女人说:“细哥,你进来坐吗?”一时再没人说话了。他,不可能坐在人们身边,一起围炉向火,谈南山说北海。
徒弟走后,小孩子们又在放炮,人们又在看电视聊天。都在做着每个年节里完全相同的事。零点过去,岁是不用守的,人们各自归家。丈夫上床歇息了,女人跟屠夫娘坐在火炉边,隐约听到有人在喊。那人压低了嗓子,喊着:“诶,诶……”
女人听出是徒弟的声音。她走出去,走到栅栏边,问他:“细哥,你是在叫我吗?”他嘿嘿地笑。屠夫娘挨着女人,问他:“你进来吗?刚才要是喊了声恭喜,他们不得说你,就让你进来了嘛。”屠夫娘一直用手抓着栅栏门,却并不是开门的意思。他说不了,不了。莫傻着喝酒,莫跟那些鬼人耍,屠夫娘念叨道。他只看着女人笑着,女人依然觉得他那不会转动的眼睛是赤诚的。
“你要学会杀猪……”女人突然说道。他噎住了似的,上身抖了一下,像打了一个寒噤,背是佝偻的。“那是,那是!”他又笑了起来。屠夫娘轻轻地撞了一下女人的背,是在提醒她,这话说得不该,不恰当。徒弟看着女人憨笑着。
回屋时,屠夫娘对女人说,莫跟他开玩笑,那个人,开不得玩笑。女人也很纳闷,不知为何会不假思索地对那人说出那句话。到底算是同情还是祝福?那人穿着一条破旧的内裤,朝她笑着的那个样子,被她给记了起来,她的心头有东西在蠕动,是蛆虫吧?她奇怪那些恶心的事物为何会被一再地记起,这让她感觉很不舒服。
八
大年初七,屠夫娘生日。女人等在小菜园前,等着她的双亲,他们要来给亲家祝寿。徒弟在小河边帮屠夫娘挑水。女人瞥见他时,想起屠夫娘说过,河边上那块垫脚的石板松了。她朝他喊道:“你稳当些啊……”他发了愣,肩膀上一对木桶像是担不起来了,脖颈愈发前倾,腿脚也不利索,迈不大开似的。
车抵院前,徒弟凑上车门口,伸手做出搀扶的样子。女人的父亲摆开了手,母亲任他搀着,又拿好奇的眼光看着他,听他说了句什么,就笑了一下。
席间,徒弟嘬着嘴,端了一杯酒,跟在屠夫与女人丈夫身后。一个客人用筷子指着屠夫,眉开眼笑地打起趣来:“好,这酒敬得好嘞——师徒兄弟,就是恩婆(母亲,指亲生的)兄弟一样的……”屠夫回过头,皱起眉,在徒弟的肩头搡了一把,嚷道:“走开些,去吃你的酒去吧!”徒弟脸上的笑塌了下来,下意识捂着手里的酒。他又想去喝那杯酒,酒在他手里嘴前微微地抖。接着他就笑了起来,那笑依旧堆在眼眶底下。
宴席结束,女人在酒楼边的拐角见到徒弟。他半张着嘴,她朝他微笑起来,他别过头,走开了。人们都在送别她的父母,他看得见的。宴席开始之前,女人的母亲就在嘀咕,那人过来搀扶时,咧咧地说道:“你老人家就像是我亲娘老子一样。”这说法,太离谱了,除了笑一笑,不知怎么回应他。母亲还说,那个人,脑子有毛病,离他远一些。丈夫也说过,莫再那么贤惠,那个人,尽做些不该做的。可女人还是对他做出了微笑。他扭头就走的样子,令她十分不快。
女人想着应该做出些样子给徒弟看。然而春天一过去,徒弟的小床被拆掉了。听说他去了村头新开的砖厂工作,工资月八百。他不会再来了,人们都这么说。可就在一个午后,他又推开栅栏门走了进来。女人不唤他了,他还是看着她,喉咙底下咕哝着。人们开始嗤笑起来,屠夫嚷道:“赚大钱了呢,怎么还想到回来?”他唧哝了一句,声太小,没人听清。
他蹲在台阶上,伸长了手臂,拨弄着新买的一个廉价的手机,一只手里同时还握了一包尚未开封的白沙烟。屠夫的侄儿,十六岁的少年人,摸着鼻子问他:“你的手机是‘苹果的吧?‘苹果几啊?”他的头半仰着,一脸愕然。屠夫妹妹掩口笑。屠夫的朋友说:“烟也换了哒,抽上‘精白沙了啊?”他“嗯”了一声,低头握紧了他手心里的那包烟。屠夫笑着问道:“还新置了业呐——手机也是牌桌上赢的?那(么)堂客也讨到手了吧?这下敢(杀猪)了不?”他骤然抬头,黄眼球突起,音量拔高了:“这是,呃……”他不服氣,又想分辩,但他还像从前一样,没有把话说完,也不敢把目光落到屠夫的身上。他把手机和烟收回口袋里,直愣愣地看着她。他看她看得恳切,信任又依恋,好像她是他的援兵,使得人们都在看向她。
屠夫的朋友笑呵呵地问女人:“你看,他这是拜的什么师?”女人大声说:“他不敢,他没得那个胆!”她像人们那样发出大笑的声音。徒弟走出栅栏门外,并没有再看向她。可她觉得,他一直在看着她。她终于做出了该有的样子,从寿宴那天,他对她扭头的那刻起,她就决定好了。
“你这一世,让他给折磨了!”屠夫的朋友拍了拍手说道。“啊,这一世,被他害了!”屠夫把头点了一下。人们大笑着。
九
秋风起,女人在屠夫家的客床上睡着了。听说徒弟拿到了低保,政府把他那间快要垮掉的房子也已经重建好,他开始享福了。还听说,他的腿断了。半夜捉鱼,从桥头栽下去,折一条腿,万幸了。女人好久没来了,徒弟也再没来过。
女人听到窸窸窣窣的声响,屠夫娘怕吵醒她。猪该喂食了。她闻到猪食煮熟了的气味。徒弟来了。他从门外轻轻地走过,径直去了屠场。踩在潮湿的稻草上,猪的四个蹄子踩过的,猪的八对奶子压过的,猪的长嘴拱过的,猪就是在这些稻草上走向末路的。他把手放在猪圈的水泥围栏上,有头猪,在他拖它的时候,腾地立起,把一双前蹄搭到了这围栏上头。他拖它的一只后蹄,它嗷嗷地叫,他拖它不动。屠夫操起它的一只前蹄,它还是死死地攀在栏杆上。他们抓着它的两只前蹄用力拽,屠夫的铁钩子钩住它的咽喉,它跌下来,他们将它往屠场拖。他感觉他们是在拖一个人。
铁钩子钩在它的咽喉,它的头啪啪地甩,不像是头猪,猪只会往后退。钩子陷到肉里,他扯它的尾巴扯它的一只后蹄,猪就没了挣脱的劲头。猪侧身上了屠凳,他臂肘子压在后臀尖尖上,说时迟,那时快,屠夫的点血刀嗖地扎穿了血管,血往前冲,哗哗地打到屠凳前的接血盆里,像一股子又腥又烫的红色自来水。盆里放了水,水里放了盐,屠夫的点血刀早早在水里拨动过,像鸭鹅的脚掌拨清波。猪抽动几下,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猪的声儿早哑了火,猪的宿命,是一个黑黝黝的悬崖,不见底。屠夫在悬崖底下接住它,烫了毛,厚墩墩的肉身子抖啊抖。一把小弯刀,剜去了尾巴。皮肉分离了,身首分离了,一堆内脏。猪应该是这个样子。猪没有眼神做给人。然而那头猪,它在看着屠夫,看着他,啪啪地甩着头,一下看屠夫,一下看他。啊哦啊哦,它在叫,像是人在叫疼那样,啊哟啊哟——它噗地一下两只前蹄弯折落地,头往下磕,像个人在跪地祈求。屠夫钩子一提,一伸手,点血刀扎进了它的咽喉,拉盆,接血,屠夫咬着牙说:“今天你是个鬼,我也把你给杀喽!”屠夫是凶神,是恶煞,它是一个人。它在悬崖上苦苦哀求过,徒弟看到它的眼睛,不是惊慌,不是恐惧,它是不可思议,是舍不得,是放不下,是无可奈何。女人问他怎么怕杀猪,他说他怕看猪的眼睛,其实他也怕看人的眼睛。
徒弟从屠场走出来,他的手摸到了纱门的门把手,门吱地开了,徒弟的手摸到虚掩的房门的门把手,啊,呃,呃,房门一截一截地开了。年轻的女人就在他的眼前,一团身子侧躺着,肩在那里,臀在那里,被子把她的身子半露半藏,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她跟他这么说过一句诗,再没有人像她那样跟他说过话。女人的耳朵红通通的,毛茸茸的鬓发,毛茸茸的额发。他趋近些,他闻到了女人的香气,熏熏的,软软的,一点点的甜。她打香水。正经女人是不打香水的,不正经的女人不会用她这号香水。女人的气味,蜜里调了油。徒弟长长地吸了一口气。藠头三三,在门口嗑瓜子,把瓜子皮吐到他的脚上。长身子,高出他半头,一张长脸,黑红色,像只紫皮藠头。三三反身压上去,骑着他,像骑一匹马,他甩她不脱。“没个胆,想都莫想!”屠夫的话是天边的一个雷,远远地滚过来,轰地在他的耳边炸开。
徒弟把手伸向女人的耳朵,挨到了,像过电一样,他的手指一麻,麻酥酥的滋味从他的小臂瞬间传到隐秘的角落。女人跟女人是不同的。年轻的女人一动不动,他的手在那只耳朵上压下去,手指插到她的肩窝,热哄哄的。刹那间,他膨胀起来。手里的肉身子开始颤动,颤动在一瞬间变成了震动,他的手被震开。“你在做什么!”女人瞪大了眼睛看着他。他是噩梦,也是噩梦之外的另一个噩梦。他不说话,定定地看着她。
“走开些!”女人朝他喊道。她愤怒,她厌恶。他扯开了被子,啊——她叫了起来。她还喊了一句话,他听不清楚。他拽着她,往屠场拖。她落在地上,双腿扑打着地面,一个劲儿地扭。屠夫说,有人杀一头猪,那猪从屠凳上蹿了起来,从屠场跑了出去,一边跑,一边叫,跑到院里,蹿上柴火堆,木头扑啦啦地往下掉。猪蹿到了屋顶,溺了一泡。那泡尿,从瓦片上淌下来,淌到人们的脑袋上,猪得了胜,哇哇地叫。还有一头猪,直着颈根撞倒了杀它的人,主家好一个晦气啊,染一身血。
徒弟剪住了女人的脚踝,倒挂着拖,拖出了纱门,拖过了檐下,他感到无穷的力量,他是膨胀的宇宙。她的头撞在门槛上,嘭,他听见了。她跟他说话,他似乎一句也听不入耳。猪在嚎叫。屠夫杀过的猪,一千两百五十三头。屠夫杀一头猪,就用粉笔画一笔,一个个正字画在门口的红砖上头。一个个正字从墙上浮起来,一笔一笔飘到屋顶下,敞开嘴齐齐地吼。刀尖划过,猪的皮唰地拉开了。女人的衣服剥开,胸前的骨头一排排。她该白白胖胖,肉要粉粉的厚墩墩的,要微微地抖。他压住臀尖尖,猪在他的手底下风情地摇啊摇。女人的头扎进了湿淋淋的稻草里,贫瘠的身子骨滑溜溜的。他在无限膨胀的宇宙中。
“为什么?”屠场屋顶的白色旋涡里,翻涌出一句话来,分不清是从哪条嗓子底下掏出来的。徒弟拨开女人的眼皮,他要看着那双眼睛,再没有什么不敢的,他的宇宙在一刹那光电交错。下山喽,正是好时候!噗——低低的一声,悠长悠长的,徒弟觉得脖子一凉,疼痛从那儿裂开了一条口子,咝咝地把他裂开了。他站在悬崖,狂风呼啸,深不见底,脖子上有一把刀。被女人插进去的,他拿過一回的点血刀。
“你要我学会杀猪。”徒弟的话突起,依然从第一个字开始低下去,轻飘飘地,像在跟随着什么一起跌落,坠入悬崖。
十
“要起来了啊……”屠夫娘在喊。女人浑身湿透了,是汗水,她醒来,觉得冷嗖嗖的。恍惚间看到徒弟,突着脖子奔来,女人瞪大了双眼。她朝向他的微笑,她喊他“细哥”,她与他说话……她对他的怜悯,使她感到自己的高尚。她以为她与周边的人不同,她总是陶醉在自己的想象中。她纵容了他,又对他感到了厌倦。她很任性,赤裸裸地表现她的厌倦。她应该坏一点,只要一点点,不回答屠夫朋友的问题,不那么哈哈大笑。她不许他太近,又后怕对他的疏离。混沌,盲目,仓皇,她终于明白她为何总会想起那只蛆虫了。她跟这些龌龊的事物一般无二。
纱门被推开,屠夫娘走了进来。女人的心撞着耳朵眼,扑通扑通响。她揉着眼睛,问有没人来过。屠夫娘说,没有。
“那个学徒弟的人还会来吗?”女人又问。
“哪个学徒弟的人啊?”屠夫娘很奇怪地答道。
我左手一式太极拳
右手一剑刺身前
扫腿这招叫清雪
破轻功飞燕
我奇筋异脉力破天
一身正气荡人间
除暴安良我心愿
老师傅再见
……
不知谁从窗外路过,手机响着一支新出的网络歌曲,从墙壁折上天花板的阳光暗下去,猪吃空了食盆里的一锅饲料。秋日短,已是夕阳西下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