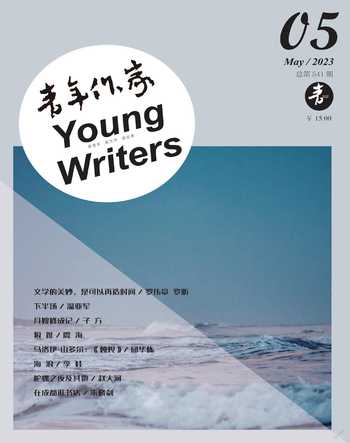离亭别宴
“简离老师候场辛苦了,喝口水休息吧。”
“好嘞,没事。”她提起戏服的裙角,坐到大化妆镜前,顺手掏出粉饼补妆。在抹上脸的那一刻,她望着镜子里的自己,忽然想起第一次演出。
那时她刚转行花旦,还在剧团任B角,基本轮不到上台。但领导照顾,外地演出都带上她一起,而且虽然每次她总要求自费,到最后也就算了。“说不定哪天A角出状况,还要你救场嘞。”团长总这么说。
说不焦虑也是骗人的。因为天生嗓音不占优势,她苦练水袖功,靠着姣好的面容和体态,也算有一席之地。但要说成名成角,差得可就远了。好在她也不在乎。那时候主要是叛逆期蔓延,在老家的江南小镇久了,跟父母相处几乎喘不过气来,满心想着如何逃离,每年一届的香港交流团,是她最大的喘息。
香港的公众场地寸土寸金,他们团一开始没有申请到独立演出的资金,借由某位研究戏曲的教授牵线,先跟高校的文化研究中心建立了联系,因此表演也是在大学课堂上的示范场次。那位教授颇有些名气,每次讲座都能招来好多听者,有些看起来还是外校来的,男女老少,将大礼堂的阶梯教室填得满满当当。讲到某一折戏,教授介绍几个团员出来台上做示范,轻易便博得满堂喝彩。许多闪动的目光四散投射,让座下的她亦心生慕意。
真是个好地方啊,那时她想。如此重视文化,尊重艺术,对世界充满探究——那些新奇的眼神打量自己,就跟她打量对方的时候一样。
她后来知道,其实也并非都如此。待到团长与校外演出场所联系,对接各种商务事宜,才发现观众根本没有想象的多。“你们有把握卖出多少票?”“有没有赞助商?赞助的金额是多少?”这些问题摆出来的时候,他们这才意识到,原来大约半个香港的戏曲爱好者都去了那场示范演出。
这些只是偶尔听领导说起,并非简离所真正操心的。对她而言,观察天空、高楼、商铺和人流,这些家乡看不到的风景才更有意思。
她第一次步下飞机,正好目睹这座浮城的落日黄昏:天边只有一缕幽兰,其它则是大片大片的粉紫、灰蒙和金光闪闪交织交错,宛如毫不怜惜的金漆银装。她张大口,呆愣愣抬头看天,难以置信自己的双眼,走神到步子踩空,差点从舷梯滚下去。这城市不仅有高楼,还有幻境?
“强台风‘天兔逐步移近香港,已于内地汕尾附近沿岸登陆,预计将在今晚稍后至23日凌晨时分往香港以北约100公里掠过,令全城处于戒备。”机场大巴上,广播如是说道。再转头望望天边的辉煌,这才明白是台风过境之前的奇特景象。仿佛宿命一般,一语成谶。
“简离老师,又有人送花来,这次叫……孙总!”化妆室的门被推开,负责场务的小张捧着一大束鲜花进来。她点点头示意摆在旁边。小张放下花,摆弄了一下花束里的留言条,出去前调笑一句:“这次演出场次不多,花收得倒不少啊!”
她听了若有所思,放下手中的粉底刷,轻声叹口气。对于戏曲演员来讲,收到台下和幕后送花是很寻常的事,但曾经身为B角,连上台都没有机会,更别提送花了。
直到遇见宋先生。
他们的相遇是在香港最繁华的商业地带铜锣湾,银灰色钢筋大厦,灯光闪烁,人头攒动,长长的购物电梯仿佛从地面直伸到天际——他戴着灰色的套头围脖,从电梯口下来,而她踩着高跟鞋刚要上去,就这么撞到一起。
本来,在700多万人口的城市里,撞见一个人实在是不足挂齿的小事。但难得在于对方道歉的口音如此软糯亲切,彼时她到港多日,听了满耳朵干涩的粤语,这惊喜便更显珍贵。他乡遇故知,喝一杯吧。谈话中她得知,对方跟她一样也是游客,刚来香港不久,还找了个本地的地陪。跟她又不一样,他对这座城市的美景似乎提不起什么兴趣。
“刚才我坐着电车绕了港岛一圈,金钟地铁站外的建筑群挂上圣诞灯饰,好漂亮啊!像在港剧里一样。”她兴致很高,耳环直晃。
“噢,是吗?”
“落雨时分搭叮叮车别有风味,你见过吗?”
“见过,还可以吧。”
她转过头来望着他:“感觉你对这些风景都没兴趣,那为什么要来香港呢?”
宋先生答了句她当时没有听懂的话:“有人说,所有的Metropolis都差不多吧。”
“谁说的?”
像被惊了一下,对方猛然从游离中回魂,扯了扯嘴角:“没什么。”
虽然没懂,但她隐约感受到背后的故事:“这么说,你见过很多?”
宋先生斜靠着吧台,眼神再度游离出去,不知望向虚空中哪个方向:“人很多,但都看不到。声音很大,但都听不见。已恨碧山相阻隔,碧山还被暮云遮。”
她歪了歪脑袋:“可是這里多热闹,跟咱们家乡小镇完全不同,好像每一刻都不会空虚呢!”
“外物不能填满心空,只会更空。”宋先生叹口气,“你知道吗,其实我曾在这里念书四年,那段记忆太苦太痛,如今想来,竟然全都忘了……怎么就能忘记?”
“什么苦痛?”
“兄弟背叛,抢走追了许久的女生,加入的社团排挤,考研失利,实习公司老板都是衰仔,本地人歧视我,同乡也看不起……说出来也没什么大事,全是些琐碎。”
“我能明白,击垮我们的,都是琐碎。我在团里是连名字都不能写上海报的B角,来港多次,从来没有机会上台。要比惨,每个人都有惨的地方。”
“不,大约只因为我是loser吧。不上不下,永远卡在中间。”
她沉默了,答不上来。她既没有在这里呆过四年,亦不懂Metropolis的含义,只感到一股汹涌的压力席卷而来,仿佛回到老家父母身边那令人窒息的催婚气场:你说你的,我说我的,这种沟通完全是无效的。对方见此也不再继续说下去,只是举起酒杯:“简离小姐,敬你一杯。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
“知道我为什么叫简离吗?离别,原本是简单的事——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她拈起戏腔,试图打破冷冰的气氛。
“只有不谙世事又不切实际的人,才会一味乐观吧……”宋先生苦笑着摇头,忽而又意识到失礼,一口干了酒,“酒后胡话,莫当真。”
她愣住一秒钟——有一种在那一秒里恶狠狠地咬紧牙齿,被人戳穿的那种崩溃,但很快恢复如常,从包中掏出一张票根:“明天在城市大学有场示范演出,欢迎来听家乡戏。”
“有时间一定去,祝成功!”
她点点头,起身打算离去,对方忽然在身后喊她:“简离小姐,需不需要送你回去?”
她挥挥手:“来之前查好了通宵小巴班次。每次我都是一个人逛的。”
良久,却见宋先生站在酒吧昏暗的灯色阑珊下,黯然垂首低语:“都是一个人……吗?”
都是一个人的。同行的团友多有演出任务,在港的日子里大都在排练,间隙还要陪着文化中心的院长参加饭局。唯独简离从没上台,不用准备什么也没人约她,倒落得清闲,常独自偷溜去市区逛街。
高高的坡道,分成一边阶梯、一边无障碍轮椅通道,台阶尺寸刚好够几个人坐着倾谈,旁边还有绿植生长。桥下空间,流浪者用废纸壳和报纸做成小小的家。十字路口除了四条常规的人行道,中央多出了两条交叉对角线作为人行过道线……她踏着小步子,一路逛一路看,风景落尽眼底,似也融入身体。在她出生的古镇,除却石板路和石板桥蜿蜒不尽,是断没有这些巧思的。
最令人惊异的是,她那晚逛得晚了,索性就在铜锣湾开了间小酒店尝尝鲜,哪知这一次就真叫大开眼界,见识到人类的房间究竟可以有多小——你明白只能一面下床的含义吗?意味着床的三面都贴墙。即便如此,设施竟一应俱全,所有用品都放在围绕墙边打进去的储物柜上,躺在床上一伸手即可拿到,无愧“胶囊旅馆”的名号。那晚她睡得快呼吸不过来,睁大一双眼睛,想着原来这便是香港。
她走走停停,也把这些念想记录下来。其实她原本在戏曲学院的专业是编剧,师傅说她有个毛病,创作单凭一股子心气,而非持续性的才华。“如果心中有最深的焦虑,就要以最大的淡然来应对。”师傅这么说。但到后来,她只是学会伪装。
“这样不行。”师傅也是看着她从小长到大的,便建议她从编剧改行为演员,先在剧中体验人间百态,从内里打开自己。她也觉得写作总是消耗,需要养料补充,这个主意倒不坏,便直接在团内跳转职务。因为小时候练过花旦的童子功,费些力气重新捡起来,跟专业的比不了嗓子,练练身段还算过得去。
虽然暂时换了行当,写作的习惯并没有丢。所以每到一个新地方,她总会搜查景点资料,抄些游记心得,有时候还哼哼两句。那夜从兰桂坊的酒吧回来已是深夜,她打开电脑,凭记忆拼了半天,才凑出“Metropolis”这个词:指大都会、大城市、主要都市、重要中心。
所有的Metropolis都差不多。这又是什么意思呢?只去过几个城市的简离感到困惑,打算次日再问。
然而次日没有寻着机会。宋先生倒来了,衣冠楚楚,还识趣地手捧一束鲜花,在后台的她惊喜到不敢相认。更惊喜的是,那日A角历史性地生病了,成为她第一次在港登台的契机!
“阿离,发什么愣呢!” 简离从记忆里回神,见到团长正站在化妆室明晃晃的灯光底下,用力拍她的肩。
她再次拿起化妆包,换了支黑棕色的眼线笔开始涂抹:“没什么,默念台词。”
“哟,你这台柱子还需要默词?都演多少遍了啊,你说!”团长调笑着打哈哈。这并非原来的团长,而是原团长身边的办公室主任,以往跑前跑后的狗腿,如今一朝天子一朝臣,但见新人换旧人。见简离不接话,他讨了个没趣,咳几声换了语气:“今晚洪老板设宴,点名要你来陪,听到了吧。”
简离冷笑一声,对着镜子把眼皮翻起来,开始画下眼线。团长自觉尴尬,重重推门出去了,半晌又大步踏回来:“不准再中途溜号,没有洪老板就没有咱团明年的演出。别以为嫁给老张就有了靠山!”她手一抖,眼线笔歪了出去,顺着眼睑飞出一道怪异的黑线。翻找湿巾擦拭的时候,她感到自己的心也在颤抖。
登台亮相,意味着接受万千瞩目,也意味着更多工作接踵而来。那日首次演出之后,她便知道了有这样的结果。
接过宋先生递来的鲜花,简离犹带戏妆的脸上飞起两片红霞:“谢谢捧场。你真是我的福星,一来我就有机会上台了。好看吗?”
“听到乡音,仿佛是回到故乡。”宋先生眼里流露出前一夜没有的灵光,口中不忘称赞,“尤其是你的舞袖,非常美!”
她不免志得意满,抿住嘴角的笑,毕竟这是第一次,往后许多年频繁的舞台生涯里,再没有过这样的满足感。
“过奖了,喜欢就好。那今晚……”
没等说完,老团长的声音从幕后远远传来:“简离,今晚聚餐你一起来!”
“我……”她看看宋先生,犹疑地道,“我就不去了吧。”
“今天你演得好,院長特意吩咐的!一定要来!”
那吼声震天,大概用了真气,穿过几层帘幕仍有回音,似在延长这段尴尬。最后还是宋先生安慰:“没关系,你先去忙,回头再联系。”
晚宴设在鼎鼎有名的“海上龙宫”珍宝海鲜舫上。这艘模仿古时候接待达官显贵的水上“歌堂船”巨趸,与太白海鲜舫和数艘辅助船一同组成珍宝王宫海上食府,有世界上最大的海上食府之称,里面亦装潢得传统,皇宫般雕栏玉柱,龙头林立,金黄色吊灯打出的色泽,处处彰显着东方富贵气息,成为外国游客必到之地。流水般的海鲜上桌,流水般的白酒下肚,在七吆八喝声的觥筹交错中,她假笑得脸皮都酸了。不知是海鲜的腥熏还是白酒的醉意,不过一会儿,她就撑不住,头开始剧烈作痛。
人群仍在兴高采烈:“再喝一杯!再喝一杯!今天可是简离小姐的首秀,大家都得好好庆祝!”
“干喝有什么意思?再来一段吧!”
“院长说的是!快,简离现场给我们唱一段助助兴!”
啊?彼时她没怎么经历过这样的场合,一被叫到,哪敢不强撑着桌子站起。此时一个浪头袭卷,漂浮在海湾上的巨型龙宫打了个晃,大船震荡不已,她胃里本就翻腾,这一晃,忍不住干呕一声,差点当场吐出来。酒桌上座是清一色的中年男士,眯着眼等候看她笑话,下座有几位剧团的演员,面露不忍但也没有出声,后来的团长——现在只是个跑腿的,坐在最下位,带着玩味的眼神看着这一切。
她咬牙,赌气一般开了口:“立志守节,岂在温饱。忍寒饥。决不下这翠楼……” 没唱到一半,喝了太多酒的嗓子就堵住了。早已不是香君,哪能不下翠楼。
终于有人看不下去:“够了,何必为难这位女士?”众人循声望去,是谁这么不懂场面?原来邻桌一个西装革履的金融才俊站了起来,瘦高个,清秀的脸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胸口井然的领带似乎在彰显绅士风范。
主座上的院长清清嗓:“Lawrence你刚从美国回来,不懂东方的规矩。这不叫为难,大家凑兴,是在给她表现机会。”接着压低声音跟领座解释道,“他父亲给我们学院捐了不少款。”上座的几人心领神会,交换了然的眼神。
“哼。”那Lawrence年紀轻轻脾气倒大,傲然盯着院长,“东方的规矩,西方的规矩,都是人的规矩!你们给她机会,也要问问她愿不愿意?”
“愿意愿意!她愿意的!”一旁的团长忙圆场答道,说完又想起什么,朝简离讨好地示意,“你愿意吗?”
简离这才回过神,一股邪气上来,她站直身子微微仰头:“今天演出太累,这船有点晃,抱歉我不舒服,先行告退了。”终究话还得说体面。
就在她无视众人反应、径直离席的时候,方才为她出头的年轻男人连招呼都没跟其他人打一句便走了过来:“我送你。”
“不用了。”她试图拒绝,但对方却不像客气,步子坚决,誓要将英雄救美做到有始有终,而院长他们也因此有些忌惮,便就从了。
下船踏上地面,亮着金色光辉的大槎屹立在避风塘,倒影在海夜中摇曳生辉,却又始终不太安稳的样子,像这繁华盛世。海风一吹,人清醒了许多。简离给宋先生发了个讯息,至于身边的Lawrence,虽没什么兴致聊天,但对方毕竟是救场恩人,亦步亦趋跟得紧,当然不好拒绝,于是随意客套:“你从外国过来的?怎么会来听这老掉牙的东西。”
对方绅士地笑:“学院邀请我father出席,他今晚没空,我就代他来了。在美国大都市呆久了,我很愿意欣赏这里古典主义的美感,虽然慢,但有味道。”
她下意识看了眼手机:“有人说过,Metropolis都差不多。”
Lawrence昂起头,挑挑眉:“谁说的?有点意思。是啊,都市病哪里都有。我从小到大都在不同的Metropolis,家教严格,上学和工作都有人安排好,真是太烦了。不过我father最中意看王家卫的老电影,缓慢的节奏,跟戏曲也很像!”
这份滔滔不绝让简离答不上来,她干笑了两声掩饰尴尬。不过听对方说起家世,她倒想到自己。外祖父曾是参与创建戏团的首任团长,后来母亲也在团里做个小中层干部,一家子都在戏团大院里。待到她出生,戏团已不复旧日兴盛,大家也各自住进了楼房,交道逐渐浅了。后来外祖父去世,母亲退休,团里人员换了又换,曾经熟悉的老人们也退出舞台,唯一有点关联的就是如今这老团长了——据说当年还是外祖父招他进团,连政审都是亲自去到他县里的老家。所以团长平时对简离还算照顾,即便没什么贡献也不苛刻,包括转换职业、申请加入演出团等,一应开绿灯。只不过像今天这种场合,他是身不由己的,就是叫他自己唱一段,也得立马粉墨登场。
也因为这样的原因,简离从小看惯了最有名的腕儿都要领导管,所以反而厌恶这一套,选择投身专业行当。只是自己始终轻浮在空中,不禁想起宋先生的话:既不上也不下,似乎是一种常态了。
“今天看美女的演出十分激动,没想到有幸还能在一起吃饭。”那厢Lawrence还在半真半假地跟她搭讪,“我这人有个毛病,见到美女就不知道该说什么。”
“谢谢。”她有些不自在,又看了看手机,一直没有回复。
“刚才那句词唱得情意绵绵,真情动人!我都快听哭了。”
“那不是真情动人。”简离冷冷回道,“是以死明志。”
“什么意思?”
“妓女不下青楼。”见对方的彬彬得体终于被打出一道尴尬的裂缝,她终于狡黠地展颜,“李香君是出了名的秦淮八艳,你不会不知道吧?”
Lawrence闻言却转头望向简离,明显会错了意,双目炯炯射出精光:“美女今晚有空喝酒吗?”
简离哑然,想起前一晚跟宋先生聊天,她这才体味到虽然并非所有沟通都有成效,但起码有些还算在同一个频道上,而另一些,痴人说梦罢了。她再开口,是一句戏腔:“痴虫啊痴虫!偏是这点花月情根,就割他不断么?”
对方愣了一愣:“什么?”
“没什么,戏本上的唱词。”
Lawrence脸上再度露出怪异表情,双手做作地轻拍:“厉害啊,简离小姐。如果没有你,剧团可怎么转?”
就在这时,手机的铃声响起,简离连忙查看,却不是宋先生打来,而是一个陌生的号码。她接通电话很快听完,眉间蹙起哀愁:“是香港警察,说我昨天见到的一位朋友在维港落海出意外,我得赶去看看。”说完转身要走。
“这样离谱的理由?”Lawrence拉住她的胳膊,“你不觉得编得太可笑了一点吗!”
“对不起,这是事实。”她抽出手臂,挥了挥,“再会。”
“简离老师,该你上场了!”
“来了。”她应道,补完最后的腮红,提裙踏起小步来到台侧帘幕后面候场。逆着冷光,她看见台下有人在抹泪。座下谁人泣最多?那晚在维港边看到宋先生尸体的时候,她也有这样的疑问。
打车赶到海边掏光了简离的钱包,下车见事故场地已被围起来,外三层里三层,她心跳得飞快,慌慌张张往里闯。身穿制服的警察走过来:“我们查看死者坠海前落下的手机,最近一条讯息是你发来的,虽然死者应该没来得及看到。你是死者的亲属吗?”
她摇了摇头,瞟一眼地上的尸体,被白布盖住看不清,除了丢在旁边沾满海水的灰色套头围脖表明了主人身份。空气中弥漫着腥臭味,不知是尸臭还是海水的鱼腥。她强忍住干呕的生理反应。该怎么说,才能解释清楚其实自己与宋先生是仅仅两面之缘的陌生人,却成了对方死后第一个能联络上的认领者?
警察在册子上飞快地记录,继续问道:“那你是否知道他由于什么原因落海?失足、自杀还是他杀?”
她再度哑然,拼命回忆跟宋先生的两次对话。他说了什么呢?好像酒吧里一群年轻人嬉闹着掷飞镖,他却说:“我不明白他们在笑什么?”
简离转头望望四周,围拢而来的人群拿着手机嘻嘻哈哈,俨然打卡景点,无一人面露悲伤。也有几人长吁短叹,是在哀香港的年轻人不争——并不清楚死者的具体身份。这使她深切感受到哀伤也需要氛围,这里实在没有老家婚丧那种众声哀嚎的气氛,搞得她虽然眼睛湿湿,但总是将哭未哭,仿佛噎在嗓子眼。看到陌生人的生命消逝,《桃花扇》里是怎么处理的?她脑子突然空了,回忆不起来,只得再度摇头,用劲眨眼,发挥演技抹出两行眼泪,算是对这段露水情缘的交代。
问不出所以然,警察叫简离签了个字,让她走了,说,会继续联系手机通讯里的其他人,有消息通知。于是她幽魂般孤身游荡过海港,风景也不复往日生动,陌生人的眼神不再闪亮,都是步履匆忙地赶路,像有鞭子在身后抽打一样,追逐着无谓的前方。曾经她从电视和留声机里认识香江,觉着这里就是乌托邦、理想地,但待到真的踏上此间,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风把惘然吹来,高楼之下的城市燃起灯火,如梦似幻漂浮半空。红砖花岗的钟楼响起钟声,人群跟着高喊:“五!四!三!二!一!”原来今晚竟是平安夜。如此不平安的平安夜,就像她答应老张求婚那天一样。
老张原是同乡,出去外地经商几年,带回来的除了日渐肿胀的啤酒肚,据说还有日渐肿胀的钱包,不知怎么看了她的几场戏,就开始疯狂追求。父母这下高兴了,想着法子地劝:“你这演员行当吃的是青春饭,过了年纪可没有机会了!”她不服:“我要做的是编剧,过几年就换过来。”“那先解决经济问题,没有了后顾之忧才更好创作啊。”
她无语,只得逃去师傅家里避风头。师傅是外祖父那辈人,凡事倒看得开:“必得先历经万不得已的苦痛、愤懑,方是词心。”
“这是什么意思?师傅你也劝我妥协吗?”
“什么是妥协?你要坚持的又是什么?”
她被问懵了,只得躲进房间里避耳不听,闭口不答。直到两年后,师傅因肺部感染突然去世,她最后的支柱也倒下了。人去楼已空。她在眼泪中终于点头答应了老张。
走到临风处,她迎面望向摇曳的海港,世界坠进一片黑暗。人群的欢笑声从远方传来,像某种哀歌。都市病哪里都有。她也终于染病了吗?
《桃花扇》 中,当年人称“南曲天下第一”的苏昆生在南明灭亡后重游南京,睁着五旬老眼,看了四代人:当年粉黛,何处笙箫?青苔碧瓦堆,处处话凄凉。最后仍觉着残山梦最真,旧境丢难掉,不信这舆图换稿!
以前,吟游诗人奏起荒腔走板的丝竹,游走四野,对日颂唱,记录人间千情百状。后来,他们化身为流浪歌手或乐工戏女,藏入人群掩饰真容。这是她游记本上曾经抄过的一段话,能够答得上师傅当年所问的坚持吗?真后悔当时没有鼓起勇气,在师傅的病榻前吐露最后一句。如今隐在后台帘幕处的简离,突然想起那日宋先生离去前的话:“我很喜欢演出结尾那支曲子。”
她想了想:“噢,你说是《离亭宴》。”
“好凄凉的名字。”宋先生若有所思,断断续续念出了唱词,“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
台上人影绰绰,大笑三声,乾坤寂然矣。秋波再转,余韵铿锵。从古传奇,有此结场否?笙箫响起,锣鼓经敲,该她上场了。这一场离亭宴,终于来到尾声。
【作者简介】吟光,著有长篇小说《上山》《天海小卷》《港漂记忆拼圖》及相关原创音乐、新媒体艺术作品,参与主编科幻集《九座城市,万种未来》,曾获中国网络文学年度新人、金车奇幻小说奖等;现居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