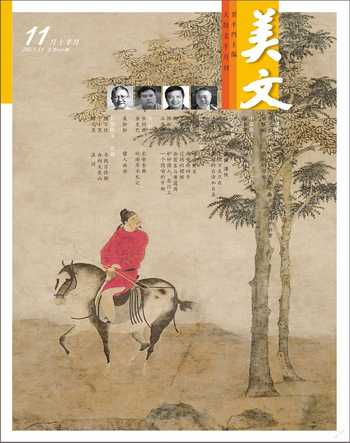猫爸爸
陈百忧
平常走到男病房的小铁门前,我会听到活动室传出打牌、下棋、看新闻的声音,有时还会有抢电视的吵闹声,感觉和社区老年活动中心差不多。
但有一天,我发现活动室极安静,连整日开着的电视机都关了,只有一个从来不坐凳子的患者蹲在窗下卷旱烟。望着空荡荡的走廊,我意识到,几个月来到处乱跑的 9 只猫不见了。
二楼长长的走廊两侧分布着二十来间病房,常年住着四五十名精神病患者,此刻他们大多躺在床上一动不动,情绪极度消沉:有人睁着眼睛发呆;有人唉声叹气,对我说“胳膊拧不过大腿”;偶尔有起身活动的人,一直在踢墙根,墙皮都被踢掉了。原本热闹的病房一夜之间变得死气沉沉。
我开始担心,患者要出事。
一
我们精神科病房在医院最深处,是一栋独立的二层小楼。这栋白墙红瓦的小楼被大树包围着,仿佛遗世独立的小世界。任何外人想进入这个“世界”,都只能按门铃,再由医护人员开门。昨天下午,院长没提前通知,突然来精神科大门口按门铃。跟在他身后的是一个陌生人,去开门的同事被吓了一跳。那人是院长的朋友,有亲戚犯病,想先来科里看看环境。院长带朋友刚来到二楼男病房小铁门前,就看到 9只猫正追逐、打闹、舔毛,院长在走廊还差点踩到一只小猫。老护工说,院长气得脸色都变了。看到匆忙赶到的主任,开口就说:“你这病房要是不想开,明天就关了!”
来到“猫爸爸”卢伟屋里,院长扫了一眼,发现散落在各处的猫窝、饭盆、水盆,闻到满屋的猫味儿。他警告卢伟:再惹事就别来住院。平时卢伟是不怕院长的。院长因为腰椎受伤,背挺不直,患者們偷偷给他起绰号“罗锅”,只有卢伟敢当面喊。但这次,卢伟怕连累主任和我们,没跟院长顶嘴。他只是站在原地,一副叛逆少年被父亲教训的模样。
院长下令把猫全抓走,之后还对我们科进行了全院通报批评。当天晚上后勤的人就来了。电工、锅炉工、厨师手拿编织袋,在二楼到处找猫,一只一只数着抓进袋子。9 只猫被装上车,放生到了医院东北边的山里。抓猫时,卢伟他们就在一旁看着,有人嘴里骂骂咧咧地抗议,但不敢把猫抢过来。那晚开始,不少二楼的男患者都不吃不睡,熬了几个通宵后,都犯病了——
老田是个老好人,他总怀疑电视剧里的对话都是针对自己的,整天仰着脑袋对着屏幕里的人骂。老米是躁郁症,多数时候都是轻躁狂。最近几天他转换成抑郁发作,不再像往常一样趴在窗边喊“开饭了”,而是躺在床上抹眼泪,说活着没意思,甚至还给老伴写了遗书。老邹有严重的幻觉,只相信脑子里的声音。他的幻觉好久没出现了。结果在 9 只猫消失的第四天,他动手打了人,非说看到对方欺负自己二姐。
精神科二楼的男病房终于不再是一片死寂。但这因患者“集体”犯病而引发的境况,却令我无比悲伤。
之前我常来卢伟屋逗猫,看一会儿猫就感觉心都萌化了,会暂时忘掉烦恼。因为有猫在,卢伟和其他患者的精神状态变得暂时稳定,病房的气氛温馨了不少。此刻,小猫们打闹的画面仿佛还在眼前,盆里的水和猫粮都在,大纸箱做的窝里却找不到猫的身影。我心里也有点难受,鼻子有点酸。
“猫爸爸”卢伟此刻用被子蒙住头,蜷缩在床上。虽然是上午,但他房间黑咕隆咚的。他怕阳光,总是把淡绿格子窗帘拉得严严实实。感觉到我在靠近,他身子动了一下,再没有反应。我坐到旁边的空床上问他是不是在哭,卢伟从被子里伸出脑袋说:“没哭!”眼睛却是肿的。
我一下意识到,这些猫回不来,这里有些人可能就“好不了了”。
二
“猫爸爸”卢伟是我们精神科一个奇特的存在。2010 年夏天,我来精神科上班的第一天,师姐叮嘱我:别和卢伟走得太近。第一次跟主任查房,我有点兴奋,也有点害怕。当时卢伟在活动室里站着抽烟,我一眼就注意到了他。他身高一米七左右,略微有点啤酒肚,没穿病号服,而是穿着干净的短袖白 T 恤。他没有其他患者迟缓的动作和呆滞的眼神,浑身带着股傲气,似乎瞧不起所有人。他递给主任一根烟,主任接过,问他最近怎么样。卢伟很自然地寒暄起来,感觉他们之间不像医生和患者的关系,反而更像是朋友。
卢伟主动找我搭话,问我哪个学校毕业,正式留下还是只是来实习。我不仅当时没能分辨出他是否患有精神疾病,挺长时间后还是搞不清楚他到底是患者还是工作人员。
后来我了解到,这人的身份果然不一般。1975 年出生的卢伟是个富二代,父亲大概是他们老家那里最成功的商人。卢伟拥有大多数人想拥有的一切,他衣食无忧,住大房子,有漂亮的老婆和可爱的女儿。卢伟的女儿曾来过我们科,才15 岁的小姑娘,身高已经超过父亲,头发又长又直,像模特一样,以至她都坐车走了,还有人趴在窗户上看。
然而卢伟几乎抛下这一切,主动住进了精神病院。
我心里一直有个疑问:他住在这里到底要干什么?直到我从同事那听说了 2008 年卢伟第一次来我们科住院时的情况。那时的他比我初见时嚣张得多,经常在病房里指挥其他人干活。他用烟或零食支使其他患者给自己倒洗脚水、打饭、清扫屋子。有一段时间,他嫌厕所臭,就直接尿在瓶子里,然后找人扔掉。他甚至在想喝酒时,让护工带酒进病房,导致那个护工被开除。为此他出了院,找朋友安排了新工作给护工。
主任不知道说过他多少次,要不是因为卢伟有“关系”,不用等院长发话,主任都想把他撵走。那个时候他看不起人,说话特别难听,骂其他患者都是傻子。主任批评卢伟:“你聪明你咋住着不走!”卢伟不说话了。
卢伟患有“酒精中毒所致精神障碍”。这是病理性的酒精依赖,主要表现是晨起饮酒,每天早上醒了就找酒喝。一天到晚基本上没有清醒的时候。停止喝酒 48 到 72 个小时就会有戒断反应:会手抖、浑身大汗、出现恐怖性幻觉。长期酗酒甚至会改变人格,变得极度自私,和犯了毒瘾没什么区别。更糟糕的是,患者还会产生嫉妒、妄想,总是毫无理由地怀疑别人,甚至动手打人。戒酒一星期之后,身体上对酒精的依赖就没有了,所有的精神症状都会消失,看起来和正常人没什么区别。但时间长了,大脑结构会发生改变。卢伟完全符合这些情况。
其实卢伟可能是精神科里最傻的人。他的病只要不喝酒就没事,但他就是不长记性。多年来,他反复出了十几次院。离开的时候,他状态不错,胖了十几斤;回来的时候则是不健康的瘦,一副肝病面容,脸发黑,颧骨发红。每次他都是因为醉酒被抬着上楼,回到他独自居住的三人间。
每天早上九点查完一楼的女病房,我都会拎着一大串钥匙,放缓脚步走上发出吱呀声的红漆木楼梯,打开男病房的小铁门,行走在长长的走廊上,进出患者的屋子。精神科的小楼太老了,雨天会漏水,一些地方的墙皮已经脱落,上面留下了浅黄色的水印。卢伟的屋子比较窄,里面有三张并排的床,他把空着的两张床用白床罩盖住,去掉了被子和枕头。自己就住在离窗户最远的床上。屋里见不到太阳,无论天气多好,都拉着窗帘。他带了不少金庸的武侠小说,在床头柜上码成排,另外还有些杂志报纸。需要看书时,他宁愿开灯,也不拉开窗帘让阳光照进来。
在我看来,卢伟在精神科二楼的男病房里,为自己打造了一个舒适的独立世界,只不过之前这个世界里只有他自己。后来,他有了一群“猫孩子”。
三
猫刚来的时候只有一只。2013 年 3 月初,路边的积雪还没化完,下午,护工带着患者们去医院的大澡堂洗澡。卢伟最先洗完,站在外面等大家时,看见草丛里有只猫在对自己叫。
这只猫可能是狸花猫和其他品种串过的,身上大部分是狸花猫的花纹,肚子上有一片软乎乎的白毛,头顶和尾巴有一段黑毛。
看着受冻的猫,卢伟心软了。他用换下来的脏衣服把猫包住,悄悄带回自己屋。医院不允许养猫,卢伟独自住在三人间,这是他在我们科的“特权”。虽然每间病房都没有门,但其他患者都不会随便进来。他找了一位熟悉的护工,要来装药的大纸箱,把一件毛衣放在里面做成猫窝,在自己的床下偷偷养猫。他又找来塑料盆装水,把一个不用的铝饭盒当食盆。最后还铺了报纸,让猫在上面拉屎。
虽然没多少人来他的屋子,但在精神科这个封闭的环境里很难有什么秘密。患者们的生活即使是十年也如一日,往往一点小改变在这里都会变得非常明显。养猫的当晚,就有患者反映听到猫叫声,但因为医院被大树和野草包围,深夜里不只能听到野猫叫,不同季节还能听到蛙鸣、鸟叫。护工也没在意。
第二天中午,老邹、老米、老田三个人首先发现了卢伟的秘密。他们在卢伟出去扔报纸时,找到了那只狸花猫。于是卢伟让三人一起来屋里,兴奋地讨论怎么养。第一件事就是起名字。这四个男人一开始叫它“二嘎子”,那是东北话版《猫和老鼠》里汤姆猫的名字。后来經老护工指点,他们才意识到“二嘎子”其实是只母猫,而且已经怀孕。四个男人七嘴八舌地改名,想起雪村唱的《东北人都是活雷锋》,他们喜欢最后那句“翠花,上酸菜”,于是猫有了名字——翠花。
因为翠花,平常不爱搭理人的卢伟和病友们成了朋友。收养翠花约三天后,我跟主任上楼查房,正巧看到老邹从卢伟屋里出来,当时他的表情有些不自然。我很少看到卢伟屋里有其他人,当时就觉得有问题。等主任查完房下了楼,我又返回卢伟屋,发现了翠花。卢伟并不打算对我隐瞒,他脸上带着笑,对自己给翠花布置的新家很得意。
“东西备得挺齐全啊。”我笑着说。卢伟一脸骄傲:“那当然!”
看着正常得不像精神病患者的卢伟,我会有种恍惚的感觉:明明他只要坚持不喝酒,生活就会比普通人好太多,但他抛下妻女,常年住在精神科。而当他看向翠花的时候,眼神里总带着温柔,脸上是得意的笑容——似乎在这个周围全是重症精神病患者的地方,只要有猫,就比在外面更幸福。
四
我决定先不主动告诉主任“病房里有猫”,我觉得养猫对卢伟也许是件好事,只是有点担心秘密藏不住。买猫砂卢伟都要“贿赂”护工,怕引起注意,护工会把猫砂分装成小包,一点一点往病房里带。卢伟养猫没两天,师弟就悄悄问我知不知道楼上的秘密。大约一周后,科里除了主任,都知道翠花就在卢伟屋里。
翠花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它有四个“爸爸”,卢伟是亲爸,其他三个是干爹。他们每天换着花样给翠花弄好吃的。当时患者每个月只交 300 块伙食费,奶和蛋要单独花钱订,卢伟会每天订两个鸡蛋给翠花。翠花不负众望,长得胖胖的,肚子也在全楼男患者的注视下一天天大起来。每天查完房,我都要看看翠花,和大家一起盼着它的孩子出生。
那段时间,我隐隐觉得病房里最活跃的几个人眼神不再呆滞,有了笑意。病房里的气氛发生了微妙的改变,有一种温柔在流淌。卢伟对翠花最用心,每晚要看看翠花才能睡踏实。病房里的患者大多结过婚,用他们的话说,他们照顾翠花比当年伺候怀孕的媳妇还认真。
一个多月后,翠花生了 8 个孩子。卢伟他们恨不得在屋里拉个“英雄母亲”的横幅来庆祝。在遇到翠花以前,卢伟没有养过猫,不知道小猫应该喝羊奶。他让护工成箱成箱地买牛奶,给翠花和孩子们补充营养。小猫能吃肉以后,只要食堂做溜肉段,二楼一半的病房都会把肉留给翠花和它的孩子们。在大家的照顾下,小猫们开始满走廊乱跑,就像毛茸茸的小精灵,可爱极了。卢伟的屋子不再是其他患者不敢踏足的“禁地”,常有人来看这一屋子小猫。卢伟的脸上会露出父亲般慈祥的微笑。
因为卢伟的身份特殊,加上翠花来了之后,病房里的氛围柔和了很多,也给管理带来了好处,主任默许了卢伟养猫。平时,翠花和孩子们就住在卢伟病房中间的那张床下。那里放着从药房要来的大纸箱子,里面有毯子和不知谁带来的猫咪玩具。纸箱开口朝着卢伟的床,旁边放着两个塑料碗,分别装着水和猫粮,铝制饭盒里放着大家省下的肉菜。靠窗的床下也有大纸箱,剪到 20 厘米高,里面铺着猫砂。床上摆满了整袋的猫粮、猫砂,还有奶和罐头。
担心屋里的猫味儿,怕光的卢伟虽然坚持把窗帘遮得严严实实,却成天开窗户通风,尽量让屋里的味道小一些。一阵风吹过,阳光就会从飘动的窗帘间挤进来。
我也在这些缝隙里,渐渐看到了卢伟的内心世界——那个总是把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的小房间。
五
卢伟的父母经常吵架,小时候的他总会用被子把自己蒙起来,然后捂住耳朵。卢伟始终忘不掉,父母离婚后,母亲把自己交给父亲的瞬间。那是小学二年级的暑假,母亲把他送到工厂外,让卢伟自己进去找父亲。卢伟曾经跟父亲来厂里玩过,但是那天眼看着母亲转身离开的他,就在工厂大门对面呆呆地站着,从烈日当头,一直站到夕阳西下。他看着大门,就是鼓不起勇气穿过不宽的马路,走到门卫那里说出父亲的名字。他记得自己很渴,渴到连口水都分泌不出来,嘴唇都粘到牙齿上。他特别想哭,又告诉自己,“男子汉不能哭”。
那天就像一个梦,始终徘徊在卢伟心中。哪怕人到中年,他依然无法从这个梦中挣脱。卢伟已经忘记,当时自己是怎么见到父亲,又是怎么跟父亲回家的。他讲述这段经历的时候,没有流露出情绪,和平时一样声音很低。我却不自觉地咽口水,他当时的口渴和悲伤似乎传递给了我。直到现在,卢伟都不敢看太阳,阳光刺眼的时候,他会觉得口渴。他说,那种渴的感觉,喝再多水也不能缓解。日落时,总有强烈的悲伤像浪一样打过来,他想号啕大哭,又觉得男子汉不能哭。卢伟睡觉时,常用被子蒙着头,我不知道他是否会躲在被窝里哭。
卢伟的羽毛球打得很好,有天晚上五点多,我叫卢伟去院子里打羽毛球。他有点犹豫,但还是来了。打了没一会儿,他就出了好多汗。开始我还嘲笑他,后来他干脆不接球了,只是原地站着。我才意识到,挂在天边的夕阳又扰动了他的心。打球前,他特地挑了面朝夕阳的位置,大概是想挑战一下自己。看着他满头大汗,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我眼前好像出现了那个小学二年级时的小男孩。
我让他上楼休息,他艰难地爬木楼梯,感觉用掉了全部力气,完全没有平时的灵活劲。卢伟进屋就在床上躺着。晚上八点发药,我上楼看他,他还是一动不动。卢伟母亲离开不久,他父亲辞职“下海”去了深圳,后来又带着钱回老家承包矿山,成了当地有头有脸的人物。他父亲外出做生意那些年,把卢伟托付给一个“铁子”,这人后来成了卢伟的师父。师父是火车司机,跑长途货运,一出车就是十来天不在家,回家就喝酒。师父总说师娘出轨,不出车的时候就跟踪师娘。家里肥皂被人动了,屋里有烟味儿,全成了捉奸的线索。师父还常把卢伟拉到一边,问家里有没有野男人来过,但卢伟从来没见过。后来师父师娘吵架升级,离婚了。现在想来,卢伟的师父应该有对酒精依赖的人常见的“嫉妒妄想”。
卢伟上初中时,跟师父喝了第一杯酒。他告诉我,自己突然觉得那种萦绕在心里的口渴感消失了。他第一次喝醉,童年时父母留给他的阴影也模糊了。之后卢伟经常和朋友们喝酒,只要喝醉,所有的压力、彷徨、痛苦就都沒了。他觉得自己的思路变得非常开阔,之前无法做出的决定喝醉后就能马上做出。喝酒,并且喝醉,成了卢伟今后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
卢伟成绩不好,勉强考上了职高,毕业后父亲让他跟着自己干,没几天他就不去了。那时父亲已经有了其他女人,生了个比他小 18 岁的弟弟。
没有工作的卢伟偶尔跟着师父跑车。父亲托人把卢伟安排进了铁路,就跟他师父搭班。这对相依为命的“父子”经常喝得酩酊大醉。这样的状态持续到卢伟喜欢上一个女孩。他从师父家搬出来,结了婚,生了个特别可爱的女儿。然而自己组建的家庭并不能抚平卢伟的伤痛。
在他心中,小学二年级的自己依然站在工厂大门外,被烈日炙烤,口干舌燥。
六
2003 年,卢伟第一次来我们科,是来照顾师父的。师父已经是肝硬化晚期,肝性脑病、腹水,肚子大得不行。一次抽腹水就能抽出 3000 毫升。他还有很多精神症状,说胡话,到最后连卢伟都不认识了,总说有人追杀自己。
当时师父住的病房就是后来卢伟住的三人间。害怕师父坠床,卢伟把两张床并在一起,自己就住在另一张床上。打滴流的时候,师父经常乱动,卢伟就一直在旁边握着师父的手,直到结束。他每次都要握三小时左右,厕所都不上。师父一直有幻觉,有时候会打人骂人,卢伟就让他打。直到后来,师父连翻身都困难了,完全依靠胃管维持。卢伟会给他定时翻身,按摩身体。就这样伺候了几个月,卢伟把师父送走了。这件事给当时的医生、护士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老田、老米这些老患者也都看在眼里。所以即使卢伟欺负人,他们也不讨厌他,因为他们知道卢伟本性不坏。只是大家没想到,卢伟重复了师父的老路,5 年后也住进了精神科病房。
2008 年,卢伟 33 岁,他喝酒后开始呕血,查出了肝硬化早期。医生跟他说,必须戒酒。卢伟主动来到我们这里。他不敢喝酒了,但因为戒断反应,他开始手抖、浑身出汗,听到走廊里的声音就害怕,常常哭。
第一次来,他决心戒酒养好身体,回去好好过日子。家人都很介意“精神病院”这几个字,打算把卢伟送去疗养中心。他坚决反对,就是要来我们这儿。
老米每天都趴在窗边看外面发生的一切,他还记得卢伟第一次来的场景。那天来了好几辆豪车,老米兴奋地叫大家去看,二楼窗户上趴了一溜儿人。卢伟从车上下来,还算精神,背着个包,后面还有人拉着他的箱子。刚开始老米就觉得卢伟眼熟,又不敢认。卢伟独自住进三人间,也不跟大家说话,整天拉着窗帘,开着灯,躲在床上看武侠小说。卢伟只待了一两个月,回去没多久,又回来了。老田说:“酒蒙子都这样,没脸。”2009 年年末,卢伟离婚了,他说自己喝上酒就变成另一个人,最终有一天,他在家喝酒时,老婆说再喝就离婚。卢伟什么都没说,只是从冰箱里又拿了一瓶酒。
我问卢伟,喜欢喝酒之后的自己,还是不喝酒的自己。他说:“喝了酒的自己。”每天早上起来,他都告诉自己,“只喝一瓶”。结果喝了一瓶后,他就数不清后面喝了几瓶了。他喜欢看金庸的小说,最能理解乔峰无处可去的痛苦。因为卢伟的屋子总是很暗,听他说话,想象他描述的画面,都会让我觉得恍惚。他说:“武侠就是一个梦,生活太苦了,醒了又干吗呢?”
七
翠花和 8 只小猫被抓走后,卢伟除了抽烟就是睁着眼躺在床上。他不看小说,也不和人交流,整天失魂落魄的。每次看到我,他只是打个招呼,不愿聊翠花。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他。
一天下午,他一个朋友来病房,说要请假带卢伟出去洗澡。医院规定带患者出去要签保证书。一般直系亲属来我们才会同意,朋友来是不让带走的,只有卢伟可以破例。东北人喜欢去澡堂子,以前这个人也带过卢伟出去泡澡、吃饭,每次都是准时回来,我也就同意了。那天晚上卢伟很晚才回来,开门的时候,我闻到他身上有浓浓的酒味儿。“你不想活了?!”我质问他。这几年卢伟都是喝得难受了才住院。他的肝硬化加重了,胃也有大溃疡,呕過很多次血。外科医生跟他说,如果他再继续喝,就只能胃大切。切了胃,肝又不好,以后的状况真的不敢想。
卢伟舌头都硬了,醉醺醺地跟我说:“活着有什么意思!”护工带着几个人把他抬上楼,其他人看卢伟喝成这样,已经见惯不惊了。我生气地对他朋友喊:“你不知道他啥毛病啊!你带他走的时候跟我保证了什么!”那个朋友觉得理亏,一个劲道歉,说自己拦不住他。
当了多年精神科医生,我同情病房里的很多患者,觉得是命运戏弄了他们,是老天不公平才让他们受此劫难。但我一点都不同情卢伟,我对他说:“我觉得你活该。你自己不愿意醒,谁也拿你没有办法。”第二天早上,卢伟觑着眼睛看着我说:“陈大夫,我想清楚了一件事。我不能在这里躲一辈子,我还是得出去。”“一定要喝了酒才能想清楚吗?你出去要是再喝,真会没命。”卢伟说自己不能一辈子都活在梦里。
养翠花的这段时间是他这辈子心情最好,感觉最踏实的几个月,他有了牵挂,有了寄托。卢伟觉得,自己应该出去照顾女儿。“我也看不起我自己,但是这一次,我走了就不回来了。”
卢伟给自己定了个任务——减肥 20 斤。不减下来,就不离开医院。他让朋友送来 iPad,里面下载了很多减肥视频。这还引起了其他患者的嫉妒,一时间好多人都让家里人买。但是病房里没有 Wi-Fi,如同想抽烟得找护工借火,他们想看点什么,也得找护士或护工帮忙下载。
因为翠花的离开,屋子里原本为翠花准备的东西都被拿走了。卢伟把另两张床推到边上,挪出一片空地,开始跟着视频跳操,早晚各一遍。我看过他跳操,非常认真,汗水打湿了地面。他真的开始瘦了,之前挺着的一点啤酒肚也渐渐消失。在他的带动下,病房里好多患者、护士和医生都跟着一起跳操。他的三人间装不下这些人,大家就把跳操的场地挪到活动室。
不到两个月,卢伟真的减了 20 斤。卢伟去跟其他人告别:“我这次走,就再也不回来了。”翠花的三位干爹来送他。老田让他“出去好好过”;老邹让他“别回来了”;老米因为翠花的事情,一直没从抑郁状态走出来,送卢伟的时候,一直在抹眼泪。
卢伟离开一个月后,有一天我上楼查房,站在活动室门口往里看。固定在墙上的老式电视机在放电视剧,老田找不到遥控器,踮起脚按键换频道;老邹和一个患者在下象棋;老米终于从抑郁里走出来,乐呵呵向我打招呼。换完频道,老田走过来跟我说:“卢伟走一个月了,这次怕是能挺过去吧。”一个月是个坎,卢伟从第一次住院开始,每次出院不到一个月就会回来。我觉得这次他真的下了决心,应该能行。老米凑过来说:“卢伟还得回来。”老邹也觉得卢伟还得回来:“人犟不过命。”
很多人认为精神病患者没有理智,其实这是偏见。他们只是在发病的时候才会失去自知力,分不清现实和幻觉。听着翠花干爹们的讨论,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只是盼望卢伟能从那天下午的梦里走出来,毕竟他的母亲已经离开他快 30年了。
八
一天下午,主任接了个电话,让护工把三人间收拾一下。卢伟又被抬回来了。他回家将近一周,又开始喝酒。一旦开始,他基本就不吃东西,不喝水,只喝啤酒。一天两箱三箱,最多再吃一点点花生米。
发现卢伟酒后的状态不好,父亲让他戒酒两天,两天后他出现了严重的戒断反应。他说有人对自己开枪,躲在被子里瑟瑟发抖;还把枕芯掏出来,说翠花就藏在里面;一会儿又开始号啕大哭喊妈妈。打了针后,卢伟稍稍安静,缩在被子里发抖。又过了两天,卢伟上厕所时突然晕倒,我们这才发现他有胃出血。
院长带着其他科的医生来会诊,和卢伟父亲在我们科的办公室商量。当时卢伟的血红蛋白不到 60 克,连正常人的一半都没有。如果保守治疗止不住出血,只能手术。他还有严重的精神症状,不知道能不能挺过去。
父亲来到屋里看卢伟。这个头发花白、个子不算高的老男人,平日里哪怕不说话,都让人觉得气场十足,一看就是主事的人物。他俯身摸了摸卢伟的脸,然后向护士请教如何看监护仪上的数字。他躺在了旁边的单人床上,头枕着手臂,侧着身子,默默注视缩在被子里的卢伟。在他面前,这个快40 岁的男人似乎在母亲离开后就停止了成长,当他脆弱的时候、委屈的时候、孤单的时候,就会变成那个在父亲工厂门口,不知所措地站在原地的小男孩。
一周后,卢伟的身体指标逐渐恢复正常,他又拿起了不知道看了几遍的《天龙八部》。我问卢伟:“怕了吗?”他放下书说自己不太怕死,但舍不得女儿。他脑子里有好多个场景,但分不清真假,其中一个是他出校门,母亲在马路对面看着他,一直跟着,却没走上去和他说话。我觉得影视剧里好像有这样的场景,他应该是记混了。常年喝酒的人是有“错构”的,会分不清事情的时间地点。但我不忍指出。
我问卢伟:“以后还走吗?”卢伟说:“这次不走了。”后来不知道卢伟是怎么和领导那边商量的,没过多久,他父亲送来一只灰色的英短猫,怕猫怀孕,选了只公猫。猫送来以后,翠花的三位干爹又来帮忙了。这一次,条件不再简陋,同时带来的还有漂亮的猫屋,各种养猫需要的东西也不再需要遮藏。
因为是公猫,“二嘎子”这个名字终于能用了。我说这猫看起来很傲慢,和这名字不配。他们倒不介意,经常在走廊里“二嘎子、二嘎子”地大喊。我常看到卢伟坐在床上看武侠小说,二嘎子则团成一团,趴在被子上。卢伟翻书的时候会下意识地摸一下二嘎子。只是他屋子里的窗帘依然拉得严严实实,很少有阳光照进来。
看着卢伟和二嘎子,我想起另一个养猫的朋友。他的猫之前总在饭店周围流浪,每天捡垃圾吃,后来去了他家,吃上猫粮,就再没翻过垃圾桶。要知道,多少猫都有过这个坏习惯,很难改。我倒觉得,或许是猫也知道垃圾不好吃,现在过上好日子了,那些艰难求生的过往就可以迈过去了。
卢伟的坎儿是母亲离去,那之后他的成长、人生都停滞了。他反复努力想迈过自己的过去,失败了就酗酒,养好身体再继续挑战。最后他发现,躲进精神病院是最好的选择。在这里,他最不痛苦。这样未尝不可,只是他在外面的世界本可以拥有许多,比如妻女、父亲、优渥的家庭。
或许,卢伟也可以和这些毛茸茸的小家伙学一学——猫的记忆力很差,只会不断遗忘,唯一记得住的事就是:好好活下去。
(本文来源“天才捕手计划”公众号,作者相关文章已结集出版《寻找百忧解》。编者注)
(责任编辑:庞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