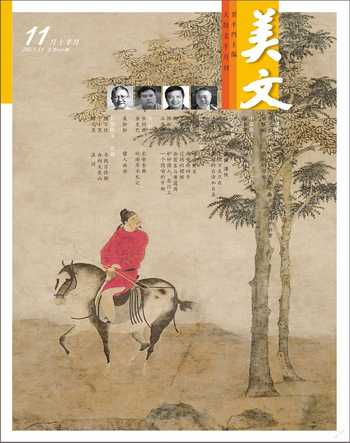野有蔓草
金克巴
野有蔓草
有时,蔓草虚张声势的样子在不经意之间便被人戳破。它们长着长着,就长成舒婷所说的凌霄花的翻版,即便颇具妍姿艳质,还要凭借别的高枝来炫耀自己。其实,在漫长的生命演化过程中,一切众生都蕴蓄和具备了自己的生存智慧。为着造物主秘不示人的原因,生命就像伯格森所说的爆炸一样,迸溅,再爆炸……如此延绵不绝。见诸狄兰·托马斯的笔端,是进程诗学的呈现;体现在植物身上,就成了“通过绿色的导火索催动花朵的力,催动我绿色的年华”。有人说,生命的意义或许就在于让自己凝结成生命史上的某个章节或字眼。所以,蔓草的生命姿态也并非可以出于人类的文化心理而一言蔽之。
在野外,与某些蔓草相遇,感觉宛如《诗经·郑风·野有蔓草》一样令人怦然心动,只不过,我的惊鸿一瞥与婀娜身姿的硕人无关,我是被大自然摄人心魄的美给征服了。记得那一次,穿过石岩湖畔的绿道,走在长长的木桥上,脚下传出跫跫橐橐的足音。两边是婆娑的碧树,不远处是一泓沉静的湖水,湖对岸有一座藏于深山晨钟暮鼓的古寺,隐约露出飞阁流丹的一角,尘廛的喧嚣被大自然的绿色海绵过滤了一遍。我的目光蓦地被一种藤本植物深深地吸引,那是数株蔓九节。它们有着与别的蔓草相近的禀性——对一切支撑既充分信赖又满是好奇。但它们也自有令人惊艳的傲人之处,与别处的恣意纵横的姿态不同,这几株蔓九节是锐意探索平面世界的艺术家,它们在桥墩垂直的平面上用茎蔓与绿叶作画:只见蓬勃的生命力喷薄而出,清晰的树状、明快的网络,不可遏止地向上蔓延,如同一幅幅令人印象深刻的剪纸作品。玄秘的纽带将那几株大小不一的蔓九节连接在一起。它们是灵犀相通的孪生姊妹,脉络的走向极其相似。其修颀、荏弱又不失优美的形态,让我的双眸久久都移不开。有人说,它们是人工栽植的,但我可以肯定地说,绝对纯然天成。它们掌握了随物赋形的惊世绝技:落在巉岩上,就长成巉岩的样子;依倚在危耸的大树上,就直起身子一直往上爬;如果什么支撑都没有,就随遇而安,长成灌木的样子,当然还不忘让长长的枝条四处探询。那种惊鸿一瞥让我的心湖顿时泛起了一圈圈柔情的涟漪,让我想到蔓生叶、蔓生花、蔓生爱恋、蔓生忧伤、蔓生光阴、蔓生白发、蔓生思念、蔓生远、蔓生古意、蔓生苦瓜……连缀起来,就像一个五彩缤纷的花环。
我已经跟蔓一别如雨,睽违很久了。我怎么忘得了少不更事时曾经朝它殷殷地颙望。那时,它是一株主藤已经手腕粗的葡萄,长在村里一户既贫穷又多舛的人家的小院里,我的这个总角之交自幼父母双亡,一株堪称亲情纽带的葡萄就成了他最重要的精神情感的寄托。小院虽小,却听任季节更番,总是一片生机盎然,那边厢绿竹如箦,这边厢葡萄沿着一株一人合抱不过来的榔榆往上爬,一直攀上枝梢。总是适时地挂出数不胜数的小花,又很快更换新的点缀,呈献一串串葡萄。从院外经过的人总是条件反射一般往树上望,忍不住暗暗地咽下口水。其时,小小院落还为另一个奇怪的女主人所拥有——她是一个不幸的驼背老闺女,注定了终生守身如玉。葡萄已经青里泛红,村里许多顽童总是经受不住百爪挠心的诱惑,伺机溜进小院,恰逢此时,老闺女总是吱嘎一声推开房门,一时骂声大作,吓得一班小蟊贼慌不择路地逃走。
我做梦都想拥有自己的葡萄树,并且频频试验过,在我家小小的植物园里扦插过数株,其中一株一度长到数尺,但后来还是黯然夭折,就像在花样年华写下《少女的祈祷》的波兰少女——巴达捷美斯卡一样。我的葡萄虽然生命短暂,却曾经怀着美好情愫在阳光下一展不俗的身手。
自己栽植的葡萄不可期待,但我可以将目光投向野外呀!野葡萄已经在山野间舒展蔓延了千年万年。《诗经》告诉我们,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亨葵及菽。那时它有着我们现在听来十分陌生的名字:蘡薁。我喜欢它的另一个别称“猫眼睛”,的确形象极了,成熟时乌黑发亮,散发着黑泽和神秘。盛夏时节在山野穿行,不时可以与猫眼睛邂逅,适我愿兮。
让人耳熟能详的一处蔓草,早就在马致远行经的古道边蔓延开了,那是一个西风清冽的秋日,一根颇有年头的枯藤让小桥流水人家蒙上了挥之不去的惆怅。其实,自古以来人们都对“见金夫,不有躬”的蔓草的第一印象不佳,因为“木为独立难,寄彼高树枝。蔓衍数条远,溟濛千朵垂”。它还时常参与渲染令人心生凉意的荒芜之境,所谓“竹障山鸟路,藤蔓野人家”,就算原本还有些许人气,也被疯长的蔓草抵消大半。当然,也有我见犹怜的时候,北宋诗人张耒冠之以“秀蔓”,诗云“秀蔓依檐老,寒枝映屋疏”,似乎老与不老,都不改它的秀色可餐。
蔓是多变的、柔美的、惊艳的,有时还成了摄人心魄的山鬼的绝佳饰物,“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山鬼一出场,一身撷自天然的装扮就让人眼前一亮,且不说她还有更厉害的“大杀器”——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身姿更如弱风摆柳,只听她芳唇轻启,宛若天音……话音刚落就让人肾上腺素飙升,就连空气中也飘荡着荷尔蒙。三闾大夫诗中的山鬼,全无厉鬼的狰狞可怖,而是有如一缕林下清风的山之精灵。若有人兮山之阿,再崎岖的山路也让人颇觉不虚此行。
从蔓九节开始,蔓又回来了,它长裙曳地牵动着我的心。那是几年前,我正處于人生中并不鲜见的又一度赋闲。出租屋里的蜗居总不乏侘傺无聊的光景,我时常在附近依山而建的燕川社区公园的山径上蹀躞而行。想起康科德的圣人爱默生的话,“社会似乎是有毒的,我相信,针对邪恶的影响,自然才是解毒剂。”所幸,我没有中社会的毒,只不过有时以职场蹭蹬的方式为平静如水的平凡生活增添一圈圈涟漪罢了。南方的勃勃生机总是轻易就让一座不大的山林充盈着阴翳之美。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其实不必请明月来烘托山之幽邃,只需白晃晃的日光就好,蓊郁的林下,日光不到,让我感到别样的静谧之美,这种被恣意纵横的翠绿翼护的感觉,不正是我孩提时最熟悉的那种感觉吗?!在大自然中,物我两忘的最好方式就是待在一处阴翳的林下,不是观众,亦非演员,而是闲云野鹤。当我在南方的山径彳亍,总会遇到正在绽放的鸡屎藤。想不到吧,这种就连名字也沾染了秽气的蔓生植物,其实是药食同源的食材。其食用方法跟艾蒿相似,采其植株磨成浆汁,加入米粉与糖,蒸制成鸡屎藤糕。经过好一番“炮制”,虽然污名犹在,但已经变成美味可口的糕点。南方人相信,它具有辟邪的妙用,与艾蒿有异曲同工之妙。
为迎接新年到来,橙红的炮仗花“噼噼啪啪”地绽开了。这种花一如其名,形似炮仗,成簇成簇的,开成一片。惯常爬上墙头顺势蔓延,把一堵原本索然无趣的墙头装点得欢天喜地。当炮仗花的花之圆舞曲还在继续,花形比炮仗花要大得多的紫葳科亲戚——凌霄花也加入进来。其时已是明艳的人间四月天了。
凌霄花的文字记载出现得很早,在先秦诗歌中就已经时隐时现。彼时,人们称之为“苕”,带着一种晦涩、暧昧、忧伤的意味,比如“苕之华,其叶青青。知我如此,不如无生”,似乎让我们听到了来自社会最底层失意的咨嗟。凌霄虽美,人生实难。只是落草为人,生之来不能却,其去不能止,超出了个体的可控范围。
野有蔓草,禾雀花是不容无视的。暮春时节,草木蔓发,莺飞草长。羊台山溪谷的禾雀花如期绽放,像是特地为这些美好的日子而荟萃一堂,一簇簇、一串串,形似禾雀。但就算静如处子,那种群集的大阵势和振翅欲飞的模样,还是引得一拨又一拨游人慕名而来。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它们承袭传统的生活方式,在溪谷里漱石枕流,聆听山泉叮咚。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陶渊明与禾雀花或许不曾邂逅,却无妨他们灵犀相通。精神的洁癖也好,对生境的苛求也罢,都是世间既珍稀又矜贵的。溪谷里的无数禾雀花翅膀挓挲,不是炫美式的怒放,而是美得内敛,我见犹怜。
还有一种藤蔓颇具一番传奇色彩,它便是使君子——一种被冠以冠冕堂皇的名字的植物,据说和三国那个扶不起的阿斗有关。据说,童呆的阿斗跟影视剧里成年时大腹便便的憨相大不一样,其时,他是一个微胖的野孩子,成天胡天胡地地在外玩耍,皇帝老子拿他没辙,只得派人跟着。有一天,阿斗趁保镖不注意,摘下一把使君子的果子塞进嘴里,因为它们实在像极了缩小版的杨桃,已经吊他的胃口好久了。没过多久,他就捂着肚子震天价响地直喊痛,可让宫里上上下下都吓坏了,连忙去唤御医,好在没过多久,阿斗就拉下了几条蛔虫(那玩意儿从前没少折磨过我们村庄的孩子)。就那样经过阿斗一番折腾,使君子的果子是一种蛔虫药的消息一阵风似的传开了。可最后人们却硬是把这种新药的发现归功于刘备,且美其名曰“使君子”。在南方,使君子是一种寻常可见的绿化植物。有几年差不多每逢假日,我就飘荡在深圳光明的田园小镇,那儿有一片沵迤平原,水泥路面的田埂上每隔两三百米就有一个被使君子覆盖的路棚,花期绵长,散发着栀子花一样的芬芳,似在招呼路人:且在这儿歇歇!
和许多藤蔓一样,簕杜鹃除了惊艳,还像希腊神话中的普罗透斯一样多变。时而忝在灌木之列,时而厕身藤蔓圈子,它长袖善舞,枝条伸得长长的,似乎生怕与有缘人失之交臂。毕竟世间失之交臂的遗憾太多太多,遗憾得几乎连遗憾都来不及,最终遗憾充其量只是一通无可奈何的长吁。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只因浇漓是世道的常态,我心里的遗憾总是情不自禁就长出了横斜逸出的虬枝。真诚稀缺,许多人不得不依靠传染病一样的演技游走于自己所涉足的圈子。我秉持的态度是:不与虚伪作对,不配合表演,而是尽量避开。
在深圳呆的时日一久,我彻底被簕杜鹃给征服了。它明明有出众的姿色,金子一样的口碑,却穿街过巷低调得一如璅璅常流。这种俗称“三角梅”的植物有着昳丽身姿,完全配得上梅妻鹤子的林逋所谓的疏影横斜水清浅;至于暗香浮动月黄昏,对不起,在簕杜鹃的生命演化过程中,昂贵的香气实在是奢侈的赘余。有人说,簕杜鹃真惹眼啊!其实细看之下,其花很小,小得要仰仗强有力的代言人——鲜艳的苞叶来为之张目,所以欣赏簕杜鹃其实是在欣赏它的苞叶呢。试想:如果代言人不干了,簕杜鹃的感召力马上一落千丈,深圳“市花”的桂冠也随之摇摇欲坠。只是,作为花朵姊妹的苞叶才不会干出那种蠢行。想当初它们都是叶子,最早的花大概在一亿三千万年前才开始出现,在那个汗漫得离谱的地质年代,当时地球正处于恐龙的黄金时代。随后,花与苞叶的分工日渐明晰,厘清了各自的责任和使命,有的叶子拼力变异成花的样子,有的则在无数次试错之后变成了苞片。一株出色的簕杜鹃,荣光归于整个植株,乃至整个物种。为了让自己出落得光彩照人,它们在作无止境地探索,时至今日,其花容月貌越来越惊艳。每年秋天,深圳都会迎来两大花展:一是东湖菊花展,二是莲花山簕杜鹃展。簕杜鹃那繁多的品种拓宽了我的视阈,让我不由得赞叹这种易生易长的花卉所拥有的美丽富藏:你到底还有多少潜藏的美丽没有被人发掘?
十年前,我暂栖在石岩一个叫坑尾的地方,每日必经的马路边上有一爿小工厂,门边生长着一丛簕杜鹃,枝蔓径直攀上三楼之上。一年四季,它都在绽放,把整栋楼都置于它美丽的彀中,那种催动花朵的长盛不衰的生力,着实令人叹为观止。
苹 婆
不识苹婆先识假苹婆。识得假苹婆,也好。运用老子的辩证法思想,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真与假自然就是一片叶子的两面,意味着我跟苹婆的缘分相去不远。
那次,从大浪的登山口去登羊台山。山路忽上忽下,很快就汗流浃背,好在一路上泉水在叮叮咚咚地唱个不停,为周末的徒步平添了些许乐趣。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可还没走到水穷处,脚板就开始黏黏糊糊,走起路来拖泥带水。同样是行山的苏东坡,曾经思考过如果还没到所谓的目的地,歇与不歇的问题,一想到“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处”便如脱钩之鱼,身心释然。我在山溪边的一块巨大轸石上休憩,突然发现水里有几片绽开的荚果浮浮泛泛,像红色的鳑鲏在水面侧身游来游去,煞是悦目。就这样,我与假苹婆不期而遇。鳑鲏在千里之外,那是故乡池塘常见的一种小鱼,色彩缤纷,永远也长不大,入口尚嫌刺多肉少且苦,似乎生来就只是为了美而存在。而今,荚果好似鳑鲏的假苹婆就在眼前,我矫首仰望,树上还有,红彤彤的荚果一如绽开的花朵,上面点缀着几粒花生米一般大小的黑色种子,衬之以绿叶,极为赏心悦目。对植物迷恋的我来说,那就是惊鸿一瞥的初识。溽热的山间不时拂过一阵凉爽的风,我记住了你,假苹婆!然则,“真”苹婆在哪儿?
在南宋,“频婆”的字眼已经不时在字里行间闪现,它跃动于周去非《岭外代答》一书中:“频婆果,极鲜红可爱,佛书所谓 ‘唇色赤好,如频婆果是也。”二千多年前《诗经》描写女性之美: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其时,又有了唇若频婆。谢谢你,频婆!你又为我呈现了美好形象的一种。频婆虽然白天看上去红唇欲滴,但在微明的夜光里張开的荚果和里面镶嵌的大颗栗色种实宛如妩媚动人的凤眼,所以人称“凤眼果”。
时光前溯,在嵇含那本前无古人的《南方草木状》里还找不到频婆的绰约身姿,其时,它们大概还生活在南亚的赤地炎天之中。但嵇含笔下有一种语焉不详的果木——“海梧子,色白,叶似青桐,有子如大栗,肥甘可食,出自林邑。”试问:它会不会就是频婆呢?倘若它就是云遮雾罩的频婆,那它在岭南的出现就与此后的三藏法师无关了。
最常见的说法是,频婆是三藏法师从西域带回的。屈大均甚至还煞有介事地说,频婆跟诃梨勒、菩提树一起被杂植在虞翻位于广州的府邸中。虞翻是三国时东吴的文武全才,满腹文章韬略自不必说,还惯使一根长矛。据《三国志·吴书·虞翻传》记载,他可是货真价实的飞毛腿,可以日行三百里,并且还跟骑着马的孙策比试过。但这个旷世奇才最终还是因言获罪被贬黜到岭南。到了广州后,他以南越王赵佗的故宫为家,岭南的奇花异草似乎极大激发了他对草木园林的热爱,他把自家园囿的规模搞得很大,在里面广植花木,人称“虞苑”。试想如此瑰奇的虞苑,堪可慰藉流放者的心。白云苍狗,虞苑沐浴过唐时风,目睹了宋时月,到现在摇身一变成了光寿寺。令人存疑的是,如果频婆是唐三藏从西域带回来的,那已经是虞翻去世四百年以后的事情了,虞翻的频婆又从何而来?
在明人吴承恩的笔下不时闪现着“贫婆”“频婆娑罗”的字眼,恍若磷光熠烁的凤蝶。恍兮惚兮,其中有物。但吴承恩也搞不清频婆是于何时在中土落地生根的,反正在《西游记》的结尾,唐王李世民宴请自西天取经归来的唐僧,宴会上琳琅满目,珍果纷呈,果然中华泱泱大国,跟西域有所不同。试想唐僧师徒奔赴西天,一路上餐风露宿,偶尔才得以饱餐一顿,在如此空前的丰盛之下,自然不至于全然无感。席间就有橄榄林檎、苹婆沙果。设若苹婆是唐僧从西域带回,大概不会那么快就端到桌上。
由于一次改名,“频婆”变成了“苹婆”,有人干脆误以为“林檎”就是苹婆的别称,其实林檎是一种结小苹果的果木,跟苹婆八竿子打不着。但昔时岭南还有一首歌谣是这样唱的:“水樃林檎大小同,盘中不辨是雌雄。”
惚兮恍兮,就连才华横溢的明永乐年间的“江西才子”曾棨也钻进另一团迷雾。此君在廷对时,文思泉涌,不打草稿,纵笔就是两万字,然而,就连他也错以为频婆就是苹果。他在《频婆果》一诗写道:“果异曾因释老知,喜看嘉实出京师。芳腴绝胜仙林杏,甘脆全过大谷梨。”写的分明就是苹果,而非诗咏苹婆。
悬疑归悬疑,苹婆早就在岭南大地上扎稳了脚跟,长得枝繁叶茂。苹婆堪吃时恰逢七夕前后,凭着胜于甘栗的美味,成了拜七姐的祭祀供品,所谓氤氲香气,动于神明,给味蕾带来愉悦的苹婆也一定是神明乐于消受的。于是,岭南遂有了这唯美的画面:一群硕女,在中国传统的情人节之夜,向摆著苹婆的香案虔诚下拜,乞求佛眼相看的神仙姐姐金针度人,赐予她们巧艺,同时赐福家人,还有啊,祷祝自己所爱的人情比金坚。其实,冥然之中苹婆还真的有相思树的意思,它原初的译名“频婆”是梵语及巴利语的音译,本意是身影,意译就是相思树。叶玉森十分清楚这种树名的出处,他在诗中写道:“须曼犹开称意花,频婆自结相思果。”南亚的相思树落户岭南,凑巧的是,岭南人亦把它当作自己的相思树。
善戏谑兮,不为虐兮。整体来说给人带来美好感觉的苹婆,也有令人可发一噱的一面。剥开苹婆果时,其皮数层,层层剥开,始见其肉。于是,骂人脸皮厚就骂那人是“频婆脸”。其实苹婆何辜,它们小心翼翼包裹起来的美味,原本就是为自己的后代精心准备的营养套餐。
很可惜,现代性把许多传统习俗都打入了冷宫,自然也冷遇了七夕节。曾经作为拜七姐贡品的苹婆再也难以走入从前人们通过美妙仪式与神灵进行沟通的氛围。钟情于这种美馔珍馐的当地人,也大有一种与之睽违已久的遗憾,慨叹它的果期总是稍纵即逝。而作为外乡人,苹婆大抵只是惊鸿一瞥。
我与苹婆的邂逅是在松岗燕川一户原住民的院墙外,只见院内一片蓊郁,桂冠上挂着许多堪称惊艳的苹婆果,刹那之间就让我大为折服,“无论天涯与海角,大抵心安即是家”的感觉便又回来了。因为长久以来,对于在此间居大不易的我,与周遭世界的疏离感总是突如其来地窜出来攫住我。后来,我又在公园和路边频频见到假苹婆。尽管它们已经沦为一种泯然众人的行道树,但在我心目中还是有一种别样的感觉,我差不多就要脱口而出:啊,假苹婆!
(责任编辑:孙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