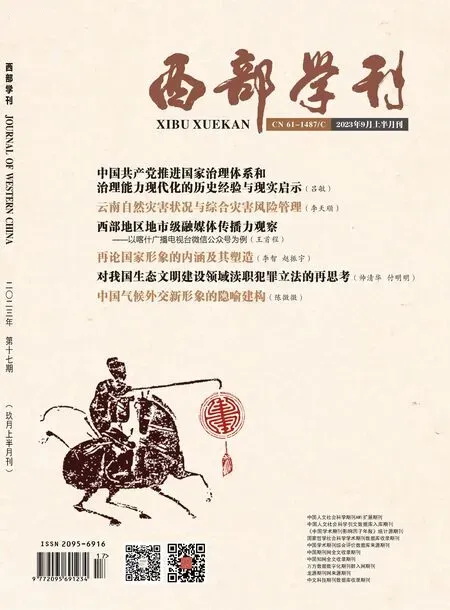“悲悯”抑或“虚妄”?
——评罗斯金“情感误置”之现代性张力
蔡成珍
(广西外国语学院,南宁 530200)
至二十世纪初,约翰·罗斯金①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 年),英国作家、艺术家、艺术评论家、工业设计思想的奠基者,还是哲学家、教师和业余的地质学家,被人称为“美的使者”,对工艺美术运动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著作有《现代画家》《建筑的七盏明灯》《威尼斯之石》等。的精神遗产已经引起中国知识界的广泛关注:李叔同称罗斯金为“天才预言家”、李大钊赞许其“道德良器”、辜鸿铭推崇其“和平的文明观”,众多文化名人都在其相关论述中提及罗斯金[1]。 本文尝试从对罗斯金“情感误置”概念的重新审视,探究其“悲悯”求真与“虚妄”反真之间的现代性张力,洞悉作家对人类“真实”与“诚实”的生命精神实质的呼唤。
一、“悲悯”之力与“诗性气质”
约翰·罗斯金作为维多利亚时代的精英人物,他的诗性散文深具悲悯意识,同时渗透着“现代性”的思辨张力。 囿于彼时民族革命性启蒙话语传播的诉求,富含颇具中道气质的“悲悯”精神的罗斯金的译介始终有限。
1856 年,罗斯金在《现代画家》(第3 卷)中提出“情感误置”(Pathetic Fallacy)的概念,用以指涉人类将意图、感情、脾性及思想投射到无生命的物体之上,借此赋予其生命的品性。 强烈的情感容易使个体产生虚妄的情感,此种“误读”(falseness)似乎是人类先天之秉性,将人们对外物的情感投射到外物之上。 值得思考的是,罗斯金的目的是否在于借此否定艺术家的强烈情感,抑或是为了提出质疑? 值得注意的是,罗斯金赋予“情感误置”以强烈的现代性思考。 他的“情感误置”并非是对“情感”的否定与摈弃,而是借此提出质疑,隐晦地传达颇具启蒙现代性色彩的批判性。 现代性是一种对时代进行持久性批判的哲学态度与气质,其本质上是一种质疑的精神。
(一)“情感误置”与“诗性气质”
“情感误置”之现代性张力首先体现在“卓越的诗性气质”,而“诗性气质”的第一个维度在于“敏锐的感受力”:
在“情感误置”中,蕴含有这种“卓越的诗性气质”(the consummate poetical temperament)的确切类型。 因为,应该清楚并持久地铭记,一位诗人的伟大性取决于这两种感觉官能:敏锐的感受力(acuteness of feeling)及其掌控能力。[2]215
透过光影交织的多元建筑,罗斯金尝试重构信仰的力量。 在《建筑的七盏明灯》(后文略称为《建筑七灯》)的开篇处,他探讨了大写的“建筑” 之含义:“‘建’字面之义乃是强化、使之‘确定’之意(confirm)。”[3]在古希腊语中,“建筑”(architectonice)乃是由“原理”与“工匠”构成的合成词,“技艺”(techne)一词则泛指所有类型的“创造”(poiesis)[2]258。 在“石头手稿”(manuscript of stone)《威尼斯之石》中,他运用了丰富的类比与隐喻手法,将“阅读”(“文本作为建筑作品”(text as an architecture work))与“建构”(“建筑作为语言”(architecture as language))融合[4]。 由此,“《建筑七灯》通过类比将艺术道德化,并将其承载的重要真理通过意象和一种独特的措辞方式传递出来。”[5]事实上,罗斯金将绘画、建筑、雕刻与诗歌视为同质的事物,颇富有远见地对“线条”“色彩”“纹饰”等视觉形式要素给予理性关注,强调对情感应有所克制,尽力用色彩与线条将对象描绘成中性物体,如此方为健康的“自然”之道。 在拉斐尔前派看来,对那些表达真情实感的“古老遗物”的同情颇为重要,其隐性地传达着对平等的追求,拒绝代表等级权力的构图,彰显颇具早期现代性的谦卑与内省精神。
(二)“诗性气质”与“悲悯”之力
“诗性气质”的第二个维度在于对“悲悯”的掌控力。 约翰·罗斯金作为维多利亚时代的精英人物,深具民族忧患意识,颇具世界主义的人道精神,其与中国传统的天下主义颇有相通之处。 或如十九世纪一批西方学者注意到的:“不论是建筑还是画作,罗氏擅于借助表层的哥特建筑‘图像叙事’,通过‘多种语言、类比与隐喻的综合运用’将艺术、人类的道德与社会民族道德联系起来。”[6]安东尼在《约翰·罗斯金的劳作:罗斯金的社会理论研究》一书中,系统地从法律、正义、权力、社会、经济、教育、工作、革命及遗产九个角度梳理了罗斯金的综合贡献,他坦言对罗斯金“一致的理解”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柏拉图“理念说”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对其的影响[7]。
由此,如果说罗斯金的“石头书写”彰显了感官的真实,其构成“敏锐的感受力”的第一个维度,那么,其第二个维度在于通过主体的想象力,真诚地展现“悲悯”之力。 《庄子·知北游》有云:“精神生于道,形本生于精。”《韩非子·解老》有载:“圣人爱精神而贵处静。”《孟子·告子上》曰:“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张子全书·语录》讲:“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在横渠先生看来,“心统情性者也。”性,乃人之本性,情乃性之表现。 如孟子所见,“情”未必为恶,喜怒哀乐,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情感表达合乎理解与情景,即谓“和”。 悲悯之“悲”指慈悲,即对人间的苦难有一种感同身受的情感,其根源源自对世界的强烈的热爱,并通过颇具中和精神的“悲悯”之心体现出来。
但值得注意的是,英国文化研究学者保罗·吉尔罗伊、伊恩·鲍科姆及威廉姆斯曾犀利地批判道:罗斯金的美学为“大不列颠帝国的殖民野心”提供了文化背景支撑,将该国的文化遗产进行了重塑,以期为文明扩张提供隐性辩护[8]。 诚然,罗斯金自小深谙古典文明遗产,但其毕生对西方文明遗产的批判以及重构性实践往往更容易被世人忽视。 在晚年,忧虑的他选择离群索居,甚至宣称自己放弃了早期“福音派新教徒”立场,转而称自己为一位“完全不信教的人”(a conclusively unconverted man)。
面对于自身散文中柏拉图式的讳莫如深的“理念世界”,罗斯金阐释道:
关于我自己,我可以告诉你们的是,你们读我的著作之时,千万勿将其看作仿佛至少是我个人性格的表达。 除了《致大不列颠工人和劳动者的信》和《过去:约翰·罗斯金自传》之外,其他皆是为每个人定义的艺术与工作法则——无论其为基督徒或犹太人、克里特人或阿拉伯人。[9]549
在后期创作的《野橄榄花冠》中,他提出了与文明研究者汤因比诉求颇似的“第四种宗教”之希冀,即能够在面临“挑战”之际,重新激发活力,积极“应战”,构建开放、多元文明协商共存的图景。 罗斯金以开阔的视野,同英国浪漫主义者们一道,有效地对“一个民族的真实心智”进行某种批判性重构。 在他看来,民族心智“最好通过审视其最伟大人物的思想来确定”[2]244。 以同时代风景画家透纳的创作为例,后者透过变幻莫测、却真实无比的光影线条,创造摄人心弦的情感张力。 他对英国诡谲多变的气候的刻画,以及早期的历史风景画作,延续了新古典主义的技法,展现了“典型美”的自然,而其成熟期逐步转向转瞬即逝的“生命美”的呈现——生命的力量与勇气。 在罗斯金看来,透纳成功地呈现了伯克式的崇高之力,即个体如大自然的气流、风暴般,在周而复始的运动中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二、“虚妄”无力与“病态精神”
有西方学者曾指出,罗斯金儿时的诗歌作品《罗斯金诗集》创作颇具新意,在现代文学史上地位较高。他的后期散文亦秉承早期诗作之真情实感,诗意化地效仿亨利·梅尔维尔,呼唤“善人在共同体的责任”,并倡导个体品格构建中“知识与爱的融合”。 因此,不得不提的是,就罗斯金“情感误置”的谬论性而言,它无疑是一种“病态精神状态”的标志(a morbid state of mind),是一种相对愚钝(weak)的精神状态。”[2]218
(一)“情感误置”与“病态精神”
当维多利亚艺术界古典式仿制品之风盛行时,罗斯金倡导恢复前拉斐尔时期的纯粹、严谨与质朴。 在《现代画家》中,他批判道:“克劳德·莫奈和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景画家们‘那笨拙的、伪如画、伪古典的头脑’(the blundering, pseudo-picturesque, pseudo-classical minds),不仅完全缺乏荷马般的实际常识,还同样无法感受水仙花草坪、翠嫩白杨以及蔓藤静谧而自然的优雅与甜蜜。”[2]244透过对艺术仿制品的批判,他进一步斥责道:“与现代诗人或小说家一致,我们认为希腊人富有诗意、理想与想象力、设想他们对其神话与世界的想法和我们的一样虚幻和虚假(visionary and artificial)。”[2]245-246
他把济慈放在他的第二等诗人中——也就是那些受“感受谬误”影响的诗人;他注意到济慈的“病态张力”(morbid strain)。 这是一种“温柔的悲伤”(gentle depth of sadness);他的思想可与透纳媲美,而且,如透纳般不被充分欣赏。 济慈的幻想是精致的;他的色彩“丰富无比”;即便偶逢可怖的主题,亦会通过完美的艺术呈现;他的刻画蕴含某种“精巧的真诚”;他的美感堪比透纳。 他的想象力使他能够精准地阐释希腊人的宗教。[2]107-108
由此可见,罗斯金极力呼唤创作之“真实”与情感的“诚挚”,在他看来,脱离中和的自然法则的作品,无疑是流溢着“病态精神”的虚妄之物罢了。
(二)“情感误置”与“虚妄”无力
在《现代画家》中,罗斯金进一步强调:“情感误置只有在它是悲悯(pathetic)之时才强大,只有在它虚妄(fallacious)之时才无力。”[2]220在他看来,西方传统的“希腊的与中世纪的——两者都由于其各自的目的而毁灭,希腊的智慧宗教是一种错误的哲学——‘似是而非的学问’(oppositions of science)”。 值得注意的是,此观点源自保罗对提摩太的劝诫,而前者成功地推动了世界宗教的生成。 或许在罗斯金看来,无论脱离真实性,抑或违背自然法则的个体,即使看似“精美绝伦”,却浸染着文明的腐朽、虚伪与惰性。
尽管罗斯金被意大利艺术批评家文杜里视作“浪漫主义批评的顶峰”,但从1850 年代开始,他的写作风格逐渐开始脱离早期浪漫主义的倾向。 他批评拜伦、雪莱等积极浪漫主义者创作中“较少的真实性感知”、较多棘手的“自我中心性”(selfishness),以及华兹华斯的“哲学家意识”,却尤为推崇司各特的“全然的谦卑与无私”[2]244。
值得注意的是,个体之“悲悯”之心亦需适度,否则仍有身陷虚妄无力之虞。 尽管罗斯金创作颇丰,然而,尽管其理论文章不断地见诸于报刊书籍,其后半生也不断地将其理论诉诸社会改良实践,维多利亚时人囿于对其晦涩的“词语谱系”的有限理解,批判之声屡屡不绝于耳,令忧虑的罗斯金愈发身心俱疲。 在关于其后半生的传记中,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真实描述:
罗斯金以前经常生病,曾有或长或短的时段,他都无法写作。 他1871 年的疾病比以往任何不舒服都更令人担忧——对罗斯金和他的朋友们来说,他看起来已经奄奄一息了。 这种崩溃或可被称为“某种精神崩溃”(a mental breakdown),因为罗斯金经历了幻觉和身体崩溃,因为在1876、1878、1881、1883 以及之后的日子里,罗斯金经历了幻觉(hallucinations),其肯定是精神性的。 1871 年7 月的幻觉被罗斯金称作“梦”,并于次年在其牛津的一次演讲中被描述[9]206。
罗斯金出现了持续的剧烈呕吐、疲劳、高烧和谵妄梦[9]207。
从他自己在危机、疾病和迫在眉睫的死亡气氛中恢复(from his own recovery in an atmosphere of crisis, illness and imminent death)。 他个人的痛苦影响了他的写作,尤其是《过去:约翰·罗斯金自传》(His personal agonies had an effect on his writing, particularly on Fors Clavigera)[9]209。
生命的忧虑成就了罗斯金超越时人的格局与视野,但是也逐步压垮了他的身体。 在罗斯金晚年,身心俱疲的他最终决定放弃从1879 年开始撰写的《过去:约翰·罗斯金自传》这本书。 其中,他回顾了“忧虑”带给他的益处——“悲怆与智慧”的并存。 诚然,在罗斯金八十多载的生命历程中,他有效地平衡了理性与情感启蒙之间的思想张力,殚精竭虑地为世人谱写中道的生命智慧。
三、结语
宋儒张载曾言,“无我而后大,而大成性而后圣。”个体通过对“私心”的克制,人心可复归天地之心。 值得注意的是,此种“无私”并非基于自我的弃绝,唯有当个体生命精神饱满之时,方能共情。 约从1860 年代开始,罗斯金愈发意识到活跃的市民生活与健康的民族文化生活之间的紧密关联。 在1864 年其父亲去世之后,罗斯金意识到自身应摆脱对财富的虚荣,接着,在母亲即将离世之际,罗斯金在《致大不列颠工人和劳动者的信》中做出了“高度保守乌托邦主义”建构的经典陈述,重新诠释“财富”概念,拷问“国民财富性质”的政治经济学,并借助“词语系谱学”重建权威知识话语[10]。 与此同时,他更加执著地投身到其社会改良理论的实践中去。
概言之,约翰·罗斯金一方面强调恢复个体真实的感受力,一方面透过彰显“公共纽带” (communal bonds)精神的中世纪建筑艺术,重塑共同体中个体真诚的“悲悯”之力,因而不失具有持久的现代性启蒙思想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