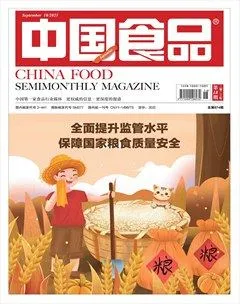中西饮食差异之跨文化比较
向思前
各个民族生活在不同的地域,而自然地理环境千差万别,由此催生出各具特点的饮食文化。饮食文化虽被归类于表层文化,但又受到深层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饮食文化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思想观念和民族性格的差异。本文从饮食观念、饮食对象、饮食形式三个方面来比较中西饮食之差异,并探究造成这些差异的深层次原因。
一、饮食观念上的差异
1.艺术性与科学性。中国饮食文化受古代朴素的辩证法思想的影响,讲究整体的配合,十分注重食物的色、香、味、形、质一应俱全。一是色,食物要有美观的色彩搭配,用几种不同颜色的食材做成一道菜,色彩要看起来和谐而不冲突,给人一种美的视觉享受,具有可观赏性。二是香,食物的香味能够刺激人的嗅觉器官,引起人的情感性冲动和思维联想,正所谓“闻香下马”,特定的香味会让人不自觉地分泌唾液,激发人的食欲。三是味,俗话说“民以食为天,食以味为先”,味是评价食物的最高准则,是中国饮食的核心所在,使得中国饮食具备有别于西方的独特魅力。四是形,即食物的样式和造型,厨师要巧妙运用一定的美术手段加以装饰,使食物的呈现更具美观性。五是质,即食物的“质地”,以触感、口感为评判标准,包括脆、嫩、有弹性等多种不同的质地感觉。中國人尽可能地调动了视觉、嗅觉、味觉等多种感官功能,体现了对于食物更为高级的追求,使饮食不再只是停留在饱腹这一原始的物质需求阶段,而是上升到了精神享受这一更高层面。
西方饮食理念与其形而上学的哲学思想体系相适应。西方人追求的是科学与健康,十分注重食物的营养价值,会考虑每顿饭的营养搭配是否合理、营养成分是否都能被身体所吸收。而且不管是美国东部还是西部的高级饭店,牛排的口味几乎一致,这是因为其烹饪过程都是严格按照统一的标准来执行,菜谱的使用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西方菜谱中一般采用“克”为重量单位,很多家庭会准备适合家庭厨房的小称重器,以便精确把握食材或调料的分量,还会严格把控每道程序的时间,以确保做出来的食物味道科学营养,这种规范化操作使烹饪丧失了许多乐趣和变化空间。
在菜肴命名方面,中西方也会有不同的倾向。除了一些大众化菜肴以写实的方法直接命名外,中国人还会赋予菜名一定的文学内涵,通过更具特色的名字来契合不同主题宴席的意境。中菜命名讲究雅致、含蓄和吉利,会使用一定的修辞手法寄托人的美好情感,比如升学宴上的红烧鲤鱼常被叫作“跃龙门”,寄托了对学子的美好祝福。西菜命名则十分直接了当,一般直接突出原料或烹饪方式,让人一看就知道是什么菜,少了一些艺术性,更为直观理性,比如煎牛排、蔬菜沙拉、烤鹅肝等。
2.“泛食主义”与“实用主义”。中国有一种“泛食主义”的文化现象,超越了一般的物质层面,渗透在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的传统节日大多离不开一个“吃”字,除夕要吃团年饭,元宵节要吃元宵,端午节要吃粽子,中秋节要吃月饼。通过饮食行为表达情感的活动也几乎伴随着人的一生——婴儿出生百天会有百日宴;生日会有生日宴;结婚时要大摆酒席以示喜庆;老人辞世也要摆席以表追悼;有客远道而来要吃,称之为“接风洗尘”;朋友即将远行也要吃,称之为“践行”等。通过“吃”,人们可以互相交流信息,联络感情。以上各种活动充分反映了中华民族对于饮食的重视程度,说明了饮食活动背后蕴含着丰富的心理预期和文化意义,从而获得了更为深刻的社会意义,饮食已经上升为表达情感、社会交际的精神需求。语言中的许多词汇也反映了“泛食主义”的文化现象,易中天在《闲话中国人》中对此种现象进行了十分生动的描述:“如把职业称为‘饭碗,思索叫‘咀嚼,体验叫‘品味,嫉妒叫‘吃醋,司空见惯叫‘家常便饭,轻而易举叫‘小菜一碟,广泛流传叫‘脍炙人口……都是见惯不怪的说法。”
而在西方国家,饮食并不具有如此深刻的社会意义,只是一种基本的生存手段和交际方式。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将人的需求划分为五个层次,饮食被划分在第一层,是人类最基础的物质需求,更强调饮食只是人进行其他活动的物质基础,没有赋予其精神内涵。林语堂先生曾说:“西方人的饮食观念不同于中国,英美人仅以‘吃为对一个生物的机器注入燃料,保证其正常的运行,只要他们吃了以后能保持身体健康、结实,足以抵御病菌、疾病的攻击,其他皆在不足道中。”由此可见,“吃”在他们的心目中只是起到了一种维持身体功能的作用。就交际手段而言,美国《礼仪事典》一书中讲到宴请的目的时,作了如下的总结:“向提供服务者表示感谢;对刚刚达成的一笔交易表示庆祝;为了赢得客户或新客户的信任;请人帮忙;引见他人;建议或讨论某想法。”从中可以发现,西方的“吃”是为了达到某一特定目标而进行,停留在普通社会交际这一表层,并没有像在中国那样被赋予更为深厚的文化意义和情感价值,饮食上表现出很强的实用主义与功利性。
3.“和合意识”与“个人意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倡导“天人合一”,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体现在饮食上则为“五味调和”,而西方国家强调突出个性,追求个人特色,体现在饮食上就是保持本味,两种不同的观念在菜品制作时便可看出差异。中国人烹饪时以五味调和为基本原则,常将食材与各种调料一起烹饪,既注意顺序,又把控时间,食材与调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从而产生出一种全新又和谐的美味。比如福建名菜佛跳墙,所需食材与配料多达十几种,有些配料虽已尝不出其原味,但整体而言却是令人叫绝的佳肴。而西方人烹饪时以突出个性为基本原则,常将多种食材分别加工,食材与配料常常泾渭分明,保持了其本味。比如,胡椒粉、柠檬汁一般是食客自己现加;鸡肉沙拉只是对鸡肉进行了处理,然后直接与生菜、小番茄、沙拉酱等配料混合在一起,食材都保留了原本的味道。
二、饮食对象上的差异
1.饮食结构。由于中西方自然地理环境的不同,人们对食物的选择也不一样。中国的气候条件适宜发展农业,早在先秦时期就形成了以谷蔬为主的饮食结构,肉类只有在节日或者祭祀时才会吃,因此自古就有“菜食”之说。《国语·楚语》中记载:“庶人食菜,祀以鱼”,意思是说平民一般以菜食为主,鱼肉只有在祭祀时才可以用。虽然如今生活水平提高,肉类也进入日常饮食中,但是仍少不了各式各样的蔬菜。而西方受游牧文化与航海文化的影响,畜牧业、渔业较为发达,主食为肉类、奶类,蔬菜只为辅助食物。因此,有学者认为中西不同的饮食结构塑造了不同的民族性格,即中国人是植物性格,而西方人是动物性格,体现在外在行为上就是中国人安分守己,西方人喜欢冒险与征服。
2.加工方式。中国人将烹饪视为一种艺术,创造了蒸、煮、焖、炖、爆、烤、煎、炒、炸、拌、烩等多种多样的加工方式,在原材料的粗加工上又有片、块、条、丁、末等多种多样的形状区别。同样一种食材,中国人可以通过不同的烹饪方法让它更具可塑性,变成各具特色的美味。比如食材是一条鱼,便可以做成水煮鱼、红烧鱼、干锅鱼等,在形状上可以是鱼片、鱼块,也可以是整鱼。相对来说,西方人的烹饪方法就比较简易,多是煎、烤、炸等比较常见的方法,同一种食材做出来的菜品样式没有那么丰富,口味也比较单一。
除此之外,中国人在刀工、火候方面都十分讲究,技艺性很强。《礼记》记载的周代八珍之一的“渍”就是古人讲究刀技的一个范例,不仅要求把肉切得片薄如纸,还讲究切断肌肉的纹理,达到“化韧”、烹调不变形的目的。火候的把控亦是如此,火候不到则生,才一过火就老,这个过程弹性空间大,只能凭厨师的经验来把握,厨师要时刻关注食物的变化,以此来调节火候的大小,使食物根据厨艺的不同呈现出不同的风味与特色。西方菜肴则没那么讲究刀工,经常直接用大块的食材,或者借由专门的机器来处理,每次做出来的食物样式或形状几乎一样。至于火候,一般都有明确的烹饪时间标准,甚至会用计时器来严格控制时间,他们在意的是烹饪过程是否按标准进行、营养成分是否保持,更多追求的是烹饪过程的技术性。
三、饮食形式上的差异
1.餐具的选择。中国人自古以来就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而西方人则认为人应该去征服、利用自然,这一点在餐具选择上有着明显的体现。中国人选择用筷子进食,筷子的制作材料本就取自于自然,并且运用了杠杆原理,任何形状的食物都可夹起,整个进食过程十分平和;西方人选择用刀叉进食,刀叉是金属制品,有一定的锋利性,进食过程略显攻击性。法国文学家罗兰·巴尔特认为筷子不像刀叉那样用于切、插,因而“食物不再成为人们暴力之下的猎物,而是成为和谐地被传送的物质”。
2.用餐方式与礼仪。传统中国人的宗族意识和家庭观念十分突出,反映在飲食文化上就是聚食制,人们往往喜欢围圆桌而坐,把所有的菜都放置于桌上,并且十分乐意为别人布菜,通过吃饭和家人进行情感上的交流。而西方人的个人意识相对来说更为突出,往往采用分食制,家人一起用餐时每个人有自己单独的盘子,食物都会提前分配好,他们只会吃自己盘子里的食物,甚至在多人聚会时也是各点各的食物,可以不考虑他人的口味喜好。自助餐这种形式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每个人端着自己的盘子各取所需,可以随意走动,大家一般互不干扰。
中国饮食讲究“礼”,“礼”的精神一直贯穿在大众的饮食过程中,最为显著的是用筷礼仪。筷子不仅仅是进食工具,还蕴含了“天人合一”的文化内涵,用筷时也有诸多礼仪。比如,吃饭时不能将筷子插在米饭里,因为这是供奉死者时才有的行为;不能用筷子敲打碗或者盘子,因为乞讨的人才会这样做;用筷子夹菜时不能在菜盘里任意翻动,因为这种动作很不雅观。西方餐桌上也有体现其独特文化印记的礼仪,例如刀叉礼仪。西方人用刀叉时十分讲究,一般是右手持刀,左手持叉,左右手配合使用;刀放置于桌上时刀锋朝里,叉朝上放置。刀叉摆放的位置不同,其代表的意思也不一样,如果吃饭过程中需要暂时离席,应将刀叉呈八字形放在餐盘上,表示还会继续吃,;如果吃完了,则需将刀叉平行摆放在盘子右半边,刀叉柄对准四点钟方向,即表示这道菜吃好了,服务员就会撤掉盘子,这被称为是“西餐餐具语言”。正餐一般会有几副刀叉,吃一道菜换一副刀叉,按由外往内的的顺序取用等。
作者简介:向思前(1996-),女,汉族,湖南常德人,助教,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留学生教育、中国文化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