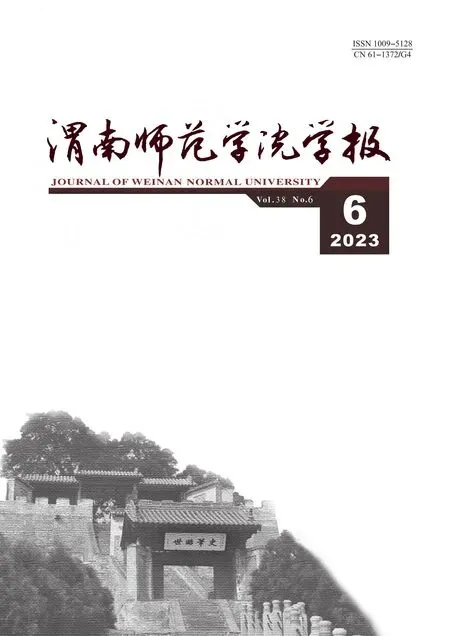《史记》中纵横家“权变”之道发微
梅 伟
(武汉大学文学院,武汉 430072)
作为战国舞台上鼓动历史风云的特殊群体,纵横家的横空出世为诸子争鸣提供了时代崭新的声音,在战国中后期诸侯博弈的过程中,他们“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1]269,可谓一枝独秀。《史记》一书,司马迁更是不吝笔墨给予纵横家列传叙平生,并明确其为“权变之士”。司马迁在《张仪列传》中赞曰:“三晋多权变之士,夫言从衡强秦者大抵皆三晋之人也。夫张仪之行事甚于苏秦,然世恶苏秦者,以其先死,而仪振暴其短以扶其说,成其衡道。要之,此两人真倾危之士哉!”[2]2304在司马迁看来,纵横家知权变才能践行其学说,从而实现政治抱负。同时,司马迁认为:“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2]3298作为史官,需通权变才能洞明世事,进而详叙史实。这是司马迁通过史官的职能用自身的体验对“权变”作论述。其在《史记·六国年表》中亦有发声:“然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何必上古!”[2]686换言之,司马迁的“权变”观取自战国,而战国践行“权变”的士人多为纵横家。由此观之,司马迁对纵横家的态度可见一斑。于纵横家而言,其“权变”则重在“择交安民”和“进取为人”。
一、纵横家“权变”的理论建构
“权变”乃司马迁首次提出。《苏秦列传》中记载:“苏秦兄弟三人,皆游说诸侯以显名,其术长于权变。而苏秦被反间以死,天下共笑之,讳学其术。然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夫苏秦起闾阎,连六国从亲,此其智有过人者。”[2]2277司马迁明确苏氏兄弟名显诸侯皆因其擅长权变,他尤其对苏秦合纵六国最为激赏,赞其“智有过人”。在司马迁笔下,“权变”对应智慧,在《货殖列传》中借白圭之口说道:“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以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2]3259可见,司马迁对“权变”持肯定态度。那么,纵横家的“权变”理论又是如何建构的呢?
首先,根植战国大势。列国变法,“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2]2549。一时百家争鸣,士人阶层逐步崛起。“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2]2343在列国争战之际,纵横家需通“权变”才能位居庙堂,睥睨天下。否则,就只能像儒家尊先王之道而不被君王所用。韩非曾在《韩非子·五蠹》中言:“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3]471这是时代大势,纵横家欲达到“可以说人,可以说家,可以说国,可以说天下”[4]19,就必须充分展现自身的智慧,上谋邦国外交,下谋处世安民。换言之,以苏秦为代表的纵横家善于“权变”,则是遵循时势。
其次,遵循天地之道。“始尝与苏秦俱事鬼谷先生,学术。”[2]2279根据《史记》记载,张仪与苏秦同拜鬼谷门下,《鬼谷子》则自然就成了纵横术的理论指导专用书籍。于纵横家而言,“权变”的表现形式是“游说”,而游说则需要遵循天地之道。《鬼谷子》中指出:“捭阖者,天地之道。捭阖者,以变动阴阳,四时开闭以化万物。纵横、反出、反覆、反忤,必由此矣。”[4]13所谓天地之道,就是遵循阴阳变化之道。万物生长随四季变化而变化,而纵横家的智慧也应随时局而动,“故先王之道阴。言有之曰:‘天地之化,在高在深;圣人之制道,在隐与匿。’非独忠、信、仁、义也,中正而已矣”[4]162。纵横家要明确:天地的造化是深不可测的,圣人的治道更是深藏不露。因此,游说之前必然需要进行细致精心的谋划,“故因其疑以变之,因其见以然之,因其说以要之,因其势以成之,因其恶以权之,因其患以斥之。摩而恐之,高而动之,微而证之,符而应之,拥而塞之,乱而惑之,是谓计谋”[4]154。明确了计谋,在具体实践过程中还要因人而异,做到随物赋形,“故与智者言依于博;与拙者言依于辩;与辩者言依于要;与贵者言依于势;与富者言依于高;与贫者言依于利;与贱者言依于谦;与勇者言依于敢;与过者言依于锐:此其术也而人常反之”[4]141。如此,则“说人主”“计国事”。清代学者秦恩复说:“今观其书,词峭义奥,反覆变幻,苏秦得其绪余,即掉舌为纵约长,真纵横家之祖也。”[4]282据此,《鬼谷子》推崇的“天地之道”为纵横家“权变”思想奠定了理论之基。
最后,汲取百家之长。诸子关于“权”亦有所指,纵横家成为“权变”之集大成者,正是对诸子的有益吸收。孔子曾说:“可以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以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1]116朱熹针对孟子“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中的“权”字作出解读:“权,称锤也,称物轻重而往来以取中者也。权而得中,是乃礼也。”[1]289儒家重“权”,道家言“变”。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时对道家“权变”进行了高度评价:“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2]3289兵家虽然讲“权”言“变”,却是分开来谈。如“势者,因利而制权也”[5]17。如“故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和为变者也。故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震”[5]168-169。而纵横家则是在权衡中不断变化整合“权变”思想,适应新的国情、世情、人情。
综上,纵横家的“权变”观正是在战国时势的基础上遵循天地之道,并从诸子中不断汲取养分,从而丰盈道术。司马迁之所以用“权变之士”作为对纵横家的称谓,也体现了对诸子思想的整合以及对纵横家的高标。
二、权变之道贵在“择交安民”
作为纵横家的杰出代表,苏秦在游说赵文侯时明确指出:“安民之本,在于择交,择交而得则民安,择交而不得则民终不安。”[2]2245换言之,列国邦交直接关系民生疾苦,若外交顺畅,则战端少起而百姓安定;若外交受困,则战端频发而百姓罹难。因此,在“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1]288的列国征伐中,安民何其不易!而纵横家针对当时的战争暴行,通过“权变”的智慧提出了“择交安民”之良策。无论合纵,抑或连横,纵横家运用自身智慧一方面有效抑制了战争,另一方面给百姓带来了一定的安稳。诚然,“择交安民”源自纵横家对天下大势的洞察与体悟,亦是“纵、横”“捭、阖”理论的实践转化。
(一)合纵之谋
《韩非子·五蠹》曰:“纵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3]483针对虎狼之秦国,苏秦率先提出“合纵”之谋,并身体力行游说山东六国相继参与,形成诸侯同盟军,致使秦国十五年不能轻易兵出函谷关。合纵之谋作为苏秦的天才战略,安国保民20 余载,一时深得诸侯激赏。由此,傅剑平指出:“纵横家的政治路线充分体现了纵横家的外交政治思想,可用战国纵横家苏秦所提出的‘择交安民,进取为人’来概括。”[6]94当然,列国地域不同,国情有别,实力有分,然而苏秦却能“伏轼撙衔,横历天下,廷说诸侯之王,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能伉”(《战国策·秦策一》)。可见,合纵之谋的背后则是谙熟天下地理形胜,洞悉列国权益之争,知晓君王性情,非权变之士不足为之。游说赵国时,苏秦指出:
故窃为大王计,莫如一韩、魏、齐、楚、燕、赵以从亲,以畔秦。令天下之将相会于洹水之上,通质,刑白马而盟。要约曰:“秦攻楚,齐、魏各出锐师以佐之,韩绝其粮道,赵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韩魏,则楚绝其后,齐出锐师而佐之,赵涉河漳,燕守云中。秦攻齐,则楚绝其后,韩守城皋,魏塞其道,赵涉河漳、博关,燕出锐师以佐之。秦攻燕,则赵守常山,楚军武关,魏军河外,齐涉清河,燕出锐师以佐之。诸侯有不如约者,以五国之兵共伐之。”六国从亲以宾秦,则秦甲必不敢出于函谷以害山东矣。如此,则霸王之业成矣。[2]2249
面对苏秦的雄辩,赵王的反应则是“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诸侯,寡人敬以国从”[2]2250。
游说燕国时,苏秦更是雄辩有辞:
夫安乐无事,不见覆军杀将,无过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赵之为蔽其南也。秦赵五战,秦再胜而赵三胜。秦赵相毙,而王以全燕制其后,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云中、九原,过代、上谷,弥地数千里,虽得燕城,秦计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赵之攻燕也,发号出令,不至十日而数十万之军军于东垣矣。渡滹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至国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战于千里之外,赵之攻燕也,战于百里之内。夫不忧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计无过于此者。是故愿大王与赵从亲,天下为一,则燕国必无患矣。[2]2244
燕文侯明确苏秦合纵之意,遂回答“子必欲合纵以安燕,寡人请以国从”[2]2244。游说楚国,苏秦更加从容:
夫秦,虎狼之国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雠也。衡人皆欲割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谓养仇而奉雠者也。夫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强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顾其祸。夫外挟强秦之威以内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无过此者。故从亲则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则楚割地以事秦,此两策者相去远矣,二者大王何居焉?[2]2261
楚王对曰:“今主君欲一天下,收诸侯,存危国,寡人谨奉社稷以从。”[2]2261
在游说六国过程中,无论是赵王的“存天下、安诸侯”,还是燕文侯的“安燕”,抑或楚王的“收诸侯,存危国”,都明确表达了对合纵之谋的赞同,这也说明苏秦“邦交安民”的外交战略不仅把握时代脉搏,而且顺应君心、民心。同时,针对不同国情,苏秦能够随势而发,言之有据,赢得君王的首肯,正是“权变”的表现。以“邦交安民”为外交战略,用“权变”之策为邦交战术,苏秦成功集结六国军队对抗秦国,身披六国相印,一时成为天下权重的人物。“周、秦诸子之言,起于救时之急,百家异趣,皆务为治。”[7]1苏秦的合纵之谋,立足时代,把握时势,进而形成燎原之势,催生六国裂变,给予天下一个稳定的时期,可谓是把“邦交安民”践行到底。近代学者孙德谦指出:“纵横者,阚子(名子我)、庞、苏秦、张仪之类也。其术本于行仁,译二国之情,弥战争之患,受命不受辞,因事而制权,安危扶顷,转祸就福。然而薄者则苟尚华诈,恶弃忠信也。”[8]71仅从事功而论,纵横家在战国时代能够做到“安危扶顷”,就非其余诸子所能相抗。虽然战国诸子相互攻讦,但纵横家合纵之谋带来的历史功绩是无论如何都抹杀不了的。
(二)连横之策
《韩非子·五蠹》曰:“而横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4]484秦国欲东出逐鹿中原,不断挤压三晋之地,被山东六国称为“虎狼之秦”,苏秦随之提出“合纵”之谋压制秦国。张仪作为秦国外相,提出“连横”之策助力秦国对抗合纵,其游说魏王:
且夫诸侯之为从者,将以安社稷尊主强兵显名也。今从者一天下,约为昆弟,刑白马以盟洹水之上,以相坚也。而亲昆弟同父母,尚有争钱财,而欲恃诈伪反覆苏秦之余谋,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据卷、衍、酸枣,劫卫取阳晋,则赵不南,赵不南而梁不北,梁不北则从道绝,从道绝则大王之国欲毋危不可得也。秦折韩而攻梁,韩怯于秦,秦韩为一,梁之亡可立而须也。[2]2286
张仪指出秦与三晋的利害关系,并成功说服魏国。
范雎作为继张仪后秦国又一位杰出的政治外交家,提出了著名的“远交近攻”策略。范雎游说秦昭王:
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释此而远攻,不亦缪乎!且其者中山之国地方五百里,赵独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王其欲霸,必亲中国以为天下枢,以威楚、赵。楚强则附赵,赵强则附楚,楚、赵皆附,齐必惧矣。齐惧,必卑辞重币以事秦。齐附而韩、魏可虏也。[2]2401
立足于秦国的国力,范雎分析秦与山东列国的关系,并极富远见地提出战略方针,此一举奠定了秦统一六国的理论基础。
宋代大文豪苏轼曾说:“且秦非能强于天下之诸侯,秦惟能自必,而诸侯不能。是以天下百变,而卒归于秦。诸侯之利,固在从也。朝闻陈轸之说而合为从,暮闻张仪之计而散为横。秦则不然,横人之欲为横,从人之欲为从,皆使其自择而审处之。诸侯相顾,而终莫能自取,则权之在秦,不亦宜乎!”[9]893秦国采用连横之策,以国家利益为重,不断蚕食列国,最后之所以能够统一六国是由其战略国策所决定的。换言之,连横之策成就了秦国的强大,为秦国东出提供战略指导。
综上,无论纵横家的合纵之谋,还是连横之策,都是立足于战国时势,从实际出发,以宗主国的利益为导向,强调邦交的重要性,在相互博弈之中诠释了“择交安民”的时代意义。王充指出:“苏秦约六国为从,强秦不敢窥兵于关外;张仪为横,六国不敢同攻于关内。六国约从,则秦畏而六国强;三秦称横,则秦强而天下弱。功著效明,载纪竹帛,虽贤何以加之……仪、秦,排难之人也,处扰攘之世,行揣摩之术,当此之时,稷、契不能与之争计,禹、皋陶不能与之比效。”[10]116孙德谦在《诸子通考》中写道:“苏、张学于鬼谷子,历说诸侯,取富贵于立谈,儒者每鄙之为不足道,然禁攻息兵,天下稍免干戈之患,其功烈亦何可轻议?”[8]2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纵横家的活动有力地推动了战国进程;从民生的角度来看,纵横家的谋略给予天下苍生短暂的安定。毋庸置疑,通“权变”之道的纵横家是战国的大战略家,他们的目光绝不仅仅是卿相至尊。从这点来说,后世儒家对他们的诟病也是值得商榷的,所以更多需要拨开历史的迷雾去洞察“邦交安民”的意义。
三、“权变”之道贵在“进取为人”
纵横家“权变”之道,不仅在于“择交安民”,而且在“进取为人”。纵横家多为寒士,而游说之路坎坷,且君主喜怒无常,其余诸子又争先恐后,当此之时,坚守进取之道方显士人本色。张彦修指出:“纵横家由布衣平民到显要高官,再到叱咤风云,实现自己的价值,把满腹的经纶转化为成功的实践,需要走完游说、高官重用、实施谋略这样的三步曲。这是一条荆棘丛生、险情四伏的坎坷之途,每一步都需要绞尽脑汁,焦神极能,倘若有半点不慎,便有可能惨遭横祸。”[11]8因此,无论合纵之谋,还是连横之策,纵横家在游说的过程中,一方面需要直面道德的苛责,即“忠信之德”“仁义之道”,另一方面需要直面生命的威胁,即“穷辱之事”“死亡之患”。
(一)不讳“忠信之德”“仁义之道”
纵横家在游说过程中更多的是从君王所需出发,这时就不能一味从忠信、仁义的角度展开。战国时代是铁血时代,天下兵戈相向,若非纵横家横空出世,可想战争之火必成燎原之势。虽然诸学派中多有鄙夷之态,但从其功烈而论,纵横家自是独领风骚。其实事功与富贵是对孪生兄弟,如果不能为君主谋取利益则无法建功,那么富贵也就是镜中花、水中月。毕竟,在现实的困境中,君王需要的是“邦交安民”,而不是谆谆教诲。所以,纵横家坚守的进取之道不避“忠信之德”“仁义之道”,而是遵从现实,寻求良策。苏秦曾言:“孝如曾参,义不离其亲一宿于外,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王哉?廉如伯夷,义不为孤竹君之嗣,不肯为武王臣,不受封侯而饿死首阳山下。有廉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行进取于齐哉?信如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有信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却齐之强兵哉?”[2]2264-2265司马迁意在批评死守忠信、仁义是无补于时势的。作为史家代表,太史公从时代的发展进程充分肯定了苏秦、张仪的历史功绩,而不是一味从道德角度进行扬弃。《战国纵横家书》亦有记载:“人无信则不彻,国无义则不王。仁义所以自为也,非所以为人也。自复之术,非进取之道也。三王代立,五相蛇政,皆以不复其掌。若以复其掌为可王,治官之主,自复之术也,非进取之路也。臣进取之臣也,不事无为之主。臣愿辞而之周负笼操臿,毋辱大王之廷。”[12]16秦高扬的进取之道正是纵横家坚守的实用主义路线。在这里,“仁义”是个人修为的体现,而非进取的关键。所以纵横家在进取过程中把“仁义”与“取利”分开来讲,一味强调“仁义”而不省察现状,则不免落入迂阔的境地。纵横家明确道德属于个人修为,而个人满足并非进取之道,进取在于为君王分忧。“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13]11曹操通过对“有行之士”和“进取之士”的对比强调苏秦的事功,充分说明诸侯选取的是国之利益而非国之礼仪。守国家、持社稷,是当时诸侯面临的时代课题,而且随着战争兼并,小国渐灭,诸侯们也感到大争之世带来的压力。如秦国一度攻陷楚国郢都,数次兵临邯郸;燕赵联军连下齐国七十二城;魏韩联军攻破函谷关,兵锋直指咸阳。所以,苏、张等人虽是纵横家,亦知兵事,可谓文武双修的国士,乱世风云要求他们必须是安邦定国的大才。在战火中即位的诸侯王们渴求的是富国强兵,而非满口礼仪的儒者之道。随着周天子对诸侯国约束能力的减弱,新兴地主阶级渐渐强大起来,“六卿分晋”的结果是韩、赵、魏成为新兴地主阶级掌权的大国,而“田氏代齐”更是说明了在大争的时代,对内对外都需要依靠实力。权势相争的时代已对道德相对疏离,道德信义逐步远离庙堂,列国之间以“利”相争,政权之内,以“利”相斗,无论庙堂内外,抑或市井街巷,形成“谈利”之势。大争之世直接的结果就是:摈弃道德、追逐智谋。
“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是最真实的社会写照。在大争的乱世中,“礼崩乐坏”更是不可改变的社会现象。战国时代的急剧变革致使上层建筑逐步丧失了春秋时期士人“诗礼唱和”的贵族风雅,取而代之的是赤裸裸的权势之争。孔子也曾强调损益,然而后世儒家已不能适应新的时代需求。所以,秉承捭阖实践哲学的纵横家才是诸侯王们倚重的士人。因此,纵横家推崇的进取之道在于有为于天下,而非单纯的自我德行修为。
(二)不畏“穷辱之事”“死亡之患”
范雎在游说秦昭王时慨然陈情:“若夫穷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2]2407作为纵横家,范雎不畏穷辱、死亡,展现了孤勇和胆识。劫后余生的范雎在魏国自有一段隐痛,由于“家贫无以自资”[2]2401,只好跟随魏国大夫须贾,后因出使齐国有功而遭嫉妒,魏相竟至“使舍人笞击睢(范雎),折胁摺齿”,然后将其扔到厕所,受尽凌辱。纵横家多为寒士,在崭露头角前只好倚仗权贵,屈辱、死亡随时相伴,可谓在刀尖上行走。张仪年轻时,“尝从楚相饮,已而楚相亡璧,门下意张仪,曰:‘仪贫无行,必此盗相君之璧。’”[2]2279由于出身贫贱,竟至被权贵诬为盗璧之贼。结果便是“共执张仪,掠笞数百”[2]2279,以至于“其妻曰:嘻!子毋读书游说,安得此辱乎?”[2]2279然而张仪并未因社会的毒打而意志消沉,反而迸发出只要舌头在就可取卿相至尊的豪气。纵横家所受的屈辱不仅来自贵族,有时家庭亲族的嘲讽更具冲击力。苏秦游说秦国失败后,“兄弟嫂妹妻妾窃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产业,力工商,遂十二以为务。今子释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2]2241作为受挫的苏秦,归家见到的不是亲情的慰藉,而是冷漠的嘲讽和鄙薄。随后,苏秦奋起而居庙堂之高,路过洛阳,亲族跪地相迎,苏秦慨然长叹:“此一人之身,富贵则亲戚畏惧之,贫贱则轻易之,况众人乎!且使我有洛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2]2262在屈辱中成长起来的纵横家,不仅体会了人性的自私,更是触摸到了世情的严苛。这些特殊的境遇,反而给予他们更为真实的人生体验,从而更好地在游说过程中能因人而异、顺势而发,进而把控局面,以通“权变”之道。如果说屈辱让人奋起,那么死亡则让人猛醒。作为舌尖上取富贵的群体,他们时刻面临多方敌对实力的侵袭,所以死亡的威胁从未消歇。然而纵横家不避刀斧,以事功为要。正如蔡泽游说范雎时所言:
夫公孙鞅之事孝公也,极身无二虑,尽公而不顾私;设刀锯以禁奸邪,信赏罚以致治;批腹心,示情愫,蒙怨咎,欺旧友,夺魏公子卬,安秦社稷,利百姓,卒为秦禽将破敌,攘地千里。吴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谗不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不为危易行,行义不避难,然为霸主强国,不辞祸凶。大夫种之事越王也,主虽困辱,悉忠而不解,主虽绝亡,尽能而弗离,成功而弗矜,贵富而不骄怠。若此三子者,固义之至也,忠之节也。是故君子以义死难,视死如归;生而辱不如死而荣。士固有杀身以成名,唯义之所在,虽死无所恨。何为不可哉?[2]2420
纵横家谙熟经史,知晓在大义面前,可以不畏生死,并能做到虽死无恨。正是这腔孤勇,使他们真正做到士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纵横家不仅不畏死亡,甚至还能以死为计,充分体现其进取之道中的权变。齐国大夫为了争宠,派人刺杀苏秦,“苏秦且死,乃谓齐王曰:‘臣即死,车裂臣于徇于市,曰苏秦为燕作乱于齐,如此则臣之贼必得矣。于是如其言,而杀苏秦者果自出,齐王因而诛之。’”[2]2266苏秦以一己之死而擒刺客并借齐王之力摧毁敌手,何其智慧。
先秦纵横家从寒士到辩士对“穷辱”和“死亡”有着不同的生命体验。作为寒士,纵横家用个体生命去触摸底层的悲凉并直面穷辱之事,对世人趋利的嘴脸进行大胆揭露。正是寒士的身份,让他们更加明确“权变”的必要性,也强化了进取的决心与勇气。在纵横家看来,卿相至尊只有通“权变”后才能更好地彰显。作为辩士,纵横家居庙堂之高纵论邦交大事,不仅要直面君王的诘难更要提防同僚的攻击,因此需要重视邦国大利且遵循攻伐大义,同时还要做好身家性命受到严重威胁的准备和应对。于纵横家而言,无论是处江湖之远的寒士,抑或是居庙堂之高的辩士,坚守进取之道都是在通晓“权变”的智慧下展开,因为游说之路从来都是荆棘遍布,这也从侧面反映了纵横家的政治抱负。
诚然,纵横家不避“忠信之德”“仁义之说”,不畏“穷辱之事”“死亡之患”,在进取过程中高扬“权变”之道。但其背后隐藏的则是对富贵的渴望,对人臣位尊的向往。张仪曾言:“且夫从人多奋辞而少可信,说一诸侯而成封侯,是故天下之游谈之士莫不日夜扼腕嗔目切齿以言从之便,以说人主。”[2]2286游说带来的丰厚回报更是进取之力。司马迁指出:“由此观之,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严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于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故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2]3271士人追求名利,皆为富厚所致,司马迁从经济学角度对天下分工作了突破性解读。侯外庐等在《中国思想通史》中曾经正确地指出纵横家重视商业货殖的政治意义:“利润与利息的意识,反映到政治生活,正贯注了策士的作用。所谓朝秦暮楚,并不能从信义堕地来解释,而是商业投机的市民行为在周末政治上的观念证件而已。因此,策士活动颇与故旧贵族之无故富责不同,而一如自由交易,合则文易,不合则去而之他。”[14]573所以,泛道德视野下的纵横家之进取之道,实则是经济行为,当然人性趋利避害,逐利亦有代价,道德不避,生死何惧。
四、结语
纵横家的“权变”之道既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也是时代演变的智慧。司马迁用如椽大笔在历史深处把纵横家描绘得栩栩如生。他们被司马迁称为“权变之士”,换言之,亦是奇才策士。李长之指出:“司马迁爱一切奇,而尤爱人中之奇。人中之奇,就是才。司马迁最爱才。司马迁举称他爱的才为奇士。”[15]93因此,需从历史发展的角度重新审视纵横家。明代李贽曾评述苏秦、张仪曰:“士之有智谋者未必正直,正直者未必有智谋,予以为智谋之士可贵也。若夫敦厚清谨,以之保身虽有余,以之待天下国家缓急之用则不足,是亦不足贵矣。”[16]4096正视纵横家的智慧和道德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必要的。只有更好地梳理二者的关系才能较为客观地回望战国风云,感怀纵横气象。纵横家之所以坚守“进取为人”,实则是有“择交安民”的时代愿景,二者皆因“权变”之道使然。纵横捭阖,鼓动风云,“权变”观为进一步研究纵横家提供了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