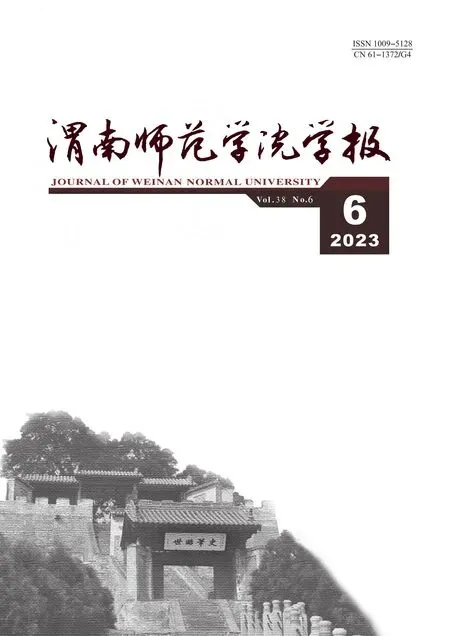“任安传”小注
——居地、狩猎及《史记》文本问题
倪豪士[著];刘 城,刘桂兰[译]
(1.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亚洲语言文化系,美国 麦迪逊 53711;2.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南宁 530003;3.湖北大学外国语学院,武汉 430062)
本文拟议谈《史记·田叔列传》[1]2779-2783中褚少孙(约公元前105—前30 年)所增补的有关“任安”(约公元前140—前91 年)生平的一些问题并进行阐释。这些阐释受叶翰(Hans van Ess)对该篇解释性翻译的启发,叶翰的释译文收录在我所主持翻译的《史记》英译本第八卷中。①叶翰的译文、注解和译者注——收录在我所主持翻译的《史记》第八卷(William H. Nienhauser,Jr,ed,Grand Scribe’s Records,v. 8,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7)——是最早研究该篇的著述之一。美国汉学家华兹生(Burton Watson)并未在其翻译的《史记》(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田叔列传》中对所附加的这部分传记进行翻译(参见Burton Watson,Records ofthe Grand Historian,Revised editio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Vol.1,pp.489-494)。而且,无论是徐兴海的《司马迁与〈史记〉研究论著专题索引》(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还是杨燕起和俞樟华所著的《〈史记〉研究数据索引和论文专著提要》(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 年版)也未见与该篇相关的条目。这两本著作都参考了清代及现代的研究成果。最新的参考文献即由俞樟华和邓瑞全编著的《〈史记〉论著提要与论文索引》(华文出版社2005 年版)指出,在徐兴海的著作中,《史记》的九个篇章未有相关研究,《田叔列传》即是其中之一。俞樟华和邓瑞全的著作也有一个索引,收录宋代以来“笔记”中有关《史记》各篇的条目,还是未见关注《田叔列传》者。捷克汉学家鲍格洛(Timoteus Pokora)生前是否关注过任安传记的这部分内容不得而知。非常感谢我在威斯康星大学的《史记》研究团队对这一篇章的诸多讨论,尤其感谢王韵龄对本文讨论的这几个文本所提供的帮助。
一、居地:“武功”的地理方位
首先考察载于《秦、西汉、新朝历史人物传记辞典(公元前221—公元24 年)》〔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the Qin,Former Han and Xin Periods(221 B.C.—A.D. 24),英国剑桥大学学者鲁惟一(Michael Loewe)著〕中的有关“任安”词条的第一部分[2]457:
任安,字少卿。所参考的史料文献并未见任安的专传,对于任安仕宦生涯的记录也并不完整,而《史记》中附加的段落即褚少孙所言确是一个补充。但是褚少孙所言有矛盾之处,亟待厘清。
褚少孙提供的信息是他担任郎官时听田仁所说,而田仁与任安相善。任安是荥阳人,少时就成为孤儿,生活贫苦。他给别人驾驭车子①中井积德(1732—1817)指出,在《诗经》之《无将大车》(毛诗,第206 首)中,“将车”一词指的是推着车辆,这表明任安也是推着车到京城,参见泷川龟太郎《史记会注考证》卷一百四,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院1932—1934 年版,第8 页。娄敬到洛阳也是如此,参见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 年版,卷九十九,第2715页。但是,“将车”的大多数评注和早期用法表明,其似乎更多指“驾御车辆”。到了长安之后,在一个郊区安顿下来,他于此以追捕盗贼而闻名。任安还在每次狩猎之后给狩猎者分配好猎物,众人皆无异议,因其诸如此类公平处事而收获好评。②译者注:鲁惟一此处所言,有两处可待商榷。第一,他说“褚少孙提供的信息是他担任郎官时听田仁所说”,而《史记》言“褚先生曰:臣为郎时,闻之曰田仁故与任安相善”。《史记》所言,是褚少孙担任郎官之时听说田仁与任安相善,而并非鲁惟一所说。第二,鲁惟一说“每次狩猎之后,他会给狩猎者分配好猎物”,而《史记》言“邑中人民俱出猎,任安常为人分麋鹿雉兔,部署老小当壮剧易处”。《史记》所言,任安在狩猎之前,会把老人、小孩和壮丁安排到或难或易的地方打猎,而非鲁惟一所说。倪豪士教授在后文指出了这一点。
鲁惟一在该词条中对任安还多有介绍,但上述文字足以为本文提供论据。
鲁惟一所说的“附加的段落”即褚少孙所言,类同于《史记》中通常被认为是“传记”的诸多《列传》。下面来考察《史记》中褚少孙所述之任安“传”③关于中华书局版《史记》的版本史,参见William H. Nienhauser, Jr,“Historians of China”Chinese Literature:Essays,Articles,Reviews 17:(1995):207-217。:
任安,荥阳人也。少孤贫困,为人将车之长安,留,求事为小吏,未有因缘也,因占著名数④“占著”指登记,“名数”指家庭成员的姓名和数量。“索隐”于此评论:“言卜占而自占著家口名数,隶于武功,犹今附籍然也。”秦朝灭亡后,因战争而背井离乡的家庭的重新安置和重新登记,在汉初十分常见(参见劳干《两汉户籍与地理之关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辑刊》1935 年第5 本第2 分册,第179-214 页),这可能也是公元前154 年(任安大约出生于此时)七国之乱后数十年中的一个趋势。公元前119 年,汉武帝下令从关东(任安的家乡)迁出72.5 万名贫民(同上,第183页)。关于汉代人口登记的大致情况,参见Denis Twitchett and Michael Loewe,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ume 1,The Ch’in and Han Empires,221 B.C-A.D.22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pp. 151 and 483。。武功,扶风西界小邑,谷口蜀刬道近山。安以为武功小邑,无豪,易高也。[1]2779
这一段直至“因占著名数”一句读起来都很顺畅。“索隐”注道:“言卜占而自占著家口名数,隶于武功,犹今附籍然也。”
王利器(1912—1998)在《史记注译》中把“占”释为“隐度”[3]2205。吴树平和吕宗力在《全注全译史记》中把“占”理解为“占著”的一部分[4]2730,与中井积德所言多有类同[5]8。“索隐”解“占”音“之艳反”,应读降调,这就从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中井积德之说。《汉语大词典》也把这个词解释为“上报家中人数附于册籍,落户定居”(“占”读第四声)[6]992a,并且引用王符(公元130 年在世)《潜夫论》作为例证:“内郡人将妻子来占著。”⑤也可参见郭嵩焘《史记札记》卷5 下,世界书局1960 年版,第350 页,其将“占”解释为“附籍”(参见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第11 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1993 年版,第955b 页)。
但为什么“索隐”于此提到他“隶(家人)于武功”呢?在中华书局版的《史记》中,这里是一个句号,接着引入“武功”这个地名,到底“武功”位于何处?该文的理解也只有在确定了武功的位置之后,才能得知任安的居住地。
找到的答案出乎意料:中华书局版漏掉了其他很多版本(事实上,我所能翻阅到的版本)都有的一句话“家于武功”①例如这四个“漏掉”的字,见于百衲本(即黄善夫版,卷一百四,第4b 页),泷川龟太郎本(卷一百四,第8页),(明)凌稚隆辑《史记评林》(五卷本,地球出版社1992 年版,卷一百四,第3a 页),武英殿(1747 年)本(卷一百四,第4a 页)。。把这句话补齐后,此处文本变得更好理解了:“因占著名数,家于武功。”
让我们把这个文本问题搁置一旁,先解决“武功”的位置问题。鲁惟一认为它是长安的一个郊区。褚少孙告诉我们,它是位于扶风郡西边的小县,山谷口处有通往蜀地的栈道。吴树平[4]2730和王利器[3]2205都认为“扶风”是“右扶风”的缩写,右扶风在汉代作为“三辅”之一,从长安往西延伸。虽然“右扶风”在《史记》的文本或评注中出现多次,但我们找不到“右扶风”简称“扶风”的例证。而且,“扶风”这个词在《史记》的其他地方并未出现。但是,“扶风”在徐广(352—425)所著《史记音义》(如《集解》所引)的评注中出现了7 次。②徐广评论的相关研究,参见Scott William Galer,Sounds and Meanings:Early Chinese Historical Exegesis and XU Guang’s Shiji yinyi,unpublished Ph. D.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2003。进一步说,如果我们把“家于武功”四个字补充进去,下一行的“武功,扶风西界小邑”看起来更像是一个注释。我们可以假设:这可能是徐广的注释,只是误置在正文中。在徐广生活的时代(西晋)确实有一个“扶风”,是在北方的雍州(西晋名为长安),名叫“扶风国”。[7]401这个扶风郡地形近似于汉代的右扶风,但其郡治在今西安以西五十五英里靠近眉县之处[8]44。在说明扶风地理位置的所有解释中,一个共现的内容就是解释为什么武功在“扶风西界”,因为无论扶风作何解释(是汉代的“右扶风”还是晋代的“扶风国”),其“西界”位于现代的甘肃,距长安以西又过去五十英里,此地无路通往蜀地。然而,如果我们把“扶风”理解为西晋统治下的扶风(也称“扶风国”)的郡治的话,那么武功县在它的西部边界地区,就应该靠近通往蜀地之路。
至于武功的位置,《水经注》提供了更多的线索。在卷十七和卷十八,即关于渭河的三卷记载的前两卷中,郦道元(公元480 年前—527 年)引用了本节所论的几行文字(稍有改动):“(褚先生乃曰:)武功,扶风西界小邑也。谷口蜀栈道近山。无他豪,易高者是也。”[9]1504由此,如果我们把它看成是一个注释,那么在大约公元520 年郦道元写《水经注》之前,这个注释就已经写入《史记》正文之中。杨守敬在《水经注》卷十八的一段评注中进一步说:“武功有斜谷。”[9]1523这个山谷可能位于谭其骧图示的汉代斜水岸边,而斜水注入距今眉县以西十英里的渭河。在这几行之后,《水经注》云:“太白山,在武功县南。”[9]1525太白山位于眉县以南二十英里之处[10]15。将“武功”定位于斜水边上——斜水在今眉县西南、太白山(北纬34.20°,东经107.650°)正西北——距离谭其骧所示武功所在地以西十多英里[10]15。这一定位更加说明:扶风在这里指的是扶风国的郡治所在地,在眉县以东数英里,且“武功,扶风界小邑”一句更像是一个可能来自西晋更可能出自徐广的评注,其大约在公元527年郦道元去世之前就已经嵌入了《史记》的正文中。这也明确证实武功绝不是长安的一个郊区。
武功定位之说,在严耕望(1916—1996)《唐代交通图考》的地图14“唐代渭水蜀江间山南剑南区交通图(西幅)”中得到证实[11]1178,该地图清晰显示(在唐代)从渭河流域到蜀地的主道经过河谷,延伸至西南,然后向正南方转弯,最后转向正西方直达三泉县。该图可见,“谷口”在渭河附近的河口处,此地位于太白山北面。图上还标记这条主道为“秦汉褒斜古道”,而这条古道名也见于《汉书》[12]1861。斜水在上文已提及,褒水是向南汇入汉水的一个支流,褒水河谷靠近“斜”③也可见《汉语大词典》的词条解释,载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第9 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1993 年版,第131b-132a 页。水河谷。斜水河谷和武功两地之间最清晰的关联,也可从谭宗义的《汉代国内陆路交通考》第一章“褒斜道”④谭宗义《汉代国内陆路交通考》,新亚研究所1967 年版,第1-15 页和第62 页地图。中找到佐证。
“斜谷”在现代陕西地图中也有明确的标示,今天的斜水流经石头河,而石头河由南向北流入眉县以西数英里的渭河。斜水逆流而上,向西南流去。“秦汉褒斜古道”这条道路现在(在古代无疑也是如此,如严耕望地图所示)沿着石头河的一条支流延伸,而那条支流是从西往南数英里之处汇入石头河①参见徐兰州等编《陕西省地图册》,西安地图出版社2005 年版,第67 页和70 页。。现代地图用红色字体清晰地标示这个河谷为“古栈道遗址”。借助这些地图可进一步推测,武功在今天的安乐镇(安乐镇位于距眉县西南不到十英里的石头河东岸)附近,位于石头河(以及通往蜀地之路)流入大山往南之前数公里处。这里大概离汉代京城七十多英里。
二、狩猎:任安作为组织者
任安在武功赢得好名声,其途径之一就是通过担任亭长以负责组织当地的狩猎活动。鲁惟一对此概述道:“他还以处事公平而收获好名声,每次狩猎之后,他会给狩猎者分配好猎物,众人无异议。”《史记》卷一百四也写道:
安留,代人为求盗亭父②虽然“求盗亭父”作为一个官职并未见于吕宗力的《中国历代官职大辞典》(北京出版社1994 年版),但裴骃于《史记集解》引应劭(公元165—204 在世)释“求盗亭父”云:“旧时亭有二卒,其一为亭父,掌开闭扫除;一为求盗,掌捉捕盗贼。”。后为亭长③实际上,“亭”由最初的军事地区逐渐变为行政区域。在重要地区及沿海地区,每隔十里设一亭,这样,武功作为谷口至蜀地的终点,也设有一亭。参见傅举有《有关秦汉乡亭制度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1985 年第3 期,第23-28 页);尹达等编《纪念顾颉刚学术论文集》(巴蜀书社1990 年版),该书收集了很多研究“亭”的论文;William H. Nienhauser, Jr., ed., Grand Scribe’s Records(vol.2, p.7, n. 20 and vol.1, p.207, n. 273)。最有名的亭长应是曾在秦朝为官的刘邦(参考《史记》卷八,第342页及之后各页)。。邑中人民俱出猎,任安常为人分麋鹿雉兔,部署老小当壮剧易处④郭嵩焘《史记札记》对此句有相似解读,参见(清)郭嵩焘《史记札记》卷五下(世界书局1960 年版,第350 页)。,众人皆喜,曰:“无伤也,任少卿分别平,有智略。”
这样看来,任安赢得人们的敬佩,在于他筹备狩猎事宜,让所有人都能参与进来并且都能捕获到猎物,而不是如鲁惟一所说在于狩猎之后能公平分配猎物。
三、文本:相关问题及启示
现在大部分(也有例外)的《史记》研究者所用的文本是顾颉刚(1893—1980)等人在20 世纪50 年代末编撰并于1959 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现代评注版。⑤奇怪的是,顾颉刚和徐文珊(1900—1998)所编《史记·白文之部》(研究院史学研究会1936 年),这一章中包含有中华书局版所漏掉的这四个字。这表明,要么是顾颉刚在中华书局版的编辑工作中漏掉了这四个字,要么是徐文珊(顾颉刚的学生)承担了1936 年版的绝大数编辑工作。参见William H. Nienhauser, Jr, Historians of China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17,1995,pp.207-217)。这个版本以张文虎(1808—1980)经过数年编辑并于1866 年刊印的金陵书局本⑥其编者声称这个版本是自晚清以来相对最好的版本。参见《史记》出版说明,参见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 年版,第1 册,第5 页。为基础⑦关于这个版本的来源,参见William H. Nienhauser,Jr,The Textus Receptus and Chang Wen-hu,in Grand Scribe’s Records,Vol.2,2002,pp.xxxiii-xlvii。。我们发现,中华书局版中的《田叔列传》漏掉了虽然很短但却很重要的文字。毫无疑问,金陵书局本(卷一百四,第3b 页)同样也漏了这一句。我们推测,“家于武功。武功,扶风西界小邑”这一句本应有“家于武功”四字但却被遗漏了,这是张文虎或其助手在誊录这一章节时漏字的一个小例子。但是目前为止这也仅仅是一个假设而已。
除此之外,首选的现代评注本(中华书局本)中的这一细微文本问题有助于揭示各相关文本之间的差异。上文提及其他的主要版本包含有“家于武功”这一句,例如,泷川龟太郎的《史记会注考证》(在众多现代评注本中其重要性仅次于中华书局本)就包含有这四个字[5]8;水泽利忠的《史记会注考证校补》研究《史记》文本最为周详,也注意到了金陵本的遗漏,但遗憾的是他错误地指出该处仅遗漏了“家于”二字[13]。我们发现中华书局本遗漏“家于武功”四个字,由此发现了张文虎的文本错误,而且还发现了水泽利忠的一个较为严重的纰漏。这一错误连带出现在那些仅以中华书局本为底本的文本中:由此吴树平、吕宗力《全注全译史记》(卷一百四,第2730 页)遗漏这一句且没有注释说明,而王利器《史记注译》收录这一句但却未提及中华书局本的遗漏,这表明此章节的翻译者参阅了除中华书局本之外的其他版本(虽然在《史记译注》的“编辑体例”中,编者指出该书是以中华书局本为底本的)。此外,青木五郎是第三位《史记》日译者,他在明治书院出版的《史记》日译本①明治书院版《史记》,先由吉田贤抗(1900—1995)于1973 年开始编著,水泽利忠继之,最近由青木五郎接手。中,试图对这个文本问题加以阐论,遗憾的是他在第十一卷第129 页的一个注释中,再次出现了和水泽利忠一样的错误结论。
如果上述解读是正确的,那么本文所讨论的中华书局本的这几行文字可引出大问题并提醒我们:在阅读《史记》时,我们仍然必须比对多个版本和注释,并且要核查中西方先前已有的注述,因为即便最出色的学者有时也会有疏漏。
【附记】论文原题为“A Note on Ren An: The Residence, the Hunt and the Textual History of the Shiji ”,收录在德国汉学家傅敏怡教授(Michael Friedrich)主编的Han- Zeit,Festscrift für Hans Stumpfeldt aus Anlass seines 65. Geburtstages(Wiesbaden: Harrassowitz,2006:275-282)一书中。感谢倪豪士教授授权翻译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