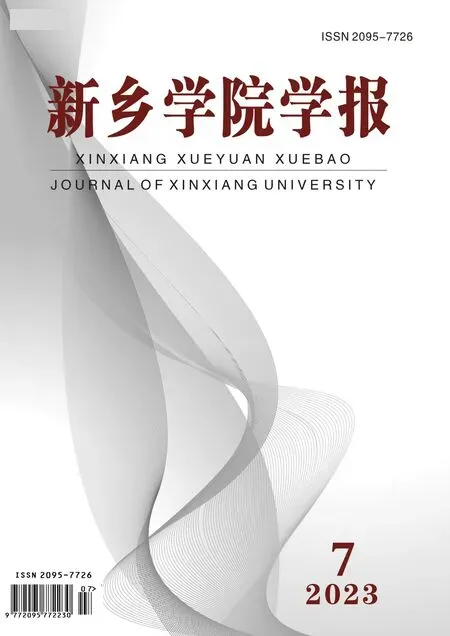《霸王别姬》故事情节和画面设计荒诞性解析
王昱伟
(新乡学院美术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3)
一、荒诞理论与《霸王别姬》
电影《霸王别姬》上映于1993年,它是中国首部在戛纳电影节上获得金棕榈奖的作品。 此外,它还获得了美国金球奖最佳外语片奖、 国际影评人联盟大奖等多个奖项。 《霸王别姬》改编自香港作家李碧华的同名小说,由陈凯歌执导,李碧华、芦苇编剧,张国荣、巩俐、张丰毅等人领衔主演。 电影上映之后,在商业和艺术两个层面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以荒诞理论解析《霸王别姬》故事情节和画面设计,有助于深化对该影片的认识。
《辞海》对“荒诞”一词的解释为:“犹荒唐,虚妄不可信。”[1]在现实生活中,荒诞之事普遍存在着。艺术作品是现实生活的反映, 因此艺术家经常以荒诞之事来表现人生的悲哀。
法国作家、哲学家阿尔贝·加缪是将“荒诞”提升到哲学高度的第一人。 阿尔贝·加缪对于荒诞感的描述多基于直接的生活经验, 他提出,“在荒诞的情绪之下, 人们常常感觉到生活没有意义, 无法战胜死亡,也无法理解、抵抗这个世界”[2]。 他还提出,每个人按照着自己的生活节奏和模式生活, 那么自然就会产生一种荒诞感,即“我为什么要这样生活”“我为什么不能按照别人的生活方式生活”[3]。
电影《霸王别姬》以段小楼、程蝶衣、菊仙三人的感情纠葛为中心设计故事情节和画面, 以故事情节和画面的荒诞性展现了创作者对于传统文化、 人的生存状态以及人性的思考。
二、《霸王别姬》故事情节设计的荒诞性
(一)二男一女的感情纠葛暗藏同性恋情
中国传统爱情故事的情节一般是男追女, 或者女追男。相比之下,电影《霸王别姬》讲述的爱情故事比较另类——男性程蝶衣和女性菊仙同时追求男性段小楼。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同性之间的恋慕还是一种隐晦的情感,《霸王别姬》 这种大胆而荒诞的情节设计使观众产生了强烈的观影兴趣。 程蝶衣爱慕师兄段小楼,为了使这一情节更容易被观众接受,影片给程蝶衣贴上了一个“入戏太深”的标签,称他“一辈子活在戏里”。影片中有这样一个场景:程蝶衣恳求师兄段小楼:“就让我跟你好好唱一辈子戏,不行吗? ”段小楼困惑地表示:“这不,这不小半辈子都唱过来了吗? ”程蝶衣激动地说:“不行,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段小楼愣了半晌,然后回了一句:“蝶衣,你可真是不疯魔不成活呀! ”
(二)戏里戏外命运的巧合折射现实的荒诞
电影的名字是《霸王别姬》,段小楼和程蝶衣最拿手的戏也是《霸王别姬》。 《霸王别姬》是京剧传统剧目, 讲述了项羽被汉军困于垓下, 与虞姬饮酒悲歌,虞姬在为项羽舞剑后自刎而死,项羽深感无颜面对江东父老,最终在乌江边自刎的故事。 电影《霸王别姬》 则讲述了扮演虞姬的程蝶衣和扮演项羽的段小楼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在电影中,程蝶衣希望和师兄段小楼在一起唱一辈子戏, 但段小楼却选择女性菊仙作为自己的人生伴侣,两人由此分道扬镳。在影片的最后, 晚年的段小楼和程蝶衣来到空无一人的京剧院。一句“我本是男儿郎,又不是女娇娥”使程蝶衣认清了现实,他并非虞姬,段小楼也并非霸王,他所追求的情感和艺术, 与现实生活之间横亘着万丈鸿沟,唯有戏剧真正属于他。 死在心爱的人面前,是虞姬的宿命,也是两千年后程蝶衣的宿命,在电影的高潮部分,程蝶衣仿效虞姬拔剑自刎,永远留在了戏中。
(三)隐喻和象征的手法展现性别改写的过程
《霸王别姬》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展现同性恋情的影片, 拍摄这部影片是导演陈凯歌的一次大胆尝试。 不过,考虑到观众的接受心理,影片还是大量使用了隐喻和象征的手法,以下以小豆子(即后来的程蝶衣)接受性别改写的过程为例进行分析。
1.女性倾向的萌生
小豆子的母亲艳红是个妓女。 小豆子从小跟随母亲生活在妓院里,母亲给他蓄发,当女孩子养。 一个男孩子,却扎着小辫,以女性的身份生活在女人堆里,这个情节告诉观众,小豆子女性倾向的萌生是有环境基础的。
2.男性生理的阉割
九岁的小豆子被母亲送到戏班,但他手指增生,不符合戏班收徒的要求。面对戏班老板的拒绝,母亲情急之下拿起菜刀,狠心切掉了小豆子多余的一指。母亲这一近乎疯狂的举动, 象征着社会对小豆子进行生理的阉割。
3.男性心理的阉割
小豆子在学戏的时候,总将“我本是女娇娥”唱成“我本是男儿郎”。 执拗坚持的背后,是一个九岁的孩子对自身性别的认知。然而,如果一直唱错,小豆子就有性命之虞。于是师兄小石头(即后来的段小楼)把烟锅塞进小豆子嘴里,流着眼泪边骂边搅。 在暴力羞辱之下,小豆子放弃了对男性身份的坚持,将“我本是女娇娥”唱得有声有色。小石头的行为是一个性隐喻,象征着社会对小豆子进行心理的阉割。
4.以女性的身份遭受侮辱
在大太监张公公的寿宴上, 小豆子和小石头在台上联手表演了《霸王别姬》。演出结束后,身着戏服的小豆子被人送到张公公的寝室中, 他随即遭到张公公的蹂躏。小豆子身着女性服装被张公公侮辱,象征着他完全失去了男性的身份。
5.以女性的身份得到一子
当小豆子失魂落魄地从张公公府中出来时,发现了一名弃婴, 他不顾旁人的劝阻, 将弃婴抱了回去。 接下来,当大家逗孩子玩时,小豆子的脸上却写满了痛苦和绝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生育是女性的职能,小豆子在被张公公侮辱之后得到一子,恰好与人们对于女性的认知相吻合。至此,影片完整展现了社会对小豆子进行性别改写的过程。
三、《霸王别姬》画面设计的荒诞性
(一)艳红切掉小豆子的手指
在北洋政府时期, 妓女艳红带着小豆子来到戏班里,请求关师傅收留小豆子,但关师傅却因为小豆子是“六指”而拒绝了她,万般无奈之下,艳红狠心切掉了小豆子多余的一指。 电影开篇便点出了人物际遇的荒诞性——一个妓女,没有家庭却有一个儿子,儿子又被当作女儿养到九岁, 为了能让儿子有口饭吃, 母亲亲手切掉了他多出的手指。 在人们的认知中,母亲这一形象是温柔慈爱的,艳红切掉小豆子手指的画面与人们的认知形成巨大反差, 因而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残酷的画面使观众对于旧社会底层妇女的悲惨际遇有了深刻的认识。
(二)小石头用烟锅在小豆子嘴里搅动
京剧《思凡》有一句唱词——“我本是女娇娥”,但刚入行的小豆子却总唱成“我本是男儿郎”。 尽管小豆子从小生活在女人堆里, 母亲也把他扮作女孩子,但他始终认为自己是男性,不愿意别人把他看作女性。小豆子只是一个孩子,他还不能准确区分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 因而执拗地把在现实世界中对性别的坚持带到了戏剧表演中。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小豆子要想继续唱戏并且成角儿, 就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本心。当戏班经理来探班时,小豆子又一次唱错了词。为了拯救小豆子和戏班,小石头直接将烟锅戳进小豆子的嘴里, 边搅动边说:“错, 错呀你! 我叫你错!”于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嘴角淌着血的小豆子终于唱出了“我本是女娇娥,又不是男儿郎”。在这个荒诞而血腥的画面中, 与其说小石头打破了小豆子的坚持,不如说小豆子为了师兄主动戴上性别的枷锁。
(三)大太监张公公蹂躏小豆子
即便是在清朝灭亡之后, 曾经服侍过慈禧太后的大太监张公公依然权势滔天。 当身着戏服的小豆子被送进张公公寝室的时候, 张公公正抱着一名女子取乐。在看到小豆子之后,张公公立刻丢下女子扑向小豆子。小豆子吓得要撒尿,张公公对此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不但要看小豆子撒尿,而且要为小豆子接尿,之后又将小豆子强行按在床上蹂躏。荒诞的画面令观众产生了一系列疑问:张公公是一名太监,怎么还和女性亲热? 张公公到底是同性恋,还是双性恋?张公公是真的侵犯了小豆子, 还是以变态心理对小豆子进行了猥亵?观众在思考这些问题的同时,对太监制度对于人性的扭曲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四)袁世卿与程蝶衣演绎暧昧情愫
民国时期,长大的小豆子改名程蝶衣。 没落的贵族袁世卿对京戏十分迷恋, 他欣赏程蝶衣对艺术的痴迷,爱程蝶衣“戏我不分”的境界,感叹程蝶衣是“虞姬再生”。荒唐的是,袁世卿将对程蝶衣表演艺术的迷恋,转化为对程蝶衣本人的恋慕。程蝶衣在袁世卿家中发现了段小楼最喜欢的那把宝剑, 不由得拿在手中观赏。这时,袁世卿从背后握住程蝶衣拔剑的手,说:“自古宝剑酬知己,程老板,愿做我的红尘知己吗?”接下来,电影镜头切换到袁世卿的庭院中,袁世卿与程蝶衣正唱着 《霸王别姬》 ……在特写镜头中,是程蝶衣的残妆以及无奈的表情。导演在处理这个情节时使用了蒙太奇手法, 这给观众留下了想象的空间。两个男人在屋里究竟做了什么,观众并没有看到,但根据画面的提示又不难猜到。
(五)程蝶衣偷窥段小楼和菊仙的夫妻生活
“文革”前夕,段小楼和菊仙在家中焚烧属于“四旧”的东西,当段小楼拿出菊仙的嫁衣要烧掉时,菊仙夺过来穿在自己身上。随后,二人举杯互敬,在酒精的作用下,段小楼和菊仙上演了“床上戏”。此时,屋内翻云覆雨,屋外狂风暴雨,程蝶衣则伏在窗外窥视段小楼和菊仙的一举一动。 由于镜头的切换,这段“床上戏”的时间得以延长,窗外程蝶衣的面孔和床上二人的动作交替出现七次之多。 在拍摄这场戏时,摄影机位于室内,镜头中,段小楼和菊仙的对话是清晰的、真切的,而白色纱窗外程蝶衣的面孔是模糊的、不真实的。 这个画面在展现程蝶衣偷窥的荒诞性的同时,也暗示了程蝶衣心中与师兄之间的恋情不过是他一厢情愿的幻想。
(六)“文革”时期众人相互揭发
在时代的洪流中, 人们无力掌控自己的命运,罪恶和死亡不可避免。 “文革”时期,当年那个被小豆子捡回来的弃婴小四成为毁灭一切的祸根。小四先是逼迫戏班老板那坤揭发师傅段小楼。在“红卫兵”的威逼下,段小楼也揭发了程蝶衣:“他是只管唱戏的,他不管台下坐的是什么人, 什么阶级……他都卖力地唱,玩命地唱! ”当“红卫兵”斥责段小楼“避重就轻、不老实”时,段小楼又补充道:“抗日战争刚刚开始,他就给日本侵略者唱堂会,他,他就,他就当了汉奸!”段小楼接下来的话更让程蝶衣崩溃:“他为了讨好大戏霸袁世卿,他……你有没有?他给袁世卿他当……当……”崩溃的程蝶衣深知段小楼最爱的人是菊仙,便把矛头对准了无辜的菊仙:“我来告诉你们她是什么人……她是花满楼的头牌妓女,潘金莲!斗她,去斗她!”而在面对“红卫兵”关于他和菊仙关系的逼问时,段小楼大喊:“真的不爱,真的! 我真的不爱她! 我跟她划清界限!我从此跟她划清界限了!”段小楼绝情绝义的话令菊仙万念俱灰,后来,她在将宝剑交给程蝶衣之后上吊自尽了。在这场戏中,火光映出一张张扭曲的面孔,几乎每个人都“疯”了,小四、那坤、段小楼、程蝶衣,他们对亲情、友情、爱情的背叛展现了疯狂时代对人性的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