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叙人生”到“叙哲学”的现代新诗
姜玉琴
(上海外国语大学 文学研究院,上海 200083)
中国现代新诗的肇始主要是缘于外国诗歌的冲击与启发,在其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对中国传统诗歌的抒情性予以抨击与解构,另一方面吸收了外国诗歌中所特有的以“事”为中心的叙事性因子,从而形成了一套不同于传统诗歌的诠释模式。当然,这种围绕着“事”,其实就是围绕着自由、民主之事构建起来的书写新传统,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即不同时期的诗人,所叙之“事”的偏重点也是不一样的。根据诗人所叙之事的主旨不同,现代新诗的叙事传统,又可以细分成三种范式类型:“为人生”的叙事传统范式、以“理”为上的叙事传统范式和在西方宗教、哲学框架下的叙事传统范式。需要说明的是,在现代新诗中强调“叙事”因素,绝非是指现代新诗呈现出一种叙事诗的态势。相反,彰显“叙事”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为了与传统诗歌的抒情框架区分开来;二是为了彰显现代新诗的一种特殊精神特质——格外强调和重视所表现之内容的充实性与现代性。
一、“为人生”的叙事传统
对于“五四”时期的新文学工作者而言,现代新诗之所以要取代传统旧诗词,其目的非常明确:就是欲用西方的一些新思想、新观念,来更新和取代传统诗歌中的旧思想观念。因此,围绕着新诗思想内容方面所展开的变革还是比较繁琐、复杂的,只能挑着那些重要的,具有代表性的潮流来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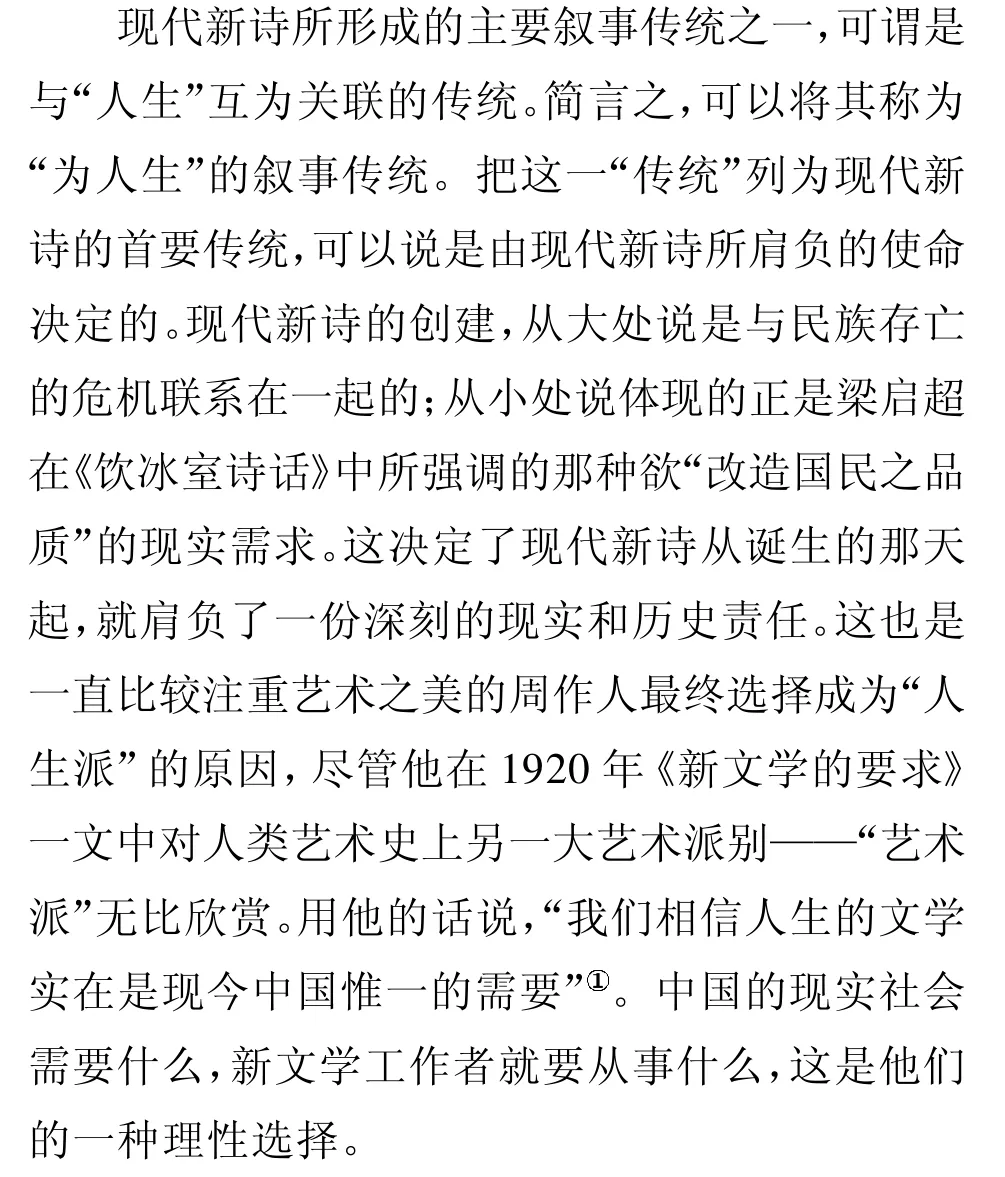

问题在于,“人生”是个笼统而抽象的概念。不同的人拥有不同的人生,即谁的人生都有其自身的独特性,难以被他人的人生所取代。这种由众多的个体化人生综合而成的一个抽象范畴的人生,是没有办法在诗歌中表现的,需要有从笼统到具体的转化过程:以某种标准把“人生”划分成几大类别,从这些类别中再选取某一种“人生”作为现代新诗所要彰显的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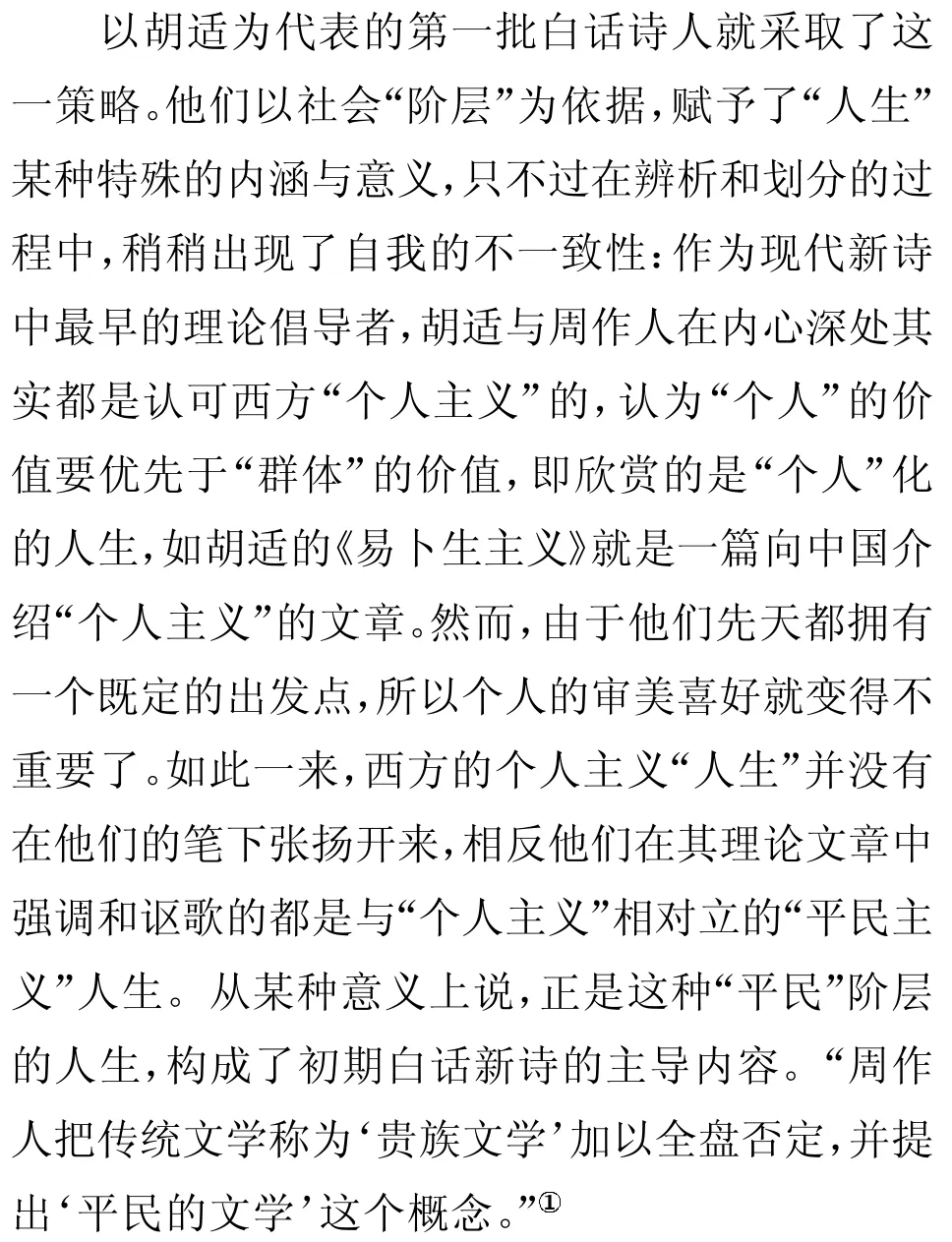
何谓“平民”,或者说平民阶层?由于这些称谓并非是本土的,而是在“五四”初期由国外引入,这就决定了其内涵的不确切性。有的新文学启蒙者认为,凡是与贵族阶层相对立的人,都可算作“平民”阶层。这个划分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即把社会中绝大部分的人都包容了进来。然而,这个“平民”阶层的“人生”还是过于庞大,依旧不可把握,如同样都属于“平民”阶层中的人,知识分子的“人生”与那些出卖苦力的“人生”就不是一回事。因此说,仅凭“平民”或“平民”阶层的这一人生设定,还是不能完成对新诗内容的实质性置换。为了让“人生”能够在现代新诗中飞扬起来,白话新诗人便心照不宣地把广义的“平民”阶层的人生,缩小至狭义的“平民”阶层的人生,即特指“平民”阶层中那些位于社会最底层的受苦人。
知晓了这样的内在逻辑置换,才会明白当时身为大学教授的胡适和周作人,不去展示自己丰富多彩的“人生”,反而纷纷摹写自己并不是特别了解的贫苦人的“人生”,分别写下了《人力车夫》《两个扫雪的人》和《背枪的人》等一系列穷苦人诗歌的内在原因。

通过对现代新诗史上第一批白话诗人创作实践的简单回顾,发现所谓的与“人生”发生联系,就是强调诗歌不要有意识地粉饰太平,而是要与下层民众的悲苦境遇发生关联。而且这种关联并非鲁迅那种自上而下的精英式批判,而是要对其赋予人道主义的充分理解与关怀,这可谓现代新诗的一大传统。这个传统,也可称为“人道主义”的叙事传统。
显然,所谓人道主义叙事传统,就是一种专门描摹和反映下层人生活的传统。然而该处存在一个问题,即对其生活展开描写的多半都是身为大学教授的知识分子,而他们本身对下层人真实而具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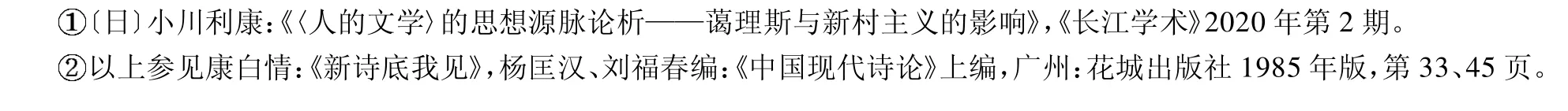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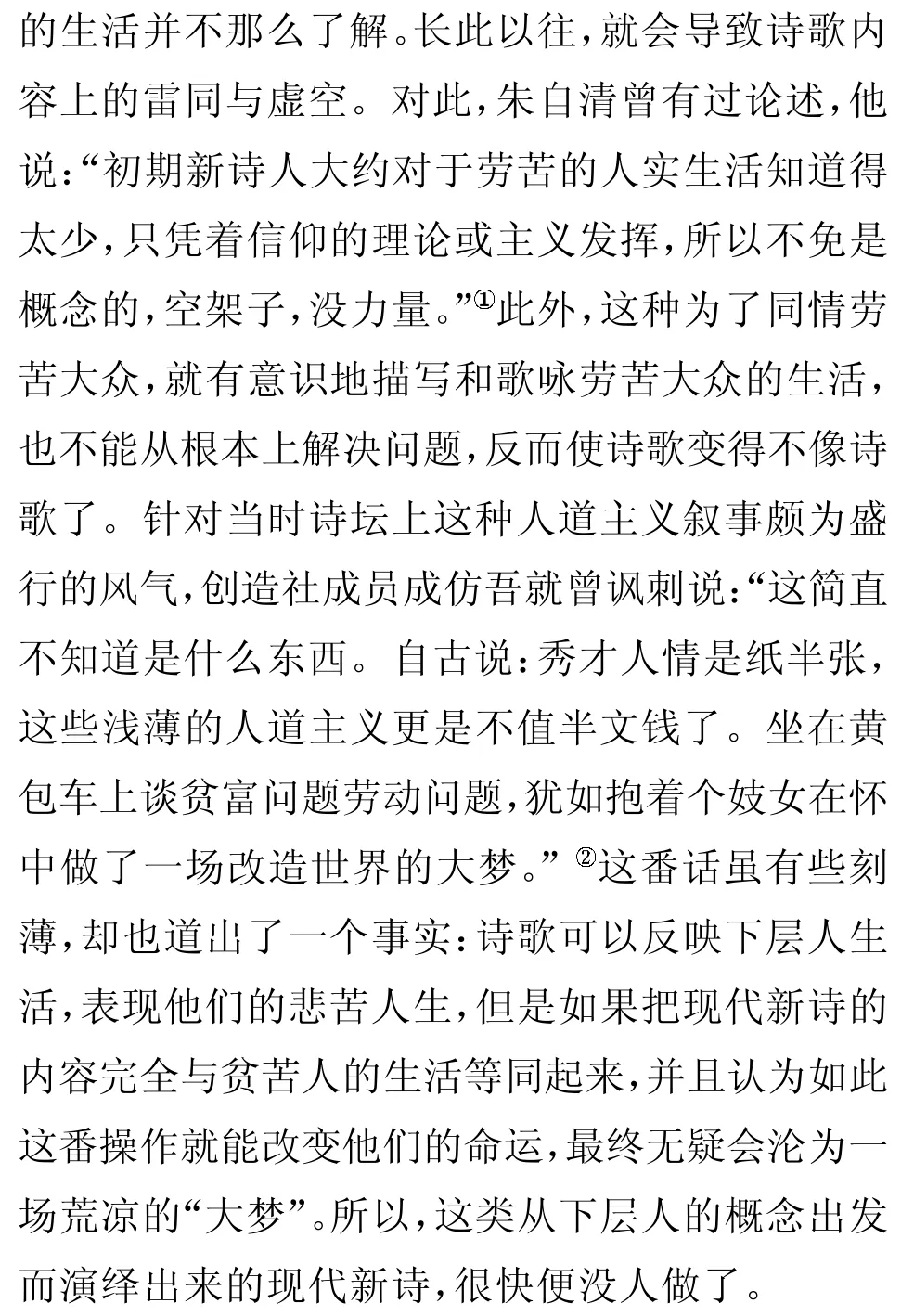
这样一来,现代新诗便拥有了它的第二个传统:以“理”为上,即诗人在诗歌中笼统地说理,而不再是专门为下层人生活鸣不平的叙事传统。
二、以“理”为上的叙事传统
人道主义叙事传统,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说理的传统,只不过这种专注于为下层人说理的传统,与该处所要论述的说理,即叙说人生或生活哲理有所区别,故而把它单列了出来。
在中国传统诗歌中,假如有诗人有意识地让诗歌这个文体来说“理”,绝非算是优点,但时过境迁,现代新诗就是从呼唤“理”和说理开始的。朱自清对初期白话新诗的这一特点,有过一个总结。他说:“新诗的初期,说理是主调之一。新诗的开创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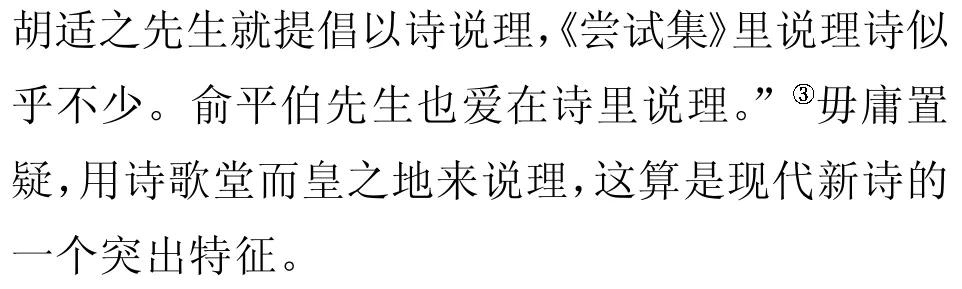
如果沿着“说理”的脉络来观察现代新诗的演变,大致可以把现代新诗分成两个阶段:初始阶段的“理”和高级阶段的“理”。所谓初始阶段的“理”,主要指诗人借用诗歌这种体裁,直截了当地说明某个物件或事情的某种道理。胡适的《尝试集》中就有着大量此类说理的成分,如看到在大雪映衬下的一枚红色枫叶,胡适便会走过去,摘下来,夹到书中。然后写下“还想做首诗,写我欢喜的道理。/不料此理很难写,抽出笔来还搁起”(《三溪路上大雪里一个红叶》)这样的诗句。冰心在其著名的《繁星》中,也写下了“成功的花,/ 人们只惊慕她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她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 撒遍了牺牲的血雨”(《繁星 五五》)。
这类借诗说理的诗歌自然也有其价值和意义,尤其是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与现实语境来看更是如此,但是对于一种艺术体裁来说,这些诗却显得有些过于浅显和直白,不能给人留下更多的想象空间。所以说现代新诗经过这种较为初级阶段说理的过渡,很快便转向了更为高级阶段的说理:诗人们尽可能地避免用朴素的具体事件或物象来说明人生的道理,而是开始考虑借助中国的传统哲学来暗示和隐喻道理。这样一来,此时的“理”,就不单纯是与人生相关的某种具体道理了。这种“理”已经超出了前期的单一性,而具有了多义性、隐喻性的特征。在这方面较为突出的首推宗白华,他出版于1923 年的《流云小诗》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宗白华也认为现代新诗应该“描写人类人性的真相”,但是他所说的这种“描写”与以胡适等人为代表的白话新诗人不同,他更为强调诗人人格的培


这首名为《夜》的诗,与初期白话诗的写作模式是两样的,诗里非但没有与底层人相关的生活内容,甚至连社会现实内容都没有,完全是诗人面对夜空时的一种放空自我的冥想。当然,这种冥想也并非是毫无根据地乱想,而是依据了中国道家哲学中的“我即万物,万物即我”之思想推演而出的,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所倡导的天人合一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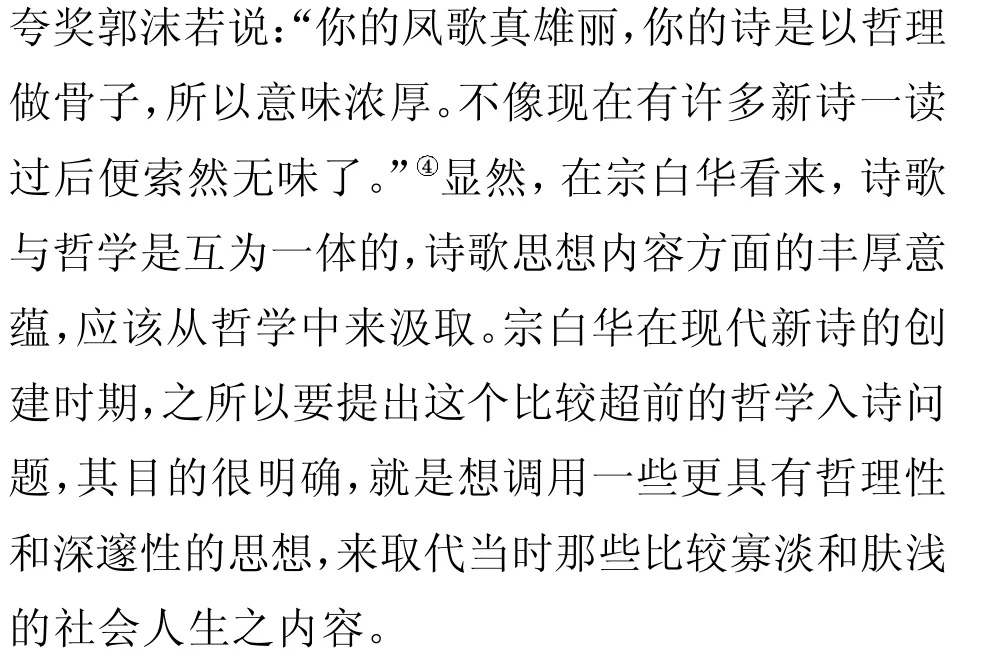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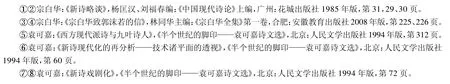
应该说,现代新诗走向反抒情的道路,是顺理成章和自成逻辑的:现代新诗从其诞生的那天起,内容上强调的就是对“理”的诠释,而不是“情”的抒发。而这个所谓的“理”又不能凭空产生,只能依靠诗人在诗歌文本中,叙述某种“事”或某种“事实”(包括哲理上的事实),才能达到和完成这种“说理”目的。这两方面的自动调和性,就使现代新诗形成了一种新的表达模式。这种表达模式大致可概括成一种叙事,或者说叙述框架下的新抒情传统。
当然,现代新诗中的这种叙事或者说叙事框架,并非是指要借助诗歌来讲述一个故事,而是要求把生活中、人生里的一些具体问题,如人生的困惑和意义等搬入诗歌中予以讨论,从而赋予现代新诗介入社会和人生的功能。如果说以胡适为代表的具有说教意味的“理”,还多半属于庸常的人生之理,那么宗白华的《夜》,则代表了现代新诗的一种新的发展趋向:试图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哲思冥想,取代那些琐碎而平常的人生道理。说得更具体一些就是,“人生”在宗白华的诗意范畴中,不再单纯是与苦难,特别是下层人的生活苦难联系在一起,相反它更是一种在空中飞扬的思想之光。
这样一来,所谓的“叙人生”也就变成了“叙哲理”,或者说“叙思想”。如此一来,现代新诗的创作内容被拓宽了,重要的是中国传统哲学作为一种文化精神资源,也能顺理成章地进入中国现代新诗的创作中,成为现代新诗传统的一个构成部分。遗憾的是,宗白华所处的时代正是开足了马力向西方学习的时代,且现代新诗从其产生的渊源上讲,西方文化的影响也要远远大于传统文化的影响。这两方面的原因,决定了宗白华的这种倡导不可能产生太大的影响力。事实也确实如此,就当时的创作情况来看,除了冰心在《繁星》中有所回应,写下了一些诸如“黑暗,/怎样幽深的描画呢!/心灵的深深处,/ 宇宙的深深处,/ 灿烂光中的休息处”等诗句外,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
即使宗白华写出了《夜》这样比同时期诗人明显要高出一筹的诗作,也并没有成为那个时代诗坛上一颗熠熠闪光的明星,这并非是偶然的,而是因为他的艺术思想与其当时所处的时代不合——“五四”追求的不是传统性,甚至不是东方性,而是与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相反的那个与西方文化相连的现代性。所以说,宗白华的民族性和东方化追求,在当时是不会有太大出路的,更不可能成为现代新诗的创作主流。
三、西方宗教、哲学框架下的叙事传统
现代新诗里一直存有这样的现象:从草创时期开始,新诗就明里暗里追求一种现代性,即现代新诗一定要有一种现代性或者说现代化的特质,这是时代和社会所赋予新诗的一项使命——文学救国的使命。问题是,这种“现代性”在新诗中的呈现方式,似乎并无人予以概说。
以胡适为代表的以“事”说“理”的现代性,显得有些过于直白并带有说教的意味;宗白华试图借用传统哲学来隐喻人生之“理”和世界之“理”的现代创作手法,由于与当时的社会要求相违和,故而也没能够发展起来。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宗白华的这种可以用叙哲学的方式来叙某种思想或观念的现代性创作理念,在其后的诗人那里却得到了发扬光大——只不过在借鉴和继承的过程中,诗人们根据时代的需求,把中国的传统哲学内容置换成了在当时人们的视阈中,觉得更具有现代性的西方宗教哲学,并通过实践把其发展成现代新诗创作中影响至今的一种叙事手法。
如果说当时诗人们的这种努力可能还是无意识的,那么今天再对这段新诗历史给予总结时,则应充分地肯定和重视这种把异域文化移植到其诗歌内容中来的实验性意义。从现代新诗的整个发展过程来看,现代新诗自从把西方的宗教哲学吸入并融汇到了新诗的内容后,便发生了一个质的飞跃。而且这个飞跃,还是与中国现代新诗史上艺术成就最高的现代主义诗歌相伴而来的。换句话说,经过写实派诗歌的简单过渡,中国以象征派为发端的现代主义诗歌的出现与发展,就与新诗史上的这种文化“移植”有关。

李金发的诗歌内容果真神秘到不可解?其实也并非如此,李金发的诗歌之所以晦涩难懂,主要在于其所展示出的诗歌内容与现实生活无关,更没有什么真实、具体的现实事件,有的都是对死亡意识的描写与渲染。从某种意义上说,李金发就是一位专门描写和叙述死亡的诗人。
作为中国人的李金发,为何要在其诗歌文本中反复书写那种“生命便是死神唇边的笑”(《有感》)诡异的死亡?以往对李金发的研究,多半注意到了法国象征主义诗人波德莱尔给他所带来的影响,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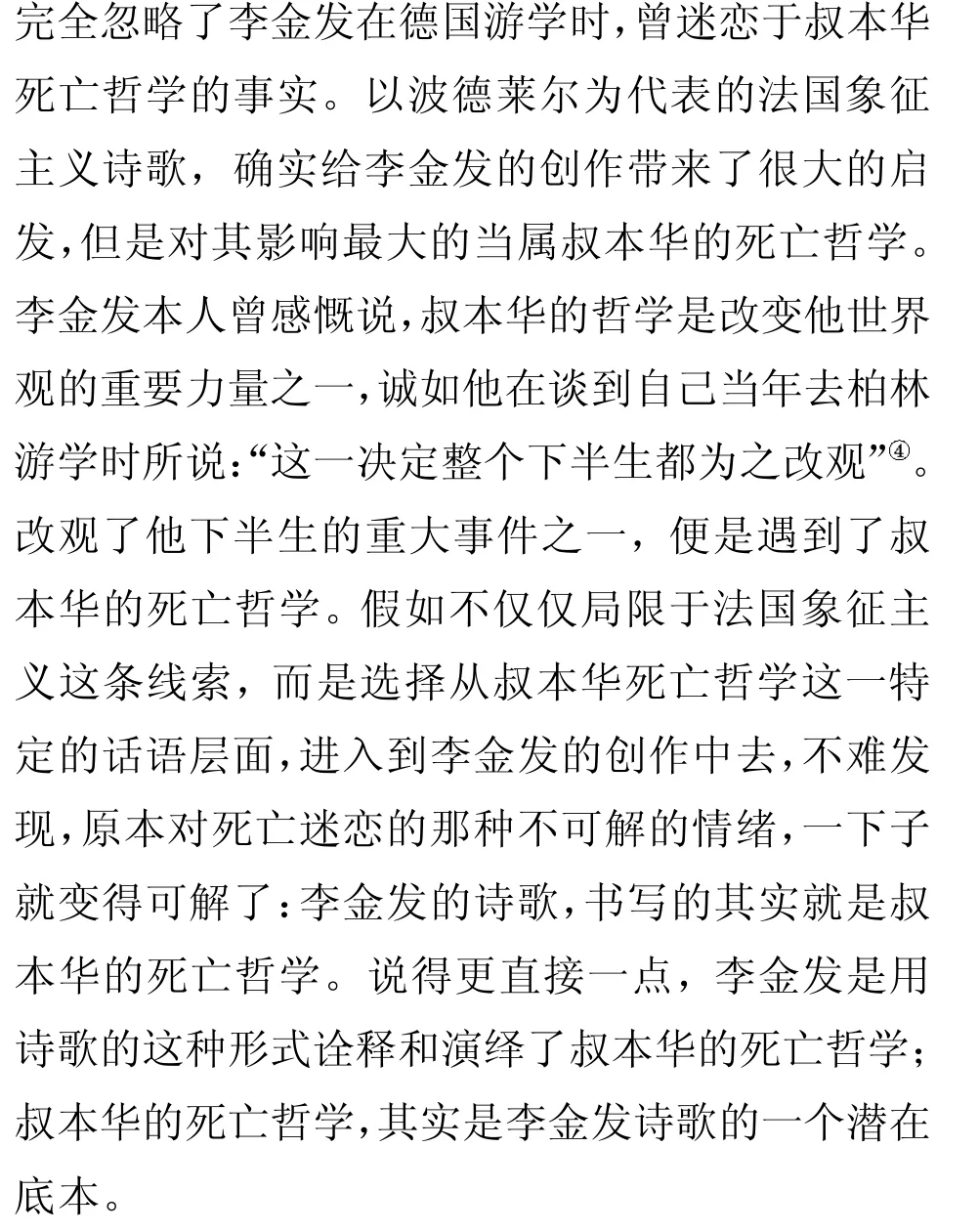
在现代新诗中,与李金发创作风格比较近似的诗人有胡也频,他的《悲》《旷野》《无知觉的生活》等诗也都是描写死亡意识的。如《悲》中有这样的诗句:“我想逃避这龌龊的活尸之围,/ 遁入仙山,以碧草为褥,海风催眠:/呵,企望着洁白的少女之臂儿,/ 终须满足于无底之空梦!”如果对李金发的《弃妇》一诗有所了解的话,会发现胡也频的这些诗句中有着李金发的影子,如他把“爱”与“墓侧”“墓旁”联系到一起;把“生命”与“阻塞”“空梦”“停顿”等相比拟,这都是李金发所惯用的手法。
从胡也频遗留下来的诗篇来看,他是在创作思想与美学风格上距离李金发最近的一位诗人,同时也是与李金发最心有灵犀的一位诗人。不幸的是,胡也频28 岁就去世了。随着他的去世,由李金发所开创的这种把死亡作为一件重大事件予以展示和描写的传统,并没有被其他的现代诗人所承继和发扬。其后的现代主义诗人,如以施蛰存、戴望舒等为代表的20 世纪30 年代的后期象征主义诗歌,一方面延续了李金发把西方的宗教哲学引入到现代新诗中来的传统,另一方面也改变了李金发那种在死亡的绝望中发掘诗意的写作路数——不再直接在诗歌中大量地描写死亡之事,而是把笔触变得更加温柔一些,即转而开始描写一种忧郁的“怀乡病”。

后期象征主义诗人笔下的“怀乡病”是一种什么样的病?或者说,诗人借助于此“病”,欲向人们叙说一种什么样的思想或情绪?“怀乡”这个词语,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中国诗歌里那些远方的游子表达对故土思念的诗歌。这类诗还有个固定的名字,叫“怀乡诗”。但是戴望舒的“怀乡”,怀的并非是家乡的故土,而是对“天”的一种怀想。正如他说:“怀乡病,哦,我啊,/我也许是这类人之一吧,/我呢,我渴望着回返/到那个天,到那个如此青的天,/ 在那里我可以生活又死灭,/ 像在母亲的怀里,/一个孩子欢笑又涕泣。”诗中引发诗人相思成疾的“天”,到底隐喻了什么?
首先,诗歌中的“天”并非是普通天空,而是一个散发着特殊光芒的场所,诗中人“我”一旦到达了这里,便能获得全身心的自由,既“可以生活”又可以“死灭”;既“可以安憩地睡眠”,又可以摆脱“心的一切烦恼”。总之,这是一个既可以让人生,也可以让人死的乐园;其次,想进入这个“天”的人,绝非诗人一个,很多人都心存愿望,用诗人的话讲,“我也许是这类人之一吧”。最后,人们“渴望着回返”,但又去不了,于是便引发出了一种疾病——“怀乡病”。毫无疑问,该处的这个“乡”并不是指家乡的“乡”,而是指遥不可及的空中乐园。在诗人看来,这个“乐园”才是人的终极目的地,即唯有回到“天”上,人才算是真正回到了“家”。
显然,这个“天”的概念,只能结合西方宗教哲学中不死不灭的“天堂”观念,才能顺利得以阐释。这样说并非只是一种揣测,戴望舒还有一首诗的名字就叫《乐园鸟》,里面也有这样的诗句:“假使你是从乐园里来的/可以对我们说吗,/华羽的乐园鸟,/自从亚当,夏娃被逐后,/那天上的花园已荒芜到怎样了?”
在这首诗中,诗人继续做着他的“怀乡”之梦,不知道天上的那个“乐园”(花园)到底怎么样了?于是,诗人便禁不住地向从“乐园”里飞来的“鸟”儿打探。从这一段诗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戴望舒确实是借用了西方的宗教哲学思想,作为其新诗的创作内容。这说明了在中国的现代诗人中,的确存在着一种把西方的宗教哲学视作新诗借用资源的创作倾向,而且这种倾向随着时间的流逝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最典型的是20 世纪40 年代“九叶诗派”中的穆旦。纵观穆旦一生的创作,总体说来他的诗歌创作风格呈现出了多样化的态势,但不可否认的是,穆旦创作于20 世纪40 年代的那批具有现代主义意味的诗歌,实际上也就是为其带来巨大声誉的这批诗歌,与他创作于其他历史阶段的诗歌确实有着不一样的质地。这种“质地”的最大区别在于,写于该历史时期的诗歌,都与西方的某种现代哲学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性。例如《我》的开头两段:“从子宫割裂,失去了温暖,/是残缺的部分渴望着救援,/ 永远是自己,锁在荒野里,/ / 从静止的梦离开了群体,/痛感到时流,没有什么抓住,/不断的回忆带不回自己。”
诗的题目是“我”,顾名思义,诗人是想借助诗歌这种形式,向人们展示出“我”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这类以“我”为主题的自画像般的诗歌,在中国传统诗歌中并不少见。如屈原在《离骚》中曾写下过“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这样袒露心迹的诗句。如果说这类诗还不能完全展示出“我”的个性特征来,那就再看一首典型的自画像诗,即清代乾隆年间的诗坛领袖袁枚所写下的《自嘲》诗:“小眠斋里苦吟身,才过中年老亦新。/偶恋云山忘故土,竟同猿鸟结芳邻。/有官不仕偏寻乐,无子为名又买春。/自笑匡时好才调,被天强派作诗人!”
以上两种情形是古代诗人比较典型的描写“我”的手法。前者借诗句表达了不管外在的社会境况如何,“我”一定要坚守住心中那份美好理想的决心;后者则表达了传统知识分子“有官不仕偏寻乐”的那份悠闲自得的心态。总之,不管是哪种写法,都是与自己的真实生活状态和精神境遇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即借此来向世人传递心志。
穆旦的这首《我》,与上述的两种情形既有一致性,更有差异性。而且,差异性要远远地大于一致性。具体说,三个人都是对“我”的生活或精神状态进行了描写,这是其一致性的地方。然而出发点看似是相同的,但导出的结果却是两样的:屈原和袁枚笔下的那个“我”,都是真实社会境遇下的“我”,顺也罢,逆也罢,都与诗人的亲身经历紧密相关,即他们的痛苦和欢乐都是源自对自己真实的现实境遇的感受与反映。穆旦的《我》则不一样,它虽然以“我”题名,其实写的不是“我”,而是“我们”或者说人类。即他的《我》叙说的是人——笼统的人,而不是特定的人“我”的苦痛。这种着重于对人类苦痛的宏观叙说模式,不可能源于诗人的某种不如意的具体生活,或不如意的具体事件,而主要是出于一种形而上的哲学思索。之所以要这样说,原因如下:第一,《我》这首诗是从“我”与母体相分离的那一刻写起,即写的是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在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传统诗歌的表述框架中,新生命的出生从来都是可喜可贺的——它是关系到一个家族未来和希望的大事件。然而在穆旦的表述框架中,“我”,即新生命诞生的这件事所代表的意义则完全被消解了:离开了母体的“我”,从原本“温暖”的庇护中,一下子被“锁”在了“荒野里”。孤独无援的“我”,只能期盼着有人能把自己从这茫茫的苦海中救出。显然,出生这件事的内涵发生了改变,由原本的喜剧变成了悲剧。第二,在中国传统诗歌的表述框架中,一个生命出生了就是出生了,开弓没有回头箭,所以基本无人会表达渴望重新回归于母亲“子宫”的心愿。穆旦的这首诗则不一样,他认为“我”,其实也就是人类只有重返母亲的“子宫”,才能获得永久的安宁和生命的永恒。
总之,穆旦诗歌中对“生”的认识,以及由此所衍生出的“仇恨母亲给分出了梦境”的人生之荒诞,甚至包括连生存这件事本身都是痛苦和不幸之思想,显然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没有太大关系,主要是受到西方现代宗教、哲学,譬如原罪论等思想观念的影响。
总之,现代新诗自诞生以来到20 世纪40 年代末期,尽管其发展过程高高低低、进进退退,异常复杂,但是从现代新诗尚新、尚理,即对世界新思想、新观念不懈追求的角度入手,可以把现代新诗的发展从理论上归纳成上述的三大叙事范式,以此为现代新诗的研究提供另一个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