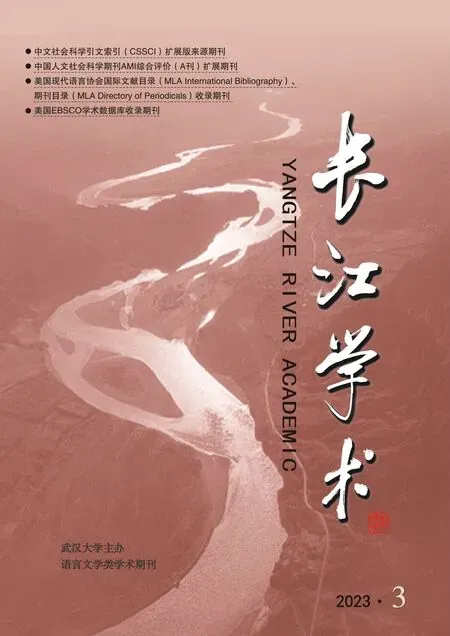意境化与知性化:现代派新诗意象与唐宋诗词
陈学祖
(杭州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1121)

值得注意的是,现代派诗人们在意象的选择与运用上始而趋同,继而分化乃至最终趋异。一部分现代派诗人追求意象意境化,呈现出朦胧空灵之美感色彩;另一部分现代派诗人则逐渐趋向于玄学化、思辨化诗风,并将其与唐宋诗词的理趣美因素相融合,从而造成浓厚而独特的知性特征。
一、现代派新诗意象意境化与唐宋诗词
一大批现代派诗人在意象运用上受到唐宋诗词的深刻影响,同时融合了西方现代派意象艺术,致力于意象意境化,其诗歌在整体上呈现出含蓄蕴藉的诗意结构,显现出空灵幽晦的美感色彩。






受到新月派、象征派以及20 世纪30 年代现代派润泽而成长起来的更年轻的一代青年诗人,如何其芳、林庚、程千帆、孙望、林英强、侯汝华、朱英诞等,均为唐宋诗词行家里手,一方面迷恋于唐宋诗词那种惝恍迷离的意境,另一方面热衷于以分行书写的新诗来表达自我内心的情思。因在调和与融通中西诗艺上所做的努力,其新诗构成因素极其复杂,作品呈现出别样格调,其中的唐宋诗词因素非常鲜明,甚至可称为诗作中最重要的色调。换言之,他们的新诗亦多用唐宋诗词的意象与语言,在诗风上呈现出强烈的意象意境化色彩,甚至将新诗写得如同唐宋诗词一般。


何其芳对唐诗有精细的阅读和精深的研究,对李白、杜甫、白居易、温庭筠、李商隐、李贺等人感兴趣,尤其是对李商隐可谓达到痴迷程度。不但早期新诗中渗透了李商隐的诗美因素,而且直到晚年的旧体诗词仍多模仿杜甫、李商隐之作,前者有《效杜甫戏为六绝句》,后者有《有人索书因戏集李商隐诗为七绝句》,其晚年创作的58 首旧体诗,竟有38首“无题”诗。此外,其《杜甫草堂》乃是歌咏杜甫之作,其14 首《忆昔》诗明显受到杜甫《忆昔》诗的启发,而《锦瑟——戏效玉溪生体》二首亦启思于李商隐《锦瑟》诗。



二、现代派新诗意象知性化与唐宋诗词
如果说戴望舒、梁宗岱、何其芳、林庚、吴兴华、程千帆、孙望、林英强、侯汝华、朱英诞等人的诗歌更倾向于情绪与情感的表现,对唐宋诗词意象的借鉴与沿袭主要是晚唐五代诗歌与唐宋词“兴象玲珑”之美,那么,废名、卞之琳、金克木、路易士、徐迟、南星则既重视“兴象玲珑”之美,又较为偏重与突出唐宋诗词意象的独特运用——善于以理性与智慧选择富有差异性的意象,并将这种差异性予以突出与强调,因而其诗歌意象与意象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异质与背离,但这些看似相互之间背离的意象,却在情感指向与艺术功能上具有惊人的一致性与统一性。换言之,他们善于以其独特的理性与智慧,在意象选择与艺术营构上体现出惊人的冷静与克制,因此,在他们的诗歌中,本为感性意味的意象,却因经过了理性与智慧的冶炼而展现出别样的知性之美,其诗歌的意象艺术,可以说是唐诗之“兴象”、宋诗之“理趣”、唐宋词之“婉约”与西方现代派诗歌之“知性”的有机融合。








这正是卞之琳诗“智慧之美”的典型体现,也是其早期诗歌与唐宋诗词之重要关联。卞之琳最喜爱的唐宋诗词家如李商隐、温庭筠、姜夔,以及外国现代派诗人波德莱尔、魏尔伦、艾略特、里尔克、瓦莱里等,其诗词作品也最能体现上述两个特征。这是上述中外诗人相通之处,也正是卞之琳看重与取法之处。






《断章》中的意象经由一般语词的连接,构成了四个意义完整的句子,第一节是虚拟的情境,尚属写实层面,第二节则转为由实入虚,由具体到抽象,由清晰到朦胧,由形而下到形而上的层次。从第一节到第二节,无论是句法结构还是语义结构,均发生了本质变化。值得提出来讨论的是,其一,第一节与第二节的“你”是否同一个人?其二,第二节中的“别人”是否就是第一节中的“看风景的人”?其三,既然“你站在桥上看风景”,怎么又说“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其中的“窗子”指的是什么?词语语义的模糊造成了此诗众说纷纭的解释,也造成了巨大的阐释空间与审美蕴涵。诗作语言形式的安排与内容的暗示多义,显然得益于唐宋诗词的类似诗歌结构,如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江畔何年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李商隐《子初郊宿》“看山对酒君思我,听鼓离城我访君。”在句子结构与语义结构上整饬中有变化,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以这种诗歌结构来融合庄禅相对与相合的辩证思想,卞之琳于此可谓深得唐诗精髓。
与卞之琳不同,前期的冯至所崇尚的是浪漫主义的诗歌,受歌德诗歌影响较深,但他所接受的歌德与郭沫若所接受的歌德存在着本质的差别。较之于郭沫若诗歌强调激情的宣泄,冯至的诗歌较多现实的关怀,可以说,郭沫若所接受的乃是歌德诗歌中李白诗式的潇洒飘逸,而冯至所接受的歌德则是杜甫式的沉郁顿挫。换言之,郭沫若是以李白、老庄去契接歌德诗歌,而冯至则是以杜甫、孔孟去契接歌德诗歌的。正因如此,冯至诗歌中自始至终保持着深沉的冷静与克制。尤其是在抗战期间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涯中,冯至自身的生命体验与里尔克对于生命存在与现实担当的深沉思考达到了高度契合,最终创作出了标志其诗歌创作顶峰的《十四行集》。






三、现代派新诗意象意境化与知性化分野之根源
中国现代新诗意象意境化或知性化,其根本成因取决于新诗诗人之诗歌阅读经验与诗歌审美心理结构,其中的某些核心因素,往往成为制约其新诗创作重要的“潜意识”,或自然而然渗透到其创作之中,或因诗人的刻意追求而使得某些诗美因素得以凸显与强化。中国现代新诗诗人对唐宋诗词意象的选择、熔铸与转化也是如此。唐宋诗词的意象有意无意地渗透诗人的诗歌思维之中,不仅成为其情感表达的重要载体,还制约其对整首诗歌意象的选择与营构。戴望舒、梁宗岱、何其芳、林庚、吴兴华、程千帆、孙望、林英强、侯汝华等诗人迷恋与崇尚唐宋诗词,某些沉淀于其诗美心理结构深层的意象便自然而然地进入其新诗之中,同时,契合唐宋诗词意象所奠定的基本情调,这些诗人也偏重于选择富有情感内涵的西方诗歌意象;而以废名、卞之琳、金克木、路易士、徐迟、南星为代表的另一部分现代派诗人,虽然也崇尚唐宋诗词中那种惝恍迷离的意象类型,但因其偏重于佛禅道儒之哲学玄思而逐渐趋向于对艾略特、奥登以及玄学派多恩等诗人那种玄学化、思辨化诗风的体悟与追随。由此,便形成了中国现代新诗对唐宋诗词意象选择、熔铸与转化的两类基本形态。

同样是对唐宋诗词艺术资源的选择与吸纳,中国现代新诗在意象形态及审美特征上却出现如此巨大的差异,其根源不仅在于新诗诗人不同的诗歌经验结构,而且还取决于对这种经验结构的扩展与转化。诗美经验扩展的基本途径是经由已有诗美心理结构对于新的诗歌资源的选择、接受与转化而实现的。那些追求新诗意象意境化的新诗诗人,因其对于唐宋诗词中注重情趣与兴象玲珑之美质的一路诗风的吸纳,决定了其诗美经验扩展的基本方向,必然走向瓦雷里、魏尔伦、马拉美、兰波等突显情感内质与感性形式的诗风。情感因素的突显必然导致意象类型化的要求,于是,以那种富有感性内涵的唐宋诗词意象去契接西方诗歌同类意象,便成为其新诗意象营构的基本途径。而那些注重融合杜甫诗歌及宋诗理趣诗风的诗人,则往往倾向于以唐宋诗词意象去契接与融合艾略特、奥登等现代派诗人之诗歌意象,其意象体系呈现出玄学思辨的知性化特征。
不同审美趣味的新诗诗人,不仅在意象选择上存在着巨大分野,而且在意象组接与营构方式上也呈现出较大差异。倾向于唐宋诗词意象的新诗诗人,往往呈现出意象的密度与并置特征;而那些热衷于意象知性化的新诗诗人,其诗歌意象往往较为稀疏,意象之间的组接往往穿插较多的修饰性语词。这种意象疏密的形成及其组接方式的设置便秉承了汉语诗歌,尤其是唐宋诗词依据情感特性及精神指向所形成的文体特性。意象的类型化、意象的疏密以及意象的组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中国现代新诗意象意境化与知性化之分野。


上述两类诗人对唐宋诗词之宗尚,同中有异,既有共同宗尚之诗人诗风,又在对同一宗法对象之具体因素的选择、接受与转化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别,因而其新诗创作在遵循现代主义诗歌整体风格的同时,在诗美品质上呈现出较大差异。其中最明显的便是20 世纪30 年代出现的“晚唐诗热”。无论是倾向于意象意境化的诗人,还是追求意象知性化的诗人,均热衷甚至迷醉于晚唐诗风,但在其选择具体诗人诗风的时候,却各有偏重。前者着意于晚唐诗歌之含隐蓄秀、深情绵邈;后者则偏重于晚唐诗风中的奥僻幽邃、冷峻镌刻。



同样是迷恋温庭筠诗词并受其影响,废名与何其芳因诗学渊源、审美趣味之差异,而导致了在意象选择与运用上的知性化、意境化之分野。虽然这只是个案的对比,但若对现代派诗人均热衷于迷恋的李商隐做具体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将会是一致的。这充分表明,造成现代派诗人对唐宋诗词意象借鉴、接受与转化中意境化与知性化分野的根源,不但在于对意象类型的选择运用,也取决于他们所吸取的与这些意象进行组合的另外一些因素。换言之,唐宋诗词只是影响诗风的重要因素,而非决定因素。

综上所述,20 世纪30 年代的中国现代派诗人从内心深处秉持着对唐宋诗词的热爱之情,使之成为其诗歌审美心理的“前结构”,换言之,唐宋诗词成为现代派诗人诗歌知识与诗学观念结构的构成因素,因而其诗歌创作大量吸取与运用唐宋诗词意象。部分现代派诗人沿袭了唐宋诗词的意象意境化追求,并融合西方现代派诗歌意象艺术,其诗歌呈现出含蓄蕴藉空灵幽晦的审美特征。而另外一部分诗人则将唐宋诗词意象中的知性化特质以及中国传统的儒释道思想,与西方以艾略特等为代表的知性化诗歌传统相融合,其意象艺术呈现出鲜明的智慧美感特征。现代派诗人的这种意象艺术的分野,既是个体诗人个性特质及诗学观念的具体呈现,更是其师法的诗学渊源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