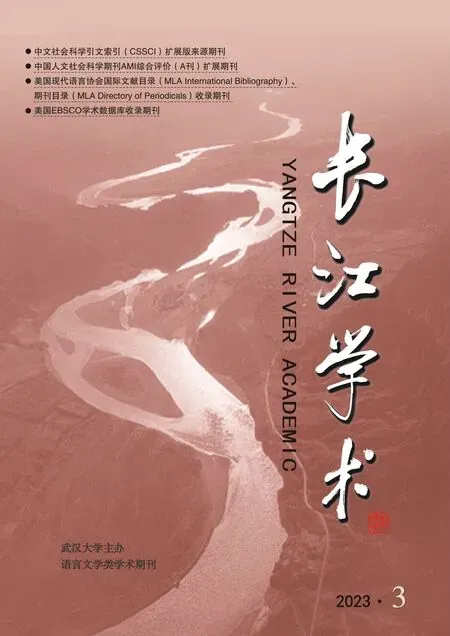新文化运动非儒批孔的思想资源
——诸子学的兴起与孔子形象重构
刘进才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一、诸子学兴起与非儒批孔的历史渊源及文化来路
对新文化运动研究的许多成果,均已注意到新




孔子要到齐国去,齐景公准备以尼谿之地分封孔子,通过晏子打听孔子的为人,晏子对孔子的负面评价及时制止了齐景公对孔子的信任行为。墨子借助晏子之口对孔子以下犯上、教臣弑君、不忠不义行为的批判,彻底改写了《论语》中孔子的仁义面目。

当然,处在文化边缘的诸子也并没有完全丧失其内在的生命与活力,经过一千多年漫长的历史低谷,诸子学在清中叶以后逐渐复兴,汉代以后,在历史文化的整合大一统中,从儒学独尊到儒、道、佛鼎力而足,中国传统文化中深层的多元因子一直在生生不息地流淌与传承。到了清代中叶以后,由于考证学的兴盛,考证古书成为一时之风气,诸子学逐渐兴起,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曾梳理此学术之潜流:
诸子学的兴起,意味着在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多元一体的共生系统中,每一种文化派别都是其有机组成和文化创造者,诸子学也和曾经定于一尊的儒家经典一样,仍然是这个文化传统的创新资源,只不过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资源或占据主导,或居于潜流罢了。




把诸子学研究的兴起作为开启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的先河,可谓独具慧眼的内部观察——“在中国发现历史”,真正是从中国文化演进的内在理路中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自我更生与创造性自我转化的可能性。中国传统文化并非毫无生机的铁板一块,在多元互补中存在相互竞争与相互纠偏的力量,有的文化主体可能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段占据文化中心,另外一种文化板块处于被压抑的边缘地位,边缘与中心可以相互移位,那种长期占据文化与体制中心的力量一旦僵化,处于沉潜或边缘的具有活力的文化就会焕发出勃勃生机,成为文化内部反叛自身的力量。新文化运动健将非儒批孔中常常援引诸子的文化资源为我所用,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二、《新世纪》“排孔”之论的影响与国教运动的刺激
我们强调新文化运动非儒批孔思潮应该置于诸子学兴起的中国内部长时段历史氛围中来观照,并非要刻意拒绝西方影响与中国现实所面临的政治文化语境。事实上,如果从新文化运动非儒批孔发生的近因观之,1907 年,远在法国巴黎,中国一批留法学生创办的宣扬无政府主义刊物的《新世纪》中文周刊不可忽视。尽管创办于海外,但其对此后《新青年》同人的影响不可小觑。后来成为新文化运动健将和《新青年》编辑的钱玄同当时虽在日本留学,却已开始关注并阅读《新世纪》,他多年以后回忆道:


在此,孔子的神圣形象已经与“狡猾”“伪装”“野蛮时代”相关联。较此观念更为激烈的则是《新世纪》的另一篇《排孔征言》文章,明确提出要实行“孔丘之革命”:





正是在这样现实语境的强烈刺激下,新文化运动举起了非儒反孔的大旗,以毫不妥协的决绝心态向中国的传统伦理进行了整体性重估与批判。
新文化运动以《新青年》为阵地,张扬“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在现代中国掀起了一场摧枯拉朽的思想狂飙运动。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随着近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报章杂志的兴起,思想借助现代报刊媒介得以迅速传播,而仁人志士和思想先驱也借助报纸杂志呼朋引伴,聚集力量,形成了传播现代思想的“集束炸弹”。《新青年》在非儒批孔的力量集结方面更是这样。胡适1921 年在评价吴虞和陈独秀的思想交往时谈到:

三、孔子“专制”“复辟”形象的建构:非儒批孔的理论资源与话语策略
大体而言,新文化运动非儒批孔的理论资源有两个方面,一是借助西方科学、民主与自由的思想理念,以革命与进化论相标榜,痛斥中国传统文化伦理及孔子之道有违于现代社会理念;另一方面则是承继了晚清以降诸子学的思想研究路径,借助挖掘被压抑的诸子思想资源批判曾经被定于一尊的儒家文化及孔子思想。

率先向孔子发难的易白沙在表彰墨家文化中批判了儒家文化。他的《述墨》开篇即说:
周秦诸子之学,差可益于国人而无余毒者,殆莫如子墨子矣。其学勇于救国,赴汤蹈火,死不旋踵。精于制器,善于治守。以寡少之众,保弱小之邦。虽大国莫能破焉。今者四郊多垒,大夫不以为辱,士不以为忧。战既不能,守复无备。土地人民,惟人之宰割是听,非举全国之人,尽读墨经。
……

易白沙的《孔子评议》一文,较早开启了批判孔子及其儒家的先河,也因此奠定了他在新文化运动中不可忽视的历史地位。该文把孔子视为被利用的滑稽傀儡,彻底颠覆了传统的素王形象。易白沙首先颠覆了传统文化中视孔子为“素王”的观念:




因此,可以说,孔子专制形象的建构与新文化运动健将对《论语》及相关典籍的重新释读密切关联。通过这样的释读,将孔子及其儒家思想置于中国传统的道家、墨家、农家等多元文化的对比中加以重新评估,不但揭示了曾定于一尊的孔子学说不合于现代自由思想的弊病,同时也发掘了处于压抑与边缘地位的其它文化传统。
至于论及孔子思想少绝对主张、态度不明,容易作为人们行事的各种借口,易白沙的论述理路颇值得玩味。文章指出,孔子乃圣之时也,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其立身之道抱定一个“时”字,认为孔子教授门徒,也因时、因地、因人而异。这种对于孔子思想的解读应该说符合孔子因材施教的思想理路。但易白沙进一步阐发道:




吴虞称道日本教育的“善于取舍”,其实是在批判中国教育的读经之弊,反对尊经与读经,参照日本教育反观中国教育之不足,尤其讲到日本舍弃中国“经籍”的教育而取“子集”的材料,值得关注。吴虞明显意识到了诸子学的兴起有可能制衡经学在教育领域中独霸一尊的专制局面,日本的教育理念对于当时中国的现代教育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借此也可感受到吴虞对诸子价值的高度认可。

发掘诸子的现代精神,利用诸子之学打破曾被定于一尊的儒家学说,可谓利用传统反传统。事实上本没有一以贯之的传统,或者可以说没有铁板一块的传统。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由充满多元、互动共生的文化板块组成的文化整体,其内部的各板块之间有互相吸纳与补充,也有相互砥砺与排斥。自从儒家文化被定于一尊之后,其它非儒家的文化流派渐渐趋于边缘,然而,边缘的活力仍在,仍然作为一种小传统或亚文化而存在。每个时代的文化改革者总是不断发现传统中那些可以与中心文化相对抗的革命性元素以批判传统,也就是利用传统反传统。而被体制认可的儒家文化也总是不断压抑与阻断异己文化的生长与流播,二者相激相荡,构成了文化与思想发展史上的奇观,这种思想奇观在新文化运动中突出呈现。

吴虞考察孔子重视礼仪的行为,认为是曲学阿世的干禄之心所致,这就在道义上贬损了孔子的人格:


新文化运动时期,在科学、民主与自由的理论框架中,孔子的形象被定格在“专制”这一符号层面,吴虞即便是借助基督教的宗教文化资源,描画的孔子仍是如此:



这里的论述已经关乎孔子的道德人格,吴虞几乎全部否定了孔子的人格,进而呼吁像西方的马丁路德进行新教革命一样,中国也要来一番“儒教的革命”。
如果说吴虞、易白沙的非儒批孔建构了一个“专制”的孔子形象,吴虞甚至在人格方面掊击了孔子的污点,那么陈独秀及李大钊则更多从国体与政体、宪法与孔教以及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多方面探讨了儒家文化的颓败之势,借此建构了“复辟”的孔子形象。
陈独秀之所以批孔,与尊孔者势不两立,其中的考量仍在于尊孔者背后的复辟问题。陈独秀把孔子之道的家庭伦理与政治理念看做一体两面,敏锐地指出张勋与康有为的尊孔也正是意识到尊孔与复辟实为一体:

既然二者结为一体,因而掊击孔子也是为了批判复辟的帝制。陈独秀看到了康有为尊孔背后的复辟策略,在他看来,尊孔与共和势不两立。要想倡导共和,必须批判与共和不相交融的孔子之道。陈独秀独具慧眼地探察出康有为复辟背后一以贯之的尊孔理念,看到了近代以来尊孔者背后所秉持的君主政治学说。陈独秀所极力维护的仍然是他心心念念的民主共和政治制度,凡有悖于民主共和的,他都极力抨击。陈独秀在该篇文章最后道出了其批孔的真正动机:


这牵涉到陈独秀的孔学观念以及对孔子之道的根本理解。陈独秀认为,孔子之道是以伦理、政治和忠孝为根本,其他均为枝叶,孔孟论政纯粹以君主的贤明与否为标准来考究政治的成败得失。不仅如此,在他看来,孔子把上下、尊卑、贵贱的观念从人伦日用上升到政治原则乃至天地之间的宇宙法则;他同时把孔子的《春秋》与《孝经》视为忠孝一贯、互为表里。因而,陈独秀担心倘若运用孔子之道治理国家,必然推导出君主政治:

从诸子学考量,认为中国古代的九流诸家远在孔子之上,通过各家的优长对比,建构了儒家孔子的专制形象。
与陈独秀类似,李大钊也认为孔子之道不合于现代生活,但他对孔子本人的人格以及孔子所代表的专制符号做了辩证区分,在这一点上,与吴虞从人格上否定孔子也有所区别,李大钊明确指出:



四、“礼教吃人”意象的儒家伦理观与孔子形象的袪魅化叙述


因而,儒家文化有时被化约为“礼教”或“三纲五常”之说,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非儒批孔有时是对“礼教”的“纲常伦理”或“忠孝节义”观念的直接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