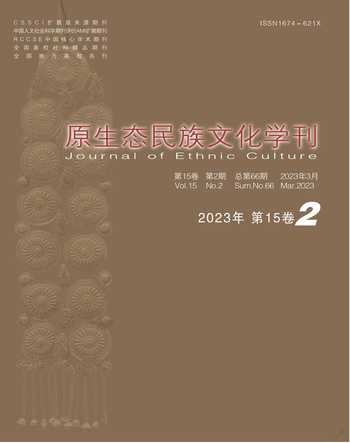十九世纪徽州基层田赋征收中的粮局与乡柜
黄忠鑫 赖意宣
摘 要:在19世纪20 - 30年間,徽州基层社会纷纷设立粮局、乡柜,以统一征缴钱粮。这是在以宗族村落为基础的赋税包揽机制发展的结果。个别粮局还以册书为首扩大到整个图甲范围。粮局有助于在经济萧条和财政困顿时期提高征税效率。太平天国战后由士绅掌控的粮局,征粮范围更为广大,但应借助了此前的粮局、乡柜的运作经验和名称,反映了民间自我管理钱粮汇集、代缴机构的普遍性。
关键词:徽州文书;田赋;粮局;乡柜;图甲;清代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 - 621X(2023)02 - 0076 - 08
自封投柜是清代法定的田赋征收之“定例”。此方案希图由粮户直接向官府缴纳纳田赋。每届钱粮开征之时,州县在衙署和乡村设置若干柜,分别称为“城柜”和“乡柜”。1粮户亲身赴柜,将应纳之钱粮包封投入柜中。如此设计,本意是避免纳税过程中胥吏、书差等人的包揽,可谓“是对明代里甲制下那种由值年里甲统一征解制度的否定”。同时,自封投柜“并不否定图甲作为官府据以逐级稽查纳税责任的职能,也不排除里长、图差一类职务在纳税过程中负有催促、稽核、追欠等责任”2。再加上技术、效率方面的缺陷,小民不可能为零星钱粮进城投纳,各类包收、代纳的代理人和机构是普遍存在的。319世纪上半叶开始,徽州社会纷纷出现以粮局作为税粮代理机构之做法,并对晚清地方田赋征收机制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粮局的产生过程
粮局的产生过程,可通过祁门县三四都一图十甲下黄发隆户的几份赋役合同窥见一二。黄发隆户是祁门瀛洲黄氏宗族的一个户头。乾隆十三年(1748年),黄氏宗族开始承顶三四都一图十甲王大用户的一个名为“王顺”的子户,到了乾隆三十年(1765年),他们将王顺户退还王大用户,并继续依附在该总户之下,成立了本族姓氏的黄发隆户(在契约文书中,又有黄发龙等写法),约定“其黄姓钱粮兵米听黄姓自行投柜完纳,不得累及王姓,而王姓钱粮亦不得累及于黄姓。自立合文之后,各管各粮,两无异说”。在这一过程中,黄氏宗族在当地购置了规模较大的田产,人口规模也持续扩大。1
针对宗族内人户的税粮缴纳不一之问题,黄氏宗族在各阶段形成了不同应对策略,订立了一些赋役合同。首先,在立户不久的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黄氏立下了设立公共田产的合同。
立议合同黄发龙户等,原因户内差房、里长、经催费用等事,恐无统绪;一应钱粮、兵米,完欠不一,是以合户公议,每名出银七钱,买得三四都四保盈字二百廿二号、土名江坑塘坞,内得实租四百十斤,递年挨次经管,收理差房、里长、经催费用。至于户内各人钱粮、兵米递年议定十月十五日齐集投柜完纳,不得延迟拖误。所有田税折实票银七分五厘,附在进福名下,递年亦是经催完纳。所有田契一纸,亦付进福收贮,日后亦不得执匿。如违等情,听自遵守人执约鸣公理论。今欲有凭,立此合同一样十三纸,各收一纸,永远遵守存照。
乾隆三十二年三月初八日立议合同黄发龙户户丁承德、天富、有斌、有进、义仟、有钦、义作、有香、义葱、有再、进福、有远、进汉2
作为子户,也需要负担差房、里长、经催等费用,需要统一筹措;户内人口众多,钱粮和兵米的缴纳速度不一,难免有拖欠之现象。这些都是图甲运作的风险,也说明黄氏虽然只是子户身份,但家户规模较大,如何统合户内人众,完成税粮缴纳任务是需要重视的问题。此时的应对措施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黄氏合伙购置田产作为公共经费的来源,可以减少对家户人众的各种临时科派;另一方面,对于各家钱粮赋税,遵照自封投柜的规定,约定在每年的十月十五“齐集投柜完纳”。不过,如何召集人众,在实际操作上似乎没有说明,似给集体赴柜纳税设想之落空埋下了伏笔。八年后,黄氏便针对这一问题重立合同,改变了纳税形式。
立议重立合墨黄发隆户人等,原因住居窎隔,一应钱粮兵米,完欠不一,以致差扰多需,深为不便。是以通户重议,每年轮流经管,一人将钱粮兵米刻定,清明后至四月内为率,务通户扫数全完。如过期,照依钱粮甘罚银一倍入众公用。倘有抗违,听自经管者执此合文,鸣官理论。至于差房经催等事,原众置有三四都江坑塘坞,实租四秤十斤。除开销差房贴费外,以作经管人盘缠之用。其田税七分五厘,附在进福名下,递年众交代纳钱九十文,今欲有凭,立此重立合墨一样七纸,各收一纸,永远存照。
乾隆四十年十一月十三日立议重立合墨黄发隆户户丁承德、天富、有进、有珊、远斌、义森、永盛3
这份文墨正说明了黄氏虽在同一户名之下,却居住分散;前一合同采取共同赴官、自封投柜的方式并不合适,由此造成了欠税及粮差追索。为规避风险,他们制订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其一,每年轮流选出一人作为经管人,将各家钱粮收足后一并缴纳。其二,族内征缴的时限,从此前的十月提前到四月至八月间。其三,增加了拖延误期之人的罚款条款以及该合同的权威性与合法性。其四,先前应对“差房经催”的公田租金中也拨出一部分作为经管人的盘缠。因此,这些合同条款说明,在清代以自封投柜为法定纳税方式的前提下,宗族内部往往可以通过协商的方式推选族内代理人及相应的保障举措,不必各家各户一一前往。这份合同将代理人的设置视为催征钱粮的关键环节。
到了道光十九年(1839年),黄氏的纳税方式又一次发生变化。
立议伦公祀粮局文约合同人登瀛堂三大房黄良煜、正基、正壆、正墅等,缘因先年合族钱粮立有发隆户口暨各的名,寄于三四都一图十甲户下。今因完粮前后不一,是身合祀嘀议,将身各的名钱粮议立粮局,每粮一钱,公议输实租一秤为则,轮流经管。阖户钱粮,上限下限,务要蚤期完纳立定,恒产恒新,以免粮差催扰。所有公议各条,一一载列于后,秩下人等(永)远遵照,毋得梗顽。如有梗顽,公同处惩。今欲有凭,立此公议合同,永远存照。
再批:改永字一个,照。
一公议,今立粮局生息,各名位钱粮个人仍照旧供兑三年,三年之后统归粮局供兑,又照。
一公议,每粮一钱,输出实租一秤,倘有興废,公议准进不准退,又照。
一公议,嗣后各名置产收税一一照则输租入局,毋得推延,又照。
道光十九年二月廿四日立议伦公祀粮局文约合同黄登瀛堂 秩下良煜(押)、正基(押)、正壆(押)、正墅(押),中见族 正車民(押)1
此时的合同表明,即便采取代理人轮流管理族内各家钱粮,仍不能保证各家能够准时完纳,仍旧是“完粮前后不一”。为了保证按时纳税,黄氏又形成了新的应对措施:设立专门应对赋税的置产机构——粮局。这一举措增加了集体应对赋役风险的保障性,也需要更大规模的资本支持,经过三年的积累和生息,才能够由粮局统一“供兑”全族的钱粮。为此,合同约定粮局由族内户众按照自身税粮多少集资生息,“准进不准退”;各家购置产业也需要一一在粮局登记。与此同时,前述乾隆四十年(1775年)的合同中族内各户居住分散的情况也不再提及。这些新规定都反映出黄氏宗族内部控制力的增强。
从这个案例来看,粮局的产生是人口规模扩大及宗族组织化进一步加强的结果。在文约的表述中,黄氏宗族的色彩体现得愈加充分,开始出现以“登瀛堂”为名的宗族内部机构,说明宗族组织进一步完善,希望用更有力的机构取代单一的代理人以保障税粮的征缴。如果说宗族组织是保障图甲赋税运作的中坚力量,那么粮局便是强化宗族征税的重要手段。从18世纪中叶设立公产,再到设置代理人,最终到19世纪30年代粮局的产生,经历了70余年的过程。
二、19世纪上半叶粮局、乡柜的集中出现
早在18世纪末的民间文书中即已出现了乡柜和粮局的记录。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六月的陈之鹤等五大股合众齐心完纳钱粮合同载:“今因钱粮孔急,虎差横行,不问衿监,俱要锁押,斯文扫地,殊深痛恨,众愤不平。奈事关国课,无可如何。是以合众齐心,议立乡柜,立文钉薄,书名押号。”他们约定乡柜的纳粮期限,每年钱粮“议做八卯完纳”,其中,正月至四月“四卯完半”,“八月至十一月”四卯全完,五、六、七三个月内免催。可见,乡柜便是地方家族自我管理钱粮的机构,能够约定自身缴纳钱粮的期限。卯期定在每月初十日,“齐至公局,或银或钱,公同估足,照例完纳。倘于中有银钱色等不能合則,首人不能充赔,尽银代完,务要细心谨慎,不致错乱。如讹错,首人理治回家,局内交票分给。”由此可知,与乡柜相配合,陈氏家族还设有公局和首人负责汇集和核算钱粮。首人不仅要管理钱粮,还需要将钱粮缴至县衙。所以陈族根据祖先思宏公“原有五股,分为五轮”的规则,“挨次每月每轮议着能人领去代完”。至于“出邑费用,公议每两出银二分,余外该轮内议自备,如挑钱人工食照钱派出,其兵米四、十两卯全完,其挑米人工食亦照米派出”。公局还可以借贷的方式援助无力纳粮的族人,“如上四卯有贫苦不能按限完纳者,该股嘀同五股收分,伊祀□代为押当不拘银钱,公议每月加二五生息,订期七月初十日,押当人备银钱,本利还清,照后收□,如不清,该股公同五股,齐心正直,收伊祀□照时价算该若干,代清押当之,银钱讫仍多□,再准伊收至下四卯”。因此,乡柜和公局的设立,可以“永不受差拘锁押,贴羞抱恨,又不至重出差钱,徒费无益,上裕国课,下宁身家,公私两便,利莫大焉”1。
在19世纪上半叶的徽州文书中还能找到几件与前节相似的粮局合同。如,同样在道光十九年(1839年),黟县王氏家族也订立了“起局经收钱粮”合同,处理的问题与祁门黄氏家族十分类似。
立合同起局经收、税粮早完免累,并清理户册文约人王仕坪、仕炓等,仝甲内江行古等,原因道新户众向来空虚,一切应该所出费用,前籍雎、瀚二人支持,各位多少充付,至今户众无归。迩来户内非昔,粮则星微,出多收少,将来难为之计。况户册自嘉庆十七年清理造册,以后接取实征,于十八年起,遗失一本,十有余年,湮灭不见。众皆袖手旁观。亦由力不胜用,以致户荒进出,无所查考。各位虚供,亦皆罔闻,病莫甚焉。再者,递年税粮,各位供解不一,每有违限啻欠,故遭差弊,屡受掣肘。何故自作其孽,依然受辱,难免钱文多去,何必早纳心闲。所以眼仝相嘀,各位顶力耑输清理造册费用,以及起局经收完粮,佥立董事数人,轮流劝谕,照则计算若干,经催交局。上限自三月初十日起收,至本月底止。下限自九月初十日起,至本月底止。齐付交局,登账查明。开则出邑,完纳户众,给付食用。上限准期四月初十日,风雨无阻交票;下限十月初十日交票,呈局验明,仍后给发各位领去收贮存照。倘有不遵限期者,公议重罚。仍要即交,以便完啚。如再恃横,不遵户众,以抗粮遗累出首,决不徇情。自定之后,各宜遵守,恐口无凭,立此合同文约,一样六纸,各收一纸存照。
内批:余规载簿,以便经理,瞩目了然,只此。
道光十九年五月二十日立合同文约王道新户,经首清册并起局定期收粮归户完纳人:王仕坪子代(押)、仕炓、仕雄、师填(押)、师瑢(押)、尚梁(押)、尚梓(书)、尚眉(押)、尚桁(押)、尚儒(押)、尚佳、尚鋾、尚修、尊焞,甲内江行古
一纸续光记收
二纸三才记收
三纸三阳记收
四纸三统记收
五纸三川记收
六纸江用训记收1
合文中提到的“王道新”户名,不见载于清前期成书的《黟县花户晰户总簿录》,应为一个子户;又有江姓与之同甲,共同参与订约和立局,应该是依附于王姓户名之下的群体。该户的构成似乎不算复杂,但一直只有两人管理,众人对该户的费用津贴及缴纳钱粮等事务颇为漠视。甚至有一本实征册遗失十余年、相关信息无从查考,众人仍然袖手旁观。故而合同有“户众向来空虚”、“自作其孽”之说法。这一情况与黄氏家族此前由个别代理人负责全族税粮颇为相似。为此,王氏家族同样采取设局汇集钱粮的办法,佥立局董数人“轮流劝谕”,依据上下限的周期,催缴户内人众的钱粮。
可见,粮局是宗族控制下的钱粮代理机构,参与钱粮管理的人员(董事)数量大大增加。董事的佥选资格,虽未见明文规定,但皆具备处理公务、应对公差的能力,应是毫无疑问的。粮局的主要作用是方便户内众人就近缴纳钱粮、统一汇缴官府。因而有的合同宣称自行设立“乡柜”,应该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的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二月祁门二十二都一图七甲王永盛户催征钱粮合同就提到这一名词。
立合文人历溪王氏玠公秩下启芫、启萌、洪法、洪贵等,为国课早完,以免拖累事。缘身一图七甲王永盛户向立经催,六殳收租饍差,催纳钱粮,所有实税朋虚,迭年完清,无有蒂欠。近因人心不古,膳差之谷,强者取多,弱者得少,往往不均,甚至故拖钱粮,累及亲房。身等屡欲合户设立乡柜,齐心早纳,以免连累。奈人众难合,是以邀仝本殳玠公秩下人等相嘀,每年钱粮先期完清,上限四月初一日验票,下限十月初一日验票,如无票者,即系拖欠顽人,每票罚出四百文归众。违者鸣官理治,膳差租谷止收六殳之一,毋许逾分。所有条例,候后酌议,切思吾民沐圣主之洪恩,无可报效,若犹拖欠国课,何以为人?今立合文一样五纸贮匣,各收一纸,永远存照
大清嘉庆二十五年二月二十四日立合文人王玠公秩下启芫(押)、启萌(押)、洪钧(押)、洪钦(押)、洪法(押)、洪贵(押)、洪沛(押)、洪瀚(押)、洪铨(押)、洪裕(押)、洪钟(押)、修纪(押)、继芳(押)2
该合同的叙述结构与前述两份合同非常接近。历溪王氏家族同样是提到委托“经催”之类的代理人负责族内钱粮事务,虽一度取得成效,但“不均”之痼疾依旧出现,造成了钱粮缴纳不一,拖累户内众人。为了“齐心早纳,以免连累”,该户自设“乡柜”,汇收并代缴众人钱粮。这显然是仿照自封投柜制度而出现的新现象。在自封投柜制度下,县内一般根据里图划分为若干柜,由县衙书吏点充柜书。每位柜书包一柜(数个里图)的钱粮;抑或除了县城设立总柜外,还在乡间设立若干分柜,由里长等基层职役人员代为看守,同样也是汇缴若干里图范围的钱粮。而这里的“乡柜”只是家族组织自行设置,收粮范围也只局限于一族一村之内,与前述粮局之特征几乎完全一致。
由此可见,乡柜和粮局应该就是同一事物,都是民间社会以集体力量规避赋役风险的主要举措,具有汇缴户众钱粮、按时代纳的基本功能。只是粮局(乡柜)一开始并没有得到有力支持。粮局需要三年的资金积累,乡柜设立之初也面临“人众难合”的困境。
这类代理机构创设的民间文书记录,多集中于19世纪20 - 30年代,除了体现宗族组织的发展之外,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代环境之变动。一方面,19世纪初经济衰退愈加明显,自然灾害频仍,粮食歉收,最终演变为“道光萧条”。李伯重就指出,1823 - 1834年是长期衰退的开始时期。另一方面,物价上涨、人口增长等因素也导致了地方官府行政開支增大,清中叶形成的财政体制趋于崩溃。由此,地方官员的钱粮征收压力剧增。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九月休宁胡氏家族所立的合同便提到,“近来日用浩繁,耗费多端,实难措办。今因现奉县主何公宪示,新例森严,不能迟延,不能缓纳”1。在此情形之下,家族内部订约按时缴纳银粮、兵米。而对于一些家族和村落来说,设立粮局和乡柜也是应对赋税催缴的重要保证。
三、缮书与扩大化的粮局
婺源县十六都四图的图甲组织设立有十全会,亦设局汇收钱粮。其道光十一年(1831年)合同称:
立议合同约人北乡十六都四图十全会等,原一图共有十甲,凡田地钱粮,不可不清。欲正其本,先澄其源。而图内远积欠,或田已卖而粮未催者,或水冲沙塞不能完纳者,或未经册付又花销不纳者,甚有顽户抗纳故意拖累者,种种弊情不一,致图差每年迭来需索,不惟花户受亏,而甲催、缮书尤多骚扰。令集各甲知事,眼同缮书严加考核,果系田去粮存,应追得业之家;果系水冲沙塞,仍照原额输纳;果系空纳钱粮,亦干原主名下追赔。并立图规,每年钱粮各甲公拟善算者一人,协仝缮书在车田六经堂设局收贮。而图内花户粮则无论多寡,的于三月十一日起至十五日止,定在五日内一票全完,不得分为上下两限,各宜踊跃。仰副国课,务祈有始有终,下裕民生,尤当无荒无怠。既属共图谊仝一体,倘有恃顽不遵者,十甲公仝呈究。立此合墨一样十张,各甲执一为据。
道光十一年岁次辛卯三月十二日立议合墨约人北乡十六都四图十甲人等,一甲吴永光、二甲江锡安、三甲江祯元、四甲吴加福、五甲胡秋桂、六甲洪文起、七甲吴美意、八甲汪祝三、九甲吴发祥、十甲胡庆生2
该粮局设于车田六经堂,由缮书(册书)和各甲书算代表共同管理。其征粮范围超越了一村一族,而是涵盖了整个图甲范围。粮局设置目的与前述局、柜一致,都是督促钱粮按限缴纳。这也表明个别地区的粮局影响范围扩大了,其原因应与册书(缮书)主导有关。
十六都四图是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新增之图甲。立图之初,便设置了“册书”一名。“其册书过图只举一人,从一甲充起,每甲承充,五年一换,将册底付下首挨次轮充,无有买底之费。”在清中叶的“顺庄滚催”的改革中,婺源县各图甲仅将册书名目更换为“缮书”,并无实质变化,3因而缮书在图甲征税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方面,缮书在图甲内部以“甲”为单元持续轮充,每甲承充五年应是婺源当地通行之做法。嘉庆十五年(1810年)婺源八都九甲黄正瑛同弟正元、正椿、正栋等分家文书亦指出:“伦[轮]当册书、图正,每甲当五年”。1另一方面,缮书对图内各甲的钱粮缴纳有总体催征之责。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六月婺源四都一下半图六个甲的人户所共立的钱粮缴纳合同便称,“上忙钱粮,各甲准六月半前完纳一半,惟有不完五分,缮书截票来甲,议认加费每洋二角无异”;“下忙钱粮,各甲无论死丁绝户,准定十月半前如数扫清。倘有蒂欠,任凭缮书截票,一粮一费,无得异说”2。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正月婺源吴氏家族合同表明,缮书的五年轮充,以及图甲范围内有田赋催征之责在清末一直存在。
自愿立承充五甲缮书字人吴烈庭,今承到本房友善公众名下,原因向例排规,轮充缮书,每甲承充五年。兹值光绪丙申,轮流本家缮书,已充三年,因所托非人,费用不支,仍有二年,未曾卸役,不能承理无人。本房董事经族内文会在场,公举身承充忝,属亲之未能推却。大众佥议津贴费用英洋八十元整。按期付身料理,限定每年正月付英洋十元,五月茶市付洋十五元,十月付洋十元,两年共付英洋七十元。仍存英洋十元,候辛丑春正付册下首兑清无异。但缮书系身承充之后,自当勤慎办公,不得误事。所是本年接征,及上下忙乡收,及一切图规、公馆大食等费,均身自理,不干本房各花户之事。倘费用不敷,身应补用无辞。或图差舞弊,因缮书之事,无论控本房谁花户,亦身自理。如各甲花户欠粮不交,任凭身带差上门按户比催无阻。各花户因粮欠不交,受累与身涉,如众人议定应付之费违期不清,任身带差上门向收无阻。申明不充缮书,无得异说。此系两相情愿,并非强压等情。恐口无凭,资源立此承充缮书字为据。
光绪二十五年己亥正月 日立承充缮书字人吴烈庭(押),见中文会吴鉴明(押)、吴耀明(押)、吴季文(押)、吴鉴堂(押)、吴焕彪(押)、吴旭东(押)、吴钦太(押),书亲笔(押)3
值得注意的是,缮书具体人选是在“本房董事经族内文会在场”的情况下确定的。族内文会就是地方士绅组织,本房董事是宗族首领,因而该缮书实际是在宗族和士绅共同控制之下的。
对于册书等群体通过推收、催征形成的权力,清末徽州知府刘汝骥曾要求裁汰册书:
该书等名为推收,实则领串下乡、征收钱粮,恃此为牢不可破之饭碗,本府早有所闻。……绩溪一县,轮广不过七十里,钱粮不过万余两,八十人虱处其间,从而吮其残膏,诚有如该书等之所称。专事推收难以资生活者,应即从严淘汰,并设柜大堂,听民间自行输纳,以铲除历年之积弊。4
不过,这一禁令恐在基层难以推行,也未见后续发展情况。总之,册书被乡族势力所垄断,是晚清田赋改革难以触及的层面,也是有清一代徽州基层田赋征收中的稳定环节,地方官员不时禁止,但难以起到根除之效。而在册书主导之下,个别的粮局可以扩大成整个图甲钱粮催征的机构。
四、结论
近二十年來,基于区域经验的晚清田赋研究愈多,逐渐改变了清中叶之后田赋制度无大变动的固有印象。1晚清田赋征收机制产生的新现象之中,粮局、乡柜一类的士绅包揽机构引起了学者的关注。根据舒满君、曹树基的研究,太平天国战后,乡柜(绅局)是歙县地方社会恢复钱粮秩序的重要机构。粮柜与绅局是同一缴纳过程的不同表达方式,粮柜侧重于缴纳地点和方式;而绅局强调的是组织完纳的人群(如绅董和亩董)。从串票内容推测,歙县的绅局大概是在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至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间产生的。从名称涵义,再到产生时间,都与本文述及的祁门、黟县等地的粮局和乡柜颇为吻合。但不同的是,歙县的乡柜与粮局是以“抵征”为主要职责,被官府赋予合法性,征粮范围大,以乡(每乡约有300村)为单位,士绅的主导作用更为显著。“抵征”的持续时间自同治二年(1863年)开始,至光绪十七年(1891年)奉文裁革亩董为止,为期29年,主要是应对“常征”难以恢复的困境。“抵征”在乡村的复杂实践中,亩董成为乡里税书与州县户房书吏的中间人,绅局(乡柜) 才是基层田赋征收的关键场所。2本文所讨论的祁门、黟县等地在太平天国之前的粮局和乡柜,只是限于一村一族的范围,或扩大到一图,都是在“常征”脉络中产生的,亦即从图甲结构演化出来的。太平天国战后由士绅掌控的粮局,征粮范围更为广大,但应借助了此前的粮局、乡柜的运作经验和名称,反映了民间自我管理钱粮汇集、代缴机构的普遍性。
晚清时期的田赋改革,仍是将法外惯例中“合理”部分制度化、合法化,难以触及摊派 - 承包模式,地方上的层层代理人,几乎没有收到太大的触动。太平天国战争虽对徽州社会形成了巨大冲击,但也没有在社会秩序恢复时形成新的机制。尽管士绅势力(绅董、亩董)被赋予了合法化的代理征缴钱粮之资格,但只是在官方赋税册籍一度缺失情况下填补空白,并非长久之计。而他们仍沿用旧体制中产生的机构和代理人、运作方式,也没有推动新机制的产生。基层社会的赋税运作中,册书仍处于核心位置,家族势力仍有相当的控制权。
[责任编辑:吴才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