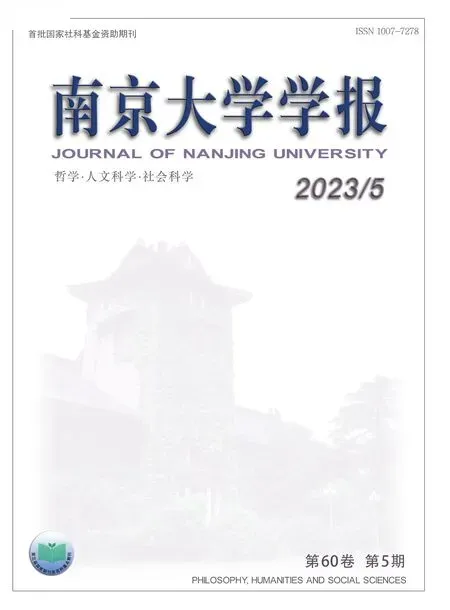顾宪成的《大学》诠释与晚明的“朱、王之争”
李敬峰
钱穆曾指出,“明清之际,学者流风余韵,犹往往沿东林”(1)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9页。,道出晚明东林学派在明清之际学风递变中的主导地位。东林学派的学术旨趣便是积极介入是时的全国性学术论题“朱、王之争”,开辟出颇具特色的“由王返朱”的方案,为朱子学在清初的复兴发出先声。而顾宪成作为东林学派的导源者,其在缔造东林学旨、回应“朱、王之争”以及影响后世学者方面,所具的典范意义不容小觑。然以往囿于史料散乱,学界关于顾宪成的研究成果少有将其经典诠释与学术思潮绾合起来进行研究的(2)顾宪成全集的搜集和整理工作已由王学伟负责完成,并于2022年10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这弥补了以往学界在此方面的缺憾,为顾宪成的研究提供了全面、扎实的文献史料。而目力所及,通过检索知网、台湾学术文献数据库等可知,目前学界尚无关于顾宪成经典诠释的研究。,这不仅不符合顾宪成依经立言的学术取向,也无益于整全地构建明清之际“朱、王之争”的学术图景。顾宪成曾敏锐地指出:“诸贤具体孔子,即所诣不无精粗浅深,而绝无异同之迹。至朱、王二子,始见异同,遂于儒门开两大局,成一重大公案,故不得不拈出也。”(3)顾宪成著、王学伟编校:《顾宪成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第1339页。也就是说顾宪成亦是在朱子学与阳明学构成的两极学术框架内思索和回应“朱、王之争”,尤其是借助于《大学》来完成这一学术诉求。朱子、阳明皆是通过采纳不同的《大学》文本,重构《大学》义理来建构哲学体系,黄宗羲对此有敏锐的观察,他说:“其(王阳明)与朱子抵牾处,总在《大学》一书。”(4)黄宗羲:《明儒学案(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7页。仰赖于朱、王二人在学术史上的肯綮地位,这一方法遂成为大多数学者介入“朱、王之争”的共法。顾宪成显然也共享了这一理论途辙,他倾力撰写《大学通考》《大学重定》《大学质言》《大学意》和《大学说》,来积极参与和回应“朱、王之争”,成为晚明学术史上为数不多的《大学》经解之作内容丰富、体例多样的学者。故而从顾宪成的《大学》经解之作切入来透视其对晚明“朱、王之争”的回应,不仅可以具体而微地反映顾宪成的学术旨趣,更为重要的是有助于完善明清之际“朱、王之争”的学术谱系,进一步展现经典诠释与学术思潮之间生成与互动的关系。
一、突破朱、王:重订《大学》文本
朱子、阳明首先从《大学》版本入手构筑理论体系,致使后世学者竞相效仿,纷纷参与到《大学》改本当中,以致明代成为《大学》改本史上改本数量最多的一代。(5)明儒刘斯原的《大学古今本通考》共收录38家,其中明代有25家之多,占绝大多数。而再综合顾宪成的《大学通考》,明代的《大学》改本则有共计有36家,这还不包括顾宪成之后的明代学者的改本。总体而论,明代的《大学》改本至少在40家以上。顾宪成在究心《大学》之始,就致意于《大学》版本,倾力撰写《大学通考》,以三卷的篇幅,罗列学术史上有代表性的《大学》改本如二程、朱子、石经本等共计29家,通过类聚的方式来备列诸家《大学》版本之异同,以学界少有的形式积极介入晚明愈演愈烈的《大学》文本竞争。他详细交代他作此书的缘由:
《大学》有戴本,有石经本,有二程本,有朱子本。近世阳明王氏独推戴本,天下翕然从之;而南海曙台唐氏又断以石经本为定;至如董、蔡诸氏,亦各有论著,莫能齐也。虽然,以求是也,非以求胜也。其同也,非以为徇也;其异也,非以为竞也。其得也,非以为在己,而故扬之也;其失也,非以为在人,而故抑之也。君子于是焉虚心平气,要其至当而已。予故备而录之,俾览者得详焉。(6)顾宪成著、王学伟编校:《顾宪成全集》,第1760-1761页。
在顾宪成看来,《大学》版本数量庞多,参差不齐,那么如何来面对这些版本呢,他主张应该秉持“求是”而非“求胜”的心态,虚心平气,以求获得公允至当的《大学》文本。这就为其厘定“顾氏《大学》改本”奠定丰富的文献基础,使其能够吸收众家之长来成就其传世名作《大学重定》。而他撰写是书所运用的方法是:“因取《戴记》以下诸本,暨董、蔡诸家之说,互相参校,沈潜反复,绎异同,如是者久之,……窃不自揆,僭加铨次,私以讲于同志。而今而后,庶几《大学》获为全书,而纷纷之论可息矣。”(7)顾宪成著、王学伟编校:《顾宪成全集》,第1756-1757页。很明显,顾宪成是综合、参校以往诸家之本,比较异同,去粗取精,才最终厘定出他理想中的《大学》文本,即《大学重定》。他对是书充满自信,认为此书一出,可以消弭以往的文本纷争,成为《大学》的终极定本。当然,在中晚明《大学》文本竞争白热化的背景下,在朱子学、阳明学权威日益弱化的情形下,顾氏此举并非孤例,有相当多的学者皆对自己的改本抱以终极定本的期许,冀此来独掌《大学》的话语权,从而根除“朱、王之争”。
顾宪成更定《大学》版本,他既不赞同朱子的改本《大学》,也不主张阳明所主的古本《大学》,他认为“朱子之说,既臆决而无凭;阳明之说,又笼统而无辨”(8)顾宪成著、王学伟编校:《顾宪成全集》,第634页。,意思是朱子的改本多是臆测,缺乏坚实的证据,而阳明推尊古本,理由又太笼统,没有进行详细的辨析。因此学术史上最具代表性的这两家版本皆不可取,不足信。而在他重订的《大学》版本中,则将《大学》分为八章,这在《大学》分章史上并不多见,因为学界主要有六章、七章、八章、十章、十一章、十三章等分法,且尤以六章之分最为常见。顾宪成的八章之分主要是:第一章为“大学之道”至“国治而后天下平”;第二章为“《康诰》曰”至“皆自明也”;第三章为“汤之《盘铭》曰”至“此以没世不忘也”;第四章为“物有本末”至“大畏民志,此谓知本”;第五章为“所谓诚其意”至“故君子必诚其意”;第六章为“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第七章为“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第八章为“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从顾宪成的《大学》分章来看,他的主要特色在于:(1)以古本《大学》为据,重新调整经文顺序。(2)拆分和移动《大学》首章。将古本《大学》首章中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一段挪至第三章,添加入“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一段之后,将“物有本末”至“则近道矣”以及“自天子以至于庶人”至“此谓知至也”,再加上“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共计三段合并为第四章。(3)改动和调整古本《大学》中的“诚意章”。顾宪成沿袭朱子的做法,将古本“诚意章”中的“康诰曰”一段作为第二章,但在第三章上,他将“汤之《盘铭》曰”一段作为开头,紧接着是首章当中的“知止而后有定”一段,尔后是《诗》云“穆穆文王”一段,再后是《诗》云“瞻彼淇澳”一段。从顾宪成的调整来看,在朱、王所主的文本之间,他完全是以古本《大学》为蓝本,只是在第二章上完全采纳朱子的做法。他详细交代自己如此改动的理由在于:
《大学》原不分经传,然说个“明明德”,便有“克明德”几条;说个“新民”,便有“日新”几条;说个“止至善”,便有“惟民所止”几条。又如“诚意”而下,皆以“所谓”二字发端,明有正文、释文之别。正文似经,释文似传。正文揭“明明德、亲民、止至善”为纲,列“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目,次第昭然,即释文次第可知。(9)顾宪成著、王学伟编校:《顾宪成全集》,第631页。
不难看出,顾宪成依然是按照经、传对应的原则来调整《大学》的经文,他调整后的第二章、第三章明显是对“三纲领”的解释,而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和第八章则是对“八条目”的解释,与朱子相比,差别在于他既没有像朱子那样给“本末”章安排释文,也没有采纳朱子的格致补传。要之,顾宪成的《大学》改本以古本《大学》为底本,依循朱子的经—传对应结构进行大幅度的调整,奉行的仍然是文本服从义理的原则,也就是以义理来调动文本,而不是相反。
从后来的学术史发展来看,顾宪成显然对自己的改本过于自信,因为它并没有消解关于《大学》版本的争论。相反,在顾宪成之后,《大学》版本之争依然在激烈地持续着,从后来清代的毛奇龄仍做《大学证文》、详考诸本异同可见一斑。而值得注意的是,顾宪成为了彻底瓦解旷日持久的“朱、王之争”的文本基础,也曾大胆地提出一个设想——“宜以《大学》、《中庸》还归《戴记》”(10)王骘:《顾端文公遗书总序》,顾宪成著、王学伟编校:《顾宪成全集》,第1901页。,也就是说让《大学》重返《礼记》。这一主张虽然不是顾宪成所首先提出(11)早于顾宪成的祝允明曾说:“自宋以来,始有四书之目。本朝因之,非敢妄议。然愚谓《大学》《中庸》终是《礼记》之一篇,《孟子》之言,羽翼孔氏,然终是子部儒家之一编耳。古人多有删驳,国初亦尝欲废罢,故愚以为,宜以《学》《庸》还之《礼》家,《论语》并引《孝经》同升以为一经。”祝允明:《怀星堂集》,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2年,第272页。,但他从理念和方法上为《大学》重返《礼记》起了助推之功,后来的郝敬、王夫之等则付诸行动,在其《礼记》经解中纳入《大学》。至乾隆二十年(1755),御纂的《钦定礼记义疏》正式全文收入古本《大学》,可谓是从官方角度呼应了顾宪成等的主张,一改“朱子有《大学》,五经无《大学》”(12)毛奇龄:《大学证文》,《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10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79页。的学术格局,以此可见顾宪成的先导之功。要而言之,顾宪成的《大学》改本虽然并没有取代朱、王本《大学》而获得独尊地位,也没有像石经本《大学》那样与朱、王本《大学》在晚明构成鼎足之势,但我们应该从这样的角度来肯定顾宪成改本的价值,即为化解“朱、王之争”在文本上开辟了一种新的可能,进一步扩充和丰富《大学》的文本阵营。
二、与《大学》不相似:顾宪成对阳明《大学》诠释的辩难
顾宪成在述及自己的学思历程时说:“宪少不知学,始尝汩没章句,一旦得读阳明之书,踊跃称快,几忘寝食,既而渐有惑志,反复参验,终以不释。”(13)顾宪成著、王学伟编校:《顾宪成全集》,第1078页。不难看出,顾宪成对阳明学经历了从服膺到质疑的转变,而这种质疑在阳明的《大学》诠释上表现得尤为明显。顾宪成围绕阳明诠释《大学》的核心要点展开逐一辩难。
就“三纲领”中“明明德”与“亲民”的关系来讲,顾宪成指出:“《大学》曰‘在明明德,在亲民’,曰‘物有本末’,阳明曰:‘明德必在于亲民,而亲民乃所以明德也。’是亲民为本,明德为末矣。”(14)顾宪成著、王学伟编校:《顾宪成全集》,第632-633页。“三纲领”之间的关系如何界定是阳明相异于朱子的关键之处。阳明将“明德”与“亲民”关系理解为体用的关系,他说:“亲民者,达其天地万物一体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于亲民,而亲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15)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067页。顾宪成则不认可阳明此意,他认为阳明此说要表征的是“亲民”为本,“明德”为末。很显然,顾宪成是借用朱子“明德—亲民”乃本末说的架构来解读阳明的思想,但与朱子不同的是,朱子说的是“明德为本,新民为末”,而顾宪成则将两者颠倒过来,即“亲(新)民为本,明德为末”,以此来解读阳明的表述,这明显与阳明本意不符。因为阳明从根本上就不赞同朱子的“本末”关系说,而是力主“体用”关系论,更何况顾宪成还将“亲民”置于“本”的地位,这与阳明的“亲民”为“用”之意更是相差甚远。
我们再来看他对阳明视域中的“八条目”关系的理解:
《大学》曰:“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阳明曰:“……格物在致知,知致而后物格矣。”然则《大学》之言不几于颠倒乎?《大学》曰:“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阳明曰:“格物者,格其心之不正以归于正也。”是以格物为正心矣。又曰:“意念所在,即欲格其不正以归于正。”是以格物为诚意矣。其语梁日孚曰:“着实致其良知便是诚意。”是以诚意为致知矣。曰:“着实致其良知,而无一毫意必固我,便是正心。”是以正心为致知矣。然则《大学》之言,不几于重复乎?阳明之说《大学》如此,谓之阳明之《大学》可也。(16)顾宪成著、王学伟编校:《顾宪成全集》,第633页。
在这段长文中,顾宪成用“颠倒、重复”四字来形容阳明在诠释“八条目”上的混乱之举。在他看来,《大学》说的是致知在格物,而阳明则说的是格物在致知。《大学》明明将正心与诚意、致知按照先后次序给予区分,而阳明则将“格物”“致知”直接等同于“正心”“诚意”。若依阳明此言,那《大学》根本不必设置那么多的条目,只需要“格物”“致知”两条目即可一网打尽。平实而论,顾宪成所批并非无故,因为阳明确实有消解“八目”次序以及将“八目”归并在“致(良)知”之下的意味,他指出:“盖其功夫条理虽有先后次序之可言,而其体之惟一,实无先后次序之可分。其条理功夫虽无先后次序之可分,而其用之惟精,固有纤毫不可得而缺焉者。”又说:“悟致知焉,尽矣。”(17)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第1071、271页。从顾宪成对阳明关于“八目”间关系之说的批驳来看,很明显是以朱子学的工夫次第说为据来裁断阳明之论,不合阳明本意实属逻辑之必然。
以上是从三纲、八目内在关系的角度来审视顾宪成对阳明《大学》诠释的批驳。下面我们深入具体的条目释读来探查顾宪成的态度。从顾宪成的《大学》注本可见,顾宪成主要是针对阳明对“格物”“致知”的解读展开深度的辨析,这也就与前述他所批阳明的“八条目”要点保持一致。个中原因在于他所指出的:“世之说《大学》者多矣,其指亦无以相远,而独‘格物’一义,几成讼府。”顾宪成首先对阳明所释“格物”的要旨分析道:“阳明之疑补格物传是也。”“朱子揭‘格物’,阳明疑其错看了‘物’字,则驳之曰:‘物内也,非外也。’……大都是有激之言,非究竟义。”不难看出,顾宪成对阳明质疑朱子“格物”补传的合理性表示肯定,因为这恰好与他的主张若合符节,也就是他同样认为朱子作“格物”补传是乱经之举。而对阳明所质疑的朱子错看“格物”之“物”字,也即将“物”理解为外物,顾宪成则认为阳明此说并没有抓住根本,只是有感而发的激情之言。顾宪成不能认同阳明此说,恰恰是因为他认为“物”涵括“上下、前后、左右、本末、内外等”。可见,顾宪成对“物”的理解依循的是朱子之义。至于对“格物”内涵的理解,顾宪成也反对阳明的“为善去恶是格物”,他说:“至以为善去恶言者,侵了诚意、正心、修身。”(18)顾宪成著、王学伟编校:《顾宪成全集》,第627、635、635、819、632页。这就是说,若把“格物”解释为“为善去恶”,就遮蔽或者说侵犯了其他条目如“诚意”“正心”以及“修身”的内涵,造成屋上架屋、床上架床的弊病。当然,顾氏此意仍然是以朱子之意来衡断阳明,并不符合阳明本意。因为在阳明那里,他是以“致良知”来涵摄其他条目,故而在其心学体系内是可实现理论自洽的。
而对于阳明将“致知”诠解为“致良知”,顾宪成指出:“《大学》言格致,文成恐人认‘识’为‘知’,便走入支离去,故就中间点出一‘良’字;孟子言‘良知’,文成恐人将这个‘知’作光景玩弄,便走入玄虚去,故就上面点出一‘致’字,其意最为精密。至于‘如鬼如蜮’,正良知之贼也,奈何归罪于良知? ”不难看出,顾宪成对阳明将“致知”解释为“致良知”是极为赞同的。在他看来,阳明以“良知”解释“知”,可以破除将“知”解释为“认知”所导致的支离之弊。另外,阳明在“良知”前面加“致”字,以强化工夫的取向避免将“良知”之学陷入“玄虚”,故而顾宪成高赞道:“阳明之‘揭良知’,直截痛快,真足以一洗支离胶固之习,当与天下共推之。”顾氏之评并非妄论。在明代中期朱子学流弊日显之时,阳明提揭“良知”来矫正朱子学偏外、支离之弊,确实有拔根祛病之效,为是时多数学人认可和称赞。当然,顾宪成并没有到不加分别、盲目崇拜的境地,他说:“阳明先生开发有余,收束不足,当士人桎梏于训诂词章间,骤而闻良知之说,一时心目俱醒,恍若拨云雾而见白日,岂不大快?然而此窍一凿,混沌几亡,往往凭虚见而弄精魂,任自然而藐兢业,陵夷至今,议论益玄,习尚益下。高之放诞而不经,卑之顽钝而无耻。”(19)顾宪成著、王学伟编校:《顾宪成全集》,第47、383、37页。在顾宪成看来,阳明的“致良知”学说并非完美无缺,在流传过程中,它既有“法弊”,也有“人弊”。“法弊”指的是阳明的“良知”学说缺乏限制性的规定,没有堵住理论上的漏洞。而“人弊”主要说的是阳明后学将阳明的“良知”学说朝向凌虚蹈空一路发展,出现荒诞不经、顽劣无耻的现象。顾氏此说确然不虚。黄宗羲亦有相近的看法:“然‘致良知’一语,发自晚年,未及与学者深究其旨,后来门下各以意见搀和,说玄说妙,几同射覆,非复立言之本意。”(20)黄宗羲:《明儒学案(修订本)》,第178页。要之,从顾宪成对阳明诠释《大学》的辩难中可见,他对阳明既非一味排斥,也非全然推崇,而是采取辩难的态度,当赞则赞,当批则批,虽然所批之处也多是他所理解的“阳明”,更准确地说是因为王门后学的流弊而上溯至阳明,但他是非分明、相对客观的态度在晚明心学风靡之际确是难能可贵的。
三、犹在离合之间:顾宪成对朱子《大学》诠释的评判
朱子注解四书,最为用力的莫过于《大学》,他曾说:“某于《大学》用工甚多,温公作《通鉴》,言:‘臣平生精力,尽在此书。’某于《大学》亦然。”(21)黎靖德:《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58页。顾宪成对朱子诠释《大学》的整体评价是:“程、朱,命世大儒。其论《大学》也,犹然在离合之间,不足以尽厌于天下后世。”(22)顾宪成著、王学伟编校:《顾宪成全集》,第630页。这就是说,即使旷世大儒程朱注解的《大学》也并非完全贴合《大学》本义,依然无法止息后世的争论。顾氏此语实际上是朱子学权威动摇的一种反映。下面我们就围绕朱子诠释《大学》的核心内容,来一窥顾宪成对朱子诠释《大学》的立场与态度。
朱子是将“格物致知”视为《大学》的第一义工夫,与之相应,“格物致知”就成为理解朱子《大学》诠释的要津所在。顾宪成认同朱子此说,提出:“‘格致’乃《大学》入门第一义。”(23)顾宪成著、王学伟编校:《顾宪成全集》,第634页。正是由于“格致”在朱子哲学体系中的肯綮地位,故而它也成为八条目中辐辏纷争最多的条目,这可从刘宗周的“格物之说,古今聚讼有七十二家”(24)刘宗周著、吴光主编:《刘宗周全集》第2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618页。得到直接的印证。而其所涉争议主要有三:一是“格物”的传文;二是“格物”的释义;三是“格物”的地位问题。首先,就第一个争议来说,朱子依照经、传对应和以传释经的原则,将《大学》划分为一经十传,并对缺少传文的“格致”进行补阙,是传虽然在学术史上毁誉参半,但从理学的视角而言,它“适应于进一步阐发理学方法论与修养论的需要”(25)陈来:《朱子哲学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83页。。而顾宪成则反对朱子的格致补传,他说“朱子之更定戴本是也,其补格物传,吾不敢知也”,而他反对的理由,我们可从其对李材之论的评判中得见一二,他说:“作《大学》者,自诚意而下,支分缕析,各为之传,何独于格致寥寥乎?若曰:‘除却家国、天下、身心,无别有物;除却诚、正、修、齐、治、平,无别有知,悬空传格致不得。’则除却诚意、正心、修身,亦无别有明明德也;除却齐家、治国、平天下,亦无别有亲民也,又何以各为之传乎?”(26)顾宪成著、王学伟编校:《顾宪成全集》,第635、634页。这段引文中的“若曰”一段便是出自李材之手。(27)李材、邹元标:《李材四书学著作四种、南皋邹先生语义合编》,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21年,第8页。李材的意思是“格致”原本在初创者那就不曾为之作传,何谈缺传之论。因为它就在除格物致知之外的“六条目”当中。换而言之,“六条目”就是对“格致”的解释。顾宪成显然不能认同李材此意,他认为若依李材之说,那么《大学》中的条目就不需要各自有传,这就有悖于经、传相对应的治经原则。可见,顾宪成是反对以李材为代表的将“六条目”作为“格致”释文的。那么,“格致”的释文到底何谓呢?顾宪成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他通过调整《大学》经文来重订“格致”释文如下:“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虽然在顾宪成以前,已经有学者如蔡清、丰坊等将“物有本末”一节四句作为“格致”的释文,但与他们相比,顾氏的释文则要丰富和复杂得多。他详细交代以此为释文的理由是:“‘物有本’一节,全为揭起一‘本’字,知得这本真切,然后事事物物一线贯到底,更无两个格物者。格透此本,每有个至善所在也,如舜只载克谐,徽典叙揆,工虞教养,各得其理,真是善格物。”(28)顾宪成著、王学伟编校:《顾宪成全集》,第637、818页。这就是说,“物有本末”一节的题眼在“本”字,而这恰恰与顾宪成将“格物”理解为“格本末”是若合符节的。可见,在“格致”的传文上,顾宪成并没有依循朱子之论,而是另起炉灶,重定新说。当然,顾氏这一“格本末”也遭到高攀龙的批评:“而谓格物只格本末,又令格物致知之工无下手。假令一无知识之人,不使读书讲论,如朱子四格法,而专令格本末,其有入乎?”(29)高攀龙:《高子遗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第291页。高攀龙反对的理由在于“格本末”没有指明切实的入手工夫,属于笼统之言。高氏之论却也击中顾氏要害,毕竟顾宪成是受过阳明学洗礼的,受阳明学圆融之影响亦在所难免。
对于“格物”的内涵问题,朱子将其解释为穷尽事物之理,且“物”的范围涵摄内外,内至一念之微,外至一草一木,皆在所格、所穷之列。(30)彭国翔教授概括陈来先生的观点:“朱子的‘格物’虽然也包括对内心念虑的省察,但穷格心之念虑在朱子的‘格物’说中并不占主要的地位。并且,朱子的‘格物’说恰恰是作为以反观内省解释‘格物’的对立主张而提出的。”彭国翔:《良知学的展开:王龙溪与中晚明的阳明学(增订版)》,北京:三联书店,2015年,第423页。顾宪成对朱子的解释回应道:
朱子之释“格物”,特未必是《大学》本旨耳,其义却甚精。语“物”,则本诸“帝降之衷,民秉之彝”,夫子之所谓“性与天道”,子思之所谓“天命”,孟子之所谓“仁义”,程子之所谓“天然自有之中”,张子之所谓“万物之一原”。语“格”,则备举程子九条之说,会而通之,至于吕、谢诸家之说,亦一一为之折衷焉。总而约之,以四言曰:“或考之事为之著,或察之念虑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讲论之际。”盖谓内外精粗,无非是物,不容妄。有拣择于其间,又谓人之入门,各各不同,须如此方收得尽耳。故惟大圣大贤,不得拘以是法,其次未有不由之而入者也。议者独执“一草一木,亦不可不理会”两言,病其支离。窃恐以语末流之弊,诚然有之;以语朱子,过矣。(31)顾宪成著、王学伟编校:《顾宪成全集》,第94-95页。
在这段长文中,顾宪成不仅对朱子的“格物”之义进行疏解,也回应了学界对朱子“格物”说的误解。在他看来,朱子解释“格物”,绝非妄测之语,分开来看,释“格”主要是融会、折中二程洛学一系诸家之论;释“物”,则有孔孟、程颐以及张载等先贤为其背书。虽然如此,朱子之义亦绝非“格物”的本义,只不过是义理精熟而已。可见,顾宪成只是从立言甚妙的角度肯定朱子之说,但从抉发“格物”本义的角度,他则并不取朱子之说。因为他认为“格物”就是“格本末”,他说:“石经本于致知格物之下,随系以‘物有本末’一条,即‘格物’二字意义了然,省却多少闲议论。”(32)顾宪成著、王学伟编校:《顾宪成全集》,第631页。
辐辏在“格物”上的最后一个争议就是“格物”在《大学》中的地位问题,也是最能反映朱子学与阳明学相异取向的一个维度。朱子将“格物”视为《大学》的首出工夫,而阳明则将“诚意”作为《大学》的第一义工夫,以此来纠补朱子“格物”论偏外遗内之弊,使“格物”在“诚意”的范导之下展开。顾宪成在诠释《大学》时,亦不惜笔墨,对此焦点问题做出如下回应:“《大学》原自先‘格致’而后‘诚意’,蔡希渊以为朱子新本,何也?且《大学》自‘平天下’推到‘格物’,则‘格物’正下手处也;又自‘格物’推到‘天下平’,则物格正得手处也。即此便是头脑,便是下落,若曰《大学》提个‘诚意’来说,是学问的大头脑。又曰以诚意去格物,工夫始有下落,则何为不先诚意而后格致乎?”(33)顾宪成著、王学伟编校:《顾宪成全集》,第633-634页。这段话的意思很清楚,那就是顾宪成认可朱子的主张,而反对阳明的观点。他的理由是依照《大学》本有的工夫次序,应该就是朱子所言的先格物后诚意,而阳明则将诚意拔擢至首要位置,建构出先诚意后格物的工夫次序,这就与《大学》的本义不符。实际上,早在顾宪成之前,与阳明多次辩论的罗钦顺就曾以同样的理由批评过阳明,他说:“审如是言,则《大学》当云‘格物在致知’,不当云‘致知在格物’;当云‘知至而后物格’,不当云‘物格而后知至’矣。”(34)罗钦顺:《困知记》,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13页。由此可见,顾氏借此批评朱子并非孤例,也反映出阳明提揭“诚意”确实有违《大学》本义。这一点,陈来先生亦极有洞见地指出:“从经典学的立场来看,阳明哲学终究还是有一些内在的难题没有解决。”(35)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9页。要而言之,从顾宪成对朱子诠释《大学》最为核心范畴的回应来看,他对朱子学的态度与对阳明学一样,皆是奉行当是则是、当否则否,但肯定之处则要远多于批评。
四、援朱救王、单向纠偏:顾宪成解决朱、王之争的方案及其意义
“朱、王之争”是中晚明全国性的学术议题,吸引众多学者介入其中,提出纷纭迥异的解决方案,既有如陈确的“既异程朱,亦背陆王”,亦有李材的“超越朱、王,回归孔曾”等路径。顾宪成的方案则是对朱子学与阳明学进行双谴双取,但更偏重于朱子学。原因在于他没有简单地在朱子学与阳明学两者之间进行选边站队,而是对两者的得失有着清晰的认识和定位:“以考亭为宗,其弊也拘;以姚江为宗,其弊也荡。拘者有所不为,荡者无所不为。拘者,人情所厌,顺而决之为易;荡者,人情所便,逆而挽之为难。”在顾宪成看来,无论是宗本朱子,还是推崇阳明,皆有不同程度的弊端。顾氏此论很明显是不持门户之见的,这也是其一贯的反对门户之争理念的具体展现。进一步,他认为朱子学与阳明学是“委有不同处。要其至于道则均焉”(36)顾宪成著、王学伟编校:《顾宪成全集》,第37-38、96页。的,也就是殊途同归的关系。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顾宪成是对两者各打五十大板的中间立场,理念与行动之间的差异相当明显。我们知道,顾宪成早年先师张淇,后又师阳明第二代弟子薛应旂,若从学术师承上来讲,顾宪成理应属于阳明的第三代弟子,这也就是钱穆所说的“东林学脉本自阳明来”以及“东林之渊源于王学”(37)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15、19-20页。。但这一学术背景并没有让顾宪成有“学一先生之言,则暖暖姝姝而私自说也”(38)郭庆藩:《庄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863页。的狭隘之见。相反,他对阳明心学则是肯定与批评并举,但批评的成分要远远多于肯定。在其文集中,多有“阳明颖悟绝人,本领最高,及其论学,率多杜撰”“自信太过,主张太勇”之类的评语,他甚至认为阳明之造诣“逊元公(周敦颐)也”,而“晦庵之功不在元公下”(39)顾宪成著、王学伟编校:《顾宪成全集》,第1077、1077、37、8页。。我们从前述他对阳明《大学》诠释的评价可见一斑。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晚明王学流弊丛生,出现“猖狂者参之以情识,而一是皆良;超洁者荡之以玄虚,而夷良于贼”(40)刘宗周著、吴光主编:《刘宗周全集》第3册,第248页。的情形,前者指的是阳明后学中的王艮一系的现成良知派,后者指的是王畿一系的先天良知派。身处此境,以道自担的顾宪成并没有盲目地排斥阳明学,他首先对其积极性的一面也给予客观的肯定,他说:“当士人桎梏于训诂辞章间,骤而闻良知之说,一时心目俱醒,恍若拨云雾而见白日,岂不大快?”(41)顾宪成著、王学伟编校:《顾宪成全集》,第37页。尔后他对阳明学的猖狂与虚玄之弊展开矫正与救赎。他开出的良方就是援用朱子学的笃实工夫来矫正阳明后学舍弃工夫而悬空追求良知本体的弊端。换而言之,他择取的是由工夫以复本体的进路,很明显是朱子学的理论底色。这一取向落实在《大学》诠释上更加清晰显豁。
当然,援用朱子学并不意味着对朱子学的全面肯定,他认为朱子学同样有其流弊,且这种流弊应由朱子以及后学共同负责。就朱子来说,顾宪成在《大学》诠释中,经常以“臆决而无凭”来评析朱子之过。而就朱子后学来说,顾宪成则指出:“不善用者,流而拘矣。”关于如何解决朱子学的流弊,顾宪成说:“朱子揭‘格物’,不善用者,流而拘矣,阳明以‘良知’破之,所以虚其实也;阳明揭‘致知’,不善用者,流而荡矣,见罗以‘修身’收之,所以实其虚也。皆大有功于世教。然而三言原并列于《大学》一篇之中也。是故以之相发明,则可;以之相弁髦,则不可;以之相补救,则可;以之相排摈,则不可。”(42)顾宪成著、王学伟编校:《顾宪成全集》,第150页。在这段引文中,顾宪成主张朱子、阳明与李材三者之学是相互发明和补救的关系,而非相互排斥和敌对的关系。但如何补救,尤其是阳明学如何来补救朱子学,顾宪成并未像用朱子学的笃实工夫来救正阳明学的玄虚那样提出翔实的方案。细究其因,这一方面当与晚明王学所向披靡,且流弊甚嚣尘上息息相关,另一方面亦与顾宪成个人的学术取向,也即深受其师薛应旂折衷朱王但偏向朱子学的学术旨趣之影响密不可分。(43)冈田武彦:《王阳明与明末儒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56页。可见,顾宪成还没有像高攀龙那样主张用朱子学与阳明学来相互救济,呈现所谓的互补其失,双向纠偏。他更多的是单向地用朱子学来补正阳明学,以此来解决和消弭“朱、王之争”。故而黄宗羲的“东林之学,泾阳导其源,景逸始入细”(44)黄宗羲:《明儒学案(修订本)》,第1450页。不无道理。这就透露出在顾宪成的视野中,“朱、王之争”的引发更多应该由阳明学来负责。
要而言之,顾宪成将解决“朱、王之争”的诉求着落在惩治王学流弊上,具体进路则是以朱救王。这一方案在晚明解决“朱、王之争”的思潮中,仰赖于顾宪成在晚明学术史上的“转移一世之学风”的地位,具有重要的典范意义:一是复振朱子学,为朱子学在清初重获官学地位发出先声。顾宪成在晚明阳明学日炽、朱子学式微的境遇下,不随波逐流,逆时代思潮而动,虽表面上是对朱子学与阳明学双谴双取,但实质上是在抬升朱子学的地位,将其与阳明学拉平对待。这一动向很快为后继者高攀龙等所洞察,接续其旨,继续推动“由王返朱”思潮的兴盛;至清初在统治者与理学名臣的合力推动下,朱子学一改晚明的颓势,再度称雄朝野,顾氏的导源之功实不容掩。二是以朱子学纠偏阳明学,范导晚明王学的走向。顾宪成对王学末流之弊有着深刻的体察,即“凭虚见而弄精魂,任自然而藐兢业”(45)顾宪成著、王学伟编校:《顾宪成全集》,第37页。。而矫正此弊,唯有对症下药,用朱子学的后天笃实工夫来填补阳明学之阙。这一摈弃门户之见的路径深刻影响高攀龙、刘宗周、黄宗羲等人的学术选择,为他们所承继和发挥,推动晚明王学由凌虚蹈空向笃实敦行一路转进,为“新王学”的建构奠定理论基础。总之,顾宪成会通中晚明学界由《大学》而入回应“朱、王之争”的学术路径,开显出“援朱救王”的方案来解决“朱、王之争”,展示出经典诠释与学术思潮乃至学风递变之间的互动关系,为我们贴切把握晚明学术思潮提供具体而生动的个案。
——一种可能的阐发途径